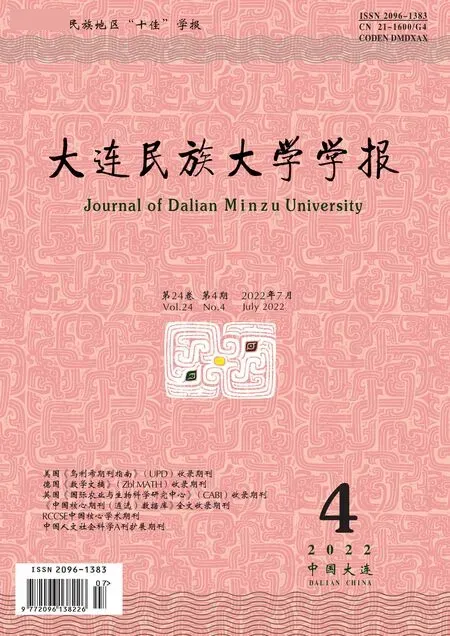论王吉鹏的学者散文
2023-01-03李晓峰
李晓峰
(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5)
一、学者散文的流脉与王吉鹏的散文创作
1990年代以后,以余秋雨、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周国平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之所以引起强烈且持久的反响,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极为特殊的创作思潮,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文革”造成的文化劫难、社会劫难、历史倒退被推进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背景之中,“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得到庚续。二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浪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使拯救与重建中国文化并通过“两创”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应对策略。因此,学者散文创作思潮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化思潮,也是一种社会思潮。三是全社会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崇拜,折射出对知识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四是“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众已经认同的既有经济体制、社会资源分配方式、资本运行模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改变形成了社会性的茫然、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或凭借自己的学识阅历、社会责任担当和对历史现实的独到思考,纵古论今、反思批判,或在传统文化的碎片中发掘人类思想的折光和民族精神生命基因,探寻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在全球化浪潮挑战中拟构新文化体系、价值观念和应对策略,形成了学者散文的“宏大叙事”和以“社会史”“文明史”“思想史”为视角的思想启蒙新的主体模式。而在记人述学、人生体验和生活阅历类的散文中,学者们也将个体人生经验与学术思想融合,形成哲学化了的“人生思考”的启蒙模式。于是,学者散文对中国历史文化、现实人生、生命价值的反思、批判、确认、重构的启蒙话语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承担了“疗救”的功能。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全球化浪潮冲击和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水区的语境中的特定文化现象。
新时代以来,学者散文发生了许多变异。首先,从文学生产和传播的角度,学者散文借助互联网的升级迅速进入到自媒体时代。其次,学者散文亦随着“学者”队伍的几何级增加,“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我“精英形象”袪魅,学者散文在保持作者的身份标识、专业背景和视域开阔、思想敏锐、学理气质、思辨品格的同时,将启蒙的本能冲动和社会功能,隐遁于张中行式的“负暄琐话”和季羡林在治学、生命、生活的平凡世界中个体人生的生命旅迹、日常生活、知识生产中的个体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文学书写。在学者散文新的转向中,王吉鹏的学者散文便是代表性的个案。
作为国内知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吉鹏先后出版《〈野草〉论稿》《鲁迅思想作品论稿》《鲁迅作品新论》《鲁迅世界性的探寻——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鲁迅民族性的定位——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中学语文中的鲁迅》《穿越伟大灵魂的隧道——鲁迅〈野草〉〈朝花夕拾〉研究史》《驰骋伟大艺术的天地——鲁迅小说研究史》《注目伟大存在的时空——鲁迅杂文、诗歌研究史》《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追踪伟大人生的轨迹——鲁迅生平研究史》《观照伟大精神的经纬——鲁迅思想研究史》《鲁迅的智慧》《鲁迅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等著作。
王吉鹏是一个走进鲁迅世界的“鲁迅化”的学者,同时也是“鲁迅化”的散文作家。
王吉鹏读高中学时的作文就被老师评语“有散文味”,他的创作始于1960年代,以散文和诗歌为主,尤以散文见长。纵观其创作,读大学时写下了《鹤埨行》《航船》《石级》,属于青春试笔;《第一课》《歌声》《林海短笛》,属于创作初期;新时期初研究生期间的《萧军访问记》《北京女师大旧址访问记》《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等,就已呈现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学者散文趋向。1980年代的《梦见亡母》《风帆》《倒影》等,标志诗体散文创作的成功尝试。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王吉鹏的鲁迅研究渐入佳境,散文和诗歌创作数量不多,但散文题材和气韵开始向学者散文和鲁迅散文靠拢。近十多年来,王吉鹏的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特别是他近年来的散文,既有清晰的“鲁迅学”的专业和知识背景,又有学者散文的思想深度、知识视野和学理思辨色彩,他循着鲁迅的血脉遁入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处,将鲁迅思想与生命精华注入自己的灵魂,在鲁迅研究专家,同时也是鲁迅毕生追求却又终生遗憾的理想的“人国”的双重身份认同下,写下了许多被思想照亮和温暖同时也照亮和温暖了读者的“朝花夕拾”和“野草”式的100多篇散文。这些散文或抒情、或叙事,或抽象、或写实,或高亢、或低吟,或热烈、或冷峻,或反讽、或自嘲的多样书写中,用个体生命历程体验自然景观、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观察人心、人品、人性和世道、世情、世风,表达喜与悲、歌与哭、恩与怨、乐与忧、情与思、顾与盼、窘与顺、明与暗、醒与醉、进与退等丰富的人生情感和思想,在作者笔下,故园沉浮、水乡风物、古都风雨、北国风光、异域风情,名人旧址、历史文物等人文与自然遗产,既彰显天地造化,又隐含对历史人文演变洞悉和沉思,在自我审视中、在对师友亲人温暖深情和家园祖国赤子之恋和殷切瞩望的诉说中,不仅有徐徐吹来“鲁迅风”,也有自己对历史、社会、人生、文化的独特思考,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王吉鹏学者散文的鲜明特色和思想价值。
二、王吉鹏散文内容的维度
在王吉鹏的散文中,“朝花夕拾”类的“回忆散文”有家族史、个人成长史和旅居见闻录三个部分。在“家族史”和“个人成长史”中,作者把家族兴衰与个人成长投放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折光和伟大时代风云变幻的侧影。其中,有《朝花夕拾》一样的“回忆的记事”对家族史的追忆、自己人生履迹的寻踪和对亲人、朋友、师长的感念,也有“朝花夕拾”式的格调、情怀与细致体验和感悟。特别是在4篇“故园亲人”、9篇“童年记忆”和12篇“负笈金陵”中,更是弥漫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父亲的病》的气息。
在学界,作为启蒙主义者的“勇士”“战士”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成为公共知识和人们熟知的“中国魂”的“大鲁迅”形象。而男人、儿子、丈夫和靠预支稿费、讲课费养家,对母亲、对妻子、对师友、对故人一往深情的“小鲁迅”则为人所忽视,而这恰恰是“活的鲁迅”明证。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鲁迅听柔石讲与母亲别离时深情地写道:我知道这失明母亲的眷眷的情,柔石的拳拳的心。对这“情”与“心”的体察,需要同样的“情”与“心”,这不是鲁迅的悲悯,而是鲁迅对“母爱”与“爱母”这两种人类最深挚情感的双重体认。这种眷眷的情、拳拳的心、深深的爱在王吉鹏9篇“故园亲人”系列散文中得到延续。在取自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句“梦里依稀慈母泪”为题的散文中,王吉鹏写“性格很内向”“很少哭,总是把泪水噙在眼眶里,然后呑进肚子里”(1)王吉鹏散文作品,均引自《家乡的水牛——王吉鹏诗文选》,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版。的母亲。写自己幼时黄豆塞进鼻孔面色发紫浑身抽搐时,无助的母亲“紧紧抱着我一夜,不说一句话,也不淌一滴泪,呆呆地看着我,好像决不让阎王派来的牛首马面抢走似的”;写自己临行前母亲特意做的“阿梗汤”“出门在外,有个好‘遇头’,遇上好人贵人,帮助你”;写临别时母亲“却转过身去,不看我们”……。王吉鹏没有象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时那样,对母亲进行抽象化、道德化和价值观普世化的评价,也没有母亲如何“深刻”影响了我的抽象总结和阐释。然而,在王吉鹏“把泪水噙在眼眶里”的平静叙述中,一个普通、内敛、坚韧、温婉、慈爱的母亲形象却生动地伫立在人们面前。
真正和谐的母子之情,一定是母爱与爱母同时在场相互依存和水乳交融的。前者深刻地影响着后者的人生,而后者则以自己奋然前行和柔石般“拳拳的心”,表达自己生命中母爱的永远在场和母爱的深刻。鲁迅对柔石母子之爱的描述,就是这种深刻,这种深刻也深深地植入王吉鹏的散文。如果说,母亲给王吉鹏的最大的影响是母亲的坚韧、平静、温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锻造了王吉鹏坚强的性格、乐观的态度、严谨的精神与温和善良、达观人生态度。而爱母的“柔石的拳拳的心”则体现在对王吉鹏对母爱的深刻感受和领悟,体现在对母亲早逝无奈的感叹和深深的怀念,体现在母亲在梦中再现和自己与母亲在梦中相见。可以说,在王吉鹏的散文中,母爱与爱母之情,正如鲁迅所期望的那样,以其相濡以沫的情感互动而感人至深。
如果说“情”是王吉鹏回忆类散文之灵,那么“理”则是王吉鹏述学游历类散文之魂。
王吉鹏鲁迅研究的启蒙老师是屈正平先生。屈正平把鲁迅的学术火种播撒在塞外草原,因拓展鲁迅学术版图而享誉鲁迅研究界。在4篇《致敬导师》中,王吉鹏把屈正平的人品、学品以及人生之坎坷,意志之坚强,思想之高远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细节展示出来。例如,在推选全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时,屈正平说“还是首先考虑蒙古族学者的好”。在屈正平倡导下成立内蒙古鲁迅研究会确定会长人选时,屈正平还是说“让蒙古族学者当吧”。这其中蕴含着屈正平推动鲁迅跨民族、跨文化研究,扶掖后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学者)的精神,这种精神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对萧红、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一大批青年人的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鲁迅对“前进”的青年寄予了厚望,正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对中国青年期望一样。屈正平继承的正是这种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同样为王吉鹏所继承。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研究鲁迅者众,而走进鲁迅精神世界者少,承继了鲁迅精神之华者则少之又少。可以说,鲁迅精神已经深深融入王吉鹏的精神血脉。在《我在仙台:探访青年鲁迅的踪迹》中,凝望着藤野先生的画像和藤野先生曾经站过的讲台和播放屠杀中国人的幻灯片的屏幕时,王吉鹏不禁扼腕叹息:“一幅好端端的放医学教学片的屏幕,其教学之旨归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却插进了炫耀侵略掠夺战争的时政片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杀所谓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围观杀头的中国人一派麻木看客相,教室里的日本学生一片欢呼,而且教室里又仅鲁迅一个中国人。试想想,多么深刻的刺激啊!”正是这样的“在场性”体验,使王吉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民族魂”从这里起歩,“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从这里出征!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这里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之海外圣地。”在这里,王吉鹏从鲁迅思想精神的当代意义出发,回溯了鲁迅思想的嬗变历程,并将鲁迅/藤野、中国/日本、历史/未来纳入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空之中,提醒世人要关注这一历史遗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伟大的国际意义”。于是,仙台“鲁迅之旅”中“多少历史的现实文化沉思和感叹”使他的散文不自觉地回归到“学者散文”共有的思想维度。而作为鲁迅研究者的学者身份,又使其散文思想始终围绕着鲁迅精神与现代中国这一中枢展开。在《富士山下》中,王吉鹏从三岛由纪夫一生的遭遇和命运结局,由衷地感叹“他的作品以生之欲求心死之向往,以真善美和假恶丑,以优雅与酷烈,以青春与老朽,从梦幻希冀与残忍破灭,以均衡和谐和扭曲撕裂,带给人们无比的心灵震撼和情感激荡,他演绎了许多相对相悖的概念与范畴,表现了男性阳刚之美的奇异色彩。”在这些滚烫的文字中,王吉鹏有鲁迅般热烈的情怀,也有鲁迅般的清醒、冷峻和鲜明的毫不动摇的知识分子立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的《野草》不仅是诗体散文的高峰,也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鲁迅认为《野草》包含了自己一生的哲学。故而,《野草》也成为鲁迅思想研究的焦点。无独有偶,王吉鹏散文创作的半壁江山正是被很多人称为“散文诗”的诗体散文。这些诗体散文虽然没有《野草》那样隐晦抽象,时而锋芒毕露、时而幽深莫测,时而冰寒透骨、时而热烈如焰,却也如鲁迅般将自己一生的“哲学”以“思想的碎片”的方式散落在一个个充满哲思的篇章之中。
《冬夜五梦》中的“梦”中,“我总回不到梦里去,好惆怅”,“她没有见到我竖起的拇指,真遗憾”,“我后悔我的入世太深,不懂得知趣”,“我恐惧,不小心就会有魔鬼来袭”各有其对人心与世态、真面与假相的隐喻和指涉。《过桥之所遇》“梦见自己和同伴过一座桥”被嵌在桥顶栏杆上的刀片划得汩汩而出的鲜血。《难忘那个小女孩》中,“我”提醒追逐鲜花的小女孩前面有垃圾坑。小女孩始于“不满、埋怨、气愤,竟至于流出眼泪”,直到看到前面的垃圾坑后,方“回报一个微笑”,但“泪珠还挂在她的眼角”。此时的“我”犹如《野草》中的隐含作者一样,用冷峻的目光洞悉了“松软的草地、污秽的陷坑、美好的追求、彩色的诱惑、提醒和怨艾……这就是这个小孩子的世界,并且是她的一生。”而多少人正在鲜花的诱惑下掉入“污秽的陷坑”?更何况这“泪珠”的源泉是对提醒者的怨怒。这种洞悉有鲁迅“有一伟大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祥,遍身有大光辉,然后我知道他是魔鬼”般无与伦比的深刻,尽管这种深刻并不为多数人所认同,因为多数人活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在鲁迅,这种知识体系锻铸了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正如《语丝再三根》中乌鸦所言“你们呀。被它们喜鹊欺骗,冤枉我们乌鸦。几千年了,从精英到平民,从武士到文人,从老人到小孩,从……”。
读这些散文,恍如进入鲁迅《野草》的世界。而如果将这些《野草》般“思想的碎片”用“思想考古”的方法拚接起来,便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一个思想者的孤独——他洞悉了人间的一切并努力用自己的思想照亮暗夜,对人性/自我,人类/人生,现实/未来进行全面介入和精细剖析并呈给世人。当然,从鲁迅式的启蒙中走出来的王吉鹏不可能再重复鲁迅。对王吉鹏而言,你可以是喜鹊,也可以是乌鸦。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在意你的身份,就象当年的鲁迅,他始终把自己置于知识分子甚至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地位,那是鲁迅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王吉鹏的此类散文,仍然是“自己”一生的哲学。
三、王吉鹏散文艺术的特征
“无法之法”的艺术境界、“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和诗体散文的诗学追求,是王吉鹏散文艺术的三个特征。
首先,任何文类都是有文体技巧的,而文体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所谓无法之法方为上法。散文之谓散文,在文体特征上概因其“散”且为“文”。散文的最高境界是“散”到极致,那种漫无边际的思想、思绪、情绪、情感由自由洒脱的字、词、句来表达,后者在书面文学或文章学的语境中,是为“文”。
在“回忆散文”中,王吉鹏把散文之“散”尽情发挥。他不讲“凤头、猪肚、豹尾”,也不讲“开宗明义”“卒章显志”之类的模式。散文本与诗一样,是生命之文体,而生命最重要的表征就是新陈代谢、自我调节和自我增殖系统的持续性和连续性。这一特征,在王吉鹏“回忆性散文”中表现极为充分。
其次,王吉鹏在其“朝花夕拾”类的回忆散文中,运用了“非虚构”的写作方法,所有深深铭刻在作者记忆中的故乡、故园、故人、故事在黎明的晨光中,在正午的艳阳里,在晚霞的余辉中,在静夜的梦境里纷至沓来,于是,他忠实于自己的生命记忆和思维的自然之轨,将之一一用最素朴、最真率的文字记录下来,形成王吉鹏式的“记忆”式“非虚构”写作范式。例如《故园亲人》9篇散文之后,都用“补记”或“再补记”首次的“非虚构”“记忆”进行补充。这种“记忆”式“非虚构”写作有三个特点和文体价值:一是作者保持了始初的“非虚构”的创作语境,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书写现场用文本自身进行了真实呈现;二是提供了书写者的记忆轨迹思维的自然形态,呈现了作者对这种轨迹和形态的有意识地捕捉与记录的真实文体语境,这种相当于“心动记录仪”的功能营造的真实语境远远超出了当下虚构的“非虚构写作”的艺术效果。三是“补记”和“再补记”还保存了人类思维和口头传统的叙述特征,具有重要的心理学和民俗学的价值。这些特征在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往往被视为重要和难得的研究“史料”。
再次,在诗体散文创作中,王吉鹏对散文的诗性追求,一方面体现为灵魂、思想、意识、情感的起伏、动荡、变幻以及节奏感和韵律感多频共振所达到的艺术境界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没有过度追求鲁迅《野草》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意蕴的隐晦性、抽象性。但象征、隐喻、转喻等诗学修辞的驾轻就熟,“梦”“乌鸦”“喜鹊”“池水”“鸟儿”“冰雪”等意象群的建构,“小女孩”“冬夜五梦”“静秋”中的诗性叙事中逻辑思维和哲学意蕴之中的整体思想观念,以“思想的碎片”的星丛的形态,达到对历史、社会、人生、人性的整体性的个体思考的特定维度和深度。
需要指出的,在中国诗体散文史上,被称为散文诗的《野草》一问世便达到了长时期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以至于出现“《野草》传统中断”的焦虑性仰视。例如,有人感叹并追问道:“《野草》一出场就是巅峰这种现象该如何解读?它似乎意味着,至少在散文诗领域,中国文学是在往下走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推断,假如后世的写作者永远难以绕过(且不说超过)《野草》,那至少从‘文学史’角度,《野草》之后仍有散文诗,便是多余的。这又显然是一个令人在理智上难以接受的判断。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代际间的审美无须一决高低,但何以《野草》高于一切当代散文诗的判断依然会让人觉得‘一定如此’呢?这背后的文化机制是什么?在我看来,重识散文诗的《野草》传统,不仅意味着要说出作为散文诗的《野草》是什么,有什么,还应追问《野草》被绝对典律化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以及当代的散文诗写作该对这种历史逻辑做出何种反应。”其实,这种焦虑和追问一是焦点过于聚焦于“散文”与“诗”的媾和,而未将其回归于诗体散文聚焦其诗学品格;二是未谙《野草》之为“野草”的魂魄——边缘的、存在的、个体的然而却是穿透历史的鲁迅式的“一生的哲学”。如果说诗体散文的诗学品格是“灵”,《野草》恰恰获得了诗体散文的诗性思维、诗性语言、诗性修辞的诗学之灵,从而使诗体散文极高的诗学规范的“灵”与“一生的哲学”之“魂”达到了妙合无垠的境界。
然而,对于鲁迅研究专家且有《〈野草〉论稿》等一大批鲁迅研究成果问世的王吉鹏则不然,他走进了鲁迅的世界,鲁迅也活在王吉鹏的世界。他不但承继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也承继了鲁迅诗体散文的精髓。虽然他的诗体散文没有超越《野草》(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但却承继了《野草》的灵魂,正如在《达子香,开放在北国的春天的山野》中结尾处王吉鹏对鲁迅名言“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的引用所折射出来鲜明的传承轨迹一样,王吉鹏的诗体散文具有与其他人的诗体散文完全不一样的气度,被称为“一股‘鲁迅风’徐徐吹来”,也就不难理解。
如此说来,在散文艺术上,一方面,王吉鹏的散文在追求散文“无法之法”的境界时,也形成了自己“记忆”的“非虚构”的文体特征;另一方面,在《野草》灵魂的指引下的诗体散文创作,不仅具有《野草》的诗学气质,而且作为王吉鹏的“一生的哲学”,散发着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光芒——在我看来,这一点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