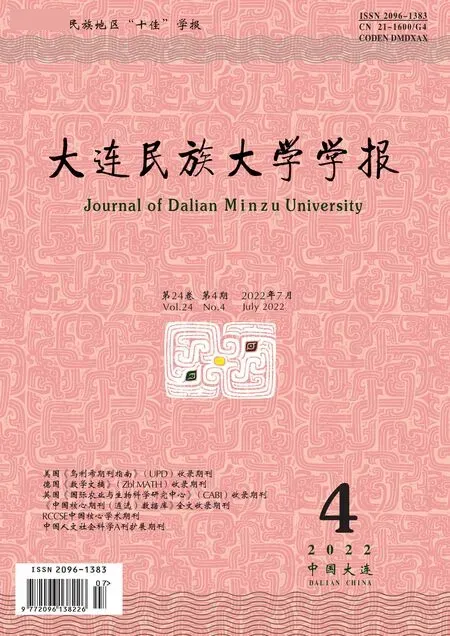论学者型编辑的学术精神
——以周振甫先生编读《管锥编》为例
2023-01-03慈明亮
慈明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00720)
“学者型编辑”这一名称的出现,或许是为了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编辑”或 “万金油型编辑”:文字编辑往往奉《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为圭臬,以“咬文嚼字”为己任,务求文字表达上正确无误;“万金油编辑”则什么稿子都编,各类知识都有所闻而不求精通,一些常识性错误是躲不过他们的眼睛。应该说,这两类编辑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出版事业默默做出贡献。而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并向深博精微处发展,对于学术性要求较高的专著,单纯的“文字编辑”或“万金油型编辑”往往难以胜任,他们往往缺少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学术操练,无法与作者共同走完学术专著诞生的最后阶段。如果说学术著作是学者经过漫长时间孕育而成的话,那么编书的过程就像是分娩生产,需要专业的助产士一起完成,从而生产出完美的“宁馨儿”。这才会有对“学者型编辑”的迫切呼唤。
单纯从名称上看,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了解其学术生产的规程,发表过相关论文,似乎都可以称为“学者”,又经过了文字方面的编辑培训,这样的“学者+编辑”,仿佛就成了“学者型编辑”。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除了必要的学术能力和编辑业务技能外,还需要学术精神——在坚守实事求是的学术底线上,通过发现著作中的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实现精益求精。泛谈总觉浅,实践出真知,本文以学者型编辑的代表人物周振甫先生编《管锥编》为例详细讨论。通过他在编书过程中如何把握著作、协商作者、解决著作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将著作尽可能完美地呈现给读者,来切实感受这份学术精神。本来编辑做的是幕后工作,无法直接呈现于著作之中,而中华书局公开了周振甫先生为钱锺书先生编辑《管锥编》时的意见及钱先生的批复,通过这一珍贵材料,能够一窥该书在编辑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加上周振甫先生发表了一些编辑心得与书评、解读文章,很多涉及《管锥编》,使我们能够较为准确把握他的“学术精神”的内涵。
一、学术追求
学术是对存在及其规律的准确把握,学术精神则是在学术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意识。在不同类型的学者身上,能够看到对学术精神不同层面的理解。作为一名有深厚学养的编辑,周振甫常说自己不过是在编辑工作中“实事求是”而已。这里的“实事求是”对于他来说有“还原事实”和“寻求背后规律”两层意思,而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他还原“事实”这一层。比如他在为臧克家《毛主席诗词讲解》加注时,指出“把酒酎淘淘”的“酎”字应为“一尊还酹江月”的“酹”字;他又指出“原驰腊象”的“腊”字应为“蜡”,以与“山舞银蛇”的“银”相对,后经过臧克家先生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改为“蜡”字。他这种求实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的,甚至还曾为自己解释错《小石潭记》中“拳”字而特地向读者郑重道歉。
但周振甫的学术理念中“事实”与“求是”是并重的,而他特别敬佩既能够揭示事实真相又锲而不舍去发现事物背后规律(“是”)的钱锺书。《求是的诗话》[1]203-204,是他对钱锺书考察毛奇龄批评“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札记,强调了钱锺书还原“实事”后能“求”“是”的精神。在他的指点下,可以清晰把握钱锺书行文的思路。还原事实上有两层意思,一是袁枚以讹传讹地错引毛奇龄的话,“定该鸭先知,鹅不知耶”的话其实不是毛奇龄的原话,二是毛奇龄没有注意到东坡诗歌题目是《惠崇春江晚景》,是根据画来题诗的,画中有鸭,没有道理写鹅或别的水中之物,所以钱锺书说“西河未顾坡诗题目,遂有此灭裂之谈”。这些是不能还原事实所导致的。二是从艺术规律看,毛奇龄也不能品鉴出这首诗的好处。钱锺书认为见鸭而写“水暖”,是诗人能够设身处地的体会(mimpathy),即实推虚,将春光水暖下鸭子写活了,“赞美春光的好处,这是画面上画不出来的”。而毛奇龄因其固执己见而将其贬低。在这两层意思之外,周振甫先生特别注重钱锺书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求”的精神:“钱锺书的谈诗是实事求是的。他看了袁枚的话并不罢手,还要找毛奇龄的话来看;看了毛奇龄的话,还要找苏轼和唐人的原诗来看;还要参考王闿运的意见。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1]203-204正是因为寻找事实背后的规律要更难一些,所以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更值得尊重和推广。因而,周振甫先生更看重钱锺书为寻求最合理的解释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是反复用“看了……还要”这种句式来强调这点的;文中还有“讲到这里,问题已经清楚了。钱锺书还不罢手……”这种“求”是的劲头到了穷追不舍的程度。周振甫对钱锺书对事实原委及其背后规律穷追不舍的精神深有感悟,其实能折射出他自己尊重事实原貌以及锲而不舍追求艺术规律的学术精神。
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学术精神的根本,也是钱锺书和周振甫两人学术切磋的基础。自从40年代周振甫为钱锺书《谈艺录》校对而两人订交以来,常有学术上的交流。周振甫敢提问题且能提出好问题的。1975年《管锥编》刚写成之际,钱锺书先把书稿给周振甫看,请他提意见。在《管锥编》的序言中,特别指出“命笔之时,数请益与周君振甫”。周先生当时也很纳闷,因为通常的“私下讨论”或同行评议,多是请教老师或同辈学力相当的,他自认为学识不高,而钱先生竟然会找到他:“钱先生的巨著,有好多种外文,钱先生知道我不懂外文。又看过我的书,知道我的中文也比较浅,为什么把这部巨著交给我看呢?钱先生在文学研究所,所里不是有不少专家吗?为什么不请他们看呢?猜想起来,大概因为所里的老专家,有的还没有解放,不便请他们看;有的可能斗过钱先生夫妇,有的反对谈艺术,所以不愿请他们看,因为我的《诗词例话》是谈艺术的,又引了钱先生著作中谈艺术部分,所以给我看吧。”[1]5当时“反对谈艺术”是指仅从“政治思想”谈文艺,反对谈审美及艺术形式,而周振甫有很大影响的普及读物《诗词例话》,主要是谈艺术鉴赏与创作,与《谈艺录》相映成趣,两人在谈艺上有默契。周先生说自己“中文比较浅”,自然有谦虚的成分,但不能不承认在两人学识、学力上的确存在差距;而钱锺书信任地将书稿交他提意见,应该是看重他在学问上能够质疑求真的精神。
对于钱锺书请他提意见,他是以学者的献疑精神认真对待的:“我是读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出原书来看,有了疑问,就把一些意见记下来。我把稿子还给钱先生时,他看到我提的疑问中有的还有一些道理,便一点也不肯放过,引进自己的大著中。”[1]11周振甫按“事实”原则,先找原书来看是否有违原意,又看著述内部是否逻辑一致。他提出的疑问,有些可能是自己理解不当,也有可能是钱锺书的表达不够周密、清晰。钱锺书也高度评价他这种怀疑精神,1975年作《振甫追和秋怀韵再叠酬之》时有:“迎刃析疑如破竹,擘流辨似欲分风。贫粮惠我荒年谷,利器推君善事工。”实事求是而能疑善析,周振甫来做同行评议是够格的。(1)周振甫先生能够形成自己的“查原著、找疑点、提意见”的学术路数,也因为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学术修养,要知道1947年他做《谈艺录》的校对时“震惊于钱锺书的博雅,提不出一个意见”。
钱锺书在“求是”上还有更高追求,而周振甫也能助其一臂之力。钱锺书在《谈艺录》修订时谈到这部多年前之作“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持之有故”是论述的证据充分,“言之成理”是说法有内在的一致性,优秀学者能够做到这两点已经很难得了。钱锺书在此之上仍追求论证的周全、通透,那种理论的“穿透力”——“澈”,这是极难达到的境地,纷繁复杂的世相在他的批评观照下变得清澈透明。毕竟个人的思维在论证时难免拘于一端,通透、周全其实很难达到;而如果有人讨论,不同思想之间交锋,取长补短,反而容易“周全”。比如《管锥编》有论“赞荔枝”,周振甫建议补入魏源的《诮荔枝》,钱锺书回复:“甚妙。已增‘周君振甫曰……’,请正之。”[1]60《诮荔枝》是钱锺书所遗漏的“补天遗石”,经周振甫一提,钱锺书马上记起,因为增补于原文贴合无间,所以他感叹“甚妙”。又如周振甫先生审读《管锥编》时,认为一处有歧视妇女的问题未加纠正:“富辰若曰:‘妇女之性,感恩不到底……’下接‘盖恩德易忘……’似可作‘然恩德易忘……男女同之,不当以苛责妇女’等语如何?”[1]40对比周振甫的改语与钱锺书的断语,会发现钱锺书忽略了挑出富辰若对妇女之根性的偏见(2)钱先生曾被朋友笑为“誉妻癖”,自然不是会歧视女性之人。,而周振甫特别纠正这种女性偏见,强调这只是“忘恩”或是人性缺陷而非妇人的劣根性,就周全多了。难怪钱锺书会大呼:“吾师乎!吾师乎!此吾之所以‘尊周’而‘台甫’也!”[1]242“尊周”是“老吾谈艺欲尊周”,此处怕要加上尊重“周”君的“周”全之思。
从周振甫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上,我们看到了学者型编辑对学术不懈追求的精神,无论是还原事实、寻找背后的规律,还是不断质疑、不断完善,“求”字是最为看重的。
二、学术眼光
1977年,《管锥编》在中华书局选题立项,周振甫先生承担起《管锥编》的编辑工作。在1977年10月所写的《〈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中,他谈道:“钱锺书愿意把这部书稿交我局出版。因为我看过部分书稿,希望由我来做编辑工作。”他点出这部书稿的特点是:“通过古今中外名著比较研究,很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1]40这一判断——在全面比较前人基础上提出自己过人的新见,后来为大家广泛接受,比如钱宁《曲高自有知音——访周振甫先生》里,钱宁对《管锥编》的认定便与周振甫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管锥编》)全书引用了古今中外近四千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钱锺书往往曲终而雅奏,在最后寥寥不足百字的评述中,提出超越前人的灼见。”[1]29-30周振甫更是借钱锺书在《管锥编》说西方哲学家治学的话来定位这部著作:“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1]11作为第一读者和钱锺书的知音,周振甫在书稿总体把握上是了然于心的。
在《审读报告》中,周振甫谈到了《管锥编》特别的著述体例,“本稿是读书札记,这样的札记以前国内没有见过,因为它包括古今中外”,“他就每部书中提出各个问题来讲,讲的时候往往用古代名著来比较;有时引用外国的名著或文艺论来作比较阐发。”[1]115读书札记往往是有感而发的,《管锥编》中只针对某一点进行全面阐释,在阐明问题时又遍引古今中外的文献,这种对古代文献中生发出来的问题“小而全面”的阐述方式,的确以前国内没有见过,不但与当时的理论架构不同,也与《谈艺录》只限于谈艺术理论与批评不同。《管锥编》采用读书札记的形式也与钱锺书的学术积累方式有关,周振甫说到自己未读到《管锥编》书稿以前,“我有问题去请教钱先生,他有时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来让我看,上面就可以找到解答问题的记述”[1]30-31。对于《管锥编》这种谈问题的策略及其效果,后来钱锺书以“打通”来概括,周振甫对此还专门撰文进行笺注。
在《审读报告》里,周振甫举例谈了《管锥编》所能达到的精深之处,展现了钱锺书先生在分析题上“实事求是”精神,同时不忘点出黑格尔对中国不知情却昧于“事实”的问题。下面周振甫概括出钱锺书论证上的特点,中外例子被归纳、分析、综合,故而能道前人之未见。
就文字训诂说,《周易》一《论易之三名》,引了“易”的一字三义,比照“诗”的一字三义、“伦”的一字四义、“机”的一字三义、黑格尔的“奥伏赫变”一字有正反两义,从而概括出“并行分训”与“背出分训”。背出分训指一字有相反的二义,“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指一字在句中同时具有正反两义。经过这样概括,提出了新的概念,这在以前讲训诂文字的书里似乎还没有见过。尤其是“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看到人们没有看到处。在这里批评了黑格尔贬低中国语文的妄论,为中国语文张目[1]11。
钱锺书能够将学问做细到极致,就是他能够在众多同类材料中归纳出最根本的正反两面,并辩证考察,提出新见。周振甫谈钱锺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归纳、分析、概括后提出新概念,发前人之未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二是通过找到相反两面又加以综合,考察得极其周全,“看到了人们没有看到处”。推其原因,古人对字有多义未必不知,钱锺书却用黑格尔解释“奥伏赫变”一词来反观古人,故而有古人不能之新解;而他又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推演,能看到他人未见之处。或者可以说,古人缺乏钱锺书这种严谨的逻辑思辨能力,所见难免失之于宽泛;而现代学者有这份逻辑思维能力,却又缺乏材料例子的积累,以见识受限而无法精进,这或许是钱锺书的见解难以超越的原因。而周振甫对其深有领会并能呈现其好处,可见学术眼光,对于钱先生的论证脉络是有清晰把握的。
对于传统的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纸质作业,多数学生缺乏足够的重视,把教师布置的考核当作强加的任务,被动接受。做作业时动笔不动心,经常是抄一遍教科书上的相关知识点,导致其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和运用收效甚微。对于综合性或应用型的题目,不能够通过主动查找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且由于每个同学的作业内容相同,有些同学对待作业,直接拿别人的答案抄袭[5],蒙骗教师,使得考核既不利于学生成绩与能力提高,又不利于教师因材施教,还助长了部分学生投机取巧的心理。
正是周振甫对《管锥编》从宏观和微观上准确的把握,为后面编审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学术尺度
学术著作不如文艺作品那样对风格化有强烈要求,更多是强调规范性,但作者特有的行文方式以及对某些问题独特理解,构成了作者论述修辞的一部分,也许要编辑做好把握,一方面不失规范要求,另一方面尽可能照顾作者自身的诉求。如何在已有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灵活机动,可以用钱锺书的妙语“富有弹性的坚定”(elastic or flexible rigidity)来概括。坚定来自对“实事求是”以及其他价值规范的坚持,弹性则来自对作者的表述的通融,甚至是对作者学术品格的信任,这是很可值得借鉴的。从《管锥编》的意见往来上,能够特别清晰地看到周振甫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照顾钱锺书的表述风格。
一些文字、标点上的规范性体例要求,周先生对这些要求持一种既坚定有又灵活的态度。比如周先生指出“《论语》、《子罕》不作《论语·子罕》,当有意如此标法,拟即照排。”[1]31(3)此处“不作”当为“应作”。明白了这种体例规范后,钱先生问:“‘《诗》、《小雅》、《桑卮》’改为《诗·小雅·桑卮》,是否?”周先生一方面说明体例,另一方面也照顾到钱先生表达的特殊性。比如有一处,按照中文的标点法,冒号后句子里用句号,但钱锺书用逗号。周先生询问“当有意如此点法,拟即照排”。钱先生解释说:“此乃西文标点习惯,似较合理,因此处语气一贯为一单位观念。乞再酌定。”[1]35-36而正式出版时,是按照钱先生的标点用的。规范不是死的,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处理。钱先生也深知学术规范对于理解作品的重要性,所以非常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权”。比如文中一处“扬雄”,钱先生做“杨雄”,周先生仍然“是有意如此写,当照排”。钱先生说明自己的依据是段玉裁“其谓雄姓从手者伪说也”,“故拙稿作‘杨’,但此等处不必立异”,所以“从通用”改。[1]36使用“扬雄”或“杨雄”对文意无影响,但如果改用习见的“扬”而用“杨”,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所以此处钱先生同意按通常用法来。
有时候,一些问题需要两人反复协商才得到稳妥的处理,对原则问题周振甫是有坚持立场的。比如周振甫对《管锥编》有这段意见:“‘《说文》称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西“羌”从“羊”;异域之人既等畜兽虫豸,则异域之言亦如禽兽昆虫之鸣叫。’此数语牵涉少数民族,是否可去……又《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很明显,古人对少数民族有地域偏见,而《管锥编》在引述时未加纠正,周振甫对此较为谨慎,从稳妥的角度建议删去。钱锺书回复是:“是极,已增改。请酌。”他增改为“汉人妄自尊大,视异域之民有若畜兽虫豸”,这样既实事求是地引述古人偏颇的话,又对其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批判。这样改后,周振甫仍坚持认为“‘羌’从‘羊’”要删,因为《说文》里并不视羌人为“羊”而是牧羊人,如果保留就是对古人的话没有按“事实”原貌来。钱锺书回复:“敬如教。倒却四平架子,无可奈何!”[1]36钱锺书删掉了“羌从羊”,还删去了东南西北四字,又原本四边缺了一边,就像四平架子缺了条腿不稳当了,但在学术严谨性上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让步。
但有时候,周先生在谈到“怪力乱神”时似乎过于敏感,钱先生也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想办法说服他,而周振甫也最终顶住了压力支持他。比如周振甫说:“‘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云云,是否同于佛法之神通,应否点明其虚妄。”钱锺书回复说:“似可不必,如谈孙行者之神通,不必斤斤随其后而斥为妄说。公以为然否?”[1]70周振甫对书稿中讲到《搜神记》各篇时说:“本篇所引各事,作者皆明有鬼,结处要不要点一下,明有鬼之妄。”钱锺书大概会笑对他的实心直口:“此卷考‘鬼火’、‘鬼死’、‘鬼索命’等不一而足,而亦屡出以嘲讽,似不必于此地特标‘不怕鬼的故事’。何如?”《不怕鬼的故事》是1961年文学所编的集子,旨在借破迷信。但后来的各种斗争,也会让周振甫以谨慎稳妥为安,时时不忘加点保险的话,钱锺书认为不必将这些谈鬼趣事搞得太无趣。周振甫作为《管锥编》的责任编辑,在当时的语境中所出版的书里面不加辨析地“讲鬼故事”,无疑要承担较大的责任和压力。1994年,《管锥编》(5卷本)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周先生说书的价值获得了全面肯定,他也借机为其中的讲鬼故事平反:“钱先生谈《太平广记》中的鬼神,是在评论这些鬼神故事,是在探索人们对这些鬼神故事的感受,是在研究人们的精神状态,所以是属于学术巨著,不同于讲鬼神故事了。”[1]47
1979年《管锥编》出版,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由沉寂走向复苏的重要时刻,读者在书中读到钱锺书的高妙论述,一洗耳目,其实这里面不知包含了周振甫先生为把好关而付出的努力呀。
四、学术交流中的“叩”与“鸣”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读后感到“于”字的问题还没解决。“于”承上文的“于”字作解,植在汶篁,不可通。检《词诠》,作“以”字解,始通。对“于”字作何解,是否要说明一下?
【钱批】遵尊意补“周君振甫曰”一节,稍加申说。杨书未睹;“于”可以训“以”早见高邮王氏书中,以《老子》“以战则胜”而《韩非子》作“于战则胜”为例。句法与此不近,故另举《墨子》一例,不识杨书有之否?请裁定之。
周振甫认为书稿里未将“植于汶篁”的“于”字解释清楚,如果承前面两个“于”字解释为“在”字,就说不通,而杨树达先生的《词诠》对于此句中“于”字做“以”解,把汶篁(汶上之竹)种植到蓟丘,就比较通顺。因此 ,他希望钱锺书对此做一说明。钱锺书认可他的意见,考虑到简单将此处的“于”训为“以”,说服力不足够(5)陈寅恪先生在《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中对此句有过讨论,可参看Q。,因为句法不相近,所以提出用《墨子》中的例子。在《管锥编》中他这样写道:
周君振甫曰:“不必矫揉牵强,说为倒装。末‘于’与前两‘于’异,即‘以’也,谓:‘蓟丘之植,植以汶篁’”;是也。其句法犹《墨子·三辩》……此语煞尾,遂变而首言燕(“蓟丘”)而次言齐(“汶篁”),错综流动……所谓“丫叉法”(chiasmus)也[3]857-858。
可以看到,钱锺书并不是简单地引述周振甫的意见,自己用“是也”加以认可;而是用了“矫揉牵强”这样富有情感色彩的表达,引发读者的趣味,只要不会有人妄猜他讥讽俞樾先生就好(6)俞樾先生在《古书疑义举例·倒句例》中提出:“此亦倒句,若顺言之,当云‘汶篁之植,植于蓟丘’耳。”。增加了周振甫的解释,解决了局部的问题,而对于为什么出现句法错综的问题,钱锺书又以“丫叉句法”结构性的解释,整个问题才算完全解决。
钱锺书非常重视周振甫的合理意见,在钱先生的回复中,常能见到这样的话:“甚妙。已增‘周君振甫曰……’,请正之。”“甚精细,已采入增一节:周君振甫曰‘洪虞’云云,请审之。”“甚缜密,即照抄加一注,并冠以大名:‘周君振甫尝足其辞曰……”这种注明“周君振甫曰(谓)”的例子,在《管锥编》全书中有十三处之多。
实际上,钱先生吸纳的意见远不止于此。周振甫有些意见不很确切,不便以“周君振甫曰”的面目出现,却能促使钱锺书作出修改,让自己的表述得更为清晰。比如对于杜牧《阿房宫赋》“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理解,周振甫认为这是杜牧写阿房宫之大,“譬诸称中国之大,同一天内,广州则春光融融,而东北则风雨凄凄”,钱锺书认为“若曰‘一时’,则尊意确矣,可以‘广州’、‘东北’为比;若 ‘一日’则如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非同时而为消息作止也。”如果杜牧写“同时”,那么周振甫就理解对了, 而“一日”就写此消彼长。钱锺书也说:“公言甚辨,亦由拙稿言之未晰。兹补数句,请酌。”[1]11在书中,钱锺书简单反驳了同时而异地的说法并清晰表达自己的解释:“如‘东边日出西边雨’也,得乎?‘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热闹、冷静不齐,犹俗语‘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言同地同日,忽喧忽寂耳。”[3]1076本来对于言简而词意含混的古文细读就可能产生多种解释,把握也只在某个词的辨析。《管锥编》能够做到“以锥刺地”式精准,也离不开周振甫这种不同的解读。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序》里特别致谢周振甫先生:“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钱锺书把自己的某些论述称为“小叩”,而称周振甫的回应为“大鸣”。周振甫担心这是钱锺书的“夸饰”之词,客气话,请求“酌改”,因为自己“不敢当”。 而钱锺书再三申明 “不可改也”[1]402,看重的是两人纯粹的学问往来,给彼此带来的精神激励。
五、结 语
周振甫先生编辑《管锥编》以及钱锺书的回复,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两位性格有异、知识背景不同、理解能力有别的情况下进行的学术交流。它给人的启迪无疑是丰富而多层面的。本文更多从学者型编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希望从周振甫先生的所思所为中寻求更为一般性的经验,即学者型编辑应具有的学术精神。
对学术所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包含了对著作进行合理的质疑以及探求真相的努力,以及为了准确、周全、透彻的表达而协助作者进行修改,都是希望借学术带给读者以丰富的、实在的生命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