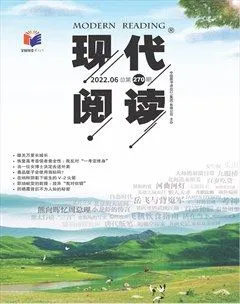皇帝与医生的“攻防游戏”
2022-12-29谌旭彬杨津涛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记载了一段“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这个故事演变成一条成语,叫“讳疾忌医”。清代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也发生过“讳疾忌医”的故事。
杜钟骏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候补知县,号称擅长医道,故被人举荐入宫给光绪皇帝看病。他后来留下了一篇回忆文字《德宗请脉记》,里面说,自己在诊病之前,已深知慈禧和光绪的忌讳:“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按中国传统医学的说法,一个人“肝郁”,往往是因为他的心情长期不愉快;能让光绪皇帝不愉快的自然只会是慈禧,而慈禧绝不愿承认自己在迫害光绪。一个人“肾亏”,则往往意味着他不够男性,不够阳刚,有损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当着慈禧的面给光绪诊病时,杜钟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肝郁”与“肾亏”这些名词。
在“给皇帝看病”这件事情上,讳疾忌医其实只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和前程。
杜钟骏入宫去给光绪治病,需要担忧的是自己的前程——之前同治皇帝死的时候,御医李德立等人均被“革职戴罪当差”;之后光绪与慈禧死去,御医张仲元、全顺等人,也都被革了职。
为了趋利避害、规避皇权的惩罚,历代御医们都练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高超本领。
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热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热衷于“从众诊断”,随大流,绝不说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话,绝不发表独到见解,如此就可以处在安全位置。
这些,而非医术,才是御医们必修的核心“职业技能”。
皇帝当然也不傻。为了反制御医们的这种手段,晚清的紫禁城发明了一种“轮诊制度”,简单说来就是以若干天数(比如5天或者10天)为一个周期,每天让一名医生前来诊病,让他单独写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药方,不许医生们彼此交流。最后由皇帝和大臣们来判断谁的诊断和药方是可信的。杜钟骏虽然不是御医,但他既是入宫看病,于是也被安排与其他被举荐的医生一起参加“轮诊”。这个外来人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对内务府大臣说:“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
我们6个外来的医生,每人负责一天,轮流给皇上看病,单独诊断单独开药,不许交流。这种办法,怎么可能把病治好呢?
大概是懒得跟这些“民间名医”解释,解释起来也麻烦,内务府的回复很简单——“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皇宫的制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你的这种意见,我不敢去说。
内务府的解释很粗糙,但杜钟骏们大约也能明白,这种“轮诊制度”的存在,乃是皇权为防被医生联合蒙蔽而专门设置;其结果往往是:诊断的虽是同一个病人,但有多少医生就会出现多少病名和药方,亦即众说纷纭、千人千方,继而使参与诊断的医生们陷入被动。所以,为求自保,杜钟骏从宫里出来,又去找了工部尚书陆润庠,对他说:“6天才允许我进宫开一个药方,还不许我们这群医生互相交流,哪有这种治病的方法?我们这些人,从民间来到皇宫,本来想着治好了皇上的病,能够博取到名声与富贵。如今看起来,肯定是徒劳无功。如果将来治不好皇上的病,究竟是谁的过错?还要请陆尚书你出来说句公道话。”
陆润庠的回复,与内务府如出一辙——“你不要想太多,宫里的事一向就是这样的,你的这些意见,我也不方便去说。”
杜钟骏对“轮诊制度”的批评,其实也并非毫无道理。就常理而言,让医生每天诊视患者、让医生们互相交流意见,才是更好的办法。而且,“轮诊制度”走到最后,相当于将判断药方好坏的决定权交给了皇帝、太后及大臣等非专业人士。
比如,号称“名医”的马文植,光绪六年(1880)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他开的药方就是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然后由大太监李莲英传旨给众大臣,说太后觉得马文植拟的药方也不错,要他们商议一下,究竟是继续服用太医院之前的药方呢,还是改服马文植开的新药方。大臣们自然是绝不肯表达任何有倾向的意见,他们集体回奏说“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我们啥也不懂,还是请太后老佛爷您自己来决定吃哪种药吧。慈禧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圣裁,她很“机智”地将太医院和马文植融为了一体——“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用太医院的药方,但得让马文植来主笔。
这种对御医的不信任,和御医对专业决策权的甘愿让渡,发展到极致,往往就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种事情。慈禧曾将名医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续断”擅自改为“当归”。光绪经常改动医生开的药方,比如擅自往里面加入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药方里的杜仲和菟丝子,有时候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教他们怎么玩“君臣相佐”。
然而,若让皇帝撤去“轮诊制度”,听任医生们互相交流,其结果又大概率会变成一场糊弄。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里,就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一场这样的糊弄。
杜钟骏说,他们6位民间医生被举荐进京一段时间之后,光绪皇帝有一次下旨,让6人合作拟出一个“可以常服之方”,且给他们5天商议交流的时间。6人接旨后,推举了其中年龄最大的陈秉钧做主笔。陈秉钧拟出的药方“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会凸显出御医们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众人都不赞成。杜钟骏还对其他5个人说: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能治好皇上的病,那就不妨批评太医们的药方;否则的话,还是不要说的好,会得罪人。然后,众人按照杜钟骏的主意,保留了陈秉钧的药方的头尾,将中间部分给改了,使人看不出是在“明言”太医们之前的药方有问题。而杜钟骏自己拟的药方,根本就没有拿出来给众人讨论。
对参与药方商议的杜钟骏来说,不得罪御医(以免遭报复)、不用自己的药方为底稿讨论(日后如果出了问题,自己不会成为主要责任人),比御医们的药方是否正确、自己的药方是否更好,要重要得多。
如此这般,皇帝与他的医生们就陷入一种漫长的死循环中。皇帝无法信任医生,医生也不敢给皇帝提供关于疾病的独立见解。双方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医患关系,而更像是在玩一种两败俱伤的攻防游戏。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