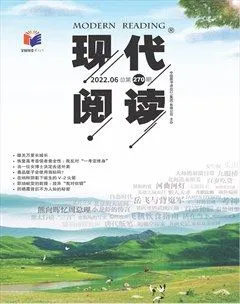自恋在阻止我们恋爱?
2022-12-29[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为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想活在当下、只想关注自我?
明明周围如此喧嚣热闹,为什么现代人普遍觉得空虚、孤独?
译/倪复生
信息革命时代,我们还同时经历了一场“内部革命”,即对自我完善及认知的史无前例的迷恋——自恋。
杰雷·鲁宾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学生反战活动领袖,当年因化装为半裸野人进行抗议而轰动美国,由此出现了生活放荡不羁、蓄长发、养胡子、男女混居等嬉皮士群落。如今,他在华尔街投资,成为富有阶级。他自称在1971至1975年间,自己一直热衷于完形疗法、生物能、拉尔夫按摩、缓步跑、太极、伊沙兰按摩、催眠术、现代舞、坐禅、锡瓦尔意识控制法、阿里卡疗法、针灸以及雷什疗法等。
在经济增长缓慢之时,精神发展便取而代之,在新闻替代了生产之际,精神消费便成为急需,如瑜伽、心理分析、肢体表达、禅宗、情绪释放疗法、团队发展、超限冥想等。
心理膨胀与经济通货膨胀雷同,而心理的膨胀对于自恋的发展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将各种情感导向“我”,促使“我”成为世界的中心,由此产生一种全新的自恋形式,力求实现自我解放、自立与独立这样的伟大目标。如果放弃爱情,那理由便是“我不需要另外的人,只为多爱我自己,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快乐”,这便是杰雷·鲁宾的新革命设想。
自恋是对无意识所发出的挑战的一种回应,结果便是“我”被责令要找回自己,“我”要投身到一种无止境的解放活动中去,通过各种手段呐喊以及释放被压抑的情感来个性化自己的欲望。性、梦等一些被当成边角料的东西,也都被加以回收利用,所有的糟粕都被纳入主体范畴。由此,无意识开辟出一条通向无限自恋的道路。
享乐主义也在分解着“我”,结果便是勤奋不再时髦,循规蹈矩、纪律严明受到贬损,欲望、及时行乐受到膜拜,一成不变的“我”的身份瓦解了,看别人脸色行事的时代也终结了。人们倒向自恋、倾向自闭,目的在于减少“我”对于他人的依赖,以至于可以说自恋就是个性化进程的代理人。
对肉体这种明显自恋性的关注表现在日常之中,是苦恼于年龄与皱纹,纠缠于健康、“线条”与卫生,热衷于一些检控(体检)和保养,迷恋日光和治疗(过度医疗)等。
不可否认,社会对肉体的反应也经历了变迁。肉体不再是一种下流,也不再是一部机器,它是我们深层次的身份,身体上没有什么地方是令人羞耻的。
在沙滩上或演出中,人们可以裸露身体以尽显其天然本质。
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也来自自恋,而对下一代的漠不关心更强化了对死亡的焦虑。
上了年纪后,生命机能退化也将不再被人看重,让人对即将到来的衰老处境无法容忍。
尼采曾说,人们所抗争的真正意义上的痛苦并非自身的痛苦,而是一种莫名的痛苦。死亡和衰老成为痛苦,而如今的莫名状态则更加深了人们对它们的恐惧。
保持年轻、拒绝衰老甚至成为一道命令,旨在消除年龄引起的不和谐。
鉴于当代人际关系面临的各种不稳定,个体越发企盼实现情感上的游离。人际关系不要太深厚,不要感情脆弱,要发展自己的情感独立性,要独自生活。
害怕失望,害怕感情无法控制,这是自恋的写照。
推崇“冷酷”的性及自由关系,谴责忌妒心及强烈的占有欲。调整对性的看法,将性从所有造成情感紧张的因素中排除,以达到一种冷漠、超脱的状态,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失望的爱情之苦,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那威胁到内心平衡的自身的情感冲动。
性解放、女权主义以及色情都旨在达到同一个目的,即树立壁垒以遏制情感并将自己置身强烈的情感之外。情感的文化、皆大欢喜的结局、曲折波动的情节都不复存在了,一种“冷漠”的文化出现了,其中每个人都要在冷漠的掩护下生活,为的是规避自己的激情以及别人的激情。
“情感”退潮,被性、愉悦、自立及暴力取而代之。多愁善感与死亡有同样的遭遇:连展现自己的激动,热烈表白自己的爱情、哭泣以及过于夸张地表现内心波动如今都变得令人不自在。谈及多愁善感就像谈及死亡一样,让人难以启齿,在涉及情感时一定要镇定自若,也即是审慎。
“情感禁入”是个性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个性化进程要努力根除那些露骨的、仪式性的表现情感的信号。
但另一方面,在这个挤满独立且冷漠的单身人士的苦海里,却到处充斥着交友俱乐部、“小告示”及网络觅友等,所表达出来的是数以亿万计的对于相逢、相识、相爱的期待。然而这些企盼,确切地说,是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在这方面,逢场作戏要比所谓冷漠的游离更实用,男男女女们总渴望一种充满激情的特殊关系,但期望值越高,奇迹般的融合越是罕见,且都越发短暂。
城市里相逢的机会越多,人就越孤独;男女关系越是自由,越是不受传统制约,得到一种激情四射的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少。到处所见的是孤寂、空虚、难以释怀,人们难以跳跃到“自我之外”;要想靠“经验”来提前逃避这种局面,那首先得拥有这种激情的“经验”。为何我不能去爱、不能因激动而战栗呢?自恋的不幸,在于已经规划好要完全沉湎于自己,以避免受“他者”影响、以防范失去自我,但既然对情感关系念念不忘,那就说明该规划是欠周全的吧。
(摘自万卷出版公司《空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