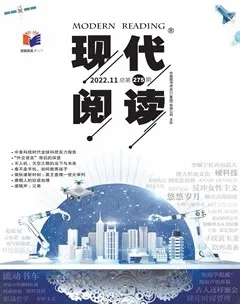新闻自由与名人隐私权——戴安娜死讯引出的话题
2022-12-29贺卫方

据报道,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在她短暂生命结束前最后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曾对一些媒体多有指责。她抨击那些小报热衷挖掘名人隐私,它们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名人的成就,而是他们的错误,并且对于错误抓住不放。之后,戴安娜很快就以她令全世界震惊的死证明了小报记者的残酷和唯利是图。
人们震惊和伤感之余,矛头自然指向了媒体——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媒体指向了媒体。这起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新闻业者的行业伦理和法律责任的思考超越了事件本身,成为一个更具反省意义的话题。
世上没有完美的自由
言论、新闻以及出版自由(这几种自由实际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新闻和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多国宪法加以宣布的法则。对于权利,我们似乎有一种相当固定的看法,即权利表示着一种正当性,流行的说法是某某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既然是神圣的,当然也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仔细想来,言论自由的种种优点或价值总是针对言论控制或言论钳制的。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公民无从自由地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加以监督和批评,而没有有效的监督,任何权力都会走向腐败。人类缤纷多彩的思想由于缺乏交流因而必然趋向单一,不同的观念失去了相互竞争的市场,一个民族的创造性的活力便不可能得以激发,久而久之会窒息民族本身的生机。此外,言论自由还是维持社会的一种“阀门”——我们的古人便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道理。
但是,言论自由也有其弊端。不受新闻检查制度控制的各种媒体各唱各的调,注定会带来信息的混乱。尽管可以通过相关法律规定对构成侵权乃至犯罪的媒体加以处罚,然而事后追诉制度肯定无法保证所有的违法行为均无例外地受到惩罚,同时诉讼过程的成本也往往使一些遭受言论或媒体侵犯的人们裹足不前。对于特定的言论究竟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判断标准的含混不清使得媒体可以“打擦边球”。与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相伴随的这些弊端是难以克服的。假如硬要加以克服,势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按照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说法,“给新闻以自由乃是极端的民主,而限制这种自由便会迅速地滑入极端的屈从;本以为两者之间会有漫长的路途,殊不知连歇脚片刻的方寸之地都找不到”。于是,结论只能是,“为了能够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到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
戴安娜所指责的媒体正是新闻自由制度下的那些小报。按照“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定律,小报对于名人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更津津乐道,因为这类消息会给报纸带来更大的发行量。既然小报经常表现得“不严肃”,把它们全部取缔,整个社会不就“耳根子清净”,名人们也不会遭受这类报道给他们带来的无妄之灾了么?这种想法只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只想要好处、不想要坏处的幻想。就小报言,在许多时候,名人们也常常从中获得平头百姓以及无名之士所难以获得的益处。此外,在有关诽谤以及名誉权的法制较为完善和有效的国家,小报也需要顾及侵权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大多数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据确凿的。对于名人的自律,对于社会的民主秩序和安全,这些无孔不入、善于制造新闻的小报的作用是大报所不可替代的。
不过,无论如何,人们的隐私权受到小报更大的威胁仍是一个必须被正视的问题。
隐私权的保护及其例外
隐私权是一种出现相对晚近的“权种”。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愿为他人知道的隐私,不过,把什么事项作为隐私,是否将隐私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加以维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见解和处理方法。
当今社会,政府官员、社会贤达名流以及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可以算是名人或曰公众人物,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和侵犯。通常人们会想,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则,无论有名与否,每个人的隐私权都该受到同等的保护。实则不然,名人恰恰由于其为名人的缘故,隐私权的完整性受到限制。
基于新闻自由,媒体常常会揭露公众人物不甚光彩的一面。应该说,媒体的这种监督对于维护公众人物操守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媒体上的这类文章有时不免在细节方面失实,导致被揭发者诉诸法律途径,指控作者和媒体犯有诽谤罪或损害其名誉权。受理诉讼的法院有时也会以一些细节失实而判决作者及媒体败诉。经年累月的诉讼过程,一旦败诉后必须付出的赔偿,相关文章的作者、编辑所需要面对的巨大风险,都使得媒体在刊发对公众人物的批评文章时不得不谨慎小心,如履薄冰。结果当然是挑刺不如栽花,批评少发为佳。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社会便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法院处理这类问题的做法或许对我们不无参考价值。1960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整版宣传广告,揭露亚拉巴马州警察虐待黑人,煽动“恐怖浪潮”,所举例证有若干失实之处。警察当局负责人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该州最高法院维持地方法院判决,命令《纽约时报》赔偿50万美元。报社不服,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并宣布了涉及诽谤公职人员的一项重要原则,那就是:当公职人员受到不实批评并遭受伤害时,不得提起诽谤罪诉讼,也不得要求赔偿,除非原告能够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批评是出于“真实的恶意”。这项判决几乎封死了公职人员在诽谤罪方面的起诉之路。
到了1988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将媒体所刊登讽刺作品包括在保护范围内,规定媒体刊登对于公众人物的讽刺作品,无论作品多么具有伤害性,即便是其中包含着令公众人物难堪的色情描写,受到讽刺的公众人物也不能够请求损害赔偿。对于法院而言,诽谤罪诉讼的目的在于确保新闻的监督功能,维持社会健康而正常地运作。
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制度对于公众人物一方有些不公平。个别情况下,批评失实,公众人物确实受到伤害,无从得到法律救济,诚然是不公平。不过,我们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更需要注意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注意个人公平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注重新闻自由对于整个社会更高的价值。况且公众人物也应当意识到他从媒体所可能导致的伤害与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摘自法律出版社《法边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