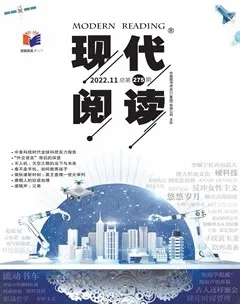忆西南联大的先生们
2022-12-29李赋宁



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我于1942年被清华大学聘任为外文系专任讲师后,由吴宓先生介绍,经李继侗先生同意,从昆中北院宿舍迁入北门街71号。
北门街71号是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单身教授宿舍。当时有许多前辈学者和老师也住在那里,我有幸和这些大师们住在同一宿舍达4年有余(1942—1946),日夕相处,耳濡目染,对我以后做人和治学都起了深远的影响。
从宿舍大门进去后,右侧有一间门房。门房右侧有一门通向里院,内有一间大厅,住着西南联大航空系主任兼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教授一家。小院左侧稍南有一门通向一个较大的院落,李继侗教授种了几畦菜,供入伙的教授们食用。院落尽头是蹲坑的厕所,条件十分艰苦。
正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里面放着一张长桌、一张圆桌和若干条凳子。住在清华单身教授宿舍的人,除了陈岱孙、叶企孙和金岳霖3位先生和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先生抱独身主义,吴宓和沈有鼎两位先生已离婚、年轻教授邵循恪和王宪钧两位先生未婚外,其余的教授都是已婚者,只是他们的夫人都不在昆明。
正厅南面是戏台,戏台上面还有一层楼,为一大间住房,住着温德先生。温德先生爱好古典音乐,他房中时常飘出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唱片乐曲。他又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新闻广播。我有幸和他住隔壁,耳福不浅。戏台对面的楼上,也有一间大房,算是这个宿舍的正房。因为面积大,里面住了5位教授:金岳霖、陈岱孙、李继侗、朱自清和陈福田先生。这5位教授各据一个角落,拉起蚊帐,互不干扰。
正房的楼下有两间小房。一间住着邵循正先生、邵循恪先生两弟兄,另一间住着王宪钧先生和杨业治先生(杨先生住在乡下,进城来上课的日子就和王先生同住此室)。正厅的两侧有一些小房间。陈嘉先生住了一间我原来住过的房间。那间房子耗子特凶。我外出上课时,耗子就爬上我的床,啃我的毯子。我不得已搬了一块很重的石头压在地面上的耗子洞口,才得暂时相安无事。就在那间陋室里,陈嘉先生在打字机上用英文创作了好几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剧本,写了好几篇介绍中国戏剧的英文文章(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受到好评)。其余那些小房间,大多是供住在乡下的教授进城上课时过夜之用。
我仍住在楼下时,和吴有训先生隔壁。黄子卿先生住在大厅另一侧的一间小室内。黄先生的家在黄土坡。他因孩子多,家庭负担重,在中法大学兼课(中法大学当时在黄土坡上课),教大学物理。黄先生是物理化学专家,教大学普通物理应是游刃有余,但他备课极为认真。有一次,为了弄清楚某个问题,他特意到吴先生室内来请教。我在隔壁听见他们讨论得很热烈。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西南联大的教授多么重视基础课的教学,多么一丝不苟!
正厅东侧楼上几个单间小室内住着叶企孙先生、刘崇鋐先生和沈同先生。那时叶企孙先生已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务,从重庆来到昆明。梅贻琦校长委托叶先生主管清华5个研究所的事务。我经常看见叶先生在正厅长桌边接待来访的客人、同事,和他们耐心地谈话、讨论。这是十分劳累的事,因为来客几乎是络绎不绝。清华这几个研究所做出的优异成绩是和叶先生的精心策划与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我记得有一次陈岱孙先生在正厅里长桌边看报,有一位客人把报上标题“斡旋”一词中的“斡”字误读作“幹”。陈先生纠正了那人,说应读wò,不应读gàn。陈先生并朝楼上正房里的朱自清先生喊话,问道:“佩弦,是念wò旋,不念gàn旋?”朱先生肯定了陈先生的读音,说“斡”和“幹”根本是不同的两个字。
张奚若先生一家住在北门街唐继尧陵园内的房舍里,离71号咫尺距离。张先生常来71号找金岳霖先生聊天,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同学和多年的老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张先生考金先生英文chasm(深渊,鸿沟,巨大差别)一词如何读音。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西南联大的老师对语言的精确,要求得多么严格。
邵循正先生是历史学家,治元史。他学识渊博,曾担任《清华大学学报》(文史版)主编多年。英国牛津大学汉学专业高级讲师休斯先生到联大进修,要iK1U3vvV2VBoJF/ZJ2DV7w==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梅贻琦校长安排休斯住在北门街71号正厅西侧楼上客房内,并请邵循正先生做休斯的导师。休斯苦读先秦诸子百家,夜以继日地和古汉语搏斗。邵先生耐心地用英语回答休斯的提问,和他讨论各家的学说和各派的不同论点。半年之后,休斯先生满意地回往牛津。邵先生为中英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当时休斯已五十开外,满头苍发,而邵先生仅有三十多岁,一头青丝。华发人认黑发人为老师,倒也有趣。
我的恩师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主讲欧洲文学史(吴先生讲课的内容还包括印度、波斯、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文学),他为了培养我的讲课能力,就把这门课的英国文学部分分给我讲。吴先生住在温德先生房间西侧的隔壁,我住在楼下正厅东侧的一间小房内。我经常向吴先生请教专业上的疑难问题。1944年,吴先生休假,去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托我看守他的房间。我于是从楼下搬到楼上,替他看房,一直到1946年复员离昆。吴先生的房间很小,摆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后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吴先生室内贴着他自己写的布告:“来客请勿吸烟”。我遵守他的规定,自己不在室内抽烟,也请来访者勿吸。吴先生室内还贴着他的朋友贺他50岁生日的贺诗,为萧公权、浦江清、林文铮等先生亲自书写。诗句和书法都十分精美。
吴先生小房楼下住着沈有鼎先生。沈先生当时对昆曲和希腊文着迷。有时他凌晨两点钟吹笛子或念希腊文,我在楼上听得很清楚。幸亏我当时没有神经衰弱,不怕他吵,照常入睡。正是以他的勤奋为榜样,我后来也学会了希腊文。
1945年,由于吴宓先生留蓉未归,外文系系主任让我独立讲授“英国文学史”课(代替“欧洲文学史”)。我在备课中遇到难题时,常向陈嘉先生请教。陈嘉先生是杭州人,清华旧制毕业留美。他本科就读威斯康星大学,是哈佛大学硕士、耶鲁大学博士,研究英国文学造诣很深。回国后,他先在浙江大学教书,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莎士比亚”。他对戏剧创作很感兴趣,曾用英文写一些抗战期间的趣事,用打字机打出来,请同事们品评。
庄前鼎先生和夫人每年春节前夕(农历除夕)都要邀请住在北门街71号的单身和家眷不在昆明的教授到他们房里吃年夜饭。我也有幸参加过两次这样的盛会。
1945年春,陈寅恪先生由燕京大学历史系助教刘适(即石泉,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护送,从成都飞抵昆明,转往印度乘船去英国医治眼疾。陈先生在昆明停留数日,即下榻于北门街71号正厅西侧一间客房里。当时陈先生的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但精神仍佳。每日来看望他的人很多,大多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人员,对陈先生的健康都极为关怀。陈先生听说话人的声音往往能辨认出来访者是谁。
上面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人和事。我在此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联大教书和在昆明生活的侧影,有助于后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艰苦条件下仍保持勤奋、严谨的敬业精神。
(摘自商务印书馆《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