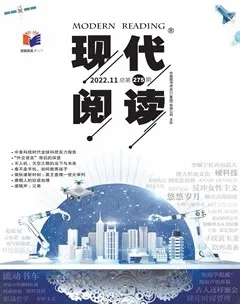雍正对造办处的全方位改造
2022-12-29高彦颐译/詹镇鹏


造办处是清代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于康熙年间成立,营运至1924年。造办处与皇室的起居息息相关,除制造、修缮、收藏御用品外,还参与装修陈设、地图绘制、兵工制造、贡品收发、罚没处置以及洋人管理等事宜,是宫中具有实权的特殊机构。
改造造办处
在雍正帝持续关注下,造办处机制在他短暂但关键的统治期内得以合理优化。他在登基之初,便建立起一套管控物料和信息的流程,并设立档案系统。至18世纪中叶,一套由他制定的运作程序涉及六房,每个房附特定职能并留档。皇帝颁发需成造的器物种类和数量的旨意,先传达至活计房,再转到特定的作坊。算档房预估器物大小和数量,在钱粮库从库中发放必要物料和银两前,换算出物料和匠银支出。督催房确保活计进度按时完成,而汇总房在监督完成后,核查所有账册。至年末,账册会送到档房保管。活计房档案中的条目,通常记:“某月某日,(皇上)传旨:着做……”
整个制造、物流供应和记录的庞大系统运行,都是围绕皇帝的个人需求和兴趣而展开、核查和相互监督,在具有成本效益和时间效益的前提下,保证器物的制作品质和数量。
雍正更扩大造办处的管理级别,加强每个作坊的匠役招募和监管。有康熙将管理造办处全权委托一位皇子的先例在前,雍正也委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为造办处监理制造和管理大臣,直接向他汇报。造办处官员的官衔或借用自(平行于)常规官署,或吸收前人再发明。随着工作量增大,数年后又增加新职位。这个由康熙初设的架构,经雍正合理优化、乾隆再扩大,至清朝末年仍持续运作,与京外第一级衙门相平行。
雍正还建立了一支与之配套的宦官队伍。太监通常作为传达皇帝旨意或进呈库房器物的角色出现,也负责宫外招募匠人之事。因此,技术知识的管理者从明廷的太监,转移到清代的亲王、包衣、旗人匠役。
每个作坊由拜唐阿(知事)和催领(从匠役提拔并会亲自处理、成造)带领。雍正朝的造办处有匠役数百名,主要源自两种渠道,各有特定的招募程序和资格评定:每隔几年,一批(数十名)隶属上三旗的兵丁和包衣青年,可进入造办处当学徒或“学手小匠”;训练完成后,他们成为“家内匠役”或“家匠”,也称“食银匠”。从全国各地私营作坊招募的匠人,统称“招募匠”或“外雇匠”,用于填补临时空缺,少数杰出者也可转为“食银匠”。招募匠时常被带入宫内,专门去培训家内匠役。
依托于这个创新体制,全国各行业最顶尖的匠人成为朝野之间手工艺交流的管道,推动宫廷和民间的手工艺与制造业在清代早中期的发展。即使有“家内”和“外雇”之别,表明了以皇上为中心,但这个体制的关键在于吸收分散全国的工匠骨干,尤其是来自南方发达地区者。
作坊每日运作仍不免面临各项挑战。怡亲王接掌上任之初,于雍正元年(1723)正月颁发一条谕令,要求各作坊的拜唐阿各尽职分,若发现工匠有“迟来、早散、懒惰、蠡猾、肆行争斗、喧哗高声、不遵礼法”,应该重罚。拜唐阿不许擅自私责匠役,“假借公务以忌私仇”。
然而,雍正五年至七年(1727—1729),雍正仍发现匠役完成应做活计后,多有旷闲,命他们去多做活计以备用。偷盗问题亦持续发生,尤其是怡亲王于雍正八年(1730)病逝之后。例如,曾有一名外招铁匠在雍正九年(1731)被发现偷铁14斤(此处的“斤”为雍正时期计量单位,与今日有差异,以下皆同)。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听闻总管太监支使或强迫匠役仿造官窑并向外销售,对擅自传做活计亦不奏明的现象严加申饬。这损害到皇帝利益,却进一步增强了宫廷与民间在技艺和品味上的互动。
内廷样式的缔造者
尽管经雍正改造后的造办处不断出现纪律性问题,但是雍正孜孜不倦地对作坊的艺术和物料资源实行管控,靠对每一件活计质量的严格要求,打造出了留下他个人烙印的新内廷恭造之式。几乎设计和生产的每项步骤,未经皇帝允许,皆不得实行。他会责罚拜唐阿,申饬匠役:他在检视赏赐用的100件新制玻璃鼻烟壶时,发现其中41件款式“甚俗,不好!可惜材料!”要求重做他认为“俗/俗气”“蠢”的样式,希望能提升到“秀气”“精细”“文雅”“再玲珑些”的程度。
一次雍正不满发怒后,怡亲王下谕:“有奉上谕夸过好的留下样子,或交出着做的活内存下的样。”因之前呈进样式甚不好,砚作的郎中被命呈看先前做过的砚样及旧存好样。
除按“文雅”或“玲珑”带主观色彩的形容词去改进一件器物的整体观感外,雍正同样会凭借自身对物料和制作技法的知识,对工艺流程做具体指示。怡亲王曾交进一块重14斤8两的朱砂,雍正传旨:“将皮子起下来做几锭墨看,做时不可对(兑)银朱,纯用朱砂。”皇上每日用朱墨批阅奏折,但在此例子中,雍正对技术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或与他个人喜好炼丹有关。随着他逐步了解内廷作坊的技术限制和个别工匠的特点后,旨意更为具体。
雍正精力无穷、关注细节、嗜好严密监控,有时甚至会过度干预。他曾命人将供奉在景山东门内庙里的汞金(即鎏金)骑马关帝像,照其样再造一尊。在随后两个月内,雍正前后下旨拨改了4次蜡样,关帝的脸、腿、马鬃、从神头盔都反复修改。皇帝的关注细致入微,连关帝腰带的松紧、身背后的衣褶也不放过。
雍正传旨活计之初,通常心中只有一个抽象概念,唯有检视匠役制作的样时,才逐步明确偏好和修改方向。在看到实物之前,他是无法确定自己喜欢与否的。皇上和工匠在地位和权力上存在巨大鸿沟,但两者是内廷样式的共同缔造者。
匠役窃取物料和仿冒官器,不仅有损雍正的经济利益,而且对构建一个独特且专属皇上的内廷样式也很不利。雍正三年(1725),怡亲王呈进象牙和黄铜制的抢风帽架两份,皇帝传旨:“它们只许里边做”,并警告如有照此样“传与外人知道”,将稽查缘由,从重治罪。问题是,雍正作坊机制的成功发展,是建立在宫廷内外匠人不断技术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也正因此,他要严格界定“内外”之别,实不乏矛盾,甚至是无法彻底实行的。
登基5年后,雍正意识到内廷样式是需要与时俱进的;要不断创新,就不得不参照累积下来的传统做法。他抱怨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但仍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但做工大有外造之气。他的言外之意是,巧妙做工实际上多来自宫外作坊,而家内匠役则需迎头赶上。为重申“内廷恭造式样”和“外造之气”之间的差异,雍正命作坊以实物或纸稿形式留样,以便匠人日后可细心研究、照样制作。承平日久,全国工艺品市场生机勃勃,技艺精益求精,珍品层出不穷。雍正敏锐地意识到家内匠役与来自南边作坊的能工巧匠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其口吻能察觉到几分戒心。
雍正之所以希望通过留样来“保存”清宫文物的皇家风格,是因为他担心匠役的知识和技艺会衰退,以及内廷样式会被稀释。他深切认识到皇家风格只能具体表现,是难以抽象化的。清初的内廷样式不是“文雅”和“精细”等空泛形容词建构,而是通过造办处匠役心、手、眼并用打造出来的大小器物逐件建立起来。在雍正的观念中,内廷样式是通过比较而非孤立而存。一件器物之所以是“内造之式”,是因为它区别于宫外作坊。正是“风格即区别”的认识驱使着清初帝王去无穷尽地追求新材料和新技术。
(摘自商务印书馆《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图注:造办处最早设于养心殿内;造办处从苏州招募捏像人捏制的泥塑雍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