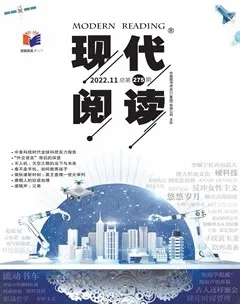童年是否决定了你现在的生活?
2022-12-29博•雅各布森译/郑世彦
自弗洛伊德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个体成年后的痛苦和性格可以追溯到童年的某些事件或情境。在整个20世纪,童年对成人生活的重要性已被视为不言而喻的事实;也就是说,它成了我们理解自己的一个背景。很多人一直在努力挣脱童年的影响,并且这种努力可能会持续很多年。今天,不仅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面谈中包括对童年状况的探究,童年和教养也成了朋友间谈话的一个重要话题。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体上也充斥着关于童年重要性的文章。
童年对成人生活的重要性,大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一种是精神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存在主义的方式。
精神分析的因果观
这种观点认为,童年时期的某些事件会导致个体在成年后出现某种精神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被父母以专制的方式对待,可能会导致他成年后极其依赖他人,并很难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从小遭受忽视,可能会导致他在成年后缺乏爱的能力以及养育的技能。
如今,许多人都有强烈的需求,想弄清楚自己的成长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人想知道父亲或母亲究竟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被收养的孩子和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希望澄清一些问题,或者了解自己的身世;受到虐待的人想知道是否发生过乱伦,是否被殴打过或受过其他虐待。他们想知道关于自己过去的真相。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需要可以被视为上述观点的结果,即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童年,这个童年对成年生活有着因果影响。
童年经历决定了我们成年后的生活和问题,这一观点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当今西方社会最根深蒂固的心理观念之一。由于纯粹的方法论原因,许多实验心理学家对这一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持消极态度。
存在主义的观点
这种观点提供了对童年角色的不同理解。每个人都不止有一种童年经验。在记忆的某个地方,我们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早期经验,它们在原则上都是可获取的。在这些经验中,我们“选择”记住数量有限的,通常是某些特定类型和基调的经验。
存在主义思想认为,将单向的因果关系附加在人类生命之上是一种扭曲。人类的心理状态和行动的原因,与台球运动的原因并不相同。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动源于他的意图,源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需求。在童年经历的虐待和成年后经历的虐待之间,可能存在主题上的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导致了后者。也可能是后者“导致”了前者,因为我在工作场所遭受的实际虐待,突然让我从庞大的记忆库中回忆起特定的童年经验。
那么,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童年的角色是什么呢?童年的角色就是,成年人利用它来定义自己现在是谁。我们都和父母一起经历过好的和坏的时刻,我们都在童年有过快乐和不幸的时光,我们都经历过成功和失败。作为成年人,我们“选择”记住的,是那些符合自我建构或自我定义的内容。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乐观的和有能力的,我就倾向于“选择”支持和促进这种自我建构的童年记忆。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不幸的受害者,在童年记忆库中保留的回忆就可能会支持这一看法。
这种观点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特定的自我建构是如何形成或加诸个人身上的,这个自我建构又是如何改变或发展的?显然,能够充分解释这一重要现象的理论仍有待发展。
无论如何,人的童年是被诠释过的童年;因此,它可以被重新诠释。不存在不被诠释的童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童年。但是,如果童年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是什么原因让许多人寻找自己的根,寻找过去的日子,寻找自己的起源?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揭示真相,想要了解父母到底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想要知道自己是否被殴打、是否经常被放任自流、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欣赏和鼓励,等等?
首先,这种需求可以被看作个人与自己达成和解的方式。与自己和解需要了解和接受自己的生活真相。其次,它可以被看作个人试图与他们人格中分裂的部分接触。
成年人通常会有许多不同的情绪和感受,它们可能就像心灵中的孤岛。这些情绪和感受,无论是悲伤、孤独、严厉、体贴、恐惧,还是其他源自人类生活的丰富情感,都可能被包裹在你只能有限地接触到的童年记忆中,但它们本身又极具吸引力。你相信自己正在从过去的生活中提取真相,但你真正渴望的是重新整合自己心灵中分裂的孤岛,让隐藏的情绪或感受重新归属自己有意识的心灵生活。
我们对比精神分析的因果论和存在主义观点,当然不是暗示童年经历对个人没有影响。毫无疑问,童年经历会通过许多方式影响后来发生的事情。它们产生影响的方式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正如发展心理学的经典研究,例如勒内·斯皮茨和约翰·鲍尔比的研究,表明童年经历有时可能会产生持久的不良影响。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对于当今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认为自己由童年经历所决定是不恰当的。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我们不约而同地利用它,使自己不必为当前的生活负责,不必认真对待当前生活的挑战。这个信念阻止了我们作出根本的改变;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幸福,这种改变可能是必要的。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