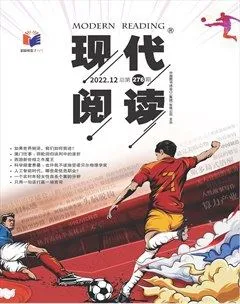穿过悲伤的河流
2022-12-29卡罗尔·史密斯


克里斯托弗26岁生日的那天,我来到杂货店的鲜花柜台前,买了一盆多花水仙。“送人吗?”鲜花柜台的女店员一边问,一边用纸巾仔细地包好花茎。我将花放在副驾驶座上,开车往我多年不曾踏足的墓园驶去。
克里斯托弗去世那年的冬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所有人来到西雅图,参加他的追悼会。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帷幔,遮住天地万物,掩去世间的色彩。
克里斯托弗安详地躺在一个简单的棺材里。到了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的家人一直在身后推我,不给我任何逃避的机会。他们担心只要我没看到他的遗体,就不会接受他死去的事实。没有人说得清失去孩子有多痛苦,但是它有什么并发症,大家都很清楚,拒绝接受事实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
克里斯托弗活着的那7年,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他还未出生时,就查出了一个发育缺陷,导致尿路堵塞,肾功能受损。看似微小的一个缺陷,却引发了一连串让人难以招架的蝴蝶效应,以及难以摆脱的后遗症。
尽管困难重重,可他顽强地活了下来,挺过了接二连三的生命危机,却没能躲过最后这一次。7岁那年的圣诞节假期,他和父亲一起去看望爷爷奶奶,却突发肠道梗阻,意外去世。我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我还活着,他却死了。
他走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
这句话,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说。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我提到他去世的事,这句话就会自动冒出来。我的理智告诉我,即使我在他身边,也改变不了结局,可是妄想是一种强大的自我防御,人们只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始终无法对他的突然离世释怀,执迷不悟地认为如果我当时陪在他身边,他就不会死去。
那年秋天,我父母带我去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展开一场寻根之旅。在他们看来,换一个环境,去外地散散心,也许对我有好处。那时的我如同行尸走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像在梦游一样,什么也记不住。到了夜里,我害怕睡觉,害怕掉入永无止境的噩梦。我将那些纷乱的噩梦写进日记本里,天真地以为只要写下来,就能将它们驱散:
梦见自己随船漂流到海上,望眼欲穿地凝视海底,不知在找寻什么。
梦见电梯门夹住了克里斯托弗的围巾,电梯开始下降,没人听得见我的尖叫。
梦见我听见急救呼叫,跑去抢救病人,可我不是医生,也不知如何抢救。
然后,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狂跳,心慌气短,浑身冒汗。我想,那个需要紧急抢救的人,是我。
我父亲的家族在好几代之前便从苏格兰举家搬迁到新斯科舍省。到了那里后,我们忙碌地研究族谱,如同在地图上寻找地标的游客,兢兢业业地研究每处支派。每发现一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就兴奋不已,仿佛挖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文物。我很感激这一次旅行,让我暂时忘了失去克里斯托弗的痛苦。
在新斯科舍省游玩了一周,我们从位于东北海岸的皮克图岛上船,前往爱德华王子岛省。我的曾祖父母曾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小岛上,并在岛上埋葬了一个男婴。克里斯托弗才刚去世,我的痛苦仍未消退。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婴儿的坟墓,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崩溃,可我没得选,我必须去。
我们在伍德岛上岸,那里的沙滩是红色的。傍晚的阳光照亮了马路两边的麦田,我们开车在岛上穿梭,留意着两旁的路标,寻找早期开拓者的墓园。我们开进许多死胡同,绕了许多冤枉路,最后终于来到一块被白桦树环绕的空地,找到了一处小墓园。我父母在前方探路,我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终于,他们在一排排墓碑中找到了它:
追忆爱子威利
年仅15个月18天
起初我很犹豫,但是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牵动了我,让我不由自主地抬脚走了过去。被岁月褪去色彩的墓碑,像一座小小的灯塔,矗立在草海中央。我一看到碑上刻着的小羔羊,就知道这是威利的墓。我奶奶每次追忆她父母,说他们在生下她之前,曾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失去过一个儿子,就会提到碑上的小羔羊。她不曾来过新斯科舍省,不曾亲眼见过威利的坟墓,但是这块碑上的每一笔刻痕,早已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中。她想象中的墓碑是那么真实,与我看到的一样真实。我跪在墓碑旁边,清理它脚下的碎石。碑上的文字触动了我的心灵——那对生命的丈量,那精确到天的寿命,精确得让人心酸。那天,温柔的霞光洒满整座墓园,墓园中藏着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墓,小墓四周长满了草,草丛里有许多蛐蛐在“唧唧”地唱着摇篮曲,歌声中混着远方雾号的“哞哞”声。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不管过了多久,都不曾淡却。
时间无法与记忆抗衡。只要记忆不允许,时间就无法逼迫我们遗忘。克里斯托弗去世后,我最害怕的是大家会渐渐忘了他,再也没人记得他的笑声,再也没人说起他对火车和牛仔的狂热。在他很小的时候,电影《生命因你而动听》曾找他当临演。有时,我们走在路上,会有路人过来搭讪,说他们曾在电影里看到过他。我从来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甚至近乎迷信地认为,只要我不看,某一部分的他就还活在这世上,等着我去寻找,寻找最后一块仍流失在外的记忆。
然而,威利的逝世,在百年之后仍然触动了来到此地的后人。在他父母身上留下的悲伤的印记,被我的奶奶感应到,通过几代人流传下来,血脉延绵。
除了失去骨肉的痛苦,我与我的曾祖父母还在另一方面有了共鸣。当他们第一次站到这里,陷入悲伤之中时,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快乐在等待他们。他们不知道,有一天他们的后人会站在这里,祭奠他们的痛苦,追忆他们的儿子。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我不可能站在这里。在他们身上,我似乎窥见了自己的未来,隐约看到一丝希望,纵使十分渺茫,像墓地里的微风一样稍纵即逝,但我依然伸出手,渴望抓住它。
在新斯科舍省的两个星期,树叶静默无声地变换了颜色,为秋日添上浓墨重彩的华裳,如一抹红霞蔓延至天边,将天地染成残火欲尽的红,预示着生与死的轮换,预示着留不住的生命。即使是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毫无征兆的死亡。
沿着族谱一路往回走,我才发现每个人走过的世间路有多短。对我而言,克里斯托弗的死,重如泰山。他的生命纵使短暂得令我措手不及,却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他在族谱上占据的位置,不比其他人大,也不比其他人小。
我停好车,抱着那盆多花水仙,朝山上克里斯托弗的墓地走去。我们将他的墓地选在一棵树边,还在树枝上挂了一只喂食器,偶有鸟儿光临那里,与他做伴,不让他孤单。
墓碑上写着“克里斯托弗,7岁”。这是我们特意为他保留的习惯,每次向刚认识的人介绍自己,他就会在名字后面加上岁数。碑上还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第372首诗里的一行诗句——“剧痛过后,麻木将至”。
我坐在树旁的长凳上,将纸鹤放在腿上,凝视着华盛顿湖。墓园门外的湖城路上川流不息,车辆驶过的轰鸣声汇聚成河流低沉的呜咽声。远处是逶迤的喀斯喀特山脉,和克里斯托弗用卡纸做的立体画一样,层峦叠翠。我的记忆也如远山般层层叠叠,渐次模糊暗淡,苍茫远去,可我却还期盼着,有一天我能重新找回它们的色彩。
微风温柔地拂过我头顶上的树枝,我的手亦曾那样温柔地拂过克里斯托弗的发。我闭上双眼,恍惚间似乎听见了他的声音,却是几只黑头山雀扑棱着翅膀,从枝头飞走,“唧唧”地齐声叫唤。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将花放在克里斯托弗的墓前,便回到车子停放的地方,靠着车门坐了一小会儿。当我不经意间抬头时,两辆车子不知何时出现,停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墓地附近,车里坐着好几个年轻人。他们一共有5个人,从车里下来之后,就站在他墓碑旁边的树下,其中两个人正兴奋地打着手语。
有一个年轻女人背着一个婴儿,一个手中拿着气球。我恍然意识到,他们也许是弗兰克那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另一半的亲人,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们来这里,似乎是为庆祝克里斯托弗的生日,也有可能是带刚出生的家庭新成员来见他。看到他们来看望克里斯托弗,我很欣慰。
曾有一段时间,我感受不到一丝快乐。结束一段近十年的婚姻,这样的结局对任何一方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克里斯托弗却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他可以用爱包容所有人。有一天,他带了一些画给我,画里是他所画的家庭——我,他的父亲,他的继兄弟姐妹,他的继母,还有我当时的爱人吉姆,全都在画上。画中有一个女人长着一头长发,用两条黄色的绳束住,那个人便是我。对他来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虽然我和弗兰克做不了一对好夫妻,但是我们对儿子的爱永远不会变。刚离婚时,我们都曾埋怨过对方。如今,我们已经原谅了年轻时不成熟的彼此。
克里斯托弗去世后,我与弗兰克的新家庭逐渐断了联系。此时,看着站在他墓前的年轻人,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哀悼与庆祝是可以共存的——悼念逝者、庆祝新生。
失去与希望,痛苦与慈悲,哀伤与快乐,都是可以共存的,也必须共存。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穿过悲伤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