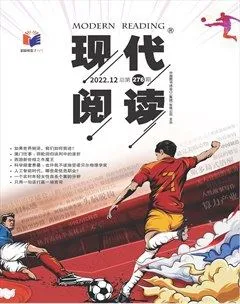用斯多葛式智慧回答什么是真正的“清醒”
2022-12-29徐英瑾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人忙碌的都市生活背后的深层逻辑,很可能建立在一些重要的概念混淆之上。一个常见的混淆就是,将“理想主义”与“业绩至上主义” 当成一回事。具体而言,很多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有理想,就要有干劲,也就需要不断拼工作业绩,将工作做得“多快好省”,否则就是“躺平”,就是“佛系”,就是“胸无大志”。因此,慢节奏的学习和工作方式被污名化,甚至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
事实上,“理想主义”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与多数人的想法相反,理想主义哲学的老祖宗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或许都是慢性子的人。他们的核心哲学思想就是要让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努力按某些抽象的“理念”来成就自己——因此,理想主义者喜欢问的问题是:你制作的这个花瓶是否符合“美”的理念呢?某某法官判的案子是否符合“正义”的理念呢?很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会要求理想主义者反复排除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瑕疵,不到完美的程度绝不提交工作成果。因此,理想主义非但不会催生“加速主义”,相反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工作拖延症”。
那么,为何“理想主义”的含义在今天会发生如此明显的颠倒呢?
因为现代社会金钱逻辑的倒逼机制实在太强大了。金钱社会的最大理想就是“快”,因为很多重要事项的运作周期都有时间限制:企业融资有还贷周期,产品上市必须赶上某个重要销售节点,演员的表演要受到档期限制,就连大学里的青年教授也都在“3年后非升即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战战兢兢。你想慢工出细活,自己把握时间做好想做的事?没门儿!金钱逻辑会告诉你,若不按照它的时间节奏调整你自己的每一次呼吸,你就迟早会被踢出局。
我们除了是火花塞与齿轮,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对于这个问题,丹麦心理学家斯文·布林克曼给出的答案是:让自己清醒。
在布林克曼看来,现代人在各种各样“快马加鞭”的“加速主义心灵鸡汤”中已麻痹太久,以至于大家已近乎放弃了对“慢生活”的感知力。我们需要一味新的思想药剂,让我们能够用一种崭新的态度来面对滚滚红尘中的种种喧嚣。
需要指出的是,布林克曼开出的药方是流行于希腊晚期与罗马时期的斯多葛主义(顺便说一句,“斯多葛”并非人名,而是指进行哲学讨论的回廊建筑)。那么,到底什么是斯多葛主义?
假设你穿越到了1642年的荷兰,化身为画家伦勃朗,正受托为阿姆斯特丹的一群有点小钱的市民画群像。既然花了银子,委托人自然希望他们中的每个人的脸蛋都能在画布上呈现得端端正正。但作为一名有艺术追求的画家,你不想再画一幅“全家福”式的平庸之作。相反,你要让这群市民全副武装,在昏暗的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夜巡,用一种若隐若现的色调来表现这整个场景——但这样的构图,必然会让某些委托人的脸蛋淹没在阴影中,使得他很难被亲朋好友所辨识。因此,这些委托人是不太可能喜欢这个构图方案的。于是,滋生于你灵魂深处的艺术理念与“金主们”的托付产生了矛盾。那么,面对这种矛盾,你该怎么做呢?
标准的柏拉图主义者的做法是:坚持心中理念,且不惜与外部世界全面开战。因此,一个满脑子柏拉图主义的画家会充满热情地向他的委托人宣扬他的艺术理念,直到后者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不过,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委托人真正被说服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做理想主义者的代价,往往是被残酷的现实抽打得遍体鳞伤。
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案,即“存在主义”(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即将残酷世界与个体自由之间的斗争视为一种常态,甚至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存在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是:理想主义依然乐观地认为只要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现实总会按照理想的要求被改造;而存在主义则略带悲观地认为,个体被别人误解这一点是很难避免的,甚至就连明日的自己也会误解昨日的自己。因此,为个体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就带有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壮。于是,一个信奉存在主义的画家既不会对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艺术理念抱有期望,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艺术探索自由——他会不停地画,不停地被批评,然后再不停地画,就像那个不断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
面对个7ZZQuv7SFSR5kVUmsG/RHVaeIFngIX3wFULFc3BkZZI=体与世界的这种张力,斯多葛主义的解决之道既不同于理想主义,又不同于存在主义。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即通过构建一个心灵中的“微宇宙”来对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压力。斯多葛主义并没有理想主义这么乐观(即认为世界一定会变好),也没有存在主义那么悲观(即认为世界注定会来压迫我),而是认为世界既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想象的那么坏。一个具有足够的斯多葛式智慧的人,应当建立起一个大致靠谱的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模型,并依据这个模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们如何让自己具有足够的斯多葛式智慧来面对难以调和的生活难题呢?作为斯多葛主义者的布林克曼给了如下建议:
第一,通过高层次的阅读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以作为自己心灵中的“微宇宙”的逻辑框架。也就是说,大家一定不要读那种低级的网络爽文,因为爽文会破坏大家对于世界的正常认知——在爽文的世界中,只要是故事的主角,就一定会一路开挂,一直攀登到人生巅峰,而在这种简化的描述方式中,社会的复杂性往往会被牺牲掉。真正好的小说往往会给你更健全的关于世界的认知:《傲慢与偏见》让你知道不能以第一印象取人;《悲惨世界》让你知道一个好人同时也可以是冒牌市长;《水浒传》则让你知道,即使是将门之后也会卖刀换盘缠。通过这种阅读,读者就能调整其对社会的期望,了解人生不如意本是常事,由此在真正面临人生不幸的时候作好心理准备。
第二,在此基础上,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要意识到人生的脆弱性,意识到自己的任何一个宏图大志都可能会被一些貌似微不足道的因素打败。这些因素可以是一次意外的车祸,可以是痛风引发的脚趾疼,可以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行动不便,也可以是视力退化引发的阅读困难等。请注意,斯多葛主义在此提供的是一种与加速主义文化用力方向完全相反的认知:加速主义文化的核心要义,是要像吹气球一样让自信心爆棚,让你不断对自己说“我可以的!我的潜能是无穷的!”;而斯多葛主义的要义,是要让你意识到,人类个体的精神与肉体都可能像芦苇一样脆弱,失败的可能性会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这种认知将引导我们反观积极心理学的疏漏之处:积极心理学无视人类本质上的脆弱性,并在伦理上将对于自身脆弱性的承认视为一种羞耻,且完全无视外部环境对个体计划可能起到的破坏作用。这种积极心理学虽然能够在某种情况下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却可能在长远透支我们的精力,鼓励提出某些不切实际的工作计划,并由于这些计划的荒谬性而导致战略层面上的重大挫折。从这个角度看,斯多葛主义能帮助我们审慎地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长更远。
第三,斯多葛主义还教导我们重新看待友谊。大致而言,一个人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愿意与你分享人生压力,一起来面对人生脆弱的朋友;另一种则是不停给你人生激励,不断对你说“你可以的”的朋友。布林克曼给出的药方就是:解雇你的“心灵培训师”,让你的心灵能够减负而行。布林克曼甚至认为,过度的心灵激励反而会恶化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既然已知那些人在生活中出现的意义就是不断带给你焦虑,你为何还要将其视为真正的朋友呢?
斯多葛主义是当下中国社会非常需要但在客观上又高度缺乏的一种哲学修养。毋庸讳言,近几年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社会过度泛滥。与之相伴而行的,则是唯意志主义思想的流行——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意志力足够强,就能逆天改命。结果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一些人甚至会在被现实狠狠打击以后陷入精神失调。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种“做加法”的思潮之外找到一种“做减法”的思潮与之平衡。斯多葛主义恰恰就是这种“做减法”的思想。
那么,斯多葛主义是不是主张“放弃一切fa38204142e066ea11092cdb3ddd21b47d66ceb3175c0f2261773385cb2498ff追求”的“佛系”思想呢?并不是。斯多葛主义的工作守则是“在你的行动半径内做你可以做的事情”,换言之,既不要随意自我加压,也不要放弃最基本的职责。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行动半径”,保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唯有如此,人生之路才能走得不疾不徐,扎扎实实。
回到开始的问题:如果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穿越到了1642年成为伦勃朗,他又该怎么画《夜巡》呢?是按照自己的艺术理念来画,还是按照顾客的要求去画呢?
一个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凭借其健全的世界观,应当能预料到:他如果按自己的想法去画的话,顾客大概率是不会开心的;但是,他也应当预料到,即使顾客不开心,由此所导致的风波很快就会过去,而在日后,世界美术史终将认识到《夜巡》的价值。所以,他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但与理想主义者不同,他不会试图向顾客宣传他的艺术理念,也不会像存在主义者那样因为顾客的“低艺术品位”而愤愤不平——相反,他会笑着面对顾客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会坚持他的构图方案,让顾客的脸蛋继续淹没在阿姆斯特丹的茫茫夜色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斯多葛主义伦理教导的核心,并不是直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一件事,而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看待你所做的某件事,并通过态度的改变来治疗世人的焦虑。对绘画的态度如此,对万事万物的态度亦如此。这种态度的自由切换能力,将让你达到符合斯多葛主义标准的“清醒”状态。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清醒》 作者:[丹麦]斯文·布林克曼 译者:黄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