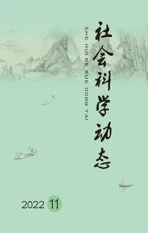身体社会理论转向下的身体与传播研究综述
2022-12-29杨璐
杨璐
一、引言
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将人视为灵魂—身体、意识—身体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在这样的框架中,纯粹意识和理性占据绝对优势,身体常常是被贬抑的一方。①17世纪,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我的心智……完全地、真正地有别于我的身体,没有身体也能存在”②,至此,肉体与心灵成为两个本质不同、相互分离的存在,身心二元的认识论框架被确定,身体沦为意识的从属,身体问题在哲学及其他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中被隐去。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身体的重视使得身体重回哲学领域,他强调身体对人存在的基础性,认为自我(self)居处于身体之中,意识乃是身体的派生③,身体才是一切事物和行动的起点。在尼采这里,身体比意识更加接近本体的地位。④由此,隐匿的身体在学术话语中重新被凸显出来。
二、社会科学领域的身体研究转向
20世纪40年代,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下简称庞蒂)提出“具身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强调身体的地位,反思并重建身心关系,打破了身心二元的认识论困境,开启了当代的身体理论研究。⑤庞蒂认为,人的主体性是通过物理性的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形成的。⑥在庞蒂看来,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其实质是物质性身体和主观性意识的统一体。他将身体视为人与世界连接的媒介,“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⑦在实践中,我们经由身体这一中介来体验世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以下简称莫斯)也从“技术社会学”(sociology of techniques)的视角出发提出“身体技术”的概念,在没有丰富的媒介技术前,人们大多通过身体进行交流,身体被莫斯视为人类最初拥有的、最自然的工具,人们通过社会传统习得使用身体的特定方式,而这些特定的身体动作和姿势即莫斯所谓的“身体技术”,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莫斯认为,身体不仅是生理的身体,更是被社会传统塑造的身体。⑧
20世纪下半叶,身体研究出现跨学科性的进展,对身体主题的关注在社会学、性别研究、哲学、心理学等学术领域中均呈增长态势,出现了所谓的“具身转向”(turn to embodiment)。⑨根据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的划分,社会科学中增长的身体研究主要可分为自然主义视角、社会建构视角和结构化理论视角。
自然主义视角的身体研究大多持进化论的观点,强调生理性身体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身体的生物性基础约束着个体行动、社会关系与社会上层结构,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将基因视为解释婚姻等复杂社会行为的核心因素。⑩此外,这一视角的身体研究在性别差异的讨论中尤为突出,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社会位置是由其区别于男性的生理功能(如生育功能)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们利用基因来解释性别差异,认为这种由生理基础导致的分工差异,即使在最平等的社会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主义者要求变革的合理性。
社会建构视角下的身体涉及女性的身体和被权力规训的身体,与自然主义视角的观点相反,其强调社会结构性因素对身体的塑造,身体沦为权力的对象与被动的客体。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女性主义者们对生理性别(sex)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提出批判,身体出现在对色情作品、代孕母亲身体商品化等主题的讨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家们的主要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和性别一样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这种身体观瓦解了男女两性之间的肉身边界,凸显了身体背后不平等的性别与社会关系。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这一视角的代表人物,她提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指出,性别的二分是被文化、社会所建构的,“生理性别”并非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性别及性别认同可以通过身体与行为表演来建构。
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另一种身体是被权力话语规制、调控甚至生产的客体,强调社会结构性因素对身体的约束和决定作用,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下简称福柯)和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以下简称特纳)等人。福柯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探讨了身体与权力的关系,他将身体视为各种权力制度规训下消极顺从的客体,指出了政治和权力运作对身体的奴役,福柯笔下的身体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完全沦为话语建构的产物。特纳则在身体社会学的视域下提出身体秩序理论,他以身体治理为核心关注点,从社会阶级与人口繁衍、人口的空间管束、欲望约束和身体的表演性再现四个维度阐述了社会系统对身体的调控。虽然特纳在关注秩序、控制等问题时比福柯更关注物理态的身体,但相对于社会,身体仍然是在秩序下被“驱使”的对象,缺乏一定的能动性。
结构化理论视角的身体观倡导打破外部结构和能动生命主体间的二元对立,在关注行动的身体基础的同时也关注身体所处的社会背景。结构化理论视角还强调身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一视角的代表学者有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以下简称布尔迪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下简称吉登斯)等。布尔迪厄受庞蒂影响,主张融合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观点,将身体放置于日常经验和实践中来进行考察。布尔迪厄将个体体验和阐述与引发这些的社会条件相结合,认为“身体处在社会世界中,但社会世界也处在身体中。”此外,布尔迪厄提出,不同的“社会场域”具有不同的秩序和规则,生产着居于其中的个体的“惯习”(habitus)。从身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角度来看,个体可以通过身体外观、能力和表现出来的品味获取身体资本,以提升自己在所处场域中的地位。尽管布尔迪厄的理论凸显了身体在当代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具身主体的能动性,但身体同时也与阶级、资本等密不可分,他对商品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强调,使得身体的其他维度在其理论中被边缘化。
吉登斯和布尔迪厄一样,认为身体在受社会结构形塑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他早期的研究关注生理身体对社会行动的约束作用,后期研究则更关注现代性背景下的身体与自我认同。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说明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有机统一又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强调生理身体与物质环境共同作用,对处于其中的行动者施加了限制,身体则为个体提供了与社会联系的基本手段。而在对现代性背景下的身体的阐述中,吉登斯更强调认知层面的反身性(reflexivity)对身体的控制,身体成为自我认同的展示场所与重要工具,其可塑性和展演性的意涵愈发凸显。
与上述领域中身体研究的兴起相似,心理学领域也逐渐开始强调身体的地位,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研究兴起。传统的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独立于身体,并将其视作一种抽象的符号加工装置。20世纪末,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等提倡关注心智的具身性,认为复杂的思维和情绪体验以身体为基础,身体的生理属性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同时,认知、身体和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尽管具身认知研究充分强调了身体基础对认知活动的重要性,但由于其多聚焦个体的认知活动,也容易落入个体主义的困境之中,从而忽略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影响。
可以看到,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身体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身体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领域的学术讨论之中。但可以明显发现,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理论视域下的身体有着不同的定位与内涵,对于何为身体、身体有何作用等问题的回答尚无统一、明确的定论。
三、传播学中的身体研究
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中的身体研究发展,从传播研究史的角度来看,身体问题在传播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度被放逐边缘。以大众传播为主要经验场域的主流传播学将“传播”视为离身性的、纯粹意识主体间的互动和关系构建过程,对传播学发展影响较大的早期美国经验研究大多采用由原因至效果、由刺激到反应的线性模式,强调关注传播主体的意识和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广播、电视等早期媒介技术的发展致力于摆脱基于身体存在的时空限制,身体在此过程中则被视为达到理想传播效果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因此,理性至上的哲学传统和主流传播学去身体化的传播观念,致使身体在传播研究中一度处于缺席状态。
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重构着人们对自身的认知与社会关系的形态。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身体与传播技术的关联愈发紧密,同时也对我们理解媒介技术、身体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这为身体与传播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契机。加之近年来各大社会科学领域中身体研究的复兴,作为媒介哲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身体问题逐渐成为当下传播研究聚焦的重点问题,“具身传播”的概念被频繁提起。
那么,到底什么是“具身”?目前研究者们对于具身(embodiment)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希林将身体定义为“一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现象”,他将身体解读为“社会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认为具身主体具备突生属性和能力(包括使个体能够走路、说话、思考、用技术附加强化自身、改变所处环境的那些特性),这使得具身主体能够在被环境所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环境。刘海龙和束开荣认为,具身立场强调心智、身体及环境三者的一体化。芮必峰和孙爽则将具身定义为“在投入到某活动时,人的身、心、物以及环境无分别地、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以致力于该活动的操持。”
总结来说,具身探讨的是身体、心智和环境三者的互动关系。具身强调身体和心理的非二元性,承认身体所具有的生理特性(如神经机制、感官、情绪等)对人类认知及实践的基础性影响;同时,身体也是社会性的、能动的存在,具身主体在实践中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具身传播,则是在具身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人与媒介的关系,强调媒介实践中具身主体与媒介、技术的交往与互动关系。
当前,多样态的传播媒介已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社交等日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中介。在媒介化生存的背景下,媒介与我们生活的环境和社会深度交融,身体与传播的研究离不开对身体、心智、媒介、环境等多种因素的考察,这要求研究者们不可忽视传播的具身性,应将其视为作为身、心与物质技术高度融合的过程,并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理解具身主体与媒介的互动关系。
四、国内外身体与传播研究现状
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层面,刘国强和韩璐爬梳了国外相关的文献,发现相关成果的关键词主要为传播、情感、感知、行为、知识、认知等,这些相关的研究认为,身体与传播中的“人机关系”经历了计算机作为中介、人机相触、人机交互和人机互嵌四个阶段的主题演进,涉及聋人手语的网络使用、网络性爱、机器人对人类身体语言的模仿、对复杂人类社会行为的感知和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情感互动和深度学习等话题。相关研究总体上以科学技术视角为主,对身体在“人机关系”中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的挖掘还相对有限。
同样,国内的身体与传播研究也保持对“人机关系”的关注,但更突出对身体与传播相关理论资源的关切。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身体与传播问题相关的理论资源梳理、对前沿研究现象的具身性解读及传播中身体研究开展路径的讨论,另一类则是在具身传播的视角下对本土的经验实践展开分析和考察。
(一)身体与传播相关理论资源梳理、前沿现象解读及研究路径探讨研究
刘海龙最早阐述了传播研究中身体缺席的原因,在梳理麦克卢汉、媒介考古学等相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阐明身体问题在当下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后续研究开展的可能路径。在理论资源的借鉴方面,现象学成为目前考察传播与身体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此外,认知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也逐渐丰富。孙玮认为,现象学的“具身化存在”论是当代身体研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理论视角。刘海龙和束开荣也从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出发,将“具身性”概念引入身体与传播研究中并加以分析。此外,也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中的具身传播,进一步拓宽了相关的理论视角。在研究开展路径的探讨方面,芮必峰和孙爽提出应将传播视为身、心和物质技术的高度融合,强调具身传播中人与媒介技术的相互作用。宋美杰也强调将媒介使用当作一种具身实践,视为感官系统与媒介、信息、时空情境的“共舞”,同时,可以将权力与文化、实践与身体结合在一起进行探索。
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新媒介语境下身体相关的前沿现象,如孙玮提出“赛博人”的概念,用以描述人与技术融合的新型主体。在这种情形下,身体本身变成媒介,在接入互联网的过程中,人的感知、行动都成为计算机数据的来源,而这些数据反过来又成为平台分析和规划用户行为的基础,规约着“赛博人”的主体性内涵与技术实践。孙玮还探讨了数字媒介对身体与传播关系的重构,认为智能传播中的虚拟身体以其现实行动能力改变着人原初的主体形态与实践方式。於春则关注人工智能主播的“身体”,从实例出发,在梳理离身与具身认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可能进路。
(二)具身视角下的本土传播实践研究
关于身体与传播研究的具体实践研究涵盖了AI合成主播、可穿戴设备、“网红脸”、手机屏幕和跨境代购者等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在诠释类研究方面,有学者以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为框架对“网红脸”的诞生及流行过程与作为技术具身的AI合成主播展开了理论性的分析。也有学者基于自我民族志,从视觉体验、行为与意义几个方面探析了手机屏幕的具身视觉建构。在实证研究的探索方面,与身体及其传播相关的若干质性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这些研究多采用观察法与访谈法,并借助这些方法来考察某一具体媒介实践中行动者、身体与媒介的互动,着重点在于探究身体在其中的意义。如谢卓潇基于田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考察了香港跨境代购者基于身体的代购活动,阐述了身体的物理属性与符号属性对跨境代购网络塑造的意义。刘国强和蒋效妹在技术现象学的视野下,通过田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考察了“带ID”式的远程合影现象中物理身体“技术缺席”和技术身体“物理到场”的双向投射逻辑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五、数字时代身体与传播研究的可能进路
从以上关于身体与传播的相关梳理可以发现,传播学中的身体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就理论层面而言,在各大社会科学领域发生具身转向的背景下,身体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凸显。而就现实层面而言,从对某一感官进行延伸的媒介形式,到虚拟与现实进一步融合的虚拟现实技术,再到时下正热、倡导人机深度交融的元宇宙,媒介技术发展的核心逻辑越来越强调身体在传播中的地位,愈发注重媒介与身心一体的人类主体的连接与交互。因此,无论从现实趋势或是学术趋势来看,身体与传播的议题在未来都存在较大的研讨空间。
然而,由于相关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目前与之相关的综述类文章十分有限,且缺乏对社会科学中不同身体研究路径的梳理。因此,本文在梳理身体与社会研究基本脉络的基础上观照新媒介语境下的身体与传播研究,对当前身体与传播研究现状展开述评,并对未来研究的发展提出建议,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研究,并为实践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资源与观察视点,对推动当下身体与传播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说,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现有的身体与传播研究。
(一)拓宽身体与传播研究的理论视角
如上所述,现象学、社会学、哲学、性别研究、心理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均对身体问题有所关注,不同领域的身体研究有着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然而,目前国内身体与传播研究的理论视角多集中于现象学,对其它学科的理论资源关注还相对有限。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身体与传播研究而言,从多样化的学科视角中汲取理论资源,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挖掘具身主体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关系,能够进一步丰富数字时代身体与传播研究的可能面向,为理解传播中的身体与身体相关的传播提供更多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二)丰富身体与传播相关的实证研究
从上述身体与传播研究现状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前国外的身体与传播研究缺少对身体在人与社会互动中社会意义的挖掘,而国内的身体与传播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成果集中在对身体与传播问题的既有理论资源梳理、研究开展路径的探寻和对身体实践的初步考察上,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解读,缺乏对数字技术语境下基于身体的传播实践的实证考察。在身体与媒介的融合、交互中,人与人以及人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形态需要深入研究,究其根本,是因为数字时代的具身传播问题回答的是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媒介交互过程中人、物、情、景的交融、人们对身体及主体性的理解等问题的回答都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受到冲击,因此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对此展开更加深入和生动的考察,与理论研究相互印证,进一步激发身体议题在传播实践研究方面的活力。
(三)扩展研究对象
尽管目前身体与传播研究已经覆盖到AI合成主播、可穿戴设备、“网红脸”、手机、手机屏幕、跨境代购实践等多样化的研究对象,但仍存在较大的可扩展空间。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构成要素,身体与媒介在当下的生活中联系着多种多样的媒介实践,随着虚拟现实、脑机接口等新技术的发展及元宇宙等新议题的兴起,身体问题在媒介技术中的重要性会愈发凸显,可从前沿的传播现象及日常的生活实践中汲取灵感,扩展身体与传播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反过来,身体与传播的理论视角也能为理解这些新兴技术现象提供更加具有学理性的洞见。
(四)创新研究方法
目前相关议题的实证研究多采用田野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在身体社会学的视域下,已有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青年学生利用运动APP打卡的现象。未来的研究可尝试采用如网络民族志、网络问卷调查等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进行考察,也可以尝试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范式,不断丰富身体与传播实践研究的考察方式。
注释:
③费多益:《从“无身之心”到“寓心于身”——身体哲学的发展脉络与当代进路》,《哲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④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⑥叶浩生:《“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心理学报》2014年第7期。
⑦杨大春等主编:《梅洛—庞蒂文集(第2卷):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6页。
⑧夏保华:《简论莫斯的技术社会学思想》,《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⑩李拥军:《自私的基因与两性博弈:人类婚姻制度生存机理的生物学解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