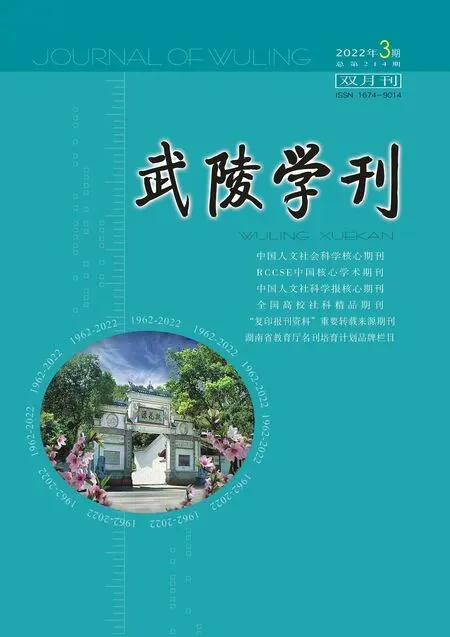论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的继承、悖逆与发展
2022-12-28魏饴
魏 饴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自1978年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的40余年,新诗一开始即走在“改革开放”前沿,出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品,诸如艾青《光的赞歌》、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当时广大人民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新诗界也对以往颂歌基调开始严肃反思。一些青年诗人对诗究竟如何表现和表现什么率先做出了探索,涌现出北岛、顾城、舒婷、食指、牧野等一大批“朦胧诗人”。“朦胧诗”以自我内在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注重在艺术手法上的变革,是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转机;及至“后朦胧诗”时代,新诗在创作上依然表现出继承传统,又敢于悖逆传统,努力创新的特点。
一、对“朦胧诗”论争的反思
“朦胧诗”论争起始于1979年10月公牛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此后臧克家、艾青、郑伯农等一大批老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先后呼应发声。论争一开始仅涉及“朦胧诗”“懂”与“不懂”的问题,随后则围绕“朦胧诗”的特点、性质以及“大我”“小我”的关系等展开学术讨论。1980年5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谢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孙绍振在《诗刊》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下简称“孙绍振文”),都力挺“朦胧诗”的个性张扬和现代写作手法的运用。孙绍振文的编者按指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在前一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个引导性的按语非同寻常,论争双方的平衡地位开始被打破。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诗刊》上,便有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李准《理论讨论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和明确性》、宋垒《难“自我形象论”》等若干文章对孙绍振文进行了“一边倒”的批评。《诗刊》所发起的这场讨论也得到了各地省级报刊的积极响应。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刊出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开宗明义指出1980年的新诗是带有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该文与前述谢冕、孙绍振文章通常被人称为“三个崛起”。自此,围绕“朦胧诗”及其“三个崛起”的论争就更加白热化,“三个崛起”还被视作诗歌界放弃“二为”方向的典型而遭到批评。“朦胧诗”作品也常因让人看不懂,而被质疑其服务功能。直到徐敬亚1984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这场论争才算基本消声。
“朦胧诗”论争虽然过去了,但新诗创作的相关探索并没有停止。上世纪末,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朦胧诗人仍在《诗刊》等报刊上发表新作品,直到“第三代”诗人兴起。今天,我们再看“朦胧诗”的那些代表作,诸如北岛《回答》、顾城《远和近》、江河《星星变奏曲》、杨炼《瞬间》、舒婷《致橡树》等,觉得它们已经并不那么难懂了。“朦胧诗”创新手法的探索在“第三代”“后第三代”或“新生代”的新诗创作中在延续,仍在对传统进行继承与创新,并获得了发展。
客观而言,围绕“朦胧诗”的论争是我国新时期开启之初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自觉的甚至是必然的事件。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文革十年”,人们已经习惯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对诗歌能不能或如何表现作者“心灵中的秘密”提出异议非常自然。特别是,当年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当口,文坛也显迷乱,围绕“朦胧诗”论争的双方均有些情绪化或偏激。
“朦胧诗”论争的根本症结,从大处看是关于“人民的诗歌”与“人的诗歌”,或“大我”与“小我”的关系问题;从小处看则是如何正确看待“诗与非诗、含蓄与晦涩、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譬如“三个崛起”论者将“大我”与“小我”做了不恰当的对立,甚至主张“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和60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1]。正是这个关于“大我”与“小我”关系的错误解读,也直接导致《诗刊》编辑部对于孙绍振文关于“二为”方向的质疑。再者,“三个崛起”论者谈到中国新诗发展时,秉持以西方为中心的单边主义思维,甚至说新诗“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做斗争”“更侧重于继承其他民族的习惯”[1]。这里所谓“传统的艺术习惯”,实际是将过去“红歌模式习惯”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传统混同。然而,“三个崛起”对中国新时期初期新诗美学的健康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朦胧诗”作者质疑政治体制和文学观念,在创作上敢于针砭社会丑恶、关心国家大事,与“三个崛起”对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不无关系。
从“朦胧诗”创作本身看,其功绩总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它改写了“文革十年”诗歌一味图解政策的宣传模式,进而表现出由非我向自我、非人向人回归的趋势;二是“朦胧诗”作者的大胆创作实践体现了其融入世界现代派诗歌大潮的迫切期望,在一定层面也代表了回归诗歌艺术本身的趋势。“朦胧诗”作者在“诗与非诗、含蓄与晦涩、传统与现代”等创作理念实践上为“后朦胧诗”时代的新诗创作奠定了较好基础。
二、“后朦胧诗”时期新诗继承创新的几个倾向
新时期新诗是以“朦胧诗”的革新面貌发端,“后朦胧诗”时期即上世纪末至21世纪前20余年,新诗的发展依然面临继承与创新两大任务。这些年尽管泥沙俱下,但新诗创作还是体现出继承传统、悖逆创新、改革奋进的繁荣格局。
首先,从传统上看,“诗最初起源于祈求丰收的祷词”[2]386。《礼记·郊特性》保留有伊耆氏祭祀万物诸神的古诗:“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3]正突出反映了广大原始先民为过上平安、顺遂的生活,希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愿望。显然,诗中“大我”与“小我”从一开始就融为一体。自“朦胧诗”开始,新诗在传统继承上则更倾向于从“小我”角度表达对“大我”思考。
今日之诗坛,张静雯写诗热衷于“小我”,甚至有意要把这种情调写得迷离,其诗充满了有如嚼橄榄的回甘味儿。她在《意义》中表白:“没有任何意义,我写诗/就像云已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将一部分自己/变成雨落了下来……/雨可能并不在乎被赋予意义。”[4]江非也希望自己的诗应是“阳春白雪”:“我不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读到它/读诗的夜晚/总是过于/陌生和漆黑。”[5]“后朦胧诗”时代,这种“迷离诗”差不多已成为不少诗人的追求。类似的诗歌还有:叶来《纯棉》(《诗刊》2016年 9月号下)、李云《切片》(《诗林》2019年第6期)、王学芯《一串旧钥匙》(《人民文学》2020年第7期)、剑男《空椅子》(《十月》2020年第4期)等。这些作品总是善于借用形象,比如《一串旧钥匙》:
短链上一串旧钥匙
经过很长年份被牛皮纸的信封想起
斜着抖落出来的锈屑和声响
散在掌心 变成
临时居室里的杂沓之物
随身在心的门 出售了旧宅
从没富足的生活滑过大多数日子
仅存的想念 围坐一起碰到的脚和呼吸
四处走散 各自偏倚的姿态
成为狭窄的光中
暗黑的一枝花朵
钥匙留下一串大的疑怆问号
没有紊乱的齿,有着任何一种凌厉
尖的 锋利的
悬立的嶙峋
在空槽之上 期望多于一个人的锁孔
丢下的凝视 倾听或意义的毫无意义
也许因为老了 也许因为
隔绝了一扇消失的门
从“在空槽之上期望多于一个人的锁孔”看,这串旧钥匙的主人是在对一个若干年前曾同居过的伴侣表达思念与“疑怆”吗?为何“四处走散、各自偏倚”?旧钥匙“悬立的嶙峋”是暗示着他们相处不易?唯有“丢下的凝视”,但至今“因为老了”已“毫无意义”。该诗内容是朦胧迷离的,但从诗末的两个“也许”看,或许表达了诗人期待突破“老了”与“隔绝的门”形成的障碍。
其次,在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诗人大都喜好思辨,着力于用诗来表达对生活的哲学认知。这不仅悖逆毋以诗说理的传统理念,更成为当下新诗坛一种大致共同的价值取向,创作出不少颇有特色的“奥理诗”。以《空》为例:
蝉鸣不是空。蛇蜕不是空
山谷的回声不是空
午后的街头,少妇裙摆下的饥饿不是空
光、灰尘和欲望飞流直下
鳄鱼的皮囊不是空
我站在无聊的人群中间,无所事事
我的目光散淡,世界空空如也
自由如此琐碎,鸡毛飞了一地
大藏而不露,小暴露无遗[6]
客观上的“空”和主观上的“空”前后虚实对照,暗含丰富哲理,甚至颠覆了“藏而不露”的智慧。尽管以议论入诗是一大忌讳,但“奥理诗”以饱含情感的意象、思辨的逻辑来理解世界,进而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理性思考。
诗人江非甚至说:“哲学才是我真正看重的东西,文字是在表达我的哲学,求证其努力罢了。”[7]2020年第3卷《草堂》还发表了他的《生活》《山居》等多篇“奥理诗”。周钰淇的《光明学概论》又为“奥理诗”别一格调,该诗引入“统计学”术语,诸如“线性相关”“假设检验”等,更增强了诗的陌生感:
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抛下远山
穿过密林小跑进入橙色的夕阳
与黄昏呈线性相关。
在乡村图书馆查阅过许多文献:
蒙尘的旧事
以很重很重的口吻拉开窗帘:历史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难免落枕。歪着脖子面对雨的参差。
文献却并未告诉他:城市交杂着
模糊的偏值和峰度。
于是他设想当窄门打开
能够抵达光明草地。
飞快地,假设检验分析出结果:
屋里布艺沙发凹陷进去的部分
是城市深处难得平坦的乡村
只有到那时
城市的雨才能和乡村的躯干
呈现朦胧柔和微弱的
标准正态分布[8]
“光明学”“概论”均是学理用词,诗歌探讨“光明学”又始终贯穿诗意描写。从学理看,“线性相关”是指含有相同向量的向量组必然关联;“峰度”在统计学中常用来检验峰态偏离正态分布时的正态量;“假设检验”是带有某种“小概率事件”原理的反证法。从诗艺看,作者娴熟地将诗意的抒写与“峰度”之类专业术语糅合在一起,其诗艺论说颇为新奇,表达了作者迫切期望缩小城乡差距和“抵达光明草地”的心情。这首诗融入了学理元素,以审美陌生化挑战读者,当是诗歌美学的新发展。
再次,与推崇诗行精短的传统审美不同,15字左右乃至几十字的“长句诗”同样形成了当下新诗一道令人关注的风景线。这类诗歌长短参差,以质朴的语言表现生活的诗意美,比如王厚朴的《川既漾》:
江水缓如平镜,最先有了动静的是岸边的蒿草、芦苇
——这么说来,应是风了
……
爱过的事物,让我撞尽了南墙——这话,我引为戒条
回想过往:
我曾对着不遵医嘱的母亲摔碎杯子,骂她老糊涂了
过后,久久捶胸自责
我曾训斥父亲在老年变得邋遢,把饭粒、菜蔬洒落身上
是窝囊废,又在江南想他,哭泣
我曾对着一个女人许诺,此生非她不娶,绝不负她
——后又弃她而去
多年后,造物把我失去的那些高高悬起,星辰一样
赐我柔然,绵延
就像,就像整个下午我对面微漾的江水
可不可以说
最先有了动静的不是吹过的风,不是我眼,是夕光将尽
我心生悔意,垂怜万物[9]
诗句短者4字,长者22字。作者短吟长歌,在较为平静、优雅的情调中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反思、悔恨和领悟,并通过“川既漾”用典,说明漫漫人生路必须把控好自己的选择和行为。
再如路攸宁《破碎》(19字,以单行字数最多者计,下同;《星星》2018年9月上)、白玛《冬天的菜市场》(24字,《诗刊》2018年4月下)、赵柏田《梵高同题:春天的果园》(28字,《江南诗》2021年第2期)、邹静之《春天》(30字,《安徽文学》2020年第9期)、吉狄马加《裂开的星球》(35字,《十月》2020年第4期)。在《裂开的星球》中,作者从人类的前途与哲学层面审视新冠肺炎疫情:
哦!文明与进步。发展或倒退。加法和减法。
——这是一个裂开的星球!
诗于中部点题照应,承上启下,再用32个“在这里”排比段写人类在不同地域,采用不同手段对星球的破坏与不敬:
……
在这里马克思的思想还在变成具体的行动,但华尔街却更愿意与学术精英们合谋,
把这个犹太人仅仅说成是某一个学术领域的领袖。
……
在这里所谓有关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争论肯定不是种族的差异。
因疫情带来的隔离、封城和紧急状态并非是为了暧昧的大多数。
……
最后诗人直面地球问题大声呼号:“我们没有权利无休止地剥夺这个地球/……善待自然吧/善待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请记住!/善待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要么万劫不复。”
全诗充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患意识,长达528行,尽显长歌当哭的抒情意味。
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创作的基本认识
围绕“朦胧诗”的论争可谓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再一次登场。虽然,“后朦胧诗”尚在探索中,诗坛还混杂着非诗因素,甚至使人产生一种每况愈下之感,这当是时代的斑驳陆离对新诗创作的投影,但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创作总体上仍然值得我们好好评价。
(一)新诗表达中的“大我”“小我”并不矛盾
我们对诗歌“大我”“小我”之关系及当下新诗自我表达的根本态度是反对以强调诗歌个性化写作而否定对“大我”的张扬,反对就诗歌“大我”的机械化理解而否定作者对生活富有个性化的表达。
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说:“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10]作为诗人,写什么是个人选择,但好诗须具备以上“三来”,也就是声律风骨兼备。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不可思议的。”[11]诗人不可能离开“大我”,然而写诗又贵在“有我”,“大我”“小我”的具体身份意识无法回避。问题也正在这里,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未能深入掌握“大我”“小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区别。
近代以前的“大我”主要与家族亲缘及其出生地连在一起;近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大我”的认同明显趋于抽象化,更强调国家、民族、阶级等概念;进入新时期后,尤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大我”内涵则转向以人民为中心,自觉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并反映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明乎此,过去有人批评《致橡树》爱情观不符合传统就显得狭隘、片面。当下,我们既需要《裂开的星球》这样一类政治抒情诗,同样也需要作者的自我表达,哪怕是基于自己较为狭窄的生活经验。“小我”首先都是自然人,基于具体身份的人生诉求在不同时期出现变化完全正常。
2014年11月《诗刊》微信号推出组诗“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其作者余秀华就是善于抒写“小我”的诗人。她在《离婚证》中写道:“一叠新翠,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12]诗中的“新翠”指身份证、离婚证,它们“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无时不在等待“开启的门”,反映了作者基本的生活欲望。诗人接着描述离婚后的感受:“36岁,我平安落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12]约20年的婚姻终于解除,诗人在现实困境中经历了煎熬,终于获得解脱。诗人接着说,生活中“身份证我总是用到”,而离婚证却“比身份证显眼呢”。“离婚证有什么用呢?”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心灵拷问后,以“我不再结婚,从此独身”结束全诗[12]。诗人对婚姻的决绝态度,引发了读者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更是提醒世人在婚姻问题上需要更加审慎。
(二)新诗借助意象抒情给人以整体美感
当年,“朦胧诗”的出现使得“诗与非诗”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究竟诗者为何?西方诗人又如何理解诗?《不列颠百科全书》特借两位西方诗人的话来解释“诗”:“法国诗人瓦莱里说,散文是行走的,诗是舞蹈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诗是用散文解释之后,尚有待解释者则须由诗来完成。”[2]386该书编者认为“这是诗的最近乎精确的定义了”[2]386。该定义说明了两点:第一,诗歌并非像散文一样以写人和事为主要目的,而重在散文解释之后的抒情取向;第二,诗是“舞蹈”,意在强调诗的整体构思及其意境营造,正如舞者和舞蹈是不可分的,诗也需要从整体上去理解情调。西方学者认为,抒情是诗歌创作之目的,而意境则是诗歌存在的基本形式,将抒情与意境联系起来认识诗歌本质的视角颇有审美眼光。
在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往往是将诗的意境美、抒情美、含蓄美等分而观之,有时难免也会顾此失彼。譬如关于“朦胧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其核心是怎样理解诗歌的意境美。从诗艺而言,诗歌意境美又取决于“意”与“境”或主观与客观之结合,二者结合得愈自然、愈和谐,意境就愈美。意境美往往是朦胧的,甚至是迷离的。迷离比朦胧更加含蓄,但只要不晦涩,能让人可赏可玩,也是具有美感的好诗。
诗是“舞蹈”,不只揭示出诗的最大美学特征,更告诉我们诗歌应如何抒情。诗的抒情美就在于借助一定的意象或意境来表达人类的苦痛,或者激起人生的斗志。洛夫的长诗《漂木》曾于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另有一首《因为风的缘故》也颇有特色。全诗分为两小节,第一小节写“我”“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为何?诗人只说“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以此表明“因为风的缘故”,“我”对远方伊人的思念未变。第二小节,诗人表达了需要珍惜当下、享受美好的迫切感。人生犹如“雏菊”短暂,诗人一连用三个“赶快”,其珍惜情愫进一步迸发:
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
赶快发怒,或者发笑
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
然后以整生的爱
点燃一盏灯
我是火
随时可能熄灭
因为风的缘故[13]
全诗隐喻自然。“因为风的缘故”在诗中反复出现三次,表明诗人对自然规律、人生理想以及男女爱情的坚守。
(三)新诗离不开奥理哲思
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里说过,诗所表现的是普遍,历史记载的是个别,诗应比历史更富哲思。古人所谓“诗言志”以及后来的“致用说”,均已包含诗文不失言理的内涵。当下“奥理诗”之兴起,一方面与学科门类划分细密以及知识发展日新月异有关,新增的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与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有很大关系。在这样一个追梦时代,诗人就应在创作中承担起揭示普遍的责任,从而让读者悟出一般,获得理性的启迪。
首先,“奥理诗”必须是诗,仍然当以抒情为本,当下新诗在这方面还显不足。其次,要注重提升说理的艺术水平。古人所谓“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14],既指出诗与理的密切关系,又暗示在诗中说理并非易事。在这方面,近几年的新诗也有较好的探索。《一串旧钥匙》《空椅子》等,就近取譬,用据事说理的方式,达到意境融洽的目的,耐人玩味;《光明学概论》,借《统计学》形而上之“道”入诗说理,其思路新颖、奇特。
(四)长句慢歌体是最自然的新诗表达形式
中国诗歌发展史中,从诗经、楚辞、汉代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直至近代以来的白话诗(新诗),无一不是在诗歌体式上不断创新。概而观之,诗歌句式不外齐言与杂言。除了格律诗是齐言诗外,其余诗体都是长短错综的杂言句式。
习惯上,新诗分为“格律诗、半格律诗与自由诗”三种。所谓格律,即诗歌广义上的结构方式,偏重于句式、节奏式、韵式、段式等。凡是诗就一定有区别于散文的地方,或多或少在句式、节奏、韵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格律形式,只是新诗相对宽松而已。
从新诗发展看,新时期以来自由诗实际已形成短句亢奋、杂言适意和长句慢歌三种体式。短句亢奋和杂言适意体古已有之,前者如曹丕《燕歌行》、李白《将进酒》,后者如李白《蜀道难》、杜甫《兵车行》等,均是古风或歌行体。长句慢歌体随着白话的广泛使用,逐渐成为反映目前全球“慢生活”理念背景下社会生活的最自然诗体。
长句慢歌体新诗,其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慢歌”中的“慢”并非指写得拖沓,而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味追求功利却忽视生活意义的深入反思。七字左右的短句诗,每句三至五顿,较宜抒发亢奋之情,而十一字以上的长句诗,大多在六顿以上,适宜发出舒缓、理性之声。长句慢歌体可根据抒情强弱和语词节奏间以适量短句,其篇幅或长或短。短者如商禽《长颈鹿》,全诗也就两个长句,以“脖子”和“长颈鹿”展开叙述[15];至于长者,暗合诵读的韵律,具有舒缓和韵味绵绵的特点。第二,长句慢歌体非常适合表现人类生老病死、爱离别怨的永恒主题以及热门政治话题。如路攸宁的《破碎》,描写了一个经历不幸婚姻的女人的前半生:“四十多岁,她已拥有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旧时光/远嫁,男人出轨,离婚,独自养育孩子。”不幸的女人虽然“积满了混浊的岁月”“尽管腰肢不再纤细,但她仍旧将自己/塞进了一条新买的裙子里。”女人虽然一生坎坷,但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追求。第三,长句慢歌体注重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增强诗歌的抒情美。诗歌和音乐可谓是最适合抒情的文艺样式,诗因兼具文学与音乐的特点,所以是最理想、最具表现力的抒情方式。诗歌用文字抒写真实的生活打动读者,用节奏韵律的变化营造氛围感化受众,长句慢歌体尤其以丰富的排比、反复、联珠等表现手段在抒情效果上显得更突出。
(五)诗歌创新需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诗歌几千年来所表现出的美学倾向有抒情言志、精炼含蓄、意格为先、利于吟诵。将诗写得完全不具备诗歌应有的样式,实际上这已是诗的一个隐秘向度。尽管诗在语言艺术上最为灵活,总是保持着一种野蛮的活力,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始终得保持其诗性品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下我们正“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16],新诗题材内容将更倾向于生活化,对生命、生活、区域、民族的关注将是“大我”的基本主题。与以往单一的发表载体不同,互联网普及已让“网络诗歌”无处不在,新媒体、自媒体出现更将诗歌推向一个全新的生态,新诗大众化已悄然成为文学史上的辉煌图景。诗歌美学于新时期初期唯西方是尊的局面不复存在,它会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符合本土实际,更加代表广大民众的审美追求。新诗大众化可能导致整体审美趣味的降低,比如新诗的无韵化倾向、散文化倾向等,各级各类学校、各级文联和作协组织要确保诗性品质不变。新诗在继承诗学传统并保持创新的过程中,生产出更多优秀的新诗作品,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