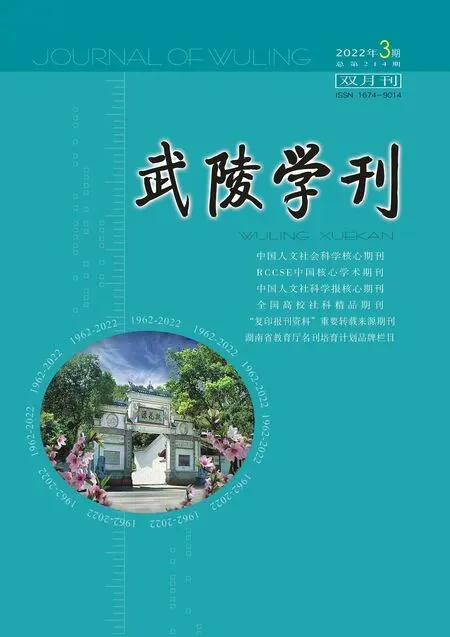论华语及其研究的历时观
2022-12-28刁晏斌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一、华语的共时与历时
提出语言的共时与历时,以及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重大贡献之一,从此以后,现代的语言研究基本就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所谓共时,是指语言发展某一阶段的情况,而历时则是指语言演变、发展的过程。所谓共时研究,就是对整个语言系统或语言的某个结构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状态的研究,而历时的研究是对某些语言事实以及整个语言系统历史发展的研究。简而言之,共时是横切面,历时是纵剖面[1]161,259-260。
时下,“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具体到某些方面,往往却并不均衡。比如华语研究,偏于共时而弱于历时的表现就非常明显。对于一个开始及持续时间还很短的研究领域而言①,这或许有其必然性及合理性,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必然会有碍其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华语研究的历时观与历时研究加以强调。
其实,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与此相关的一般性表述。比如,李如龙指出:“海外形成华人的通语——华语,是后来的事。大体和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开展是同步的。”[2]这是就华语“前端”所作的简略阐述,而以下的论述则更加具体:“所谓的‘华语’是到了20世纪才在新马慢慢出现的。新马先辈怀着浓重的方言背景来学习1919年的北方话,他们所习得的这种‘方言式华语’兼‘1919年华语’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因而让新马的华语既带有‘方言味’,也带有1919年北方话(尤其是书面语)的‘古早味’,再加上是多语环境,于是形成有异于中国现代普通话的‘新马华语’”。[3]以上是从“认识”的角度所作的表述,从“研究”的角度,邱克威认为,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除了共时层面的比较异同,还应该追溯历时脉络探索其形成过程[4],而姚德怀更是直接提出应进行近百年来华语演变过程的研究,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归根结柢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5]。
2015年,笔者讨论了华语的历史基础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传统国语(即上世纪前半叶的汉民族共同语)与当今的海外华语、台港澳国语和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之间,具有派生关系,即后者都是前者的地域/社区变体,至于普通话与华语/国语之间,则没有这种派生关系。所以,如果着眼于历史源流,我们显然不能认同“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这样的华语定义,而如果改为“以传统国语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则是可以接受的[6]。
2017年,笔者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全球华语有其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其背后则有很强的规律性和丰富的理论内涵,由此提出了“全球华语史”的概念[7];而在次年出版的《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一书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系统梳理与阐述[8]130-208。
就目前所见,与历时相关的相对比较具体的表述,多是着眼于华语、早期国语与当今普通话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比如,周清海指出:“1949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9]这里的一“多”一“少”,一方面使得华语与早期国语保持了更高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使之与普通话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周清海进一步就此举例说明:(香港报纸)独用的“称”(述说),“逾”(超过),“遂”(就,於是),“故”(因此),甚至“人妖”“吊诡”等词都见于1936年出版的《国语辞典》。这些词,新加坡和其他华语区也用,都是“国语”现象的存留[10]。
也有一些表述是针对某一地区的华语而言,比如黄华迎指出:“由于远离中国大陆,加上两地语言多年隔绝的关系,马来西亚华语并没有跟上中国汉语标准语的发展变化,一些在汉语标准语己经不常用的古语词,在马来西亚却沿用至今。”[11]贾益民、许迎春以新加坡《联合申报》2005年全年报纸为语料,找到116例前人未研究过的与普通话表达内容相同或相近但形式不同的词语,在对这些词语的来源分析中,列出了“旧词语取舍不同”一项,即华语仍然使用而普通话已经放弃使用的词语,如“窗扉—窗户、攫夺—抢夺、状—公文、女佣—(女)保姆、丕变—大变、食阁—小吃店、堂费—诉讼费、庭令—判决书”等[12]。施春宏调查了“泰式华文”的用词特征,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普通话,泰式华文词语的“历史”色彩较浓。这首先表现在其字义或词义显得比普通话要“古旧”一些,即文言色彩明显。泰式华文词语“历史”色彩较浓的更为显著标志是,一些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被看作历史词或准历史词(即在特定表达中偶有使用)的词语,在泰式华文中的使用仍比较普遍。文中列举了“庶民、冠盖、矢言、墟日、京畿、苦主”等,来作为具体的证明[13]。
对于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李计伟、张翠玲从传承语的保守性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所谓“保守”,其实是因为传承语使用者对祖籍国所发生的一切不那么敏感了,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当祖籍国语言发生变化之后,远离故土的传承语使用者依然保守着之前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并将之传给下一代[14]。
以上讨论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华语言语社区,但得出的却是具有共同性的结论,即相较于普通话,东南亚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具有更高的一致性与相似度,这一点在词汇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
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角度,我们的认识是,华语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就后者而言,大致包含以下内涵:
第一,东南亚华语来自20世纪初中国的早期国语,即当时的全民通用语,是后者的域外变体,因此二者之间保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当然前者也有因处于特定社会及语言环境下而产生的发展变化。
第二,华语有其不同于早期国语的另一变体即普通话的发展历程,并由此而与后者形成了同中有异的关系。就“同”的方面而言,当然是由于二者有共同来源;就“异”的方面来说,则是二者不同历时发展过程的反映和表现。
第三,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牵拉与推动,百年来的华语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应该而且能够对其进行历时发展演变的研究。
然而,以上三点目前对不少人而言并不是特别明确,远未成为共识,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少有反映,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对华语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由此入手,来分析由于历时视角与立场的缺失而对华语研究所造成的影响,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从而把华语研究引向深入。
二、华语历时研究检视:基于一项已有研究的调查
在上述“历时观”下,我们来看当今的华语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做出改进。为了使以下的讨论能够建立在比较具体的事实基础上,我们以已有的一项研究为例,即赵敏的《马来西亚华语“者”缀词语的变异性考察》。文章刊于《汉语学报》2018年第3期(以下简称“赵文”)。
赵文开篇指出:“本文基于语料库数据,以‘者’缀为例,探讨马来西亚华语词缀的变异性,并对相关现象进行解释。”总体而言,文章条理清晰,事实充分,分析也比较到位,如果按时下比较普遍的华语观及其研究模式衡量,是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然而,如果考虑历时的因素,赵文就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不足,以下就此进行说明与讨论。
赵文的基本作法是,立足于并仅限于共时平面,对“者”缀进行描写和解释,而我们的作法则是以早期国语“者”的使用情况为参照,来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由此来弥补赵文的不足,并获得新的认识。下面以赵文的主要内容为线索,分别进行考察。
(一)关于“业者”
赵文第二节的标题为“‘业者’的变异性”,指出马来西亚华语的“业者”已经成词,而“X业者”的使用非常宽泛,例如“电讯公司业者、摩多店业者、航空业者、印刷厂业者、房地产业者、种植业者、美容院业者、餐馆业者、假村业者、旅游业者、德士业者、驾驶中心业者、茶水档业者、饮食业者、工厂业者、养鱼业者、捕鱼业者、小贩业者、咖啡店业者”等。文中指出,马来西亚华语中,凡做生意的人都可以用“业者”来表达,其所指非常复杂,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营业者、经营者、投资者、企业家、公司老板、经销商、批发商、商贩、个体户、服务员、工作人员”等,此外,“业者”还可以指公司、企业、行业等。
赵文所说的以上情况,在早期国语中也普遍存在,比如仅在《申报》上世纪20年代之前的报纸上,就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卖药业者、贸易业者、旅馆业者、贩盐业者、制盐业者、制糖业者、牲畜业者、生产业者、印刷业者、钢铁业者、手工业者、海运业者、职业媒介业者、棉业者、钱业者。”②以下举几个实际的用例:
(1)政府于边境征收此税,既为国家增加收入,又以保护工商业者,此所以保护贸易主义也。(《新青年》,1915年第1卷1号)
(2)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
另外,赵文还列举了几个“业者”独立使用的例子,其实这也是早期国语中已经存在的用法,例如:
(3)吾国茶产蔓延十余省,业者皆散商,茶名至杂,多以千计。(《申报》,1923年11月11日)
(4)欧战期内,汽车为极广,树胶之价,因之飞涨,每磅售英金四先令,业者莫不利市百倍。(《申报》,1923年11月6日)
其他媒体的用例再如:
(5)最近耸敦(按即伦敦)即有四分之一劳动者失业的事。这种责任是谁负的呢?不是业者本身应该负的,是社会制度应该负的。(《先驱》,1923年1月9日)
对于上述现象,赵文的结论是,“马来西亚华语里的‘业者’由于高频使用,因而发生了词汇化和语义扩展现象”。这一结论值得商榷,以下一例提供了相关线索:
(6)东京电,全国莫大小业者(织造汗衫线袜等业)协议会今日开会,议决同业联合会创立大会定于来月五日十日之间在农商务省开会。(《申报》,1917年10月22日)
这一用例把“业者”的来源指向了日本,查日语中确有“業者”一词,《广辞苑》第6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重印本)的释义是“1.商工業者を営む人(经营工商业的人),営業者,企業者;2.同業者。”另外,日语中“X業者”的组合形式也比较常见,既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集体,如“商工業者、文房具業者、不動産業者、悪質業者”等。再如,“MOJi辞书”(一个中国日语学习者常用的辞典App)也列出了以下一些(括号中是汉语释义):“出版业者(出版社)、制造业者(生产厂家)、旅行业者(旅行社)、建筑业者(建筑工人)、仲介业者(中间人)、斡旋业者(交涉人)。”③
以下一例似乎就有比较明显的日语背景:
(7)所有金矿之采掘权虽有不让渡于民间之规定,然拟为该新会社特权新例,付与此项采掘会社,得使信用可靠之一般民间业者采掘。(《日本劫夺东三省各种重要事业》,载《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2)》1934年)
通过以上信息,再结合清末民初中日语言交流以“引进”为主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业者”以及“X业者”系早期国语由日语引进,而马来西亚华语则是延续早期国语用法,另外在此基础上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
(二)关于“有者”
赵文第三节的标题为“‘有者’的变异性”,列举了一组诸如“收集黑胶唱片的人其实很复杂,有者只买不卖,有些是买来炒”这样的用例,指出其“有者”可以解释为“有的人”。赵文对这一形式追溯到中古时期的汉语,列出以下一例:
(8)佛诸弟子中,有者双足越坑,有者聆筝起舞,有者身埋粪壤,有者呵骂河神。(《续传灯录》)
其实,“有者”的这种用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早期国语中似乎还要稍微常用一些。比如,以下是《申报》1911年10月24日所刊一则“新发明秘制美髯卫生枪上戒烟膏”广告的片断:“成瘾之人,岂不竭思戒除?有者身体素弱,有者戒志不坚……”。二十多年后,该报刊登的戒烟广告仍然用到上述形式:
(9)鸦片红丸之毒,害人不浅,然吸者何尝不想戒除?因有者被工作所困,有者被经济所缚。今本院以最低廉之费用,又以最和善之方法戒除,故无论走戒住戒,均可照常工作而毫无痛苦发生,有此癖者,盍速来乎!(《申报》1933年3月23日)
其他方面的用例再如:
(10)(我国各地之地史后期地层)在其他各地,发育甚佳,为红色土之一部,而在周口店本地,有者为上新统下或中部之堆积,有者为可与泥河湾相比之堆积,有者亦可列为下更新统而年代较周口店猿人产地较老之堆积,有者则比猿人产地年代较新之上洞。(杨钟健《中国新生代地质及脊椎古生物学之现在基础》,载《地质评论》1942年第7期)
此例显示,“有者”的所指并不仅限于人,所以上引赵文所说义同“有的人”可能不够准确,比较准确的含义当为“有的”④。
我们甚至还在当代人的著述中看到同样的形式,似乎是“复旧”的表现,例如:
(11)(人们)认识到相火非一脏所主,有者以肝肾主相火,有者以包络主相火,有者以命门主相火,有者以三焦主相火,有者以脾主相火,还有的说相火的重点在“位”。凡有部位的器官组织应该皆主相火,众说不一,如何统一认识呢?(张华山《中医学秘里求真》,中医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此例中,“(还)有的”与前边的几个“有者”相对,意义相同,正可以证明我们以上所说。
(三)关于其他形式
另外,赵文还指出,马来西亚华语“死者”的用法更加宽泛,可以前加修饰语,例如“男死者、女死者、男女死者、小死者”等,普通话没有这样的表达;有些“者”缀词语虽然低频,但是很有特色,如“为夫者、为妻者、坐者”等,这些词语在普通话里是不用的;普通话一般场合下不说“评者、讲者、重者”,但是在马来西亚华语里它们都能使用。
以上“低频”及“特色”,实际指向的是马来西亚华语中“者”常用于临时性的组合之中,而普通话“不用”或“一般场合下不说”,也与此密切相关,即通常不在临时组合中使用。其实,这一点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国语“者”的使用特点,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整齐的对应性。比如,我们仅在民国时期的一小部分语料中,就看到了以下一些现在普通话中基本不用的形式⑤:全熟者、握有权利者、聋哑者、痛苦者、自私自利者、大多数者、体力强壮者、继承者、反对者、同年龄者、愚昧无知者、代表者、不可缺者、同调者、发号施令者、新者、旧者、犯罪者、暴富者、管理家务者、主持家务者、服侍者、享用者、供给者、经营此业者、有政府执照者、继起者、有瘾者、广义者、谋国者、谦逊而服从者、不平等者、罹中风者、崇拜者、劳作者、垄断者。
仅就以上赵文所举各例而言,几乎都能在早期国语中找到相同的形式。例如,《小说新报》1922年7月号所刊侦探小说《新婚惨案》中就有“女死者”,而《世界日报副刊》1927年第18期则刊登了吴伯箫的《寄给一个小死者》。以下再就其他形式略举数例:
(12)吾国所谓德教,固有迫人使不得自立者,三纲为德教之根源,为君者奴其臣,为父者奴其子,为夫者奴其妻,臣子与妻既无自主之余地,而列入奴籍矣。(《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
(13)在巴列人中,为妻者留伴他的父母,至产生孩子时为止。(《晨报副刊》1921年12月26日)
(14)旧法过重形式,学生作业,往往潦草塞责。全班学生所回讲的,都是前日所听通的相同的材料,讲者和听者都不能发生兴味。(《晨报副刊》1925年8月19日)
(15)因此,新五代史记一书,评者以为“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端是不甚经意。”(《晨报副刊》1925年8月19日)
总之,经由以上简单的对比,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马来西亚华语中,“者”的用法与早期国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其与普通话的诸多差异,并非由高频使用下的词汇化和语义扩展造成,而是对早期国语的传承。
三、华语研究历时观的构建
(一)历时观的缺失:当代华语研究的一个普遍模式
上一节中,我们结合赵文对其所讨论的马来西亚华语中“者”缀的变异性表现进行了溯源,其实赵文基本代表了当下华语共时研究一种比较普遍的模式,简言之就是在历时观缺失的情况下进行华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对比研究。以下我们再以另外一项研究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王彩云《马来西亚华语介词的变异》(刊于《汉语学报》2015年第2期,下简称“王文”)也是一篇事实充分、从内容安排到分析过程都堪称中规中矩的论文,文章着眼于马来西亚华语介词与普通话的差异,从使用频率和使用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统计、描写与分析,在后一方面主要讨论了“从、往、往着、向、自、自从、在、把、对、比”等介词的独特用法,认为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华语介词变异的重要表现。以下,我们就从这些表现中选取若干个点,重复以上的操作,即对其在早期国语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王文指出,“往着”是马来西亚华语特有的介词,普通话中没有,但是在早期国语中,却不乏用例,如:
(16)全体二十五位同学,皆兴高采烈的,抱着埋头苦干的精神,勇敢地往着我们目的地进行。(《申报》,1936年8月11日)
(17)正当危急万分的当儿,有一个童子,听见了可异的“悉索”声,往着眼子里探望。(《申报》,1939年1月9日)
王文还指出,马来西亚华语介词“向”位于动词后表方向时,谓语动词所受的限制小于普通话,因此像“袭、割、抓、示、撞、踢、攻、啄、掠”等动词都可以与“向”组合,而普通话不能这样用。其实,与“往着”一样,上述动词与“向”共现的用例多数在早期国语中都能见到,以下是一组《申报》的用例:
(18)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自然而然的袭向人来。(1933年12月5日)
(19)日俄贸易最近颇示向满足之进展,过去六个月间之对俄输出为四百五十万元,俄国之对日输出为八百万元。(1927年6月3日)
(20)他夫人见了,怒的像什么似的,随手举起一根司的克就向阿灵乱打,阿灵向外狂奔,劈头撞向汉麦先生身上,几乎给他跌了一交。(1923年6月3日)
(21)他的鞋儿脱卸在出入要道,出入的人不知不觉的你一踢我一蹴,鞋儿便失了原有的位置,一只踢向东面十余步,一只蹴向西面八九步。(1921年6月11日)
(22)(我方)攻击第七架敌机,继之攻向第八架敌机,但见该两架敌机悉是引擎处吐出黑烟,尾随于敌机编队后方向云中进去。(1944年11月21日)
(23)风掠向河面和沙原,静静躺着的大地在阳光下苏醒过来。(1939年11月26日)
王文谈到,马来西亚华语中,“在”与名词组合表处所时,可以位于谓语动词的补语“了”之后,如“才推开房门,蓝逸就立即呆了在原地”,而这样的形式在早期的一些翻译作品中也时有所见,例如:
(24)有些小鸟从树枝上掉在冰冻的地上,冻僵了在这冷气之中。(《晨报副刊》,1921年12月22日)
(25)好像他后来所说的样,唾液亦干了在他的口里。(《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1日)
总之,王文所列出的一些华语介词与普通话的差异点,在早期国语中基本都有相对应的用例,由此再一次证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然而,在分析上述差异现象的产生原因时,王文谈到了语言的欧化及欧化程度、普通话的影响、方言的影响、语言的类推作用,以及同类词语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词义的多寡等,却并未提及早期国语相同用法的存留。总之,都是仅立足于并着眼于共时平面,未能从历时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察与分析,而这样的研究模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二)“变异”向度的错误认知:华语研究历时观缺失的必然结果
在当今的华语研究中,无论涉及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等,“变异”都是一个高频词,其基本取向是,凡与普通话不同者,均为变异,比如以上我们分析过的两篇论文就是如此。
谈到变异,首先需要先明确一点,这就是它以什么为基础或参照点,换言之,也就是相对于哪一个对象而言。如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基本都以普通话为参照点,李计伟对此作过非常客观的分析与表述:“从方法论上讲,我们谈论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某个华语变体的特色,大都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采用普(通话)—华(语)对比的方法来描写该华语变体;凡为该华语变体所用而普通话不用或者极少使用者,均视为该华语变体的特色。”[15]
我们认为,以普通话为参照与依据的“变异”,有可能是把事实弄颠倒了。实际的情况是,“变异”的可能是普通话,而不是华语,以上我们所作的调查,证明的就是这一事实。关于这一点,上引李文接下来的表述,就说得很清楚:“但在归因大陆地区之外的华语变体特征的形成原因时,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方面,那就是现代汉语标准语百年来同样发生了较大变化。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国台湾现代汉语、东南亚华语变体‘同源异流’,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华语变体的某些特色可能就是直承早期现代汉语而来,只是这些特色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消失了。”[15]很显然,“直承”当然是不变,而“消失”无疑是变化所致。
周清海也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研究华语的区域变体,目前普遍存在一些不足,其中的第一点就是“过去研究华语的共同倾向是从普通话的立场来单向地看待语言变异。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研究者‘挑出’华语中与普通话不同的语料加以讨论,认为这些就是不同地区华语的特点”[16]。至于这一作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是“这并不足以让我们看到各地华语的整体面貌。这种研究方法只告诉我们各地华语‘变’了什么,却忽略了‘不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于强调‘变’的部分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16]。
周文对上述问题看得很准,但是对其弊病的分析却不甚妥当,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变”与“不变”至少有一部分也说颠倒了⑥。
著名的华语研究专家尚且会有这样的认识,更遑论一般的研究者了,而我们也确实看到不少类似以下这样的表述:
由于历史的原因,华语已成为普通话的区域性变体。[17]
华语并不等同于普通话,但是源于普通话。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在华人间充当社交的共同语。[18]
在这种认识下,上述“变异说”的产生与流行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鲁国尧在批评某些汉语史研究存在的弊病时指出:“有些论著,冠以‘近代’或‘魏晋南北朝’,所引材料上下数百年,地域遍全国,而书中却没有或较少言及时空的差异,则有压时线成时点,聚平面为一点之嫌,仍然有欠于精深。”[19]我们认为,这里虽然说的是汉语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同样也适用于当今的一些华语研究,而以上把华语当成普通话的变体,或者说认为前者来源于后者的表述,正是比较典型的“压时线成时点”,是历时观缺失的表现,而这也是上述研究模式及其所反映和代表的“变异观”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于华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参照与类比以下的论述:“上世纪的40年代末是国语的发展被分隔在两个区域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时间点。大致从这一时期开始,‘国语’产生两个分支:一是大陆的‘国语’,后通称普通话;一是台湾的‘国语’,袭旧称未变,仍称国语。也可以说老派国语衍化为同一层次上相对的两个变体。”“从国语在台湾的历史来看,台湾国语不可能是普通话的变体。”[20]
我们认为,以上表述客观、准确,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老派国语”即本文所说的早期国语产生的分支是三个,另外一个就是华语,它与普通话也属于同一层次上的变体。[8]24-27其实,这一观点并非我们首创,周清海、萧国政早在1998年就指出,“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两种社会变体”⑦。
以上华语“者”及介词用法与普通话不同而与早期国语相同的事实,正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至于上述“变”与“不变”,以及谁变谁不变,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正确的认识和表述。比如,本文第一节引用李计伟、张翠玲所说华语作为传承语的保守性,其实就是强调其“不变”的一面;徐杰、王惠则明确指出:“新加坡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广华语的,其长期用作学校教材的书面语也是五四时期的书面语。……中国普通话变了,而新加坡华语并未跟着改变,不同也就出现了。有些中国普通话不用的词语仍然活跃在新加坡华语中。”[21]
把本部分的内容简单总结如下:
第一,对于华语而言,“变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应该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以之为抓手,来了解和认识其基本面貌与特点;
第二,华语与普通话属于同一层次的变体,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基础产生变异,要谈变异,必须回归到二者共同的“母体”即早期国语,以早期国语为参照,来考察以及确定二者的变与不变及其背后的促成原因;
第三,目前相关研究的普遍模式及其中存在的偏差,主要是由华语历时观的缺失造成的,由此提醒我们,应建立“历时华语”的概念,以及倡导华语研究的历时观,这样才能避免一些相关的失误,从而把华语研究引向深入。
(三)华语研究历时观的正确认知与实践
本文倡导华语研究的历时观,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提出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来进行初步的阐述。
第一,华语研究历时观的内涵是什么?
本文第一节末尾所提历时华语的三点内涵,已经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下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补充说明。
首先,从发生的角度说,历时观是基于华语历史与现实的一种认识。如上所说,目前在已有研究中,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均非空穴来风或无根游谈,而是基于一定的事实,因此都是对华语历史与现实及其发展的一种认识。
其次,从存在的角度说,历时观是基于上述认识而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对认识华语和研究华语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之一,它的从缺会造成华语研究的死角,进而由此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从而直接影响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再次,从操作的层面说,历时观“外化”为基于上述认识和观念而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或方法,即华语研究中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以及华语共时中的历时与历时中的共时⑧。这种范式与方法随着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第二,为什么要建立华语研究的历时观?
首先,这是由华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决定的。比如,就大的发展而言,周清海指出:“现代汉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阶段,可以叫做现代汉语的分裂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是现代汉语的融合阶段。1949年以前的‘国语’,无论词汇或语法现象,都保留在各地的华语里。加上华语区多语社会的影响,使华语出现许多特点。这些部分我们以前都关心得不够,研究也做得不多。”[22]这里以现代汉语(按即普通话)为参照,只说了1978年前(即“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情况,而下文则谈到了此后的发展变化,即一些融合方面的表现。总之,华语有一个完整的历时发展过程,而这就是建立华语研究历时观的客观事实基础。
其次,这是由华语的当下研究状况决定的。以上引语已经提到这方面关心得不够、研究得不多,而我们上文中所作的调查,以及由此而归纳出的一种当下的普遍研究模式,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建立历时观的必要性以至于急迫性。可以说,上述事实使得华语历时观的提出和建立成为当务之急。关于这一点,邱克威立足于词汇研究,从正面指出:“各地华语词汇之间全面且合理的比较,也有赖于理清各自词汇系统的历史脉络。所以说词汇的历时考察对于共时描写与比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23]
第三,华语研究的历时观怎样在具体的研究中实现?
我们目前能够给出的答案大致是:
其一,建立共时研究的历时视角,在华语研究中真正贯彻“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华语现象的观察、不同区域华语之间的对比,以及具体现象的解释等方面都应遵循并确实有所体现,如能做到这一点,以上调查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就可以避免,而由此自然会使研究质量与水平有所提高。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样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比如,李计伟指出,中国台湾现代汉语中动词“帮忙”的特殊用法(按指作为及物动词带不同类型的宾语)源自早期现代汉语或者说传统“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的这些用法,虽不能排除英语影响、习得偏误等原因,但主要源自早期现代汉语[15];王晓梅指出,马来西亚华语“较”字差比句承继了早期国语的用法,并认为这一点与港式中文、台湾国语有相似之处[24];王文豪也认为,海外华语中普遍使用的致使动词和目的连词“俾”是对近代国语的继承[25]。与赵文、王文相比,这样的历时视角的加入,使华语研究由共时向历时延伸,从而更加全面、完整,同时也避免了由于历时视角缺失而造成某些结论的片面性。
其二,立足于华语的历时发展,对其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以上所说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是就某一项具体研究而言,而这一原则的另一表现,则应该是把它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与另一领域即共时研究形成互补的分布,共同构成华语研究的两翼,从而使之在总体上趋于均衡。在这方面,徐威雄已经提出“马新华语史”的概念[26],但是目前所见称得上这方面研究的只有一些着眼于“初期”的零星考察与表述,如徐文对马新华语一些代表性词汇现象的考察,车淑娅、周琼对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时间词历时变化的讨论[27],至于华语百年来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具体调查,则基本属于空白。
其三,放眼并立足于世界华语圈,进行全球华语史的研究。以上两点基本只是立足于东南亚华语研究,而我们认为,华语研究历时观的最终实现,是建立本文开头提到的全球华语史,而不仅仅是上述的“马新华语史”或“东南亚华语史”。我们给出的全球华语史定义是:全球华语史是以全球华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华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也是整个汉语/华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华语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全球华语的发展演变,分析和解释造成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
全球华语史的实质是倡导建立全球华语研究“史的格局”,简单地说就是对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程关注,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关注点:一是华语从哪里来,二是华语向哪里去,而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全球华语的“来龙去脉”[8]109,112。由华语向哪里去,把华语研究从现实的描写引向对其未来发展的预测,而这也是上述历时观在具体研究中的实现。
注 释:
①本文所说的华语,主要是指东南亚华语。祝晓宏、周同燕指出,华语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算起,到现在才不过30年时间,而真正在全球华语观念和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却是开始于本世纪。参见《全球华语国内研究综述》,载《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第49-59页。
②以上《申报》中的相关信息及下文的《申报》用例,均由辽宁师范大学的刘兴忠老师提供。
③以上日语相关信息由博士生国本延爱与董庆进提供。
④“有的”已经成词,各版《现代汉语词典》均收录。
⑤因为以“者”为检索关键词,找到的用例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只取其前三百个,便得到以上一些。
⑥作为早期国语的变体,相对于后者,华语当然会有所发展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增添其“地方特色”,而这才是其“变”的部分,虽然这种变化有可能造成华语与普通话的不同,但这是两种变体在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差异。至于不变的部分,自然也是着眼于跟早期国语的对比,而不是与普通话的比较。
⑦参见《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该文曾在1998年3月11日-13日澳门理工学院主办的普通话(国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转引自陈琪《新加坡华语词语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⑧萧国政著《汉语语法研究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指出:“区别历时和共时很重要,但是注意共时中的历时,也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和沉淀着历时。”于根元著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载《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也就此说道:“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以上表述自然也适用于华语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