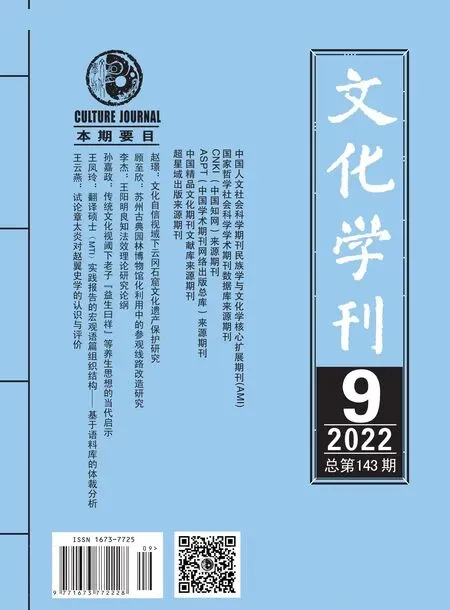从《虬髯客传》到《红拂记》人物形象的嬗变
2022-12-28陈畅
陈 畅
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史上,有一个普遍的传统,那便是事有所本,借人家酒杯,浇自己块垒,根据旧有题材敷演加工,创制新作,从《虬髯客传》到《红拂记》即是如此。张凤翼的改编受到了明代戏曲自开始便有的教化观念影响,也受到晚明内忧外患政治形势影响,其个人遭际在《红拂记》中同样留下了痕迹。可以说,两部作品人物形象的嬗变,是时代造就的必然。
一、虬髯客:从粗豪游侠走向有志人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云:“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作意好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的小说创作。《虬髯客传》作为豪侠小说,最“奇”之处当在虬髯公形象的塑造,他虽怀有大济苍生的儒家政治理想,但其豪侠气却不可避免地露于文中。首先是他的出场,“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2]“虬髯”指的是蜷曲的连鬓胡须,蓄此须者,本就威武气大增,再加上赤红的颜色,他的形象便奇异得让人望而生畏了。他将随身的革囊利落扔于炉前,随即取来枕头斜靠着欣赏陌生女子。这是底层英雄的痞性流露,也是爽利豪放、不拘小节的表现。其次,是对他食负心人心肝的描写,“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作者丝毫没有隐晦,而是将这一过程分明写出,虽然以今时眼光看来,这一行为不失残忍,但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爱憎分明的气魄,游侠的胆量和英雄的豪气。再者,是他骑的“蹇驴”。此驴也非一般人能有,“其行若飞,回顾已失”,作者将蹇驴写成了有奇异功能的神驴,通过反复渲染驴的奇异来衬托虬髯客的非同寻常。最后,当虬髯公确认了“真天子”后,他“默居末座,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而后让李靖持其之赠,以佐真主。这体现出他拿得起放得下的特点,可称“侠之时者”,进则全力以赴,不可进则成人之美,洒脱与豁达浑然天成。
但在明代张凤翼创作的《红拂记》中,虬髯客身上的豪侠气被大大削弱了。首先,虬髯客的人物出场基调由威武放肆的豪侠转为意欲建立功业的志士,大段的宾白不仅介绍了虬髯客姓甚名谁,还介绍了他杀人避仇的经历,以及想要建功的愿望。此时他的行为全然没有了原作的随性豪放,多了深思熟虑后的伺机而动。在虬髯公和李靖初次见面时,对他轻浮行为的描写没有了,仅以“作看旦”的科介交代,其底层英雄习气被弱化,之后二人交谈使用的“足下”“正是”“相逢何必曾相好”的对白十分文雅,也更符合“礼”的标准,却不像从江湖游侠之口说出的。其次,《红拂记》中关于食人心肝的描写也被淡化了,虬髯公“却人头”“切心肝”“共食之”的动作描写被“取出人头并心肝”的科介取代,二人对话的重点变成对虬髯公杀人原因的交代。“腹中怀剑”“笑里藏刀”这种不符合儒家处事规范的行为被作者树立成了反面典型,借虬髯公之手加以惩罚。再者,本能增加虬髯公神秘色彩的“蹇驴”,在《红拂记》中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坐骑,对其“食肉”“神速”的奇异特质全然不提,“蹇驴”不再奇异,虬髯公也不再神秘。
从《虬髯客传》到《红拂记》,豪侠气的转弱一方面由于戏曲和小说的表现形式不同,戏曲的表现力不在于传神的文字描绘,而在于人物对话和舞台表演,因此,张凤翼大量删略了原作中对人物的描写,转以平实的科介、文雅的宾白替代,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物特质的表现力降低了;另一方面,作者将虬髯客塑造成一个听天命、有谋略、最终又愿意归顺中国的异邦国王形象也大有深意。
明代元而立,明廷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抵御外敌入侵上。但尽管如此,明朝依旧是我国历史上首度追求并曾掌握了制海权的朝代。明永乐年间郑和的航海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贸易推到巅峰阶段,明廷借此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权。虽然朝贡贸易的经济收益十分有限,但明朝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权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到了张凤翼生活的隆庆年间,朝贡贸易虽难以维系,但“隆庆开关”使得延续了二百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促进了海上私人贸易的繁荣。从“郑和下西洋”到“隆庆开关”,“海权”思想深深植根于明人心里。张凤翼受其影响,将原作《虬髯客传》中的“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扩充为“髯客海归”“扶余换主”两出,并增加了最终虬髯客归顺中国的结局,这些都是明代海权思想的外化表现。
明代戏曲自产生之始,就被赋予了教化色彩。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不仅在政治上对皇权极端崇尚,在思想意识领域也格外强调汉文化的正统性,推崇儒家的伦理思想道德。明太祖朱元璋曾提出“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明)徐渭.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南词叙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0.,在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下,宣扬儒家的教化观念成为贯穿戏曲作家创作戏曲的第一要义。《红拂记》继承了原作《虬髯客传》儒家政治理想的同时,对其加以强化,强调其为政治服务的功用。原作中虬髯客的形象,代表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和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素王传统。而在《红拂记》中,这样的一位“素王”,更加顺应天命,第九出“太原王气”,第十六出“俊杰知时”,第三十四出“华夷一统”,虬髯客最终的结局是作为海上一国的国王归顺中国。较之原作,《红拂记》对“天命”渲染的增强,对虬髯客最终结局的改编,充分说明了“王权天授,不可觊觎,只可皈依”的主题,其教化意较之原作更加明显。
二、李靖:从有才士子走向民族英雄
从《虬髯客传》到《红拂记》,李靖人物形象的底色并未改变,作为一个渴望建功立名的有才士子,从初出茅庐、进京求职,到最后迎娶红拂、任朝中要职,他的人生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士子成才的必经之路和所需的种种条件[3]。但在两部作品中,李靖最后实现抱负的方式发生改变,《虬髯客传》中以寥寥数字简要交代其成才经历—持人之资、辅佐真主、匡扶天下、位居高官。但在《红拂记》中,张凤翼增加了“奉征高丽”“计就擒王”等情节将李靖塑造成了一个民族英雄,这与时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虬髯客传》传统主旨历来被归结为维护唐朝封建统治,宣扬封建正统论与天命观。但细读文本会发现李靖所代表的进取精神实际上是对天命的反叛,是对个人能动性的积极宣扬[4]。传统主旨认为,李靖作为虬髯客所称的“真丈夫”,最终辅佐李世民平定天下,是他顺应天命的必然选择,但实际上这是他甄别人物、审度时局、权衡利弊后的主动选择。一开始他想要投靠司空杨素,但在发现了其骄矜踞傲的性格缺陷,又听到了红拂对其“尸居余气”的评价后,便改变了原先的政治意愿,不再于客舍中等候消息,而是与红拂一同前往太原,寻找下一个可仕之主。在他认识到李世民是“真人”后,也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权衡了两方的实力。到后来偶遇虬髯公,再会刘文静,他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反复观望,最终接受了虬髯公的馈赠和建议后才决定辅佐李世民,这种对个性的宣扬是唐代思想开放的体现[5]。虽然《虬髯客传》创作于唐晚期,其时国力衰微,国家动荡,但在思想领域,与理学思潮笼罩下的宋、元、明、清时期相比,唐代始终是开放、包容的,人们受到的思想束缚较少。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二云“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2)容斋随笔·绩笔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M/CD].,唐代开明、宽松的时代氛围使得文人的个性得以充分舒展,因此李靖形象反映出的思想主题不应被简单归为对天命的顺从,小说通过李靖形象想要展示的是一个呼吁反抗、斗争与进取的时代。
到了《红拂记》,李靖抱负实现的方式发生改变,“南平吴虏,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今又平高丽。功高愈下,宦成无毁”,他的赫赫战功使其成为了民族英雄的化身。这不仅是张凤翼个人愿望的书写,也是那个时代百姓心声的真实反映。
张凤翼青年时期便有建功边庭的志向,“仆自弱冠即有意用世、占毕之暇,每索《阴符》《六韬》《孙》《卫》诸书,究其端绪,且锻炼筋骨,开张胆气,冀一旦为边疆之臣,庶可效用一割”(3)(明)张凤翼.处实堂集·卷一[M].,他十九岁时改编创作了《红拂记》,独属于青年的豪气贯穿其中。他笔下的李靖是一个满腹经纶、胸怀大志、建功立业的民族英雄,这是其思想心迹的表露。在他生活的明中晚期,国家承平不再,北方“吉囊及俺答连岁大举入寇”,西边“洮、岷藩贼数反”,东南地区倭患猖獗[6]。在这样边患丛生,国力衰微的年代,自少渴慕边庭建功的张凤翼将个人志向寄托笔端,“耀武边陲,乐浪临屯尽扫除。早验征西记,胜置安东尉。百战谢天威,无劳折矢,平定安集,敢负师中寄,只待擒王奏凯归”(李靖唱【驻云飞】),征服异邦,在作者笔下是指日可待的必成之事。《红拂记》不仅展现了李靖的赫赫战功,更虚拟了大国的炎炎之威,盛大军势。可现实与作者所写截然相反,他的建功立业、大国神威只是文学创作中的海市蜃楼。大明江山最终走向崩毁,他个人的举业之路也坎坷多难。
整个明朝统治中国时代,前半期常受北方和西方的外族势力侵略,后半期更加上东南倭寇和东北女直(即女真)的骚扰,前后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没有一年曾长年安静过。一旦边患战事发生,受到摧残最严重的当然是底层的劳动人民。打仗需要的人力财力最终都来源于搜刮百姓,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趁此机会发国难财,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明中后期,普通人的生活受战争波及较大。因此,在明朝人所作的很多小说和戏曲中,无论是英雄武侠,还是才子佳人,故事的最后,往往不是征番凯旋,便是平寇班师,然后得到朝廷封赠,家人团圆。在《红拂记》中,作者始终掌握“时来有志须遭遇”这一命运观念,将李靖塑造成一个扫除边患、安定中国的英雄人物模范,也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拂记》不仅仅是一部描绘作者个人“白日梦”的作品,更是一部反映当时人民意愿和历史背景的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张凤翼的其他作品中,也能找到同一类型的抗敌人物,如《祝发记》里的王僧辩,《窃符记》里的魏无忌,《灌园记》里的田单,《虎符记》里的花云与花炜。考虑到戏曲的表演效果,作者将主要的思想倾向隐藏于不经意的地方,但细细品读,便会在豪情之外体会到作者对现实的关切。
三、杨素:从骄贵权宦走向开明贤臣
《虬髯客传》开篇对杨素和李靖出场的描写虽只有寥寥数字,但作者借此完成了对全篇矛盾的铺设。“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颤之心”“李靖以布衣上谒,素亦踞见”。作者将杨素定位成了一个位高权重,却居功自傲,纵情享乐,忘记责任的权宦重臣,而将李靖定位为了有志不得展的寒门士子。二人的矛盾实则是两个阶级的矛盾:上层统治者的“骄贵”行为,截断了民间之士入朝为官的上升阶梯,堵塞了上下阶层交流与融合的转化渠道,使统治的根基渐趋枯乏,使像李靖一样的布衣之士在封堵中被迫走向暴发,这是贯串全篇,促使人物行动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虬髯客传》通篇并未有对天下之乱缘由的交代,“隋炀帝”的形象也几乎缺失,提到天下形势时,仅以“时乱”“天下方乱”带过,这样的略写和开篇对杨素奢纵放诞的强调不禁让人联想:是上层权臣的昏庸导致了天下之乱。将乱世罪责的发生归因于权臣乱政,而君王只是因蒙蔽而犯错,如此情节将君王尊贵而不容侵犯的地位凸现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虬髯客传》对君权的维护就不止表现在结尾极力宣扬天命归李世民的一段文字叙述,还表现在用“君明臣暗”的意识形态为晚唐统治者开脱。
到了《红拂记》中,杨素形象发生转变。第一出传奇大意,张凤翼对杨素的评价为“撇得下爱宠杨司空”,在整部戏曲中,杨素不仅是红拂和李靖的成全者,更是陈公主能够破镜重圆的促成者,拥有舍自己所爱成全他人的气量,这是作者为杨素定下的形象基调;之后在第五出越府宵游中,作者添加了对杨素的经历介绍,从中可知,他常亲临督战,且治军有方,是位励精图治的贤士,这是对其品质的二次肯定;而后在第十七出物色陈姻中,当杨素得知红拂与李靖私奔,他并未差人追寻,而是由着他们,只因他不想做一个“轻贤重色,不近人情”的人,在这里作者借陈公主之口再次肯定了杨素的义士之度,仁人之心。通过三次肯定,杨素在《红拂记》中的形象已和《虬髯客传》中的大不相同,从目中无人的骄贵权宦转变为爱才通达的贤能之士。杨素形象的转变消解了贯串《虬髯客传》的矛盾,而张凤翼在《红拂记》中重构了一组新的矛盾,“奸雄方竞逐,社稷将倾覆”“况边庭黩武连年,繁刑重敛谁不怨”,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成为《红拂记》中人物行动的推动力。
从《虬髯客传》到《红拂记》,张凤翼利用旧有题材,进行了自己的创造,他根据自己的时代生活感受、个人生活体悟,提供了超越前人的东西,这使得《红拂记》在继承原作思想基础上又具有了时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