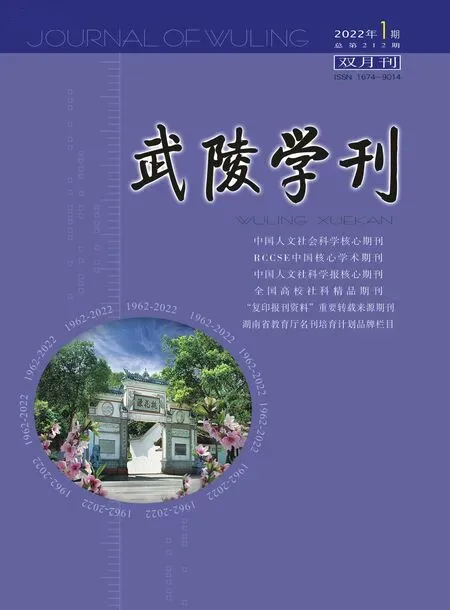《管子》政教思想体系探究
2022-12-28黄少雄
黄少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前 言
《管子》为托名管仲之作,其书非成于一时,亦非成于一人。考历代官志书目,《汉书·艺文志》列《管子》为道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列《管子》为法家。《管子》虽历来列入道、法二家,然而若以后世“九流十家”之说视之,则其中“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1]。就内容而言,《管子》书中包含各家论述是其基本形态。各家学说或言天道,或论地势,或谈法禁,或析兵法,或及君德臣忠、任贤使能、农本商末、安民体国,“庞杂重复”[2],给人以各家学说杂凑之感。《管子》本身组构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研究《管子》视角的分离性,故而学者多“将《管子》一书割裂开来,分别归入诸子各家”[3],单就某一家思想进行研究。毋庸赘述,这种分述割裂的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管子》整体思想倾向的统筹把握。
万宗乾先生认为,针对《管子》研究,“不可执其一端以概其全体,亦不可举起全体而揜其一端”[4],提出将《管子》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观点。何隼先生同样秉持整体视域的研究思路,认为《管子》中“必有其一致之观点,而有系统条理之可寻焉”,意指《管子》存在一定的思想体系,有其特定的思想倾向。他指出,《管子》汲取各家言论,虽表面离析,但实则相合,“所采之说,均不离其旨趣”,是围绕某一中心思想构建的论述网络[5]。张岱年先生亦认可“整体论”者关于《管子》具有中心思想的观点,称“我认为,《管子》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著作,具有自己的中心观点”[3]。
至于《管子》中心观点究竟为何物,张岱年先生认为是“法教统一,或者说兼重法教”[3]。《管子》重法自然无疑,历代官志书目多列《管子》为法家。《管子》中《版法》《法法》《明法》等多篇均与法家思想有关。然“法”是否为《管子》思想中心,则多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赵辉祖先生认为,《管子》虽重法,但“法”不过为“教”的实现途径,“其所以立法为教育之本者,不过借此为达其目的之具耳”[6]。谢源和先生与之论同,认为“法治实在只不过是他(管仲)过度的政策。根本的办法,还是在养成人民有最高的德性”[7]。在赵、谢二位先生看来,“教”在《管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贴近《管子》思想核心。何隼先生认为,《管子》之所以重“教”,盖因在《管子》的治术思域中,“养成人民之齐一的德性,为政治之最高目的。反之,此种德行又为推行政令之基础,且为国家之生命所寄托焉”[5]。上述学者的看法为《管子》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管子》所欲构建的是一种政治治理与道德教化双向涵摄的治术体系,将《管子》一书的中心观点聚焦在政教思想范畴,为整体把握《管子》治术精髓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一、《管子》政教思想的哲理基础
中国传统政教思想可以归结为“寓教化于政治,寓政治于教化,政治活动本身就是教化活动”[8]。这种政治与道德教化双向涵摄关系的建立最早可以导源至商周之际的天命观流变。据胡照厚先生的看法,殷商之时,殷人相信天上存在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帝”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界,决定气候变迁、谷物丰歉、兵伐侵夺、祸福灾殃,具有无上的权威。殷人的先王,殁后可以配天,称为“王帝”,与“上帝”有同样的权威,成为殷人的“祖先神”[9]。另据郭沫若先生研究,殷人所崇拜之“帝”即是殷民族的祖先帝喾,故而“帝”既是“至上神”又兼殷人的“祖先神”[10]。总之,“帝”既然赋予殷人以政治权利,殷人又与“帝”有如此亲密之关系,殷人自然认为“帝”将永续自身的政治寿命。及至纣王,自以为“有命在天”[11]17,于是耽于享乐,暴虐百姓,最终身死国亡,天命不再。
殷商的兴亡教训使周公等周初执政者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经过深刻反思天命转移与政事变迁的因果关联后,周初执政者认为殷亡因“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故天“哀于四方民”,“遐终大邦殷之命”[11]137-139。如此,周初执政者将殷人观念中的天伦理化,认为欲常保政权必须顺应天道,于是构建了“敬天—修德—保民”的德政治理逻辑,为自身的政治使命增添了天赋的伦理色彩。顺天之道的责任感使周初执政者认识到,“为政之道,非仅为君者须有人君应遵守之极则,亦应使庶民百姓能共同遵守‘皇极大中’之道”,如此方能承当“上天‘生生之德’之彝伦明训,亦可以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2]286。因此,周初执政者将政治治理与道德教化紧密联系起来,肇启了中国传统政教思想的开端。
《管子》虽托名管仲,但其成书与管仲实有密不可分之关联①。管仲处东周早期,周初以政教为立政之本的治国策略尚留余韵。清何如璋称:“夫管子之学,周公、太公之学也。”[13]瓦永乾亦认为《管子》于周公德礼教化思想多有继承[14]。《管子》一书在吸收周初天道观念之余,亦有自己独特的哲理逻辑。
《管子》同样认为世间有一种超脱万物之上的神秘力量,称之为“道”或“天道”,但《管子》不认为道对包括政权更替在内的世间万物的运行发展有任何主动取舍,它扬弃了殷周之际将天拟人化、主观化的思考路径,把对这一神秘力量的理解转向了彻底的客观化。在《管子》看来,与其说道是世间万物的“神灵”“主宰”,莫若说是一种长存世间的规则。
道之本体是“虚无无形”[15]759的存在,不可以形体限极,“其大无外,其小无内”[15]767;不可以质料限极,“其重如石,其轻如羽”[15]810;非语言可谈论,“可安而不可说”[15]759;亦非声色可预闻,“谋乎莫闻其音”[15]932。如此,《管子》在道的初始境地就赋予它超越感观世界的能力,成为非限制的、不可定义的存在。道的超脱属性使得感观世界中的任何物质、现象都不能阻滞道的运作,于是道无所不在,“遍流万物而不变”[15]770。同时,道又有万物本源的意味,是“扶持众物”[15]1182的根本所在。因有道的存在,万物方得以生养,“万物以生,万物以成”[15]937,万物各自的自然生命程式方得以完成,“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15]1182。《管子》以其“道论”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哲理构架,赋予世间万物某种形而上的共同属性,使万物在这一基础上与道产生联系,并且认为这种联系不可剥离,是万物体现内在价值和顺利展开内在生命逻辑的前提条件。
道虽虚无,但在道与万物产生联系的过程中仍流露一定痕迹,为人捕捉道的信息提供了可能。《管子》将道在世间运行产生的痕迹称为“德”,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15]770《管子》认为德是道的效能属性,是道之“馆舍”②。当道的存在转化为德之效能时,道即寓寄在德之中,通过自身的效能属性彰显存在。“职”即“识”,意指人可于德之效能,在万物的生命律动中把握道存在的迹象,进而体道、悟道、依道行事。这样,《管子》建立了一套由德用循阶而识道体的理论模式,“‘德’表明了‘道’本身所固有的功能:赋予万物以生命;使人的心智有能力体认‘道’的实质”[16],借之剥离了道虚无缥渺的“神秘”外衣,拉近了道与人间的距离。
道既流布万物,则“虚之与人也无间”[15]767,人之物质环境乃至情理环境理应皆由道所涵摄,这是《管子》道论展开的必然逻辑。人生在道的润泽之中,与道无间。因此《管子》承认,“职道之精”是人本性皆具有的能力。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道仍是“神秘”的,道与民众之间存在“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15]938,“民之所以,知者寡”[15]810的矛盾。“道满天下”是就道之“虚”体而言,“普在民所”是就道之“德”用而言。“民不知”,在《管子》看来,则是民众对道的原始感通能力受到了某种遮蔽,这种遮蔽导致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问题。
《管子》进而在其人性理论上解释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管子》将人性分为心性和情性两端③。从修养角度而言,《管子》认为“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15]241。此“心”非指器官之心,而是“智之舍”[15]770,“精之所舍”④,是人之思虑功能的总和,即是《管子》所谓的心性。心性作为道寄寓人之生息的映射,上承天道,是人生命活力的实质来源,代表人思索生命本质、探求宇宙奥妙的初始能力。从物质生养而言,《管子》认为“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15]1012-1015,此“情”即是《管子》所谓情性。情性代表人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是人心对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等基本生存需求的渴盼,常表现为对物质滋养的欲望。《管子》认同人生存于世,理应得到基本物质条件的满足,但反对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和情欲的无限膨胀,因为物质欲望的充斥会降低人观照外部世界的能力,“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15]767,更有甚者,会破坏心对于道体的原始感通,“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15]931。这种由人之情性扰乱产生的自我矛盾,导致人本有的与道感通能力的丧失,隐含对人自身价值的反对。因此《管子》强调人应通过修养,祛除情性的过度发挥,“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15]942,使心性和情性在终极的道德准则下保持和谐统一。
《管子》将排除物欲与情欲干扰的修养方式称为“静”,由“静”可以体达与道同频的“虚”的境界,认为“人如果使‘心’作到虚静,即免受情欲的干扰、可以有效地节制感官机能,那么他就能够消解成见和虚妄不实的言论,据此获得超越常人的智慧”[16]。《管子》将触及这种境界的人称为圣人(或明君)。圣人在道与万民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使道与万民的亲和成为可能。
《管子》由道论出发,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哲理构架。道具有宇宙运转源头的性质,决定了人间政事体道、悟道,依据道揭示的自然规律行事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最符合事物本质、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由于人性之中情性对心性的干扰,道与人事之间的贯通受到阻隔,因此“政治活动之内容即须以教化黎民百姓依道修为、循性成命为主要核心”[12]337,而教化任务自然成为圣人(明君)的职责。《管子》的道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性的探讨,成为《管子》将政教作为开展政事活动首要任务的理论依据。
二、《管子》政教思想的精神纲领
由上述可知,《管子》所言“虚无无形”之道与老子“无名无形”道论相类;由静启虚、抑制情欲的修养理论亦与老子少私寡欲旨意相同。然而相较而言,“老子多言治道之体,而管子则于用为详”[17]。《管子》更关注道的形而下效用,“淡化了‘道’的虚无和超越性,而导向了其客观和物质的属性”[18]。《管子》谈道论德的终极目的是为人间政事寻求合乎宇宙本源的哲理支撑,并为制度、政策的拟定提供承接宇宙运转逻辑模式的参考。在这种观念下,《管子》自然而然地在道所构建的外部环境中探究搭载政教思想的理论进路。
天、地以及天时日月、地利山河是人参悟外部世界的基本位面。“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15]550《管子》认为天地所展现的自然规律中预制了道的启示,因此开展政事活动的基本路径即“参天地之吉纲”“承从天之指”[15]662,在天地规律中把握人事规则的脉象。如此《管子》在制定制度的初起,就将人间政事置于天地之中,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思索人事极则。
“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15]799《管子》俯仰天地,认为天地之间有某种力量维系,它是维持天地运转的根本法则。析而梳之,天有日月,地分南北,天地之间其大略可分为阴阳两种极则。《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19]一阴一阳是中国古人对道内在运动张力的本初认识,是对万事万物中相对立而又统一的动态结构的朴素描述。在《管子》这里,阴阳是道所赋予天地的基本运行规则,在阴阳二者交互变化中又可析分为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15]838。阴阳、四时成为天地之道的根本表现,遵循阴阳、四时即能把握贯彻天地之间的正理,以之辅应人事可以利行天下,培植邦国根基⑤。
天地既以阴阳、四时维系,又以《管子》“参天地之吉纲”的理论脉络贯穿,人间亦应有某种力量作为维持,以对应天地阴阳、四时之结构⑥。《管子》首篇《牧民》即曰:“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15]11“维”之本义为系车盖之绳。《说文》曰:“维,车盖维也。”段《注》曰:“许以此篆专系之车盖,盖必有所受矣。”[20]658据林素英考据,管仲时齐地百姓有渔猎习俗。渔网四周以“网维”组成,渔民操控网维以达收放自如之效;田猎习射之侯(箭靶)以小绳缀四角系于植,称为“维”[21]。渔网、侯四角之维,起到收放、固定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则维由系物绳引伸出纲维、纲要之意。“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5]3《管子》将礼义廉耻并称国之“四维”,盖以齐地日常生活经验喻指礼义廉耻之枢要,认为“四维”是维系人间和谐有序、统领道德教化的精神纲领。
礼义廉耻“四维”内涵阴阳之道。宋欧阳修认为“四维”可归为“礼义”“廉耻”二端,曰:“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22]实则《管子》亦常将“礼义”并称、“廉耻”并举⑦。义是对某种得宜之理的精神向度的归纳,此理导源于道,顺应此理即是有道,“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15]770,“顺理而不失之谓道”[15]557。礼是此义此理的制度向度规定,“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15]770。礼义合参,使得“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15]198,制定人世间的名分,以收“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15]551之效。如前所述,《管子》将人性区分为心性、情性两端。心性为人启悟天道的能力,依靠“静”的方式提升修养。《曲礼》曰:“毋不敬。”郑注曰:“礼主于敬。”[23]礼的内在动力在于引发人之恭敬之态。《管子》认为,礼义为人培育心性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因“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15]947。由礼启敬,由敬入静,由静反性——礼为心性架设了循序渐进、内外相应的修养路径,成为心性悟道之阶梯。
礼义上承天道,是天道降应人间的制度导向,廉耻则是人自身的灵觉。《说文解字注》曰:“廉,棱也。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20]444廉由原初边棱之意引伸为正直、清廉、节俭、不贪物利等诸意。《管子》之廉为防制物欲之廉,曰:“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15]76“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15]298《说文解字》中“耻”与“辱”互为转注:“耻,辱也,从心耳声。”段《注》曰:“辰部曰:‘辱,耻也。’二篆为转注。”[20]515耻即内心羞辱之感的会意字。“廉不蔽恶,耻不从枉。”[15]11廉耻并举,强调以内心高度的道德自觉,以自身对恶行、邪枉的羞愧感抵御物欲的危害。《管子》以情性代表人对物质利养的本能追求,同时主张防止物欲、情欲过度膨胀对人观照能力的妨害。《管子》设廉耻为维,即是以廉耻对治情性,以防“营于物而失其情”[15]989,使人“意定而不营气情”“耳目谷”[15]1012-1013,进而显发本有之德能。
《说文解字》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又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20]502董仲舒谓:“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24]“情”即《管子》“情性”,属“阴气”。“阴则隐,隐则难明,难明则蒙昧生”[12]322,故《管子》以廉耻节情性,使不至荧惑本性。“性”即《管子》“心性”,属“阳气”。“阳则显,显则易明,明则不昧”[12]322,故《管子》以礼义导心性,使之依循修道。
《管子·形势》曰:“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15]42天地以阴阳、四时为维系,人间则以礼义廉耻为维系。礼义、廉耻各守阴阳两端,可知“四维”是《管子》效仿天道阴阳、四时的理论创设。《管子》以“四维”立教,为其政教设立了基本德目规范,作为网罟政教的精神纲领。
三、《管子》政教思想的制度构建
《管子》认为,阴阳、四时之所以为天地纲维,因天生四时已御万物生命律动之枢要。万物置于四时构拟的时序网络中,自然化育繁盛;“四维”既张,已把握政教施行之纲目,万民生存于“四维”架构的德育环境中,政教功成自然可期。故曰:“天不动,四时云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15]510“四维”有此成效,因其效仿四时,有如四时一般兴“化”之能。
齐国位于山东半岛,倚靠渤海,东临莱国、东夷,多与夷狄杂处。太公初封齐国遇夷狄侵扰,“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25],至管仲时齐国仍战事不绝,先有公孙无知弑齐襄公、雍林人杀无知,后有公子小白、公子纠争立;其地又多盐卤,“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26],农耕开发不畅,民众多所流徙,以渔、牧为生。复杂的政治、生存环境致使齐地民风羁荡,不喜约束。欲治百姓,使其敬上重令、安于生产,必先变俗易习,故《管子》重化,曰:“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15]107所谓“化”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15]106,强调润泽人心,久久为功,是一项将“四维”精神纲领与民生政策相结合的教化工程。《管子》通过“化”,将政教寄寓制度手段当中,使道德教化与百姓生活起居巧妙融合,以达“君民化变而不自知”[15]256“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15]605之效。
据《管子·小匡》记载,桓公初问政管仲之时,管仲即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15]445对之。“参国伍鄙”是管仲设立的行政区划。“参国”即将国中士农工商“四民”分为二十一乡,士农十五乡,工商六乡。桓公统帅十一乡,高子、国子各帅五乡,乡设乡长;“伍鄙”即将士农十五乡中每三乡编为一属,属设属长。“武政听属,文政听乡。”⑧“参国伍鄙”为政教推行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了运转有序的层级结构。每年正月,桓公亲自督促各乡、属道德教化,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15]416-417以举贤、惩罪掌赏罚二柄,“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15]417。以德行为选拔标准,在邦国开设了较为畅通的晋升渠道。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各级官属以督善为能,“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15]417,各地百姓以修善为尚,“民皆勉为善”[15]418,形成尊贤尚德的良好风范。
《管子》中记载了士农工商“四民分居”制度,即根据职业需求将“四民”安置在不同区域,“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5]400。《管子》认为,“四民”不可使杂处,因“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15]400,百姓生活在复杂的环境中,易受外界干扰,不利于固守本业、虚静安养,有悖心性由静启修的修养理论。“四民分居”似有僵化之嫌,实则只为便于“适应环境以施教”⑨。就其利益而言,“四民分居”为同业百姓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场,营造了良好的修养环境,“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15]400,使道德训练与日常生活牢不可分,“旦昔从事于此”[15]400,进而形成稳固的道德信念,“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15]400,使政教功成润而无声、化于无形,“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15]401。
正如何隼先生所说:“《管子》注重标准之德性,而不重视个性之发展。”[5]管仲相桓公,正处齐国大乱之后,彼时疮痍未愈、民心涣散,欲整肃民心,非有整齐划一的政令统摄不可。“四维”已先在精神层面构筑了道德情感认同,“四民分居”等政策又在制度层面构拟了道德境遇统合。《管子》政教方略在这种高度统一的政事规划下,具有鲜明的制度化、标准化倾向,以期“养成人民之齐一的德性”[5],进而导向更高的治道境界。
四、《管子》政教思想的价值指归
《管子》以其道论为万物寻求了某种共通的存在依据。鉴于万物与道之间的紧密联系,“《管子》在天道的意象塑造中,还要求把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27]。万物综视的整体观赋予《管子》精深博大的思考路向,使其在一种普遍联系的视角下构象天地、政事与人的关系。因此,《管子》自然而然地将政教的对象扩及万物,使政教方略的任务和目的超脱一般的政务逻辑,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哲学视域中。因此,《管子》之政教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道德教化,更包含了超越政治组织的、内涵形而上因素的价值指归。
《管子》曰:“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15]565-56“6先王”是就其治道理想而言,未必有具体所指,有时冠以“明君”之名。“与民为一体”,“此谓国与民不离为二,则国即民,民即国”[28],强调国体与民本的和合。《管子》常借人之身体比喻“和合一体”之道。《管子·君臣下》曰:“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15]585“六道”指人阳明、少阳、太阳、太阴、少阴、厥阴等气血通道,“四正五官”分别指君臣父子及五行之官。君臣父子代表人间伦理生活,五行之官代表人间职能生活,《管子》以此喻旁系左右、上下国众气脉相通,有如一体。
“和合一体”非是否认差别,《管子》也承认人事有名分、职责的不同。在《管子》拟设的举国一体架构中,君如身之心,“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15]583。心是《管子》哲学概念中的重要范畴,《管子·内业》曰:“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15]938陈鼓应先生将《内业》所言“心中之心”解释为“心之官中还蕴藏着一颗更具根源性的‘本心’”[29],彼“心”是人之所以得道、悟道的根据,“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15]935,即是本文所述之“心性”。《管子》以心喻君,非是从心之官能出发比拟君主的重要地位,而是从心之灵觉出发比拟君主于政教方略的主导作用。《管子》犹如众星拱月一般,将政教的枢纽归聚君主一身,“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15]583。各级官属如身有九窍,“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15]759,以“四维”德教安身行事,“事君有义,使下有礼”“义以与交,廉以与处”[15]619-620,尽其职分,助君教化。百姓如身之有骨有肉,为国所成立之根本,“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15]569,顺受“四维”德教,“和子孙,属亲戚”“爱亲善养,思敬奉教”[15]1167。
总之,《管子》所谓“和合一体”即是有序,君、臣、百姓各司其职,以君为承道设教之核心,以臣为推行政教之股肱,以百姓受教为政教之完成。百姓自发遵从教化,服从国家意志,同时君应以道为教化依归,以百姓意志为原则,“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15]565,构成“君—臣—百姓”各行司职的有序环节。总而言之,《管子》以“和合一体”为政教的价值指归。“和合一体”是道德教化的结果,道德教化是“和合一体”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道德教化,才能使举国上下形成精神层面的价值认同和行为举止的协调有序,才能达到和合安乐的治理境界。《管子》借由其“和合一体”之论,欲使治道理想和民意达成统一。“和合一体”作为《管子》治道理想的抽象总结,预设了政教方略贯彻之下的伦理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事逻辑。
结 语
洪佳景博士认为,《管子》在历史视域及思想视域均有诸子所难兼顾的突出价值,然而当前研究多将《管子》割裂为各家学说或肢解为现代各学科,尚存在缺乏整体性的理论统观和缺乏体系性的理论建构等不足[30]。洪博士所述意在呼吁以一种整体性、统摄性的观点综视《管子》,将其视作一部独立、完整的经典,探讨其思想体系和精神主旨。《管子》思想体系之有无,关乎对《管子》各篇内在联系的理论视角和理解程度,关乎对《管子》的定位能否脱离“各家学说杂凑”之窠臼,能否真正还原古人著述《管子》的苦心孤诣等问题。
殷周之际,周初执政者经过反思殷亡教训,构建了以政教为核心的德政治理体系。管仲去周初未远,其理国政策及治国思想中仍有周初余韵,在《管子》一书中可以看到二者继承关系的痕迹。笔者由《管子》道论出发,从心性修养、制度纲领、施政指归等方面就《管子》政教思想展开论述,认为政教思想贯穿《管子》行文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管子》之核心主旨。
《管子》政教独具特色。李源澄先生认为,与儒家政教相比,儒家“其政治思想乃其道德思想之附庸”,而《管子》“即在以道德完成政治”[31]。《管子》将政教职责赋予君主,使政教成为国家事务,其道德教化是制度性的、标准化的,常辅以政令推进,而又以政治哲学层面的和合一体为指归。诚如李源澄先生所言,《管子》政教思想的教化内容、教化对象、运行机制、教化目标等均与实际政务有不可分割的关联,隐含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笔者认为,《管子》政教所呈现的上述特色,应在具体时代背景中把握。管仲之时,周王室权威不再,文化层面上,礼崩乐坏,诸侯相继僭越;政治层面上,夷狄侵扰,“中国不绝若线”[32]。管仲相齐,意在尊王攘夷,开创霸业,重建秩序。欲达其志,非有强力的组织力量不可。故管仲于有周政教文化之发用,绝非简单因袭而多有演变,其一变繁为简,其二变缓为急,因时制宜,强化政策制度对道德教化的导向作用,以期在短时间内达成一定的教化规模,统一彼时社会情态的精神意志,说明其对人事秩序重建有独到的理解和探索。
孔子曾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3]盖在孔子看来,管仲于尊王攘夷之事功之余,其更为卓著的贡献即是对有周以来逐步成型的华夏文化之延续,避免了这种文化在夷狄侵扰中消亡。管仲借助政教,恢复诸夏对有周文化的情感认同,甚至进一步扩大了有周文化的影响圈,使彼夷狄接受了华夏文化之熏染,以一种更为彻底的方式减缓了夷狄侵扰,延续了周王朝的政治命脉,进而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文化传承。
《管子》内容博泛,论理精微,非一文一笔可遍论及。如《管子》久列法家,其所涵纳的法治言论俯拾即是。然而如崔兰海博士所言:“从教化角度审视《管子》法治思想,是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实在《管子》看来,法治一如道德,其教化意义显著。”[34]若只就法家论《管子》法治,而忽略了《管子》深含的政教思想导向,则难免有失偏颇。又如《管子》重农,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15]924然而如谢源和先生所言:“教育是促成国民道德最好的方法,经济是养成国民道德的基本条件。”[7]《管子》重农,有将其视为政教先决条件之意,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5]2;若只就农论《管子》之农,则难解《管子》深意。是故,笔者论述政教思想之于《管子》的主旨地位,并非认为《管子》全部内容均不离政教思想范畴,而是欲为《管子》研究提供一个立足文本旨意的思想主干,为系统探究《管子》治道精髓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
注 释:
①池万兴综合古今学者观点,认为《管子》成书始于春秋管仲时代至战国末年稷下学宫衰亡前,其书作者包括春秋时齐国史官及管仲门人弟子、后代和后世推崇管仲、被称为“管仲学派”的学者等(参见池万兴的博士学位论文《〈管子〉研究》第22页,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尹清忠认同池万兴观点,认为《管子》早期文本为史官记录的管仲时期政策、事迹,这些文本藏于官府并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后世参著者研习的原始材料(见尹清忠的博士学位论文《〈管子〉研究》第27-31页,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本文认为,史官所录可以视为管仲思想的直接表达,后世所著录部分亦应不离管仲思想主旨,《管子》一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管仲思想的阐述与说明。
②黎翔凤先生言:“道为虚位不可见,道即寓于德中。前后‘舍’字皆为馆舍,此处不应独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772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本文从此说。
③多有学者论述可以佐证本文观点,如王新军认为《管子》的人性结构是一个包括“心性”和“情性”的二维结构(参见王新军著《〈管子〉的人性思想研究》,载《管子学刊》2015年第4期)。王辉认为《管子》以“心性”“情性”作为人性理论的架构,表明其对人性的深切洞见(参见王辉《〈管子〉心性与情性的辩证法》,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④《管子·内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句,尹知章注曰:“心者,精之所舍。”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937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⑤此句论述可由《管子》文句佐证。《管子·势》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管子·四时》曰:“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分别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886、837-83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⑥《管子·白心》曰:“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799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⑦如《管子·五辅》:“上下合同而有礼义。”《管子·霸形》:“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管子·权修》:“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管子·立政》:“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分别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92、454、53、79页,中华书局 2004年版。
⑧见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0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三国韦昭注《国语》“工商之乡六”句曰:“工、商各三也,二者不从戎役也。”参见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第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武政听属,工商不从戎役,故属仅含士农十五乡。
⑨天游先生认为《管子》“四民分居”只是就大体而言,并非强制干涉居住自由,其目的只是为使百姓适应环境以施教(参见天游著《“管子”之民众教育思想》,载《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