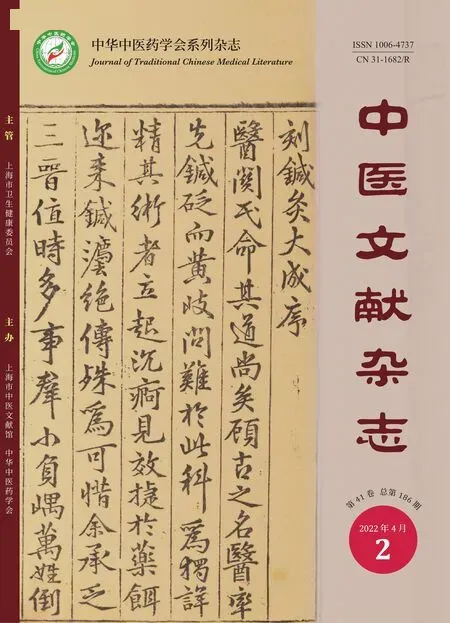朱承汉“元气先亏,火热迫妄”论治呕血特色*
2022-12-27王洁宜陈明显
王洁宜 陈明显 傅 睿 陆 拯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310053)
朱承汉(1917—1990年),字渠深,浙江湖州人,著名中医临床家、教育学家,生于中医世家。其父朱子文(1875—1944年)受业于晚清余杭名医葛载初(1839—1909年)门下,亦是湖州一代名医。朱承汉15岁随父学医,同时师事宋鞠舫(1893—1980年),1934年又赴杭州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深造,1938年开始独立行医,1983年获评浙江省名老中医。朱承汉早年发起中医学术研究社,主编《吴兴医药月刊》,创立湖州市中医院,晚年又任湖州市中医院附设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撰写了《中医妇科》《湖州十家医案》等20余部著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临床人才。
朱承汉临证擅治内妇虚劳及时病,对急危重症的诊治亦有创见。如对呕血一病,他认为,“元气先亏,火热迫妄”是其根本病机,据此辨治屡立奇功。今将其论治呕血的经验特色整理如下,以飨同道。
病机认识
《素问·调经论》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为血之帅,故血证究其根本当责之于气。呕血病中往往气虚和气逆同时存在,对此朱承汉进一步指出,气虚者,元气亏损也;气逆者,火热迫妄也。可谓切中呕血病机之关键。
1.元气亏虚则血溢
元气可指代人身根本之气,最早见于《难经·十四难》“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经李东垣阐发,形成了“脾胃是元气之本”的观点。朱承汉强调元气在呕血发病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元气乃人体立命之本,元气虚则固摄失司,为血液妄行甚至冲出脉管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呕血过程中,血液的流失必然继续耗损元气,危重情况下还会出现亡阴亡阳的证候。
2.火热迫妄则血出
情志不畅所致气机逆乱上行是呕血的重要诱因。《素问·举痛论》云“怒则气逆,甚则呕血”。《诸病源候论·呕血候》亦言“夫心者,立血;肝者,藏血。愁忧思虑则伤心,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肝心二脏伤,故血流散不止,气逆则呕而出血”[1]。此为呕血急性期,朱承汉认为,此时主要表现为气机壅上,火热迫妄,则血溢孔窍,正与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血溢》中描述的“血溢者,上出也。心养于血,故热甚则血有余而妄行”[2]相一致。但壮火食气,气随血脱,急性期过后气虚的本质会更加严重,同时,实火向虚火转变,常见面色萎黄、神倦乏力等表现。
3.瘀血留邪贯始终
瘀血是呕血病程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火热迫妄可以阻碍血液的正常运行而发生瘀滞,元气不足也会导致血液“推动、温煦”功能减弱而形成瘀血,瘀血可贯穿于呕血病的始终,故止血不留瘀是治疗本病的要点之一。
论治特色
论治当从病机、传变入手,针对“元气不足,火热迫妄”的病机,可以看到呕血不仅要责之于血,而且要责之于气;同时还要关注呕血病程中“气逆血溢”向“气虚血亏”的发展。病机与传变规律两者相结合,即可以得出相应的治则:针对气的传变,当先降气再固气;针对血的传变,当先凉血再补血;此外,见瘀化瘀,避开用药禁忌也十分重要。
1.先降气再固气
呕血的诱因往往是情志不畅,诱发肝气冲逆,导致火热内生。治疗上首先当抓住“气逆”这一病机,以降气为先。如《证治准绳》所云“夫口鼻出血,皆系上盛下虚,有升无降,血随气上,越出上窍,法当顺其气,气降则血归经矣”[3]。缪希雍也提及“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4]。对此,朱承汉喜用旋覆代赭汤加减调治,去温燥之生姜、半夏,入栀子、黄芩、龙胆草一类药物,增强清火泻热、沉降气机之力。对于病情相对轻浅者,也可选用佛手柑、芍药、生甘草以柔肝、理气、缓急,制衡逆乱之气。一旦有明显“神倦疲软、萎靡不振”等“元气亏虚”的表现,或是出现出血量过多甚至虚脱的情况,即便患者处在呕血病的急性期,也当以固气为要,降气清火为辅,重用人参、炙甘草等药来补其元气、固其根本。
呕血病的恢复期,治疗上既须重视“元气先亏”这一根本病机,也不可忽略“火热迫妄”对元气进一步的戕害。宗李东垣之旨,元气乃脾胃气血化生而来,其不足代表脾胃功能受损,而脾胃损伤多从寒化,故对于元气亏虚,用药要以温补为主。寒凉清泄在急性期出血证尚可适用,但在后期只会衰败脾土,使得气血化生乏源。故朱承汉特别指出,此时用药当顾护元气,不可寒凉伤中。临床所见自觉发热、汗出频多、面色潮红等虚热症状,正是元气不足、气虚生热的表现。故对于呕血病的恢复期,可选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四君子汤加减调治,恰合“阴血生于阳气”之意。虚热重者,亦可酌加黄芩、黄连、山栀。
2.先凉血再补血
急性出血期的气逆所导致的血热,朱承汉认为,当清之凉之,法宜酸寒、苦寒、咸寒或辛凉,用药可选黄芩、黄连、山栀、大黄、牡丹皮、赤芍、人中白等,其中人中白最善清心经火热。《万病回春·失血》云:“一切血症,皆属于热。药用清凉,俱是阳盛阴虚,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而为逆也。”[5]这正是呕血病中血热病机的印证。针对气逆所导致的血热,朱承汉常用三黄泻心汤来凉血泄火,达到降气的目的。除此之外,朱承汉还喜用地榆、紫珠草凉血止血。若后期元气不足,无以生化血液,朱承汉取“气为血之母”之意,选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四君子汤加减补益脾胃之气。
朱承汉指出,凉血即可降气,补气亦可补血。“降气”与“凉血”针对急性出血期的“气逆血溢”,“固气”与“补血”针对缓解期的“气虚血亏”。抓住由“气逆血溢”向 “气虚血亏”逐渐转变的证候特点,则法度明晰,方药自出。
3.血瘀者见瘀化瘀
呕血病中“肝气上逆”或“元气亏虚”均会导致血块瘀积在内,阻滞不通,可见舌质暗,面色黧黑,皮肤紫斑,脉涩紧沉迟,甚至呕血夹有血块等症状。朱承汉在止血之中兼顾化瘀,使血止不留瘀。对于出血难止,甚至有血块者,无论寒热,可酌加大黄粉、三七粉、白及粉化瘀止血,上述药物既可煎服,也可用凉开水调服。这点与何梦瑶在《医碥》所言“盖瘀败之血,势无复返于经之理,不去则留蓄为患,故不问人之虚实强弱,必去无疑”[6]不谋而合。
4.明辨呕血用药禁忌
呕血用药禁忌颇多,当慎思明辨,既不可过温助火,也不可过寒伤中。朱承汉强调,“气虚络损而失血者,温热药可动血耗阴”,附子、肉桂之类助阳益火,是呕血的忌用之属。其次,“津血互生”,失血之人津液不足,温燥药夺津耗液,故也将苍术、半夏、白芥子等温燥之品列为血证忌药。另,“汗血同源”,还应忌辛温发汗,麻黄、桂枝之类不仅能鼓动卫阳,使汗随阳泄,还能动血,即使失血兼有表证的情况亦不可使用。此外,血不循经,溢出络外,宜安络宁血,故呕血病还当忌辛温行血,如当归、川芎加快血行,反而容易导致血络不固。最后,呕血用药不可一味寒凉,恢复期更当主张顾护脾胃生气,使血归其源。
虽然呕血病机理多端,但若配伍适当,上述忌药也可取得良效。如《金匮要略》黄土汤治脾阳虚之便血,用苦寒的黄芩来制约附子、白术温热动血之弊。同样,朱承汉指出,尽管半夏温燥,但善于开泄结滞、降气定逆,可治中满宿瘀之吐血证[7],若用黄连加以制约,还是能取得较好的止血效果。
5.辨传变虚实
呕血病的治疗首先需要明确病情阶段,再根据传变特点确定证型,并结合具体证候辨证组方用药。在呕血病的急性出血期首当降气收敛、清火凉血,使血循常道;若病情迁延日久,则须重视固摄元气、补血通络,使血得归经。
案例举隅
1.火热迫妄致元气虚脱呕血案
林某某,男,45岁。1973年9月6日初诊。胃脘隐痛10余年,发现十二指肠溃疡3年,此次住院乃吵架后气急所导致的呕血,血色鲜红,血量较大,约100 mL。诊时患者刚呕过血,处于躁狂状态,面色红赤,手足舞动,但握其四肢,发现肌力下降,无法对抗阻力,且舞动渐渐缓慢,似有亡脱之征象,病情危笃。处方如下:制大黄15 g,炒黄连15 g,炒黄芩15 g,生甘草20 g,人参20 g(另煎分冲)。3剂。
患者尽服后,呕血止,未再出现明显狂躁表现,乏力也稍有好转,故嘱其以糜粥自养使胃气来复。静休半月后,患者能自行下床活动,再逐渐恢复日常饮食,一月后病愈出院。
按:情志不畅,内郁化热是呕血的重要诱因之一。该患者来诊时正处急性出血期,结合气急攻心的诱因,以及其人面赤狂躁、呕血血色鲜红的表现,朱承汉推断其主要病机为气逆上冲,火热大生,热灼血络,无以罢休。因病情危笃,以清热泻火为第一要务,急投三黄泻心汤去其火热之象。但又见患者形神渐脱,符合素体“元气亏虚”之根本病机,加之失血量大,急须益元气、防脱变,故再入人参大补元气,至于生甘草,取培植中州、生津益气之用,使脾阳得以升发,呕血亦可得宁。因止血及时,元气耗损并非十分严重,又恐汤药加重胃肠负担,故嘱患者糜粥自养,此亦是取生养脾胃之意。
2.元气亏虚挟火热致反复呕血案
蔡某某,男,33岁。1978年11月1日初诊。患者十二指肠溃疡病史已3年,其间反复呕血、便血,出血量一般,遂于1978年9月29日行胃部手术,但术后13天再次呕血,对症处理后情况稍有好转,间隔2日呕血。1978年10月26日再次手术,术后仍然呕血。现症:呕血血色鲜红,夹有瘀块,大便4日未行,面色少华,四末不温,口微苦,苔薄黄,脉濡数。此乃血热妄行,血中夹瘀。处方如下:制大黄12 g,炒黄连10 g,炒地榆30 g,紫珠草30 g,仙半夏10 g,生甘草10 g,生晒参10g(另煎分冲)。3剂。
1978年11月4日二诊:呕血已止。处方如下:大黄炭10 g,炒黄连3 g,炒黄芩9 g,炒党参15 g,云参15 g,炙甘草6 g,炒麦冬9 g,白芍10 g,大生地10 g,乌贼骨15 g,佛手柑6 g。6剂。
1978年11月10日三诊:未出现呕血,继续观察20余天,病愈出院。
按:本例诊时仅有苔薄黄、口苦、脉数等火热证候,热象并不十分明显。但朱承汉认为,在呕血急性期,无论热象轻重,都须依据“气机逆乱、火热迫妄”的病机进行论治,用苦寒药泻火凉血。故一诊选用大黄、黄连清火去热、祛瘀生新,也是取“泻心即是泻火,泻火即是止血”之意,配伍地榆、紫珠草凉血止血。佐半夏行滞解郁,取“气降则火降”之意。该患者呕血病情反复迁延,虽处在急性出血期,但并无脱证表现,人参力峻,恐闭门留寇,故选用性平之生晒参稍资元气。复诊时呕血已止,但脾胃元气不足的表现较为明显,故将重点放在滋养脾阳,云参、党参两者性味温,同属桔梗科,在温补脾胃、益气固脱的功效上,较西洋参、沙参更为适宜。再加入佛手柑疏理肝气,炒麦冬、大生地、白芍滋阴养血,大黄炭、炒黄芩、乌贼骨止血。剂量调整中暗含治则的变化,一诊予炒黄连10 g取泻火降气之意,二诊3 g则是取清虚火之意。处方巧妙地融降火与补气为一体,宁沸溢之血,固欲脱之气,寓养血于止血之中、温补于降逆之中,全方升降相因,消补兼施,环环相扣,切中病机,因而取效。
讨 论
呕血多由上消化道急性出血所致,出血部位包括食管、胃、十二指肠、肝、胆、胰,原因可见于消化道本身疾病以及血液或全身疾病。有回顾性研究指出,十二指肠溃疡是上消化道出血最常见的病因[8],且十二指肠位于上消化道的末端,其体表投影位于“大气所归,百川之汇”的气海穴附近,与元气关系更为密切。故朱承汉指出,虽可从“元气”角度切入论治上述各种消化道出血,但针对十二指肠溃疡所引起的呕血最为合适。
朱承汉从“元气先亏,火热迫妄”切入呕血病的论治,与现代医学诊疗上消化道出血的方案也具有一致性。针对病因不明的危险性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最新专家共识指出,静脉联合应用质子泵抑制剂和生长抑素治疗,待病因明确后再行调整[9],这与朱承汉“急则治其标,先降气凉血以最大程度减少出血、减少并发症”的思路一致。另外,朱承汉对于“元气”的表述,与血流动力学有相似之处。有实验证明,人参皂苷能够改善休克犬的血流动力学状态,提高血氧含量,减轻组织缺血缺氧及微循环障碍[10],故通过益气固脱,能一定程度恢复血容量并维持重要器官灌注,保护人体机能。此外,朱承汉诊治呕血还有两点独特之处,归纳如下。
1.实证也有虚在前
朱承汉提出,“元气”是呕血病的核心要素,“元气亏虚”是呕血的根本病机。历代医家中,李东垣虽对“元气”一词解读颇深,认为脾胃受损则元气亏虚,但并未将其与呕血病直接联系。龚廷贤、唐容川等人将呕血定性为“实证”[5,11],忽略了其本虚的一面。在出血急性期,定性为“实证”是适用的,它更加明确地指导了临床实践,“清泻实热”的止血效果更为快速、显著。但若从长远来看,患者素体不足,凉血可解一时之急,长期应用必然加重病情。
朱承汉说“呕血患者在发病前就存在元气亏虚的病机”,即是由长期饮食、劳倦、外伤、思虑等因素缓慢发展而来的消化道出血。由此他认为,改善发病群体的体质,早期干预呕血的病程,是中医治疗的重要目标,临床医生应当用整体观来看待疾病发展,治疗“元气先亏”,不能局限于发病当下,需要将疾病发展时间线向前推移,见微知著,考虑患者的发病原因,在发病前期就通过“中药补虚”“调神养性”“节欲慎食”“不妄作劳”“食疗保健”等措施及时截断病程,这也符合中医“治未病”理念。
2.寻找规律防重症
朱承汉提出,“先降气凉血,再固气补血,兼顾化瘀”分阶段治疗呕血,提示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对应的疗法也有所不同。掌握疾病的传变规律,可以从病邪的性质入手。以六淫为例,不同性质的邪气会有不同的特点,风邪轻扬开泄,易伤津夺液;寒邪凝滞收引,易生痰饮水湿;暑邪湿热并存,易袭脾胃;湿邪黏滞,阻遏气机;燥邪干涩,易损津液。至于和呕血最密切的火热之邪,它羁留人体,可耗气动血、煎灼阴津,使素体元气愈虚。通过病性可大致判断疾病的趋势与走向。
除了把握疾病传变规律,还须了解该类疾病可能出现的危重并发症。以呕血为例,该病在急性期表现为呕血不止,中医证属“火热迫妄”,甚则可能并发“四肢湿冷青紫、血压进行性降低等”休克样表现,故治疗上须以止血为首要目标,西医可内镜介入,应用质子泵抑制剂制酸止血,避免危急情况的出现,而中药以“降气凉血”之治,与现代医学一同降低休克发生概率。
辨病论治首当“谨守病机”,这点在朱承汉辨治呕血时表现为:把握“元气不足”的根本病机与“火热迫妄”的急性表现,以及由“气逆血溢”到“气虚血亏”的传变,治疗上急性期降气凉血,恢复期固气补血,同时注意清泻不可过猛,补益不可过早,不然有加重瘀血之患。故在临证中,须深刻把握疾病发展规律,做到审因审证,才能明确法度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