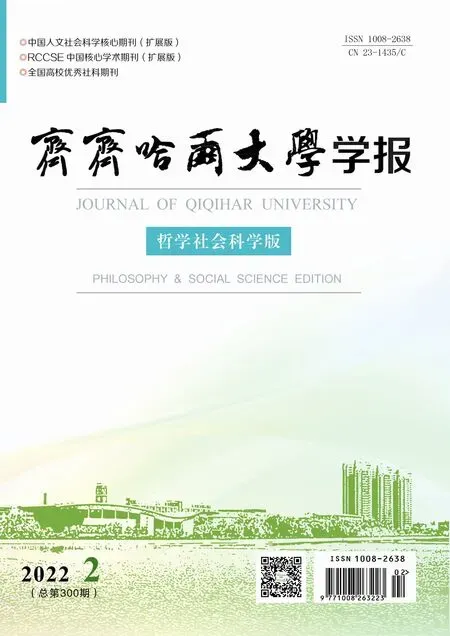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方式
2022-12-26王华胜
王华胜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民间借贷。后来随着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民间借贷的含义扩大到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行为。[1]“自然人借款”一词最早出现于1999年的合同法,它与非自然人借款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合同形式上,自然人借款可以是口头的,而非自然人借款必须是书面的(第197条);二是在生效要件上,自然人借款合同自标的物交付时生效,而非自然人借款则无此要求(第210条);三是在有偿性上,自然人借款如约定不明即视为无偿,而非自然人借款如约定不明则可另行确定(第211条)。新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上保留了原合同法的规定,只是将借款合同自提供借款时“生效”改为自提供借款时“成立”。这一修改意味着在借款交付之前双方的约定不受法律保护,从而使自然人借款真正成为一种要物合同。这种基于自然人身份而对借款行为所作的特殊规定,似乎不太符合古典合同法所奉行的身份平等原则。尽管当代合同法存在着“社会私法”(social private law)的趋向,[2]但“自然人”概念并不代表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或社会角色,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群体而予以特别立法就会面临着一种正当性疑问。
对于自然人借款合同的特殊成立方式,比较权威的解释是“自然人借款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同”,[3]但这种解释似乎是对实践性合同的一种误解。所谓实践性合同也即要物(re)合同,它是源自古罗马的一种特殊合同形式。在古罗马时期,自然人借款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其中只有消费借贷(mutuum)是一种要物合同。而现行的自然人借款并不具备消费借贷的某些特殊属性,所以消费借贷是要物合同并不能证明自然人借款也应该是要物合同。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将罗马法中的消费借贷与现行的自然人借款进行一番比较。因为民法典中的债权法,只有与罗马法传统中相关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和解释。[4]本文接下来将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消费借贷的特点,揭示消费借贷在现代民法中嬗变的原因,进而探讨消费借贷要物方式的合理性,最后分析我国自然人借款与消费借贷之间的差异,以期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方式提出完善的方案。
一、罗马时期消费借贷的主要特征
(一)消费借贷是一种口约式借贷
罗马法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交易行为只有遵循严格的法定形式才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同一种法定形式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交易行为,而同一类交易行为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法定形式。以借贷交易为例,早期常用的合法形式有天平铜块方式(gesta per aes et libram)和要式口约方式(stipulatio)。当天平铜块方式用于金钱借贷时称为“nexum”(耐克逊);用于要式物买卖时称为“mancipium”(要式买卖)。[5]但对于亲戚、朋友之间的日常消费借贷来说,这两种法定形式并不适宜:其一是因为繁杂的形式使日常消费借贷行为变得极为不便;其二是因为朋友邻居之间的生活借贷是一种无偿的施惠行为,其基础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信赖关系。如果要求有证人在场见证(耐克逊),或是要求借贷人不断地用誓言来承诺归还(要式口约),[6]p.163这无疑是对借贷人的一种不信任。因此,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借贷,罗马人通常会在口头约定后直接交付标的物。这种口头方式的借贷罗马人称之为“mutuum”,国内学者常译为“消费借贷”。尽管消费借贷因为不具有没有法定的形式而得不到法律保护,但施惠者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如何帮助别人而不是如何获得救济。
(二)消费借贷是一种无偿的施惠行为
消费借贷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属于一种无偿的施惠性行为。由于这种口头约定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借贷人是否如期还款则完全取决于他的诚信。即使双方有关于利息的约定,这样的约定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如果要进行有偿的借贷,当事人就需要采用天平铜块方式或要式口约方式。
大约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罗马的《西里亚法》(LexSilia)引入了一种新的法定诉讼形式――请求给付之诉(condictio),从而使有关金钱的消费借贷获得了救济。后来的《卡布尼亚法》(Lex Calpurnia)又将该诉讼的救济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一切确定的可分物(酒、油、谷物等),消费借贷的出借人从此获得了全面的救济。[7]当请求给付之诉适用于金钱借贷时,债权人可以提出特定借贷之诉(actiocertaecreditaepecuniae);当适用于可分物借贷时,债权人可以提出返还指定物之诉(condictiotriticaria)。[8]p.591由于请求给付之诉是一种严法诉讼,裁判官对此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所以原告在诉讼中只能请求返还其出借的数目,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原告在消费借贷时约定了利息,该利息部分仍然无法得到保护。所以,消费借贷之所以是无偿的,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进行无偿借贷时才会采用消费借贷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消费借贷的保护方式无法涵盖到利息。换句话说,只要法律不承认消费借贷口约的效力,消费借贷就只可能是无偿的。
(三)消费借贷以标的物交付为合同的成立方式
由于请求给付之诉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原告只要认为被告具有归还一定钱物的义务,就可以对其提出诉讼,而无需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合同关系。这种归还义务的产生,通常是以原告先期的钱物给付为前提的。[7]比如在消费借贷中,出借人必须先向借贷人交付一定数量的钱物,从而在两者之间产生一种债务关系。如借贷人到期不归还同等数量的钱物,出借人就可以对其提出特定借贷之诉或返还指定物之诉。这类诉讼的依据并不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协议,而是一个古老的罗马法原则:即任何一个人不可因自己违反自然公平的错误行为而获利。[9]无论是消费借贷还是错债给付,只要接收钱物的人不归还同等数量的钱物就构成一种不当得利,给付人均可以通过请求给付之诉要求其归还所得的利益。
由于请求给付之诉并不是基于双方约定,而是基于原告的先期约付行为,所以罗马人最初并没有将消费借贷视为一种合同(contractus),而是将其归类为因交付行为所产生的债。比如罗马法学家拉贝奥(Labeo,前54-公元10/11年)曾将债的产生方式分为的三种:“做”(agantur)、“管理”(gerantur)和“订立合同”(contrahantur),其中的“做”就包括物的交付(re)。[10]到了盖尤斯时期,“合同”一词已经普遍用于所有合法的交易协议。在《法学阶梯》中,盖尤斯按照缔约方式的不同将合同为四类,[6]p.162其中的第一类盖尤斯称之为“Re contrahiturobligatio”,意为“通过物的交付所缔结的合同”,也即后世学者所说的要物合同。从盖尤斯的解释也可以看出,罗马法学者仍然不承认消费借贷中口头约定的效力。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合同的成立方式并不是基于双方的合意而是基于标的物的交付,所以标的物交付也就成为消费借贷合同的成立方式。
二、消费借贷在现代民法中的嬗变
(一)消费借贷的商业化
由于消费借贷既不能约定利息,也不能约定还款的时间、地点,所以消费借贷并不能单独适用于商业目的。为了解决利息和还款的时间、地点问题,罗马人通常采用“消费借贷+要式口约”(mutuumcumstipulatione)方式,即在进行消费借贷的同时,再用要式口约方式来约定利息和钱物的偿还问题。[11]比如,在《法学汇纂》中,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带利息的借贷罗马人也会使用“mutuum”这个词,这表明在罗马社会后期“mutuum”已经广泛应用于商业借贷了。既然单独一个要式口约就可以进行商业借贷,贷款人为何要采用这种复合方式呢?其原因在于复合方式更有利于维护贷款人的利益。因为消费借贷是要物式的,即使双方就借贷问题达成了协议,在钱款交付之前贷款人随时可以反悔,并且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采用要式口约方式,则在要式口约结束后贷款人就有交付钱物的义务。很明显,这种复合方式比单纯的要式口约对贷款人更为有利。
由于消费借贷的救济方式是请求给付之诉,而要式口约的救济方式是要式口约之诉,那么在“消费借贷+要式口约”模式中,债权人需要提出两个不同的诉讼还是只提出一个诉讼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罗马法学家提出一种债务转换(novatio)理论,[8]p.600认为先前存在的消费借贷已经被转换成要式口约了。罗马法学家彭波尼(Pomponius)就曾提出:当我们用要式口约来转换一个“mutuum”方式的借贷时,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债是因金钱给付而产生的,而是认为它产生于后来用要式口约所进行的债务转换;因为其意图只是一个要式口约,金钱的给付被理解为仅仅是以完成这个合同为目的的。[12]根据这样的解释,债权人在提起诉讼时实际上只需要提出一个要式口约诉讼,就可以要求债务人返回所借的款项和利息,因为后面的要式口约已经将前面的“mutuum”之债转换成要式口约之债了。通过这种灵活的解释,“消费借贷+要式口约”模式完全可以像单个要式口约那样便利。于是,除了日常的朋友借贷仍然采用消费借贷外,商业借贷普遍采用“消费借贷+要式口约”模式。
随着要式口约的逐渐书面化,在书面形式中要式口约与消费借贷之间的区分已不再明显。随着消费借贷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mutuum”的无偿性逐渐被人们忽视了。结果,19世纪的共同法(ius commune)学者在捍卫罗马要物合同制度时,更多是基于逻辑而非伦理来进行论证。他们认为要物合同在逻辑上是必需的,在概念上是令人信服的。认为债的产生在逻辑上是因为物的交付,所以是这个“物”(res)决定了债的基础和性质,[13]至于借贷的无偿性和口约性已经不再是决定要物方式的因素。共同法学者对要物合同所进行的逻辑论证,虽然为现代民法保留消费借贷的要物性提供了依据,但却使消费借贷丧失了口约性和无偿性。
(二)消费借贷与普通借贷的混同
在罗马的形式主义法律体系中,合同的命名和分类通常是依据法定的缔约形式而不是交易的内容。比如对于借贷行为,根据其采用的形式可以分为天平铜块式借贷(nexum)、要式口约借贷(stipulatio)和要物式借贷(mutuum)。此外,有偿和无偿的法律行为其名称也不相同。比如无偿的寄存叫“depositum”,而有偿的寄存则属于“locatio-conductio”;无偿的借贷叫“mutuum”,有偿的借贷可以是“nexum”或是“stipulatio”。随着这种合同形式主义在现代合同法的消失,合同的划分不再以缔约形式而是以合同的内容为标准,于是罗马时期不同形式的借贷在现代合同法中都统称为借贷。现代合同法通常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述罗马时期不同的合同概念。比如在德语中用来表示借贷的词汇是“Darlehen”,它原本是指邻居之间的帮助性行为,[14]与罗马的“mutuum”一词意思相近。但在1900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中,“Darlehen”既可以指无偿借贷也可以是有偿借贷。
此外,由于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罗马时期的某些概念有时很难在现代语言找到与之对应的概念,结果在用现代概念表述罗马概念时,就无法体现出罗马概念所特有的属性。比如在法语中还没有一个与“mutuum”相对应的词,法国民法典使用用“pret”来统称所有的借贷行为。对于罗马法中的“mutuum”一词,法国民法典称之为“pretdeconsommation”(消费借贷)。因为“mutuum”是一种要物合同,所以与之相对应的“pretdeconsommation”也被法国民法典视为要物合同。实际上,用“pretdeconsommation”来对译“mutuum”并不确切,因为法语中的“pret”(借贷)既可以指有偿借贷也可以指无偿借贷,而“mutuum”却只能是无偿的。可见,随着罗马形式契约体系的消失以及语言表述上局限,罗马时期的各种消费借贷形式在现代民法中已经合而为一了。
三、消费借贷要物方式的合理性
合同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形式主义到诺成主义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无偿的消费借贷在有些国家却始终没有诺成化,其中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施惠者需要予以相应的保护。
无偿的消费借贷是一种施惠性行为,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施惠性允诺通常不应当具有强制性。对此,中世纪的经院法学家曾作过深刻地阐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经院法学家将交易行为分为交换正义和慷慨行为两种类型。[15]交换正义强调的是一种利益上的互惠性,而互惠性允诺应当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相反,慷慨行为强调的是一种利益上的利他性,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德性伦理而非正义原则。依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点,慷慨是指一种财富方面的适度,是将财富以正确的方式、以适当的数量、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的人。[16]如果财富的给予是无原则的,那就不是慷慨而是挥霍;如果给予人在给予时没有感到快乐,甚至是带着痛苦,[16]那么这种给予同样不是慷慨。因此,如果一种施惠性允诺并不是恰当的,或者履行允诺会给施惠者带来痛苦,那么赋予这种允诺以强制力并不符合德性要求。所以,中世纪法学家卡吉坦(Cajetan,1469-1534)认为,在慷慨行为中,允诺者受诺言约束的唯一情形只能是:不履行诺言会对信赖诺言者造成严重伤害,否则允诺者无须对受诺者承担义务。[17]16世纪的法学家康那留斯(Connanus,1508-1551)也曾认为,伤害允诺者的诺言并不应当遵守,除非来源于明示的、包含着这个约定的合同,或者是来源于允诺物的交付。[18]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来说,法律自然应当鼓励人们作出慷慨行为,但也要对施惠者予以适当的保护,以避免因不审慎的允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二)要物方式具有确保审慎的功能
由于简单的口头承诺有可能是轻率的,为了避免施惠者不审慎地作出允诺,对于施惠性行为,法律通常要求双方在达成协议之外还要附加一定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具有一种告诫功能,以确保行为人审慎地做出决定。对形式的告诫功能,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在评述罗马的《辛西亚法》(LexCincia)时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该法的目标是要阻止愚蠢和仓促地赠与行为,而这一目标是通过法定形式来实现的。因为形式都要求一定的时间和仪式,这就给予了赠与者有机会去反思他正在做的事。[19]而法学家耶林除了认可萨维尼的观点外,还提到了形式所具有的警示作用。比如要求当事人签字,可以警示当事人这样的事实:他们正在离开纯粹社会和习惯语境,正在进入法律领域,这将使他们处于警觉状态。[20]以消费借贷为例,在出借人作出允诺之后,法律不承认口头允诺的效力,其目的是让出借人在交付标的物之前能三思而后行,以免轻率地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如果出借人交付了标的物,则可以证明出借人的施惠性允诺是审慎的,此时法律就应该让这种慷慨行为得以实现。再以利他性更强的赠与为例,各国法律通常对赠与有着更严格的形式要求。比如在古罗马时期,实物赠与只有采用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方式才是有效的,否则赠与人有权提出返还原物之诉。在君士坦丁时代,赠与则要采用登记形式。[21]而现代各国大多要求采用公证形式(法国民法典第931条,德国民法典第508条)。在实践中,如果没有采用公证形式但已经交付标的物的赠与,法律也认可其效力,这无疑是让实际赠与具有要物合同的特点。由此可见,对于施惠性的口头允诺,法律通常不会承认其具有强制性。
四、我国自然人借款成立方式的正当性问题
受欧洲罗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民法也保留了要物合同制度。为了与罗马时期的消费借贷相对应,我国创设了“自然人借款”这一概念,将标的物的交付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但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罗马法中的消费借贷(mutuum)与自然人借款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消费借贷必须是无偿的,而自然人借款则可以是有偿的;其二,消费借贷是口头约定的,而自然人借款则可以是书面的。由于无偿性和口约性是消费借贷成为要物合同的合理性基础,既然自然人借款缺乏这样的基础,那么规定其为要物合同就必然存在着合理性疑问。
首先,将有偿借款规定为要物合同会损害借款人的利益。有偿借款合同是一种双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法律对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特殊保护的必要。如果有偿借款合同是要物合同,则意味着贷款人在钱款交付之前随时可以反悔,在势必使借款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一般来说,贷款人在借款合同中处于强势地位,强势地位的贷款人反面获得特殊的保护,这种规定的合理性诚实让人难以理解。有学者认为,因为自然人借款大多是无偿的,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法律有必要确认自然人借款合同的实践性。[22]然而,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是值得疑问的。据中信证券的研究报告统计,早在2011年中国民间借贷总规模就已经超过4万亿,其中自然人的参与率比较惊人。比如在江苏省泗洪县的石集乡约30%左右的农户参与了借贷行为;[23]而在珠三角2011年民间借贷总量达3000多亿,其中多为熟人朋友之间的拆借;[24]在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参与了民间借贷。[25]尽管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来统计自然人借款在民间借贷中所占的比例,但可以想见,随着我国民间金融活动的发展,无论是从整体规模还是从纠纷发生率来说,自然人之间的有偿借款远远多于无偿借款。退一步来说,即使当前的自然人借款“大多”是无偿的,也不能证明将有偿的自然人借款规定为要物合同具有合理性。
其次,将书面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存在保护过度的问题。由于口头方式的施惠允诺有可能是轻率的,为了确保施惠者审慎行事,基于一种父爱主义原则,法律要求在口头允诺之外附加一定的形式。除要物形式之外,书面形式或公证形式同样具有告诫功能。这意味着如果贷款人已经采用了书面形式或公证形式,就足以表明其出借行为是审慎的。如果在种情况下还将借款规定为要物合同,则是对贷款人的一种过度保护。我国民法典将自然人借款规定为要物合同,而不考虑它是否采用了书面形式,实际上是忽视了书面形式与要物形式在功能上的相似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借款合同成立方式的规定,其合理性是难以证成的。考虑到我国未来自然人之间的有偿借款会日益增多,因此有必要对民法典第679条作出限制性解释:将“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的规定仅限于无偿的自然人借款。
综上,要物式的消费借贷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合同法是否还应该保留这一制度,学者们对此一直争议不断,大陆法系各国的态度也不一致。比如法国依然保留了消费借贷为要物合同的传统,而德国、瑞士民法典则完全废除了有关要物合同的规定。至于我国民法是否应该坚持消费借贷的要物方式,自然是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无论是选择保留还是废弃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要物方式存在的基础。对于消费借贷来说,罗马法要求以标的物交付为成立要件,其合理性是以借贷行为的无偿性和口约性为前提的。如果抛弃这两个前提,武断地将自然人借款规定为要物合同,这无疑给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方式带来一种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