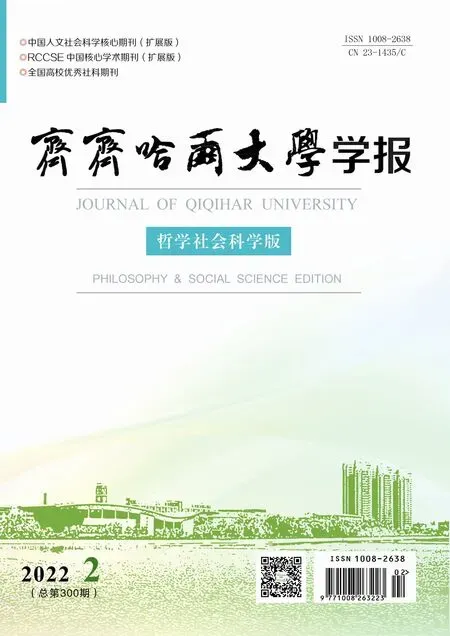论《庄子·说剑》中“天子之剑”的境界哲学
2022-12-26安汝杰
安汝杰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化”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在庄子学说中常与“物”一词联用,庄子也有所谓“物化”的思想。这一与物俱化的思想在《庄子·说剑》篇中的天子之剑上也有所体现,而天子之剑又已臻于合于造化、超乎阴阳的逍遥境界。《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171这就是说,天子之剑的逍遥境界是庄子与物俱化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那么,应该如何以“化”来追索庄子的逍遥本义?此“化”对于诠释《庄子·说剑》篇中天子之剑的工夫境界又有何启示?笔者将在宋代注庄者罗勉道等人以“化”解庄子逍遥真义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回答。
一、剑术境界与“化”之小大
“化”在《庄子》一书中共出现70多次,如《逍遥游》篇中的“化而为鸟”,《齐物论》篇中的“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之谓物化”,《人间世》篇中的“将执而不化”、“胡可以及化”、“是万物之化也”,《德充符》篇中的“命物之化”,《大宗师》篇中的“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以造化而大冶”、“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安排而去化”。
(一) “化”是逍遥的本有之义
“化”在古汉语中有变化、削除、大自然、教而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乞讨等义项,而以“变化”义最具有哲学诠释潜能。“化”在庄子哲学中可与“变”互释,方立天先生在解释庄子“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思想时说,“万物的变化,时而虚空,时而盈满,没有固定不变的形状。未来的年岁不能提取,将逝的时光难以挽住;消灭、生长、充实、空虚,终结了再开始,这是在讲大道的方向,阐述万物的道理。万物的生长,就如骏马的奔驰一般,没有一个活动不在变化,没有一时不在迁移。总之,万物都是不固定的,都在永恒的变动转移之中,无一刻静止,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流”。[2]145《逍遥游》篇中的“化而为鸟”之“化”即有变化之义,职是之故,宋代学者罗勉道以“化”解庄子“逍遥游”本旨亦有其合理性。
“化”是庄子《逍遥游》篇的主题之一,“《庄子》的外篇、杂篇也宣传‘逍遥’论”,[2]397由此《说剑》篇中所言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与庶人之剑亦内涵着“化”的哲学。宋代学者罗勉道甚至认为《逍遥游》篇的本旨在于一“化”字,如其在《南华真经循本》一书中即说,“篇首言鲲化而为鹏,则能高飞远徙,引喻下文,人化而为圣、为神、为至,则能逍遥游。初出一‘化’字,乍读未觉其有意,细看始知此字不闲”。[3]2“化”是渐渐的“变”,“变”是迅速的“化”,变与化是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不同的运动发展阶段,如北宋理学家张载即说:“变,言其著;化,言其渐”。[4]70“化”是隐微的、不显著的运动状态,由“变”到“化”,是显著到隐微的过程;同时,“变”、“化”又统一于鲲化为鹏或《说剑》篇所暗含的庶人之剑化为诸侯之剑、诸侯之剑化为天子之剑的境界提升过程中。鲲化为鹏,其“质之大者,化益大也”,[3]9是化之大者,同于诸侯之剑的意境,而蜩鸠是“化”之小者,其化同于庶人之剑运乎肢体之间的意境,庶人之剑拘累于“上斩颈领,下决肝肺”[5]265的剑术招法之域,并不得逍遥,天子之剑由庶人之剑、诸侯之剑的层层否定而来,已入自在的逍遥境界。
(二)“逍遥”的境界之分
《逍遥游》篇中的鲲鹏能扶摇而上九万里,可谓是化之大者,蜩鸠飞不过榆枋之间,可谓是化之小者,这一方面符合庄子一贯的抑小扬大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表明,境界的高下在于化有大小。罗勉道说,“鲲言大不知几千里,鹏言背不知几千里”[3]2,鲲化而为鹏,“要见天池,距天实有九万里,太虚寥廓,神游无碍”,[3]9自得其乐的蜩鸠嘲笑大鹏高空起飞也同“人之以小见而笑大道者”。[3]6同类,虽看似如魏晋时人郭象所言“适性逍遥”,实则因境界低下而未能逍遥。逍遥即能“游”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拘累,“游”“其意主要包括形体之游和精神心灵之游两方面,前者为庄子游的形而下层面,而后者则构成了庄子游的最为主要的境界层面”。[6]162同理,《说剑》篇中赵文王在见到庄子之前的剑术境界与《逍遥游》篇中的蜩鸠处于同一层次,即是说赵文王以诸侯身份持有的是庶人之剑,也因之需要如庄子般懂剑道的说客晓之以习剑用剑之理,以促使其剑术自觉地从庶人之剑到诸侯之剑再到天子之剑的境界跃升,赵文王剑术境界开始提升的标志就是《说剑》篇结尾处昔日与赵文王练剑的庶人肉体生命的人为结束。
逍遥,即与物俱化,也即免于“物累”。宋代学者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逍遥游》开篇即说,“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器之累,惟至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7]154在王雱看来,至人经由无我、无心的逐渐摆脱形器之累的体道过程而与无方所、无上下的道融合为一,与道为一也即与物俱化的体道状态,与物俱化即能“物物而不物于物”,即能进入自在无碍的逍遥境界,这种逍遥境界同样为《说剑》篇中的天子之剑所共有。与天子之剑的逍遥境界相比,庶人之剑由于拘于物累,受制于阴阳而是“化”之小者,化之小者之所以没有合于道、不自由,一是自身肉体的束缚,一是外在存在物的束缚,束缚就意味着庶人之剑“有己”、“有待”,“有己”和“有待”决定着庶人之剑不能进入自在逍遥的剑道境界,它在庄子《说剑》篇中的剑术境界中处于最低层次,是化之小者。
二、天子之剑的“优等逍遥”与庶人之剑的“劣等逍遥”
庄子《说剑》篇中同于蜩鸠意境的庶人之剑的境界自然是劣等逍遥,合于四时、吞吐日月的天子之剑的境界属于优等逍遥的层次,而境界处于天子之剑与庶人之剑之间的诸侯之剑可谓是中等逍遥,由于天子之剑“化”的对象是诸侯,诸侯之剑“化”的对象是四乡,而庶人之剑“化”的对象仅仅是斗剑场域中一己和对手的肢体。
(一) 天子之剑是“化”之大者
郭象在《逍遥游注》中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147宋人王雱将郭象的解释概括为,“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7]154冯友兰先生认为:“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1]148在郭象及其后学看来,大鹏、蜩鸠虽形体大小不同,其飞也有高低远近的不同,但由于它们都能各当其任,都能自适其适,在其性分内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因而都一般无二地进入了逍遥境界。从总体上看,郭象的逍遥义一方面为其政治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又符合庄子的“齐物”思想,但将万物不作人为分别而将其视为一物的前提是万物的分别,即是说不分别以分别为思想基础。正是基于此分别,罗勉道根据鲲鹏与蜩鸠“化”之大小,将逍遥也分为优等逍遥与劣等逍遥,如其所说,“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为逍遥游有优劣”。[3]15
庄子《说剑》篇中的天子之剑与《逍遥游》篇中所谓“至人”境界相同。何谓天子之剑?庄子《说剑》篇中说:“天子之剑,以燕溪石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5]265庄子指出,一个人达到逍遥境界就会成就理想人格,成就理想人格者就是至人、神人、圣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4至于“无己”、“无功”、“无名”,冯友兰先生注云,“无己故物顺,顺物而至矣”,“夫物未尝有谢生于自然者,而必欣赖于针石,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助,与至理为一,故无功”,“圣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是以名其所以得也”。[1]150无己顺物者是“圣人”,顺物自然者是“神人”,“圣人”合于物性而不知其所以然。圣人之逍遥在于会万物之妙,通万物之性,以无为之策而使天下各安其位。圣人无为,神人因化之无迹而“神”,至人则兼圣人、神人二者之长而“无己”、“无我”,无我则能超越,同时这也是天子之剑的至真逍遥境界,由于天子之剑合于四时的运行法则有神人无迹的人格气象,其匡扶诸侯的剑道之用也契合圣人无为而治之旨。
(二) 庶人之剑是“化”之小者
何谓“庶人之剑”?庄子《说剑》篇中说:“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5]265庶人之剑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所习用的剑法招式,庄子以蓬头垂冠来描述其击剑时的衣着,以“瞋目而语难”形容其神态,以“上斩颈领,下决肝肺”道出其剑法招式,以“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状写其功用。这就是说,庶人之剑的作用对象是人的肉体,以制服、杀伤对方的身体为技击目标,其招式无非是停留在“术”的层面上的击、刺、进、退、拦、拿、躲、闪、踢,但这些要素聚合的前提是百姓之“命”的存在,庶人之剑也因其受制于“命”之所累而只能处于劣等逍遥境界,据罗勉道所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为逍遥游有优劣”。[3]15由此说来,庶人之剑“化”之范围仅仅是敌对双方的肉体生命,是化之小者,化之小者与“遥”而未“逍”的鲲鹏相比,其“化”是“逍”而未“遥”,因而处于罗勉道称之为劣等逍遥的境界状态。
庄子《说剑》篇将庶人之剑向诸侯之剑再到天子之剑的境界转进视为一个完整的剑道修炼过程,即是说庶人之剑、诸侯之剑是向上通达天子之剑逍遥境界的一个必由阶段,而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庶人之剑经过类似于黑格尔但又与之不尽相同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层级递进而进入剑道至境,成此境界的天子也即庄子所谓的“至人”人格。庶人之剑与诸侯之剑、天子之剑相比,是化之小者,从庄子万物皆化的观点来看,小者之化的“化”之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其本身亦符合万物化之道理。宋代解庄者“罗勉道仍以‘化’字去解有用与无用,以其意,若以人为设定之工具价值去评判事物,则事物所体现之‘无用’则为‘未化’,‘未化’即非逍遥;若能顺遂物性之自然或因事物之资质而用之,则事物即可由‘无用’而转为‘有用’,此‘则化矣’,即为逍遥。”[8]98庄子《说剑》篇认为,庶人一旦肉体生命结束,其所习之剑即于国事无用,但这“无用”由于“化”之作用而有推动庶人之剑向天子之剑“大用”境界提升的动力意义。
三、庶人之剑向天子之剑的境界提升
“无用”的庶人之剑实则寓含着“大用”,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化”,由于顺遂物性之自然的化即可逍遥。进一步言之,庶人之剑的劣等逍遥有向天子之剑的优等逍遥进行境界转进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与物俱化。
(一) 与物俱化即入自在逍遥的剑道境界
天子之剑代表着庄子《说剑》篇所推举的剑道境界,由于合于四时,与物俱化的天子之剑已入逍遥之域。天子之剑已超越剑器大小、长短及剑术招法等形器方面的拘累,无待于物,“物物而不物于物”,是为逍遥境界。“无待”即无累,无累则逍遥,魏晋时人顾桐柏曾言,“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9]6-7与之同期的名僧支道林以“物物而不物于物”[10]81的命题来框定庄子一书所言的至人逍遥之义。宋代学者王雱认为:“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器之累,惟至人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7]154显然,王雱在以“无累”解庄子逍遥义的同时,又继承支道林“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致思路向。“物物者”,即是道,由于“道”一方面是超越于物之上者,另一方面却又能与物俱化,是物之化的主宰者、推动力。在王雱看来,至人能够体认无方、无物的大道,因免于形器之累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7]197的体道境界。而天子之剑显然已由无我、无心的挥剑讲武之所而进入与物俱化、自在逍遥的剑道至境,此境亦是习剑者的至人境界。
庶人之剑向天子之剑境界提升的关键在于与物俱化。与物俱化,即入自在逍遥的剑道境界。以世俗的价值判断来看,“无异于斗鸡”的庶人之剑其主人一旦命绝身亡,即于国事无功,练剑的庶人在庄子《说剑》篇结尾处以自杀的方式人为结束肉体生命的事实表明,庶人之剑也并非全然有益于习练者的身家性命。但庄子又有“无用中寓大用”的思想,这表明庶人之剑的用处在于它使喜剑的赵文王等诸侯意识到诸侯身份并不必然地标配诸侯之剑,即是说赵文王剑道境界从遮蔽到显现的前提是庶人之剑的被否定,其契机是习剑庶人的自杀。庶人的自杀及庶人之剑的被否定显示出赵文王的庶人之剑由向诸侯之剑,进而到天子之剑境界提升的可能性,其可能性在于“化”,与物俱化,即可逍遥,由于“若能顺遂物性之自然或因事物之资质而用之,则事物即可由‘无用’而转为‘有用’,此‘则化矣’,即为逍遥。”[8]98与物俱化,即合于物性之自然,如此庶人之剑即可同于天子之剑的剑道境界。罗勉道即说:“夫天之所赋,各有定分,岂可强同蜩、鸠、斥鷃于鲲、鹏哉!而人则无智、愚、贤、不肖,皆可以阶大道,然亦有自视若蜩、鸠、斥鷃者焉。……苟能因其资质用之,随事而化,岂失其为逍遥游哉。”[3]15-16“随事而化”,也即与物俱化,在罗勉道看来,不论是智、愚、贤、不肖之徒都一般无二地有“可以阶大道”的可能性,进一步言之,庶人之剑若能与物俱化,顺物性之自然,即可跃升至天子之剑的自在逍遥之境。
(二)庶人之剑“化”之潜能
不仅天子之剑有“化”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本质,庶人之剑亦有化之潜能,否则庶人之剑向天子之剑的境界提升就没有可能性,没有可能性就不会有现实性,若没有现实性,“化”的哲学就难以展开自身的概念与现实的融通、转化运动。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某物成为一别物,而别物自身又是某一物,这某物自身同样又起变化,如此递进,以至无穷。这种情形从反思的观点看来,似乎已达到很高甚或最高的结果。但类似这样的无穷进展,并不是真正的无限。真正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从过程方面来表述,就是:‘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11]201“在别物中返回自己”可与“与物俱化”相互格义。天子之剑的逍遥境界从庶人之剑、诸侯之剑的非逍遥意境而来,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又由于不论是何种剑都有道与器两个层次,天子之剑亦有其形制大小、攻防招法等方面的自身转化,即是说天子之剑也可以有其斩诸侯杀庶人的具体之用,它的逍遥也非绝对无限度,它认识自身逍遥境界是以庶人之剑、诸侯之剑为其境鉴,也正是在否定后二者境界的基础上才“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天子之剑是剑道境界的化之大者,“‘化’可以是造化,可以是参赞化育;甚至也可以是物化,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隐含着道家美学”[12]131与哲学的真精神。
境界稍高的诸侯之剑是对庶人之剑的直接否定,而与鲲鹏同其意境的诸侯之剑的境界是“遥”而不“逍”,鲲鹏虽能腾空而上九万里,“亦不免乎阴阳之累,是以摄制于造化而不能逍遥”,[13]3即是说诸侯之剑受制于阴阳而未入逍遥之境,而“无异于斗鸡”的庶人之剑更是等而下之,居于剑道境界的最底层。而属于中等逍遥层次的诸侯之剑本身亦有向上和向下一路的通贯作用,其向上一路可接近天子之剑的逍遥境界,由于诸侯之剑亦能“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5]265其向下一路也有安服众邻,匡扶四乡的作用。就此而言,诸侯之剑与庶人之剑招法变化的共同规则是,“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如环之无端”。[13]3如果说庶人之剑到诸侯之剑再到天子之剑的工夫进阶是习剑者在践行的一种向道的境界上升运动,那么剑道散而为阳进阴退的剑法招式,剑法招式分化为俯仰翻转等身体动作则是道下降为器的逆向运动,而逆向与正向(上升)运动由于其受制于阴避阳、阳化阴的剑术法则的制约根本上还是“有为”,有为则不能于物无累。庄子《说剑》篇即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5]265“为剑”是“有为”的具体体现,“为”即人为,人为或是庶人之剑的“逍”而未“遥”,或是诸侯之剑的“遥”而未“逍”,二者皆因受制于阴阳而未能逍遥,而超越阴阳又合于阴阳的天子之剑已入剑道的逍遥境界。
四 、境界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超越阴阳、免于物累的天子之剑本身即是剑道境界的哲学象征,同时,天子之剑的这种剑道境界已入任运自在的逍遥之域,而与诸侯之剑及层次最低的庶人之剑相对应的只能是同于鲲鹏意境的中等逍遥与同于蜩鸠意境的劣等逍遥。天子之剑的剑道境界经由习剑者的“艺术创造”而转化为剑术意境,其中内蕴着由道到术的哲学遗产抽象继承问题。
(一) 由剑道境界到剑术意境的“艺术创造”
“境界”是一个合成词,“境与界二词,都是界域的意思,二者无甚分别,可以单独用境,也可以单独用界。王国维有时就单独用一境字代表境界,如《人间词话》第26条谓‘樊抗夫谓余词……凿空而通,开词家未有之境’,这个境指‘用意’而‘力争第一义处’,它当然是境界;如写境与造境之别,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别,都是”,[14]188-189“境界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或本质,它不可分析。而意境一词只有当做境界即纯粹直观理解,才不可分析”[14]189,即是说境界比意境更具有本体不可分析、难以言说的形而上意蕴。简言之,境界和意境分别用于庄子《说剑》篇中天子之剑与诸侯之剑、庶人之剑所达到的境界层次之称。此外,“境界”与“意境”都内含有“境”这一概念,“境指景物或对象,所谓‘观物’”,[14]189如果说庶人之剑、诸侯之剑的剑术意境属于有我之境,那么天子之剑作为剑道的哲学象征,其境界自然属于与物俱化的无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4]187(《人间词话》第3条),而“以物观物”在庄子《说剑》篇中就与天子之剑“与物俱化”的剑道境界相对应。
天子之剑发挥作用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冯友兰先生指出,《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不需要继承,但《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句的“抽象意义”依然有其用处。[15]94-95《说剑》是庄子一书的杂篇,“《庄子》的外篇、杂篇也宣传‘逍遥’论”,[2]397由此《说剑》篇中所内蕴的剑道哲学遗产是庄子逍遥思想的具体展现,其中已入自在逍遥之境的天子之剑的境界哲学遗产抽象继承的可能性在于当今习剑者以之为剑术范本的创造性转化,而这种转化本身就是“艺术创造”。宗白华先生认为:“一切艺术创造问题,即在如何将无形式的材料造为有形式的,能表现其心中意境的另一实际”,“即在使材料象征化,形式化,而表现其意境”,从而“将作者心中境界表出,输入他人之心境中”。[16]547所谓“输入他人之心境中”,即是指抽象继承的代际“默认”,可以说是天子之剑剑道境界的隔代“输入”,输入以“输出”为前提。天子之剑的境界输出为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意境,这些意境植入习剑者的攻防意识中,从而使剑道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得以可能。
(二) 以身体技艺为基础的“抽象继承”
天子之剑在庄子《说剑》篇中是一种治国安民的政治哲学隐喻,以剑喻治国理政也就意味着天子之剑的招式技法相较于以杀伤对手身体为目的的庶人之剑具有更多的抽象意义,天子之剑所达到的层次也只能用难以言说的“境界”一词来接近它,并且这种境界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须以庶人之剑“‘武术套路’的存在形式、‘拆招喂手’的训练方法”[17]49等身体技术为入手之处。从代际“默认”与隔代“输入”的角度而言,庶人之剑也是一种“自在存在”,“它的自在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他存在;自在存在,作为无自我的或无主体的东西,真正说来,是被动的东西,或是为另外一种自我而存在的东西”,[18]118即是说庶人之剑攻防进退的有为的“有我之境”以天子之剑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之境”为其归宿,它的“自我”是需被诸侯之剑、天子之剑递次否定、扬弃的“自我”,也正是这种被否定,天子之剑完成了它境界哲学的抽象继承,庶人之剑攻防进退的日夜操练也由一般民众个别技击意识的外化而提升为普遍性的剑道创造。黑格尔即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说,个别意识的“目的就是普遍的目的,它的语言就是普遍的法律,它的事业就是普遍的事业”,[18]119-120由此说来,能够在诸侯之剑、天子之剑那里扬弃其局限性的庶人之剑是天子之剑境界哲学遗产抽象继承的立足点。
天子之剑哲学遗产抽象继承的范型之一就是近代拳学宗师王芗斋先生所创立的意拳。王芗斋先生在《论意拳之哲理根据》一文中援引庄子“物物者非物”一语来论意拳的本体。先生道,“意即使物质成为物质,并非物质,意拳主张一切力量都是精神之集合,亦可谓力者非力也。换言之,使力成为力者并非力,乃精神也、意念也。此即意拳所以名为意拳之实质所在。”[19]87意拳以“意”为哲学本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将“意”释为“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志即识,心所识也。意之训为测度,为记。训测者,如论语毋意毋必,不逆诈,不億不信,億则屡中。其字俗作億。训记者,如今人云记忆是也。其字俗作憶。”[20]506-507由“心”可知“意”,“意”是“心”之已发,“古人认为心是思维器官,从心里发出的声就是人的想法”。[21]692“意”有“感知”义,如《荀子·正名》篇中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22]840“天官”,即感觉器官。此处“意”“物”联用,意物就是以感觉器官感知物,而感觉器官在古人看来就是“心”,“心”通过“意”作用于“物”。“心”是未发,“物”是已发,而“意”就处于已发与未发之间。如果说,未发之心是“体”,已发之物是“用”,那么“意”则是处于心、物之间的“相”,相具体而言就是意拳的“形”,如青龙探爪、野马亮蹄等形。王阳明也说,“意之所在便是物”,[23]13也就是说,“心”之所发即是“物”,物是“招式技法的‘存身之所’”。[24]93而王芗斋意拳将本处于心、物之间的意提升为该种武术派别的美学本体,足见其武术哲学思想的抽象继承精神在于形成心-意-物的创造性转化或以拳拟剑、拳剑合一的道器贯通机制,这足资使其成为庄子《说剑》篇中剑道哲学遗产抽象继承的范例。
综上所述,庄子齐生死,忘物我,把自己虚构的无差别性赋予世界的本根,又反过来以本根的无差别性作为自己追求的认识和修养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提出的“物化”。物化是指生命的转化以及生命之循环无端,如庄周梦蝶之喻,周与蝴蝶,虽然有分,但大生命是循环不息的,所以二者之间虽分,而又可以互相转化。化的对象是“物”,作为天子之剑“化”之对象的诸侯之剑、庶人之剑在庄子《说剑》篇中形成一种上下贯通、周流循环的剑道境界提升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化与被化本身也随着习剑者剑道境界的提升在事实上参与着万物宇宙的大化流行,这自然是宇宙之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是说化本身也变动不居,因而名之曰“与物俱化”。庄子这种“与物俱化”的哲学思想在《说剑》篇中天子之剑的境界上有所体现,而揭示出这种境界所蕴含的剑道哲学遗产及论证其抽象继承的可能性则是本论文的目的所在。此外,庄子《说剑》篇所内蕴的其它哲学遗产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