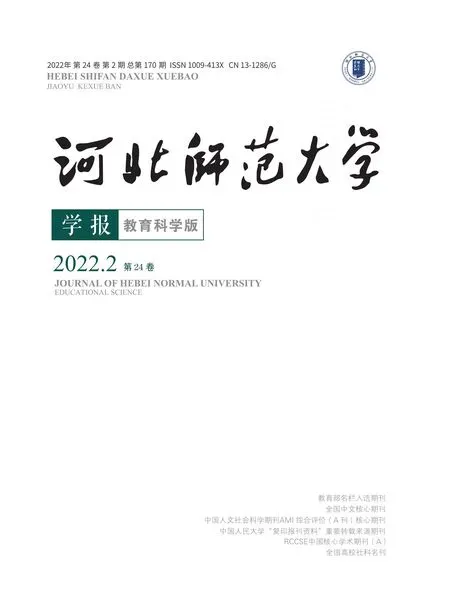高等教育评估文化建设
2022-12-25常桐善
常桐善
(1.加州大学 校长办公室,美国加州 奥克兰 94598; 2.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评估是高等教育运行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保障教育质量、践行社会问责的关键。但如何确保评估的有效性,尤其是完成以评促改之初心,仍然是当前教育管理部门以及高校面临的艰巨挑战。美国高等教育评估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大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评估效果仍然有与时俱进的提升空间。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对高校本科办学质量和学科进行评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建设,已初步形成了反映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特色的模式,但成就、成效与困境并存。就中美高等教育评估而言,建设具有凝聚力的评估文化是改进评估效果、摆脱困境的关键所在。如理查德·贺士(Richard Hersh)和理查德·克灵(Richard Keeling)所强调的,营造校园评估文化是提升评估效果的关键……大学必须通过重构评估文化凸显大学教育和学习的优先地位[1]。翟亚军和王战军也指出:“重塑评估制度、重构评估伦理和重塑评估文化,营造优质高等教育评估软环境,已成为提升高等教育评估质量的迫切需要。”[2]
首先,美国常用的与评估活动相关的术语包括“evaluation”“assessment”“accreditation”“review”“appraisal”等。这些术语翻译成中文时常用“评价”“评估”“认证”“审核”等。除了“appraisal”通常是指教职员工的绩效评价外,其他几个术语虽然有各自特定的意思,如“assessment”常指学生学习成果评估,“accreditation”则特指认证,“review”是专业/学科评价,但这些活动包含的内容都与中国目前开展的本科教育质量和学科评价相似。本文通用“评估”主要是与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名称中使用的“评估”和学科评估中的“评估”保持一致,以便读者理解相关内容。所以,除了特别强调外,本文所阐述的评估文化建设均适应于所有相关的评估活动。
其次,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常常反映了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对某一事物的习惯和信仰。高等教育评估文化就是在高等教育质量领域形成的共识和大家共同遵循的习惯。艾莫斯·莱考斯(Amos Lakos)和雪莱·菲普斯(Shelley Phipps) 将其界定为:“评估文化(a culture of assessment)是组织基于事实、研究和分析制定政策的组织环境,并以此规划学校提供的各项服务,优化教育成果,影响服务对象。”[3]温迪·威娜(Wendy Weiner)从高校的教育目标、评估概念、教师参与、评估技能培训、评估计划、学习成果评估、学科评估、大学效能、信息共享、改进行动等15个领域阐述了评估文化的塑造[4]。中国学者在评估文化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用“评估文化”和“评价文化”这两个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查看相关研究论文,共查到42篇文章,而且只有一部分文章与本文阐述的高等教育评估文化有关。其中,张继平从评估生态性角度对评估文化的界定比较完整。他强调,评估文化是“促成评估主客体的思想、行为、动机、价值观等和谐统一的氛围与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中,参评高校能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评估,以原始的状态对待评估,以真实的‘面貌’示人,以形成客观的评估结果”[5]。 显然,评估文化涵盖的维度非常广泛。本文从评估组织管理、质量标准、证据、参与、改进等五个方面简单介绍美国评估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组织管理文化
组织管理是评估文化建设的基础,包括管理机构、职责职能、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建设。美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组织管理可以粗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层面,包括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主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同时通过审批第三方评估机构、经费支持、贫困学生资助、问责、审计、绩效评价等手段管理评估活动,并营造政府负责的评估法治文化氛围;二是社会层面,包括第三方评估机构、咨询机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默契配合,共同构建有利于高等教育评估的社会文化环境;三是大学内部的评估机构,这是三个层面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形成了包括评估专家、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在内的评估委员会、学校层面的评估管理办公室、学科/学院评估协调人员、提供数据分析的院校研究办公室等网络状组织管理结构,是实施评估工作的主体,并在营造校园评估文化中担负重要职责。当然,这三个层面之间也通过各种评估实施工作、培训、数据交换、咨询、问责、结果公开等形式开展密切合作,构建彼此信任、信息透明的评估组织管理文化氛围。
除了政府层面的管理机构外,社会层面和学校层面的评估机构都有强大的专业评估团队。美国很多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设置评估、测量等方向,为美国高等教育评估培养了大批集高等教育管理、教学及评估理论和实践技能相结合的评估学术研究和实践人员。另外,美国高校的评估委员会通常是学术委员会的一个分委员会,或者是由教务长与学术委员会共同领导的由各学科教师和各领域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为学校层面的评估工作提供专业指导。所以,学校层面的评估人力资源构成不仅包括从事学术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包括从事评估的职业管理人员,形成了浓厚的职业与专业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的评估组织管理文化氛围。
二、质量标准共识文化
质量标准是高等教育办学的准则,是评估赖以有效实施的前提。美国高等教育评估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大学学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简称AAU)制定的以提升博士教育质量为目的的博士专业质量标准,后来延伸为美国博士专业的学科评估标准。几乎在同一时间,AAU也开发了本科教育认证标准。后来区域认证机构相继成立后,AAU终止认证工作。但AAU通过规范大学办学标准提升大学办学质量的行动开创了美国高等教育规范质量标准的先河,对美国评估质量标准共识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一百多年的认证实践也证明,质量标准在评估中所展示的坚韧刚强作用是有效践行评估工作的前提。
当然,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和稳定,美国以问题为导向的评估日渐盛行。其中学校内部开展的学科评估更加聚焦于解决学科发展的问题。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学科评估就是围绕一百多个问题诊断和分析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学科愿景发展策略。但学科评估仍然不能完全脱离与对标高校的比较,也就是与行业质量标准的比较,亦称之为标杆比较(benchmarking)。另外,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高校实施的学生就读经历(learning experience)、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和增值(value-added)等评估为认证、学科评估注入了新鲜的评估血液,使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从“输入-输出”(input-output)评估迈入了聚焦教育成果的“输入-成果”(input-outcomes)的评估发展历程。而后者,也更加关注质量标准,形成了“知己知彼”,共同提升的质量评估文化。全国性学习投入调研(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6]和研究型大学就读经历调研(Student Experience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SERU)[7]堪称本科教育质量标准共识文化建设的典范项目。
三、循证文化
简单地说,评估就是回答诸如教师教了什么、学生学到了什么、学生毕业后能做什么、如何改进办学绩效等问题的过程。显然,证据是回答这些问题唯一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证据便无法衡量教学是否达到了质量标准,评估的有效性也便会受到质疑。为此,大学必须构建评估的循证文化,养成基于事实、研究和分析开展评估的组织环境和校园文化氛围。事实上,评估的循证文化也是科学决策和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决策模式的奠基人赫伯特·西蒙(Hebert Simon)提出的“信息收集-方案设计-方案选择”的科学决策三步骤[8],以及罗素·艾可夫(Russell Alcoff)提出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的金字塔决策模式[9]都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循证决策文化的重要性和实践路径。这些模式也可用于诠释和设计评估的循证文化建设路径。
在循证文化建设的具体操作中,美国高校的经验是加强院校研究工作。美国高校的院校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其初心是大学自查,后来拓展为通过数据收集、分析、报告,支持大学决策过程的组织机构。事实上,院校研究兴起的时期也几乎与科学决策模式和计算机决策支持工具诞生处于同一时期,其发展与“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所涵盖的大数据建设、信息挖掘、网络报告等领域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中,受信息时代信息文化的影响,院校研究也形成了别具特色、服务大学决策的高等教育院校研究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在高校内部根深蒂固,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大学赋予院校研究数据治理的重要职责,自然就承担评估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所以,院校研究文化为评估循证文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文化养料。
四、参与文化
帕特·哈钦斯(Pat Hutchings)曾强调,教师参与评估是保证评估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黄金准则”,因为教师参与评估是评估结果能在课堂上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10]。但目前的高等教育领域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都在呼吁学生要积极参与学习等各类活动,但教职员工却没有积极参与能够提升教学质量的所有活动,评估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部分教职工也参与了大学认证、学科评估等活动,但并没有把评估这项活动有效地与自己的教学、服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目前的很多教学和服务活动是忽视质量标准的。教师没有把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设计嵌入到课程教学中,行政服务人员也没有把改进教学质量的有效理念融入到自己的行政管理决策之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碎片化”教学、“碎片化”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本文阐述的评估参与文化所强调的是将“评估”融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形成按照质量标准“吾日三省吾教”的习惯。但是要形成这样的参与文化认知,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为此,美国高校的教务长于2009年就呼吁,更多的教师参与评估已成为提升评估效果的首要任务[11]。帕特·哈钦斯也提出了为教师参与评估敞开大门的六项建议:一是围绕日常教学工作建立评估体系,将评估理念融入到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设计中,包括教学计划、课堂活动和课后学习任务的开发和考核体系;二是将评估培训嵌入到教师职业发展之中,提升教师的评估技能;三是将评估纳入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为他们未来从事教学工作和参与评估打好基础,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四是同等对待教师的评估工作与学术研究,为教师积极参与评估活动、实践评估理论创造激励环境;五是构建教师之间的评估对话机制和校园评估文化,为不同高校相同学科教师之间的评估交流提供机会和支持;六是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机会和工具(如学习进展电子档案袋等),鼓励学生参与评估是促使更多教师参与评估的有效途径。
五、质量改进文化
克斯顿·福勒切(Keston Fulcher)等把基于证据改进质量的模式称之为“评估、干预、再评估”,而且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称猪、喂猪、再称猪”的过程[12]。他们所说的“干预”或“称猪”实际上就是基于评估结果的质量改进过程。他们强调“评估”本身不能改进质量,如同“称猪”本身不会给猪增膘;只有通过合理的教学“干预”才能改进教学质量。而这种合理的“干预”必须是基于“评估”结果而制定的;而要了解“干预”效果,就必须“再评估”。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常态化后,便形成了评估的质量改进文化。
美国高校评估质量改进文化的建设至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大学进行质量改进,对公立大学来说更是如此。例如,从1979年起,先后有25个州采纳基于绩效的拨款模式(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model),将学生的毕业率、就业率、完成的学分等指标纳入州政府给高校的预算制定方案中[13]。州政府出台的其他督促高校改进的法案更是枚不胜举。二是在制定评估计划时提前作好质量闭环分析(closed-loop analysis)和改进监测(progress monitoring)设计,也就是“干预”计划。目前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担的认证评估有非常详细的回访计划,也就是要求高校在评估周期内提交质量改进进展报告。学校内部开展的问题导向的学科评估更是如此,尤其是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所开展的再评估对质量改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督促作用。三是提升评估数据的透明度。虽然美国评估机构和高校并没有特别公布评估结果及其相关数据,但政府、各类高等教育学会及高校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已经最大化地公布了高校办学绩效方面的数据[14]。这样的行动不仅有利于大学有效利用评估数据制定改进计划,也为社会监督大学提供了证据。四是高校成立特别委员会(task force)深入研究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启动针对质量问题的改进项目(initiatives)。五是在“后评估”“再评估”中重点审核对上一轮评估发现问题的改进情况。
结 语
评估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塑造。美国高等教育评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虽然有待继续改进,但其范式也彰显了很多优秀的评估文化特征,也为世界高等教育评估方法和实践贡献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历史还较短,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从评估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目前还没有合理的组织架构,尤其是高校内部的评估组织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普遍认可的评价制度和质量标准;高校的评估内动力和教职工参与评估的主动性有待提升;高校的院校研究还非常薄弱,相关人员缺乏信息素养,支撑评估的数据系统也需要加强。当然,美国积累的评估文化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更何况美国的评估文化也有很多需要深化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何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文化,需要中国学者和评估实践人员结合中国的国情及中国高等教育当前所处的普及化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深入思考,总结过去评估的经验教训,建立稳定的评估模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评估文化氛围,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改进把脉献策,也为世界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贡献知识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