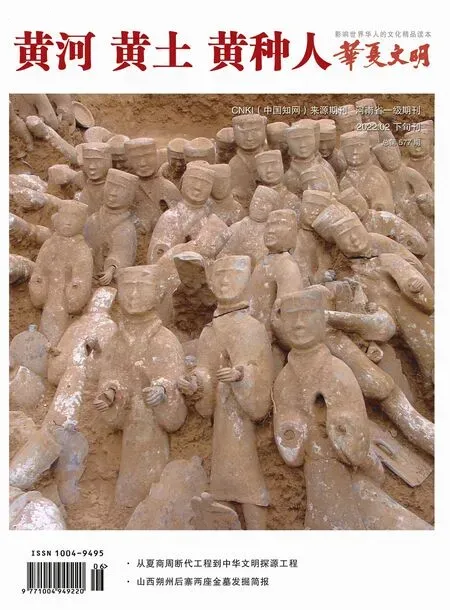新寨文化动物器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2022-12-25郭荣臻曹凌子
□郭荣臻 曹凌子
新寨文化①早年调查简报中,“新寨”“新砦”两种写法并存,此后40 余年间,学界对该遗址、该文化名称的写法一直存在“寨”“砦”的异字现象。 2020 年年初,李维明先生专门在《河南密县“新砦”“双洎河”称名辨异》(发表于《河南博物院院刊》第一辑)一文中指出该错别字问题。 依据田野考古调查对遗址按其所在地居民点名称或该地点专门名称命名的方法,联系河南省测绘局、密县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密县地图》显示“新寨”地名及笔者实地调查该处确系“新寨”而非“新砦”的事实,判断“新寨”“新砦”两种写法中,以“新寨”称名为是。 故在本文中,采用“新寨”写法。是以河南省新密市新寨遗址第二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代表性遗址有新密新寨、巩义花地嘴、郑州东赵等,该文化出土了颇具代表性的遗迹、遗物。其中带有动物纹样或动物形态的器盖引起了学术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为了解新寨文化艺术特征、 文化内涵乃至社会状况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拟从学术史角度切入,梳理不同学者研究状况,以期促进学界对新寨文化更多的关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新寨文化动物器盖的考古发现
为寻找介于煤山遗址夏代早期、 二里头遗址夏代晚期之间的缺环[1],在河南省密县②新密市前身,1994 年,新密撤县改市。文物部门魏殿臣等先生所提供线索的基础上,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芝荃先生带队在密县新寨遗址做了试掘, 发现了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形态遗存[2]。这次试掘是新寨遗址的首次发掘,学界开始关注新寨类遗存。
随着学术界夏商文化讨论的深入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 研究项目对新寨遗址相关遗存也给予了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袂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正式将新寨遗址遗存进行分期, 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3]。 另外,在此次工作中,发掘者自新寨文化单位T1H24 中发现了一件带有兽面纹的陶器盖(1999T1H24:1)[4]313,315。 可惜的是,这件器物出土时已残损,保存状况不佳。
前两次发掘, 揭开了新寨期遗存乃至新寨文化研究的序幕。 不过,在第二次发掘时,发掘者已认识到囿于发掘面积,所见新寨文化遗存尚少,还不足以做更深入研究,为解决新寨期遗存等相关学术问题,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0 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在新寨文化单位中发现了一件猪首形陶器盖(2000T6⑧:782),泥质,颜色呈浅灰色,器盖顶部呈猪首状[4]311-312[5]。 不但形状具有特色,而且制作颇为考究,方法多样,形态逼真,彰显了制作者独具匠心。
另外,2000 年度的发掘中,还出土有两件动物形器纽,一件呈狗或狼首形(2000T11⑦A:64)[4]374-375,一件呈羊形(2000T13H87:11)[4]353-354。 据发掘报告中线图、照片观之,尚不能排除这两件器纽为器盖纽的可能性。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新寨遗址被列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大学考古系等单位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若干次发掘,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材料,对新寨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不过检视2002 年度以来已刊发的历年发掘资料, 未再见类似器或其他具有动物形象的器盖。相对较为特殊的具有动物形象的器物,就现阶段而言,仅发现有上述器盖及器纽。
二、新寨文化动物器盖的研究回顾
前述新寨文化兽面纹陶器盖(1999T1H24:1)、猪首形陶器盖(2000T6⑧:782)出土以来,引起了学界相当的重视。不少学者撰文,就新寨文化的这两件特殊器物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在艺术考古、认知考古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 现分类简述于下。
1.兽面纹器盖的研究现状。 新寨遗址1999 年度发掘参与者与简报执笔者之一的顾万发先生,在发掘简报所载刊物的同一期即已发文讨论兽面纹陶器盖问题。在文章中,他对纹饰主体做了部分复原, 认为这件饕餮纹器盖的类虎面特征受到了东夷图腾文化的影响。 在对这件器盖及其他器物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他得出了该纹饰所表现出来的东方因素应来自海岱地区而非其他地区的观点。至于此器盖发现的意义,除有助于考古发现及传世饕餮纹研究外, 还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献史料中后羿、寒浞相关史事,并为二里头文化中的类似因素提供了新证[6]。
此文一出,即引起学界同行关注。如王青先生即在顾万发先生文章的基础上, 联系其他遗址所出器物或博物馆藏品,分上、下两段对此器盖上不完整的纹饰予以更系统的复原, 认为饕餮纹上方应有凤羽纹, 并推论其对二里头文化乃至商周青铜器上的“高羽冠饕餮纹”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7]。在此专文讨论之后, 王青先生在多篇其他研究论文中也提到或重申其对新寨文化此件器盖图像的认识。 如见刊于2004 年的两篇镶嵌铜牌饰文中,在对相当于二里头时代诸遗址所出或其他馆藏、收藏所见镶嵌铜牌饰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 王青先生认为以梭形眼为特征的Ab 型牌饰上纹饰与新寨遗址“头戴高羽冠的梭形眼神像”有较强关联性,后者很可能是前者来源,并认为Ab 型牌饰体现出了夏人用本族神徽对夷人神徽加以改造的痕迹[8],甚至有助于追溯更早的镶嵌铜牌饰,并有助于探索早期文明化进程[9]。 2019 年,王青先生将早期图像研究文章汇集出版, 前述诸文皆得以收录其中,唯各文文题有一定程度更易,如新寨器盖专题讨论的文章名被修订为 《饕餮先声——新砦遗址出土残器盖纹饰的复原与思考》[10],正文内容大抵从前,此处不复赘述。
前述顾万发先生关于新寨文化器盖文刊发后不久, 李丽娜女史也对此器盖纹饰相关问题予以关注,并著文讨论。该文不认同顾万发先生前述观点,认为该纹饰具有中原文化特征,而非东夷因素[11]。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一些学者对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的研究中,也提及了该件器物,并将其纹饰视作与龙相关的图像。如杜金鹏先生称该器盖图案为“龙头”,并据残图推论其龙首龙尾相接, 环绕器盖一周[12];又如朱乃诚先生据2004 年确认的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论定新寨文化器盖上的饕餮纹为龙纹[13]。 此二文虽皆非专题讨论,但在讨论相关龙形遗物时皆将新寨此物作为重要证据。
鉴于李丽娜女史的商榷及其他学者的论点,顾万发先生①笔名顾问。在同年的新寨期综合研究文章中以页下注的形式再加简论,认为其准确内涵应系羽(社符)饰冠北斗神图,重提该纹饰为图腾或神徽的旧识。 此段中顾万发先生所用主要对比案例同王青先生前文,且“肯定”地认为该纹饰体现出了“浓厚的东方天文信仰内涵和形式”, 并陈述了其基于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而得出此结论的理由[14]。 此简论虽非专文讨论,但所提观点明确,所列证据亦较清晰。
王青先生对新寨文化器盖纹饰复原文见刊后,顾万发先生等曾撰文提及其《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文中器物图中少一条线[15]。 此后,顾万发先生又专题讨论该器盖纹饰的复原问题,在该文中,他不赞同王青先生的复原实践,认为王青先生文中的鬓耳部分、面冠高度存在问题,至于该纹饰的确切原状,尤待更新证据。 同时,就其他学者提出的器盖图案龙形说,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该图案为“神面冠饰”的可能性更大[16]。
赵春青先生未对此器盖进行专题论述, 仅在所撰《试论新砦遗址出土的“猪首形陶器盖”》一文中对其有所提及。 他将该器盖上刻画的图案视作龙首图案,并对功用加以蠡测,认为其可能系祭祀乃至宗教活动相关器物[17]。 事实上,对前述王青先生文中所提到的Ab 型镶嵌铜牌饰,叶万松、李德方先生更早的文章中曾有其他见解, 将其阐释为龙或虬龙[18]。 若认同王青先生对此类牌饰与新寨文化器盖关系的解读, 或可将这些学者观点视作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赵春青先生在此文中还提到,2002 年发掘简报中, 发掘者将此器盖图案判定为饕餮纹。
综上可知, 目前学界对这件器盖上纹饰图像内涵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 一则将其视作图腾或神徽类图案,如顾万发、王青等先生;一则视其为龙形象,如李丽娜女史,杜金鹏、朱乃诚、赵春青等先生。 但需指出的是, 即便是持相同意见学者之间,也有细微差别,对这件器盖纹饰因素来源亦呈现出两种观点并存局面: 一则认为该器物有东方因素或受到海岱地区先民影响,如顾万发、王青等先生;一则认为其系中原文化特征的延续,如李丽娜女史。
2.猪首形器盖的研究现状。 除兽面纹器盖外,新寨文化另有一件猪首形器盖, 也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与上述兽面纹饰器盖研究相较,该器物的专题研究文章偏少。 目前仅见赵春青先生对这件器物做了专文讨论, 在对此件器物形态详细描述的基础上, 他梳理了早于新寨文化的其他文化所见猪形陶器,根据大汶口文化、龙虬庄文化所见猪形陶器, 推论新寨文化猪形器盖受到了东南地区的影响; 并根据史前诸文化猪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祭祀现象, 判断此件猪首形器盖可能并非单纯的生活用具,而与宗教活动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对于其所覆盖器物,目前尚缺乏有力证据[17]。
另有一些研究,虽非对新寨文化器盖问题的专题讨论,但涉及猪首形器盖或前述动物形器纽,也值得关注。如:伍秋鹏先生对黄河流域史前动物雕塑[19]、郭梦女史对中国史前动物陶塑[20]的综合研究中,都注意到了此件器盖,将其作为重要证据加以讨论。 齐磊先生在其关于夏代早期都城演变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在对新寨文化重要器物的介绍中,也用到了此件猪首形器盖及前述饕餮纹器盖[21]。褚金刚先生对新寨期的综合研究中,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将猪首形器盖、羊首形器纽厘定为来自石家河文化的因素[22]。 王琼女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新寨文化陶器群做了文化因素分析, 除此猪首形器盖外,前述狗或狼形①王琼女史在文中称其为“马形”,与发掘报告相异,但王琼女史未言明如此更名的依据。、羊形器纽统归于丙群,认为这些因素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23]。这两位学者所见相似,但与赵春青先生略有差异。杨远、朱畅然先生在论及嵩山文化圈史前美术遗存时,将新寨文化猪首形器盖作为“距今5000—41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案例提及[24]。
三、新寨文化动物器盖的研究思考
新寨文化常见器盖为折壁、弧壁器盖两种类型,常见装饰有弦纹(凹弦纹),偶见小圆孔者[4]246-248。本文所涉及两件器盖,或带有兽面纹,或整体呈猪首状,在平淡无奇的陶器盖群中显得突兀。如果说它们并非有意加工而成,恐怕与史实未必相符。问题是,这样的装饰图案或造型,究竟反映了怎样的人类行为?是先民何种意识的写照,是否能够从认知考古角度加以解读,如何能够透物见人?就以往考古发现来看,先民动物形象的创造,或直接来自现实生活, 或是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经过复杂的思维重构而成。 新寨文化这几件器物的动物形象也不外上述情形, 与先民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联。不只是新寨文化,其他文化也频见各种类型的动物雕塑、动物器物、动物纹饰等,对此类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与生态环境研究相结合。 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生态环境适宜一定的动物群生活。 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有些直接来源于现实世界,有些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再创造。 随着动物考古理念的普及与动物考古方法的推广,考古发掘中的动物遗存愈加受到重视,其中部分对相应时期、相应区域的自然环境具有指示性意义。 在今后的研究中, 若能有针对性地将人工遗物的动物造型与其时生境相结合,可能有利于理解时人的行为。
2.与经济形态讨论相结合。 动物造型、动物图案的研究有必要与基于动物骨骼辨识、 统计的动物考古研究相结合。 肉类食材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区先民不但将肉类食材作为重要的生存资源, 而且对主要家养动物、重要哺乳动物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措施,诸如随葬、祭祀、以其为原型加工人工制品等。 作为新寨文化先民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乃至精神文化资源,上述动物形象也应与当时经济形态、资源结构、社会现实有较强的关联性。如前述赵春青先生的研究即梳理了诸文化中猪骨遗存现象, 有利于对猪类造型的人工遗物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在今后的研究中, 或可对基于动物考古记录的当时经济形态给予更多的关注。
3.与文化因素分析相结合。 文化因素分析法在判断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方面的作用已经反复为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所证实。 新寨文化与周邻区域同时代甚或更早时代文化因素的密切关联已是学界常识, 单就本文所言的动物造型器盖、 器纽而言, 前述多位学者已注意到其他文化对新寨文化的影响。 除这些动物因素器物以外, 新寨遗址2016 年出土的一件彩绘陶鸟也引起了研究者关注。耿广响先生即由之入手,在综理文献史料和早于新寨文化鸟类人工遗物并进行区域比对的基础上, 推论新寨文化陶鸟所具备的东方因素及在祭祀中的仪仗用途[25]。 这种异域文化对该文化动物造型的影响在今后可持续加以关注, 除这种直接的造型外, 原器物形象在原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或许有助于理解该形象该器物在现有文化中的性质与功用。
4.与认知考古推论相结合。 认知考古在理解先民精神世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暗示了此类研究在史前乃至狭义先秦时期考古研究中的潜力[26-29]。前述学者对新寨文化两件特殊器盖的内涵、文化因素等解读虽然存异,但普遍认同这两件器物在仪式性等活动中可能的功用。另据顾万发先生等人研究,花地嘴遗址所出两件朱砂绘陶瓮图案,文化因素或与海岱龙山文化相关。在梳理其他区域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顾万发先生等人进一步综理相关文献资料, 不但称其为“神像”,而且视其与北斗信仰相关[30]。 准其或部分准其阐释,则新寨文化对待考古发现中的异性器或特殊器物的研究,可以从认知考古的角度阐释先民的精神生活。不过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考古学研究中,认知考古难度大,学者所用材料、方法、理论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
虽然前述学者已从多方面剖析了新寨文化与动物形象相关的器盖, 但并未取得一致甚或趋同的认识。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而言,这种基于既有考古发现、 后世史料及研究者自身学力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假说的阶段。 诸家对相同图案做出相异的解读, 且在他们看来自身的研究符合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有如此不同见解,且未达成共识并难以达成共识,正是此类研究不具唯一解、具有持续性的反映,也从侧面说明对于相关纹饰、 相关动物形象犹有探讨的空间与继续研究的必要。考古发现具有唯一性,而对考古发现的阐释却可以多样化。随着材料的进一步积累,学界研究将更深入且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四、结语
作为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可能性的早期夏文化, 新寨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早期夏文化甚或夏文化整体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新寨文化所出上述陶器盖在新寨文化器物群中颇具代表性,甚至可能是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见证物,在早期文明化进程中先民的意识形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动物形象器盖既是艺术品,也可能是生活实用器,用途与艺术特征的探研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此,艺术特征之外的人类社会信息、人类行为体系更值得我们关注。前述学者研究再一次表明,在学术研究之中,小题亦可大做,而且需要大做。只要勤于思考,便能产生好的研究题目;只要坚持研究,便能得出有见地的结论,对后来学习者或有启迪。 需要承认的是,在史前夏商考古学研究中,如何透物见人,运用何种方法借诸何种理论进行何种阐释才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仍将作为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随着新寨遗址与新寨文化其他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新寨文化动物形象、其他图像问题的认识将更加深刻,对新寨文化社会状况的认识也将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