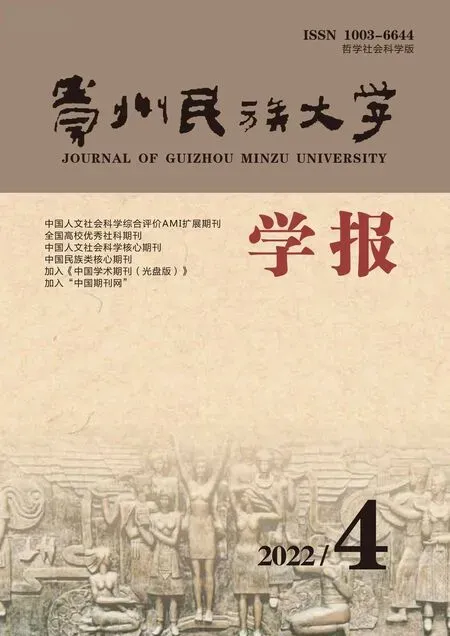论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
2022-12-22刘坤新
刘 坤 新
潜邸出身官员群体是北宋官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官僚群体中,“至上莫若君父之前”,潜邸出身官员作为皇储、皇子的近臣,其中不乏时之名儒,且往往伴有帝师荣衔。他们多从儒家的道德要求出发,严格省视自身,以道德和学识来教育皇储、皇子和辅佐君王,同时他们又以忠正之心引导士风,以良臣和明主的遇合模式来构筑和谐的政治关系。这类官员虽不一定能当过执政,但对政治政治和社会风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对此学界也早有所关注(1)陈峰:《北宋潜邸出身将领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其凡:《宋太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汪圣铎、孟宪玉:《宋真宗潜邸旧臣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张其凡:《冯元--博学多识的大儒》,《暨南学报》1998年第3期,等等。,但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对北宋潜邸官员的个案或某一朝之研究,少有对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群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表现和影响进行详尽分析,故本文拟对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起用
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选于宗室,即位后“志在有为”,因此面对宋廷之积弊甚重,英宗“有性气,要改作”。(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30卷)《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95页。同时,其子宋神宗长于宗室,英宗即位时,年已十六,按照古人标准已经成年。作为皇子的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且对北宋“积弊”有着比其他深宫皇子更为深刻地见解,立志“雪数世之耻”(4)脱脱:《宋史》(第16卷)《宋神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页。。英宗早逝后,神宗受命于危难之际,年二十,也是大有作为之时。他“日夜恐惧,以思为治之道”,笃定“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确如仲伟民先生所言:“神宗是一位有主见而且性格相当坚强的年轻皇帝。”(5)仲伟民:《宋神宗》(第2版),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9页。
总体说来,“改革皇帝”宋神宗的变法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其皇子教育阶段,神宗就尤为喜爱法家思想。宋代皇子、皇储习经史、六经六艺等,但不学法家之说。故神宗在潜邸时自学法家学说,其喜爱程度窥见一斑。英宗命韩琦“择宫僚”,遂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永、邵等人,故“号天下选云”。(6)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治平二年(1065)十月,神宗拿出最新抄录《韩非子》一书,让其潜邸宫僚进行校对,但受到侍读孙永的批评,言:“非险薄刻核,其书背六经之旨,愿毋留意”。神宗只能掩饰说:“广藏书之数耳,非所好也。”(7)脱脱:《宋史》(第342卷)《孙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00页。很显然,“非所好”并非神宗的真心话。潜邸时期,韩维还提醒神宗,“圣人功名,因事始见,不可有功名心”(8)脱脱:《宋史》(第315卷)《韩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05页。。神宗亲掌国柄后,在讲到“古之立功名者”时,明确指向管仲、商鞅、吴起这些变法人物,这样从侧面说明神宗的变法思想可谓由来已久。
然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在他怎么做”。(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1页。皇帝一般都有心理障碍,而这种障碍的出现往往是出于安全感的缺失,神宗也不例外。自仁宗嘉祐六年至神宗即位,宋廷形成了左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和次相曾公亮两派对峙的治政格局,且自韩琦担任宰相来,关于他“专权”的议论不断。“初临御”的神宗“颇不悦执政之专”,并欲收回权柄。作为神宗早期最信任的潜邸出身官员,一直与韩琦一派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他们能否助力神宗完成收回权柄的政治任务呢?
自宋仁宗朝始,宋廷便形成用台谏官监督和制约宰执的“祖宗”之法,故台谏官成为宋帝“分邪正,助风化”之“耳目”,故在百职之中,尤为重要。神宗即位后,便将潜邸心腹王陶擢升为御史台最高长官御史中丞。而王陶从何能潜邸众人中迅速地“脱颖而出”,从其潜邸表现便可见一斑。仁宗朝,王陶“请早择宗室亲贤,以建储嗣”,于英宗即位有功。英宗朝,曹太后之弟曹佾欲除使相,时为皇子的神宗遂“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輔臣”。韩维、孙思恭不但不同意,更劝谏神宗“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因此神宗“卒使陶言之”。王陶却欣然受命,将神宗的意思转达给宰执。(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02卷第2版)《英宗治平元年夏六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93页。由此可见,神宗与王陶“一心不可转”渊源颇深。因此当察知神宗对宰执“不悦”,“本是储王羽翼客,今为天子腹心人”的王陶自然心领神会,“翻作吠尧之犬”,主动出击。(11)吕希哲:《吕氏杂录》(下卷),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10),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王陶先奏请起用被韩琦贬斥的吕大防、郭源明等台官,神宗手诏王陶,表示赞同和支持。韩琦知“意欲逼已”,故颇为不悦。嗣后,王陶为“尊奖主威”,助力神宗“收还君柄”,不仅以御史台名义不遗余力地弹劾“宰相不押班”,更将矛头直指韩琦,斥其“骄主之色过于霍光”,迫使韩琦上表待罪,居家不出。面对王陶的弹劾,韩琦一派官员参知政事吴奎不仅认为“阴阳不和,实由陶所致”,同时还提出“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官,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邵亢与王陶都曾从侍神宗潜邸多年,时虽任谏官,因被神宗疑心曾有“建垂帘之议”,一直谨小慎微,故明知王陶此举“切合”神宗心意,起初仍保持沉默。面对吴奎的弹劾,一方面,邵亢再证自己无“建垂帘之议”,事神宗以忠;另一方面,驳斥吴奎,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而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且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邵亢此举“盖欲并撼琦”,十分契合神宗心意,故神宗“益眷公深”。(12)杜大珪编,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第19卷)《邵安简公亢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81页。在对待韩琦“专权”事上,王陶、邵亢与神宗步调一致,直接充当了神宗打击韩琦的“枪手”,引发韩琦被罢,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与韩琦不合”王安石的起用创造了条件。
当然,在王陶、邵亢“迎合”神宗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潜邸出身官员持中立的态度。在治平四年三月,御史蒋之奇察觉神宗心思,将炮火指向韩琦一派的官员欧阳修,神宗立即表示要降重罪于欧阳修。后神宗密问其潜邸出身官员孙思恭的意见。孙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笃于事上”(13)脱脱:《宋史》(第322卷)《孙思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46页。,故深受神宗信任。而后在孙思恭的援救下,虽欧阳修得以体面“罢免”,但蒋之奇被神宗赞以“敢言”,足以说明蒋之奇攻击欧阳修符合神宗本意。还有,在神宗潜邸时最为活跃的韩维对待韩琦一事又是什么态度呢?当王陶弹劾宰相韩琦跋扈时,韩维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罢台职?令为学士,是迁也。”当得知参知政事吴奎因“论陶事,出知青州”,韩维上疏神宗,“进退大臣,不当如是”。诚如朱义群所说:“神宗欲尽快收回下放已久的权柄,因此与当政的韩琦有矛盾,但韩琦是有‘定策’功的元老重臣,神宗不敢率性而为,收权行动只能迂回进行。”(14)朱义群:《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
神宗继位后,下诏广求治国良策,并向宰执和近臣流露出“图治”的心思,但却苦于缺乏帮手和人才。拥有辅翊之功的潜邸出身官员具有先天优势,自然最早被神宗列入辅助帮手,以韩维、孙永为例。韩维因“东宫旧人”,被“留以辅政”,成为神宗的政治顾问。在神宗居丧期间,韩维注释《滕世子问孟子居丧之礼》一篇,供神宗参考,神宗“嘉纳焉”。然当神宗询问治理国家问题时,韩维给神宗的意见是“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设,自有先后,惟加意谨重”(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09卷)《宋神宗治平四年二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77页。。基于对这为初登帝位的年轻天子的性格了解,韩维给出的意见是治理国家要忌急躁、求稳重。而孙固“知神宗志欲经略西夏”,却言:“兵,凶器也,动不可妄,妄动将有悔。”(16)脱脱:《宋史》(第341卷)《孙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74页。在神宗看来,臣子直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与国家“无补于事”。因此,二人虽为“忠臣”,但政治主张过于保守和谨慎,与己求富求强的政治理念不相匹配,无法助力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夙愿。故神宗开始另觅帮手,并将目光转向“今之贤人”王安石。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之所以能在神宗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与韩维、孙永、时君卿等潜邸旧臣的崇拜和推崇密切相关,并且经常在神宗面前讲述王安石和他的主张,使得神宗“宸心繇是注意”,愈发“想见其人”。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载: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17)叶梦得:《石林燕语》(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1页。
王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有“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18)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第84卷)《送孙正之序》,《王安石全集》(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89页。的抱负,但却与神宗毫无渊源,又与宰相韩琦间隙较深,纵有经世之学,也无缘“结君心”。这使王安石只得另辟蹊径,通过结识皇储宫僚,迂回前行,从而达到“结新君”之最终目的。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如果没有宋神宗潜邸出身官的桥梁作用,就没有王安石的被起用,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充当着“明君+忠臣”遇合模式的重要契机。
二、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对保甲法、青苗法的质疑
韩琦被罢外任后,相比韩维等的激烈言语,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孙固用词要较为委婉。神宗“以(孙)固东宫旧僚”,询问孙固:“王安石可相否?”孙固回答:“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为人少从容。”(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50卷)《宋神宗熙宁七年二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83—6084页。孙固委婉地指出王安石“执拗”的性格缺陷,但欲国家治事“于一变”的年轻神宗,丝毫不顾孙固等的质疑与反对,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士大夫莫不额手相庆。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神宗,“欲求近功,忘其旧学"(20)脱脱:《宋史》(第314卷)《范纯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84页。。嗣后,君臣“如一人”,变风俗,立法度,青苗、保甲、免役、水利等诸政并兴,开始进行一场“与战无异”(21)③⑧汪圣铎:《宋史全文》(第11卷)《宋神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61,662页。的改革。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在王安石的倡导下宋廷在京畿实行保甲法,但随着新法的展开和进行,新法种种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朝野士大夫纷纷质疑。王安石“既引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又荐维以代吕公著,欲其兄弟助己也”(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0卷)《宋神宗熙宁三年四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00页。,是而韩维成为御史台最高长官。但事实上,韩维并没有如王安石所希望的助力变法,对保甲法提出质疑,认为全面推行保甲法使“乡民警扰”,并言:“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23)脱脱:《宋史》(第327卷)《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46页。。然此时韩维并没有彻底否定保甲法,并建议在农闲时推行。王安石性本强忮,遇事无可否,故“恶其言保甲法”,对韩维予以疏远和压制。诚如姚治勋先生所言,“变法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很快暴露出王安石及其一派所标榜的和他们的实践有很大差距,所以很多‘有识之士’,看到变法的种种弊端、看到百姓所受的种种迫害和苦难的时候,就不能不出来讲话……可惜王安石缺少一个政治家必需的恢弘气度,以致对于所谓‘异论’一概采取排斥、压制和打击的态度。”(24)姚治勋:《排斥异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而这导致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对变法持中立、反对、甚至是早期支持的人,聚合更大的阻力,将王安石及其变法完全置于更加孤立境地。后韩维“”以言不用,请郡”,神宗虽诚心挽留。但韩维以“若缘攀附旧恩以进,非臣之愿也”(25)脱脱:《宋史》(第315卷)《韩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07页。婉拒。同年八月,“两府阙人多”,神宗询问王安石两府人选。王安石客观回答,“今两制如孙永、韩维,最为可者,然其志未尝欲助兴至理也”。自变法以来神宗潜邸官员多不支持变法图强,且逐渐站到反对变法的阵营中,使神宗恨言“维辈”不晓吏事。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神宗从潜邸时期的“正衣冠拱手”以表尊师,但现在的“维辈”,足见神宗对其潜邸出身官员的失望和愤恨。
弓手改革是变法中保甲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宋代的弓手类似于近代的警察,由乡中富户充当,代表宋廷行使地方搜捕盗贼、巡捉走私之职能,是维护宋代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之一,也是国家权力向地方的延伸。(26)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与此同时,囿于宋廷对弓手管制约束不到位,再加之元丰改制前弓手无薪酬,致使部分弓手趁查捕之机骚扰生事、巧取豪夺,造成不少恶劣影响。故时人将弓手下乡搜捕视为“纵虎出柙”。“以除盗贼,便良民”是保甲法的作用之一。鉴于弓手和保甲的职责多有重合,遂王安石以“乡巡弓手实无所济,但有骚扰”为名,奏请用保甲法取代弓手。神宗原本已“从安石言”,但“复令追还”,足见其对“罢乡巡弓手”之犹豫不绝。直到旧臣孙永“奏至”,言“北人苦乡巡弓手”,与“安石议略同”,神宗遂下定决心,应孙永之请,诏“雄州归信、容城县弓级,自今无故不得乡巡免致骚扰入户。”(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35卷)《宋神宗熙宁五年七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00页。保甲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弓手的困境,就连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也不得不承认:“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28)脱脱:《宋史》(第177卷)《食货志上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16页。
与此同时,神宗收到大臣张利一的奏疏,张利一为真宗潜邸出身官员张耆之子,时与孙永同俱在河北任职,言:“忽奉朝旨依孙永所奏,令抽罢乡巡弓手。北人既见怯弱,即自侵陵,自抽罢后,巡马过河人比前后人最多。”神宗遂询问王安石对此事的看法,王安石明确地表明支持孙永,并指责张利把“边事不了”归于“朝廷用孙永之言”,实乃“生事”。同时,王安石还建议神宗,“张利一生事,致北界骚动,宜惩责”。同年十一月,王安石又建议神宗,以孙永任庆州郡守,但神宗以“孙永前帅秦、极不善”为由,否定了王安石的建议。
青苗法是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推出的较早的一项变法措施,以“今抑兼并、振贫弱”(29)脱脱:《宋史》(第176卷)《食货上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83页。为务。然从青苗法实行的情况来看,只是将民间高利贷收入转化为国家高利贷收入,并不能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问题的。因其抑兼并、振贫弱的效果不佳,从而遭到不少官员的质疑,并引发陈荐与王安石的直接冲突。李定本为泾县主簿,因言“青苗法皆便之,无不善者”,而得王安石的赏识,并“密荐于上”。同时,“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0卷)《宋神宗熙宁三年夏四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13页。,故李定擢任监察御史里行的清要之职。对于李定的任命,时权管御史台陈荐以“李定匿所生母丧,不宜为御史”为理由,坚决反对。而王安石则力挺李定,言于神宗曰:“独陈荐言者,荐亦知李定无罪,但恃权中丞得风闻言事故也。”(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3卷)《宋神宗熙宁三年秋七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75页。嗣后,王安石又言“荐必封驳李定除命”,于是陈荐任职御史台不足二十天,被罢,改任礼官。宋神宗以另一位潜邸出身官员孙固兼权管勾御史台、知通进银台司,代替陈荐。出乎神宗意料的是:继任的孙固也反对李定的任命。同时,对于李定的争议并没有停止,仍在继续,宰执曾公亮认为,李定未尝追服,应当令礼官定夺。恰逢陈荐已改任礼官,因此王安石十分反对,认为“礼官陈荐今为长,岂可使礼官定夺。”(3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4卷)《宋神宗熙宁三年八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09页。神宗也支持王安石的建议。在王安石变法前期,陈荐因与王安石意见多不和,多被压制外任。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四月,知蔡州陈荐任期已满,宋神宗本欲召回陈荐,又考虑到“(陈)荐见孙永知开封必不乐,不如就与一郡”,遂询问王安石何郡可行,王安石却言“未有郡”。陈荐“遂以疾匄闲”,神宗“许之”。(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44卷)《宋神宗熙宁六年四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42页。
与韩维、陈荐的政治“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王广渊受到王安石“赏识”。王广渊因“近昵献文于英宗潜邸”而受重用,后有“窃取功名之心”,而遭司马光弹劾,出知齐州。神宗出于旧情,直接“内省传达章奏”,改任京东转运使而遭王安石反对。后王广渊为迎合神宗、王安石,“以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因王广渊的此举“与青苖钱法合”,王安石立马转变态度,其视为“人才”,并“以为可用,召至京师”。时御史中丞吕公著“摭其旧恶”,台官程颢、李常也“论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但王安石错认为御史台是借攻击王广渊而打击新法,因此毫不犹豫的站出来,支持王广渊,言:“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举事如此,安得人无向背?”同时,王安石又以“广渊在京东宣力”有功,力排众议,坚持任王广渊为河东转运使。(3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1卷)《宋神宗熙宁三年五月丁已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38页。后神宗有意任命王广渊知渭州,遭到保守派冯京以“广渊非端良,故人多毁之”而反对。王安石再次支持王广渊,并言:“广渊在庆州,奏事皆实,殊无诈妄”。(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40卷)《宋神宗熙宁五年十一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830—5831页。通过上述分析,再次印证了王安石以是否支持新法作为判断人才、选用人才的标准,且凡是被其认定为支持新法者,王安石定会予以全力维护。论述及此,神宗潜邸出身官员邵亢亦值得一提。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邵亢基本保持沉默,避而不谈新法之弊。一日,神宗欲用从欧阳修为执政,遂问“以修何如邵亢”?王安石认为“修非亢比也”。这不仅是因为邵亢对新法“沉默不言”,更是囿于欧阳修质疑和否定青苗法。故对于任何质疑和否定新法之人,王安石便会毫无留情地“毁之”。因此时人吕诲言:“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36)脱脱:《宋史》(第321卷)《吕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30页。
敢于斗争是王安石面对保守派的一贯态度。但在对待新法问题上,王安石又是极为敏感和偏执,而这直接影响了他的选人、用人标准。故在他眼中,凡是对变法持“异议”者皆划为“敌人”;凡是对变法予以赞同之人,纵是小人也是“人才”。正因为王安石“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1卷)《宋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35页。,使其“人才”队伍中充斥着各种投机钻营之徒,他们借变法之名,行为己谋利之实,较大程度上破坏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形象,加速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进程。且据张金山研究:“王安石应属A型性格的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自尊心强烈,对别人的反应十分敏感;个性极强,固执己见,容易偏激。”(38)张金山:《王安石变法失败中的性格因素——兼谈成功管理者的情商》,载于《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王安石虽具有高智商,但却兼具低情商。正是低情商的缺陷,其领导的变法失败也不言自明。同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支持者神宗,“虽对王安石的变风俗、立法度的各项建议完全同意,而且十分赞赏的,但那都是未经过逻辑思辨和具体分析情况下的反应,一到面临改革的现实,神宗就会做出另一种表现和反应。”(39)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6—237页。
众多周知,流言多属于有意识传播,并具有较强的指向性、迷惑性和破坏性。随着变法的逐步展开,社会上便出现“三不足”流言。潜邸出身官员是神宗获得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陈荐则将这些流言传入神宗耳中。陈荐旧事神宗于藩邸,为人忠厚质直,神宗“素知”,然却将不实的“三不足”流言告知神宗,使流言不断传播扩散,不仅流露出其反对变法的真实意图,更销蚀着王安石与神宗的信任关系。
三、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对新法中礼制、用人政策的“异论”
王安石不仅致力于制度上的变革,而且在礼制上面也有较大的动作,因此围绕礼制,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再次与王安石发生摩擦。先是,神宗下诏为秦王置后”,但“秦王廷美、楚王德芳后”事,礼官议所不一。判太常寺陈荐、周孟阳主张“以嫡统为重”,而知礼院韩忠彦、陈睦主张“用本宫最长”。于是,神宗询问王安石,“陈荐所说如何?”王安石则表示:“惟有庶孙,则当立庶孙而已”(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2卷)《宋神宗熙宁三年六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53页。,支持韩忠彦的意见。而后司马光、韩维等也加入其中,赞同“秦王、楚王后,宜如荐议”,故朝廷一时“异论纷纭”。对于英宗、神宗父子二人而言,选于宗室、异于仁宗血统,本就是不愿让人提及和触碰的“伤痂”。但此时大臣却就“血统”弄得不可开交,神宗难免由此及己,十分不悦,于是“令黜罚礼官”,“元议官”陈荐、周孟阳等降官一级,韩忠彦、陈睦等各罚铜三十斤,“再议官”司马官、韩维等各罚铜三十斤。时陈荐已移任,“审官院当勿论”,但神宗还是坚持对与己“心迹不合”的陈荐进行处罚,并言:“荐实议首,不可原也”。于是,陈荐“以议典礼不合”,知蔡州。但诏书下达后,神宗还是出于潜邸之情,“已而不行”,收回了将陈荐外任的命令。嗣后,韩维、孙固等与王安石又围绕是否以“僖祖尊为始祖”的礼制问题,产生争议。王安石主张尊僖祖为始祖,神宗特问其“维意谓何”?韩维表示反对,认为“上古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又呈孙固议”。神宗遂“复疑”王安石的意见,“令礼官议之,更尽众说”。时任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周孟阳为神宗潜邸旧臣,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因周孟阳所议“亦与安石合”,所以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神宗遂折中采纳周孟阳的建议。
熙宁三年九月,台州推官论王安石理财、训兵之法为非,王安石“大恶之,密启于上,御批黜文仲”,但遭到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的反对。先是,通进银台司齐恢、孙固屡封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皆求对,“力言文仲不当黜”。而后,韩维连上五疏,言:“陛下无谓文仲一贱士耳黜之何伤,臣恐贤俊由此解体,忠良结舌,阿谀苟合之人将窥隙而进,为祸不细,愿改赐处分。”面对潜邸出身官员的集体反对,神宗也开始犹豫,“以手诏问之”,王安石认为:“陛下患韩维辈出死力争文仲事,臣固疑其如此……今韩维欲出死力争之,若陛下姑息从之,则人主之权坐为群邪所夺,流俗更相扇动,后将无复可以施为。”(4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15卷)《宋神宗熙宁三年九月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46页。因此神宗坚定“不听”,罢黜了孙文仲。次年四月,“御史台阙中丞”。神宗考虑到自己的潜邸出身官员陈荐、孙固“皆权领台事”,欲任命韩维接任。但王安石认为,“维必同俗,非上所建立,更令异论益炽”,因此表示反对。经过慎重思考后,神宗“从之”。
四、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对农田水利法、免役法的否定
农田水利改革是王安石变法中最能“为天下理财”的措施,而淤田是农田水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汴河穿开封城而过,并成为开封城的生命线。宋太宗曾言:“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42)脱脱:《宋史》(第93卷)《河渠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7页。但长期以来,由于河道淤塞,致使开封洪水屡屡泛滥。据闵宗殿研究开封水祸平均1.6年一次。(43)闵宗殿:《历史上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治理》,《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因此,北宋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汴河放淤和治淤问题的治理。早在熙宁二年,王安石设提举沿汴淤田、都大提举淤田司、总领淤田司等官职,专司放淤、治淤,这使淤田成为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争斗的又一重点。熙宁四年五月,神宗对王安石言:“陈荐前日上殿言,喜朝廷觉察,罢却淤田,问荐何谓,荐言人号诉以为不便。”面对陈荐的攻击,王安石言辞激励地予以回击,言:“陛下用陈荐辈为股肱耳目,为股肱当为身捍患,为耳目当听察广远。今荐权发遣开封府,府界内淤田其罢与不罢及利害初不曾知,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赖。”后韩维也否定放淤新令,不赞成“匮财用于荒夷之地”。神宗和王安石排除干扰,坚定治淤。然事实证明:经过熙宁时期北方大规模的放淤,治淤,汴河两岸大规模淤田,“尽成膏胶”,迅速促进了广大淤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神宗发自内心的肯定和称赞治淤“费虽大,利亦博矣”(44)脱脱:《宋史》(第95卷)《河渠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68页。。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去疾苦,兴民生”的重要措施。宋代行户对官府有承买官物和提供工役的义务,称为“行役”。由于“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导致众多贫下行户破产“失职”,而这也是王安石创设免行法之“初心”。所谓免行钱法即通过输纳钱币的方法,免除行户的行役负担,因此有利于减轻贫下行户的负担。但免役法还是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士大夫一言不便者甚众”,成为朝臣争议最多、斗争最烈的一项改革措施。神宗“询问旧人”孙永,“青苗、助役之法,于民便否?”深知神宗心思的孙永,这次回答较为保守,言:“法诚善,然疆民出息输钱代徭,不能无重敛之患。若用以资经费,非臣所知也。”(45)脱脱:《宋史》(第342卷)《孙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01页。嗣后,为查实免役法是否“便民”,神宗特派韩维、孙永考察免疫法利弊,以平息士人争辩。史载:
辛酉,诏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知开封府孙永据详定行户利害所供行户投行事,追集行人体问,诣实利害以闻。于是,王安石以吕嘉问等具析条件并案牍进呈,言:“此皆百姓情愿,不如人言致咨怨也。”神宗言:“韩维极言此不便,且云,虽取得案牍看详亦无补。”安石曰:“维既有此言,欲差孙永同维集众行体问。”前此嘉问等尽括行户,细碎无所遗。已而有诏详定所更勿遣人体问,自贫下行特减钱一万缗。维等言:“方集众行体问利害,全系纳钱多寡,须竢臣等见得的确,合减分数,别降指挥。今如此,则是吕嘉问等所定有得而臣等所言为不足信,伏乞改命可信之人,使毕其事。(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51卷)《宋神宗熙宁七年三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30页。
神宗本就对潜邸出身官员不断对新法发难,十分头疼。神宗欲借韩维、孙永“追集行人体问”免行钱法一事,希望他们给予新法中肯的评价,以平息争论,缓解王安石与其矛盾。但是事与愿违,神宗潜邸出身官员没有给出令神宗满意的答案。经过韩维、孙永等“体问”,最终给出行人“欲仍旧”“不愿纳钱”的结论,从而驳斥王安石“此皆百姓情愿”。韩维又“极言”免行钱法“不便”,希望罢免役法,但神宗考虑到“一切罢去,则无人抵应”,且官府所需无从筹措,决定“罢维等议”。
事实证明:通过调查免役法一事,韩维、孙永没有给出神宗一个满意的答案,而二人也没有改变神宗对免役法的态度。最后,神宗只能再令吕嘉问重新调查,从而激起韩维激烈的抗击。韩维言:“陛下待臣乃在吕嘉问之下,臣虽不才,先帝所命,以辅陛下于初潜,行年六十,未尝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己利,未尝有一言不尽理道以补圣听……乃不得与新进小生为比,臣复何面目出入禁闱。”同时,韩维还“以言不用,数求去”。(4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52卷)《宋神宗熙宁七年四月巳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57页。而作为旧人的孙永,为人“虽逼以势,亦不为屈”,因此转向弹劾“尝属宰臣王安石子雱”的僧人本立“不法”,“屡上殿及此”,其意“欲以及安石也”。同年十一月,韩维与孙永因“同定夺免行钱不当”,分别落端明殿学士和枢密院直学士。孙永虽被降职,但因敢与王安石异,被时人赞为“仁义人”。(4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54卷)《宋神宗熙宁七年六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08页。直到次年十一月,韩维、孙永才被复原职。
整体而言,神宗即位起初对其潜邸出身官员信任有加。但在变法开始后以韩维等为代表的潜邸旧人,转向反对新法,神宗虽对其以责罚,但囿于旧情,还是给予其区别处理,未像对待其他反对变法的大臣一样处罚较重。而后,神宗多次对潜邸出身官员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转变对新法的态度,支持变法。但多数潜邸出身官员还是坚定的站在反对者的行列,这使得神宗十分恼怒。以元丰五年曾巩草制韩维制词被罚事件为例,曾巩称韩维“纯明直谅,练达今古,先帝所遗,以辅朕躬。”见到韩维的制词,神宗立即批复:“维不知事君之义,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谓纯明直谅,姑以藩邸旧恩,使守便郡”。(4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329卷)《宋神宗元丰五年八月丁已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919页。由此可见,神宗对韩维之态度。当得知“曽巩既坐草制罚铜”,韩维遂“数引疾求罢”。于是神宗顺势推舟,“从其请”,终神宗朝不得大用。
五、余论
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顺利完成神宗的潜邸教育,助力于神宗潜邸形象的塑造,维缮神宗和曹太后的关系。神宗即位后,面对宋廷财政匮乏,他们首倡节俭,顺利解决英宗葬礼问题,并在神宗权柄的回归和国家治理方面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然当“改革”皇帝神宗,力图改革,一扫宋廷积弊,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之时,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却由王安石的“崇拜者”变为“反对者”,这令神宗十分苦恼。但宋神宗对于其潜邸出身官员并没有完全抛弃,一方面为彰显自己“明王圣主,尊师重道”,在反对变法的潜邸出身官员处置问题上也是格外留情,基本保持“小惩”的原则,并时常还给予其潜邸出身官员超乎规格精神和物质“奖励”。如得知孙永丁忧、家贫,特诏“可特给月俸添支”;得知陈荐“久苦足疾”,诏“诸祠摄事免一年”;得知孙永生病,“遣上医调视,六命近侍问安否”,并“虚枢密位以待”。同时,为彰显对“宫僚之异恩”,神宗特任韩维、陈荐为“非尝任宰执者不除”的资政殿学士;虽“终薄”王陶之为人,但仍以东宫旧臣而授观文殿学士,等等。另一方面神宗潜邸出身官员虽多反对变法,但神宗还是将他们时常派任京师,并用他们的“异论相搅”来牵制王安石,以达集权之目的。最终,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彻底成为保守派的一分子,他们逐渐腐蚀神宗与王安石的信任,并成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推手。以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为例,神宗问王安石曰:“闻泛使来,人甚恐,如何?”王安石问到:“泛使来,不知人何故恐,但不逞多口之人,因此妄说尔。”神宗遂引述王陶之语,言:“大旱,又泛使来,人惶扰,必致大乱。”同月,韩维回京,又言:“近日畿内诸县,督索青苖钱甚急,往往鞭挞取足,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货,旱灾之际,重罹此苦。(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第251卷)《宋神宗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38页。神宗“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王安石“不悦,屡求去”。(51)脱脱:《宋史》(第176卷)《食货上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86页。确如漆侠所言:“在变法斗争的过程中,这个年轻的皇帝一再表现了游移不定、动摇彷徨。”(52)漆侠:《王安石变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正是基于对宰执大臣的不信任和对其潜邸出身官员的失望,神宗在熙宁后更将其信任重心转向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