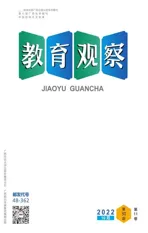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师幼空间位置关系的现象学分析
2022-12-16冷欣
冷 欣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幼儿主动参与活动的教育过程。[1]幼儿园教育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是指幼儿园中有教育价值的、能促进幼儿发展的教育活动;狭义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是指幼儿园日常开展的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2]本研究所指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是狭义上的,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是指在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
本研究借助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利用“悬置”“直观”“描述”“还原”和“反思”,对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通过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背后的含义,可以深刻理解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作为隐性教育现象的教育价值,可以看到师幼空间位置关系在生活教育世界中所处的位置。
一、相关研究
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一般涉及教师的教学站位和座位编排。教师教学站位是指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幼儿的空间位置关系。[3]教师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合理站位对活动的有效开展和幼儿在活动中获得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师幼空间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教育研究价值。
有研究指出,教师的站位是组织幼儿活动不可忽略的环节之一。例如,在体育活动中,教师站位要有利于教师与幼儿之间相互交流,也要便于教师观察,教师站位对幼儿德育有一定的影响。[4]在进行体育教学活动时,“多路纵队”“单排”“圆形”“双排”等都是合理的幼儿队形和教师站位,有助于良好活动秩序的维持。[5]还有研究深入探讨了在幼儿体育教学活动中合理站位的几对关系,认为教师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教师站位和幼儿站位之间的关系,教师的站位要随着幼儿的状态、活动的展开进行调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教师与保育员之间的关系;规则与自由的关系。[6]除体育教学活动外,音乐教学活动也时常采用“马蹄型”“圆圈型”的座位编排方式,这种方式能让幼儿看清教师的动作,方便幼儿看到教师在准备什么、听到教师在讲什么,有利于教师与幼儿互动,调动幼儿的积极性。[7]此外,在幼儿园中,“秧田式”的传统桌椅排列方式也依然存在,即教师在活动室的最前面,下面整齐排列着幼儿的桌椅。研究指出,这样使教师居高临下的排列会让幼儿产生距离感,前后排幼儿之间也难以交流。[8]这种座位编排和教师站位带来的空间位置关系是单向的、静止的。
以上研究所涉及的教师站位和座位编排多聚焦于教师视角,讨论的中心在于教师的站位如何影响教学活动和幼儿的活动,力图通过改变教师的站位引导教学活动朝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些研究体现出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有一定预设,是忠于教学目标而做出的理性活动,并没有涉及幼儿在各种具体教育活动中的真实体验和内心感受。因此,本研究试图对幼儿园中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进行深入的、基于幼儿视角方面的探讨和分析,以期透过师幼空间位置的现象看到师幼互动的本质,这是坚持以儿童为中心进行教学的体现。
二、师幼空间位置关系类型
(一)教学活动中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站位和幼儿的座位安排上。有研究指出,幼儿园座位作为一种安置身体的“物”,它的意义体现在师幼与座位的关系互动之中,不同的座位形式,形成不同的教学空间格局,也形成不同的物理场、关系场和意义场,从而对场中的人产生不同的效果。[9]比较常见的一种幼儿的座位安排是单排半包围型或双排半包围型(依幼儿数量而定),教师位于圆弧或座位前,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常见于语言或音乐教学活动中,距离上能让幼儿有亲近的感觉。还有一种是幼儿围着桌子坐,而教师位于活动室的前面位置,这种座位安排常见于依赖多媒体的教学活动,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传统的“秧田式”座位编排。客观来看,“秧田式”的座位方便了教师进行观察指导,常用于科学活动等手工操作活动。还有一种是幼儿坐成半圆型,教师坐在圆心的位置,每名幼儿与教师之间的距离相等,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一种空间位置关系。这些座位设置下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显示教师居于空间上的主导地位。此外,学界普遍认为,幼儿园座位安排需要遵循公平性、尊重性和互补性原则,因此,在幼儿园实际教学活动中幼儿的座位安排时常是变化的、流动的,幼儿的座位和教师的站位体现着动静结合、相对公平的教育追求。
座位安排是影响师幼互动的重要物质手段之一,座位是教育中进行空间分割的重要工具,不仅分隔了幼儿室内活动的物理空间,同时也隔开了师幼之间、幼幼之间的空间位置。由上文可见,集体教学活动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比较多样化,而“马蹄型”座位是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典型座位排列方式,“马蹄型”座位两边长,中间短,幼儿坐在教室的中后部,往往被分成三组,而教师位于教室前部,面向幼儿。本研究以“马蹄型”座位安排方式为例解释和分析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背后的含义。
(二)游戏活动中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游戏中隐藏着教育动因,蕴含着教育契机,因此游戏活动中正确的师幼互动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而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也可以从师幼互动中看出端倪。由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大部分表现为幼儿与教师近距离接触,幼儿总是满怀热情地亲近教师,如向教师展示活动或操作成果、向教师寻求指导和帮助、与教师共同游戏、告状或者寻求教师的关注与抚慰等。在幼儿发起的互动中,师幼之间往往会产生身体接触,空间距离为零。而在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中,有部分是与幼儿近距离接触,如指导或帮助幼儿游戏、与幼儿共同游戏或交流、安慰幼儿或表示关心。但在一些互动情境中,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距离比较远,如教师的要求、提醒或指令,评价幼儿或让幼儿进行演示等。由此可以看出,游戏活动的师幼位置关系比较灵活,会受到师幼互动的具体行为特征以及师幼互动行为的发生环境的影响,可以根据具体的师幼互动情境进行变换。[10]
有研究指出,由于游戏的教育形式的相对灵活性以及游戏活动的丰富性,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的师幼互动中,非正式化的、个别情境下的互动和接触会更加普遍,师幼空间位置关系和作用与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不同。基于“儿童中心”教育观以及对游戏活动中教师“观察幼儿”能力的考量,本研究将以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行为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为分析对象,并将它定义为“距离尺度型”师幼位置(有近距离接触也有远距离互动),考察在这种师幼互动情境下教师与幼儿空间位置关系背后的现象学含义。
(三)生活活动中
幼儿生活习惯的养成、人际关系的形成、规则意识的建立大都是在幼儿园生活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幼儿的生活活动主要指幼儿的进餐、午睡、如厕、盥洗等常规性活动,与其他活动相比,幼儿园生活活动更具生活性,发生频率高、耗时短,活动项目具体且烦琐。因此,生活活动比游戏活动更加灵活多变,会出现多种师幼互动行为,也由此生成了多种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有学者将幼儿园的生活活动分为进餐活动(如厕、盥洗和整理活动)和午睡活动,并将活动中的师幼互动分为教师发起的互动和幼儿发起的互动。[11]进餐活动中教师发起的互动主要是询问、指令,幼儿发起的互动主要是询问、请求;如厕、盥洗和整理活动中教师常发起指令、点名等互动,幼儿也常发起询问和请求,这两类生活活动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是随具体互动行为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相比如厕、盥洗和整理活动,进餐活动中的师幼位置相对固定,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距离也比较平均。而午睡活动中多为教师发起的互动,包括指令、点名等,幼儿发起的同样是询问、请求互动,而师幼空间位置几乎是固定的。
由于如厕、盥洗和整理活动中师幼的相对位置比较随意,而午睡活动的师幼空间位置又相对固定,本研究将进餐活动中教师与幼儿的空间相对位置视为生活活动中的典型师幼空间位置关系,并定义为“进餐型”师幼位置。进餐时幼儿的座位是根据桌子进行条状座位安排,这样安排方便教师分餐,幼儿也比较有规则意识。
综上可见,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幼儿的座位安排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教育资源。很多时候,坐在前面的幼儿会比较聚精会神地听教师讲话,而坐在后排的幼儿会时不时地做小动作,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坐在前面的幼儿在教师的“私人空间”内,能强烈感受到教师的存在,会更直接地受教师的影响。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隐含着教育公平的问题。[12]
三、几种典型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
VANDENBERG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方法,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态度。[13]在现象学看来,现象不是事物的外在表象,也不是感觉材料,而是事物本身,是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事物在人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样子。胡塞尔指出,现象学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现象学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方法和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14]现象学分析方法就是通过现象学还原现象,让现象回到事物的本身:通过“悬置”,把种种假设搁置起来或封存起来,使人摆脱这些假设的干扰,从而能使意识过滤(抽离)出“杂质”而成为纯粹的意识,把呈现在意识中的事物本身描绘出来。例如,当我们进入幼儿园时,我们便带着许多假设(前提),这使我们遮蔽了视线,觉得幼儿园的某些地方一无是处,甚至对幼儿园不屑一顾,这些都是我们认识事物之前的先见。现象学分析方法要求先“悬置先见”,让我们观察到事物本身。现象学分析方法如下:第一,以“悬置”和“直观”呈现事实及相关现象;第二,以“描述”和“还原”讨论事实及现象背后的问题;第三,以“反思”寻找师幼空间位置关系的本质。“悬置”的原意为“加上括弧”,即把主观成分以及一切不是发自纯意识的知识放入括弧,然后将它们搁置起来。[15]“悬置—还原”是现象学态度的核心特征。[16]采用“悬置”与“直观”的方法,可对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进行现象学分析。“还原”可以理解为一旦我们向一个现象敞开自己,我们就会试图发现和揭示这个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现象的本质和意义。[16]“反思”是在“还原”之后探究现象的本质,反思自己的“先见”以及改变以往的行为和态度。
本研究从上述现象学分析方法出发,对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进行直观描述并分析不同位置关系背后的不同含义,分析不同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下幼儿的真实体验和感受,还原师幼空间位置关系的本质。
(一)马蹄型
“马蹄型”座位呈“U”型排列,和半圆型的座位排列方式相似。“马蹄型”座位安排情境下,坐在不同区域的幼儿与教室前部的讲台和教师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与教师的方位关系也是不同的。“马蹄型”座位前端的位置离教师位置很近,侧对着教师;位于“马蹄型”座位中部的幼儿与教师的距离稍远,也是侧对着教师和黑板;位于“马蹄型”座位后端的幼儿距离黑板和教师相对最远,但是方位上正对着教师。
一般来看,坐在前端的幼儿距离教师更近,教师的注意力多放在这些位置上的幼儿的身上。很多时候幼儿自己选择位置,选择坐在前端的幼儿离教师近一点,他们表现得更积极主动。而选择坐在中部的幼儿离教师稍远,教师的注意力较少放到他们身上,而且他们坐在中后部的两侧,如果幼儿自己不积极主动地吸引教师注意的话,教师与他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少。选择坐在后端的幼儿离教师最远,但是正对着教师和讲台,教师与这些幼儿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较远但仍有交互联系。上述是常见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的解释。然而,用现象学解释“马蹄型”座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现象学要求“悬置”,要求解释者进入一个前概念化、前理论化的开放的生活空间,在解释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时,幼儿在课堂上与教师的空间位置关系所带给他们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最重要。空间位置关系会影响师幼互动,进而影响幼儿与教师的心理距离,影响幼儿的当下内心体验和感受。位置离教师较远的幼儿如果感受不到教师的关注就会觉得教师与自己的心理距离特别远,会认为教师不喜欢自己,不关心自己,也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讨人喜欢。距离教师更近的幼儿如果稍有动作或和别的幼儿讲话会被教师注意到,如果这个时候教师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哪怕只是眼神互动和交流语气缓和,幼儿就能够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因此内心也会感觉到安全和满足。
(二)距离尺度型
游戏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是灵活变换的,在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情况下,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距离较近,游戏活动中向教师寻求帮助和指导、与教师共同游戏等活动都需要幼儿走到教师面前或教师来到幼儿身边,这样师幼的空间距离就缩短了,师幼的空间位置也靠近了。在教师发起的互动中,有部分是近距离接触,但也有部分是远距离互动,例如,教师对幼儿的要求、命令和评价,以及对幼儿进行演示等活动都是和幼儿之间有一定距离的。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位置中,人们常认为教师与幼儿的空间距离越近,师幼互动质量会更高。在师幼近距离的接触中,幼儿会感觉到教师的关心和关注,师幼的心理距离会更近,特别是当教师主动去靠近、接触幼儿时,幼儿会更加欣喜。在教师发起的部分互动中,师幼距离较远,而且多以命令、控制的方式,幼儿自然不会喜欢,师幼空间位置关系自然比较疏远。现象学中“悬置”观念关注在不同位置关系上幼儿内心的真正感受和体验。有研究指出,在生活和游戏活动中,师幼之间身体距离的远近、教师身体动作和姿态等身体语言是反映师幼人际关系的风向标。[9]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对违规幼儿发起的“坐到我身边来”这一互动行为拉近了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距离,但这种互动情况下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是物理上的亲密,幼儿对教师反而会产生恐惧心理,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惩罚。幼儿主动要求的往往是近距离的师幼位置,他们对教师的靠近和回应往往充满期待,此时若是教师采取适当的策略,幼儿也会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反之,则会感觉到不安和焦虑。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师幼空间位置关系受到教师处理方式的影响,即使在空间距离较远的情况下,教师采取适当的策略拉近与幼儿之间的心理距离也能使幼儿感到内心满足并获得良好的互动体验。
(三)进餐型
在进餐活动中,幼儿在进餐时往往按摆放位置就座。一般情况下,班级里会摆放5—6张桌子,每张桌子坐5—6人,幼儿进餐时的座位一般由教师安排或确定,教师在固定位置为幼儿打饭,这样的安排是教师权力意志作用的表现。[17]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进餐秩序,让幼儿减少交流、专心吃饭。因此,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是相对固定的,只有在幼儿需要加菜的情况下教师才会四处走动。我们一般认为,在幼儿进餐时师幼空间距离比较固定,而且没有很亲近,因此进餐活动只是在教幼儿一些生活技能,不具备情感上的教育功能。如果幼儿的进餐活动在室内进行,也是一直处于教师的监视之下,幼儿一般无法选择和好朋友坐在一起,同时也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进餐。现象学分析关注幼儿在进餐时对教师位置和动作的内心感受,教师对幼儿进餐的时刻关注会影响幼儿当下的进餐体验,同样,教师对幼儿要求的及时回应也会让幼儿内心感受到安全和满足。
四、回到事物本身:回归生活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
超验现象学提出要“回到事物本身”,即要关注所体验的事物在意识中的显现,而不是关注外在事物,要关注生活世界、关注人的体验。[16]教育现象学研究是西方教育学者由于不满当代教育中盛行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等科学主义范式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教育现象学家认为,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主的教育研究,往往过分注重研究方法和技术,忽视了很多教育中的日常生活意义以及实践性特征。[18]教育现象学是一门探究教育生活现象及其体验的学问,教育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进行师幼空间位置关系分析的重点在于回到幼儿的生活和经验,关注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体验和感受。存在主义的“此在”思想与教育现象学的观点一致,首先关注教育生活中的人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活体验,其次强调学生是动态发展的、有意识的存在,他们在生活的体验中不断发现自己、超越自己,展现出无限可能性。
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师幼空间位置关系不是表面上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空间距离,而是有其深层次的生活含义。空间位置关系是心理距离关系的外部现象。在现象学视角下,师幼空间位置现象的本质是师幼之间的心理位置关系,即教师在幼儿当下生活中的位置,幼儿在教师心里的位置。在幼儿园的教育实践中,要把握好师幼空间位置关系,教师就必须以幼儿为中心,对幼儿心理状态保持高度敏感,以幼儿的生活体验为依据,灵活调整自己与幼儿的空间位置和身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