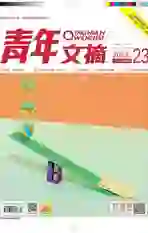一次针对“时间”的恐怖袭击
2022-12-07王健飞
王健飞

1894 年2 月15 日下午,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公园附近发生了一场恐怖袭击。一个26 岁的法国男人穿过公园,来到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门口,引爆了他棕色手提袋中的一大盒炸药,一时间现场惨不忍睹,恐怖分子当场死亡。
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但一些评论家推测,这场恐怖袭击的目标是时间。确切地说,是在10 年前刚刚确立了格林尼治平均时间的格林尼治天文台。这个推测并非毫无来由,在那个精确时间体系刚刚被发明出来的年代,不少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都爆发了针对时间,或者说针对时钟的恐怖袭击。理由很简单,群众对精确的时间感到愤怒。
作为一个21 世纪的读者,你可能会感到奇怪,甚至不能理解这种愤怒,那事实上恰恰说明了一点:时间已经异化了你我。
在现代时间体系被发明前的千百年间,人类的大多数社会活动,都不严格遵从时间来进行,而是与自然的运转息息相关。以农耕为例, 二十四节气并不严格指导农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 许多地区的农民从未听说过二十四节气, 因为地域间的差异以及年与年之间的气候误差, 使得农民必须观察真实的自然迹象而非谨遵固定的历法。学会看天,比精确的历法对务农更有用处。
在古代, 秋季并不一定是九月份开始,它是由第一片黄叶来定义的;对正午的定义, 则是“太阳位于头顶,没有影子” 的那个瞬间。但随着14 世纪精确计时工具的发明,以及天文测量水平的提高,大多数社会生产和交际活动便脱离了自然节律,开始遵循人类定义的节奏进行。
时间的发明,有助于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造福社会。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时间没有发明出来的世界,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因为几乎一切的生产活动,其底层都是一条被精确计时的流水线。但时间这种工具被发明出来之后,最先被异化的却是人类自己。
我们无法用时间来精确计算四季的流转,但是,发明了时间以后,我们却精确地对人进行了行为上的统治。
标准化时间的推广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在时钟发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间并不是统一的,各地方采用自己的时间来达到与自然界更加贴合的状态。比如,即便是在同一个时区内,每一个经度地点的落日时间都是不同的——因为地势原因。一个山阴之处的小镇,可能与山峰另一侧的城镇在距离上并不足以导致显著的时差,但如果没有强制的划分,他们可能会遵循完全不同的时间,因为对于山阴小镇来说,太阳在每天的正午才会出现。
欧洲最先使用标准化时间的是各大铁路公司,为保证列车时刻表的高效运转,要求铁路沿线市镇采用国际标准化时间。随后,标准化时间随着铁路像病毒一样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随之带来的愤怒,引发了前文提到的恐怖袭击。
标准化时间的推广过程,就是对生活的异化过程。
最初,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我们有了精确的计时工具,为协调整个社会的运转, 开始规定每天早上八点起来劳作,无论那时的天候是否适合劳作;再之后,我们有了标准化时间表,开始规定人必须按照时间表到达指定的地點(赶火车)。
父母一定对如下场景不陌生,那就是当孩子玩游戏或看电视时,如果你与他们约定“再玩/看五分钟”,往往是一个无效约定。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约定都不能被很好地履行。因为我们实际上玩游戏有“一局”之说,看动画有“一集”之说,时间实际上不能规划我们的一切生活。
再比如,在午饭时间之前或之后吃午饭,是一种令人羞愧的职场行为,即便领导没有做出指责,这样做的员工仍然会有一种压力。我们将午餐时段规定在中午的十二点开始,是因为大多数人会在这个时间段感到饥饿,但在实际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却以十二点来判断是否该开始吃饭,而几乎不考虑是否会提前饥饿或错后饥饿。
自精确计时工具发明以来,人就成了被时间主宰的客体——我们掐着时间劳作,对着时间表追赶交通工具,为了自律精确地限制娱乐生活——因而精确时间与不精确的肉体(我们不是齿轮)之间的矛盾,便会在现代生活的每一处表现出来。
(摘自《读库2204》,知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