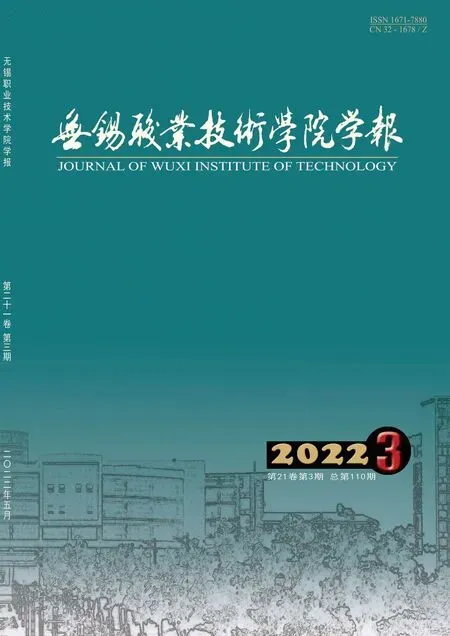杜诗中的“仁”文化解读
2022-12-07吴红欣
吴红欣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素质教学部, 江苏 无锡 214125)
在中国诗词的历史长河中,杜诗堪称翘首,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杜甫是儒学思想的贡献者。杜甫生于盛唐,生活于由盛及衰的中晚唐。杜甫家世显赫,其十三先祖杜预,不仅是一位活跃于西晋政坛、文武双全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研究儒学经典、博学多才的文学家。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人,德才兼备,一辈子“奉儒守官”。杜甫在家族的文脉相承、耳濡目染之下,塑造了德才兼备、宅心仁厚的性格,成就了儒家文化在唐诗中的坚守。杜甫以“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为出发点,不遗余力地践行着为官之道,关怀国计民生。第二,杜甫具有恻隐之心。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2]15即人以“仁”为开始,立于“恭、宽、信、敏、惠”之上,即恭敬、宽厚、信义、勤敏、慈惠,囊括了人性、慈爱、至善的人格准则。
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恻隐之心和悲悯之情。在悲悯之情的驱使下,他能推己及人,体恤同样饥寒交迫的众生。杜甫的一生将“仁”贯穿其为人与诗词中,将“仁”作为一切言语与行动的基础,进而构成了杜诗的灵魂与精髓。杜甫把孔孟的“仁”文化融入他的血脉,水到渠成地投射到他的诗词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子,他一方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孔子主张的“有差等的爱”。相较于孔子重视血缘亲情上的“有差等的爱”,杜甫在“仁”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无等差的大爱”,即无阶层的泛爱。相比于佛家的慈悲为怀、墨家的兼爱非攻、基督的平等博爱,杜甫所传承的泛爱更有人情味,也更有现实意义。
1 杜诗中“真”是“仁”的基础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诚如朱熹所言:“日‘思无邪’,盖《诗》之言,善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3]因此,读诗不仅能打开人类社会情感的生活之窗,而且能磨砺人的性情,施展人的抱负。因为诗词不仅具有美学及社会教化的作用,而且蕴含着民族精神、时代特点以及生命意识。同时,诗词背后的隐性文化,能够帮助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自己的文化坐标,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
杜甫的每一首诗中都承载着家国情怀与使命。在杜甫的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古诗词充满生命的律动,体悟到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缩影,还能感受到杜甫内心强烈的理想与抱负。在这种强烈情感碰撞的背后,我们能深刻体会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子们不仅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脑,而且是优秀文化的承载者。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与社会关系的构成中,有着自我理性的价值评估,自我憧憬的价值实现以及参与、干预社会现实的雄心。他们自觉地生发出个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以国家和人民为奉献对象,以操守和名节为精神标杆。他们有着“第一地位”的自我认知,具有“忠君、忧民、爱国、济世”的文化心态,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他们觉得诗歌只是道德的外化,“真、善、美”才是道德的底线,“真”不仅是前提条件,而且是儒家中心思想“仁”的基础。
所谓“真”,即是真情实感、真性情。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矣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善于谄媚、讨好于人的人必定是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的人,他们充满了虚伪,没有真情实感。因此,他特别批判虚伪,提倡真情实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刚毅木讷”的人,流露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能从自我出发,老实本分地做人做事,是最接近“仁”的人,而“巧言令色”的虚伪之徒,是以别人为主,以讨好迎合为目的,是远离“仁”的。由此可见,“真”是“仁”的基础。反映在中国古诗词中的“真”,一是指情感的真,有真情方有真诗;二是指表现生活的真,也就是艺术的真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有真感情、能写真景物的称为有境界,反之为无境界。换言之,就是要求诗人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在杜甫《石壕吏》中,“真”与“仁”的彰显最明显。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此诗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如实呈现了一场差吏抓壮丁的人间惨剧,它如电影放映般,通过一帧帧影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作者以生动细致的文字向读者描述了傍晚时分的石壕村,差役气势汹汹捉人的景象。差役们的凶神恶煞与老妇人的哭哭啼啼、唯唯诺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像一部诗化的小说,清晰而明确地讲述了作者夜间投宿石壕村目睹的人间悲剧。一个穷苦人家,夜里有差役敲门捉人,听到敲门声,家里的老翁第一时间跳墙逃走,老妇人出门查看,见到凶狠的差役,她无奈地啼哭,显得无比可怜。作者接连用了两个感叹句,表达了自己看到惨状时爱莫能助的悲叹。作为一个路过投宿的人,杜甫只能旁观,惭愧自己无权干涉这样的事件,只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无能为力。接着,老妇人在差役的逼问下,上前说明她的三个儿子都去邺城服役去了,并且其中两个兄弟已经战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活着的人尚且朝不保夕,死去的人又能指望什么?家里没了成年男性,只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子以及无一件完整衣服出门的儿媳。老妇人年老力衰,毛遂自荐,愿意跟从差役去河阳营地。如果赶得快,还能为营地的官兵准备早餐。夜深人静,唯有断断续续、隐隐约约的哭声传来。天亮时分,临行之时,作者唯有与老翁告别。
在这首诗里,作者详实地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无能为力的心酸,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现实残酷的谴责。由此不难看出,当自己所坚守的信仰与道德被现实蹂躏、冲击时,身为儒家文化传承者的杜甫是何等痛心疾首,他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能做的只是通过吟诗作赋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沈伯俊称赞“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伟大之处在于其将对人民的深刻挚爱之情凝结为不朽的诗篇,升华为时代的精神”[4]。在杜甫的诗文里,用文字诠释了赤诚的仁者之爱以及浓浓的爱国情怀,用行动担起了民族、国家的脊梁,他配得上“诗圣”的称号。
乾元二年春,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从华州往洛阳看望妻儿,路途中见证了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写下充满悲天悯人情感的“三吏”“三别”,《石壕吏》便是“三吏”中的一篇。在《石壕吏》中,杜甫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深刻地揭露了官吏的残暴无情、兵役制度的冷酷黑暗,表现出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苦难的同情,也深刻地认识到李唐王朝的种种弊政。清代诗人袁枚在《马嵬》中写道:“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石壕村里的这对老夫妻,相较于帝王之恋,更能体现出寻常生活中真真切切的苦难与困顿。相对于情爱的分离之苦,石壕村里的这对老夫妻,还有骨肉分离、夫妻离散、家破人亡之苦。而杜甫身为皇帝的“近侍之臣”,官至左拾遗,虽不被皇帝待见,但毕竟是朝廷的命官。当他看到石壕村老夫妇的遭遇,虽无能为力,但他内心的“仁”文化还是喷涌而出,随之以诗文为匕首刺向罪恶。正如邓魁英、聂石樵所言:“杜甫的一生是用诗歌谱写的一个悲剧,它的意义在于揭露了唐王朝盛极而衰这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矛盾、动乱、黑暗和腐朽,揭露了形成他悲剧的那个恶劣的社会环境,展示了他坚韧、不屈、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精神。”[5]杜甫虽身在体制之内,但他对体制内外执行者的不合理行为持批判的态度,说明他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2 杜诗中的“爱”是“仁”的内容
子曰:“泛爱众,而亲仁。”[2]3这是孔子儒家文化中关于“仁”的思想,提倡仁者爱人,进而广泛地爱众人,去亲近有仁德的人,让自己也变成有爱人之心的人。“仁”这个字,从中国汉字构造的角度来看,表现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关系联结的纽带是“爱”,“爱”不仅是“仁”的内容,还是“仁”的表现。因此,孔子进一步阐释了“爱”的内涵,曰:“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说苑·政理》),即爱别人的人,别人才会爱你;爱人才会有人爱。“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才会对你好,但建立这种良性相互关系的前提是“爱人”,而“爱人”的前提是尊重别人,承认别人也是人,也一样拥有人的尊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由心而发同情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
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圣”,诗歌创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他具备博爱的胸襟,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真情实感,有自己深陷困顿之中,仍心系老百姓、关心民生疾苦的大爱精神。他把儒家的“仁者爱人”当作其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仁”政,且理想在现实中的实施,最务实的就是“仁者爱人”,它贯穿于一切伦理道德及规范中。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一切的爱都是从人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因此,孔子在讲“仁”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真情实感,而真情实感的核心是“真”,也即至诚至真的心。有了这样的心,才会生发悲悯之心,才会拥有恻隐之心,才会对别人产生同情之心,才会与别人的痛苦和欢乐建立情感连接,进而在自己的心中产生共鸣;有了这样的共鸣,才能推己及人地“爱人”。在孔子的“仁”文化中,“爱人”是“仁”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前提,“仁者爱人”既体现了“仁”的精神内核,也彰显了博爱的胸襟,让“仁”在“爱”的光芒照耀下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6]的境界。“仁者爱人”不是外在文化的强制行为,而是一种自觉行为,是建立在以人性为内在欲求基础上的大爱,它能唤起人最深层的体恤之情,并使之成为人的自觉行动,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的儒家思想与杜甫的内在情怀以及人生信念高度契合,杜甫也身体力行地将儒学精髓“仁者爱人”的思想付诸行动。
《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这是一首如话家常般的劝解诗,诗中杜甫劝解吴郎,先前自己居住草堂的时候,就从未制止过隔壁的孤寡老妇人来草堂的枣树上打枣。为此,他也反对吴郎在草堂边架起篱笆,不让老妇人来打枣。在现实生活中,苛捐杂税已经盘剥得老妇人穷困潦倒了,再加上时局动乱、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生活已经无以为继,如果连打枣充饥都不允许,那还让人怎样活下去?此诗中明确地表达了诗人对老妇人的悲悯与怜惜之情。同样,诗人也希望吴郎对老妇人保有慈悲之心,饶恕老妇人的无礼行为。虽然诗人自己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仍不忘体恤底层大众的困顿。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箐洞不可掇。”杜甫的小儿子饿死了,他在无限悲恸之余,依然想到了处境不如自己的百姓。自己作为朝廷命官,享有不服兵役与免除交租纳税的特权,生活都无比困顿,何况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远守边疆的士兵,他们该是如何缺吃少穿?这种忧民忧国的情绪一直堆积在杜甫的心头,层层叠叠。宋人陈严肖曾对此诗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杜甫的“仁者爱人”之心,甚至对草木虫鱼也抱有无限的爱怜,体现在诗作中,如“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缚鸡行》)。他担心家里的鸡被卖掉,呵斥家里的下人为鸡松绑;在夔州东屯劳作的时候,杜甫因担心伤及洞穴中的蚂蚁,就捡拾穗禾送给孩童,以免蚁穴遭到破坏,“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杜甫的种种行为看似痴傻,其实所表现出的是“仁者爱人”的慈悲之心。因为在仁者眼里,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有感情、通人性的生命,都值得被珍惜。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也说:“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全唐文》卷360)他始终践行着“仁”的精神,在爱妻儿、爱朋友的基础上,将“仁爱之心”给予天下百姓,将满腔的“爱”挥洒人间。
在儒家文化中,“仁”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它的品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2]19,即一个具有“仁者爱人”的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一个以济世济众为己任的人。“仁”的前提条件是自己要有实力,只有自己站稳了脚跟,才能有帮助别人的可能。杜甫因祖上官爵的庇佑,成为拿着朝廷俸禄的小官,虽然仕途失意、生活困顿,但是他仍不改儒家士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把“仁者爱人”的大爱寄托到诗词上,以诗词含蓄蕴藉的内在特点,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荣格说:“伟大的诗歌总是从人类生活中汲取力量,假如我们认为它源于个人因素,我们就是完全不懂它的意义,”[7]也就是说,伟大的诗歌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反映生活。杜诗字里行间都关切着国家、民族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而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无所庇护的读书人,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写于上元二年秋天,成都浣花溪边,一间能栖身的茅屋,被一场大风刮走了屋顶上的茅草,南村的孩童抱走了茅草,使得屋漏床湿、无所遮蔽。看着屋内盖了多年像铁板似的被子,杜甫关心的不是如何修缮房屋,而是没有居所的天下读书人,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庇护之所,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杜甫不禁畅想:如果有许多宽敞、高大的房子来庇护这些困顿的读书人,那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然而,这只能是杜甫的理想,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理想越大,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远。在那个百姓颠沛流离的乱世,更多的人都选择明哲保身、苟活于世,而杜甫偏偏要“自不量力”地推行济世之道,即便到了屋漏床湿的境地,心里想的还是别人,这种处事思维反映出“仁者爱人”的儒家文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诗词创作成了杜甫抒发情感的渠道,作为一介文人,手中的笔是最好的武器,他以诗歌的表达形式表现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道德观念以及伦理准则等。
中国文化浸润下的古诗词所表达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西方文化注重“理性”,以法治为尺度,而中国文化在乎“德性”,以思想教化为出发点。因此,在具有“德性精神”的中国文化中,把人作为一种道德的存在,将“天道”与“人德”相连,展开一种“合内外之道”的德性生活,寻求“我与我”“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和谐统一[8]。这样的统一,在杜甫所践行的“仁爱”里,不仅找到了它救世济民的社会实践意义,而且落实在他所推崇的人命无贵贱的“仁爱”情怀里,充分体现了杜甫赤诚的人道主义精神,实现了最理想的“爱”的融合。牟钟鉴提出的“仁爱通和之学”说法,主张以“仁”为核心理念,以爱为基础情感,主张天下一家、天人一体、和而不同、通畅无碍,看重和爱护生命,提倡修已成物,向往世界大同[9]。在爱的感召下,万事万物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和谐共存、相互补给、相亲相爱,这才是儒家“仁”文化的归途,儒家“仁”文化的最高境界。
3 结语
杜甫草堂现已成为后人瞻仰杜甫的首选之地。杜甫能得到高度的肯定与赞扬,主要在于他心系大众的高尚情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将“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10]作为评价好文学作品的标准,由此可见,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来自人民群众,而且需要为人民群众发声、服务。杜甫作为底层大众苦难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人间的疾苦,痛斥统治阶层的残酷与冷漠,因此才有了振聋发聩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正如莫砺锋所言:“少陵之于诗也,熔铸八代之丽辞,尽得古今之体势,摹写宇宙之万态,沾溉后代之骚人。”[11]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杜甫的一生都在儒家界内,信奉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且经常称自己为儒生。杜甫的一生都在努力实现儒家“仁者爱人”的理想信念,因为儒家所期待的君子身上必须具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2]这样的能力,即在对事物穷尽研究获得知识的基础上,打理好自身、家庭、家族的事情,最终的目的还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安邦定国是每一个封建士大夫铭刻在心底的责任,也是他们一生孜孜以求的使命,被儒学浸润的杜甫,他的这种心思更强烈。然而,杜甫生不逢时,让他施展拳脚的空间很小,唯有诗词才是他抒发情怀的出口。早在青年时代,杜甫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怀,然而那时的他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深层次思考,也缺乏现实生活的磨砺,直到在长安求官十年,经历官场失意、时局动荡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才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底层人民的疾苦,这时他的诗词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以及忧国忧民情怀,也展现了他经世济民的人生信念。
中国的传统诗人都是士子,他们有士的道德标准,即儒家的道德标准。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15(《论语·泰伯》)“仁”是士子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孔子要求的“完人”境界。在《礼记》的《儒行》中对士的形象要求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13]355。孔子对儒家文化践行者的要求是先自觉把自己打造成宝玉,等待诸侯行聘礼采用,努力学习来等待别人询问、心怀忠信来等待举荐、尽力而行来等待录取,从而实现为国家、社会、朝廷服务的理想。这样做的前提在于个人意志,士子要有“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及“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13]357的品行;儒者要有不贪心、不沉迷、不惧怕、不忘义的操守,具备不被胁迫、不被威逼、不可侮辱的品行。只有拥有这些品行,才能使得像杜甫一样的封建士子在接受这些品行的教养后形成他们的道德主体,即积极参与政治、为民请命、积极入世的情怀。杜甫将一己之悲升华为天下人之悲,以一己之痛感念天下人之痛,他的人格境界达到了儒家所崇尚的“圣域”,他的精神上升到了“世界性”,甚至“全人类”的高度,杜甫作为儒家士子的佼佼者,值得全世界人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