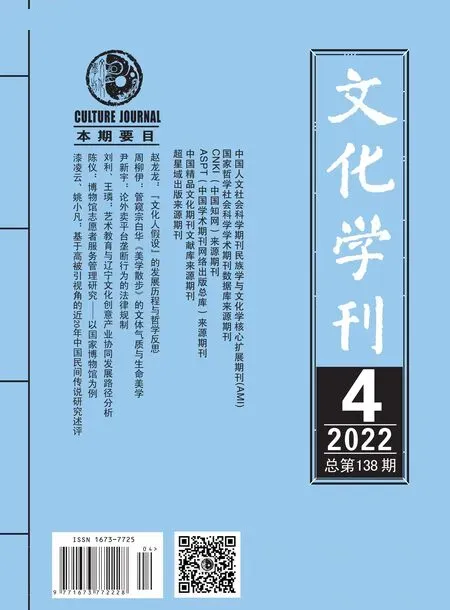颤栗的突围者
——从《使女的故事》看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与重构
2022-12-07赵琳琳徐鹏飞冯晨晨
赵琳琳 徐鹏飞 冯晨晨
美剧《使女的故事》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作家凭借这部小说摘得了英国文坛最高荣誉布克奖,根据该小说创作的同名美剧“横扫”了第69届艾美奖,引起广大观剧爱好者和小说爱好者的关注。
影片讲述的是执政者为了解决生育率低下这个社会难题,将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保护”起来,通过训诫和教导后分配给上层执政官,为执政官生育后代,但是在规训过程中遭到女性不断反抗的故事。本文通过层级研究、角色分析、主体消解以及意识重构等多种视角对《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群体进行深度剖析,来探究其自我意识的缺失与重构过程。
一、阶级的分化和被赋“使命”的群体
同小说描绘的社会状况相似,影片展现了一个文明正在逐渐崩塌的社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诸多隐患,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繁衍的后代正遭受着自然环境的威胁,造成整体社会生育率低下,面对该难题,政府迫切需要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多孕育后代,以此来提高社会的出生率。因此,执政者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将社会各阶层进行明确划分,女性被划分为贵族夫人、教导者、使女和“非女人”。贵族夫人是执政官的配偶,负责协助丈夫出席活动并帮助丈夫维持家庭秩序;教导者被称为“嬷嬷”,主要负责教导使女以及配合夫人管理日常琐事,通过一些惩罚措施和感化政策来让使女心甘情愿地为主教生育子嗣,为社会做出贡献;使女是被控制人身自由的女性,她们具有生殖能力,被强制赋予延续后代的职责,被要求脱离原来的姓名和家庭,只负责为执政者提供生育服务;“非女人”是年龄较大、违反了规定和不具备生育功能的女性,她们被安排去做苦工或佣人。
影片主要通过抓捕、惩罚、杀戮的过程来展现社会的混乱和权力的滥用,借由人们的麻木和不苟言笑的表情来展现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冷漠。其中,具有阶级划分象征的黑、蓝、红和棕等不同颜色的服装是一种隐形霸权,被区分的人没有选择服饰和装扮自己的权利,这种区分将所有人的地位和职能置于明处,以便彼此监视。
女性在被迫接受阶级划分之前是社会事务的参与者:女主角琼是位职业女性,她热爱自己的事业,有恋爱的自由和娱乐的权力,她的女儿是她和丈夫爱的结晶,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琼的朋友莫依是一个洒脱不羁,独立并乐于享受生活的人;艾米丽是一位生物学家,具有较高的学识,同时也是一位出柜的同性恋者;高级执政官的夫人曾是参与制定政策的高层人员,因为阶级划分,她只能按照规定协助在国家权力机构工作的丈夫,做他的幕后支持者。
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在最初都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例如:琼,对于爱情勇于追求,对于孩子疼惜万分,对于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公敢于挺身而出;执政官夫人,在丈夫面对社会难题时,为丈夫出谋划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帮助丈夫在高层决策团中提升发言权;艾米莉,在专业领域有一席之地,在感情上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阶级划分之后,男性掌控和分化社会权利,女性被剔除出权力系统,丧失了社会功能,不能管理和支配自己的财产,同时,部分女性因为环境污染丧失了生育功能。女性群体迫于生存和角色功能丧失带来的压力,必须按照新的社会规则来规训那些仍旧可以生育的同类:夫人和嬷嬷没有生育功能,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用《圣经》感化和肉体惩罚来约束使女为执政者服务,不能生育的女性要想生存就需要“匍匐”在男权脚下,利用分配给她们的权利来统治另一群女性。具有生育功能的女性被划分为使女之后在不同程度上会遭受一系列的打击:如琼的丈夫被枪击(未死)、女儿被抓走、嬷嬷的惩罚、被迫和主教发生关系等都使得琼痛苦万分,陷入想要逃离但又寻路无门的境地。琼被限制自由后,偶然间知道艾米莉私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境外组织取得联系,并亲眼目睹了艾米莉在逃离困境的过程中被监视机构发现并抓捕回去割除了阴蒂,伙伴的这次失败出逃,增加了琼对未来生活的恐惧。
女性在成为使女之后受到的是监视、惩罚和歧视,她们被重新赋予的社会角色和职责均是以牺牲她们的社会权利为出发点,社会给她们佩戴了一顶延续后代的高帽,却期待她们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在“囚禁”与被监视中磨灭掉。
二、敌对的双方和被单独剥离的器官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真正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就是说寻求正义,而不取消自由,给个体负担但不消灭个体性。由于女人的状况问题,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怀孕简简单单地比作像服兵役一样的一种工作或服务”[1]81。影片中,女性被按照所属功能进行分配后,女性生育子嗣被当作是一种工作或者是服兵役,这些具有生育功能的女性承载着整个社会存续下去的希望,她们本身享有的社会价值被磨灭,人的存在价值被压制,尊严不再被提及,只剩下被过分放大的“优秀”的生育功能。这种安排深入而彻底地破坏了使女的生活,迫使她们无条件地将自己交付于社会掌权者,可是掌权者不直接掌控和摧残使女,他们要保持高高在上的形象,需要借由不能生育的女性作为第三方来控制能够生育的使女,使不同阶级的女性成为敌对的双方,形成制衡的关系。
影片中,训诫和教导使女是嬷嬷的职责,安排使女和主教共处一室是夫人的职责。在训诫过程中,使女会因为反抗而当众遭受到酷刑和侮辱,这种被围观受罚也是一种规训手段,可以起到震慑其他人的作用。夫人和嬷嬷,是使女反抗和斗争的对象,她们是反抗的直接“受体”,会在规训使女的过程中受到她们的憎恨,在她们的反抗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使女的杀害。使女的身体“被作为一种工具所利用”,是各种力量交汇冲突的“地盘”,是“暗藏着各种危险的所在”[2]。使女的身体是所有人的关注点,使女如果违反了规定,其他人会受到惩罚,使女会因为生育功能而减轻惩罚。人们在暗地里进行角逐,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她们都处于男性权威的笼罩下,受到男性权威的压制,失去原本拥有的权力,她们想要生存必须依附于这个权力,按照男性所规定的那样去敌对同性:夫人想要生存和保持地位需努力让丈夫拥有后代,嬷嬷想要生存需依附《圣经》和惩罚手段让使女“听话”,使女想要生存需“隐藏”自我,依附和交出自己的身体。女性被男性设定为臣服者,同时女性和女性之间又是施压者和反抗者,但是事实上她们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和献祭者。
身体是被鞭笞的对象,子宫是被崇拜的器官,意志是被消解的终点。“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务要更深入地破坏女人的生活:任何国家都从来不敢强制性交”[1]81。在列基国,夫人在床上怀抱使女,任由丈夫和使女发生关系,强迫使女附属于所服务的主教,背离原来的姓名和家庭,代替夫人生育孩子,整个过程他们都不能直视对方,不然将被认为是一种冒犯,这种没有任何感情的关系,深度地破坏了两个家庭,打碎了女性的心理防线。使女的真正价值在于拥有可生育的子宫,如果子宫可以脱离母体而存在,可以设想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没有存在价值;使女的身体会受到惩罚和折磨,但是子宫不可以受到伤害;使女可以被杀害,但是孕育生命的子宫可以挽救她们的性命;使女的器官比生命更有价值。教导嬷嬷们通过使用严酷的电击和《圣经》近乎“洗脑”般的训诫来打造一个“被驯化了的身体”,以限定使女的活动范围和行为规范来“消灭”使女头脑中原本的认知和产生的抗争意识,使其服从于社会分配的新的角色。影片主人翁琼把自己比作“行走的子宫”,诚然,当灵魂和主体意识尚存时,女性遭到了“生育机器”般地对待,用“行走的子宫”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但是当权者制定规则和实施惩罚的目的在于消解女性的主体性,在那些失去主体意识和灵魂的那些女性身上,她们无异于子宫这个器官本身,是丧失了权力庇护而裸露在大众面前的子宫,是因众人聚焦的期望目光而颤栗的器官。
三、献身的困境和在绝境求生的意志
影片中女性是要被秘密筛选的,生育过孩子的女性在通过安检时,就会被国家机关强制留在国内并统一安排到一个地方,这些女性被告知她们拥有了一个光荣的职责:成为使女,生育孩子。人们不会强迫女人生孩子,但是会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孕育生命是她们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风俗把婚姻强加给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禁止离婚[1]82。在列基国,尽管当权者对使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强迫女人怀孕不是最体面的做法,于是便有了冠以新的姓名,配予当权者,以及随处可以看到的对《圣经》的诵读以及对使女身体的管控和行为姿态的要求;作为使女的她们如果想获得更近一步的自由和地位,那就是生育。这一群被划分出来献身的女性,是一群被训练的肉体,按照权威的规定来进行揉捏和伸展,原本自由而激情的肉体在训练中逐渐僵硬,最终实现思想上被驯化。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新孕育出来的小生命被众多夫人围观,她们对这个小生命和这个家庭的夫人赞不绝口,而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使女被隔离在包围圈外,完成生育职责的使女在面对被剥夺孩子的那一刻,也由最开始的喜悦变为惊讶和惶恐,最后语调中转为哀求。处于此种献身困境中的女性,她们就算依附于当权者也无法摆脱被左右的命运,也无法真正拥有自己的权力。
世上一向都有反抗自己社会角色的女人[3]。这个角色是周围环境或社会现实安排给她的,不是女性心甘情愿接受的角色,也不是女性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角色,所以女性要么被动接受,要么奋起反抗。影片中的使女们被安排了使女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由社会需求创造而来,由设定好的场合、服装、姿势和态度将使女困在这个角色中,这些规则都是使女求生或逃离途中需要打破的藩篱。
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4]。影片中的层级监视很明显,里面的“天眼”是用来监视除了权力机构之外的人的,“天眼”之外还有教导嬷嬷以及家里的佣人,是为求得自己生存而为权力机构服务的人,她们渗透在“天眼”看不到的位置,也正是这些监视网络导致使女在逃离困境的过程中屡次失败。所以使女仅仅逃离这个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完全与当权者抗争,只有联合了所有类似于琼这样的反抗者,才能真正地重获属于自己的权力和自由。上文提到,使女被困于社会安排的角色中,主体性尽可能地被压制和消解,但是在困境中求生是人的本能,重重压制之下是人的反弹。烧掉衣服、改变迎合的态度和走出固定的场所等都是打破困境或逃离出角色设定的必要方式。使女在规训中被压制和消解主体意识,同样在围观受刑和强制性交中重新构建主体意识,这个重构过程就是使女的反抗过程,而承受直接伤害的对象就是贵族夫人和嬷嬷:莫依和琼将前任嬷嬷锁在地下室,使得莫依成功逃出困境;艾米莉在垃圾场毒死了之前所属家庭的夫人,作为对她的报复;夫人也逐渐意识到这个生病的社会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向当权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女们也认识到生育子嗣也不一定能获得所谓的自由,私下逐渐联合起来。
影片1—2季中,使女的抗争过程尚未触及到权力层级,但是她们一直试图打破禁锢她们的条条框框:走出限制自由的场所,拒绝集体惩罚“犯错”的使女,尝试和境外组织取得联系等等。这些抗争只是对不想被看作是生育机器,反抗被分配的角色而做的努力,而联合起来,反抗整个病态的社会才是救赎本身。强制女性生育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践踏,为了人口延续而剥夺女性的社会权力,只能刺激到那些被强迫的女性,使得寻求生的渴望和对公平的向往变成拯救自我的信念,这个信念促使女性强烈地想要在这个男权社会为自己呐喊,从而为自己的主体地位和自由而不断抗争。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依旧存在影片中表现出的现象。过分推崇女性生育功能和男性权威的情况正在导致女性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在丧失,但是也迫使女性逐渐向男性权威发起对抗,找寻自我。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作都将着眼点放在女性这个本体上,以女性阶级地位的弱势和角色选择的无奈来展现女性生殖力量的强悍,侧面掩盖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和能力。在男性权力的渗透和运作中,以阶级分化和身体惩罚为手段,以精神和意志消解为终点的权力压制,使得女性急需寻回在社会上的主体地位,成为为自己权力和自由战斗的发起者,成为打破男性权力网络的一个突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