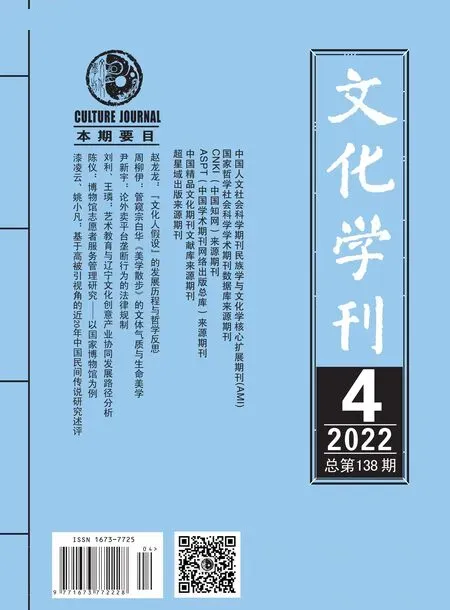论自传记忆书写和身份认同之关系
——以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自传为例
2022-12-07归溢
归 溢
记忆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身份认同理论在很长时间里经历了大转变,“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从一元论过渡到多元论……[1]26”,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离不开记忆的辅助。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指出,人的身份认同的实现建立在人具有自我反思的思维意识之上,这种反思的思维意识毫无疑问与记忆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的思考行为能够回溯到过去的任何一种行为或思想,那么这个人的身份认同就能得以确立[2]45”,即,身份认同可以通过记忆实现。同时,“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于个体在时间的流变中对自我作为同一的自我的认识。”[2]45。时间等因素的流变会促成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身份认同更像是‘短暂的却又极具变化性的一种状态’。身份认同的发展是需要用人的一生去完成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完结状态的过程[2]43”。
记忆主体因其个体差异会对同一现象形成不同的记忆,但是,若个体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且处于相同的历史环境中,他们的记忆会呈现共同特质,与之密切关联的身份认同亦然。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的自传记忆书写和身份认同存在很多共性特征。
在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的名录里有罗萨·查塞尔、孔查·门德斯、玛利亚·特雷莎·莱昂、玛利亚·桑布拉诺、艾尔内斯蒂娜·德·常布尔辛、卡门·孔德等,她们是西班牙20世纪文学“白银时代”的杰出代表,她们通过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的创作在西班牙20世纪文坛留下独特的痕迹,为20世纪西班牙女性文学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所有上述提到的女作家都著有自传:莱昂的《忧伤的记忆》(1970)、查塞尔的《从天明开始》(1972)和日记三部曲 (1982,1998)、孔德的《开始生活:在梅里亚的童年记忆(1914-1920)》(1991)、常布尔辛的《艾尔内斯蒂娜·德·常布尔辛的日记和自传片段》(2008)和桑布拉诺的《胡言乱语与命运:一个西班牙女人的二十年》 (1989),这些自传一方面记录了她们作为女性的个体经历,另一方面构成了西班牙历史见证文本,同时,它们彰显了女作家们为实现身份认同作出的努力。
“27年一代”女作家们的自传通过记忆书写实现身份认同,同时体现了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本文旨在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证。
一、童年记忆书写体现身份认同对过去的选择性重塑
自传体记忆是现在的自我对过去记忆的建构,“现在自我是个体对自己当前属性的认知和评价,与人格、近期目标和信念相联系,它会影响个人如何去回忆自己的过往,如何在自传体记忆中提取信息[3]”。
几乎所有“27年一代”女作家的自传都投入很多篇幅描绘童年生活,其中查塞尔的自传更是集中描写自己生活的前十年,孔德的自传也聚焦在她的童年生活,在莱昂、常布尔辛和桑布拉诺的自传中,童年生活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孔德的自传的序言里,传主回忆自己离开童年生活的城市时的痛苦,并为童年时光已逝而遗憾,其他作家,尤其是桑布拉诺笔下的童年也隐藏着对过往岁月的留恋。对童年的记忆书写一方面表现出传主对回归童年的渴望,另一方面是为了剖析和反思童年生活对自己人格形成的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
杨正润指出,“传记的初始形态是记录生平;其后,传记开始注重表现人格;到现代传记, 传记家又力图解释人格[4]14”。通过自传来解释生平,进而分析人格的形成,是从卢梭的《忏悔录》开始的,它经历了两个时期:1.传统的人格解释方法,包括通过介绍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生活道路来解释传主;2.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新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给传记的解释指出了三种主要途径:俄狄浦斯情结或性心理,精神创伤或变态,童年经历[4]15”。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童年生活的经历是解释作家人格形成的关键,童年时代被看作“是决定自己一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4]15”。
在“27年一代”女作家关于童年的自传记忆书写中,都对自己的出身、家庭关系作了交代。菲力浦·勒热讷对“自传”定义如下:“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5]”。家庭的起源是个体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莱昂的《忧伤的记忆》中,她介绍自己的父亲:“我父亲曾跟随里维拉将军进行独裁冒险,并组建了他的团[6]157”;她还追溯到她外曾祖母的时代:“她是总督女王的侍女[6]149”;关于她的外公外婆:“在我的记忆里,外公是个花花公子。我不知道我是否曾见过他。他住在巴黎,死在马德里[6]147”。她用将近两页的篇幅来叙述外祖父母的轶事,主要反映外祖父对家庭的不负责任,这让我们看到作者是如何间接地揭示外祖父的大男子主义和当时社会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自传并非按线性时序撰写,关于她的家庭情况介绍留有许多空白。这样的安排表明,作者进行记忆书写的意图是实现身份认同,而非记录家族历史。
在查塞尔的自传中,祖父原先是军人,后来成为一名律师;查塞尔的父亲也打算成为士兵,但没有走上这条路:“他认为他的性格使他无法遵守军事纪律,他太暴力,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命令[7]23”。作者用半页篇幅介绍她父亲的家族历史,用更多篇幅介绍母亲家族,并说明原因:“我重新追溯到上个世纪,描摹一下我的父亲和母亲家族人们的生命轨迹,从而解释为什么原先被大洋隔离的两个孩子最终在西班牙的一个城市相遇,并划出了共同的轨迹……也奠定了我的命运[7]23。”
除了家族记忆,女作家们的书写都关照了对自己童年产生影响的人或物。如查塞尔记录父母对自己在艺术和阅读方面的重大影响;莱昂花大篇幅介绍自己的姑姑(西班牙第一位女博士)如何对她进行启蒙;桑布拉诺大力夸赞自己的学校,因为学校促进了她的健康成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自传都提及童年的自己对书籍的无比喜爱。莫罗伊指出书籍在西班牙自传体写作中的重要性:“自我与书籍的相遇是至关重要的:阅读经常被戏剧化,在一个特定的童年场景中被唤起,突然赋予整个生活以意义[8]”。
作家们追溯家族历史回答了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自己成长产生影响的人或物是自我人格形成的条件,对其进行回忆是为实现身份认同奠定基础。童年是一个人最具有完整“自我”的时期,自传中大量关于童年的记忆表明她们对自己的根的追寻,这是传主们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第一步。同时我们看到,传主们对童年生活的素材有目的地进行筛选,都是为了服务于身份认同的建构。
二、消解男权主义定义的女性特质,体现身份认同的流动性
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这一特点与记忆的本质相同。“记忆就是一个根据现实需求不断对过去进行确认、筛选、改造、重组和想象性创造的过程”。“所有认同都在一套社会关系体系内构建起来……不应把认同……看作个‘事物’,而应看作‘关系与表述的体系’……维系一者的认同是……一个持续重组的过程,而不是个已知物……认同被看作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集体行为[1]36”。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主体通过日常行动持续不断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2]43”。“27年一代”女作家笔下的自己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日常行为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有明显差异,尤其是童年时的自己。此外,她们用日常行动挑战传统的社会规范,认为这些规范限制了她们。
首先,她们不约而同地塑造了“淘气”“叛逆”的女孩形象。如常布尔辛在自传中突出自己童年时的淘气,并强调在童年时就知道自己与其他女孩儿不同:“我们住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花园里有很多苹果树,绿色的果实是我们贪婪攻击的对象。尽管有蛀牙的威胁,但雨后潮湿的青苹果吃起来很不错。我和哥哥不顾一切禁令,毫不留情地攻击它们[9]”。女孩儿像男孩儿一样爬树摘果子,这在常布尔辛所处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莱昂儿时叛逆的例子很多,如学生时代在天主教学校看禁书,导致被学校开除的后果。在20世纪初一个女孩儿看禁书的行为,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种种桎梏发起的挑衅。
值得一提的是,查塞尔表现自己儿时的独特个性时,没有塑造自己“淘气”的形象,而是极力展现自己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非凡的智慧。她在《从天明开始》中不断强调幼年的自己是个“严肃、有判断力和有主见的女孩儿,习惯于不断观察别人,保护自己的空间不受大人影响[10]”。她对事物的判断都基于自己的思考,不受他人影响,甚至有些固执:“我不是对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评价它们。这就是说,别人的某些意见对我有很大价值,而其他意见则不[7]64”。她对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分析也持这种态度:“我含蓄地、不断地评判我的父母:他们是我唯一坚持不懈地、系统研究的对象……我只认可我自己的结论[7]35-36”。她还称自己从阅读中获知她自己不能发现、不能创造的东西,她坚信自己能理解和吸收所有读过的内容。上述话语构建出一个自信、有主见、智慧的女孩儿形象。
除以上列举的大量女作家们消解男权主义定义的女性特质所作的尝试,这些女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对其他社会传统提出挑战。如莱昂虽然非常年轻时就结婚生子,但是当发现家庭生活禁锢了她,她毅然离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主动摆脱婚姻桎梏的女性。在认识诗人阿尔维蒂后,她清楚自己后面要走的路,于是坚决地离家,跟祖母道别:“祖母,我要离开了,我要继续我的旅程。拉法埃尔和我的手永远不会分开[6]203。”就此,她摆脱了传统家庭和父权社会为女孩准备的生活。
桑布拉诺对男权社会给女性定下的规则也表现出不满:“如果不是为了哲学,为了那个愚蠢的野心,她——一些爱她的人认为——会成为这个或那个,她至少会结婚,……[11]31”。当时人们都认为女性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智力活动上,桑布拉诺的话对此进行反驳。
上述事例中,或淘气、叛逆,或有主见、智慧的女孩形象,通过对自我的坚守成功实现了身份认同。根据女作家们儿时所处的传统社会标准,淘气是男孩儿的属性,与女孩儿无关,后者应该安静、听话。但是,淘气的形象事实上是女孩儿“完整自我”的体现。根据埃里克·伯恩的人格结构理论,所有人都表现出三种基本的自我状态:父母、儿童和成人。在儿童状态下,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地表达感情;恶作剧是“儿童”状态的本质。
女作家们所处的传统社会用其传统意识形态为女性设立身份,给女性贴上“温柔、顺从、无主见、依附男性”的标签,使她们与“智慧”“主见”无缘,这是一种话语霸权。女作家们用她们的自传消解男权主义定义的女性特质,颠覆这种霸权,完成身份认同。上述女作家们为实现此身份认同所做的努力也证明,身份认同是个建构的过程,具有动态的特性。
三、记忆书写实现社会身份认同
“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认同。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建构的认同被称为社会认同,而依据个人的独特素质而建构的认同被称为个人认同。社会认同是个体对自己与有相同背景的他人(即我们) 的相似性的感知, 同时也是对我们与其他群体或类属成员(即他们)的差异性的感知[12]”。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指出,“自我身份认同”是“社会身份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在争斗中最终达到的和解和妥协[2]44。不可否认,“27年一代”女作家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这些女作家的自传,几乎在每本开篇都先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如莱昂自传的序言,查塞尔日记的开篇,都亮明了自己流亡者的身份;桑布拉诺的自传虽然将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用于记录自己的流亡生涯和心情,但是从第一部分开始,就以一个流亡者的视角回顾自己的童年。流亡者这一特定身份让她们在书写历史时的角度有别于留在西班牙的人,也有别于非共和派的人。叙述主体在孤立、无根的情况下通过自传来实现自我表述,此时她们的身份与第二共和国时期、西班牙内战乃至流亡前所有的身份都构成对立和冲击。这些自传在书写历史时,从个人焦点转向了群体,转向了对西班牙内战及之后状况的揭露。历史对于这些自传而言不再是背景,而是重要内容。莱昂用呐喊的方式书写那段特殊的历史;查塞尔用缄默作为反抗的手段;常布尔辛用平静的、局外人的角度来叙述;桑布拉诺以哲思方式来书写……她们的书写都是对当时西班牙国内已经写就的社会记忆发起的挑战。
作家身份也是她们着力构建的社会身份。查塞尔、莱昂和桑布拉诺的文本都记录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如查塞尔的自传很大篇幅回忆如何从父母处继承对文学鉴赏的天赋;莱昂的自传中记录很多她与同时代著名作家的交流;桑布拉诺在自传中强调书籍对她生命历程的重要性,并坦言,在30年代的西班牙,作为女哲学家、女作家,她几乎被视为“异端,是马戏团的奇葩[11]20”。然而,写作的成功增强了这些女作家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作家的身份让她们从男权传统社会观念中的客体转变为主体。
四、结论
笔者认为,通过“27年一代”女作家们的自传记忆书写,我们看到了其与身份认同的种种关系,一方面,记忆对过去进行选择性地重塑,从而成为实现身份认同的手段。正如《文学、记忆、身份理论初探》一文所述:“回忆让我们形成对自我的意识。通过记忆我们构建起自己的身份[13]。”另一方面,记忆书写体现和证明了身份认同是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身份认同“总是以个体的行为能力和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影响能力为前提,并且在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被重新界定[2]43”。记忆和身份认同都没有终点,它们永远在流动,而“流动本身,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种生活,乃至这其中的一切有关自我认知的行为,最根本的核心价值所在[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