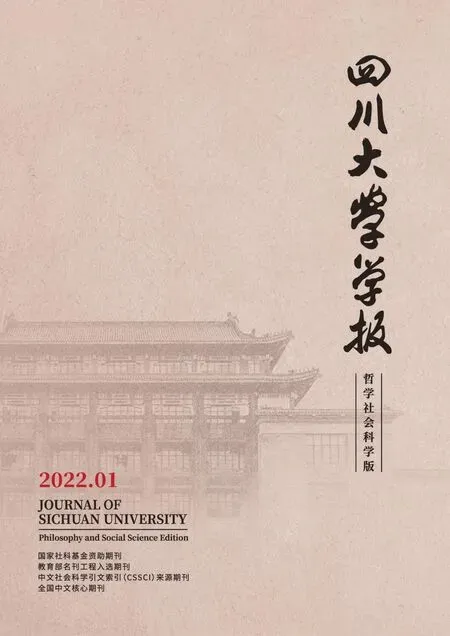美国劳工史的跨国转向及其路径
2022-12-07蔡萌
蔡 萌
关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史学的几次重要转向,国内外学术界业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讨。虽然多数历史研究领域都卷入了史学变革的大潮之中,但每个具体的领域由于自身学术传统和研究特性的不同,变革的发生路径、呈现方式和利弊得失也各有不同。笔者曾撰文梳理了20世纪美国劳工史演进的脉络,尤其是60年代劳工史的社会转向,以及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劳工史的冲击,然而囿于篇幅,对于21世纪以后劳工史的跨国转向未能充分展开论述。(1)可参考蔡萌:《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第141-154页。关于历史学的跨国转向问题,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在整体上进行过讨论,但对劳工史这一具体研究领域却所言甚少,(2)国内研究跨国转向的代表性成果包括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4-160页;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第4-23页;刘文明:《跨国史:概念、方法和研究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57-63页。目前仅有王心扬教授撰文论述过该话题,主要讨论的是帝国劳工史的兴起、创新和问题。(3)王心扬:《跨国劳工史在美国的兴起、创新与问题》,《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第134-146页。本文将在王心扬教授研究的基础上,从更大的视野来考察近二十年来美国劳工史迈向跨国转向的路径,及其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一、挖掘劳工史的跨国特性
美国劳工史在经历了1960—80年代的鼎盛期之后,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走下坡路,陷入题材陈旧琐碎,阵地不断收缩,核心分析范畴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等多重困境。在困境中支撑了十多年之后,跨国转向犹如一股春风,给沉闷的劳工史带来了很多新气象。(4)美国劳工史的跨国转向,既体现了20世纪末整个史学界反思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大趋势,也是劳工史自身发展的结果。相关讨论可参考王心扬:《跨国劳工史在美国的兴起、创新与问题》,《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第135-137页。史家们纷纷热情拥抱跨国转向。以作为该学科主流期刊之一的《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史》(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ClassHistory)为例。该期刊创立于学科鼎盛的1972年,每年两期。据2021年10月12日在JSTOR数据库里对这份期刊的检索结果,全文中含有“transnational”一词的文章共有202篇,其中2000年以前只有36篇,2000年以后大幅增加到166篇;全文中含有“global”一词的文章共有462篇,其中2000年以前有147篇,2000年以后翻了一番还多,达到315篇。
其实,跨国视角在劳工史中并非崭新之物。劳工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国际性的运动,以劳工运动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可能对这种国际性熟视无睹。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劳工史中,讨论域外因素(如欧洲的激进派和劳工活动分子、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等国际组织)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探究美国与其他国家工人之间的跨国联系和团结(如美国工人激进分子对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同情、英法工人对美国内战的关注等),考察美国工会组织模式(如劳动骑士团和劳联等)的跨国传播等,诸如此类的论著早已有之。2000年之前《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史》刊登的36篇含有“transnational”一词的文章,大多也属于此类。可以说,20世纪的美国劳工史家一直在撰写某种形式的跨国史,只不过,他们的撰写是随意的、边缘性的,要么被笼罩在以论证“美国例外”为宗旨的民族国家叙事的阴影里,要么被淹没在支离破碎的地区研究的洪流中。直至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跨国史兴起之后,此类研究才具备了方法论意义,被视为劳工史跨国转向的路径之一。
作为七八十年代劳工史代表人物之一的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晚年曾多次提出,研究20世纪美国工会或社会运动,不能忽略全球经济网络和跨国事件所起的塑造作用。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蒙哥马利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商业和领土扩张是如何激发劳联推广工联主义模式的梦想,使之从原先反帝主义的立场上后退,转变为帝国权力的鼓吹者和实施者。(5)David Montgomery,“Workers'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 Imperialism: The Progressive Era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Vol.7,No.1,Jan. 2008,pp.7-42.同样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劳工史老将谢尔顿·斯托姆奎斯特(Shelton Stromquist),近年来也推出多部有影响力的论著,尝试把自己擅长的地区研究与跨国视角和国际视野结合起来。2008年他主编《劳工的冷战》(Labor'sColdWar)一书,其中收录的9篇论文,分别以洛杉矶的拉丁裔工人、底特律汽车工厂中的非裔工人、新墨西哥州的墨西哥裔矿工、密尔沃基和圣路易斯的劳工左派联盟等为例,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冷战初期的反共产主义思潮如何在地区层面分裂了劳工的组织和斗争,扭转了自新政以来美国的社会改革进程。(6)Sheldon Stromquist,ed.,Labor's Cold War: Local Politics in a Global Context,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最近几年,年轻一代的学者也撰写了多部超越共和范式、从跨国视角重新审视劳动骑士团运动的论著。这些研究强调,劳动骑士团不是一场美国的运动,而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通过梳理19世纪末劳动骑士团运动在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传播,这些论著试图彻底清算“美国例外论”的痕迹,将劳动骑士团视作工人国际主义的一种重要模式,将这段历史作为解决当今世界与劳工相关的诸多棘手问题的一个“有用的过去”。这些论著还发出呼吁:美国其他的劳工组织和运动,如劳联、产联等,都应当被置于全球或跨国视野中来重新审视。(7)这类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史蒂夫·帕菲特,他的相关论著包括Steven Parfitt,“Brotherhood from a Distance: Americ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sm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58,No.3,2013,pp.463-491; Knights Across the Atlantic: The Knights of Labor in Britain and Ireland,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 “Constructing the Global History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Labor: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 of the Americas,Vol.14,No.1,March 2017,pp.13-37.
上述研究,基本上属于跨国视角与传统研究范式的结合,考察的是跨国联系和域外因素对于美国劳工组织和运动的影响。然而,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转向的冲刷之后,劳工史早已超越了制度中心主义,普通的底层劳工,包括大量没有参加工会的“不能言说者”,早已取代工会组织和工运领袖,成为了史家笔下的主角。因此,若要重新挖掘劳工史与生俱来的跨国特性,仅从组织制度的层面入手显然是不够的,势必要把研究重点转到工人自身。在这方面,1990年代移民研究的新进展为劳工史这一重要突破提供了关键资源。
1950年代,著名的移民史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把移民视作背井离乡、抛弃原本生活方式、艰难融入另一种文化和社会的“离根者”(uprooted),进而提出了影响颇大的“离根说”。(8)Oscar Handlin,The Uprooted: 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Boston: Little,Brown,and Company,1951.“离根说”是一种典型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解释框架。“离根”和“同化”的过程就是摆脱原先的民族国家身份,寻求另一种民族国家身份的过程。此后,移民史学界一直有学者质疑“离根说”。无论是鲁道夫·维库利(Rudolph Vecoli)对芝加哥意大利裔移民的个案研究,还是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对20世纪初美国多个移民群体的整体考察,都强调“旧世界”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习俗惯例在“新大陆”的延续性。(9)Rudolph J. Vecoli,“Contadini in Chicago: A Critique of the Uproote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1,No.3,Dec. 1964,pp.404-417; John Bodnar,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这些研究启发人们:仅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解释移民问题是不够的。
1990年代初,琳达·巴施(Linda Basch)、妮娜·席勒(Nina G. Schiller)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多年来对居住在纽约的格林纳达、圣文森特、海地和菲律宾移民的跟踪调查,彻底颠覆了“离根说”。她们发现,这些移民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以各种方式与自己的母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传统移民研究的两分法范式无法解释这些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跨国参与,于是,她们开始用“跨国社会场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来描述这些移民在母国和移居国之间建立的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关系网络,用“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来描述这一关系网络建立起来的进程。(10)相关研究可参考三人撰写的多部论著:Nina Glick Schiller,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Blanc-Scanton,“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2,pp.1-24; “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Vol.68,No.1,Jan.,1995,pp.48-63;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London: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1994.
与传统移民研究相比,跨国移民研究在理论预设和研究主题上均有着显著的区别。在考察移民现象的成因时,它不再固守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藩篱,在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内部寻找推和拉的因素,而是将其置于资本和劳动力全球配置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尤其侧重于探究塑造移民流动的结构性力量。从这一角度来说,跨国移民的研究者通常是某种程度上的世界体系论者。他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被全球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单一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与离根理论一起被推翻的,还有传统移民研究中的同化理论。跨国移民研究强调,移民的身份认同是流动的、多样化的。无论在自己的母国还是移居国,他们都被贴上了不同的身份标签——种族的、族裔的、性别的、宗教的、地区的、国家的等等,而这些标签本身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也就是说,在跨国空间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移民们参与的是两个(甚至多个)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移民始终是美国劳工队伍的主体,因此,移民研究与劳工史向来密不可分。虽然有不少移民研究学者认为,跨国空间的出现是当代的现象,是交通和通讯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种族主义抬头等当代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劳工史家这里,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当代。他们运用跨国主义的理论去考察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移民劳工,探究他们的跨国关系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总体来说,劳工史家们试图回答以下几类问题:那些处于美国劳工市场底层的移民劳工是如何把跨国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抵御种族偏见、缓解经济剥削、改善自身境遇、实现阶层提升的?在跨国关系网络中,移民劳工形成了何种复杂多元的身份认同?移民的跨国行动如何影响了母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政治整合和民族国家的建构?
就近些年的研究状况而言,最具突破性的进展来自对意裔和亚裔移民的研究。大约在2000年左右,唐娜·加巴西亚(Donna R. Gabaccia)、弗雷泽·奥塔内利(Fraser M. Ottanelli)、托马斯·古列尔莫(Thomas Guglielmo)等学者开始对全球范围内的意大利散居群体进行系统研究,其中包括19世纪晚期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他们研究指出,这些移民工人原先只有对自己所在村庄和地区的身份认同,只是到了美国之后,为了回应本土主义者的攻击,才形成了对新成立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些移民工人不仅关心自己祖国的共和政治实验,还积极投身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事业,成为怀揣共和理想的新美国人。(11)Donna R. Gabaccia,Fraser M. Ottanelli and Thomas Guglielmo,eds.,Italian Workers of the World: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Multiethnic States,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与研究欧洲移民相比,研究美国亚裔移民的多重身份认同所面临的阻力要大得多。近年来,王心扬教授曾多次撰文阐述这一问题。他指出,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的影响,“美国化”的主题在亚裔移民史学中长期占支配地位,讨论多重身份认同问题是绝对的学术禁区,会被扣上为白人种族主义开脱的政治罪名。直至跨国主义理论兴起之后,这块意识形态铁板才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12)王心扬:《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第3-15页;《跨国主义与美国移民史学》,《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49-54页。华裔学者徐元音(Madeline Hsu)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广东台山的移民,认为他们的目标并非是融入美国社会,而是衣锦还乡,其身份认同具有跨国和多元的性质。(13)Madeline Hsu,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日裔学者东英一郎(Eiichiro Azuma)更是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二战期间的日裔移民更忠诚于自己的母国日本,而非美国,从而颠覆了史学界对于美国政府拘禁日裔移民政策的传统解释。(14)Eiichiro Azuma,Between Two Empires: Race,History,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二、发现跨国空间
在2015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王立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跨国史。一种是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跨国史,另一种是作为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的跨国史。前者重在揭示塑造美国历史的跨国联系和域外因素,后者旨在重现跨国空间内的人类经历。(15)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4-160页。从组织制度和跨国移民的多个层面挖掘美国劳工史的跨国特性,大致可归为第一种类型,而近十多年来劳工史家对于美利坚帝国的研究则属于第二种类型。
与1990年代兴起的新帝国史不一样,劳工史家关注美利坚帝国,重点不在于把帝国研究从外交史移置到文化史,也不在于强调帝国边缘对中心的影响,而是把美利坚帝国视作一个跨国联系和互动的空间,考察这个跨国空间内复杂多样的劳动力流动、雇佣和管理机制,以及形式各异的控制和反抗活动、模糊不定的人际关系与身份认同。与以往所有的劳工史研究路径相比,帝国劳工史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修订了“工人阶级”的定义,进而极大地拓展了劳工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工人”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拥有自由意志;二是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为生。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劳工史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且走的是制度主义路径,因而其研究对象基本限定为参加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产业工人(还包括少量农业工人),时间段则主要偏重于内战之后。1960—70年代的新劳工史旨在研究“自下而上的历史”,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逐渐扩大,大量没有参加工会的底层劳动者和“不能言说者”统统被囊括了进来。而在帝国劳工史家看来,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是否除了出售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都不重要,所有身处帝国这个跨国空间内,为其建立、维系、扩张和发展而付出劳动的人,似乎都成为了研究对象。
朱莉·格林(Julie Greene)是近年来帝国劳工史的最主要推动者之一。2009年她出版了重要著作《运河建造者们》(TheCanalBuilders),还多次为期刊撰文和组织专栏,在多部重要著作中撰写章节,在各种专业性历史学家协会发表演说,对帝国劳工史进行理论阐释。(16)Julie Greene,The Canal Builders: 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New York: Penguin Press,2009; “Moveable Empire: Labor,Migration,and U.S. Global Power During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Vol.15,2016,pp.4-20; “Builders of Empire: Rewriting the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Global Power,” Labor: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 of the Americas,Vol.13,No.3-4,2016,pp.1-10.帝国劳工史的另外两部代表作是《让帝国运转起来》(MakingtheEmpireWork)和《建造大西洋帝国》(BuildingtheAtlanticEmpires)。两部论文集都出版于2015年,总共收录了20余篇论文,进一步廓清了帝国劳工史这一研究范式的样貌。(17)Daniel E. Bender and Jana K. 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5; John Donoghue and Evelyn P. Jennings,eds.,Building the Atlantic Empires: Unfree Labor and Imperial Stat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1500-1914, Leiden: Brill,2015. 帝国劳工史的其他代表论著还有Jana Lipman,Guantanamo: A Working-Class History between Empire and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Paul A. Kramer,“Power and Connection: Imperial His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6,No.5,Dec.2011,pp.1348-1391.从这些代表性研究来看,帝国劳工史家们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productive labor),但主要不是指产业工人,而是指在各地柑橘、甘蔗、咖啡、香蕉等种植园里为帝国提供商品和创造财富的农业劳动力。二是从事“建设性劳动”(constructive labor)的人,主要指的是建造和维系帝国的人,包括开采资源、运输物资、建造定居点以及道路、运河、港口、仓库、监狱、轮船、政府官邸等基础设施的劳动者,也包括做饭、洗衣、打扫房间、照顾伤病员的妇女,还包括为帝国征服殖民地、镇压反抗活动的军队士兵等。帝国劳工史家们强调,以往劳工史和经济史学者更关注前者,一方面原因在于,“生产性劳动”是维系殖民地生计,推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直接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更清晰可见、更容易量化,而后者“建设性劳动”则很难用生产率之类的标准来测量。(18)“Introduction,” in Donoghue and Jennings,eds.,Building the Atlantic Empires,pp.1-24.
在这些从事“生产性劳动”和“建设性劳动”的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帝国创造的流动的工人群体,如20世纪初在波多黎各蔗糖种植园劳动的加勒比海劳工,在夏威夷劳动的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劳工,在菲律宾劳动的中国劳工,在巴拿马运河区劳动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安提瓜、格林纳达劳工,以及美国本土的白人、黑人和少量北欧、南欧人等等。朱莉·格林对这种劳动力的“流动性”(mobility)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对帝国境内的劳动力进行如此大规模地挑选和调配,绝不是随意之举,而是一种帝国的统治策略,是美利坚帝国用来统治、规训、管理劳动力和确保生产效率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把20世纪初的美利坚帝国称为一个横跨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庞大的“可移动的帝国”(moveable empire)。(19)Greene,“Moveable Empire,” pp.4-20.除了跨国流动人口以外,帝国劳动者还包括大量非流动人口,包括那些一辈子没离开过太平洋群岛的马绍尔农民、终生在种植园里劳作的萨尔瓦多咖啡工人、在马尼拉参加抗议游行的菲律宾工人等等。这些非流动人口在跨国主义的棱镜中是没有踪迹的,但在帝国劳工史中却占据重要篇幅。
从狭义的产业工人,到把“生产性劳动”和“建设性劳动”、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等所有建设帝国的人都囊括在内,帝国劳工史研究对象的范围拓展不可谓不大,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跨越在于,它抹去了自由劳动与不自由劳动之间的界限,把强制劳动纳入了劳工史的研究视野。
帝国劳动史家在考察帝国的劳动制度时,特别强调其强制性的特征。他们指出,无论哪种类型的劳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劳动者或是听命于帝国的强制征调,或是服从于帝国的严苛纪律和强制管理,都不能算作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当然,这一步巨大的跨越并非归功于劳工史家的一己之力,而是得益于几十年来多个相关研究领域的推动。
早在1970年代的奴隶制研究中,经济学家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就试图运用计量学的方法来证明,内战前美国的奴隶制度是高效率、高利润、有活力的,意在强调奴隶制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4.他们的研究备受争议,但影响深远,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投身奴隶制的研究中。这些年轻学者都关注美国历史,都强调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动力在于奴隶制与现代工业扩张的紧密结合。他们成为后来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主力。同样诞生于1970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重在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实现一体化的同时,其内部的极端不平等性。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基础之上的,包括奴隶制在内的各种强制劳动制度则是这一等级结构运作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世界体系理论进一步解构了自由劳动的神话。(2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990年代以后日渐兴盛的大西洋史研究,把早期现代以来的大西洋及其沿海内陆地区视作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进行持续不断跨国互动的空间,尤其注重考察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是如何把大西洋世界的不同地区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主要劳动力支撑的各种不自由劳动制度,包括奴隶贸易、种植园奴隶制、契约奴役制等,在大西洋史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2)相关研究成果极多,如Paul E. Lovejoy and Nicholas Rogers,eds.,Unfree Labo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lantic World,New York: Routledge,1994; John Thornton,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Atlantic World,1400-16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hilip Morgan,“Africa and the Atlantic,” in Jack P. Greene and Philip D. Morgan,eds.,Atlantic History: A Critical Appraisa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23-248; Simon Newman,A New World of Labor: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ation Slavery in the British Atlantic,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那些表面看上去是自由雇佣,实际却处于不同程度的强制劳动之下的士兵、水手甚至海盗,也因其为帝国建构做出的贡献,而被一些史家称为“流动的无产阶级”(floating proletarians)或“大西洋无产阶级”(Atlantic proletarians)。(23)相关研究可参考Marcus Rediker,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Pirates,and the Anglo-American Maritime World,1700-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The Many-Headed Hydra: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Boston: Beacon Press,2000; Marcus Rediker,Outlaws of the Atlantic: Sailors,Pirates,and Motley Crews in the Age of Sail,Boston: Beacon Press,2014; Niklas Frykman,“Seamen o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Warship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54,2009,pp.67-93; Denver Brunsman,The Evil Necessity: British Naval Impressm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lantic World,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3.近年来,这些关于不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逐渐被整合到新资本主义史的名下。新资本主义史旨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在广阔的全球背景下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和转型。它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分析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如何依赖于对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劳动力进行强制性的征调和重组。(24)新资本主义史对于不自由劳动有大量研究,代表性成果有Martin Ruef,Between Slavery and Capitalism: The Legacy of Emancip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eds., 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 Seth Rockman,“The Unfre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in Cathy Matson,ed.,The Economy of Early Americ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New Directions,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35-362; Alex Lichtenstein,Twice the Work of Free Lab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vict Labor in the New South,London: Verso,1996; Sven Beckert,et al.,“Interchang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101,No.2,2014,pp.503-536.在相关领域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帝国劳工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可谓水到渠成。(25)帝国劳工史兴起之前,也有劳工史家注意到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存在强制劳动的现象,但往往都是简略提及,并没有把强制劳动问题作为考察的重点。相关研究可参见David Montgomery,Citizen Worker: The Experience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Democracy and the Free Marke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与之前的劳工史家不同,帝国劳工史家极力揭示劳动制度的强制性,带有一种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
从学科内史的角度来说,1990年代以后,劳工史的研究阵地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学者加入该领域,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越来越得到重视。2000年以前的《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史》中,除了欧洲和美国以外,只会偶尔涉及一些拉美地区的劳工史。2000年以后,该期刊的地理涵盖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展,频频推出讨论东亚、南亚、中东、非洲地区劳工史的专辑。这些对于非西方世界劳工史的研究,严重动摇了自由劳动与不自由劳动的界限。例如,有学者研究20世纪初非洲东海岸的奴隶,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由于拥有一技之长而很少被主人贩卖,其地位非常接近工匠或技术工人。研究巴西种植园奴隶制的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结论:有些奴隶虽然依附于主人,但能够占有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所得,他们和工资劳工的区别非常模糊。对于广泛存在于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苦力制度,学者们长期以来存在争议,有人称其为一种新型的奴隶制,有人却认为它是“几乎自由的”工资劳动制度。(26)代表性研究包括Jan-Georg Deutsch,Emancipation without Abolition in German East Africa,C. 1884-1914,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2006; João José Reis,“The Revolution of the ‘Ganhadores’: Urban Labour,Ethnicity and the African Strike of 1857 in Bahis,Brazil,”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29,1997,pp.355-393; Hugh Tinker,A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 Labour Overseas,183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1974.这些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各种形式的劳动之间具有流动性、渗透性,经典的“工人”定义充其量只是欧美经验的产物,并不适用于解释欧美以外的其他地区。
因此,劳工史研究走向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将工人阶级“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 the working class)。在2012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全球劳工史”概念的提出者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对“工人阶级”做出了一个极其宽泛的界定。他认为,只要满足了两个关键特征——劳动力被商品化、遭受经济剥削,就可以被归为“工人阶级”的一员。(27)Marcel van der Linden,“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Labor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Vol.82,Fall 2012,pp.63-66.2019年7月15日,朱莉·格林在上海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也谈到了帝国劳工史中“工人”范围的拓展问题。她赞同这样的定义:“工人”应当包括所有在全球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固化结构中遭到剥削和压迫的人。(28)关于这次讲座的情况,可参考《朱莉·格林、王心扬:重思美国史与劳工史的疆界》,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42451。
三、跨国劳工史的机遇与挑战
1990年代以后兴起的跨国史是一股强大的史学潮流,渗透到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沉寂多时的美国劳工史也借着跨国转向的东风再度活跃起来。从近年来接连涌现的多部题材新颖、观点独到的论著可以预测,研究以往被忽略的跨国空间内的劳工,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工史的主要发展方向。那么,这场方兴未艾的史学变革究竟给劳工史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呢?
跨国转向之所以能受到众多美国劳工史家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让1960年代以来劳工史的一些重要写作传统,如坚持底层取向,重视工人的自身经验、主观感受和能动性,关注身份认同和阶级形成问题等,有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
自1960年代社会转向以后,美国劳工史便一直坚持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把工会组织之外的底层工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跨国转向兴起之后,“工人”的范围得到了大幅度拓展,大量“底层以下”(beneath the bottom)的、从事各种形式不自由劳动的人统统被囊括了进来,从而打通了劳工史进一步民主化的通道。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继奴隶、士兵、水手、海盗、种植园农民之后,罪犯、性工作者、参与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劳动者等也都成为了劳工史家笔下的主角。(29)“底层以下”和“底层转向”的说法出自Talitha L. LeFlouria,“Writing Working-Class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 and Beyond,” Labor: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 of the Americas,Vol.16,No.4,December 2019,pp.29-34.
斗争是劳工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1960年代那一批劳工史家的笔下,所有的劳动者在面对压迫性权力的时候,永远都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来改善自身境遇。在工作场所中,他们为了工资工时而与雇主斗争;在社区生活中,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亚文化传统而与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斗争。跨国转向兴起之后,工人斗争的领域和方式进一步扩展。研究跨国移民的学者认为,身份建构是一个竞争性的领域,竞争的一方是民族国家的支配性力量,另一方是个体或群体移民通过跨国主义而打造的一个去疆域化的跨国空间。主动维系自己的多重身份,是跨国移民对抗统治者支配的一种反抗方式。(30)Schiller,Basch and Blanc-Scanton,“Transnationalism,” pp.13-14.关注20世纪初帝国劳工的学者认为,流动性也是一个斗争的领域。它是美利坚帝国的统治策略,也是工人用来改善自己生活的工具。在巴拿马运河区劳作的工人利用流动性来逃避帝国政府的监控和管理,并将其作为和雇主谈判的砝码;很多从农村来到城市艰难谋生的人选择加入帝国军队,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激励,更是为了养家糊口,实现阶层提升。(31)Greene,“Moveable Empire,” pp.4-20.
自从1960年代把研究对象从工人组织转向工人自身,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便成为美国劳工史撰写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从地区、行业、工种、技术水平,到族裔、宗教、文化、性别,再到跨国进程和跨国空间,劳工史家们发现,塑造工人身份认同的因素越来越多。考察具体时空情境中工人身份认同的塑造机制,以及多重身份之间的重叠、交叉和流动,成为几代劳工史家们孜孜以求的事业。
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阶级的形成。1960年代,汤普森从共同经历和共同文化切入考察英国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然而此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劳工史一直讨论的则是:美国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法形成?各种塑造工人身份认同的因素,都被视为阻碍了阶级形成,分裂了阶级团结。1960—80年代新劳工史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揭示了族裔、宗教、文化、行业、工种、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如何造成了美国工人群体的分裂。90年代以戴维·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他们以爱尔兰裔劳工为例,展现了种族身份认同是如何压倒阶级身份认同的,进而提出了“白人工资”(the wages of whiteness)一说。(32)David R.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New York: Verso Books,1991; Noel Ignatiev,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New York: Routledge,1995.把跨国因素纳入考量之后,美国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法形成的问题有了更多答案。有的劳工史家提出了“帝国工资”(the wages of empire)一说,强调美利坚帝国创造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新的工人阶级,但这个工人阶级绝不是统一的、同质化的,因为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扩张主义,不同的人感受不同,反应也不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张力远远大于团结。(33)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 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Bender and 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pp.35-58; Greene,“Moveable Empire,” pp.4-20.还有的劳工史家提出了“反共产主义工资”(the wages of anti-communism)一说,认为冷战政治腐化了新政以来的左派政治联盟,美国各地劳工组织纷纷被反共产主义“招安”。(34)Seth Widgerson,“The Wages of Anti-Communism: U.S. Labor and the Korean War,” in Stromquist,ed.,Labor's Cold War,pp.226-257.
虽然跨国转向给劳工史家们开拓了视野、带来了灵感,使传统议题有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然而,它并不能包治百病。1960年代以来的一些“顽疾”依然存在,劳工史未来发展仍面临挑战。
自1960年代起,美国劳工史起便一直保持向其他学科取法的姿态,但是,取法的代价是自己学科边界的模糊化。60—80年代社会转向期间,便有学者评论说:“劳工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史的一个分支。”90年代以后,劳工史向后现代主义敞开怀抱,造成了“阶级”这一劳工史核心分析范畴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性别、种族和语言被视为塑造工人身份认同的更重要的因素。此时,劳工史家们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学科正经历独立性危机,甚至有被其他学科“吞并”的危险。(35)可参考蔡萌:《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第141-154页。在90年代以后的美国著名史家中,说到琼·斯科特(Joan W. Scott),人们首先想到她是社会性别研究的开拓者,说到戴维·罗迪格,人们会说他是一位研究“白人特性”(whiteness)的种族史家,但人们通常不会想起,这两位在性别史和种族史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其实也是劳工史家,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劳工。
跨国转向兴起之后,劳工史家所担心的学科独立性危机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突破自由劳动的限定,并与工业化脱钩之后,劳工史变得越来越像全球史或者“长资本主义史”的一个分支,它与移民研究、奴隶制研究、妇女史、家庭史、种族史、大西洋史、底层社会史等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让帝国运转起来》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讨论帝国创造的亲密关系。该文把为美利坚帝国士兵提供有偿或无偿性服务的当地妇女也当作帝国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理由是她们从事的“再生产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维系了帝国的稳定和运转。若不是出现在这本论文集中,着实很难想到该文与劳工史有什么关系。近年来,几乎所有讨论跨国转向的学者都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认为跨国劳工史未来发展的前景,取决于能否进一步向其他相关学科取法。然而,在不断向其他学科取法的同时,劳工史能否确立和捍卫自己的学科边界,成为一个愈发严峻的问题。
劳工史的另一个“顽疾”是过度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一直以来,美国劳工史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研究领域,其强烈的底层取向是1960年代激进社会运动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劳工史本身就是激进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劳工史家们普遍把批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为底层民众、边缘群体说话,当作自己的道德义务。权力越不平等,他们就越迫切地想要证明被压迫者的能动性。当年,古德曼把每一件损坏的工具、每一根被偷的雪茄都当作工人反抗的证据,并由此被人批评为“感情泛滥”“浪漫地迷恋人民”。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某些跨国劳工史的著作中,那些因为买到不新鲜的鸡肉而跑去跟小店老板理论的家庭妇女,被视作勇于抗争的劳动者;那些挑战船长权威的水手和劫掠帝国商船的海盗,被说成是“有阶级意识的”“为了捍卫自己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而奋勇斗争的人”;海上航行的商船则成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斗争的场域”,成了“社会和经济民主化的学校”。这种由于过度现时主义而带来的“感情泛滥”,不仅是美国劳工史,而且可能是所有坚持底层取向的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