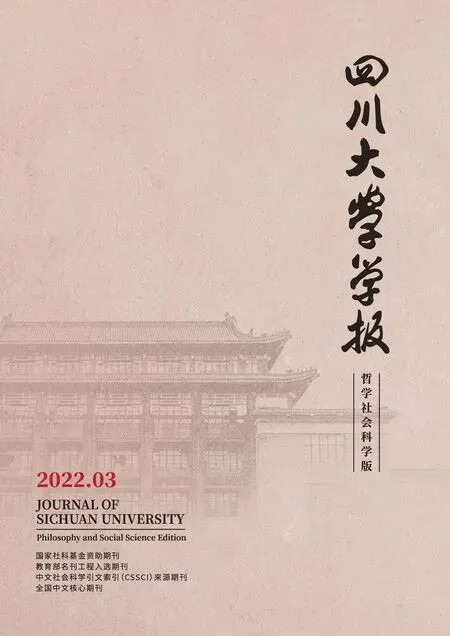器物比德与中国文学批评
——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考察
2022-12-06闫月珍
闫月珍
中国儒家以德为美,(1)本文所谓“德”主要侧重于品行意义上的“道德”,《尚书·洪范》所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列出了正直、武德和文德,突出了“德”的行为准则意义。杜迺松《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德”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发现西周时代“德”的特点:一是贵族称颂其祖(祖父)考(父亲)有美德,并极力要按照祖考的德行去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二是人们把“德”与孝神相沟通,说明“德”是神赐给的,那自然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是把“德”和“天”结合起来,说明奴隶主贵族的德行和统治都是上天(上帝)赐予的;四是把“德”和“孝”结合起来,纪念祖先和同辈时,必须继承他们的德行,方算是孝;五是把“德”作为其时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发现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直至西周初年,都还不完全是道德之“德”,人们所理解的“德”在很大的程度上源于制度和礼的规范,可谓“制度之德”。春秋战国时期,在国家政治以外,个人的品行操守也被视为“德”,特别是孟子真正将德从天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将之深入人的心灵的层面。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如果文学不能承载道德教化之“善”,便不能称之为“美”。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比德”传统。人们以道德观念比附客观事物,将人的主体精神投射到具体对象上,形成了山水比德、金玉比德、植物比德等多种比德方式。与自然物比德相比,学术界对器物比德的探讨相对较少。(2)关于文学中的比德说,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整体出发考察“比德”概念,二是从山水审美意识出发探讨“比德”现象。如钟子翱《论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指出“比德”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理论观点;薛富兴《先秦“比德”观的审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则认为“比德”是以自然事象指喻人类主体德行的儒家美学思想。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文心雕龙》的“以器比德”现象,探讨道德、器物与文学之间精神的契合。
在中国早期语境中,“道德”既用以统称,如《庄子·天道》:“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3)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65页。《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5页。也用以分别称谓,如《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5)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6)《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总之,道和德分别是与天和人对应的,而道德则是天人两个维度的契合。(7)可见,“道”“德”是有分别的。刘康德《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通过对“道器统一”哲学思想的阐述,说明了“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喻道”“明理”的功能。贾晋华《道和德之宗教起源》(《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指出“道”的本义为天道,代表天帝的权威及宇宙的秩序法则;与道相联系,德之本义为天帝/天道正直无私、生生不息的美德、力量及施行。陈鼓应认为“道”的显现与作用就是“德”,他指出“形而上的‘道’落实到人生的层面上,其所显现的特性而为人类所体验、所取法者,都可以说是‘德’的活动范围了”,即“落实到人生层面的而作为我们生活准则的这一层次上的‘道’,就是‘德’(《老子》书上虽然仍称为‘道’,但其意义与‘德’相同)”。(8)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2页。这说明道德包括超越和实践两个层面。
在中国早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器物的功能也发生着变化,这是因为“春秋时代,已经在某个意义上,从礼乐的时代转向了德行的时代,即‘礼’(乐)的调节为主转变为‘德’(行)的调节为主的规范系统”。(9)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陈来发现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德感”的基因,显示出德感文化的醒目色彩,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8页。西周至春秋时期,德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即从“仪式伦理”向“德行伦理”的演变。其中,外在化的德目的是与礼仪文化相适应的,内在化的德目的要求正是与礼治秩序解体相伴而生的。(10)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第376页。在此一过程中,器物的道德形态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是一致的,以器比德成了最为典型的方式。
一、以辨器比识德
在古代封建等级社会之中,器物的形制、色彩、材质等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文心雕龙·铭箴》言“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是说正器物之名、审器物之用能够引发人们对于道德的思考。此一明慎辨物的传统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周易·未济》谓“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论语·子路》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11)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3页;《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53页;《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71页。儒家重视“正名”,认为君子应当明辨名物,才能使社会尊卑有序,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由此,古人以辨器比识德,认为明辨器物的正形、正音、正色、正材,方能领悟到纯正典雅的道德之美。以布帛、漆器为代表的器物色彩之辨,是《文心雕龙》“以辨器比识德”现象的典型代表。
一些器物因其特定的置放方式,具有了辨别空间和时间的功能,这被人们赋予了道德意义。如槷是用以测影以校准时间的天文仪器,由“圭”和“表”组成。“圭”在西周就已经出现,是正南正北平放的测定日影长度的量尺,“表”是直立于水平地面测日影的木杆或石柱,它们组合起来用以记录时间。《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匠人在建造城邑时,树立表杆以悬水法测量地平,用悬绳的方法设置垂直的木柱,以立柱为圆心画圆来观察日影,分别识记日出与日落时的投影,白天参究日中时的杆影,夜里考察北极星的方位,用以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这种确定方位的方法类似于“日晷”。因此,槷具有了法度和准则的意义。由圭表引申出了道德意义,一是诚信,东周时期流行夫君以槷赠予夫人的习俗,以槷喻德的本质在于由时间引申出道德意蕴。(12)冯时:《祖槷考》,《考古》2014年第8期。二是中正和中庸,通过槷测影“立中”是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们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最大特征。(13)何弩:《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可见,通过圭表辨别时间和方位的功能,人们发现其置放方式具有确立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槷的置放方式也被寄寓了道德意义。
色彩是器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器物形式美的构成部分。中国古人受到自然色彩的启发,通过人工的方式将自然的色彩用涂抹、洗染等方式覆于器物之上,制造出绚丽多彩的彩陶、织物、漆器等。约八千年前,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便已出现了紫红色三足彩陶钵。(14)甘肃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编:《大地湾遗址出土文物精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6页。织物自新石器时代出现后,逐渐在先秦时期成了人们色彩审美的主要载体。受传统道德美学观的影响,中国人的色彩审美也被置于伦理道德的框架之下,如儒家就认为器物色彩之美在于其蕴含的伦理道德。器物的色彩因人的比附与阐释而有了尊卑高低之分。古人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以绀、红、缥、紫、流黄为间色。正色往往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专属色彩,如《文心雕龙·章表》“敷表降阙,献替黼扆”(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08页。中的“降阙”即绛阙,指绛色的宫廷,只有君王才能居于其中。而由多种色彩混杂而成、不够纯净的间色则多用于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起居之中。
色彩因承载了社会等级和礼仪规范,而具有社会意义。如《论语·乡党》言说君子服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16)《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31页。就从服饰的角度论说君子对于间色的弃用,将色彩与君子人格联系了起来。对于这种自先秦流传下来的以器物色彩比德的观念,刘勰在《序志》中有如此描述:“齿在踰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25页。漆是古代贵重的涂料,多作礼器。漆器往往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内外均为正色,典雅大方。丹漆礼器具有丰富的道德意义,“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18)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君子亲贤远佞,择善而居,通过对贤德之人的学习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刘勰以丹漆之梦谓追随前哲,体现了漆器颜色的道德意义。
相较于漆器,《文心雕龙》中的儒家传统色彩观念更多地体现在丝织品上。《辨骚》引《离骚传》曰:“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认为屈原的《离骚》高洁脱俗,不为世俗所污,甚至可与日月争光。“涅”是黑色的染料,“缁”指黑色的丝织品,语出自《论语·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至白之物无法用涅染黑,谓君子处尘世而不染。此外,朱紫之分更是儒家传统色彩观念的重点。《阳货》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19)以上引文参见《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35、240页。先秦时期,紫为间色,朱是正色,鲁桓公、齐桓公好紫服,扰乱了以朱色为正色的周代礼仪秩序,而孔子则反对以间犯正的社会现象。辨明服饰用器的正色与间色,就是辨明道德礼法的雅正与淫邪。刘勰继承了儒家传统色彩观念并加以发展和引申,如其《文心雕龙·正纬》有“东序秘宝,朱紫乱矣”和“世历二汉,朱紫腾沸”(2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30、31页。两句,即指两汉时期谶纬之书大行其道,其文虚妄荒诞,不合正体,与真正的符命珍宝真伪混杂,令人迷惑。纬书之于正统经书,犹如紫之于朱,扰乱了正统秩序。辨明朱紫之色,就是去伪存真,刘勰用朱紫两色的伦理意义论说经书与纬书的真伪之辨。
刘勰对传统色彩观念的运用还体现在以正色言说文章的品德和文风,如其《祝盟》云“季代弥饰,绚言朱蓝”;《体性》云“雅丽黼黻,淫巧朱紫”。正色意味着雅正,间色则意味着淫靡,辨别正色与间色,就是辨别雅与俗、正与邪。这种色彩观念被刘勰从伦理学范畴引申到了文学范畴,呈现出器物、德行、文章三者的结合,其《情采》言“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即认为理想的文章应当具有真挚的情感和正确的道理,而不是徒有虚浮的艳丽辞藻,如同锦绣织物上应当是朱、蓝这类代表纯善的正色光彩闪耀,而红、紫这类淫邪的间色则应当被摒弃。不过,刘勰虽继承了儒家的道德化色彩观,但并不被其束缚。生于齐梁这个“美的自觉”时代,刘勰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了色彩的纯粹审美意义,并用以言说文学创作。如《定势》云“宫商朱紫,随势各配”,意即文章体裁的选用如同服饰用器的色彩选择一般,要根据体势调配而并非只能选择正色。《诠赋》更以色彩作比,指出赋应当文质兼备,所谓“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21)以上引文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78、506、539、530、136页。即丝织锦绣的材质再好,也需要各种彩线调和搭配。这里的“朱紫”不再带有道德意义,而是纯粹视觉审美的色彩。
二、以器质比德质
文与质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基本议题之一,最初源于对器质与纹饰的思考,即对本质美与形式美关系的探讨。《礼记·聘义》借孔子的话总结了玉的人格化所具有的11种品质: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22)《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670页。
这是儒家“玉德”观的基础,阐述了“君子比德以玉”的内涵,将玉的11种特质与君子的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11种德行相比拟,以玉德作为修身养性的典范。
与玉之温润不同,金则体现出坚硬的质感。《荀子·劝学》:“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这里以木变直、金变利为喻,说明德行和智识是一个逐渐达到完善的过程,强调了后天教化对人品行的意义。《荀子·性恶》:“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又言:“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23)以上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35、441页。荀子将材料成器的过程视如人之德行臻于完善的过程,认为对器物的雕饰和制作可以实现礼制和引导德行。
“文”的本义是相交错的线条纹理,指人们通过镂刻和雕绘造就的器物外在形式之美,如色彩、纹饰等。“质”具有多重含义,(24)“质”可以指器物的本质、原材料,即质实;也指器物的实用功能,即质用;还指器物装饰较少的质朴形态,即质素。参见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与“文”相对时,主要指器物的本质、材料,即质实。美质经雕饰以成文,是人类美感的启蒙。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造物纯为实用而造,器物粗糙简陋,其功能意义远大于审美意义。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产生了审美意识,并在器物制作中显现出对器物形式美和本质美相统一的追求。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出现了许多精美的石雕、骨雕、玉雕、彩陶,如为人们所熟知的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朝阳纹蝶形牙雕等。宗白华指出:“‘体’上之‘饰’‘文’,‘朴’上之‘巧’‘雕’;骨,牙,玉,铜,陶之饰文,为美观之出发点。”(2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15页。对器物的雕饰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萌生之处。
从器物到人伦,对于器质与纹饰关系的探讨启发了人们对道德的思考。建安时期的徐干在其《中论》曰:“学犹饰也,器不饰则无以为美观,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26)孙启智:《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是说人要学礼以修德,如器要雕饰以为美。文化和礼仪的教育是人为的手段,而雕饰的前提是要有美质。孔子用治木和筑墙来说明德质的重要性:“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27)《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9页。即有了美质也需加以雕饰,使文质兼备,才能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高度。刘勰继承了孔子以器质比德质的思想,从器物的文质关系出发探讨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如他在《程器》中论作家才德时说:“《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2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18页。木匠将良材雕削成器后施以丹漆,泥工砌起墙后进行雕镂绘饰,刘勰认为作家也应当如这样的木器、墙壁一般,兼有器用与文采。
相比于崇尚质素而反对任何人工修饰、主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58页。的道家,以及讲求极端功利使用价值、推崇质用的墨家,主张“文质彬彬”的儒家肯定了文饰的作用,但仍以质为根本,美好到极致的质地甚至可以不加修饰。孔子有言:“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30)刘向:《说苑·反质》,程翔:《说苑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4页。质地本身散发出光辉,是最高级的美,因此,宗白华认为中国人理想的君子人格是“温润如玉”,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3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页。刘勰《情采》说:“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3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538页。“贲”指文饰,而白贲是贲卦最后一爻的爻辞,经历了“由质而文,又返质”(33)阳志辉、骆彤:《〈周易〉“贲”卦对中国美学的启示》,《中国美学研究》2018年第2期。的过程,是文饰的最高境界,即以质为文。刘勰视白贲为艺术的极致之境,认为华彩藻饰最终应当归于自然。
玉器是器物制造与欣赏中以质为文的典型,展现了美善合一的审美理想。玉器之质被古人称为“玉德”,是需要综合利用触觉、听觉、视觉等来感受的本质美;而玉器的颜色和自然纹理被称为“玉符”,指向直观的视觉审美感受。玉的“符”与“德”相对应,虽然一个外显易察、一个内隐难辨,却都是美的象征。当玉符与玉德相协调、形式美与本质美相统一时,玉器便能焕发出夺目光彩。这种文质相称的境界在刘勰笔下被称为“符采”,《宗经》曰:“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范文澜注:“《论语·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詹锳按:“四教之中,文与行领先,所以‘四教所先’就是文与德行。”(34)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23、29页;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页。“符采”实质上是指玉器的文质相彰、尽善尽美的状态。文采要立根于德行,德行又要靠文采来传播,正如玉符以玉德为根本,玉德因玉符而显扬,二者相互协调统一,方能成就玉的浑然之美,为文者要内修德行、外修文辞,才能立德立言,流芳百世。
从道德引申至文章,刘勰以“符采”言说文章内外统一、文采焕发的状态。前引《铨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就是指文章的巧丽之词和明雅之义,如玉的纹理光彩和玉的美质一般相称。在《风骨》中,刘勰认为理想的作品应既有风骨又有文采,并总结说“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关于“符采”一词,牟世金认为“旧注多指‘玉之横文’,刘勰虽沿旧说,但还有其具体命意。‘符’,信也,本是合以取信的意思;用‘符采’指玉纹,正取玉的花纹和玉合而为一之义”。(35)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36、514页;牟世金:《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下)》,《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才华卓越之人能将文章的风与骨、情与气相结合,像玉德与玉符一般浑融一体,呈现出更美好的状态。儒家重文饰,而以道德本质为根本,主张文质相符,“白贲”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体现了以质为文的思想。刘勰的符采说主张人的道德品性与外在修饰要相称,以器质比德质,用玉器之美彰显德行之美与文章之美。后世归有光秉承儒家思想,也道出了德文相符的观点,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3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周本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4页。无论是器物还是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质地本身散发光辉。
三、以制器比修德
器物之制作在中国古代被用以比喻人格修养逐渐完善的过程,表达理想的人格典范和社会形态。(37)闫月珍:《儒家的制作图式及其与道家的分判——以中国早期哲学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君子”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在西周时期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诗经》中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贵族,如《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雨无正》的“凡百君子,各敬尔身”等。(38)《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70、732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著述中君子道德内涵开始确立。《论语》中包含了大量对“君子”的描述,并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体系;《墨子》里“君子”的道德标准略显零散,包含行义、兼爱、无斗等多个方面;《庄子》里的君子则行事合乎天理而不拘于仁义,其标准在于能够顺应自然、保全本性。(39)何李:《先秦“君子”:身份标志向道德内涵的延伸》,《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3日,第15版。可见,基于不同的主张,人们论德行的标准也是不同的,但其所遵守的道德维度是群体性的和公共性的。
在儒家看来,德是道的寄寓,本自天赋,但需要经过后天的教化而习得。《诗经·抑》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里的“磨”即教化的过程,以白玉之污点尚可磨除,喻人说话不慎,也有挽回的可能。又,《淇奥》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诗序》说此诗“美武公之德也”,孔颖达疏:“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谓武公,能学问听谏,以礼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见切,如象之见磋,如玉之见琢,如石之见磨,以成其宝器。”(40)《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校点本),第1167、214、216页。则这首诗是夸赏卫武公按照规谏的要求,如治玉石般修养自己的德行。二诗皆以雕琢玉器比修行美德。
以制器比修德,是因为工匠的制器经验与君子致道修德之理相通,《论语·子张》中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又,《卫灵公》中载孔子以工匠制器的经验来比喻培养仁德的方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而》中有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安国注:“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能自切磋琢磨。”都是将器物制造的过程与德行修养渐进过程相比。尽管孔子主张“君子不器”,(41)见《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校点本),第257、210、12、19页。力倡“为人” 的“道”“仁” 境界,(42)刘绍瑾:《孔子复古思想的审美文化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君子不器”,即所谓“为己之学”。刘绍瑾认为,“自境界言,‘为己之学’成就的是修身养性、娱情悦性、玩物适情,也就是后来注家所谓‘美其身’‘附其身’‘因心会道’。而自发生言,‘为己之学’因‘得之于己’,忠实自己的真实性情和真实感受,厚积薄发、闳中肆外、绷中彪外,体现的是一个因内符外、诚中形外的自然流布过程;而‘为人之学’则‘欲见之于人’,趋世媚俗、矜己耀能,把学问、文章当作鬻声钓世、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前者得诚,后者易伪,程子‘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的解说可谓切当。因此,‘为己之学’包含了抗俗拔俗、坚守纯粹的学术品格、保持独立的人格操守的深意”。但我们发现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修养的过程,并将德行的完善比喻为器物之制作,说明两者都是后天逐渐实现的。工匠经过重重步骤,将泥土、木料、青铜等原材料制成精美的器物,正如同人通过外在教育和自我修炼提升道德境界、使人格臻于完善的过程。
制器首先要对原材料进行处理。木匠需要砍削掉木材上多余的枝干,玉工需要通过切磋、琢磨去除璞玉上的瑕疵,冶工则需要通过冶炼去除金属中的杂质。徐干在其《中论》中云:“夫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斯其性与?良工为之,以纯其性,若夫素然。故观二物之既纯,而知仁德之可粹也。”(43)孙启智:《中论解诂》,第48页。良工可纯珠瑾,君子可粹仁德,这种通过工匠人为加工而使得质料更加完美的过程往往被用来比喻君子修德进业的努力。相比于木工、玉工来说,冶工对原材料的加工改造进行得更为彻底。古代青铜器以铜锡合金铸成,因为原始的红铜硬度较低,不宜制作工具,但适量地加入锡后便能造出坚韧耐磨又易于锻造的青铜,用来制作工具、兵器、饮食器等,中国也由此进入了青铜时代。“金锡”乃铜和锡,青铜经过冶炼变得纯净而不含杂质,被古人用来比君子之修德,故《淇奥》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44)《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校点本),第219页。刘勰《比兴》曰:“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他在这里以金玉并论,意谓金玉因材质美而工艺精形成了器物,德行之修炼同样需要如此。又,其《颂赞》曰:“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45)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01、158页。所谓“黄白”,也是指铜锡合金,“黄白之伪说”典出于《吕氏春秋·别类》,其中相剑者说锡可以增强硬度,铜可以提升韧度,故铜锡合铸可为良剑,但非难者却偷换论题,说锡使剑不韧、铜使剑不坚,怎可能制出利剑。这一匠人制器的辩论前后经历了逻辑的变换,刘勰用“黄白之伪说”形容挚虞《文章流别论》在论“颂”这一文体时前后矛盾,虚妄如同那没有铸剑经验却胡乱质疑相剑者的非难之人一般。
在准备好原料后,匠人会在严格遵循规范的前提下制造器物,以圆规、曲尺、绳墨定方圆曲直,以黄钟律管定乐器的标准音,以陶范、泥模铸造青铜器。《说文》云:“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南唐徐锴注:“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46)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0页。可见遵循程式规范是器物制造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对于“巧饰”的要求。
在中国古代,乐器承载着礼乐教化功能,要求乐声雅正合律,因此乐器制造最为关键的步骤之一便是测音定律。刘勰《书记》论“律”曰:“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律管是古代标准定音器,由12支竹管或铜管组成,其中最长的一支叫黄钟管,发黄钟音,是整个律管最重要的起始音。(47)戴念祖、白欣:《中国音乐声学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23页。刘勰强调乐律正音始自黄钟调,其《声律》曰:“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48)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58、553页。就是以《诗经》为黄钟,即正统之标准,认为《文赋》继承了楚辞的用韵,却失去了《诗经》的正统之音。
《说文》曰:“律,均布也。”说明“律”意味着平正不偏,诸事有法可依。黄钟律管以其整齐、稳定、精确的特性,启发了人们的规范标准意识,所谓六律协而五音正,五音正而德音成。刘勰《乐府》云:“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4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02页。律管的制作工艺至汉代已失传,三国时期杜夔奉命调律,使得音乐雅正舒缓,荀勖改变了钟磬悬挂的距离,使得声音哀戚急促,不合中和之音,直到周代的古铜尺出土,荀勖才认识到钟磬悬挂距离过短的错误。刘勰以“杜夔调律”“荀勖改悬”之典,强调了律的法度标准与德音、正声的密切关联。《周语》曰:“度律均钟,百官轨仪。”(50)《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人们度量律管以调和钟磬之音,定出各种行事的法则,《汉书·律历志》即以度、量、衡之概念皆出于律。音乐因有律而和谐,可以成教化、助人伦,国家因度量衡标准的制定巩固集权统治,经济贸易则因有了统一的标准而能顺利交易,整个社会都因有“律”而秩序井然,故段玉裁注《说文》曰:“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5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从原料的制备到具体的制作工序,器物的制造需要遵循法度和规范。中国人由器物制造而产生了“律”“度量衡”“规矩”等观念,其中蕴含着修身正己、持中守正、遵礼循法的道德观念。
四、以器用比德彰
器物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被制造出来的,有“用”方能称之为“器”。中国古代器物可主要划分为实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三大类别。(52)陈少明:《说器》,《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在日用之外,器物还满足了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圭璋、编钟、青铜鼎等器物便承载着礼仪道德,使用这类器物便意味着道德的彰显与弘扬。
一是器物之佩带方式。这体现为人们对阶层与其佩玉方式有着规定,《礼记·玉藻》云: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縕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
这里的“德”实质是指礼制,玉的分别其实是权力和阶层的分别。在具体实践层面,《玉藻》中有如此要求:“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并对君子佩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旋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53)《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14、913页。
“君子于玉比德焉”,“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这些佩玉规范着意于君子应该“中规中矩”,行动有法度,举止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君子行止须有规矩还体现在古代深衣形制中,《礼记·深衣》中有“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 “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54)《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561-1562页。等记载。其中,深衣袖圆符合圆规,象征公正无私;背缝垂直似墨线而领子方正,象征正直不阿;下摆齐平如锤和砰杆,象征志向恒定而处事公正。沈文倬认为,礼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名物度数’,就是将等级差别见之于举行典礼时所使用的宫室、衣服、器皿及其装饰上,……把这种体现差别的器物统称之为‘礼物’”;二是“‘揖让周旋’,就是将等级差别见之于参加者按其爵位在礼典进行中使用这礼物的仪容动作上,从他们所应遵守的进退、登降、坐兴、俯仰上显示其尊卑贵贱”。(55)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服饰不符合礼制的行为就是“僭礼”。《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叔孙说:“服美不称,必以恶终。”这是说,人的衣着、装饰不与其人相适应,必得恶果。《诗经》中也有讽刺“僭礼”行为的诗,如《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人们强调文饰与质地的一致,所以《论语·雍也》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6)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校点本),第1054页;《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校点本),第474页;《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校点本),第78页。
这就形成了一套相对较完整的祭祀礼乐制度。如关于食器的使用,天子(周王室)用“九鼎八簋”,诸侯(分封于各地的公、侯、伯、子、男)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为周王室或者诸侯国服务的大臣)用“五鼎四簋”,士(周代贵族的最低一级,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
二是器物之放置方式。这体现出人们由器物的状态抽绎出社会和伦理意义,如《荀子·宥坐》: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5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0页。
欹器的特性,在于警示鲁桓公满则易覆,应守中庸之道。而孔子观欹器谓人要有谦虚中正之德,观明堂壁饰而悟周之兴盛在于德。(58)《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于明堂,睹四方之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徘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参见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第72页。可见,器物的纹饰、颜色等外在属性,也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意义。
玉佩相击之声整齐而有韵律,方能显示佩玉之人行为举止大方有礼,对此刘勰《声律》云:“古之佩玉,左宫右徴,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宫、徴是中国古乐基本音阶。孟凡玉指出,以羽—宫、角—徵这两个小三度音程为代表的“君子音程”呈现出平稳、柔和和内敛的特点,符合君子人格理想特质。(59)孟凡玉:《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君子音程”》,《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1期。君子佩玉以节其步,步伐端正、步调稳重能使玉声有序动听,刘勰认为作文也要以音来规范文章,正确使用音律声调,其《丽辞》云“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玉润双流,如彼珩珮”,(60)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554、589、590页。均以君子佩玉之音来言说对偶所呈现出的和谐对称、精致圆转之美,文章的修辞如玉佩一般在平衡中又有富有变化。
在所有玉器中,圭和璋是最能代表德的贵重之器,均是古代被用于聘礼、朝见的瑞玉。聘礼为诸侯邦交之礼,若使节持圭璋以行聘礼,不需要多余的钱币就能享受到不受阻碍的通达待遇。正如君子有德,不需凭借他物便能成事,故《礼记·聘义》曰:“圭璋特达,德也。”(61)《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670页。以器物之用譬喻人之有德,是常见的思维方式。刘勰也多次提到圭璋,如《比兴》云“珪璋以譬秀民”,就是沿用《诗经》中以圭璋比有德之君子的说法阐明“比”的含义;又,《风骨》云“文明以健,珪璋乃聘”,意在说明若文章风清骨峻,就能如君子持圭璋行聘礼一般,在文坛中得到普遍的赞誉;《时序》以圭璋言说文学才能,云“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物色》以圭璋形容人应时感物的心灵,云“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62)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01、514、675、693页。圭璋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玉礼器,既有美质,又有器用,故可以喻指君子明德善行,并逐渐成为文章、文才的理想。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中“器用”与“文德”的关系。刘勰在书中专设《程器》一篇评议文人德行,其标题中就以“器”喻文人之德。器以有功用为德,故人之才用被称之为“器用”,人学以成才被称之为“成器”。《礼记·礼器》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郑玄注:“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人情以为田’,‘修礼以耕之’,此是也。”(63)《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716页。学礼修德有如以耒耜耕种农田,人因有礼而成器用、有盛德。赵树功指出《后汉书·班彪传》中“德器”连用,是以器为德的体现,也是以成用为德思想的发展。(64)赵树功:《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3页。文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具有多重含义,而刘勰在《程器》中的所使用的“文德”,指的是器用与文采兼备的文人品格,(65)寇效信:《〈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页。器用乃文德的一部分,文德以器用为本。《程器》多以木材器用来论说文德,如“《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说上好的木料质地坚实细密有美丽流畅的纹路,兼具器用与文采,故能任国之栋梁。又如,“楩柟其质,豫章其干”,这是取用陆贾《新语》所言“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66)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页。认为文人应当有楩柟豫章之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此方能称之为有文德。再如,“雕而不器,贞干谁则”,(67)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18、720页。所谓“贞干”即桢干,是古代以版筑之法筑墙时所用的木柱,杨公骥指出“桢干”的方正、坚实与否直接决定了筑墙工程的成败,因此“桢干”逐渐转化为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人或事的抽象名词。(68)杨公骥:《漫谈桢干(学习哲学和语言学的札记:词根探索之一)》,《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刘勰在这里以“贞干”喻指成大事之贤才,是以器用比德彰,指出若只雕饰文采,却不注重器用,就无法能成为于国有用的贤才。
结 语
器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衍生出了意义。伊恩·霍德在《物的意义》中提出从三个方面考察“物”的意义,即:“情境”(context)、“结构”(structure)和“行为者能动性”(agency)。(69)Ian Hodder, The Meanings of Thing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73.在仪式活动中,人们通过程序的设置和规定,使器物具有了典章制度的意义,成了人文的物质显现。在此一过程中,“德”成了礼制的体现,器物被赋予了道德意义。器物不仅包含着仪式意义,还包含着德行意义,如《礼记·礼器》所言:“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70)《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716页。这里的礼和德是一体的,礼是德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德的施行,德的实质体现于礼。
人们以器比德,显示了尊卑有序的等级,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社会与个体、器物与道德被有机地统一起来,(71)彭兆荣《体性民族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法的探索》(《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认为,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天地人”三才、三维、三位的形制为文化体性的根本,从文化体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民族志,有利于超越民族志表述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主位/客位”二元对峙的阴影。吴光帜《“物的民族志”本土化书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认为,围绕“何为物”的话题,西方哲学层面上形成了唯物与唯心、物质与精神、存在与虚无、客体与主体、客观与主体、世俗与神圣等二元结构的世界认知图式,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物”与“事、人、礼”置于一体,物即事、物即人、物即礼,塑造了天地人三维一体的认知图式。这说明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会治理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材料、技术和制作是物质性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是意识形态性的。人们对前者的社会学意义进行了规定,这意味着前者承载了相对抽象的社会意义。从表面上看,这种道德叙述甚至掩盖了物质性,但恰恰是物质性的存在成就了道德的合理性,技术落实于器物,实现了对社会文化的治理功能。也是在此意义上,器物具有文化治理功能。在上述关于器物之道德形态的叙述中,技术、伦理和审美三者有机结合成为一体,由此可以说,人们对道德的塑造既是硬性的,同时也是柔性的。彼得-保罗·维贝克认为:“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mediation)的作用,用图式表示就是:人—技术—世界。技术不但影响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72)“道德物化”是当前技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维贝克称伊德的进路为“解释学的”(hermeneutical)视角,拉图尔和伯格曼的进路为“存在主义的”(existential)视角。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技术通过影响人的“微观知觉”和“宏观知觉”调节着人对世界的感知,即影响着世界呈现于人的方式,其机制是“放大”和“缩小”;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技术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调节着人的存在形式,即影响着人呈现于世界的方式,其机制是“激励”和“抑制”。两种视角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后现象学的技术中介理论。参见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哲学动态》2013年第3期。其中,实现物的文化治理功能,其途径在于将物转化为人认知、情感和意志的一个有机部分。
器物具有约束和调节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功能。一方面,器物对公共情感具有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器物对个体心理具有疏导作用。进一步言,以器物比德是一种文化建构的方式,这种文化建构可以有力地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器以有功用为德,故人之才用被称之为“器用”,人学以成才被称之为“成器”。人因有礼而成器用、有盛德,后世也多以“器”论文人之德。“器”的语义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由对象到主体的演变路径,而这种变化与器物中的道德内蕴是分不开的。
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刘勰继承了儒家道德观念,在《文心雕龙》中以“器物比德”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他以辨器比识德,主张明辨朱蓝之正色、黄钟之正响,推崇道德与文章的雅正之美;其次,以器质比德质,从木器、泥墙的先质后文到玉器的以质为文,从器物的文质关系出发探讨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再者,以制器比修德,将金属冶炼时对质料的重塑、律管定律时对器物的规范,喻指人修身正己的过程,并将其引申至文体的规范性;最后,以器用比德彰,借玉佩、圭璋等玉器之用比君子之德行和文章之美,又以木材喻人才,论说文德以器用为本。可以说,《文心雕龙》中的“器物比德”现象俯拾即是,这根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器以藏礼”的礼法观念。
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天地万物与人相通,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器物的创制依据上,这体现为“观物取象”的方式;在器物的制作程序上,则体现为天人合一之道,即天时、地利、材美、工巧四者合一,方能成就良工;在器物的外在形式上,呈现出器物承载天地之道的形制,即如《考工记·辀人》所言,“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73)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页。圆形的车盖和方形的车厢分别象征着天、地,三十条轮辐象征着日月,二十八条车弓则象征着星宿,人居于车中如处于天地之间,深刻体现了车辆制造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天地生万物有其道和德,人类效仿天地,所造之器也承载着“道”与“德”。这就将物质与观念联系了起来,使得以人的道德观念比附客观物象的“比德”方式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器以藏礼”的礼法观念是“器物比德”现象的社会基础。《左传》有言:“器以藏礼,礼以行义。”(74)《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91页。“礼”是儒家倡导的社会行为规范,是维护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器物是礼的载体,抽象的“礼”需要以器物作为具体的象征。“器以藏礼”的观念使得形而上的道德与形而下的器物联系了起来。人们赋予器物以道德内涵,以器物来诠释“礼”。“礼”与“德”相统一,德是具有导向性的本质内核,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而礼是有着一定强制性的外在规范,是受到普遍认同的行为模式。礼中蕴含着德,德又借礼而显现,二者统一于“人”这个主体之中,形成“德内而礼外”的关系。儒家倡导以德化民,以礼齐民。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乃道德之器械”。(75)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7页。人心之德与天地之德相通,德由内而外呈现为礼,而德和礼往往落实于器,形成天、人、器之间的意义序列。器物是观念和意义的统一体,器物比德的实质是以器载德、以器彰德。这使得器物在功利的实用价值和纯粹的外观形式之外,因道德寄寓而包含了更丰富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