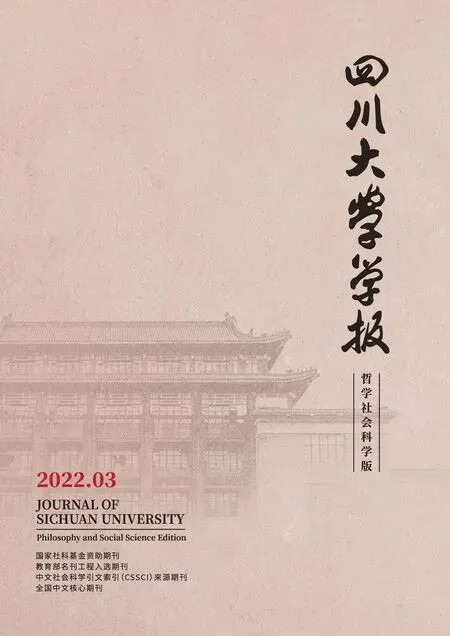《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2022-12-06张培高
张培高
一、问题的起源
现本《中庸》原为《礼记》的一篇,宋以前虽有韩愈、李翱等推崇,但影响有限。至宋代,(1)黄宗羲把“胡瑗”等称为宋初三先生,准确地说,“三先生”的主要活动年代已是北宋中期,而本文所说的邢昺、田锡、陈充、赵湘主要活动年代最迟也在真宗早期,所以称为宋初更为恰当。其地位与影响得以极大提升,并成为四书之一。相关《中庸》在宋代地位提升的成因,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最初得益于释僧智圆,宋儒推崇《中庸》是受智圆启发的结果。该主张由陈寅恪最早提出。他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且不详论。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页。陈先生在此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从时间上,《中庸》在北宋受重视实由佛教徒始发,二是从原因上,儒士重视《中庸》主要受佛教徒的影响。十几年后,钱穆亦提出相近的观点:“盖自唐李翱以来,宋人尊《中庸》,似无先于智圆者。”(3)钱穆:《读智圆(闲居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5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1页。21世纪以来,随着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入,这个问题再次受到学者的关注。2001年,漆侠指出:“宋人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但最早探索《中庸》的不是儒生,而是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的方外之士——释智圆。”(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余英时先生也说:“北宋首树《中庸》之帜者必数智圆,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85页。
较早对该说提出质疑并加以反驳的是饶宗颐。他说:“宋代已有所谓‘新儒学’是寅老首先提出来的,他把宋代新儒学的先觉人物的美誉颁给智圆,然而智圆是否真的能担当得起呢?这还是有问题的。我们仔细考察历史,宋代初年以‘中庸子’为号的实际上最早是陈充……《全宋文》卷一零一据《藤县志》录陈充《子思赞》,有句云‘忧道失传,乃作《中庸》。力扶坠绪,述圣有功’,足见其揭橥‘中庸’年代在智圆之前。智圆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1021),陈充则卒于大中祥符六年(1014),年七十。充于太宗雍熙中登进士,乃智圆的前辈。宋初儒者邢昺于景德间曾指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而言(《宋史儒林邢昺传》),所以不能说重视《中庸》是出于释氏的提倡。”(6)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310页。该观点得到了一些学人的赞同。朱汉民、肖永明就曾引述饶先生上述观点;(7)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4页。吴国武亦认为漆、余两先生继寅老之论而加以做实,是“考虑欠周详”和“似亦不准确”的。(8)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回过头来看,饶先生的证据虽较充分,但仍有待明晰。第一,饶先生没有指出陈充、智圆重视《中庸》的具体或大概的时间。如果仅以出生或生活年代的早晚而作为陈充推崇《中庸》早于智圆的关键证据,显然不充分。如果说陈充死于智圆少年时,此据或许可以成立,关键在于两人生活的年代交叉不少。第二,饶先生并没有分析陈充、邢昺与智圆的关系。如果他们与佛教徒关系密切,亦可能他们重视《中庸》源自释氏的启发。第三,余英时和其他学者(如夏长朴)也注意到邢昺推崇《中庸》的材料,既然如此,为何他们还会说智圆先于儒士重视《中庸》呢?这就涉及对这条材料的诠释问题了。余先生对邢昺推崇《中庸》作了以下解释:“邢昺曾教过真宗《礼记》,自然熟悉《中庸篇》的内容。他特别指此篇为说,似乎显示《中庸》已可脱离《礼记》而具有独立的地位。此事发生在范仲淹‘省试’前八年,则更值得注目。但是他专挑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一章来发挥‘大义’,可见他仍视《中庸》为讲‘外王’之作,并未重视其‘内圣’的部分……当时只有佛教徒如智圆之流对此最擅胜场,儒学阵营内似少其人。”在此,又可以理解为智圆之所以是“首树《中庸》之帜”者,不在于邢昺与智圆推崇《中庸》的时间之先后,而在于谁先从“内圣”角度解读《中庸》。也就是说,即使邢昺重视《中庸》在时间上早于智圆,也不能由此断定儒家重视《中庸》早于释氏。因为“北宋释氏之徒最先解说《中庸》的‘内圣’涵义,因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谈辩境域’。通过沙门士大夫化,这一‘谈辩境域’最后辗转为儒家接收了下来”。(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4、96页。夏长朴也持此观点。他还注意到:“这些学者(指陈充、宋太初、晁迥等)共同的治学特征是以《中庸》来会通儒、释,甚至会通儒、释、道三教。”(10)夏长朴:《论〈中庸〉兴起与宋代儒学发展的关系》,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148页。对照余、夏两位先生的论述,显然饶先生及其同调的分析未能切中要点。
青年学者杨少涵把学界对《中庸》在宋代升格之因的探讨概括为“回应说”(杨儒宾)“回流说”(余英时等)两种(笔者认为二者未有根本的区别),并总结道:“《中庸》升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礼记》的升格,《中庸》也水涨船高,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必读熟读书籍。这是《中庸》升经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庸》自身文本富含思想性、思辨性,能够成为道士清谈与佛徒格义的借鉴文本,也方便科举考试的策论出题与考生引以答问,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庸》升经的内在原因。”(11)杨少涵:《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中庸〉升经再论》,《文史哲》2019年第3期。大体上看,该结论有些道理;然仔细辨析,该论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回应上述两种说法。首先,《中庸》之内容,自其形成之日就已如是,儒释之紧张关系也时日已久,为何《中庸》只是到了宋代才蔚然勃兴呢?其次,对于朝廷或大臣重视《中庸》,余先生已有分析,如,“《中庸》通过好禅的试官而进入贡举制度毋宁是很自然的”,(1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2页。若不分析朝廷或大臣与佛教的关系,自然不能有效回应余说。遗憾的是,杨文中对此并未阐述。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宋儒从“内圣”上解释《中庸》是否主要受智圆的影响?第二,邢昺解说《中庸》是否只讲“外王”?第三,陈充的立场是会通三教吗?
二、田锡引《中庸》入科考
宋儒推崇《中庸》是否源于智圆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智圆是什么时候开始重视《中庸》的。虽然智圆(976—1022)重视《中庸》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大概时间可寻。智圆阐释《中庸》的文章均在《闲居编》。他曾对自己的文章进行过两次大的整理。第一次是1014年,他说:“予自滥预讲科,于先圣之道虽不能穷微睹奥,而志图训诱。于是备览史籍,博寻经疏……始景德三年(1006)丙午岁,至今大中祥符七年(1014)甲寅岁,于讲授抱疾之外,辄述科记章钞,凡得三十部,七十一卷。”(13)智圆:《目录序》,《全宋文》第1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第二次是1021年,吴遵路《闲居编序》说:“始自景德丙午,迄于天禧辛酉(1021),集其所著,得六十卷,题曰《闲居编》。”(14)《全宋文》第16册,第183页。现在看到的《闲居编》收录文章的截止时间为1022年,即智圆去世之年。《闲居编》不少文章是诠释《中庸》的,虽然有些文章的具体写作年代不可考,但肯定皆在此时间范围内。这就是说智圆阐释《中庸》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1006年。那么,在此之前,就没有儒士推崇过《中庸》吗?回答是否定的。
田锡(940—1003),宋初名臣,以直言谏上而闻名,大有魏征气概,范仲淹赞为“天下之正人”。(15)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三“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贵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范仲淹考进士的时间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其应试文为《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可知考题必与《中庸》有关。主持该年考试的试官是赵安仁、李维、盛度、刘筠。余英时考证1015、1019、1024、1027年14名试官后指出:“《中庸》通过好禅的试官而进入贡举制度毋宁是很自然的。”(1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2页。从这14名试官好佛的比例(占一半)来看,余先生这一结论可谓有理有据。但事实上,《中庸》进入科举考试,是由田锡开其端,且远远早于范仲淹考进士的时间。至少在咸平六年(1003)前,在田锡出的试题《试进士策》中就已提到“中庸”了:“问:‘富国备边,实资农战,化民导俗,本贵儒玄。尚玄以清净为宗,尊儒以礼乐为本。《书》称偃武,《春秋》谓不可弭兵;《礼》重中庸,刑法欲畏如观火。圣人垂训,取舍何从?国士怀才,是非必当,愿闻至理,上副旁求。’”(17)田锡:《试进士策第一道》,《全宋文》第5册,第252页。虽然“中庸”与《中庸》有别,且“三礼”皆讲“中”,但在“三礼”中,“中庸”一词只出现在《礼记·中庸》中,且该书论述最集中、系统,所以,即便没有出现“礼中庸”一词,也完全可以说,田锡其实说的“《礼》重中庸”就是“礼中庸”。退一步说,即便田锡只是泛言“中庸”,也会使人直接想到《中庸》一书,因为在儒家经典中,只有此书讲“中庸”最集中与系统。从内容上看,田锡在此讲了两层含义:一是治国、治民之方有儒老之别,二是若以儒治国、治民,亦有《书》之偃武与《春秋》之重兵、中庸之德与刑法之畏的区别。举子们完全可以选择某角度或某方面展开论述。虽然田锡在此肯定了“玄”亦有益于治国、治民,但并不表明他是好佛老的。据史载,他曾反对太宗耗资修寺庙:“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爨血。”(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太宗端拱二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6页。且崇儒立场鲜明:“窃尝以儒术为己任,以古道为事业。”(19)田锡:《贻杜舍人书》,《全宋文》第5册,第220页。
田锡之所以纳《中庸》入科考,除受朝廷的影响外(下详),与他对《中庸》的尊崇密切相关。他曾明确表示:“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20)田锡:《贻宋小著书》,《全宋文》第5册,第218页。只是田锡没有分析《中庸》的专著,仅有提及《中庸》的文章。田锡对《中庸》的阐发重在外王方面。如他在《试进士策》中说:“富国备边,实资农战,化民导俗,本贵儒玄。尚玄以清净为宗,尊儒以礼乐为本……《礼》重中庸,刑法欲畏如观火。”在此,他强调的是中庸与刑法作为治国治民的手段是不同的。又如他在《论时政奏》中说:“抑臣闻君子恐惧于所未闻,戒谨于所未至,故未萌者所以易虑,未兆者所以易谋,谋于外则先靖于中,制于远则当思于近。”(21)《全宋文》第5册,第 252、117页。在此,“恐惧于所未闻,戒谨于所未至”就源自《中庸》,田锡以此强调治国治民需防患于未然。
总之,从内容上看,虽然田锡还未阐发《中庸》的“内圣”思想,但从他把《中庸》纳入科考的时间及其卒年来看,显然早于智圆重视《中庸》。而且,他把《中庸》纳入科考,必然加速《中庸》的传播,扩大《中庸》的影响,对北宋《中庸》学的兴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邢昺先佛道释《中庸》
邢昺(932—1010)也较早推崇《中庸》。先看邢昺在解说《中庸》之前,是否亲近佛道?史载,邢昺对皇侃《论语注疏》以佛道解儒大为不满,故作《论语注疏》时大量删除皇疏。下举两例。皇侃释《子罕》“毋意”为:“此谓圣人心也,凡人有滞,故动静委曲,自任用其意,圣人无心,泛若不系舟溪,寂同道,故无意也。”(22)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7页。这解释显然颇具玄学色彩。试看王弼注释《老子》第38章之言:“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赡,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23)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页。稍加对照,就能发现皇注采纳了王说。而邢昺对“毋意”的解释是:“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师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为度,故不任意。”(24)邢昺:《论语注疏》卷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显然没有了“玄学”之意。又如皇侃对“德不孤,必有邻”的解释:“邻,报也。言德行不孤矣,必为人所报也。故殷仲堪曰:‘推诚相与,则殊类可亲。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应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邻也。’”(25)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二,第52页。释“邻”为“报”,为皇侃所独有,与《说文·邑部》“五家为邻”、《释名·释州国》“五家为伍,以五为名也,又谓之邻。邻,连也,相接连也”完全不合,显然是受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的影响。而邢昺摈弃该说,注曰:“此章勉人修德也。有德则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与之为邻也。”(26)邢昺:《论语注疏》卷四,第53页。这种解释体现了儒家重德的思想,已无佛教的色彩。
邢昺对《中庸》的推崇,史载仅有一次,即景德四年(1007),“昺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真宗景德四年”,第1483页。但该史料简略,未记载邢昺向真宗所陈“大义”之具体内容,使后人有了发挥的空间。余英时就认为邢昺只是向真宗陈述了“外王”之道。事实恐怕未必。首先,从《中庸》原意来看。《中庸》道:“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段是接着上文“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来讲的,意思很明确,即由“修身”到“治人”再到“治天下国家”,“修身”是基础。所以从上下文来看,“九经”只不过是上文“三事”的具体化,正如孔颖达所说:“前文夫子答哀公为政须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为哀公广说修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种常行之事。”(28)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16页。可见《中庸》的原意是讲修身为治国之基,由内圣到外王。
其次,从邢昺本身的思想来看。邢昺是著名的经学家,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儒家经典既有丰富的“内圣”思想,亦有丰富的“外王”思想,那他是不是只讲“外王”呢?《宋史邢昺传》明确记载,他常向诸王讲“父子君臣”之道,“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29)《宋史邢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800页。表面上看,“父子之道”只是伦理纲常,侧重“外王”,然而若不从“修身”讲起,父子之道能落实吗?所以《大学》《中庸》皆认为“修身”是“亲亲”或“齐家”的基础与前提,而《中庸》的“慎独”“至诚”和《大学》的“正心诚意”则为“修身”之方。由此可推,他向真宗讲“天下有九经”时不可能只讲“外王”。
最后,从后人的记载及对此事的解释来看。范祖禹《帝学》对该事有明确记载:“帝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篇》图,昺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耸听,帝甚嘉纳之。”(30)范祖禹:《帝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6页。据此,邢昺之“大义”一目了然。“修身”即为“内圣”之学,“尊贤”可为“外王”之术。显然,邢昺之意是“内外”兼备。南宋的王应麟对此也有解释:“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然必亲师友,然后修身之道进,故尊贤次之。道之所进,莫先其家,故亲亲次之。由家以及朝廷,由朝廷以及其国,由其国以及天下,此九经之序也。”(31)王应麟:《玉海》卷三十九“景德崇和殿《尚书》《礼记》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38页。内圣外王之意亦很显明。王应麟的解释或许受程朱的影响,但与范祖禹的记载非常接近,应符合邢昺和《中庸》“九经”之本意。
综上可见,邢昺对《中庸》的发挥“内圣外王”兼备,而不是只讲“外王”。
还有一事须厘清。虽然邢昺给真宗讲《中庸》的时间为1007年,晚于智圆推崇《中庸》的时间(1006),但邢昺早在雍熙三年(986)就已对《礼记》进行分门别类,作《分门礼选》20卷献给太宗。(32)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二皇子诸王杂录》,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页。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他给太宗讲过《中庸》,但从逻辑上说他必然熟悉《中庸》的内容,就是说他对《中庸》的重视及对其中“内圣外王”的发挥,不可能是受智圆的影响,因为在雍熙四年时智圆才11岁。同时,邢昺的“分门”之举为太宗及朝廷注意《中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四年之后,即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就下诏“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赐中书、密院、两制、三馆、御史中丞、尚书丞郎、给谏等人各一轴”。(33)文彦博:《奏〈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全宋文》30册,第287页。请注意,这则材料显示《儒行》《中庸》已经脱离《礼记》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而宋太宗诏印的目的,亦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谕令依此修身为治”,(34)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三十“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第749-750页。显然,太宗与邢昺一样注意到了《中庸》“内圣外王”的思想。不同的是,朝廷的表彰较之士人的推崇影响力更大。田锡把《中庸》纳入科考正与此有关。
四、陈充随朝廷崇儒而释《中庸》
陈充(944—1013)也是较早重视《中庸》的儒士,但他的情况与田锡、邢昺大有不同。史载,他可能与“九僧”有较密切的交往,(35)祝尚书:《论“宋初九僧”及其诗》,《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九僧诗集》(36)晁公武说:“《九僧诗集》一卷。右皇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也。陈充为序。凡一百十篇。”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70页。就是他编的。尽管关于他的史料有限,难以具体了解其思想轨迹,但他推崇《中庸》最晚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他作《子思赞》称:“尼山道德,群贤是宗。伋承家学,无愧祖风。忧道失传,乃作《中庸》。力扶坠绪,述圣有功。”(37)陈充:《子思赞》,《全宋文》第6册,第4页。虽然尚不知他相较智圆推崇《中庸》的早晚,但可以断定,他推崇《中庸》不是出于释氏,而是源自朝廷上下崇儒风尚的影响。因为,在他作《子思赞》的前一年,真宗曾给孔子及其门人作《赞》,在朝廷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祭祀孔子、广修孔庙的热潮。《子思赞》就是在此背景下撰写的。尽管该赞内容简略,但肯定了子思作《中庸》的述圣之功,指出了子思作《中庸》的原因在于“忧道失传”。虽然他所说的“道”之具体含义已无从获知,但这一解释把子思自觉传道之意揭示出来了,这表明陈充对《中庸》有较深入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肯定《中庸》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由此亦可知,陈充推崇《中庸》绝不是站在会通三教的立场。
五、 赵湘以《中庸》兴儒排异
赵湘(959—993)史载其以文闻于世,“名籍场屋中”。(38)赵湘:《南阳集》之“原序”“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305、347页。今暂不论其文风,只述其思想。他虽与重黄老道家的罗处约(958—990)及诸多僧人有密切的交往,但其儒家立场亦很明确:“余世为儒,少学,七岁横经……余亲友或痛予处贱位,未能耿耿发为儒光者,故为余悚憟不敢当是说。”(39)赵湘:《南阳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 345页。在此,赵湘既表明了自己的儒家立场,又道出了自己未能把儒学发扬光大“壮志未酬”的感慨。以下,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推崇《中庸》的。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原教》中,选录如下:
道之为物也,无常名,圣人之所存者七。《中庸》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其具有五曰:仁、义、礼、智、信,合而言之是为七。七者,皆道之所由生也……教所以存天下也。栢栗、有巢之世,其民饮茹而朴,道易而教隆,不亲亲,不子子,巢之穴之,然则七者具于其中矣。圣人者,能因其化,不烦于教也,故七者不复萌。尧舜已降,氓之性不由道矣,然而圣人者不以其不由道而弃之。是故宫室之,庖燧之,衣服之,寒燠之,暑凉之,而后教之以七者。禁不齐则礼,礼不齐则刑。示之以君臣、父子、夫妇之事,节之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之道。是七者之教,圣人无他心,但欲其复道而已矣……情与性纷纷焉,交乎其中,乱乎其外……栢栗教之于无知之前,尧舜教之于有知之后。无知者,性情也。教有知于无知,不亦难乎。或曰:“七者之过,氓知是七者,若之何能无知乎?”对曰:“亡是七者,禽兽也。古之无知者,心湛然坐忘遗照,性情之不挠,喜怒哀乐之未形,暴乱奸邪之不作,果混乎禽兽而不疑。然而七者作,岂害于无知乎?道存而已矣。性情者,生乎人之心者也;七者,治人之性情也。七者果存道焉。《易》曰:‘圣人以此而洗心’,七者作于外而存乎内,喜怒哀乐之不生,冲冲然、寂寂然,以乐天下之不争者,是复之于无知也。故曰:‘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本乎心,非在乎无知有知之相害也。’舜之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是教天下,无他说焉。”……噫!杨墨之小,申韩之异者,皆所以惑人之心。心惑则情性乱,情性乱则道异,道异则教舛,君臣、父子之不分,暴乱、奸邪之不息,其欲教有知而至于无知,呜呼,其不可知其几矣!(40)赵湘:《南阳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334-335 页。
有巢之世,民众素朴,不教而化。可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到了尧舜之世,已民心不古,但圣人不嫌弃,对民众进行教育。为什么栢栗、有巢之民素朴,而尧舜之民“不由道”呢?问题在于能否处理好心、性、情三者之间的关系。栢栗、有巢之民,因“心湛然坐忘遗照”,所以“性情之不挠,喜怒哀乐之未形,暴乱奸邪之不作”,结果便是民由其道。然而到了尧舜之世,民众未能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情与性纷纷焉,交乎其中,乱乎其外”,所以民心不古。那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即治性情,实亦治心,因为“性情者,生乎人之心者也”。如何治呢?赵湘认为应以“七者”治之。何谓“七者”?“五常”(仁、义、礼、智、信)加《中庸》之“率性”“修道”,合而为七。以七者治之的结果便是“喜怒哀乐之不生,冲冲然、寂寂然,以乐天下之不争者,是复之于无知也”。为什么这七者能治性情而教化民众,使其复道呢?原因在于,这七者出自最高的本体“道”,故能担此重任。既然“七者”能导民复道,那么也能使杨墨、申韩之异端不兴。因为心不乱,则性情不乱,性情不乱,故异道息。由此可见,作者把《中庸》中的某些重要资源作为复兴儒学、排斥异端的重要依据。总之,异端之不兴的关键在于治心,正所谓“古之人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将正其身,必治其心,将治其心,必固其道”。(41)赵湘:《南阳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336页。
六、结 论
最后还需指出,宋初对“内圣”“心性之学”有所重视的儒士并非只有邢昺、赵湘等。这是一股思潮,同样崇儒者大有人在。如与田锡有密切交往的王禹偁、张咏。王禹偁(954—1001)反对佛教,(42)王禹偁对真宗说:“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以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也。”《宋史王禹偁传》,第9797页。亦推崇“心性之学”,他说:“得治心之方,体和而自适。”又说:“能正其心,然后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后能齐其家;齐其家,然后能治其国。”(43)王禹偁:《野兴亭记》,《全宋文》第8册,第74、38页。张咏(946—1015)更明确指出治国之本在于治身,治身之本在于治心。他在《詹何对楚王疏》中写道:“楚王问詹何治国之法,何对曰:‘治身重。’询之故,又曰:‘未有身治而国乱者也。’……求其治身,必先治心;治心之本,在乎中正。”(44)张咏:《乖崖集》卷六,《全宋文》第6册,第125页。这与后来崇儒者的思想很相似。另,田锡虽未阐发《中庸》的内圣思想,但他对心性之学也有强调,如太平兴国七年(982),他在《论边事奏》中就以“修心”规劝太宗:“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45)田锡:《论边事奏》,《全宋文》第5册,第113页。由此亦可见,在宋初,推崇儒家“心性之学”者甚众。
综上所述,在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赵湘对《中庸》已有所重视,而且邢昺对《中庸》的心性之学还有所强调。邢昺推崇《中庸》的目的是告诫君主和士人注意修身,由“内圣”通向“外王”,但还没有以此作为反对佛教的依据,而且在如何“正心”“修身”的问题上,也没有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特别是与后来的儒士(如理学家)相比,邢昺、田锡等对《中庸》的解说有很大的不足,但他们通过自己对《中庸》的推崇,无疑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
或许有学者会对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即尽管在时间上宋初儒士发挥“心性”“内圣”思想比智圆早,但仍不能否认陈寅恪等先生的说法。其原因于:(1)“内圣”“心性”是释氏的擅长。如北朝的道安便有“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46)道安:《二教论》,《大正藏》第52册,第136页。之说;智圆也云:“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47)智圆:《中庸子传上》,《全宋文》第15册,第305页。(2)李翱发挥《中庸》心性之说,恰是佛教刺激下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宋人讲“内圣”“心性”岂能不是佛教刺激的结果!表面上看,此质疑似有理,但经不起推敲。
首先,心性或内圣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先秦儒家经典中。只不过,相对而言,《中庸》比较集中表达了此思想。如《中庸》一开篇就讲“性”“慎独”“中和”,而后半部分又集中讲“诚明”,故有“儒书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48)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五“非韩上”,纪雪娟点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5页。“《中庸》者,言性之书也”(49)黄宗羲:《宋元学案华阳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9页。之说。《中庸》“内圣”“心性”思想,绝非为佛教而设,实为经世济民的前提与基础。无论从“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之论,还是从“天下有九经”之语,皆可知晓。这便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心性思想资源。而且,对于宋初的儒士和朝廷来说,最大的担心并非是佛教的威胁,而是政权的不稳和更替。短短50年间,战乱频发、政权繁更、百姓颠沛流离,可谓不堪回首的悲苦。心有余悸的他们深信,导致悲剧的关键在于儒家价值观的丧失,故欧阳修有“五代之乱极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50)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第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9页。之语。所以,为保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最佳的办法便是挖掘儒家的“内圣外王”资源,以使朝廷、大臣和普通士人尽职尽责。了然于此,我们就能理解淳化三年(智圆仅16岁)宋太宗表彰《中庸》之良苦用心。两年后,他再次借用《中庸》思想责罚大臣,(51)宋太宗:《黜翰林学士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禹偁制》,《全宋文》第4册,第371页。目的亦为要大臣高度重视“修齐治平”修养,进而对朝廷尽心尽力。同理,田锡、邢昺等大臣推崇《中庸》亦是希望皇帝、大臣和普通士人皆重视“修身”。由此,我们也可明了邢昺“反复陈之”之用心及“坐者耸听”之感触。
其次,释教内外的挑战是佛教徒智圆重视儒家经典《中庸》的原因。从外部来说,宋初柳开、种放等儒士对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种放就有“(佛教)蛊蠹家国……能嗣禹者,韩愈也”之语,智圆曾作《驳嗣禹说》进行反驳。(52)智圆:《驳嗣禹说》,《全宋文》第15册,第265页。从内部来说,宋初释教内便有主张学儒以批佛者:“吾门中有为文者,而反斥本教以尊儒术,乃曰:‘师韩愈之为人也,师韩愈之为文也,则于佛不得不斥,于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53)智圆:《师韩议》,《全宋文》第15册,第267页。智圆需以“中庸”为切入点来调和两者的关系。(54)张培高:《论智圆对〈中庸〉的诠释》(《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智圆的性情思想》(《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有详细论述。如他说:“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55)智圆:《中庸子传上》,《全宋文》第15册,第305页。这里的“修身”其实是前文的“饰身”,并非是从“内圣”上讲,而是就“外王”而论。换言之,尽管《中庸》有如此丰富的心性思想,但智圆只注意了其中的方法论,相应地,对释教的“治心”却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有人或许会说,智圆如此之论会反面刺激儒士,进而促使对其的重视。如此,陈、余等之论仍可成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儒家众多经典中,为何智圆会对《中庸》情有独钟,这难道是他的独创吗?其实,若从思想渊源上说,唐代的柳宗元早已用此法,故章士钊有“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目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56)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58页。之语。而且智圆对柳氏甚为佩服,把他作为儒家道统中的人物:“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韩退之、柳子厚而已。”(57)智圆:《叙传神》,《全宋文》第15册,第264页。但这相对于朝廷、儒士推崇《中庸》对智圆的影响弱得多,毕竟朝廷、儒士是现实、直接的影响,而智圆与柳氏相距了150多年。另外,略晚于智圆的释僧契嵩推崇《中庸》的原因也提供了旁证。契嵩说:“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说,吾《中庸》存焉。’”(58)契嵩:《镡津文集》卷九《上富相公书》,第203页。正因如此,他重视并诠释《中庸》,欲与儒士争辩。与智圆不同的是,他除看到《中庸》的方法论意义外,还注意到其中的心性思想。
最后,田锡、邢昺等儒士及朝廷推崇《中庸》的影响力远大于智圆。田锡不仅因正直受太宗、真宗的重用,而且在当时是可与赵普并提,“岂惟齐贤,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之知也”,(59)陈明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契丹和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3册,第52页。对塑造良好士风作用巨大的人物:“昔真宗皇帝临驭群下,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六“哲宗·元祐元年”,第8781页。所以范仲淹对之有“天下之正人”的高度评价。
邢昺的影响力就更大了。他不仅是著名的经学家,是《论语正义》《尔雅正义》《孝经正义》的领撰人,官至礼部、工部尚书,而且是东宫侍讲,深得皇帝尊崇。他对《中庸》的推崇,直接影响皇帝,促成了朝廷对《中庸》的重视。而智圆虽在当时亦有不小的名声,但对士人的影响远不及田锡与邢昺。从现存《闲居编》可知,与智圆交往的多为僧人,与之交往的士人不仅少,而且除有“梅妻鹤子”之称的林逋较有名气外,几乎都是无名之辈,如在《宋史》中只有区区几条的记载的吴遵路、孙合,又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关键文献都未曾记载的骆偃等。依此,即便只与赵湘相比,其影响力也大不如。因为智圆虽与赵湘一样以“文”而知名,但赵死后“名籍场屋中”,智圆则无类似评价,影响力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加之,《闲居编》在智圆圆寂约40年(1060年)后才刊发,(61)祝尚书:《论智圆的文学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也耽搁了在士人中的传播。而1060年之前,朝廷、儒士推崇《中庸》已蔚然成风:朝廷在1027—1059年间多次赐《中庸》于进士;(62)王应麟:《玉海》卷三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635-636页。胡瑗(993—1059)已刊发释《中庸》之专著。总之,相对于田锡、邢昺、赵湘等宋初儒士,智圆对扩大《中庸》影响力、提升《中庸》地位的作用小得多。不仅如此,智圆之所以热衷于《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不过,《中庸》地位在宋代的最终确立,并非仅限上述力量的推动,更得益于范仲淹、胡瑗、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及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朱为主要代表的儒士的重视与诠释(另文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