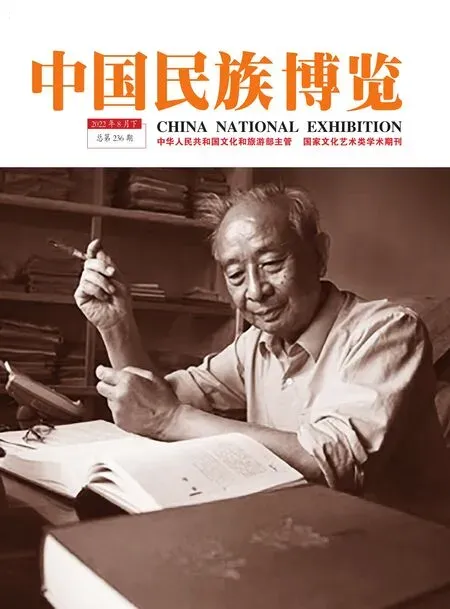寻古问今
——《尼克尔男孩》的政治历史意蕴探析
2022-12-05乔昊阳
乔昊阳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作品简介
《尼克尔男孩》(The Nickel Boys)是美国著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1969—)于2019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极高的评价,并一举斩获2020年度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小说以一所美国历史上存在真实原型的工读学校——尼克尔学校——作为美国社会的缩影,通过两名黑人少年——埃尔伍德和特纳——在学校内的命运,将矛头指向了伪善而充满隐性暴力的吉姆·克劳法:一个有着自由世界灯塔美名的国家却如同一座巨大的炼狱,充斥着血腥暴力和歧视不公。该小说延续了怀特黑德对美国黑人生存问题的政治关切,运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和现实主义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美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现实。
整部小说萦绕着一种浓郁的历史氛围,历史与想象、真实与虚幻交汇渗透。怀特黑德将自蓄奴时期以来跨越近二百年的黑人苦难巧妙编织进小说的历史叙事中,创造性重构历史,实现了时间、空间的穿越交织,使文本的历史本质得以深刻阐发。另外,作者还通过种种内涵丰富的意象和情节,对美国当今的社会生态、政治秩序等领域中积重难返的种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讽刺与批判,从而赋予了文学文本以丰富的政治目的,也赋予了其解构主流政治话语的权力。
二、探寻历史:非裔苦难史的再现与重构
在小说《尼克尔男孩》中,作者怀特黑德巧妙地将百余年的美国非裔历史浓缩、编织进其有限篇幅的文学叙事中,实现了时空的交错、融合,营造了浩瀚广阔的历史空间,使历史之本质在其文学文本中得以深刻阐发。从中,读者不难发掘出自蓄奴时期至2010年来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系列民权运动、跨越近二百年的美国黑人血泪历史。
小说的前言便将读者带入到浓厚而真实的历史氛围中。怀特黑德以一则真实的新闻事件,揭露了美国种族隔离期间一所劳教学校的罪恶行径和一群美国非裔少年的悲惨往事。在南福罗里达大学考古系学生对尼克尔学校(The Nickel Academy)公共墓地的一次考古发掘活动中,有人发现了在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下掩埋的种种异常——三分之一的墓碑空白无名,学校档案残缺不全,出土遗骸上布有弹孔痕迹……事态逐渐发酵,直到塔拉哈西当地媒体派出一名记者,随后国家级媒体也曝光了此事,这所劳教学校的罪恶历史真相才逐渐大白于天下,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罪恶终于缓缓拉开帷幕。
首先,小说作者怀特黑德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向读者生动再现了美国种族隔离时期的真实历史图景。小说正文部分聚焦美国吉姆·克劳时期两名非裔“尼克尔男孩”艾尔伍德·柯蒂斯(Elwood Curtis)和杰克·特纳(Jack Turner)的成长经历。其中,前者短暂而悲剧的一生正是万千美国黑人悲惨遭遇的缩影。20世纪50年代,艾尔伍德生长在美国南方腹地——弗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的一个黑人社区,他自小被父母抛弃,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彼时的南方,反隔离运动不时兴起,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将矛头直指学校隔离,最终致使“隔离但平等”制度被判定违宪;然而,由于反隔离法令尚未强制执行,种族隔离现象仍肆虐横行,导致平权屡屡受挫,黑人叫苦不迭:游乐场只对白人小孩开放,酒店雇佣黑人员工却仅为白人顾客服务,白人学校绝不招收黑人学生,人们凭借肤色乘坐不同档次的交通工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艾尔伍德无时无刻不饱受着“隔离但平等”制度的毒害。当艾尔伍德升入林肯高级中学(当地一所黑人学校)时,由于缺少教科书,黑人学生不得不使用白人学校淘汰的二手教材。不仅如此,他们收到的二手课本上还时常被白人学生写满“去死,黑鬼!臭死了!吃屎!”(2019:27)等恶毒的咒骂之词。即使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艾尔伍德仍坚守自我,发愤图强,后因学业出色,收获了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然而,就当看似一切向好之时,剧情急转直下,艾尔伍德彻底堕入了恐怖黑暗的牢笼。在前往大学的路上,因误搭一辆盗窃来的赃车,艾尔伍德被判入尼克尔学校劳教,并最终丧命于此。更有甚者,艾尔伍德家族三代均是美国社会种族对立的无辜牺牲品,然而此类悲剧对当时的黑人而言却是稀松平常。艾尔伍德的曾外祖父死于监禁,入狱原因却是“一名白人妇女控告他在人行道上未向其让路”(2019:59)。后来悲剧重演,其外祖父在饭店制止一场纷争时,不幸被椅子砸中头部身亡,而他仅想从三名白人男子的手下挽救一名洗碗工。最终,其父——一名二战退伍士兵,从太平洋战场生还归来,却成为被众人欺凌的邪恶对象,只因他是一名身着军装的黑人。尽管他热爱军队,还因控诉军中种族不平等现象而获得过表彰,但这未能改变这名黑人的社会处境。直到他在拜访朋友的途中停下加油时,被人无故打倒,才意识到白人男性“对穿制服的黑人随意动用私刑”[1]20世纪60年代的世道于黑人之艰难。随后,在遭遇了更多挫折如借贷无门后,他与妻子决定离开家乡,去加利福尼亚州碰碰运气。于是,艾尔伍德的父母便丢下年仅六岁的小艾尔伍德,离开了他们仅有的亲人,从此杳无音讯,“甚至未寄过一张明信片”(2019:102)。
其次,怀特黑德通过戏仿奴隶制种植园,拓宽了小说的历史视野,创造性重构了黑人种族历史,揭露了美国各领域种族主义现象之劣根性。无论是从其运作模式还是从其压迫黑人的血腥事实来看,尼克尔学校与其说是一所少年教养院,不如说是一个现代版种植园。例如,尼克尔学校的学生被强制要求在校内以及校办工厂充当免费劳力,以此累积 “绩点”,争取尽早获释(绩点水平达到最高等级“Ace”才会“毕业”)。这些男孩“负责一切事务,为校内所有建筑烧制砖头,浇筑混凝土,修剪草坪等”(2019:43)。仅尼克尔的印刷厂便“承担着佛罗里达州政府所有的出版业务,从税收法规到建筑规范再到停车罚单”(2019:43)。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厂完全依靠这些少年劳工的无偿体力劳动来运作,而牟取的钱财则最终流入了学校管理者的口袋。除此之外,尼克尔男孩还必须定期在政府官员或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家里工作,来为学校牟利,但这些钱也以 “维持学校运转”的名义落入管理者手中。然而,尽管男孩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待遇却很差。在学校,男孩吃的是变质的燕麦片,里面“倒了一堆肉桂以掩盖糟糕的味道”(2019:48),喝的是“水一样的葡萄汁”(2019:66),且不得不睡在“挤满60个男孩的房间里”,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可见一斑。另外,如果他们违反了校规,便会被拉到学校的体罚场所“白宫”(the White House)接受鞭打,甚至被秘密处决,而他们的尸体则会被随意掩埋在学校的公共坟场“靴山”(Boot Hill)。由此可见,作者怀特黑德用其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笔法,展现了一幅“种族主义炼狱”之恐怖景象,其中,非人的囚禁虐待,高强度的强制劳动,恶劣的食宿条件——俨然构成了一座“现代版的奴隶制种植园”。据记载,在18—19世纪的南方种植园,黑人奴隶整日被囚禁在园中,每日劳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种植烟草、棉花和甘蔗等作物,为园主积累了巨额财富,而自身却难以果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19世纪弗吉尼亚州黑奴的食宿费用仅为每日6美分;然而,彼时阿拉巴马州的囚犯每日的伙食费尚有25~40美分(唐陶华 1980:128)。此外,黑人奴隶的居住空间也十分逼仄,平均每6个奴隶就要挤在一个16英尺宽、18八英尺长的房间里(Aptheker 1945:126)。更糟糕的是,他们可以被主人任意出售、强奸和鞭打,逃奴若被发现或抓捕,则会被鞭打、烙印或阉割(Kolchin,1993:10)。可见,无论是食宿条件、劳动强度,抑或刑罚方式,尼克尔学校都与百年前的奴隶制种植园高度契合。怀特黑德在此通过“戏仿”百余年前的蓄奴期种植园,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现代版的奴隶制式少年监狱,将种族历史上两个至暗时刻并置于文本空间中,实现了历史于时空的交错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创造性重构了吉姆·克劳时期的非裔苦难史,同时也暴露了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之根深蒂固、积重难返。
反观当下,特朗普主义余孽未消,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制度性种族主义难以根除,“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种族平权运动掀起浪潮,执法、司法等领域针对非裔群体的不公行径时有发生……在其中,我们不难窥见蓄奴、隔离时期的影子。可见,作者借古喻今,借隔离时期历史投射社会现实,侧面印证了美国社会政治景观的倒退。
三、拷问现实:美国社会生态的讽刺与批判
在谈及其创作初衷时,作者怀特黑德毫不掩饰其对当前美国非裔群体生存现状的担忧和对种族主义盛行之下美国社会风气的批判,他曾坦言创作此部小说正是“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对他们漠不关心”,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已形成风气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以及白人执法者对黑人的态度,可以说1850年发生的事到现在为止还在发生着”。“如果你选择写作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我们作恶的能力,你可以写1850年、1963年或2020年,不幸的是,它在这些年代都是适用的。它正在进行中,而且还会持续很多年。”因此,虽然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但是怀特黑德仍在多部小说中,表露出其对非裔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怀以及对美国制度化种族主义的批判。本部小说亦不例外。
在本部小说中,怀特黑德广泛运用了隐喻的手法,通过寓意深刻的情节与意象,表现了美国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下黑人的艰难处境,批判了种族主义肆虐下美国虚伪的历史、病态的社会以及畸形的体制。
首先,作为小说主人公活动的主要场景——尼克尔学校——正是美国政治生态的缩影。尼克尔学校的一切制度都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等级制度之上:劳动、惩罚、待遇都因肤色而不同,如学校会偷偷变卖黑人学生的餐食,并用质量极差的食物替换之,施加给白人和黑人学生的工作量、体罚程度亦相差甚远;学生根据表现被划分为四个等级——“初学者”(Grub)、“探索者”(Explorer)、“先驱者”(Pioneer)和“顶尖者”(Ace),学生根据其表现挣得“积分”(merit)、提升等级,而只有达到最高等级“顶尖者”(Ace),方可正常“毕业”。于是,面对学校施加的残忍虐待和繁重劳动,学生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只求尽早获释。
其次,“空白百科全书”(empty encyclopedia)的隐喻在小说中亦多次出现。这部百科全书是在艾尔伍德十二岁那年,在酒店后厨的“洗碗比赛”中获胜而赢得的。然而,这来之不易的“战利品”除开篇几页外,全部空白无字,甚至连所谓的“比赛”也只是一场恶意的戏耍。彼时的小艾尔伍德曾是酒店后厨的得力助手,洗碗的技术无人能敌。然而,勤恳、卖力的工作,换来的却是书中的片片空白,也正是主流记忆中黑人生存痕迹的空白。从古至今,黑人总是“承受着来自社会各处的种种压迫力量,大如吉姆·克劳法,小如身边人”(2019:25),他们不想给予黑人一丝喘息之机。这些压迫的呈现形式可归为两类:“百科全书是空白的。有的人戏弄你,笑着给你一片虚无”(2019:25),此处“虚无”(或“空白”,emptiness)一语双关,既指代那套空白无字的百科全书,也喻指社会对黑人群体的排挤和压迫,这是比言语乃至肢体冲突更深入骨髓的冷暴力,然而白人往往一笑了之,带来的却是黑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乃至历史、话语的抹杀。而另一群人则“直接夺走你的尊严”(2019:25),比如,美国社会针对黑人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又如,小说中尼克尔学校对黑人少年儿童的虐待、性侵、杀戮等残忍行径。“墓地”(cemetery)的隐喻则更为明显,贯穿全文,是小说中重要的隐喻之一。墓地指尼克尔学校的公共墓地,但与其称其为墓地,不如说是一片乱葬岗,能很自然地引发读者关于“死亡”“埋葬”“腐烂”的联想。在小说的前言中,当那片“神秘墓地”中埋藏的尸骸被首次发现时,便令地产商和律师颇为头疼。因为对人们来说,“这片墓地本应被清除、夷平,干干净净地从历史中抹去”(2019:8),一如美国官方叙事对黑人历史的抹除。坟前树立的十字架上“仅有三分之二刻有姓名,其余则都是空白”(2019:8),而唯一能证实他们身份的途径——学校的记录,也是“混乱随意且支离破碎的”(2019:8)。此处十字架和学校记录无一不影射了美国官方历史叙事中黑人历史被破坏的状况。正如率先发现尸体的南弗罗里达大学的卡迈恩教授所言:“一英亩的土地下能埋藏很多,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黑人男孩的尸体、遗物,亦是尼克尔学校数十年来所犯下的罪行,更是非裔美国人那被官方话语所粉饰、掩藏甚至破坏、清除的长达数百年被奴役、被迫害、被歧视的苦难历史。”
再次,“白宫”(the White House)这一政治隐喻愈加大胆而显著。“白宫”是尼克尔学校中体罚场所的官方名称。不同于白人学生对该场所“冰淇淋工厂”的戏称,黑人学生则直呼其名,只因这一名称十分贴切且无须加以粉饰,又因这里的“白宫”同样地“制定规矩而且每个人都得遵守”。接受体罚时,学生被管教从后门带入[人称“挨打入口”(beating entrance)],里面“臭气熏天,尿液和其他体液已然渗进了砖块里”(2019:57),走廊里仅有一个咝咝作响的昏暗灯泡用作照明。当艾尔伍德第一次踏入此地时,他便明白了为何这所学校并没有围墙、栅栏或铁丝网,然而却仅有很少的学生逃跑——“这里就是关住他们的围墙”(2019:57)。当刑罚开始时,风扇便噪声大作,将男孩的惨叫声淹没其中。刑罚手段主要是鞭打,刑具是一条被管教称为“黑美人”(Black Beauty)的三英尺长的黑色皮鞭,男孩在受刑过程中失禁、晕厥乃是家常便饭。压抑恐怖的氛围、阴森幽闭的环境、残暴血腥的刑罚,怀特黑德近乎哥特式的描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然而,这座血腥恐怖的刑房却被冠以美国的国家象征和中心之一——美国总统府邸“白宫”之名:怀特黑德对美国制度化种族主义的讽刺、批判不言而喻。
最后,小说中杰克·特纳的更名换姓所造成的个人身份“双重性”以及错位与割裂可谓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困境的恰如其分的隐喻。作为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特殊现象,黑人文化身份认同困惑(black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指生活在以盎格鲁—萨克逊人占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迷惘。W.E.B.杜波依斯认为,在美国黑人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种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通过周围充满轻蔑和同情的人群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每个黑人都能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与黑人的二重性(twoness)——每个黑人都有两个灵魂、两种思维、两种难以调和的竞争和在一个黑色躯体内的两种思想的斗争”(Chase 1980:1753)。这种若即若离的“二重性”成为黑人身份认同最大的烦恼和困惑。小说的最后部分,在逃出生天后,一方面为了纪念亡友、为其复仇;另一方面为了掩人耳目、躲避追捕,特纳“盗用”亡友艾尔伍德(Elwood Curtis)的姓名和身份,开始辗转各地、打拼生计,“为他(艾尔伍德)而活”(2019:162)。在此后长达五十年(1964—2014)的时间里,他一直戴着“艾尔伍德·柯蒂斯”的假面生活,始终用好友高尚的价值标准引导、约束自己,最终如愿以偿地“成长为一个他认为艾尔伍德会为之骄傲的人”(2019:162);甚至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复述、修正、演绎艾尔伍德的故事,将自己由内而外地塑造成了“艾尔伍德·柯蒂斯”的完美替身。然而,长时间的身份错位与内在割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特纳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恐慌。特纳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名为“艾尔伍德·柯蒂斯”的亡者面具之下,甚至当他“在日头底下走过百老汇大街时,在漫漫长夜的尽头伏案读书时”(2019:162),艾尔伍德的声音都会时不时在脑海中响起。然而这一切却在几十年后的2014年,开始全面崩塌。2014年作为尼克尔学校暴行的亲历者以及受害者亲友,特纳不顾其曾经的通缉犯身份,毅然重返塔拉哈西、重返尼克尔学校,为官方调查举证。在这里,特纳故地重游,来到尼克尔的校园,但当他翻过围墙、穿过草场、来到那片熟悉的树林时,不禁发现“两个男孩都已消失不见”(both boys were gone)(2019:162)。曾几何时,他利用艾尔伍德的身份重获新生,然而此时此刻,当他真真切切地站在这里时,才恍然发现艾尔伍德这一身份早已和他的肉体一同被埋葬、消亡——他的面具脱落了。失去面具后的特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迷茫,一种不真实感充斥着他的内心,不得不在妻子的一声声“杰克、杰克、杰克”的呼唤中,在相互蜷缩、依偎中捕捉一抹真实的余晖。
四、总结
“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历史可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尼克尔男孩》这部由美国著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撰写、讲述种族隔离时期一所劳教学校中黑人少年悲剧故事的小说,在美国上下掀起平权示威运动,前两个月获奖,无疑会引发人们对曾经的美国历史和当今的美国现实更加深刻的思考。书中,怀特黑德通过其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内涵丰厚的意象和情节,颠覆了美国官方历史宏大叙事,重构了黑人的种族历史记忆,批判了美国各领域积重难返的种族主义思想,赋予其作品以深刻的政治、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