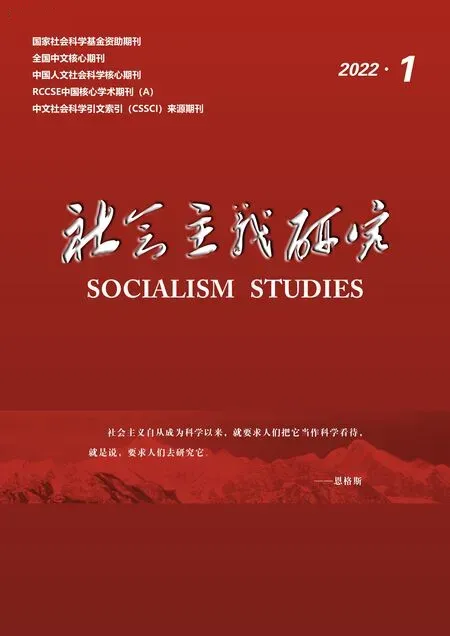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传播与中国应对
2022-12-03李格琴
李格琴
自2016年以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影响力忧心愈重。2017年末美国战略界与学术界炮制“锐实力论”,西方舆论界顺势炒作“中国影响力威胁”。国内学术界对“锐实力论”展开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通过研读智库文本、解读新闻报道,学者们指出,“锐实力论”是西方国家惯有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旨在攻击中国的文化与海外影响力。学者们的研究提升了中国决策层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但较少有成果从战略传播的视角系统解读“锐实力论”的传播意图、传播模式、传播策略与传播影响,而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调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厘清“锐实力论”的传播过程,评估其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实际影响,从而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意图
“锐实力论”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2017年12月以题为《锐实力:崛起中的威权主义影响》研究报告的形式正式提出的,但它绝不仅仅只是美国学术界层面的论调,其背后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2021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大会上指出,美国不和中国搞新冷战,不搞军备竞赛,但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主要在制度、价值观与发展模式方面展开竞争。1"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9, 2021,Speeches and Remark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而“锐实力论”的主要内容,恰好是美国对中国在制度、价值观以及发展模式等软实力方面的集中指责与攻击。
研究报告对“锐实力”概念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中国、俄罗斯等威权主义国家利用民间外交、学术交流、媒体、信息技术以及政治捐款、学术资助等手段影响他国政治与舆论,但这些手段并非依靠吸引、说服,而是进行操纵与强制。这种非“软”也非“硬”的力量,就是“锐实力”,即一种“能够穿透、渗透目标国家政治和信息环境”的能力,就像“刀尖”或“注射器的针头”。1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From‘Soft Power’to‘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NEW FORUM REPORT,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Published on December 5,2017,the Full Report[PDF],p6,(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
报告煞费苦心地运用比喻试图把“锐实力”概念的特征形象描绘出来。然而仔细阅读该基金会长达156页的研究报告发现,报告实证部分在具体述评中国在拉丁美洲、中东欧等地区的“锐实力”活动时,其事实与数据几乎都是中国如何与对方增进民间交流、提供留学资助、进行文化投资以及为该地区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培训等公开且合情合法的软实力活动。报告把中国增强软实力的正常活动界定为“锐实力”运作,将中国因软实力增强而获得的海外影响力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威胁,事实上与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发生变化相关。
美国战略界真正开始关注中国软实力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2009年3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推出报告《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启示》,对中国在非洲、美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软实力发展进行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尽管有努力,中国“弱”的软实力并不对美国地区与全球影响力构成威胁。2"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A Report of the CSIS Smart Power of Initiative,Edited by Carola McGiffert,March 2009.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也认为彼时中国的软实力远远不如美国。他在2012年撰文《中国软实力的赤字》、《中国软实力为什么这么弱》,阐述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来发展软实力,但没有获得同等的回报。除在非洲、 拉丁美洲等地区,中国在周边国家与欧美地区的软实力并没有明显增强。3Joseph S. Nye,"China's Soft Power Deficit",May 8,2012,(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4 51104577389923098678842.html.); Joseph S.Nye,"Why China Is Weak on Soft Power",January 17,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1/18/opinion/why-china-is-weak-on-soft-power.html?_r=1&scp=4&sq=Chinese+president++++Western+culture&st=nyt.)
美国战略与舆论界对中国软实力“比较弱,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的认知在2015年后开始发生变化。时年中国软实力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方针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重要成就。以孔子学院为例,首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创立。到2014年,中国与122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4“驻加纳大使孙保红在孔子学院日活动上的讲话”,2014/09/30,(https://www.mfa.gov.cn/ce/cegh//chn/dszl/dsjh/t1196999.htm.) 6Robert D. Blackwill,Ashley J. 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Tellis_Blackwill.pdf.)孔子学院或课堂主要教授中文以及大家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当地欢迎。但西方舆论界开始出现指责与抵制孔子学院的声音。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呼吁美国各个大学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议员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孔子学院;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用整版刊登批评孔子学院的文章,指责孔子学院妨碍西方社会的学术自由、财务不透明以及有强行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嫌疑。语言与文化上的跨国界交流与互动,本是一个典型的软性活动。但短短几年,美国精英眼中“弱”的中国软实力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妨碍学术自由、强行灌输意识形态”的“强悍”行为。这其中的逻辑实质上是:中国的软实力一旦强大到威胁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就不是由“弱”变“强”了,而是由“弱”变“坏”了,这也是“锐实力”概念得以诞生的心理背景,即美国与西方世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认知与心态发生变化。而促成这种认知与心态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对华战略认知的转变。
与上述对中国软实力看法发生变化的时间线一致,美国战略界也是在2015年前后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战略与中美关系。早在2015年3月,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出台了一份《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指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试图使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做法是失败的,这一做法对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产生了新威胁,并最终将在全球对美国的权力形成挑战。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大战略,来平衡中国的崛起。新战略不用遏制的手段,但很可能是激烈的战略竞争。
美国智库的声音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所反映,战略报告不再提及寻求与中国建立全面合作的关系,而是更强调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保持警觉,敦促中国在各方面遵守国际规范,打击中国网络犯罪、商业窃取等。1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ruary 2015,(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奥巴马政府还提出了“亚太再平衡”地缘战略。到2017年,美国战略界的“接触派”声音进一步萎缩,“反思派”开始占据主流。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是直接将中国、俄罗斯等称作“战略竞争对手”,第一次超越恐怖主义被认定为美国安全与利益的头号威胁。
2021年拜登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3月份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把应对中国的挑战列为美国八大战略优先事项之一,并着重强调要团结盟友与伙伴共同应对。2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2021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旨在向美国技术、科学、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手段同中国展开竞争,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长达1000多页的法案以《无尽前沿法案》为母本,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等立法作为修正案加入其中,几乎包罗了所有涉华事务,这其中包括应对中国舆论宣传、影响力扩散等战略目标与措施。
综上我们认为,民主基金会推出“锐实力”报告并促其全球传播,意图是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整体战略转型、对抗中国影响力、在软实力方面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围堵与舆论宣传。尽管在2021年10月中美高级官员在瑞士会晤时,美国态度较之前有所缓和,提出了“负责任竞争”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中国的这场舆论战。
二、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传播模式
国家战略传播,是政府作为主体主导的、为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目标的信息与传播活动。国家战略传播是当前信息化与大战略时代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支柱。美国最早将“战略传播”引入政府话语与实践。作为美国对抗中国软实力影响的舆论工具“锐实力论”,其传播模式也运用了典型的战略传播模式。而美国战略传播模式最经典的特征就是全政府—全社会的联动传播。
由于冷战的历史经验,美国非常擅长在涉及重大战略议题方面实施全政府模式。全政府模式,主张汇集相关组织资源、通过跨部门协调达到共同应对复杂问题的目的。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着手建立全政府模式的对外传播体制,9·11事件之后更是提出“战略传播”概念全力打造具备完整全政府模式的传播机制。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战略传播架构》,建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决策核心,以常设“战略传播机构间政策委员会”为跨部门协调的战略传播机制,将安全、外交、国防、情报、发展援助等部门进行统筹安排,全部纳入到战略传播整体框架中。3U.S.President,"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2010,(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27301.)此外,美国的立法机构众议院、参议院也会通过各个委员会出台报告、举办听证会等手段参与进来。在战略传播机构间政策委员会的统筹与协调下,美国各重要的权力部门负责人定期协商,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下统一战略目标,然后分头指挥各个机构,形成了全政府式传播网络。
2017年底启动的“锐实力论”,就是这种全政府式战略传播的典型实践。从特朗普到拜登,无论他们在其他领域政策分歧有多大,但其政府发布的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战略文件中,都会涉及到相似的“锐实力”叙事;美国国会也不定期地就“中国锐实力”议题举办听证会。2019年5月美国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举行主题为“中国外交影响与‘锐实力’战略”的听证会,发言人除了和以往一样举证中国在出版、媒体、孔子学院、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锐实力”行动,在谈到对策时还首次指出:应对“锐实力”是一场治理模式的战略竞争,是一场观念的战争。4"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and Sharp Power Strategy to Shape and Influenc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May 16, 2019,(https://www.ned.org/chinas-foreign-influence-and-sharp-power-strategytoshape-and-influence-democratic-institutions/.)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最新发布名为《来自中国挑战的要素》的报告,用超长篇幅罗列了中国“锐实力”行为在全球各地区的影响,并重点讨论如何应对这种新挑战。1"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020,(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20-02832-Elements-of-China-Challenge-508.pdf.)除了官方文件发布、举办听证会,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行政机构通过新闻发布会,总统、国务卿、情报官员等通过接受采访、参加国际会议、研讨会等方式为“锐实力论”“中国影响力威胁”制造舆论、加戏加码。2021年3月初国务卿布林肯发表首场外交政策演说,强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列出8大优先工作事项,中国是唯一被列入优先工作事项的国家,其他7项则属于内政事务;2Antony J.Blinken,"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March 3,2021,(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3月底率队与中国在阿拉斯加高层战略会谈上“唇枪舌战”之后,布林肯马不停蹄地赶往欧洲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与盟友磋商如何应对中国、俄罗斯所谓“威权主义”国家的挑战。
然而,仅仅依靠全政府模式,“锐实力论”无法获得广泛的传播与认可,这就需要将全政府模式与全社会模式结合起来。
全社会模式通常是指动员媒体、企业、智库、大学、个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个层面参与目标一致的行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实施“遏制苏联”战略,曾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参与对抗。美国战略界深知,“锐实力论”要想获得预期效果,除了政治官僚体系,去政治化的社会系统参与才能达到更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效果。政府主导的战略议题传播,必须拓展其信息源的多元化方向,尽可能让民间社会参与进来。事实上,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通过资助、捐款、“旋转门”等方式培养了大批亲政府立场的民间智库、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或关键意见领袖,在政府需要时能为其背书、站街与助威。另外,美国政府也建立了成熟的与社会系统协调关系的公关体制,重点协调与独立媒体之间的关系,争取获得媒体在国家战略议题方面的支持。总体来说,但凡遇到重要的战略议题特别是对外战略议题,美国民间社会一般会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并充当国家战略传播的马前卒。这种全政府—全社会联动式战略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
“锐实力论”最先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出,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战略传播的模式特征。由“民间智库”来做舆论的首发阵容,再加上西方主流媒体的助攻,“锐实力论”很快就成为全球舆论的热门话题。很多国际民众首次认识“锐实力”一词,即从《经济学人》上看到,《经济学人》接连刊发相关文章,为“锐实力论”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其他大报如《华盛顿邮报》《卫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等加上著名学术杂志如《外交事务》《外交政策》《民主文摘》等也紧紧跟随。
除了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全社会传播模式更能展现其优势。以社交媒体推特为例,2018年初“sharp power”成为其热门关键词,智库、媒体、杂志以及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各界人士纷纷直接发布“锐实力论”内容,然后又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评论与转发。由此,“锐实力论”通过美国政府的暗中操控,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力量达成共识,形成传播合力,最后将议题传递给国际受众。
三、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传播策略
全政府—全社会联动传播是美国“锐实力论”的基本传播模式。要想让其议题与论断被美国公众乃至国际受众所接受,还需要运用一定的传播策略。而美国“锐实力论”的传播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创造新概念进行 “问题界定”
“问题界定”是主体在传播中塑造观念与取得认同的主动性策略。中国软实力的增长与扩散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非常自然的大国成长过程,每个大国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关注自身软实力的建设,包括建构良好国家形象、拓展文化影响力、争取国际话语权等。然而要想将这个正常的过程界定为一个“问题”,就需要通过创造新概念来进行“问题界定”。将“中国软实力发展”界定为“中国向全世界使用‘锐实力’的问题”,此举事实上是把中国正常的软实力提升界定为“不正常的问题”,将原本正常的国际传播活动定性为“渗透”“操纵”与“胁迫”。
民主基金会如此界定“锐实力”概念:运用如匕首、注射器式的手段渗透到目标国家的政治、信息环境中。报告辩称:“威权主义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通过媒体、文化、学术等方法实施影响力,其手段不以软实力的吸引与劝服为特征,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操纵”与“干扰”。报告指出,锐实力既不是硬实力的运用,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软实力,而是中国等国家输出影响力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对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From‘soft Power'to‘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NEW FORUM REPORT,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Published on December 5,2017,the Full Report[PDF],p.6.(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报告出台后,美国主流媒体紧跟着使用“锐实力”概念来提出所谓的“中国问题”。《经济学人》率先运用头版头条的封面文章介绍“锐实力”概念,接连刊发评论文章如《中国的锐实力如何抑制海外的批评之声》《面对中国的锐实力我们怎么做》等,2"How China’s sharp power is muting criticism abroad",Dec 14th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7/12/14/how-chinas-sharp-power-is-muting-criticism-abroad.);"What to do about China’‘sharp power’",Dec 14th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还有众多著名报刊与学术性杂志也纷纷加入传播队伍,“锐实力”一词在国际舆论场域迅速窜红。无论是新闻报道、学术文章、研究报告,其主要概念、核心观点甚至连例证都与民主基金会报告内容如出一辙,即利用“锐实力”新词界定他们眼中的中国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以“锐实力”为主题的相关专著在欧美出版,还有数篇以“锐实力”为关键词的硕博论文出现。3参见Andreas Fulda,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Mainland China,Taiwan and Hong Kong:Sharp Power and its Discontents,Routledge,2019;Douglas F.Larson,"China’s Emerging Soft/Sharp Power Strategy in Hollywood",Assistant Section Chief,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BS,National University,September 2019;Angie heshamabdoahmedmahmoud,"China’s pursuit of Dominance;Sharp Power in Taiwan and Australia",Masters Dissertation,October 2020.2020年10月一篇发表在《战略桥》杂志的学术论文还声称:如今,“锐实力”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有关国家实施权力的重要方式,必须引起西方社会关注。威权主义国家使用“锐实力”,使民主国家与其进行战略竞争的能力大大降低,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折。4James Micciche,"A Democratic Disadvantage: Sharp Power and Regime Typ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ctober 12,2020,(https://isdp.eu/publication/sino-austrian-relations-in-the-era-of-sharp-power/.)该文章使用“锐实力”概念将“中国影响力威胁”上升到战略新高度。
(二)利用学术话语的包装增强其战略传播的可信度
传播学有一个所谓“可信度递减规律”,即国际受众特别是西方民众,在看待不同信息源的可信度呈现这样的递减趋势:依次是第三方立场(包括专家、学者、民间组织等)、媒体、政府。政府这个信息源在西方民众的印象中属于最不受信任之列。1参见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于是,将“锐实力论”包装成一个学术话语传播,是增强其战略传播可信度的有力策略。
除了研究报告、专著、学术论文,2020年来美国学术界还精心打造了针对“锐实力”议题而专门设立的学术网站、博客、播客等,以求学术信息的持续更新与广泛传播。前述提到的胡佛研究所设立了名为“中国全球‘锐实力’每周预警”的专门网站,每周都更新相关的信息与研究成果,目的是“让全球的专家学者都能搜索到有关‘锐实力’的研究成果与相关动态”4"China's Global Sharp Power:Weekly Alert",A Product of Hoover Institution,(https://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hina-global-sharp-power-weekly-alert.)。民主基金会也建立了名为“权力3.0:理解现代威权主义影响”的博客,目的是“揭示威权主义国家如何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生存、发展、繁荣,以及民主国家如何与之竞争”5"Power3.0:Understanding Modern Authoritarian Influence","About Power 3.0",(https://www.power3point0.org/.)。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西方学术界将会持续跟进所谓“锐实力”的研究,最终提升“锐实力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从而增强其战略传播的可信度。
(三)运用意识形态批判获取战略传播的道德共情。
“锐实力论”不仅具有专业的学术包装,更是通过“根源分析”“道德评判”将文本叙事深入到所谓“威权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在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这种传播策略试图将“锐实力论”这种政治话题融入到普通民众也能接受的道德共情与公共性空间。就传播的策略与效果而言,学者们发现,“道德煽情”比起理性的“逻辑推断”更具有广泛的传播力。特别是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度,本国对他国进行制度或意识形态批判一般更能激起本国受众恐惧、焦虑与愤怒的情绪。美国“锐实力论”在传播过程中涵盖着大量的“道德煽情”正是利用了此点。
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锐实力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这是中美在恢复邦交、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很少见到的。自2017年“锐实力论”传播以来,中国遭遇美国舆论的意识形态攻击愈发明显。美国舆论界将“中国锐实力”归咎于中国的制度与价值观。《经济学人》一篇题为《西方如何误判中国》的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中国将西方价值观视为实现自我野心的障碍。文章据此判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锐实力”的目的,实质上是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不仅仅只是经济竞争。1"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Mar 1st 2018,(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7517-it-betchina-would-head-towards-democracy-and-market-economy-gamble-has-failed-how.)
最近两年,一些政客、学者将香港骚乱、台湾选举、新疆民族问题甚至全球疫情等敏感的话题都与中国“锐实力”勾连起来,统一推演到意识形态、价值观批判层面,以此来推高西方民众的关注度,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热度,从而获得道德共情。2020年4月詹姆斯敦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剪报》中一篇文章声称: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意大利的“魅力攻势”(“锐实力”的另一称谓)正在加强。2Dario Cristiani,"The Chinese Charm Offensive Towards Italy as the Coronavirus Crisis Deepens",The Jamestown Foundation,China Brief,Vol 20 Issue 6,April 1,2020,(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Read-the-04-01-2020-CB-Issue-in-PDF.pdf?x96727.)6月《外交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以“对于中国的‘锐实力’全世界正在觉醒”为题目,评论中国大陆首先对香港使用“锐实力”,压制香港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行动与呼声。而中国疫情的爆发与全球疫情的蔓延让世界见识了中国的“锐实力”。3Simon Shen,"The World Is Awakening to China’s Sharp Power",June 23,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the-world-is-awakening-to-chinas-sharp-power/.)利用敏感的话题,加上西方社会喜闻乐见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价值观口号,“锐实力论”在短短几年内从学术话语转变成学术、政治兼具的公共性话语。
四、美国“锐实力论”战略传播的影响与中国应对
基于美国成熟的全政府—全社会联动的战略传播模式,加上概念创新、学术包装、道德共情等传播策略,美国“锐实力论”在全球特别是西方世界迅速传播,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外舆论环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阻滞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正常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一)美国“锐实力论”战略传播对中国的影响
其一,“锐实力论”的传播妨碍了中国孔子学院在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与亚太地区的发展势头。中国孔子学院曾是中国拓展软实力、发挥文化影响力的有力举措,从2004年起在全球迅猛发展。然而美国“锐实力论”将孔子学院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政府、国会纷纷出台限制其发展的措施。虽然美国学界素以“独立”著称,但各高校仍然受到这种舆论传播的负面影响。自2018年以来孔子学院在美国遭遇“关闭潮”。2017年时,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有103家,而2018年2月时就关闭了一半多,还剩下55家。8月,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校方认为孔子学院的教学与大学理念不相符,决定终止合作。北佛罗里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西佛罗里达大学也先后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4林祖伟:《美国继续关闭更多孔子学院:软实力变锐实力背后》,BBC NEWS中文网(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237598.)瑞典是欧洲第一个接受孔子学院的国家,2018年6月其7个城市的学校也陆续停止了孔子学院的活动。此外,在“锐实力论”的助推下,英国、德国、法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国家的高校也陆续宣布关闭孔子学院。
其二,“锐实力论”的传播毒化了中美、中西之间民间交流的正常氛围。“锐实力论”集中对中国大陆的外宣媒体进行攻击,指出中国媒体受政府控制,试图在海外输出审查,控制言论。在这种舆论氛围下,2020年美国政府大幅消减了中国官方媒体的签证数量,中国政府作为外交回应也驱逐了美国某些在中国大陆工作的美国记者。除了媒体,在科技、学术、留学、文化等领域,两国的正常交往也受到了“锐实力论”传播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收紧了中国学生与访问学者的签证政策,加大监管美国之外的科研资金与多国合作。美国情报机关对中美学术交流的监管日益严密。例如,近两年就有多名美国华裔科学家或研究者因与中国大陆有敏感领域的合作项目而以各种理由被捕,甚至还有美国大学如北德州大学决议驱逐所有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公派访问学者与留学生。5瑾岩、王一苇:《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逐客令:要求中国访问学者尽快回国》,知识分子网(http://zhishifenzi.com/depth/depth/9931.html.)
将我院2017年10月-2017年12月收治的520例医保患者视为研究对象,对其住院费用进行分析。全部患者中,男性患者271例,女性患者249例。年龄最大85岁,最小23岁,平均年龄(52.3±1.4)岁。疾病类型涵盖了医院各个科室系统。
其三,“锐实力论”传播助推了一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敌意,这些敌意特别集中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正是“锐实力论”传播策略中所突出的部分。皮尤研究中心一项“2019年春季全球态度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3个国家当中,有21个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超过半数以上,相对比美国,他们对美国的正面评价超过中国;33个国家当中仅有7个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超过美国。1"Around the world,more see the U.S.positively than China,but little confidence in Trump or Xi",(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1/10/around-the-world-more-see-the-u-s-positivelythan-china-but-little-confidence-in-trump-or-xi/.)2020年以后,除了“锐实力论”继续发酵,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抹黑中国,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负面形象达到历史新高。2020年10月,皮尤公司的调查显示,在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与加拿大等国,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这一调查覆盖的14个欧美与亚洲的发达国家。2"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2021年7月,在17个发达经济体中进行的一项新民意调查发现,尽管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方面的得分有所改善,但国际声誉仍落后于美国,继续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3"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remains broadly negative as views of the U.S.rebound",(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6/30/chinas-international-image-remains-broadly-negative-as-views-of-theu-s-rebound/.)
可见,美国“锐实力论”的战略传播增加了西方国家从政界到民间对中国的敌意,阻碍了双方共同开展的、正常的媒体交流、科研合作与其他文化或数据交流,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国家形象。
(二)创新战略传播策略,积极应对国际舆论
对于美国战略界推动的“锐实力论”,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警惕,因为它的性质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舆论风潮,而是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一次持久的舆论战。由此我们需要从战略传播的高度,创新战略传播策略,积极应对国际舆论。
第一,战略传播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连接国家最高层的战略决策,还要求社会各界的联动反应。因此,国家战略传播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从“锐实力论”的战略意图来看,“锐实力论”绝不只是个案,此后美国战略界运用类似的传播模式在国际舆论场制造了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全球抵制新疆棉花事件以及持续炒作香港人权问题。因此中国的应对,也应从创新中国战略传播机制入手。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06月02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初步建成了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有效开展了国际舆论引导与舆论斗争。但是面对新的国际变局与形势,特别是美国发动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战略传播活动,我们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的战略实践对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提出的新要求。
在2018年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成为管理中国对外传播与宣传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一委员会集合了外交、宣传、统战、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的决策议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兼任主任,其成员包括外交部、统战部、宣传部、外宣办、国防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此委员会的设置,提高了中国在外事方面决策议事的权威性,促进了对外传播的跨部门参与,加强了统筹协调能力。然而从战略层面的高度来看,目前中国的宣传特别是对外宣传并未与中国的安全战略系统直接挂钩,因而缺乏战略传播意识与战略协调;我们的对外传播活动还未从战略高度与安全、情报、信息、国防、新闻出版、发展援助等多个相关部门组成深度合作与协调的全政府体系。事实上,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直接影响国家软实力、影响力扩散甚至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将传播与安全战略机制挂钩成为决策层需要考虑的现实选项。中国国家战略传播机制需要将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强调的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等融合在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中,并协调各部门参与具体实践。具体的战略传播协调机构应该在国际舆论事件突发时,制定相关预警与风险评估机制。如此我们才能主动应对“锐实力论”等一系列舆论战,稳固与推进中国良好的发展与复兴大局。
第二,中国学术界需要加强学术话语与相关理论体系的建设,揭露与对抗西方政治与学术话语霸权,创新自身的战略话语。
正如中国学者陈曙光所言,西方政治话语走向霸权的逻辑,就是通过自命为“科学”获得,即借助学术包装赢得话语优势。1陈曙光:《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生成与解构》,载于《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冷战后,美国为了使其超强的文化霸权合法化,创造了“软实力”概念,强调其权力的吸引力与认可度。然而新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实施的单边主义军事反恐暴露了美国权力的弊端,于是美国学界又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意欲呼唤“软实力”的回归。而如今美国学界提出“锐实力”,则是针对中国、俄罗斯在国际舆论、文化交流领域的影响力提升,意图将其树立到“软实力”的对立面。从“软实力”到“巧实力”再到“锐实力”,如何破除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可以围绕“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命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视角创造性地阐释中国权力增长、中国权力有别于西方语境以及中国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的特质,并尝试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学界逐渐在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外交、正确义利观、国际总体安全观等国际安全、外交与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概念与理论话语体系,并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基础的权力理论方面,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原创性思考与理论探索,破除西方学术语境,从中国语境寻找中国和平崛起与文化影响力辐射的国际合法性与全球认可度。
第三,美国“锐实力论”的传播带有非常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国的战略传播策略则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要继续大力传播“非意识形态化”的交往理念,例如,“和而不同”“多元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避免掉入意识形态对抗的陷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主动应对,以“文化自信”为核心内容优化中国文化影响力资源,改变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激发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是美国惯用的传播策略与技巧,而我们则需要保持理性,继续以“新型大国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国际传播上,不主动挑起意识形态攻击,而更多地围绕如何共同应对当前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来展开话语传播。例如,继续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来反制美国“锐实力论”的意识形态攻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观念,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依托着中国发展的生动实际,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具体靠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来体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话语设计,需要立体地涵盖上述这些方面。
其次,中国不与美国进行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与回避传播意识形态话语。相反,中国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信念下,可以真诚地、有技巧地展开意识形态传播。正如习近平书记在5月31日的讲话中提到:“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06月02日。因此,我们以“文化自信”为核心内容优化中国文化影响力资源,改变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最终消解“锐实力论”的负面影响。
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内涵丰富而多元,从历史到现实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成长与奋斗实践,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与思维方法,是中国文化宝贵的财富,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不可缺少的资源。
从传播话语建构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和合文化”“义利观”“天下情怀”等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对外基础性话语资源,向外界呈现一个爱和平、重道义、有担当的国家与民族;以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成果、革命价值为特征的中国革命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对外话语建构,从而清晰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采用什么方式得以长期执政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从制度层面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引导力、驱动力、凝聚力等方面增加外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认同,从而助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道路的拓展。1陈明琨、陶文昭:《文化自信视阈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转向以受众为中心。二战后传播学出现了“使用与满足”理论,此理论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寻求使用媒体进行自我满足。2参见[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321页。该理论赋予了受众以主体的地位,提出了以受众为中心的新的传播模式。21世纪以后,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不断强化。为了增强劝服效果,中国的话语传播也需要以受众为中心来设计传播的各个环节。由于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是国外的社会公众,其在欣赏趣味、政治态度、利益诉求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面对国际受众时,必须对其进行细化、量化,细分为不同需求与个性的“国际分众”。
经常进行国际受众问卷调研是了解不同国家受众需求的好方式。北京大学“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课题组经由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国际在线调研公司,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沙特六国进行了大样本概率抽样问卷调查。3关世杰:《五年间美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喜爱度大幅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问卷调查之一》,载于《对外传播》2018年第2期。另外针对沙特、俄罗斯、日本、印度、德国的问卷调查分别刊登于2018年第3、4、5、6、7期。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认知度并不相同,对于某些文化符号其认知度与喜爱度也并不一致,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调查数据恰到好处地运用语言、图像、符号去容纳与体贴这些不同受众的“经验范围”,扩大与其经验范围的重叠面,从而降低认知障碍,获得预期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