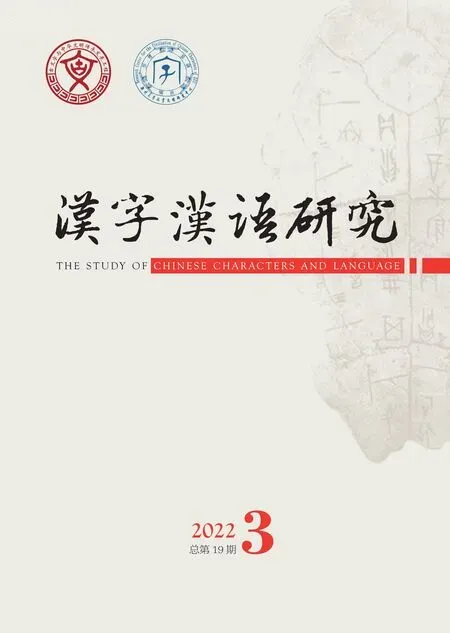汉语史视角下粤方言疑难字的考释方法*
——以清代粤剧疑难字为例
2022-12-02李嘉怡曾昭聪
李嘉怡 曾昭聪
(暨南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清代粤剧中的疑难字考释,需要将汉语史与方言学的知识相结合,将共性的考释原则与粤方言个体特色相联系,从“形、音、义”三个角度综合进行。利用字形时,考虑共时字形材料和变换部件;利用方音时,联系语音底层、外语接触、破除假借与分合音问题;利用字义时,注意语义的细微区别。
1.早期学者考求本字之法
早期学者在考求本字上已有心得,可以总结为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遵循传统语文学的方法,从古代韵书和字书中寻求与现代音义相合的字。学界称之为“觅字法”。章炳麟《新方言》就是使用该法的典范,罗翙云《客方言》、黄侃《蕲春语》皆属此类。第二种是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即根据字音来确定其所属的历史层次,最后在确定的层次内考出本字。梅祖麟(1995:2)、杨秀芳(2000:111)称之为“寻音法”。
随着学者频繁地使用两种主流方法考求本字,他们意识到两者各有千秋,又各有不足。前者音义相合即可求,简便又切实可行,但“无法解决不同历史音韵的时代层次问题”,对于层次复杂的方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后者确定层次更科学,但“又容易忽视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与冲突”。为了提升本字考求的精准度,学者们结合各种语言学理论不断补足,衍生支流,不尽同向。邓晓华(2006:111)提倡运用同源词理论及语言接触的理念解决方言的本字研究问题;甘于恩等提倡结合地理语言学的知识,革除由地理位置的隔绝所引起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疑难问题(参看甘于恩、曾建生,2010);潘悟云(2015:289-294)沿“觅音法”之路,更精准地提出“觅轨法”,通过音变轨迹确定本字,对研究者掌握音变规律和规则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总体而言,目前方言本字的考释仍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继续完善:第一,侧重语音,略轻形义。方言字的表音性很强,故部分学者侧重方言内部语音系统的证据。其实,从字形线索考释方言疑难字也大有作为,字形共时写法的相关性和迁移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精妙的线索,下文结合例子详谈;第二,不重视书证材料。部分学者认为通行于清代训诂大家的“觅字法”早已落后于时代,于是书证材料也通通抛诸脑后。其实,语例恰恰是字义科学性与时代性的关键证明,有“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之效;第三,未结合所考释方言的个体特色。方言字的产生与该方言所处的共时语言环境及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考释疑难字时如果事先了解该方言的起源与发展,结合其语言底层和语言接触情况精准切入,往往能捉住关键线索,在探源析流上事半功倍。
本文以《广州大典·曲类》所收的清代粤戏剧本为研究语料,将其中未载于大型字书或意义未详的字视作疑难字。结合汉语史与方言学的相关知识,联系共性的考释原则与方言的个体特色,在考释过程中总结方法。本文语例后注名册数和页码,“J20:94”即《广州大典·曲类》卷20,第94 页;注音参照《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表》。
2.粤方言疑难字的考释方法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方言字也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对其考释必须从这三个角度出发。
2.1 联系共时字形,考求中间环节
书写者的个体差异助长了方言字的随意性。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字形的共时写法不能作为考本字的重要依据”(甘于恩,2009:77),但总体而言,语言文字的使用是一种社会现象,共时材料在用字上还是存在相对一致性。张涌泉、曾良等汉语史学者正是通过排比敦煌写本、明清小说的俗字来总结方法论,可见联系共时字形是学界考辨俗字的重要方法。
2.1.1 重视共时字形材料
重视共时的书证材料,一方面从字形的同一性中挖掘线索,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寻找出记录同一个词语的不同字形,才能更好地对疑难字进行析源探流。下面以“噱”的考释为例:
(1)《三弃过其祖·卷一》:“(水白)无错咯,二叔呀!嘅的礼物抬过尔个边就做得噱。”(J20:98)
(2)《三弃过其祖·卷一》:“(其白)佢未曾肯呀吗?(转身)师爷有乜计呢?(师白)有噱!前往叫历成县做媒,父母官责落嚟,哪怕他唔肯。”(J20:97)
(3)《三弃过其祖·卷二》:“(运白)带埋亚獬去添啦。(水白)做得咯,二叔尔翻去噱。”(J20:102)
《说文·口部》:“噱,大笑也。从口豦声。”《广韵·铎部》:“嗢噱,笑不止。其虐切。九。”《汉书·叙传上》:“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可见“噱”在辞书和典籍用例中多为“大笑”,也表示“口腔”,如《羽猎赋》:“沉沉容容,遥噱虖纮中。”颜师古注:“口内之上下名为噱,言禽兽奔走倦极,皆遥张噱吐舌于纮罔之中也。”这两个义项均与文义不合。
虽然排除“噱”是本字,但它的来源和流变仍有许多可能,仅仅依赖粤戏剧本中的语境很难探明究竟,在广泛阅读清代粤方言文献后,可找出记录该语气词的不同字形:
(4)清代粤语辞书《分韵撮要》:“罅,良化切,隙也,漏也。”
民国粤语辞书《粤音韵汇》:“ 【la—】①书籍凡例后写明[x—]为高去调(参见黄锡凌,1957:68)。罅。”
(5)清代粤剧《上炉香》:“(银叹)唉,我地亚姐了,你妹母子分离就难舍割罅。姐,你灵神庇佑佢长大成人,唉,唉唉唉唉。(宗白)而家好大个罅。”(J20:231)
(6)清末粤地学话教本《粤音指南》第三章:“乜人打门呀。老爷几晏嚹,请你快啲起身喇。”②参看(清)佚名(2014:665)。
(7)清末传教士粤语小说《路加传福音书》第八章2-3 小节:“耶稣讲完呢的、就大声话、有耳可听嘅、就要听嚹。”③参看(清)佚名(1873:22)。
(8)清粤戏剧本《七贤眷黄土岗祭奠·上卷》:“救命呀,老虎嚟嘑!”(J20:39)
(9)清粤戏剧本《大闹南溪·上本》:“(明白)噎吔,我估边一个,原来系罗相嚟,请落船坐嘑。”(J20:180)
参看例(4),“罅”本指缝隙,清代粤地读为“良化切”,拟音[la33];而粤语中有一语气词音[la55]或[la33],于是当地人借用声韵同而声调有别的“罅”来表示,即例(5)。可能为了区分“罅”的“缝隙义”与用作语气词的“感叹义”,时人在“罅”上加注形符“口”,标示其类属,组成新字形“嚹”专门记录该语气词,见例(6)(7);后来,为了书写简便,书写者将“嚹”减省部件写为“嘑”,见例(8)(9);“嘑”“噱”两字形近,故讹写。
收集了同时期的方言辞书、学话教本、传教士小说、粤戏剧本中的字形材料后,我们可以归纳记录粤语中音[la33]的语气词的四种形式:“罅”“嚹”“嘑”“噱”,它们都可看作异写词,在古籍校勘时可考虑注释。其变化链条总结如下:

2.1.2 变换部件
方言中“有音无字”的现象非常突出,想在汉字原有体系范围内解决此问题,“假借”和“训读”可以称得上是极为高效且常用的方法。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假借字和训读字并非最终呈现的结果,而只是字形演变的中间环节?在清代粤戏剧本中,我们发现有一类特殊的粤方言字,这类字都由字形复杂、笔画较多的假借字或训读字演变而来,通过对其部件进行简化、省略或改换等一系列的操作,最终得出面目全非的疑难字。这时,变化部件以考求中间环节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清代粤剧中常见的动词“”“”为例:
(10)《文丽卖新客·上卷》:“(鳄鱼用尾拂,下食同入)(生白)不好了,伙记被鳄鱼食去了。”(J20:447)
(11)《幻醉广寒·卷二》:“何况你有仙缘功成可待。(吴唱)开此言,不由人,情窦大开,走上前把衣,休嫌弃,站埋来,问美人可允从。”(J20:486)
笔者初看此字被声符所迷惑,但一直无法找到粤语中音“尽”的动词与之对应,所以猜测其可能是经过变形的方言字。如果抛开语音的因素,往往是笔画繁杂的字才需要作简化或变形处理。尝试将声符繁化,可得“孻”“”二字,且都出现于清代粤戏之中,以下举例:
(12)《文丽卖新客·上卷》:“不好了,鳄鱼食了伙记,水鬼孻了头家,如何是好?”(J20:447)
(13)《偷摘莲花·下卷》:“若有歹心,将娘抛弃,折堕我,躝街趷地,无处藏尸。猪又孻来,狗又啮,蛇伤虎咬,碎剐凌迟。”(J22:704)
(14)《火烧大沙头·卷二》:“(下孻扯上唱)多蒙李道春筵请,庆叙同乡故旧情。”(J20:450)
(15)《火烧大沙头·首卷》:“我姓何,个个事头婆系大碌木。当初住落新填地个处第九局,做生涯,当地狱。呢时话人,个时话封屋。”(J20:453)
故“孻”应为“拉”的同音借字,由于字形复杂,书写者通过简化部件变为“”。但无论是“孻”还是“”,从字形上已经看不出二字与“拉扯”的动作有关。为了更好地提示词语含义,书写者又进一步改换形符为“扌”,造出“”和“”。综合以上,总结出四个方言字字形的演变链条如下,可以看出假借字“孻”在字形演变中处于关键的中介位置。

考释方言疑难字时,如遇语音线索不明的情况,从字形着手也是一条好路。重视共时字形材料,考求中间环节,尽最大努力增加可以利用的形、音、义的线索,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2.2 把握方言特色,巧用方言语音
粤方言字重视表音性,如清代粤戏剧本常用“㤃”不用“慌”,用“”不用“慢”,用“抯”替代“扯”,就是选用简单明了的声符,使读者见字如同听音,立即明义。利用方音助力考释工作,必须摸清粤方言的源流背景,其上千年“汉越杂居”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深厚的外族语言底层、沿用大量古语词的习惯、通商以来多与外国人接触的历史渊源,皆是其个体特色。
2.2.1 联系语言底层
陈忠敏(2007:44)认为:“语言底层是语言用户操习得语时所带有的母语,或底层母语(指已经死亡了的母语)的成分或特征。”早在1953 年,岑麟祥《从广州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一文就运用“底层理论”来考察粤方言与周边方言的联系,也得出粤地土著所用之语与壮语同属一系的结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欧阳觉亚、李锦芳、游汝杰等人纷纷沿此思路,分析出粤语中的“壮侗语族底层词”。在分析清代粤剧中本字不明的疑难字时,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是否有语言底层的残留,并查阅辞书,寻找相关的语言证据,佐证推测。此以疑难字“脌”为例:
(16)《西关妈》:“留心睇吓佢胸前,个个从来冇大脌。”(J504:278)
“脌”见于清代粤地诗歌集《西关集》中,《中华字海》收此字,但“义未详”。其他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广州方言词典》《广州话词典》均未收。
猜测“脌”为记音字,形符“月”提示与身体器官相关,而声符“年”提示字音与[nin11]相同或相近。根据音义线索,查找粤方言字典,可寻“”字,《广州方言词典》:“【】 nin乳房。(人的)乳汁:饮~||俗字”;《广州话词典》:“【】nin1乳房。奶:食~。”从字形构造来看,“”和“脌”形符的类属相近,声符相同,很可能是记录同词的不同字形;代入语境中,例(16)表乳房义的“大脌”与“胸前”意义相合。
但“年”音为何有“乳房”义?笔者在查阅辞典时还发现客家话中将表示“母亲”的词写为“阿哖”,明本潮州戏文中将“母亲”记作“阿姩”,三者之间有无关联?温昌衍(2011:13)对比了客家话、潮汕话、广府话的人体类词语,发现三种方言中表示“乳房”义的词,词根相同,属于底层词,来自古百越语,广府话的“脌”正与南部壮语表“乳房”义的[nin]音同。由于乳房是女性独有的器官,被视作母亲的象征,李瑶(2013:32)通过调查指出“侗水语支语言的父亲、母亲称谓分别以pu、ni居多”,由此可以看出,另外两种方言都将“母亲”一词记录成以“年”为声符的字,可以说也与古壮侗语底层密切相关。
2.2.2 考虑外语接触
身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节点,清代粤地人民由于经商、接受教化等原因常与外国人接触,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说几句简单的外语。为记录这些外语词,粤语区人民创造了不少音译用字;同时期西方传教士译著、教材载有其独特的记录音译词的书写方式,这种文字形体也被俗文学加以借鉴。下面以“”“叻”“呖”为例进行说明。
(17)《父女为响马·五卷》:“咁样呀,你系访寻丈夫,易事!想我贸易几十年,庇石叻,大小吕宋,大小辟呖,金山上海,个个埠头,都有交易。”(J20:411)
例(17)中,一名在各地经商的华侨,常与人打交道,所以热心帮助女子寻夫。在清代传教士译著或戏曲文本中,音译词多用“口”旁提示,且结合后文的“金山”“埠头”等关键词,可以猜测“庇”“石叻”“辟呖”皆为外国地名。根据这些字词的粤语读音,并参考西方传教士音译外国地名的规则,尝试反推外语音标,得出外语单词,如表1 所示。
表1 还原方言字“”“叻”“呖”的推导过程

表1 还原方言字“”“叻”“呖”的推导过程
英语元音[a:]可对译粤语元音[i],如“Arrack”对译为“哑力酒”或“桠力酒”①该节出现的对译用字均可见于同时期传教士书籍用字[参看(清)唐廷枢,2014:215-279;另可参看张荣荣,2020]。。故“辟呖”对应马来文“Perak”[pera:k],即马来西亚联邦州之一“霹雳”。
英语元音[æ]可对译粤语元音[a][ɐ],如“Africa”对译为“亚非力加”或“亚乎利加”,“Peru”对译为“庇理”。故“庇”对应英语“Penang”[pɛnæŋ],即马来西亚的联邦州之一“槟城”。
元音[e],英语、马来语和粤语共有,可直接对应,“石叻”对应马来文“selat”[’sɪlet],即华侨华人对“新加坡”之称。
通过总结音译规则,特别是韵母间的对应规律,对于破除音译外来词也大有裨益。此以“沙贱”为例:
(18)《荷池映美·卷一》:“我个女儿又唔想你,分明你系一只四爪蠄劳,满肚淫丝,你好好听我良言。你就快些了支兼趷支。如若不然,我就叫街坊、地保、沙贱、绿衣来拿住你,把你剥骨煎。”(J22:245)
“沙贱”应为Sergeant 的音译词,最早特指英国警察中的巡佐,在殖民期间也是香港警察的官衔,推导过程如表2 所示。

表2 还原英译外来词“沙贱”的推导过程
元音[a:],英语和粤语共有,可直接对应,如“France”对译粤语“化兰西”或“化兰士”;粤语元音[i],对应英语元音[ə],如“opium”对译粤语“阿片”,“pium”[piəm]对译“片”[phi:n35]。综合排列后可反推得出对应的外语词“Sergeant”。
2.2.3 破除假借
无论在哪种粤方言文献中,都存有数量相当的同音或近音假借字,这使得大量独具特色的粤方言词语得以书面化表达。在清代粤剧中,音[hɐu55]表“看上”义的词借近音字“吼”,音[sou55]表“理睬”义的词借同音字“苏”表示。但表音性太强,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表意的线索,使读者在阅读方言词时“摸不着头脑”。所以破除假借,对于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是十分必要的。下面以“舌”为例:
(19)《文明结婚·首卷》:“杂货兼油豆,点知又水患。由地搬上楼,呜呼兼哀哉,有气冇地抖,舌了几百银。”(J20:420)
“舌”当为“蚀”。清代粤语韵书《分韵撮要》“蚀”入声审母益韵:“日月之相掩曰蚀。”“蚀”为曾摄字,粤语中曾梗摄字多有文白读之分,《广州话词典》(第2 版):“ 【蚀】xid1(读音xig6)。”①《广州话词典》(第2版)注音凡例第二条:“条目中的字如有读书音和口语音区别的,注音用口语音,读书音另外用‘读音’标明。如‘禁’kem1(读音gem3)。”“蚀”文读为[sik3],与韵书反切相合,白读为[sit2]。“舌”音与“蚀”白读音相同。《分韵撮要》“舌”入声审母屑韵:“口舌。”
又有“舌木货”一词,未载于辞书:
(20)《嫦娥女下凡·上卷》:“噎吔,我估发财招牌原来舌木货,告秉爹爹上面招牌是林婆选婿。”(J23:123)
(21)《十德女诚家·下卷》:(文白)你说道女子是舌木货女子,此话不可乱讲,有的带你一家荣华。”(J20:18)
据上述考据可知,“舌”当为“蚀”之借字,而“木”则由“本”省写而来。清代通俗作品中多省笔俗字,如“诉”俗写为“”、“瓜”俗写为“爪”。“舌木货”实则为“蚀本货”。除了方音的影响,普罗大众的通俗用字习惯也很值得关注。假借字与俗字组合的情况在清代粤戏剧本的书写中并不少见,掌握俗字规律,利用汉语史背景知识也有益于方言词的考释。
2.2.4 考虑分音合音
分音合音古已有之,清人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二中提道:“古人语急,则二字可缩为一字;语缓则一字可引为数字。”《小尔雅·广训》:“诸,之乎也。”王引之注:“急言之曰‘诸’,徐言之曰‘之乎’。”粤方言中也有很多分音成词、合音成字的现象,如“噉”由“个物”合音而来,“寻日”之“寻”由“昨晚”音变后合音而得。联系语流音变的规律,也是考释时很好的切入点。以“举”为例:
(22)《大闹南溪·上本》:“(明白)叫便个老举哑?(罗白)叫六个琵琶仔陪饮,一个大老举过夜,呢十两银拈去开厅办菜。”(J20:180)
(23)《大闹南溪·上本》:“(罗白)大老举有乜新货冇哑?(明白)先几日有两个香港番上,叫唔叫呢?(罗白)唔好。”(J20:180)
“老举”即妓女,《清稗类钞·文言类》:“老举,广东妓女之上乘者。”《切口·粤妓》:老举,妓女也。”《普通话、广州话词汇用法对比词典》:“老举,旧时指挂牌娼妓,‘鸡’指暗娼。”但查《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广州方言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举”的释义,均未发现与“妓女”义相合的义项。对于“老举”的来源主要有两类四说,两类主要为“得名于民间故事”与“得名于音近讹变”,四种说法分别为:
其一,“举”的“妓女”义源于唐代名妓郑举举之名。袁枚在笔记《随园诗话》卷十二中首次谈到该观点:“广东称妓为老举,人不知其义,问士人亦无知者。偶阅唐人《北里志》,方知唐人以老妓为都知,分管诸姬……有郑举举者,为都知,状元孙偓颇惑之。卢嗣业赠诗云:‘未识都知面,先输剧罚钱。’广东有老举之名,殆以此始。”
其二,“举”指粤地妓女举头傲慢状。《晶报》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河下老举大,即妓女之称,其‘举’字……缘粤妓不事迎送,傲慢懈惰,奇物自居,故云。”
其三,“举”“妓”音近相讹。清人张心泰在笔记《粤游小志》中反驳了袁枚的看法:“俗呼妓女为老举,即随园以为举举师师之义。其实举即妓也。”孙橒《余墨偶谈》:“举与妓粤音相近,老举即老妓之讹。”
其四,“举”为“妹”之讹。《中国风俗》:“粤中妓女,向称老举。‘老举’二字不知所取何义。或言老举系老妹之讹,‘妹’者女子也,‘老’者称谓发语之词,犹言老李、老张。”
第一、二种说法都取自民间故事,袁枚的考据并未解释历代名妓之中为何单取“郑举举”之名,《晶报》的解释甚至没有具体的事例,两说疑为流俗词源。将“妓女”称为“老举”仅在粤地常见,可以猜测其得名与方言语音相关,第三、四种说法显然更为可靠。逐一而言,“妹”明母灰韵,粤音[mui35],“妓”属见母支韵,音[kei22],“举”见母鱼韵,音[kɵy35],“妹”和“举”声韵相差较大,“妓”和“举”更为接近。禤健聪(2013)认为“妓”音转为“举”与粤方言“屋居”音转为“屋企”相似,是同一语音关系的反向演变。
笔者认为,“举”可能为“妓”“女”二字的合音。从语音上看,“妓”是见母止摄开口三等平声字,与“女”的韵母结合为[kɵy35],读同遇摄三等上声字“举”,声韵调皆符合,前加“老”为词缀,以此形成“老举”。对于此类非正当交易,人们碍于情面不直接道明,分音合音再造是一种很好的委婉表达。与此相似的还有“皮条”一词,由“嫖”分音而成,同见于清代粤剧,试举一例:
(24)《火烧大沙头·卷一》:“(泊艇河边埋位唱)沙艇做埋皮条婆(白)我叫做皮条金,每日送客开埋大沙头,兼做皮条艇。于今天色近晚,坐在舟中,等吓个班外江佬开嚟叫艇罢咯。”(J20:45)
2.3 区分字义,处理关系
字形相同的粤方言字在粤戏刻本中比比皆是,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根据它们的意义来厘清关系:如果意义皆不同,很可能只是同形偶合;如果意义之间有关联,就需要进一步厘清本义和引申义。然后再辅以字书保存的字义信息为突破口,逐层抽丝剥茧,才能更好地处理同形字问题,挖掘字形偶合的规律。下面以清代粤剧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为例分析:
(27)《正德下江南》:“(梁白)甚么?讲万岁下江南去了?(众白)不错,前几天,江宾诱他去了。(梁白)吔吔,不好了。”(J20:159)

3.总结
笔者在考释粤方言疑难字时,最深切的体悟是要做到两个“结合”:首先是将汉语史与方言学的学科知识结合起来,方言字的产生与方音和通俗用字习惯都密切相关,故其内部语音系统的规律与外部的字形证据都需结合进行审视。其次是将共性的考释原则与方言的个体特色结合起来,各种语言学理论并非对每种方言都具有适用性,了解所考释方言的历史文化背景,把握关键矛盾,才能更加敏锐地发现线索。希望本文对于揭示方言文献疑难字的性质和俗文字学的理论建设有小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