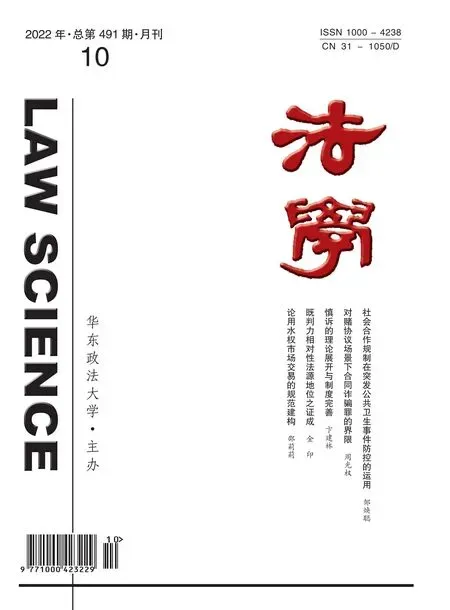遗嘱信托的规范构成与体系效应
2022-12-01张永
●张 永
一、问题的缘起
遗嘱信托是指委托人预先以遗嘱的方式,将包括交付信托后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在内的财产规划内容详订于遗嘱中,待遗嘱生效时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遗嘱的内容管理信托财产。〔1〕我国《信托法》上没有“遗嘱信托”的法定概念,《日本信托法》第3条关于信托第二种设立方式之规定可资借鉴,即委托人订立一份遗嘱,将财产转移给特定的人,授予财产担保权或者允许为其他处分,由其按照确定的目的管理、处分该财产,并实施为实现该目的所必要的行为。另外,有日本学者认为,遗嘱信托使受托人取得了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而受益人则拥有向受托人要求以支付遗嘱信托利益为内容的债权,即受益权。参见日本东洋信托银行:《日本银行信托法规定与业务》,姜永砺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遗嘱信托具有与遗嘱继承、遗赠相似的属性,〔2〕参见张平华:《遗嘱信托是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62页。例如遗嘱信托是单方法律行为、死因行为与要式行为。与遗嘱继承、遗赠不同的是,遗嘱信托具有高度灵活性、〔3〕参见葛俏:《我国继承法遗嘱信托制度构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强资产隔离性与持久性。遗嘱信托的成立与生效必须满足信托成立与生效的一般要件。例如,在“曾某甲与李某遗嘱继承纠纷案”〔4〕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4)临民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民一终字第266号民事判决书。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其遗嘱信托内容过于简单,信托财产、受益人无法确定,该信托不生效。〔5〕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申392号民事裁定书。
遗嘱信托具有许多传统财富传承制度无法实现的功能,在英美法系中是主要的信托形式之一,〔6〕参见[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2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457页。比较典型的如戴安娜王妃的遗嘱信托、迈克尔·杰克逊的遗嘱信托等。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也有诸多运用场景。〔7〕常见的遗嘱信托适用场景,例如保障配偶生活需要的信托、未成年人利益信托、浪费者信托、兼顾配偶生活与慈善事业的信托等。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565页。其一,遗嘱信托可避免后位继承的风险。例如,甲可通过遗嘱信托约定其父母和儿子为遗嘱信托的受益人,但其父母去世则受益权全归属于甲的儿子,从而避免后位继承风险。〔8〕参见张平华:《遗嘱信托是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63-164页。其二,相对于遗嘱继承,遗嘱信托具有强大的资产隔离功能。在上例中,甲的儿子只是作为受益人,信托财产不构成甲的儿子的责任财产,未来不得强制执行。其三,遗嘱信托可使立遗嘱人的遗愿贯彻得更加彻底和长远。即使立遗嘱人已身故,其遗愿依然可在信托财产的管理、使用、分配中发挥作用,并对受益人作出行为引导。例如,若受益人考上知名大学,则由受托人支付一定的奖励金;若受益人成年后每跑完一次马拉松,则可获得相应的运动奖励。因而,西方有法谚曰:遗嘱信托是死者从坟墓中伸出的手。〔9〕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沈朝晖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170页。其四,遗嘱信托兼顾财产转移与财产管理,具有明显的造血功能,〔10〕参见张永:《慈善信托的解释论与立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诺贝尔基金就是典型。正因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组合投资、分散投资,信托财产得以不断保值、增值,〔11〕See Witmer v. Blair, 588 S. W. 2d 222(Mo. App. 1979).进而使得立遗嘱人能够更加持久地支持某项信托目的,例如慈善事业、〔1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申5415号民事裁定书。对亲戚的长久照顾。〔13〕参见林奇:《信托遗嘱与公证》,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7期,第75页。其五,对遗嘱信托的受益人原则上没有限制,〔14〕《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函〔2018〕37 号)规定,家族信托受益人只能是委托人的家庭成员,考虑到家族信托属于典型的民事信托,与具有资管产品性质的信托产品不同,这种限制的合理性是存疑的。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立遗嘱人可指定任何人为遗嘱信托受益人。〔15〕参见宋刚:《关于遗嘱信托的几点思考——以继承法修改为背景》,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73页。
据悉,目前在国内有效成立的遗嘱信托并不多见,法院对遗嘱信托整体上依然是陌生的,相关法条也基本上处于“死法”的状态。例如,在号称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的“钦某某、李某1与李某5、李某6、李某7遗嘱信托纠纷案”中,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就认为遗嘱信托在我国较为新颖,缺少先例。〔16〕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30894号民事判决书。鉴于此,遗嘱信托相关规范的解释有待深入研究,诸如遗嘱信托何时生效、形式要件对遗嘱信托生效的影响、受托人缺位对遗嘱信托生效的影响、财产登记对遗嘱信托效力的影响、能否突破特留份的限制、信托受益权约定移转限制的对外效力、信托资产隔离效力与债权人保护的关联、债权人撤销权与有限继承的关联等问题正是本文着力研究的议题。
二、遗嘱信托成立与生效的影响因素
(一)遗嘱信托成立与生效的形式要求
我国《信托法》第13条规定,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民法典》第1134-1139条明确规定了遗嘱成立的七种形式。《民法典》新增的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等形式是基于技术进步而为立遗嘱人提供更多选择的考虑。〔17〕参见杨立新:《中国民法典释评·继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页。但《信托法》第8条又规定设立信托应采取书面形式。由此,遗嘱信托的成立是否必须满足书面的形式要件即发生矛盾。对此,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信托法》第8条对信托成立形式的规定是特别法,而《民法典》第1134-1139条属于一般法,应将录音录像遗嘱排除出去。二是《民法典》作为新法以及民事领域根本大法,代表最新立法政策,而《信托法》则生效于2001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第一种解释路径无视最新的立法精神,有“刻舟求剑”之嫌。本文认为,应放松对遗嘱信托的形式限制,赋予委托人更多的选择自由,便于设立遗嘱信托,因此遗嘱信托不应局限于书面形式,在上述两种解释路径中以后者为宜。
第一,从历史解释来看,《信托法》生效于二十多年前,当时对遗嘱形式的认知局限于原《继承法》的规定。比如,当时对录音录像遗嘱的认知不足,但时至今日手机等便携式设备非常方便且功能强大,相关的视频资料极易获取且储存方便,录音录像甚至更能再现事实的原状,包括具体细节,作为遗嘱信托的表现形式足够胜任。〔18〕参见和丽军:《民法典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65-166页。需要担心的是这类遗嘱易面临被篡改的危险,因为相关的视频编辑技术极为发达,造假成本较低。可考虑由比较权威的、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遗嘱保管。
第二,从目的解释来看,法律要求某一法律行为须采用特定的形式,往往是着眼于以下三种功能:(1)警示功能;(2)证据功能〔19〕Vgl. Hans-Martin Pawlowski,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5. Aufl., 1998, S. 181.;(3)咨询功能〔20〕Vgl. Dorothee Einsele,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5. Aufl., 2006, § 125 Rn. 70-72.。就书面形式的要件而言,一方面当事人虽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但已履行了相关义务,其实际履行行为通常表明已对此法律行为予以慎重考虑,履行之事实发挥了与书面形式类似的警示功能。另一方面,在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已履行有关义务的情况下,通常即可认定存在法律行为,有争议的只是法律行为的细节方面。此时法律行为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若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的主要内容,则不能再以缺乏书面形式为由将法律行为判定为不成立。〔21〕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1页。
第三,从比较法解释来看,英美衡平法更重视意图而非形式。最关键之处在于是否有确定的设立信托的意图或意思,至于是否采用了特定的形式则无足轻重,因为形式要求的目的也是为了方便查明是否有确定的设立信托的意图或意思。追根溯源,英美法采用遗嘱信托的主要目的就是规避关于遗嘱法定形式的繁琐要求。我国法上虽然不存在英美法上那么繁复的遗嘱形式要求和遗嘱检认(probate)制度,〔22〕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沈朝晖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但像《信托法》这样普遍规定书面形式的要求比《民法典》继承编更加严格,会极大限制遗嘱自由。〔23〕参见赵廉慧:《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探析》,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8期,第82页。
第四,从体系解释来看,《民法典》第490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基于法律要求书面形式的目的考量的相似性,在遗嘱信托情形,虽采用录音录像的遗嘱形式,但部分遗产已转移到受托人名下,甚至受托人已开始运营、管理,此时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90条。〔24〕参见赵廉慧:《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探析》,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8期,第83页。
第五,从实际操作来看,若过于限制遗嘱信托的形式,将对立遗嘱人的行为自由形成困扰。例如,对于遗嘱继承、遗赠、遗嘱监护等,当事人采用录音录像的遗嘱形式没有障碍,但对遗嘱信托则必须再采取打印遗嘱、公证遗嘱等书面形式。若认可录音录像遗嘱可设立信托,本来一份遗嘱就可以解决。
(二)遗嘱信托成立与生效的时点
《信托法》第8条规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在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该法第13条又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230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可见,我国法关于遗嘱信托成立与生效的规定整体上是混乱且自相矛盾的,〔25〕参见伍小美:《浅谈中国信托法的缺陷——从信托的生效要件到信托所有权归属谈起》,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74页。存在立法的碰撞性漏洞。〔26〕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页。
按照《信托法》第8条,采用其他书面形式的信托自受托人承诺时成立。还有学者折衷地认为,若受托人的承诺是立遗嘱人死亡前作出的,信托自立遗嘱人死亡时生效;若受托人的承诺是在立遗嘱人死亡后作出的,信托自受托人承诺时生效。〔27〕参见王清、郭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条文诠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本文对此持反对意见。首先,遗嘱作为无相对人之单方法律行为,一旦做成就应立刻成立,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诺,否则难与双方法律行为相区分。《信托法》第8条规定遗嘱信托还需要受托人承诺才能成立,显然是以信托合同的要约、承诺之成立方式作为立法参照系,混淆了遗嘱与合同。〔28〕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30894号民事判决书。该条尾句要求满足受托人承诺这一成立要件,对遗嘱信托来说实属画蛇添足,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无端惹出许多法律适用麻烦。〔29〕参见周勤:《信托的发展与展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其次,在比较法上,无论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各国都适用遗嘱法或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信托均自遗嘱生效时起成立并生效。〔30〕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最后,通过遗嘱设立信托,在遗嘱成立时,由于遗嘱信托还没有信托财产,此时谈不上信托成立与生效。仅在立遗嘱人死亡时,遗嘱作为死因行为才立刻生效,遗嘱信托方成立与生效,信托财产也立刻确定。
(三)受托人缺位对遗嘱信托生效的影响
受托人缺位并不影响遗嘱信托生效。首先,在比较法上,英美信托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信托不因为缺乏受托人而不成立、不生效,〔31〕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即使受托人不存在、拒绝受托、中途丧失行为能力、破产倒闭等,衡平法不允许信托因缺乏受托人而无效。〔32〕参见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日本信托法》第4条第2款也规定遗嘱信托自遗嘱生效时生效,即使被指定的人没有表示接受的意思或拒绝接受,甚至遗嘱根本没有明确指定受托人,遗嘱信托依然成立,受托人接受信托的,应溯及至立遗嘱人死亡也即遗嘱生效之时生效。〔33〕See Edward C. Halbach, Jr., Gilbert Law Summaries on Trusts, Thomas/West, 2008, p. 82.其次,基于目的解释,若认为此时遗嘱信托不生效,则原本用来设立信托的财产将根据一般的继承规则归入法定继承,如此处理显然没有最大程度地尊重立遗嘱人的遗愿。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应将遗嘱信托的生效时点确定为遗嘱的生效时点,遗产立刻全部或部分转化为信托财产,从而受信托关系的约束。再次,我国现行法也确立了信托存续原则,《信托法》第40条对此作出具体规定。〔34〕参见葛俏:《我国继承法遗嘱信托制度构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该书认为,若依据《信托法》第13条无法产生受托人,则信托不成立。本文则认为在解释论上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146条,在立法论上可赋予法院指定受托人的权力,不应轻易地让信托失败。在立遗嘱人身故时,遗嘱信托没有指定受托人或者受托人拒绝担任与此种情形相仿,应当坚持“相似事物相似处理”的原则,而不宜轻易否定遗嘱信托的效力。最后,在实际操作上,若遗嘱信托生效时指定的受托人拒绝受托,或者此时已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且遗嘱明确规定了受托人补选规则,则按照遗嘱条款处理。若遗嘱没有明确规定相关补选规则,则适用《信托法》第13条第2款予以处理,且新受托人的资格溯及至立遗嘱人死亡时。
(四)受托人产生机制
受托人缺位虽然不影响遗嘱信托效力,但是遗嘱信托的运营终归离不开受托人,因此必须使受托人尽快产生,立法上也必须有适当的受托人产生机制,以确保在受托人缺位时及时补位。遗嘱信托与合同信托的重大区别在于,后者是由委托人、受托人双方协商而成,双方在信托合同上签字、盖章即可,而前者是死因行为,其指定的受托人可能不愿做受托人,或可能出尔反尔、事后反悔。〔35〕有人认为应当将生前信托(合同信托)与遗嘱信托一视同仁,均可由法院指定受托人,这种看法无视合同与遗嘱的不同,违背“不同事物不同处理”的原则。参见周玉华:《信托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97页。
我国《信托法》第13条规定了受托人缺位的递补制度,但从实务角度讲,为了避免上述麻烦,立遗嘱人宜在立遗嘱时就与意向中的受托人充分讨论、协商,建立互信,甚至由受托人作出书面承诺或做成公证文书。即便如此,依然会出现受托人事后丧失行为能力、意外死亡、破产等情形以及受托人缺位问题,因此《信托法》第13条仍有意义,但亦有不足之处。
从目的解释看,《信托法》第13条允许受益人指定受托人有所不妥。立法者的本意可能是此时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主体作出指定,但考虑到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角色定位,受益人很可能指定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受托人,由此导致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制衡关系失效,〔36〕See Lusina Ho, Trust Law in China, Sweet & Maxwell Asia, 2003, p. 81.而事实上受托人与受益人的彼此制约是信托的重要一环。〔37〕参见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2017)豫1521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5民终4342号民事判决书。《信托法》没有规定法院指定受托人的机制,立遗嘱人宜在遗嘱中明确受托人的遴选机制,或指定多个受托人以备不测。〔38〕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33419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1307号民事判决书。这是国内首次以司法判决确认遗嘱信托的财富传承方式。遗嘱中虽未出现“遗嘱信托”字样,但法院认为其符合遗嘱信托的全部要件,确保了信托财产安全,而且委托人指定了多个受托人,使委托人的真实想法得以贯彻。
从尊重立遗嘱人遗愿的角度看,在有些情况下由受益人指定受托人可能会明显违背立遗嘱人的意思。例如,立遗嘱人特别信任其指定的受托人或有其他特殊考量,在遗嘱中指明若被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或不能担任受托人,信托不成立,信托财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对此显然应严格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思,受益人无权指定受托人。
从实际操作看,若遗嘱未规定受托人,也未规定其相关遴选机制,按目前规定由受益人指定,可能会存在受益人较多且彼此有利益冲突的情形,如何协调受益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这与常见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不同,〔39〕参见《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1号)第七章。遗嘱信托是典型的他益信托,同一个遗嘱信托可能有多个受益人,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选出大家都认可的受托人可能会旷日持久。另外,尽管《信托法》第13条规定了多层次的受托人遴选机制,但依然不能穷尽极端情况。
从比较法来看,各国信托法均承认以下两点。首先,若遗嘱指定了候选受托人或规定了指定候选人的方法,应当按照遗嘱的规定指定新受托人。其次,遗嘱未作规定的,英国信托法规定由法院指定。〔40〕英国《1925年受托人法》第41条规定,只要法院认为指定新受托人是适宜的,或者没有法院的协助就很难或无法指定新受托人,法院就可以发布命令指定新受托人,以替代现有受托人或增加新的受托人。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在英美法上,受益人永远也不能指定受托人。在信托文件没有规定相关受托人产生机制或离任的受托人未指定新受托人的情况下,法院有权指定受托人。〔41〕See The Trustee Act 1925 of England and Wales, s. 41; Th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rusts (1959), § 108.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移植了上述英美法规则,由信托当事人申请法院指定受托人。〔42〕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日本信托法》第5条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催告制度,即遗嘱条款指定特定的人为受托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催告遗嘱指定的人在期限内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信托,但遗嘱如果设定了先决条件或生效时间,利害关系人只有在该条件成就或设定的时间到来后才能提出要求。该法第6条规定了法院指定受托人的权力,即若遗嘱中没有指定受托人的条款,或遗嘱指定的受托人未能或不接受信托,法院可依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指定受托人。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46条也规定遗嘱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或不能接受信托的,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得声请法院选任受托人,但遗嘱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
我国信托法上没有利害关系人催告制度以及法院指定受托人的制度,为补充这一法律漏洞,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一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146条,其根据在于遗产管理人与受托人都是信义关系中的受信人,两者地位相似,都负有严格的信义义务,要为死者处理身后遗产分配等相关事宜,可以本着“相似事物相似处理”的原则予以类推适用。在英国1983年发生的“Re Speihgt案”中,法官认为在现代社会,法院已不再区分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和受托人,其依照同样的原则承担责任。〔43〕转引自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法院既然可应继承人的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应当也有权力应遗嘱信托受益人的申请乃至在必要时主动指定遗嘱信托的受托人,以免问题久拖不决。二是充分挖掘《民法典》第1147条第6项的解释空间,扩展该兜底性规定的适用范围,将指定遗嘱信托的受托人纳入“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如此解释完全没有障碍,况且依然在其文义解释的射程之内,充其量属于扩大解释,无需舍近求远地运用类推适用及目的性扩张等法律续造方法,因而更具说服力和正当性。在立法论上有必要在修订《信托法》时明确规定受益人催告制度以及法院指定受托人的权力。〔44〕参见徐卫:《遗嘱信托受托人选任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3期,第84页。
三、信托财产登记的效力
通过法律行为实现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通常须以登记作为公示手段,尤其是合同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登记往往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即不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民法典》第209、214条)。至于非通过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例如基于继承发生的物权变动自继承发生时发生效力,即此时立刻发生物权变动,作为遗产的不动产登记与否仅会影响后续处分的效力(《民法典》第229-232条)。但遗嘱信托的财产登记效力如何?是设权登记还是仅具对抗效力,抑或只是对既有物权变动的外部宣示?《民法典》未予直接规定,能否直接适用第230条也存在争议。我国法上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信托法》第10条。然而,该条第2款“不补办(登记)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之规定的解释是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认为,对遗嘱信托仍应坚持与《民法典》及主流民法理论保持一致,遗嘱信托自立遗嘱人去世时生效,此时相关财产尤其是需要登记的不动产即刻变为信托财产。现以下例予以说明:假设立遗嘱人于2018年1月1日去世,但其拟设立信托的房产直至2018年5月1日才登记于受托人名下(例1)。按《民法典》第1121条,2018年1月1日遗嘱已生效,根据《信托法》第13条第1款,遗嘱信托应于2018年1月1日生效;但按照《信托法》第10条第2款,该信托于2018年5月1日才生效。那么,在2018年1月1日至5月1日此段期间应如何处理该房屋呢?可能的方案有两个:一是将其作为法定继承财产并予分割;二是将其作为无主财产,可能会收归国家所有。
上述两种处理方案显然都不符合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因为立遗嘱人就是要将该房屋纳入信托财产,至于该房屋何时能够登记是立遗嘱人无法左右的。若按《信托法》第10条处理,财产须经登记才发生信托效力,则该笔财产在登记前都不是信托财产,就面临被作为法定继承财产处理甚至收归国有的风险,不仅与社会实际不符,而且难以有效保护受托人、受益人。〔45〕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6页。本文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显然不妥,毕竟被继承人死亡,遗产何去何从应尽快确定,不能坐等遗产登记完毕或交付完成。〔46〕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3页。这也从侧面显示了《信托法》第10条第2款与第13条第1款存在冲突。
于此,应回归遗嘱信托的遗嘱本质,即遗嘱信托自立遗嘱人去世时生效,与作为信托财产的不动产、股权是否办理登记无关,因为遗嘱是死因行为,与生前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不同。《民法典》第230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遗嘱信托和遗嘱继承本质上都是因继承而发生物权变动,继承人即刻取得遗产所有权,受托人也即刻取得信托财产所有权,只不过在遗产分割前表现为共同共有状态。
那么,《民法典》第232条中的登记该如何理解呢?根据文义解释,此处的登记显然与《信托法》第10条中的登记不同,后者对信托生效与否有影响,而前者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仅影响新权利人后续对财产处分的效力。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232条中的登记在性质上属于“宣示登记”,不同于该法第209条第1款中的“设权登记”。〔47〕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8页。在例1中,信托于2018年1月1日生效,5月1日的房产登记仅影响受托人对该房屋后续处分的效力。
作为不动产的遗嘱信托财产的过户登记需要与基于信托合同的信托财产登记区别开来,根本原因在于遗嘱信托是单方法律行为、死因行为,而后者是双方法律行为,多是交易行为,若涉及物权变动,理论上以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作为分析工具。〔48〕关于这一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319页。我国制定法上则确立了区分原则,《民法典》第215条明确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信托法》第8条第3款第1句,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签字、盖章时,信托成立。根据《民法典》第502条,依法成立的信托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委托人应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受托人并办理完毕必要的登记手续,信托才能成立,即区分信托合同的成立、生效与信托的成立、生效。
综上,在合同信托的情形,应尊重《民法典》第215条的区分原则,信托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基础是《信托法》第8条第3款第1句和《民法典》第502条,而信托成立与生效的依据是《信托法》第10条,如此方能与《民法典》的立法政策保持一致,也可与遗嘱信托区分开来。作为不动产的信托财产的过户登记仅是宣示登记,而非设权登记,对此不能以《信托法》第10条作为基础,在解释论上应当以《民法典》第230、232条作为依据。
四、信托受益权移转限制约定的对外效力
无论是在遗嘱信托还是在家族信托〔49〕关于家族信托的界定,参见《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函〔2018〕37号)。等生前信托中,委托人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对信托受益权作出各种限制,但信托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往往无从知晓该种内部限制,尤其在我国信托登记制度极不完善时更是如此。善意第三人在与某一信托受益人进行受益权移转的交易时,极可能遭遇不测,于是这种受益权移转的内部限制能否对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生效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现行立法及司法实务立场
我国《信托法》对信托受益权移转限制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47、48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95条第2款也予重申。《信托法》第47、48条有利于充分贯彻立遗嘱人的意志,是对立遗嘱人遗愿的最大尊重,同时有利于保护信托受益人,以免信托财产外流。相关司法实践也严格遵从《信托法》的规定,认定通过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受益权转让限制的条款具有绝对效力。例如,在“上海翌银玖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晨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均认可此类禁止转让特约的法律效力。〔50〕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1003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民终422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新华锦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财产权属纠纷案”中,法院认为:“2004年7月27日《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违背了信托受益权不得分割转让的约定,但2004年9月10日的《补充协议》约定将所有受益权进行转让,对其内容进行了修正,应当视为双方约定将受益权进行全部转让。”〔5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有学者认为若无该后续协议,违背最初的转让限制约定进行转让是无效的。〔52〕参见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467页。
实际上,我国《信托法》第47条中的“法律、行政法规……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是无的放矢,因为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均无明确限制信托受益权清偿债务的除外规定。〔53〕目前明确对信托受益权转让予以限制的只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1号)第29条,但该管理办法只针对营业信托,对民事信托没有适用空间,且在位阶上只是部门规章。日本的信托法专家能见善久认为具有人身属性的受益权基于其特殊性质不能转让,例如以抚养特定受益人为目的的信托(特别是抚养残疾人、老人等的信托)是为了保护特定的人而授予的受益权,原则上具有人身属性,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54〕参见[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在英美法中,法律也禁止保护信托和浪费者信托中的受益权转让。〔55〕关于保护信托,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7页。关于浪费者信托,参见张淳:《信托法原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现以下例予以说明:若A将B及B的儿子D(小学生)列为受益人,则该信托受益权属于D的个人财产(例2)。我国《民法典》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B及其妻子C作为D的法定监护人不得随意转让D的受益权以清偿债务,否则构成权利滥用。
问题的关键是《信托法》似乎忽略了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至少在文义解释上如此,由此构成开放的法律漏洞。在例2中,A在遗嘱信托中规定B的信托受益权不能转让,不能用来清偿债务,这虽然有利于保护信托财产安全,但可能对B的债权人S极为不利。在B逾期不清偿债务时,S原则上当然可要求B以受益权清偿债务,或者B转让受益权给善意第三人X以获得清偿能力。但后来查明B的受益权根据遗嘱不能转让,也不能用来抵债,此时S、X就比较被动。尽管S、X可主张B因隐瞒真相构成欺诈,并请求撤销合同,但如此只能主张B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而请求信赖利益赔偿,而不能基于违约责任主张履行利益赔偿,这对S、X很不公平。
(二)比较法立场
尽管日本法上对信托受益权的属性有债权说、物权说及新型权利说等不同见解,〔56〕从《日本信托法》第2条的表述来看,信托受益权是一种债权。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信托受益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参见葛俏:《我国继承法遗嘱信托制度构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但各国法对财产权应具有可流转性却存在共识。〔57〕《德国民法典》第413条明确规定,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准用于其他权利的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日本信托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受益权流转限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20条同样规定信托受益权之让与准用其“民法”第294-299条之规定,由此信托受益权转让限制之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英美法上同样存在对受益权移转限制约定的外部效力之质疑,普通法对其转让限制持强烈的厌恶态度,基本的逻辑是任何资产都具有可转让属性,信托受益权也是一项资产,有何理由不得转让而享有特殊待遇呢?〔58〕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沈朝晖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
(三)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出路
我国《信托法》第47、48条欠缺“信托条款的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表述,在市场交易中可能对善意第三人不利。此处的第三人不管是受益人的债权人还是受益权的受让人都涉及交易安全,《信托法》这一立法政策的正当性不足。
首先,从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的基本属性可知,债具有相对性,内部约定不能产生对外效力。虽然遗嘱与合同不同,立遗嘱人与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与合同关系不能完全等同,但在相关条款的内部性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因为这些条款均没有规定相应的公示手段,外部人难以察觉信托受益权上存在限制从而可能被相关限制条款突袭。《信托法》第47、48条的规定显然与《民法典》第465条的立法精神相冲突,也有违保护善意第三人与交易安全的价值追求。
其次,基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禁止或限制流转的内部约定如无适当的公示手段,都不应发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无论受益权让与限制还是债权让与限制都是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43条第2款即明确规定,若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抵押期间抵押物禁止转让,则该约定仅具有内部效力,但若已登记公示,则可对抗抵押物买受人,使其不能取得抵押物所有权。
最后,《民法典》第54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受益权是指受益人按照信托文件定期或不定期取得信托利益的权利,具有相对性、请求力、执行力及保持力,这种信托利益在多数情形下表现为金钱利益。因此,受益权是具有金钱属性的财产权,而且原则上可以流转,虽然目前包括营业信托在内依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信托受益权交易平台,〔59〕目前《信托登记管理办法》(银监发〔2017〕47号)及《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管理细则》基本上未涉及信托受益权流转及相关登记问题,相较于其他资管产品,信托受益权的流通性比较差。但也没有理由禁止民事信托中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受益权流转。对于遗嘱信托受益权流转限制条款的对外效力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45条。
五、遗嘱信托的资产隔离效力与债权人保护
遗嘱信托是信托的一种,而信托的本质是资产隔离,《信托法》第15、16、17条以及《九民纪要》第95条均重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此即信托财产的“闭锁效应”。〔60〕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实务》,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0页。信托财产虽在形式上归受托人所有,但不是受托人的责任财产。对委托人来说,信托财产根本不在其名下,信托财产自信托生效之日起就不再是委托人的责任财产。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没有受益权之外的任何权益,信托财产不构成受益人的责任财产。〔61〕参见耿利航:《信托财产与中国信托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第96页。如何协调遗嘱信托的资产隔离效力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
(一)遗嘱信托的资产隔离效力弱于生前信托
遗嘱信托作为一种死因行为,与生前信托有所不同,根本原因是在前者被纳入信托的是立遗嘱人的遗产,即立遗嘱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在后者被纳入信托的是生前财产。现以下例予以说明:在某家族信托中,委托人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将2000万元资金纳入信托,只需双方签字、盖章且将2000万元资金转入信托专户,信托即成立并生效(例3)。若在3年后,委托人负债5000万元,其债权人不能申请强制执行该笔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依然可享受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托利益,这就是信托资产隔离所具有的避债功能。同理,若委托人去世时负债累累,但由于其在生前财务状况良好时已合法设立了家族信托,则其子女作为信托受益人也不必偿还委托人的生前债务,更不能用信托财产偿还委托人的生前债务,因为2000万元的家族信托在委托人生前就已成立并生效,且已从委托人责任财产中剥离出去,已非委托人的遗产。
但遗嘱信托与家族信托不同,后者是生前行为,前者是死因行为,须等到立遗嘱人死亡时才生效。这意味着在逻辑上的一秒钟,遗产的一部或全部被纳入信托,成为信托财产。以例3中的2000万元为例,若其属于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则在立遗嘱人生前存在大额未清偿债务的情形,债权人可依据《信托法》第12条申请法院撤销该信托,从而击穿遗嘱信托。
对于受益人已凭借受益权获得的信托利益应区分对待。若受益人知道立遗嘱人生前负有大额债务未清偿,则债权人可追及该笔信托财产;若受益人为善意,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立遗嘱人生前有大额债务一直未清偿,则法院撤销信托不应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其法律依据为《信托法》第12条第2款。〔62〕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可能要受到严格限制。因为债权人撤销信托虽然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取得的信托利益,但受益人的受益权仍受影响,即使受让受益权的投资者是善意的,其受益权也会受到影响,结果是可能导致这类业务难以开展。所以,日本在2006年修订信托法时重新规定,若受益人是善意的,委托人的债权人就不得撤销信托。我国制定法上没有类似规定,此时若要限制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只能求助于《民法典》第132条。
若将来开征遗产税,由于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也是遗产,则该笔财产应为纳税对象,而生前成立并生效的家族信托则能合法规避这一税收负担。因此,与生前信托尤其是家族信托相比,遗嘱信托的资产隔离属性稍弱,立遗嘱人生前的债权人可依据《信托法》第12条撤销信托,将相应的信托财产纳入立遗嘱人的责任财产。
(二)债权人撤销权与有限继承之关联
在立遗嘱人企图以设立遗嘱信托的方式诈害债权人时,债权人可依据《信托法》第12条撤销遗嘱信托,从而使资产隔离失败。但在遗产上存在未清偿债务的情形,《民法典》第1163条亦有适用余地。因此,与遗嘱信托资产隔离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
在例3中,若立遗嘱人去世前仅有这2000万元个人合法财产,且完全被纳入信托,子女是信托的受益人。受托人在立遗嘱人去世3年后才知道其生前负债5000万元,此时债权人要求偿债。由于并非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与遗赠,无法适用《民法典》第1163条,债权人可能的救济途径是《信托法》第12条,即先撤销该遗嘱信托,再按照《民法典》第1159条处理。
如果情形稍微复杂,即立遗嘱人除了2000万元的遗嘱信托外,尚有3000万元通过遗嘱继承给予其子女,还有1000万元遗赠给其侄子,另有1000万元遗嘱没有涉及。此时,原则上应按《民法典》第1163条之文义处理,不宜先适用《信托法》第12条撤销2000万元的遗嘱信托。
其逻辑在于《信托法》第12条所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的一个核心要件是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足,却仍然企图通过设立信托隔离资产,使自己陷入“无资力”而逃避债务,〔63〕参见崔建远:《论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第142页。所以仅在债务人没有其他足够的财产偿债时,债权人才有可能依据《信托法》第12条请求撤销信托。〔64〕为使判断委托人是否意在逃避债务更加客观,甚至有加害推定之制度,目的在于减轻债权人的举证负担。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6条规定:在信托成立后6个月内,委托人或其遗产受破产宣告的,推定设定信托的行为害及债权。在这个法定期限内,委托人的债权人无需承担举证责任即有权申请法院撤销信托。在依据《民法典》第1163条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吐回”的遗产即可偿债的情况下,《信托法》第12条不予适用,即《民法典》第1163条优先于《信托法》第12条适用。如果立遗嘱人生前欠债6000万元,则上述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部分显然不足以偿债,此时尚存1000万元债务待清偿,债权人当可依据《信托法》第12条请求撤销该遗嘱信托。但此处的撤销应有所限制,因遗嘱信托财产有2000万元,只需要撤销其中的1000万元,没有必要全部撤销,即部分撤销。
我国相关民法理论及《民法典》没有部分撤销制度,在解释论上有两种路径可以证成。一种是对《民法典》第156条进行扩大解释,即无效既包括自始无效,也包括因撤销而溯及既往地无效,由于《民法典》第155条赋予无效和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完全相同的法律效果,基于“相同事物相同评价”的原则,这种扩大解释在方法论上有坚实的基础。〔65〕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63-464页。
另一种路径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40条,该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认可部分撤销。《民法典》第538-542条与《信托法》第12条均针对债权保全问题,其实质构成要件均为债务人以各种手段逃避债务,使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通过设立信托使相关财产由债务人名下转移到受托人名下,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同样会使债务人陷入无资力,同样会使得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两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完全满足类推适用条件。虽然财产由立遗嘱人名下转移到受托人名下只是形式上的所有权转移,与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转移不同,但由于是受益人实际享有信托利益,尤其在遗嘱信托生效的情况下立遗嘱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受益人,相关财产利益将通过信托这一管道输送给各个受益人,债权人的债权在债务人责任财产本就不足的情况下就更难以实现。从经济效果上看,遗嘱信托与《民法典》第538条中“无偿转让财产”的本质完全相同,只不过实际取得利益的不是常见案型中的受赠人,而是遗嘱信托的受益人,这也是英国法将受托人所有权称为普通法所有权,而将受益人受益权称为衡平法所有权的原因。〔66〕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三)债权人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
在立遗嘱人的债权人根据《信托法》第12条行使撤销权时有一个争议问题,即其除斥期间应从何时起算。现以下例予以说明:若立遗嘱人2018年2月1日设立遗嘱信托,其债权人2018年3月1日就知晓此事,而且有证据证明立遗嘱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就是损害债权人利益。立遗嘱人于2020年11月1日死于新冠肺炎(例4)。则债权人何时可依据《信托法》第12条请求撤销该遗嘱信托,即该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是哪一天?
结合《民法典》第538条的文义,可能的解释方案有两种:一是从2018年3月1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超过2019年3月2日则撤销权消灭;二是从2020年11月1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超过2021年11月2日则撤销权消灭。
本文赞同第二种方案。从学理解释看,撤销只针对已生效法律行为,对于已成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只能撤回,不能撤销。由于遗嘱信托是通过遗嘱设立的信托,而遗嘱属于死因行为,在立遗嘱人死亡前遗嘱只是成立,而未生效,其随时可能被立遗嘱人依据《民法典》第1142条撤回,所以债权人对未生效的遗嘱信托不能主张撤销。
基于目的解释,不管行为本身表现为减少积极财产,如让与所有权、设定他物权、免除债务,还是表现为增加消极财产,如新负担债务,只要使债权不能得到满足,债务人的行为即足以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67〕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7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页。在例4中,在2020年11月1日之前,由于遗嘱信托未生效,相关财产依然是立遗嘱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发生物权变动,也没有产生受托人的请求权,并没有损害债权人的债权,不满足《信托法》第12条的前提条件。
基于文义解释,如此处理也与《信托法》第12条的表述不冲突。既然遗嘱信托虽成立但未生效,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外溢,不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则仅仅成立但未生效的遗嘱信托不构成该条所规定的撤销原因。只有因立遗嘱人死亡而生效的遗嘱信托才是该条规定的撤销原因,因此债权人于债务人死亡之日及以后知道该撤销原因的,撤销权才可以行使,相应的除斥期间才开始计算。
除了除斥期间对该撤销权的限制外,对于某些意在履行特殊法定义务的遗嘱信托能否主张撤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日本学者认为此时债权人不能主张撤销,否则构成权利滥用。若某人设立遗嘱信托,将与前妻共同生活的幼儿作为受益人,目的在于履行作为父亲应当承担的给付抚养费的义务,且信托财产的价值对抚养费而言没有明显超出,则即使委托人在设立信托后一年内“破产”或者其财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也不应当撤销信托。〔68〕参见日本学者2000年11月在我国有关单位召开的信托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这种处理在价值衡量上有其道理,值得借鉴。在解释论上可借助于我国《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或对《信托法》第12条进行目的性限缩,将这种情形排除于可撤销的情形之外。
六、遗嘱信托的资产隔离效力与特留份的关联
资产隔离意味着纳入遗嘱信托的财产只能由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从中获益。如此,需要特殊照顾的利益相关者被信托排除在外时,有关特留份法律规定之目的可能会落空。因此,遗嘱信托的资产隔离效力与特留份制度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核心在于遗嘱信托能否排除特留份制度的适用。
《民法典》第1141、1155条都使用了“应当”的表述,这意味着在设立遗嘱时必须为某些特殊人群留下一份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25、31条对此也予以重申。那么,采用遗嘱信托的方式能否排除特留份条款的适用呢?
有学者认为信托是极富弹性的制度,原则上可以不受特留份的限制。〔69〕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遗嘱信托确实具有灵活性,遗嘱信托本身就有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原始基因。因为遗嘱信托的雏形是古罗马法上的遗产信托,〔70〕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9-410页。而遗产信托的出现有其特殊背景,即当时法律规定有些人不能成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他们主要是异邦人、尤尼亚拉丁人、尚未出生的人;另外,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奥古斯丁,对未婚的成年人和无子女的已婚者的遗产接受能力也加以限制。〔71〕参见徐卫:《遗嘱信托制度构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正是为了规避这些苛刻的要求,遗产信托才应运而生并最终演化为遗嘱信托。〔72〕参见[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本文则持反对意见,即不能通过遗嘱信托制度排斥特留份制度之适用,其历史起源上规避法律的基因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遗嘱信托的灵活性也应当保留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
首先,《民法典》第1141、1155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范〔73〕参见姚明斌:《“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以〈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第1279-1280页。,其核心立法目的是照顾特殊的人群,尤其体现为对弱者的人道关怀,若允许通过遗嘱信托排除这些条款的适用,则其立法目的无法实现。若遗嘱信托突破特留份的限制,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25条,将部分信托财产扣回作为特留份,剩余部分依然作为信托财产以保持遗嘱信托的效力。
其次,若立遗嘱人将全部遗产都纳入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使得形式上不存在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也不存在继承份额,以此排除特留份的适用,则在解释论上属于脱法行为〔74〕原《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及原《合同法》第52条第3项都曾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这种行为与脱法行为的关系似乎比较模糊。学界和司法实务对这种行为定性的争议均很大。《民法典》取消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表述,其原来所指涉的脱法行为只能交由《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处理。,即当事人为了躲避法律障碍、禁止性法律规范或负担,试图借助其他法律构造形式实现同样的法律或经济效果。〔75〕Vgl. Reinhard Singer, in: Staudinger Kommentar BGB, 2004, § 117 Rn. 15.通过遗嘱信托规避特留份的强制性规定,其目的就是将相关群体排除出遗嘱信托受益人,进而使《民法典》第1141、1155条的立法目的落空。
再次,《信托法》第13条第1款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遵循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特留份是《民法典》关于遗嘱自由的重要限制性规定,有其特殊的立法政策考量,遗嘱信托应予遵循。〔76〕反对意见认为信托法规则优先于特留份制度适用,否则会影响信托功能的发挥以及立遗嘱人意思的贯彻。参见杨崇森:《信托法原理与实务》,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3-74页。
最后,在比较法上,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指出,遗嘱信托与遗赠具有相同的经济效果,在解释上应类推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25条的规定,赋予特留份权利人以扣减权,即遗嘱信托并不当然因此无效,只是特留份权利人可以向受托人、受益人请求扣减以满足其特留份而已。〔77〕参见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也认为,遗嘱信托违反特留份制度的,应予扣减,但遗嘱信托并不因此无效。〔78〕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69年台上字第1279号判决。在英美法上,曾有信托剥夺亡夫遗产份额,法院认为该部分条款无效,配偶的特定继承权不能被信托剔除,〔79〕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沈朝晖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此与特留份的处理具有相同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