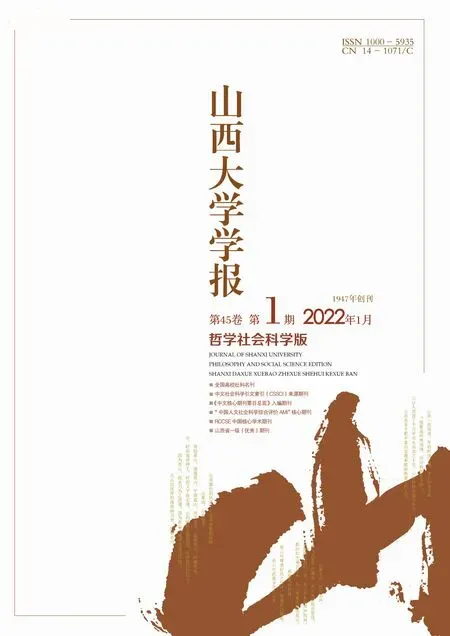嵇康《声无哀乐论》对艺术感应论的解构
2022-11-27陈莉
陈 莉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和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而,维护大一统政权的文艺观念逐渐弱化。曹操以“唯才是举”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东汉的“清议”演化为魏晋的“清谈”,人们以风神气度以及才能而不是以伦理标准来衡量一个人。这种社会观念折射到艺术中则形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1],同时也是各种艺术全面走向自觉的时代。在书法方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圆转自如、风流潇洒的行书改写了书法仅仅只作为书写工具的历史,开启了书法艺术独立的历程;在文学方面,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2]的观点,将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音乐方面,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提出了与传统音乐观念不同的音乐美学思想,彰显了魏晋艺术独立的时代精神。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魏晋六朝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世说新语·文学》中载丞相王导到江东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3]意思是王丞相到江东之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个方面的玄理,其他观点多由这三个方面派生而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评价《声无哀乐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4]。今天《声无哀乐论》依然是艺术美学研究方面得到较多关注的篇章,但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它在艺术独立方面的划时代意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关注音乐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建立了音乐的自然本体观,这无疑为中国音乐美学注入了活力,但在论证“声无哀乐”这一核心论点的过程中,嵇康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了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也解构了艺术的灵韵。如何看待嵇康对音乐情感性和音乐神秘感应论的解构,这也是《声无哀乐论》研究中应该回答的问题。本文拟将《声无哀乐论》置于中华美学发展的谱系之中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从这篇音乐美学专论中获得更多的理论思考。
一、《声无哀乐论》对音乐情感蕴含的否定
传统儒家艺术观念认为,艺术以情感为基础,是人心为外物所触动的结果。正如《礼记·乐记》所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5],艺术与人心相通,艺术中蕴含着人的精神和情感,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这种寄寓在艺术中的精神和情感而彼此沟通。所以,“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察其生离。”[6]200当然,统治者也正好利用了艺术的情感性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即一方面通过音乐了解民风民情,另一方面又通过悦耳的音乐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嵇康以儒家传统的音乐理论为辩难的对象,强调艺术的独立审美价值,目的在于使“声与政通”的儒家音乐理论架空。他对音乐情感性的反驳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嵇康依据物质中不包含情感,推论出声音中也不包含情感。嵇康指出,天地合德,世间万物得以产生。寒往暑来,五行得以形成,接着五色、五音得以产生。五音就如同气味一样客观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进一步讲,“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6]200嵇康认为声音是一种物理性的客观存在,只有好坏的区别,其中不会包含哀乐情感。显然,嵇康将音乐看成纯粹的自然现象,否定了音乐的情感性和社会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嵇康的逻辑,音乐艺术没有情感,只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存在,那么古人和今人就不能够通过蕴含在艺术中的精神和情感相互沟通。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儒家的音乐观念。儒家乐论认为,季札通过听乐,可以了解各国的精神面貌;师襄演奏琴曲,孔子能够从中感受到文王的精神气质。嵇康反驳道:如果文王的功德和风俗的盛衰能够在声音中体现出来,如果师襄的演奏技巧能够在声音中保存下来,那么三皇五帝也能够在今天存在了,古代的事物也可以在今天存在着了。嵇康用肉体的人不能超越时空存在推论出精神也不能超越时空而存在,进而证明古代人的精神不可能通过音乐传递给后世人,最终消解了儒家通过音乐来教化后人的目的。
其次,嵇康以物质的客观性作为推论的基础,类比性地论证了音乐没有情感。他说:“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6]204-205酒能使人产生喜怒哀乐之情,但酒是客观物质,本身没有情感。嵇康以此类推,音乐能使人产生情感,但音乐本身没有情感。嵇康还用泪水中没有情感来类推音乐艺术中没有情感,他说:“夫食辛之与甚噱,熏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易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辣出来的眼泪,笑出来的眼泪,被烟熏出来的眼泪,以及因哀哭而流出来的眼泪,都一样没有甜和苦之分。所以,嵇康得出结论:无论什么人演奏的乐曲,都是一样的,没有欢乐和悲戚的情感区别。在这里,嵇康完全将音乐等同于客观物质,将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套用在具有主观性的音乐上,认为音乐与万物一样是造化所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音乐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但音乐之善恶不会随人的悲哀或喜悦的心境而变化,音乐不是社会治乱的折射,也不会影响社会的治乱。显然,嵇康反对儒家用教化功利观念来禁锢音乐,认为音乐有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和标准,从而构建了音乐的“自律”理论。
再次,嵇康进一步用乐器的客观物质性来论证音乐的客观性。他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6]208意思是完美和谐的音乐出自金石和管弦等乐器,与创作者和演奏者都没有情感关系,是客观存在。音乐的不同属性只是缘于乐器的不同发声原理。嵇康说:“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节数,故使形躁而志越。”“琴瑟之体,闻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6]215嵇康的意思是,琵琶、筝、笛这类乐器的发音部位间距较近,所以这类乐器演奏的乐曲音调较高,旋律的起伏变化较为频繁,听这些乐器演奏的音乐,人的情绪容易激昂;相反,由于琴、瑟等乐器发音部位间距较远,所以它们演奏的乐曲音调偏低,旋律起伏变化较小,因而能使人情绪平和、安静。总之,不同的乐曲由这些客观的、物质性的乐器发出,乐器中没有情感,乐曲中自然也不会有情感。在嵇康看来这就证明了音乐的客观实在性,证明了声无哀乐的观点。
在声音客观性的基础上,嵇康构建了以“和”为中心的音乐形式美学理论。但嵇康所谓的“和”与传统儒家的“和美”音乐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儒家认为音乐的“和”来自天地的和谐,因为音乐中折射着天地和谐的精神,和谐的音乐具有神奇的作用,能够使百物化生,使群物呈现出秩序。《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5]天地万物的和谐与音乐有着内在的感应关系,也可以说是音乐促进了天地的和谐。但嵇康的“和”不再指音乐与天地精神的和谐,以及音乐与社会的和谐,而指的是音乐旋律本身的和谐、悦耳。在嵇康看来声音的排列组合是否和谐优美是音乐的第一要素,也是音乐能否感人的首要原因。嵇康指出:“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6]208,即和谐的音乐来自乐器本身发出的和谐的声音。嵇康以声音的和谐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形式主义的音乐美学观念。
嵇康将音乐等同于自然物质,将物理性的声音等同于音乐,在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之间进行类比和推论,建立了客观机械化的音乐理论。嵇康虽然是一个音乐艺术家,但他的音乐理论中却没有运用艺术思维来思考问题,而是用唯物的、实证的思维模式否定了艺术的情感性,解构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艺术观,但也将社会性的音乐艺术等同于客观物理性的声音。
二、《声无哀乐论》对音乐神秘性的解构
华夏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对时序变迁、季节更替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和感受。中国古人以一种“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自然界,认为外在世界的一草一木、山河大地都富有灵魂,从而建构了一个富有生命气息的泛神世界。如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7]天地与人一样有着喜怒之情、哀乐之心,山河大地、动植飞潜都成为与人一样的有情之物。在这种逻辑体系中,万物之间有着神秘的感应关系,音乐与自然及社会人生之间也有着冥冥之中的感应关系。如《尚书》中就指出,音乐具有使“鸟兽跄跄”“凤凰来仪”[8]的神奇作用。《荀子·劝学》讲:“昔者瓠巴鼓琴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9],瓠巴鼓琴,鱼儿会浮出水面静听;伯牙鼓琴,马儿会仰着头静听。《礼记·乐记》中指出:因为礼乐的施行,所以天地呈现出光明,阴阳相辅各得其所,万物得到抚育,草木茂盛,种子发芽,一切都呈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韩非子·十过》中记载师旷弹琴具有神秘的作用,可以使玄鹤二八飞来,可以使大风大雨兴起,可以使帷幕列、俎豆破、廊瓦飞落,使晋国大旱,赤地三年[10]。在这里音乐具有神奇的作用力。《吕氏春秋· 古乐》指出在古朱襄氏和陶唐氏时期,音乐和舞蹈都曾有过平衡阴阳,促进万物繁衍生长的作用[11]。董仲舒《春秋繁露》也指出:“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12]即调试好琴瑟,弹奏宫调,别的宫调就会应和;弹奏商调,别的商调也会应和。五音同类而鸣,就是艺术方面的同类相动现象。可以看出,赋予音乐以神性灵光,不仅是儒家音乐观念的特点,而且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共同基因。
这本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原始思维在音乐理论中的体现,但是这一音乐观念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可以说统治者正是以此神化自己的统治,达到治理的目的。《礼记·乐记》指出:雅正的音乐,会有顺气与之感应;奸邪的音乐,将会有逆气与之感应。不同性质的音乐与自然之气有着不同的感应关系,进而会影响到听这种音乐的人。《毛诗序》也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3]统治者利用了音乐艺术的这种神秘感应作用来神化自己的统治,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发展到东汉时期则形成铺天盖地的艺术感应观念,如《纬书·礼稽命徵》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14]王者制礼作乐,是天意的体现,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景星呈现。在这里音乐不是表情达意的文艺形式,而是来自宇宙深处的一种神秘声音,它隐含着来自上天的秘密,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神秘符号,是神通广大,包罗一切的天书。魏晋时期统治者进一步夸大音乐的功能作用,使神秘主义音乐观在统治阶层颇为流行。嵇康反其道而行之,以唯物论和实证论否定了艺术的神秘性,对统治者企图神化君权的歧途予以有力的一击。
嵇康对艺术和人之间的神秘感应关系的批判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于“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嵇康指出:“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鸟兽皆能有知,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解其语而论其事,犹传译异言耳。”[6]209在嵇康看来,牛非人类,所以,不可能有与人一样的心。如果人能听懂牛的话,这就等于说,鸟兽都有知觉了。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讲,鸟兽与人不可能相通。在对“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的批驳中,嵇康站在素朴唯物论的角度,证明了人和牛的不相通性,但却不能认识到,牛和人之间也可能有超越语言的一种感应和沟通关系。其次,对于“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竟”,嵇康也是站在科学实证的角度分析指出,楚国与晋国相去千里,声音不可能传到那么远的地方。再次,对于“羊舌母听闻儿啼,而知其丧家”,嵇康也是用实证方法质问:羊舌母听到的是今天的儿啼声,还是曾经听到了如此这般的啼哭声,而之后有这种哭声的孩子被证明就是个丧家子。即便是如此这般的哭声,也不可能通过相同的哭声,就推知有相同的心性。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嵇康认为一切都应当以科学和实证为出发点,否认人和自然之间有超越实证的感应关系。
嵇康反驳儒家传统的音乐观念,其核心正在于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模式来批驳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性。这实际上是用科学思维来批判诗性思维。嵇康论乐仅仅只考虑音乐的客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音乐混同于自然界中的声音,否定了音乐艺术的主观性,否定了创作者的主体精神。嵇康通过实证的方法证明了音乐不可能超越时空形成感应效果。无论是音乐的情感性还是神秘感应论,其实都是一种诗性思维的结果,是中国古人感知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同时,这种超验的诗性思维又是艺术思维的核心,可以说没有超验的感知和想象,艺术之花就失去了丰富的土壤。反观古今中外的艺术现象,有哪一种艺术能离开神秘文化的滋养?
三、嵇康解构神秘音乐观念的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神秘文化弥漫始终。即便是儒家思想源于礼乐文化,表现出一定的人文理性精神,但是其背景却是天命鬼神观念,天地山川以及祖先神对人的控制力是礼乐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形而上根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加关注人的行为的自觉,“不语怪、力、乱、神”[15],从而使儒家文化的形而上根据被弱化。但到了汉代,万物相通,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一发不可收拾。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盛行,整个汉代社会笼罩在神秘文化氛围中。面对这种极端发展的神性文化,王充以科学、理性为出发点,对谶纬神学及其影响下的艺术观念进行了全面批判。比如在《论衡·感虚》篇中,王充否定了音乐的神秘感应论。他分析指出,也许某一次师旷弹奏《清角》的时候,天正好要刮风下雨,风雨过后,晋国碰巧遇上大旱;晋平公喜欢听乐曲,淫乐过度,偶然得了手脚麻痹的病。总之,王充认为师旷的演奏与晋国的大旱,以及平公的手脚麻痹与淫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论衡·纪妖》篇中,王充针对闻濮水之上师延所奏乐曲而亡国的说法[16],批驳说:师延投濮水自杀,形体腐烂在河水中,精气消失于污泥中,怎么能再奏琴呢?如果师延能在水中奏琴,那么屈原也能在江底写文章了。扬子云写文章悼念屈原,屈原为什么不回答呢?所以,“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的说法也就成为“虚言”。可以看出,王充在以唯物的和实证的方法对抗神秘的艺术观念时,落入机械唯物主义的陷阱,并以此为出发点全盘否定了神话、传说的价值,也否定了艺术想象和夸张的合理性。
嵇康否定音乐艺术的神秘感应性,其论证方法和主要观点与王充如出一辙。嵇康同样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力求切断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打破统治者利用艺术神秘性来愚昧民众的做法,但也将艺术的情感性、想象性和神秘性特质一起否定掉了。
与其说“声无哀乐论”是一种艺术观念,不如说它首先是嵇康政治伦理态度的一种曲折表达。具体来说,司马氏集团的虚伪名教观念是嵇康反对名教的直接社会背景。嵇康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仍。正始十年,司马氏集团突然发动了“高平岭之变”,摧垮了曹爽集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司马氏集团提倡儒学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却暗中阴谋篡位,对曹魏宗亲和不愿依附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任意杀戮,搞得整个社会人人自危。表面上司马氏政权推崇儒家思想,崇尚“名教”,主张以礼法治国治民,强调音乐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其实“名教”不过是司马家族篡夺曹魏江山的遮羞布。因而,在那个倡导名教的虚伪时代,为避免祸事,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有识之士隐居山林,清谈玄理,且纷纷表现出对虚伪“名教”的不屑。自然也对名教背景下的艺术观念表示不屑。
首先,高中生要加强关于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的认识,加强对这些硬件的结构和通讯方式的认识,充分掌握这些硬件的工作原理,从而学习如何利用这些硬件来进行信息的传输和接收,如何进行命令的发出。因此,在机器人编程学习课堂上,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鼓励,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常识,引导学生如何去观察机器人的动作和行为,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对于编程代码和参数意义的认识。所以,在高中生机器人编程学习课堂上,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非常重要,让学生在观察机器人动作行为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学生对于机器人编程的认识,更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魏晋改朝换代之际,朝不保夕的险恶生存环境也造成了士大夫性格的扭曲和极端化的行为方式。嵇康对音乐自然本质的极端强调,也是士人极端性格的一种表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1]530可以说,正是因为要在夹缝中执拗地表达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态度,嵇康的音乐理论才具有了极端否定艺术的情感性和神秘性的特点。
从嵇康个人的身世来看,嵇康从小就才华横溢、“远迈不群”[17],但父亲早逝,在母亲和兄长的厚爱中长大,嵇康较少受到礼教约束,本身就对礼教不以为然,而且他又与曹魏宗室有婚姻关系,因而对司马氏政权采取了更为强烈的反叛态度。嵇康愤世嫉俗,公开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倡导的儒家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声无哀乐论》正是嵇康极端化思维方式在音乐理论上的反映。包括嵇康对郑卫之声的认可也与其他的反叛精神有一定关系。嵇康一反儒家“文以载道”“乐以言志”的传统艺术观念,从音乐本身出发,对“郑声”的美学效果予以肯定。郑声过多表达儿女私情,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被认为是淫声,孔子说要“放郑声”,但嵇康却认为:“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乐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6]221嵇康认为“郑声”是美妙的, 而对美的喜爱又是人的天性,这正如同对美色的迷恋是人的天性一样。大家都不是圣贤,哪用得着抵御这种声色享受呢?嵇康不但不否定“郑声”,反而充分肯定了郑声的美妙。嵇康对郑声的肯定具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可以说嵇康就是一个具有社会反叛思想的“愤青”,因为不与统治者合作,所以反叛所有统治者提倡的一切。
综上所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提出“声音中没有情感”和“声音不具有神秘感应性”两个要点,将音乐从伦理载体和政治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是魏晋时期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但是在批驳儒家文以载道音乐观念的过程中,嵇康从机械唯物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音乐,否定了音乐艺术的情感性,否定了音乐与天地神人的感应关系,同时也消解了音乐的灵韵。这是汉代王充《论衡》以唯物的观点来批驳谶纬神学的哲学思想的延续,也与嵇康所处的时代语境和个人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与其说“声无哀乐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音乐思想,不如说它是嵇康极端反叛名教的政治态度的极端表达。
四、如何正确认识艺术的神秘性
《声无哀乐论》表面上围绕的是音乐中有无哀乐的艺术问题展开的讨论,其实作者的旨归在于反对司马氏的虚伪统治,反对思想控制,反对利用音乐艺术来达到政治目的。为了切断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嵇康在理论上首先切断艺术与情感的联系,使音乐成为客观实在。他的音乐思想具有诡辩性和极端性,也与其艺术实践有一定的距离。与汉魏时期的其他乐器赋一样,嵇康的《琴赋》充满了神秘感应的色彩。
在《琴赋》中嵇康首先赞美了制作琴的梧桐树“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夕纳景于虞渊兮,旦晞干于九阳,经千载以待价兮,寂神跱而永康。”[6]84-85梧桐树生长在崇山峻岭之间,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吸纳了天地之灵气,因而枝叶茂盛,花飞于天。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天人感应、万物相通思想的体现。此外,嵇康写到琴乐的效果时说:“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王豹辍讴,狄牙丧味。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舞鸑鷟于庭阶,游女飘焉而来萃。”[6]108这段写到,琴声响起时,金石匏竹等其他乐器都不再发出声音,善讴的王豹不敢出声,善辨五味的狄牙丧失了辨味能力,水伯天吴从深渊跃出,王乔等神仙从云中飘然落下,神鸟鸑鷟受到感应舞于庭,游女受到感应纷纷前来。嵇康所写的事物多为想象中情景,无可验证。这恰好是《声无哀乐论》中所批评的“虚妄”之象。由此可见,嵇康“声无哀乐”的观点只是一种理论的设定,在艺术实践中并不能被完全体现。
嵇康同时代的阮籍的《琴论》几乎是儒家礼乐感应思想的翻版,其中写道:“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奏之方岳,而地祉上应。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不用而民自安。”[18]在阮籍看来音乐与天地万物相通,可以协和阴阳,调适万物,在圆丘演奏,天神下降;在方岳演奏,地祇上应。阮籍的音乐观念与传统儒家音乐观念一脉相承,显然与嵇康极力消解音乐的社会内涵的观点完全不同。
综合嵇康《琴赋》中的音乐思想,以及同时代其他士人的音乐思想就会发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逻辑上并不周洽,在实践上也并不能被彻底贯彻。这些都说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一定程度上是时代夹缝中的奇葩言论,具有一种极端反叛精神。也正如那个时代“扪虱而谈”的怪异行为一样,带有为了反叛而反叛的色彩,是夹缝中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士人带有变态色彩的极端言论。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艺术的神秘性?如何评价嵇康对声音情感性和神秘性的批判?毋庸置疑嵇康对声音的纯粹审美价值的认识具有理论开创性,开启了对形式美的理论思考。嵇康也认识到统治者对于音乐艺术情感性和神秘性的利用。他通过否定声音的情感性,从而否定了音乐对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进而否定“声音之道与政通”的音乐意识形态;嵇康否定声音与万物神秘感应关系的目的在于消解统治者利用音乐艺术达到控制人心的目的。但反过来讲,不能因为艺术的情感性和神秘性被统治者利用了,就完全否定艺术的神秘性。
神秘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感知和体验。这种特殊的体验最早来自人类对于日月星空、苍茫大地的无知和无助。人类想象出在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看不见的神灵在冥冥之中控制着整个世界,而万物都有灵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认知能力得到提高,未知的范围逐渐减少,在人类能探索太空的时代,在灯火辉煌的都市,神秘文化逐渐退隐。但是人类倾其所能只能认识宇宙中很有限的部分,因而宇宙对于人类而言永远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此外,神秘的想象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存空间,使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物的世界,而且能够放飞自我,翱翔于丰富的想象空间。神秘文化以原始思维为主要思维特征,且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无意识思维模式。这种想象中的神秘世界,以艺术为根据地。也可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自由徜徉其中的神秘的空间越来越小,艺术成为保留神秘文化最集中的阵地。科学可以发展,技术可以进步,但神秘的艺术世界可以成为纯粹客观物质世界的有益补充,可以构成人类生存的另一维度。神秘使艺术富有灵韵。如果艺术世界也完全客观化了,那么,艺术将失去灵韵,将变成刻板僵死的东西,人类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生存维度,人类将变得贫乏和片面化。从此角度看,嵇康《声无哀乐论》还不能辩证认识艺术世界不同于客观的物理世界的特殊性,嵇康对艺术神秘性的批判也具有矫枉过正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