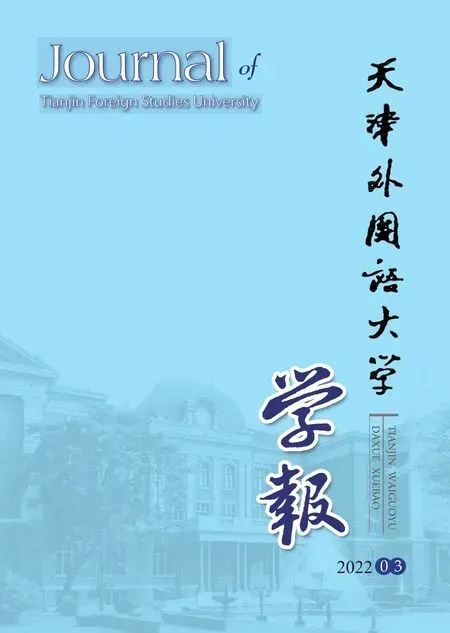希望中的忧思——《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
2022-11-27郭丹阳
王 卓,郭丹阳
希望中的忧思——《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
王 卓,郭丹阳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恩古吉《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真实再现了肯尼亚的历史、体制与社会危机,可谓一部茅茅运动简史。恩古吉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大历史,从不同角度再现了肯尼亚殖民时期普通人所遭受的创伤,并通过非线性书写观照现实。《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既标志着恩古吉个人创作的成熟,又在继承发酵期余韵的同时推开了肯尼亚英语文学繁荣期的大门,承担起了国家独立后非洲英语文学的新使命。
恩古吉;《一粒麦种》;历史书写
一、引言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1938-)是东非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创作的《大河两岸》(,1965)、《一粒麦种》(,1967)等小说均在世界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恩古吉的大部分小说都以真实的非洲历史事件、历史背景为依托,带有鲜明的历史性。在历史对非洲的重要意义这个问题上,恩古吉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认识,他在一次访谈中阐释了被殖民的非洲历史被扭曲和改写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的历史都一直被帝国主义的文化需求所扭曲,也就是说,为了迎合帝国主义者的意志而扭曲肯尼亚历史,其目的就是表明肯尼亚人民没有为了改变自己的自然环境而去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去与自然、与人进行斗争。也是为了迎合帝国主义者的意志,以表明肯尼亚人民没有抵抗外来统治。(Killam,1980:10)
关于创作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恩古吉在《隐居》(,1975)前言中有过这样的思考:“我的创作的确是一种为了了解自己和我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而进行的一种尝试。”(Thiong’o,1975)从恩古吉对非洲历史的认知和对历史书写的定位可以看出,其历史书写的目的有以下四点:其一,恢复被殖民者扭曲的历史的本真面目;其二,由非洲人重塑非洲历史;其三,厘清自我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其四,考察历史的现实观照。可以说,恩古吉充分发挥了非洲历史书写特有的“作为武器”的力量以及非洲文学作为“一种历史话语模式”的功能(Mazrui & Mhande,1990:47-48),成功地重写了这段纷繁复杂的非洲历史。
恩古吉作品中的历史书写可谓“开启了重述肯尼亚历史的先河”(朱振武、陆纯艺,2019:38)。他的小说《一粒麦种》就是典型的代表,这部小说是他创作生涯的分水岭(Ahmed,1992:18),在创作风格、政治主张等方面均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该作品浓缩了肯尼亚独立前的一段黑暗历史,涵盖了肯尼亚从茅茅运动(Mau Mau Uprising)到1963年宣告独立的肯尼亚解放史。不同于传统的官方历史书写,《一粒麦种》中呈现的非洲历史显得复杂而多维,这和茅茅运动这段历史依旧迷雾重重有很大关系。“这场运动是一个阶级冲突宣言,还是基库尤人的种族复兴?该运动的领导人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还是投身于解放运动的理想主义者?”(Mazrui & Mhande,1990:50)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本真?这些问题都是书写茅茅运动时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因非洲殖民历史、多种族冲突而变得异常复杂。这也是恩古吉的历史叙事常常选择多重声音、多元视角、多个时空交错、多种意识流并行的原因所在。
二、一部茅茅运动简史
对于历史小说而言,衡量其价值的首要标准无疑是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性。那么,如何衡量虚构文学作品中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2003:126)对这一问题曾有论述:“叙事中所讲的故事是对历史现实领域中经历过的故事的模仿,而仅就这个故事是一个准确的模仿而言,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真实叙述。”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可以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虚构填补史料记载的空隙,从而形成历史和文学之间“共建的互文性”(王卓,2012:163)。恩古吉在《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正是如此。
首先,恩古吉对历史的尊重体现在对历史中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尊重。恩古吉在小说中为虚构人物的活动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一粒麦种》浓缩了肯尼亚独立前的一段黑暗殖民岁月,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肯尼亚反英群众组织成立、1952年茅茅运动发起、1963年肯尼亚宣告独立等重大历史时刻。小说中第二章更可谓一部茅茅运动简史,它艺术地再现了肯尼亚反殖民斗争的复杂性以及斗争中的小人物。这和恩古吉自我定位的茅茅运动“代言人”的身份十分吻合(Acworth,1990:41)。这段简史覆盖了从白人踏上肯尼亚的土地,“声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p. 10)①,并宣扬英国女王的恩泽,到之后反英运动的发展,包括真实历史人物反英领导者瓦亚基的牺牲与乔莫·肯塔雅的被捕等历史事件、历史节点。通过对重大历史时刻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再现,恩古吉为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与情节提供了真实的社会背景,充分体现了对宏大历史的尊重和对民族历史再现的使命感。
其次,恩古吉力求在文本中反映从殖民期间到独立之后的种种真实的社会问题。其中,以土地问题最具代表性。殖民时期,肯尼亚的英国殖民当局不断利用法律掠夺非洲土地,这也成为“引发‘茅茅’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陆庭恩,1981:92)。1938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白人“专用的土地达1.67万平方英里,称为‘白人高地’,占肯尼亚土地总面积的7%,约占其良好土地的20%”(高晋元,1997:32)。20世纪50年代初,“光拿占有土地的绝对数字来说,白人移民平均每人占有的土地正好是非洲农民占有土地的470倍”(陆庭恩,1981:94)。肯尼亚独立后,政府声称“国有化无助于非洲社会主义的推进”(Branch,2013:9),反而助长了财富集中、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独立前后,英国殖民势力与非洲进行了谈判,通过“百万英亩计划”(Million Acre Scheme)在非洲本土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使得少部分非洲人得以拥有大规模土地,而大量平民依然贫穷。恩古吉在小说中艺术地再现了这一问题,比如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哈里·苏库“咒骂白人满口讲着仁慈和庇护,实则剥夺了肯尼亚人民的土地和自由”(p. 13),自由战士寇义纳唱到“没有土地,没有真正的自由”时流露出的悲伤与他“平日的欢乐爽朗截然不同”(p. 23)。独立之后,泰北村村民基孔由(Gikonyo)找议员申请贷款希望买下一片小农场,最终却发现议员成为了新农场的主人。这些情节都体现了恩古吉通过历史书写反映真实社会问题的努力。
再次,恩古吉对历史真实的追求还表现在对欧洲殖民者的刻画中。面对给肯尼亚造成深重灾难的白人殖民者,如何在历史书写中暂时放下仇恨,消除偏见,还原真实的殖民者形象,这对肯尼亚作家无疑是一大挑战。尽管《一粒麦种》表现了“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有力批判”(Lutz,2003:172),但恩古吉既没有被仇恨所左右,也没有为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刻意妖魔化殖民者,而是注重探测白人殖民者复杂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了被殖民主义洗脑,被庞大的帝国机器裹挟,人生也同样充满悲剧色彩的白人殖民者形象。恩古吉在《一粒麦种》中以虚构的殖民者汤普森为例,真实展现了白人殖民者自身面临的道德危机。汤普森在牛津大学研究英国历史时,曾坚信“大英帝国版图扩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伟大的道德观念发展的过程”(p. 59),是为非洲的“完全野蛮和不驯的状态里的自然人”(黑格尔,2001:101)带来“光明”和“文明”的“正义”行动(王卓,2021:96)。然而,当他来到非洲,真正面对殖民统治时,他的信念受到了冲击。当殖民者为了切断村民与自由战士的联系,要求村民烧毁旧屋时,汤普森“感觉自己正往一个死胡同走去”(p. 62)。汤普森曾在日记中引用艾伯特·史怀哲博士的话:“在与非洲人斗争的过程中,每一个白人都不断地陷于道德崩溃的边缘”(p. 62)。恩古吉呈现了一个较为客观真实的梦想幻灭、面临着严重道德危机的殖民者形象,这种幻灭感与道德危机也是所有殖民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历史书写中的真实与虚构正如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1947-)所言:“从经验论上讲,过去的事件存在着,但从实证论上来讲,我们今天却只能通过文本来知晓它。历史再现只能给予过去的事件以意义,却非存在。”(陈后亮,2010:82)可见,历史书写无法再现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其重点在于意义的表达。恩古吉把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置于真实的社会背景中,能够通过文学虚构的种种细节引发读者的情感体验,赋予茅茅运动、殖民掠夺、去殖民化等历史事件以意义,进而成功反映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同时,恩古吉从复杂的人性的视角探究殖民者的内心世界,客观地呈现了同样处于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之中的白人殖民者。这体现了恩古吉不仅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实,更能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性,还原人所处的特定的“伦理现场”(聂珍钊,2014:256),再现真实的人类困境。从《一粒麦种》的历史书写中,读者可以对肯尼亚的历史、体制与社会危机形成较为客观的认知。
三、泰北村中的小人物与茅茅运动的大历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恩古吉的历史书写并非追求史料记载式的刻板还原,而是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虽然《一粒麦种》主要呈现的是肯尼亚从茅茅运动到实现独立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但宏大的战争场面却几乎从未出现,恩古吉的创作基点也并非全然讴歌独立战争,渲染肯尼亚民族主义,构建肯尼亚“大写”的民族身份。《一粒麦种》更多的是关注了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泰北村中的普通村民,以虚构的小人物的视角呈现了这段“大历史”的不同侧面。不同于官方宏大叙事中的民族英雄,《一粒麦种》的叙述者们“被受阻的独立前景所困扰,被殖民主义的幽灵所折磨”(Gikandi,2000:99),遭受着不同类型的殖民创伤,心灵难以愈合。
小说围绕着谁出卖了茅茅运动领袖基希卡(Kihika)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而对这一答案的追索也成了小说的“中心行动”(Aborisade,1990:66)。四个主要人物:穆苟(Mugo)、卡冉加(Karanja)、基孔由(Gikonyo)和梦碧(Mumbi)。他们的命运也和这一问题的答案息息相关,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肯尼亚殖民时期普通人所遭受的不同创伤。
被认为是“活着的基希卡”、传奇英雄的穆苟却是真正出卖了基希卡的人。他有着不为人知的多面人性,时常处于为谁“做事”的两难困局之中。崇高的激情和出卖茅茅运动领袖领赏的念头时常掺杂在一起。这个悲剧性人物的行为充满了讽刺和巧合。他去白人处告发基希卡,却被认为提供假情报而备受凌辱。出卖了基希卡的穆苟时时生活在罪恶感之中,而这种罪恶感随着他被民众英雄化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基希卡牺牲日聚会上的坦白,对他而言既是一种赎罪,也是一种解脱。
卡冉加是典型的民族背叛者形象,其经历体现了民族背叛者所面临的身份危机与心灵创伤。因为害怕自己被抓进拘留营,再也见不到心爱的梦碧,卡冉加出卖了茅茅组织,同时也出卖了国家、民族与自己的尊严。表面看来,他从白人那里获得了权力与地位,但实际上,他始终面临着背叛者的身份困惑与心理创伤。卡冉加的身份困惑与心灵创伤主要体现在他背弃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受到黑人同胞的唾弃,又无法在白人那里获得新的身份,得到白人的尊重。卡冉加面对白人上司时唯唯诺诺、俯首帖耳,最害怕“白人权力在肯尼亚的终结”(p. 42)。但是在白人心目中,卡冉加与其他“未开化”的黑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黑人对于叛徒卡冉加既恐惧又憎恨,卡冉加深爱的梦碧也对其背叛行径直言羞辱。卡冉加在面对黑人同胞时,一方面利用白人的权力压迫他们,一方面又害怕他们,“在与他们恶言相对之后,又会低三下四地跟他们套近乎”(p. 41)。
基孔由的视角展现了拘留营中白人对黑人的迫害,同时也表现了基孔由所遭受的国家与家庭两个层面的创伤。囚犯们的生活是早上离开铁丝网去采石场做工,晚上重新回到铁丝网中,日复一日。基孔由觉得铁丝网“外面的世界已经死绝了”(p. 121)。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对妻子梦碧的思念,基孔由选择了招供。这一行为给他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心灵创伤。他无法忘记自己走向审讯室时的脚步声,在回乡的时候害怕面对熟人。他的面容也发生了变化,从进集中营之前的青春洋溢到现在“嘴巴一闭紧,脸上就像挂着一副怒容,仿佛只要有一点刺激,他就会暴跳如雷”(p. 114)。基孔由的讲述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殖民统治对人性的摧残。
梦碧的讲述展现了殖民战争中村庄里村民的生活,并以女性视角特别突出了女性在殖民过程中所遭受的压迫。首先,泰北村的普通村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当前方的森林战士重创白人政府的玛溪警署后,白人政府便展开了报复行动——拆毁旧泰北,逼迫村民两个月内建立新屋。而村中剩下的村民大部分为妇女、老人与孩子,妇女只能像男人一样劳作。其次,殖民时期的妇女还遭受着性压迫,区专员甚至“允许士兵把妇女带回他们的帐篷里”(p. 154)。在村庄被封锁、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有些女人会主动“把自己的身体给士兵取乐”(p. 157)。但是最终梦碧选择以一种坚定、独立与自信的姿态开展新生活,代表了肯尼亚人民虽饱受创伤,仍然坚定开启新生活的决心,代表了未来的希望。
历史书写的重点在于“谁在向谁讲述或书写什么,他们是如何讲述或书写的”(Sale,1992:46)。恩古吉的历史书写通过泰北村普通村民的讲述,展现了小人物对历史大事件的参与,给宏大叙事中无法发声的“历史失语者”以发声的机会,从而多角度地充实了历史大事件的书写。霍尔(Hall,1989:68)曾指出:“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一行为中总是暗含着我们言说或书写的立场——阐释(enunciation)的立场”。恩古吉多重视角的历史书写立场在于以小写、复数的历史为肯尼亚普通人民发声。
四、非线性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
恩古吉通过泰北村在独立日庆典前四天的故事呈现了自1952年茅茅运动发起到 1963 年肯尼亚宣布独立十多年的历史。恩古吉能够实现时间上的这一巨大跨越主要在于插叙、倒叙等叙事策略的运用。那么,恩古吉打破线性时间的用意何在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恩古吉历史书写的意义。《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归根结底是为了从历史中探寻非洲社会现实中种种复杂矛盾的根源,希望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而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恩古吉将文本中的“现在”设定为独立日庆典前这一看似充满希望的时间,却又通过倒叙、插叙等手法揭开了独立的盛大景象背后隐藏的种种危机。
肯尼亚人民首先面临的仍然是严峻的生存危机,主要体现在土地问题上。小说通过插叙讲述了殖民期间肯尼亚土地被白人掠夺,黑人失去土地的悲惨境遇。茅茅运动的领袖之一基希卡指出:“白人拥有的土地成千上万”,而黑人在田间辛勤耕耘“一个月却只能挣到十个先令”(p. 107)。当小说回到“现在”,即独立日庆典之前,人民议论纷纷:“政府还会严惩那些交不起税的人吗?工作岗位会不会增多呢?会不会有更多的土地呢?”(p. 230)。然而,事实上,严峻的生存危机仍然存在。在首都内罗毕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连一家黑人商铺都没有”(p. 68)。独立日庆典之前,基孔由向议员申请贷款,想要买下一个小农场,议员说“银行都还在欧洲人和印度人的掌控之下”(p. 69)。最终基孔由发现自己想买的小农场早已被议员暗中买下。
小说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表现了殖民力量仍盘踞在非洲大陆并且与少数人合谋继续对人民进行剥削的现实。在肯尼亚独立后,最先品尝独立果实的不是在战场上拼杀、在拘留营中受苦的自由战士,而是“那些没有参加过茅茅运动的人,那些为了避难跑到学校以及机关去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完全就是肯尼亚的叛徒、白人的走狗”(p. 76),他们同殖民力量同流合污,继续以隐性的方式剥削肯尼亚人民。人民无法获得土地,国家经济仍被殖民势力控制,所谓的去殖民化成了一个“空壳”(Gikandi,2000:98),最普通的民众没有在独立中获得切实利益。
肯尼亚人民面临的另一深层危机是信仰危机。其中,最具讽刺性的情节在于穆苟的背叛,这一背叛情节主要通过穆苟的意识流叙事来实现。小说开头,穆苟因为掩护民族英雄基希卡而进入拘留营这一光辉事迹被视为民族英雄,村民对其敬若神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党(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多次邀请穆苟在独立日庆典发表演讲。然而,穆苟却始终拒绝这种莫大的荣耀,他的意识中经常弥漫着一种恐惧,“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自己,无法摆脱”(p. 184)。当基希卡的妹妹梦碧亲自恳求穆苟出席典礼时,穆苟的回忆交代了他因为妒忌和贪图赏金而出卖基希卡的情景,这解释了穆苟的种种反常举动。这段跨时间的插叙揭示的真相极具讽刺性。最终,当时间回到“现在”,穆苟在庆典大会上当众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击碎了人民对所谓民族英雄的幻想。
其实,穆苟的问题并非个案。正如基孔由所言:“我们中很多人都大谈自己对茅茅组织的忠心,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其实都在自欺欺人。”(p. 75)在独立日的庆典中,人们不禁要扪心自问:究竟谁才是民族的英雄?民族独立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何在?可见,独立不但没有使广大肯尼亚人民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也未能帮助他们实现民族文化身份的深层认同。恩古吉通过打破线性时间的方式,直接对比历史与现实,表达了对现实中矛盾的深切关怀,这也是其历史书写的意义所在。
五、希望中的忧思:恩古吉历史书写与非洲文学发展
前文提到历史问题一直是非洲英语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包括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在内的多位非洲作家的多部文学作品均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周和军,2022:98)。茅茅运动这一关乎殖民与独立的历史事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肯尼亚文学而言,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母题式的存在,不同时期的肯尼亚作家均试图重新书写茅茅起义(Lindfors,1979:110)。在某种意义上,“茅茅运动是连接肯尼亚过去和未来的关键”(Atieno-Odhiambo,1991),这也是肯尼亚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这段历史的原因所在。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他们不仅能完成抨击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命,更能以史为鉴,更好地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包括诸如约西亚·姆旺吉·凯里尤基(Josiah Mwangi Kariuki)、塞缪尔·卡黑加(Samuel Kahiga)和莱纳德·奇贝拉(Leonard Kibera)等在内的肯尼亚作家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重述,从各个角度表现肯尼亚反殖民斗争。
关于茅茅运动的历史书写跨越了肯尼亚英语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发酵期与繁荣期。发酵期的肯尼亚英语文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重述历史”(朱振武、陆纯艺,2019:37),恩古吉的前两部作品《孩子,你别哭》(,1964)与《大河两岸》都描述了茅茅运动这段充满矛盾冲突与斗争的历史。《一粒麦种》相比起前两部作品“在思想上更为深刻,体现的矛盾也愈发激烈,不仅有对殖民主义的控诉,更有对国家独立之后的思考”(同上:38),标志着恩古吉创作的真正成熟。这正是恩古吉创作中典型的“社会历史决心(socio-historical determination)”(Aborisade,1990:61)的表现。恩古吉在重现这段历史时既讴歌了起义中的民族英雄,表达了对民族独立的希望,也表达了对独立后种种社会矛盾的忧思。恩古吉对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把后殖民非洲描写成一个复兴条件已然成熟的希望之地;另一方面,他似乎也认识到实现这种憧憬的“不可能性”(Amoko,2010:2)。
另外,恩古吉虽然被归为发酵期的作家,但从《一粒麦种》的历史书写已经可以窥见繁荣期的影子。如果从恩古吉本人创作意识衍变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是从他早期的民族意识到革命意识过渡和转化的标志(Aborisade,1990:67)。民族意识几乎是所有现代非洲作家的共同意识,是对欧洲政治殖民和文化殖民的一种对抗策略。然而,评论家们注意到恩古吉创作《一粒麦种》时经历了“明确的成长”(Aborisade,1990:65),他开始关注独立后的肯尼亚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一时期的很多非洲作家像恩古吉一样,越来越关注非洲语境中的社会现实问题,带有明显的革命意识。这一转变和肯尼亚独立后的国内政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肯尼亚独立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英国垄断财团仍然部分地控制着肯尼亚的经济,社会危机加剧。所以繁荣期的肯尼亚英语文学以批判现实、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恩古吉在《一粒麦种》的历史书写中已经预见了肯尼亚独立后的种种危机,其后续作品,如《血染的花瓣》(,1977)、《十字架上的魔鬼》(,1980)、《乌鸦魔法师》(,2004)均致力于批判独立后的社会不公问题,带有鲜明的革命意识。可见,《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对于恩古吉本人的创作与肯尼亚英语文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既标志着恩古吉个人创作的成熟,又在继承发酵期余韵的同时推开了肯尼亚英语文学繁荣期的大门,承担起了国家独立后非洲英语文学重视现实、反映独立后的危机、为普通民众发声的新使命。
①本文有关《一粒麦种》的引文均来自参考文献[16],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1] Aborisade, A. 1990. National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wo Phases of Ngugi’s Artistic Praxis[J]., (2): 59-74.
[2] Acworth, W. 1990. Interview with Ngugi wa Thiong’o[J]., (2): 41-46.
[3] Ahmed, K. 1992. Oral Tradi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Ngugi WA Thlongo’s Devil on the Cross[J]., (2): 18-32.
[4] Amoko, O. 2010.[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5] Atieno-Odhiambo, S. 1991.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in Kenya: The Mau Mau debate[J].,(25): 300-307.
[6] Branch, D. 2013., 1963-2012[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7] Gikandi, S. 20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Hall, S. 1989.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J]., (36): 68-81.
[9] Killam, D. 1980.[M]. London: Heinemann.
[10] Lindfors, B. 1979. East African Popular Literature in English[J]., (1): 106-116.
[11] Lutz, J. 2003. Ngugi’s Dialectical Vision: Individualism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in[J]., (2-3): 171-198.
[12] Mazrui, A. & L. Mhande. 1990. The Historical Imperative in African Activist Literature[J]., (2): 47-58.
[13] Sale, M. 1992. Call and Response as Critical Method: African-American Oral Traditions and Beloved[J]., (1): 41-50.
[14] Thiong’o, N. W. 1975.[EB/OL]. https://www.doc88.com/p-7922535014981.html?r=1.
[15] 陈后亮. 2010. 论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特征[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80-84.
[16] 恩古吉·瓦·提安哥. 2012. 一粒麦种[M]. 朱庆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7] 高晋元. 1997. 英国对肯尼亚殖民政策的演变[J]. 西亚非洲, (3): 32-38.
[18] 海登·怀特. 2003.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 张万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黑格尔. 2001.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 陆庭恩. 1981. 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J]. 史学月刊, (2): 92-97.
[21]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王卓. 2012. 论丽塔·达夫《穆拉提克奏鸣曲》的历史书写策略[J]. 外国文学评论, (4): 161-177.
[23] 王卓. 2021.“黑色维纳斯”的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帕克斯戏剧《维纳斯》[J]. 外国文学研究, (1): 92-103.
[24] 周和军. 2022. 国外关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天堂》的研究述评[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1): 96-101.
[25] 朱振武, 陆纯艺. 2019.“非洲之心”的崛起——肯尼亚英语文学的斗争之路[J]. 外国语文, (6): 36-41.
I106.4
A
1008-665X(2022)3-0039-09
王卓,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诗歌和诗学、英语国家族裔文学、英语教育研究
郭丹阳,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国家族裔文学
(责任编辑:张新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