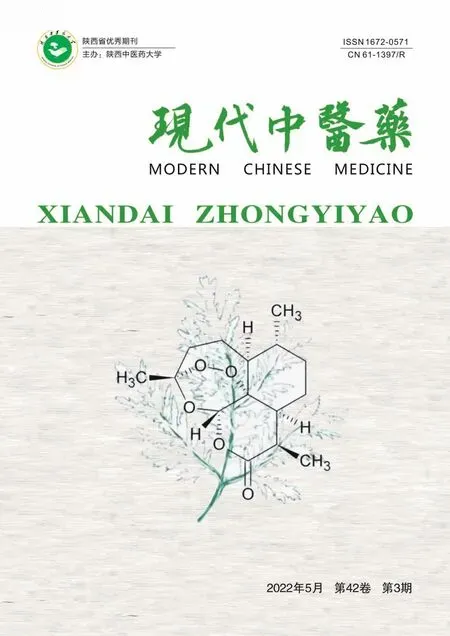从湿热论治银屑病文献研读*
2022-11-27刘美丽李晓强闫小宁
刘美丽 李晓强 闫小宁
(1.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科,陕西 西安 710003;2.志丹县中医医院皮肤科,陕西 延安 717500)
湿、热是中医致病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由于两者在很多疾病的病理过程中同时或相继出现[1],因此,两者常常并称,即湿热。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疾病[2],属中医“白疕”“干癣”等范畴。早在隋代《诸病源候论》中就对其病机有了论述,“干癣,但有匡郭,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是也。皆是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所生”[3]。可见,从那时起,人们就认识到了湿邪在银屑病的病机中的作用。而热邪在银屑病病机中的作用被明确认识较于湿邪要晚得多,《寿世保元》[4]曰:“夫疥与癣,皆热客于皮肤之所致……毒之深沉者,为癣也,多因风毒夹热得之……”。但以苦寒药治疗银屑病的实践一直存在于临床,《圣济总录》中收录的治疗银屑病的大量处方均含有清热类药,如黄连丸等。由于古人对于银屑病的认识常与其他皮肤病混淆,因此,在湿热方面的认识也一直相对比较混乱和片面。近代以来,人们对于湿热在银屑病病机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入,但缺乏全面及系统梳理。因此,梳理从湿热论治银屑病的研究进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湿热病机
虽然湿热在银屑病发病过程的重要性已被很多医家所认识,但关于湿热在银屑病病机中的具体作用却存在诸多不同观点,《诸病源候论》[3]曰:“皆是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所生”。指的是邪在皮肤,后至血分;《严氏济生方》[5]曰:“古方所谓干癣、湿癣、风癣、苔癣之类……此由风湿毒气与血气相搏,凝滞而为此疾也”,即风湿在血分; 而《外科大成》[6]曰:“癣发于肺之疯毒……总不外乎风热湿虫四者相合而成”说湿热在肺。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对湿热在银屑病的病机中的具体作用认识不一,就目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湿热蕴肤、血分湿热、脾胃湿热、肝胆湿热、湿热壅肺和湿热痹阻关节六个方面。
1.1湿热蕴肤 由于银屑病是以皮肤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人们很早就认识了到了银屑病是外邪(风寒湿热)客于皮肤的结果,《诸病源候论》和《寿世保元》都持这一观点。一般认为湿热蕴肤型银屑病多由禀赋不耐,邪毒侵犯,或湿热之体,受药毒侵扰,体内湿热蕴蒸,蕴于肌肤而为斑、水泡,甚则糜烂渗液,表皮剥脱,剧痒。李彬[7]认为湿热蕴肤证在就诊的患者中并不少见,此证型的患者多为体型肥胖、有烟酒史、素食膏粱、内脏滞热之辈。
1.2血分湿热 血分湿热的观点同湿热蕴肤一样,是最早被认识的银屑病病机。《诸病源候论》提出,银屑病为风湿等外邪客于腠理,与血气相搏而成。后世很多著作多遵此说,如《圣济总录》《济世全书》等。但基本都认为血分湿热并非银屑病的单一病机,而是多与湿热蕴肤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正如石云[8]总结到,本病患者大多由于湿热蕴结,灼伤血络,迫血妄行,溢于肌肤而为斑。
1.3脾胃湿热 相对于前两者,脾胃湿热是真正意义上的内生湿热。脾胃乃后天之本,素体脾虚或嗜食肥甘厚味易使脾失健运,湿邪内生,湿邪郁久可化而为热。正如《冯氏锦囊秘录》[9]曰:“湿热之原,因寒湿积饱失常,喜怒劳役过度,以伤脾胃。胃为水谷之海,调则运行五谷而致五谷精华,伤则动火熏蒸水谷,而为湿热。且胃司受纳,脾司运化,今脾既不能运化,则饮食停积,而湿热愈生矣”。由此可见,湿热最容易内生于脾胃,脾胃湿热焦灼,郁毒发于肌肤,遂成银屑病。尤雯丽等[10]认为湿热型银屑病以脾虚为主,湿毒为标,久则入于血分外发于肌表。
1.4肝胆湿热 内生性的湿热除了脾胃之外,肝胆是最容易出现湿热的。肝为刚脏,易生怒动火,肝喜条达,情志不畅,易肝气郁结,郁久化火。加之外界之湿热及饮食肥甘,易成肝胆湿热。张莉等[11]认为,一方面,患者多嗜食肥甘,多逸少劳,加之肝气郁结,久而化火,热入血分,遂成此病;另一方面,银屑病给患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日久则肝气郁结,情绪急躁易激动,气郁日久化火,化毒,毒热内盛入血分,血受热煎熬瘀结成块,加之,饮食不节而生湿,湿气与血热交杂,遂致湿热缠绵。
1.5湿热壅肺 银屑病与肺的关系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除了《外科大成》《证治准绳》[12]曰:“夫疥癣者,皆由脾经湿热,及肺气风毒,客于肌肤所致也……风毒之深沉者为癣”,《明医指掌》[13]曰:“癣亦有五,风癣、顽癣、湿癣、马癣、牛皮癣之别,皆由肺受邪毒,运于四肢,以生肉蠢。”但真正明确提出湿热壅肺则是当代学者,范叔弟等[14]认为银屑病多因感受外邪,日久不去,郁久化热,热盛蕴毒;或嗜食辛辣厚甘,湿热内生;最后,热毒互结,壅滞于肺,发于肌表。
1.6湿热痹阻关节 银屑病性关节炎是一种与银屑病相关的炎性关节病,具有银屑病皮疹并导致关节和周围组织炎症[15]。湿热除了促使寻常性银屑病的发生发展外,在关节病性银屑病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外感风湿热邪,久病而湿热毒邪滞留于肢体、关节、经络,痹阻气血筋脉,进而形成银屑病关节炎[16]。孟洁等[1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银屑病关节炎急性期多以湿热证型为主。卢芳[18]同样认为银屑病关节炎致病因素湿热之邪尤为重要,有外感和内生两个因素。他认为久居炎热潮湿之地之人,外感风湿热邪,袭于肌腠,壅于经络,痹阻气血经脉,滞留于关节筋骨,而致营卫行涩,经络不通,故而发生关节病变。
2 治法
2.1清热燥湿 针对湿热蕴肤证银屑病,李彬[7]采用苦必春消银方治疗,方由萆薢、椿根皮、苦参三味中药组成。实验组给予苦必春消银方,入组36例,对照组给予复方青黛胶囊,入组36例。治疗8周后,发现苦必春消银方在改善银屑病PASI评分方面与复方青黛胶囊,且无明显毒副作用[7]。
2.2清热解毒、祛湿凉血 石云[8]在湿热蕴结,迫血妄行的病机基础上,应用清热解毒、清热利湿与清热凉血三法合一治疗银屑病,取得较好疗效。在药物的选择方面,清热解毒常选用板蓝根、大青叶、蒲公英、连翘、栀子、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土茯苓等;祛湿选用茯苓、泽泻、薏苡仁和菝葜;凉血常用药用水牛角、生地、丹皮、紫草、赤芍[8]。郭靓[19]用白疕合剂(金银花、白茅根、板蓝根等)治疗湿热型银屑病有效率达95%。虽然郭氏在文中未说明湿热的病位,但根据其组方用药的特点来看,其所治患者应为血分湿热。高志学[20]自拟白虎丹方:白藓皮、紫丹参各30 g,虎杖、赤芍、蚤休、威灵仙、琥珀各15 g,白僵蚕10 g。治疗血分湿热型银屑病,取得满意的疗效。
2.3健脾利湿除热 尤雯丽[10]结合成都的地方特点,认为在治疗银屑病中应重视健运脾胃、扶正以驱邪,提出进展期以健脾除湿、清热解毒为法;消退期以健脾除湿、养阴润燥为治则;恢复期以健脾除湿、益肺固表为治法。健脾利湿法贯穿始终,以四君子汤为基础方,常用南沙参代替原方中的人参,因其性味平和、不温不燥。后期以玉屏风散益肺固表,防止复发[10]。郭岱炯等[21]以健脾祛湿法治疗脾虚湿热型银屑病湿疹样变患者疗效显著,在改善瘙痒程度、皮损方面均优于口服雷公藤多苷片联合开瑞坦治疗组,且安全性好。李寿甫等[22]用清热利湿、和营通络法,方用土茯苓、苡薏仁、白鲜皮、地肤子各30 g,苍术、丹参、生地各15 g,萆薢、防己、黄柏、威灵仙各10 g,槐米18 g,三棱9 g。有效率达90%。杨素清等[23]用燥湿苦参汤(苦参10 g,乌梢蛇30 g,苍术20 g,黄柏15 g,薏苡仁30 g,土茯苓30 g,萆薢15 g,猪苓15 g,泽泻10 g,白鲜皮20 g,金银花20 g,连翘15 g,蒲公英30 g,甘草6g)治疗以脾胃湿热为主的银屑病,经8 w治疗后,总显效率为77.4%,明显优于对照组(复方青黛丸)。邱曙光等[24]用四君子汤加减治疗湿热型银屑病,患者的瘙痒、红斑、鳞屑、乏力困倦等临床症状改善程度明显。
2.4清利肝胆湿热 张莉等[11]基于肝经湿热的理论,运用清热利湿法治疗银屑病取得显著效果。以龙胆泻肝汤为基础组方,其组成为龙胆草9 g,黄芩9 g,栀子9 g,柴胡9 g,生地黄21 g,牡丹皮9 g,当归9 g,金银花30 g,土茯苓30 g,泽泻9 g,车前子15 g,连翘15 g,甘草6 g。李继荣[25]采用清利湿热、凉血解毒的治则,仍以龙胆泻肝汤为基础方,组方:龙胆草10 g,栀子10 g,黄芩10 g,柴胡6 g,生地30 g,当归12 g,僵蚕10 g,土茯苓20 g,苦参15 g,刺蒺藜20 g,白鲜皮20 g,丹参15 g,乌梢蛇10 g,治疗肝胆湿热型银屑病50例,15 d为1疗程,经过4个疗程的治疗后,总有效率92%。
2.5清肺利湿、活血解毒 针对湿热壅肺型银屑病,范叔弟等[14]认为应以清热利湿、活血解毒为法,方用桑白皮汤合五味消毒饮等。
2.6清热祛湿通络 谢娟等[26]自拟消疕通络汤联合甲氨蝶呤治疗银屑病关节炎湿热痹阻证,临床试验发现,消疕通络汤(生地黄15 g,牡丹皮10 g,女贞子10 g,墨旱莲10 g,黄柏10 g,牛膝10 g,苍术10 g,丹参10 g,薏苡仁15 g,川芎10 g,威灵仙10 g,鸡血藤10 g,杜仲10 g,甘草6 g)联合甲氨蝶呤片组治疗12 w后,患者ESR、CRP水平改善明显优于单纯使用甲氨蝶呤组(P<0.05),且副作用更少。张秦等[27]采用当归拈痛汤联合甲氨蝶呤治疗银屑病关节炎湿热痹阻型,结果显示当归拈痛汤联合小剂量甲氨蝶呤较单纯用甲氨蝶呤起效快,副作用小。马丛[28]等采用清热养阴丸(由金银花、连翘、半枝莲、虎杖、生地黄、白芍等药组成)治疗湿热型银屑病关节炎,结果显示有一定疗效,无明显毒副作用。章光华[29]对43例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给予自拟克银方(白鲜皮30 g,金银花36 g,连翘18 g,生地黄24 g,白茅根36 g,苦参15 g,防风12 g,地肤子18 g,丹参18 g,鸡血藤24 g,当归12 g)合湿热痹煎剂(雷公藤15 g,忍冬藤24 g,络石藤24 g,黄柏18 g,土茯苓60 g,苍术18 g,薏苡仁40 g,赤小豆24 g,姜黄18 g,木通18 g,川芎18 g)口服,治疗3个月,总有效率达88.37%。孟洁等[17]对银屑病关节炎急性期病人采用清热祛湿、活血化瘀的治则,方用四妙丸合身痛逐瘀汤加减,疗效较好。叶遂安等[30]对急性期银屑病关节炎以清热利湿、合营通络,予宣痹汤合萆薢渗湿汤加减,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2.7其他 临床上,很多患者证型并非以上单纯的某一型,多表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部位的湿热并存的现象。因此,在治疗往往多方兼顾,但总的治法仍为清泄湿热。刘玉梅[31]观察了大黄合剂治疗湿热型银屑病的疗效,发现经过75 d的治疗,大黄合剂(大黄9~12 g,乌蛇肉、鸡血藤、白茅根、茜草根、生槐花、白鲜皮、土茯苓各30 g,丹参、生苡意仁、地肤子各15 g,泽泻9 g,木通、川连各6 g)治愈率达80%。朱建龙[32]认为湿热蕴结证治法当以清利湿热、解毒通络为主,方用龙胆泻肝汤、当归拈痛汤、三妙散等加减。药物:龙胆草、生栀子、当归、黄连、黄芩、生地黄、苍术、黄柏、生薏苡仁、川牛膝、猪苓、苦参、茵陈等。任素华等[33]湿热方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湿热型银屑病,总有效率达97.5%。方药组成为生地30 g,茵陈30 g,黄芩15 g,土茯苓30 g,薏苡仁30 g,云苓15 g,栀子9 g,二花15 g,元参9 g。魏黎[34]主张湿热型银屑病应用托里消毒汤加减治疗。周冬梅[35]认为湿邪贯穿银屑病始终,在血分论治的基础上,以清热除湿汤和除湿胃苓汤等治疗湿热型银屑病,疗效较好。欧阳晓勇等[36]用云昆水榆汤(云南茜草根30 g,昆明山海棠15 g,水牛角30 g,生地榆30 g,茵陈15 g,滑石30 g,川木通15 g,石菖蒲10 g,射干15 g,黄芩15 g,连翘15 g,白蔻仁10 g,浙贝母10 g,藿香15 g,薄荷5 g)加减治疗湿热型银屑病,疗效满意。赵运昇[37]用自拟消银解毒汤(金银花20 g,连翘20 g,白鲜皮15 g,牡丹皮15 g,乌梢蛇15 g,羌活20 g,桂枝12 g,细辛6 g,独活20 g,桑寄生15 g,牛膝15 g,秦艽20 g,藁本15 g,威灵仙15 g,防风15 g,川芎20 g、赤芍20 g)治疗湿热型银屑病,疗效较好。
3 基础研究
除了从临床表现和药物治疗方面对湿热在银屑病发病中的作用研究外,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探索。郝平生等[38]利用同位素相对标记与绝对定量技术(iTRAQ技术)对湿热型银屑病患者血清蛋白质组学进行分析,结果共鉴定出787个蛋白质组,具有生物信息学分析功能注释的蛋白质共有718个;与正常人比较,发现了651个显著性差异蛋白(P<0.05),其中有强显著性差异的蛋白418个(P<0.01)。并且比较了湿热型和血热型银屑病,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多种如糖蛋白类、脂蛋白类、免疫类等表达差异性蛋白[39]。辛昊洋等[40]分析了银屑病关节炎湿热内蕴证、寒湿阻络证、阴虚血燥证之间的免疫因子,发现3组患者IgA、IgG,IgM水平均高于正常范围,但各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湿热内蕴证患者ESR、CRP、TNF-α、IL-17、IL-23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1)。李凤仙[41]发现湿热证方(土茯苓、黄柏、茵陈、苍术、秦艽、地肤子、白鲜皮、苦参、山慈菇、黄药子、丹皮、生栀子和紫草)对乙烯雌酚诱导的小鼠阴道上皮过度增殖模拟银屑病病理改变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王玉芝[42]采用复合多因素造模法,给予豚鼠肥甘饮食加白酒并湿热外环境以制造湿热证的模型,同时用心得安乳剂构建了豚鼠银屑病模型。并以此模型,研究发现预防性应用玉屏银屑方(黄芪20 g,白术10 g,防风10 g,金银花20 g,柴胡10 g,土茯苓20 g,薏苡仁30 g,车前草30 g,白花蛇舌草20 g,板蓝根20 g,紫草10 g,生地20 g,丹皮10 g和赤芍10 g)可降低造模动物的CD4+/CD8+比值,调节T淋巴细胞免疫水平[43],降低IFN-γ/IL-4比值,调节细胞免疫[44]。
4 展望
作为皮肤科常见疾病之一的银屑病,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目前尚无根治药物[45]。中医对其发病机制的认识历史悠久,也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治法和方药。元代朱丹溪《格致余论》[46]曰:“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之八九。”指出湿热之邪是重要致病因素。杨雪松等[47]通过对412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症状、舌象、脉象等四诊信息的分析,发现湿热是寻常型银屑病的重要病机。本文系统性综述了银屑病病理过程中湿热的病位、病机、治法和基础研究等最新成果,发现湿热在银屑病的病机主要有湿热蕴肤、血分湿热、脾胃湿热、肝胆湿热、湿热壅肺和湿热痹阻关节六个方面。与之对应,在治法上,主要为清热燥湿,清热解毒、祛湿凉血、健脾利湿除热、清利肝胆湿热、清肺利湿、活血解毒,清热祛湿通络。湿热学说虽然很早就被人们提出,但其发展较为缓慢,加之目前学界大多将目光集中在“从血论治”,而忽视了包括湿热在内的其他病机,截至目前,有关湿热的研究仍停留在临床表现的归纳和药物的观察上,缺乏深入的机制研究。通过梳理此学说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至今仍然缺乏对湿热在银屑病复杂发病过程的系统认识。相信通过对湿热在银屑病发病中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于银屑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丰富中医关于银屑病病机的理论,提高中医治疗银屑病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