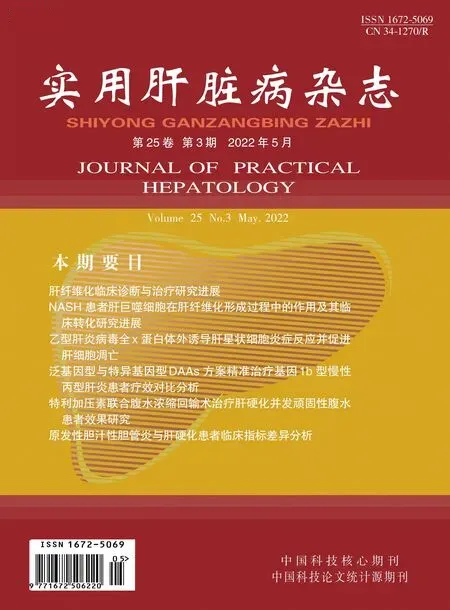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2022-11-26年福临鲁晓岚
年福临,鲁晓岚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种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和遗传易感密切相关的代谢应激性肝损伤[1],组织病理学特征从肝组织单纯脂肪变性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再到晚期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严重阶段。新的国际专家共识将NAFLD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MAFLD),更强调了代谢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以糖代谢紊乱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其特征是慢性高血糖,伴有胰岛素分泌不足和/或作用障碍。DM与NAFLD之间互为因果,共同促进疾病进展。DM可增加NAFLD进展期肝病的风险,NAFLD也可增加DM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因此,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相关机制,能够进行更优质的疾病管理,减轻社会疾病负担。
1 流行病学
NAFLD是一种多系统受累的代谢性疾病,已经超越病毒性肝炎成为全球最常见的肝脏疾病[2],影响着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约有10.5%全球成年人罹患DM[3]。NAFLD是2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2,T2DM)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表现。IR是T2DM的标志,肝脏脂肪沉积可作为IR强有力的预测指标[4]。有研究表明,在平均随访3.7年里,在3万人群中发现1486名个体发生了T2DM,且BMI为25.0 kg/m2是T2DM发展的截断点[5]。最近的一项Meta分析指出,在全球DM患者中NAFLD患病率为55.5%,NASH患病率为37.3%[6]。DM与NAFLD之间的作用双向且复杂。高血糖可诱导脂肪从头生成和肝脏纤维化等各个过程。在老年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9年随访时间内NAFLD组发生T2DM的风险是非NAFLD组的2.76倍,且自第5年起NAFLD组T2DM累计发病率显著升高,提示老年人群NAFLD也是T2DM发病的远期独立危险因素[7]。在NAFLD的多重打击学说中,肥胖、IR和T2DM则是NAFLD进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与未患DM人群比,DM患者发生肝病的风险比增加,血糖每升高1 mmol/L,NAFLD、肝硬化、酒精性肝病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发生风险分别升高1.07倍、1.07倍、1.10倍和1.04倍[8]。肝脏脂肪变性、炎症、合并存在的高血脂血糖和高凝状态可能通过恶化IR等因素增加远期并发症的发生。在1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1,T1DM)合并NAFLD患者,神经病变发生率是未患NAFLD的6倍[9]。T2DM患者肝纤维化的肝脏硬度也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10]。同样地,晚期肝纤维化也被证明是T2DM患者发生蛋白尿的独立危险因素[11]。
2 NAFLD与T2DM相互促进机制
2.1 IR NAFLD与T2DM联系的中枢环节是IR。IR的实质是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也被认为是进展为NAFLD的独立预测因子和危险因素[12]。激素敏感性甘油三酯脂肪酶(hormone-sensitive lipase,HSL)是脂肪动员过程中的关键酶,受到胰岛素的调节。在IR状态下,胰岛素的抑制作用减弱,脂肪不断水解,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增多,超过肝脏代偿能力即可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脂质沉积除了能引起脂肪细胞缺氧导致慢性炎症外,还可激活巨噬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作用于胰岛素靶细胞,影响胰岛素受体底物磷酸化,进而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加重IR[13]。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1c,SREBP-1c)与碳水化合物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rbohydrate-responsive element-binding protein,ChREBP)都是肝脏脂质代谢的关键调控基因。T2DM患者高血糖与高胰岛素血症分别通过ChREBP和SREBP-1c诱导肝脏从头脂肪生成,增加肝脏脂肪酰辅酶A的合成[14]。NAFLD患者体内升高的FFA水平对糖代谢产生负面影响,促进糖异生,加重IR,而T2DM也因为IR的存在,一方面升高FFA,另一方面调控脂质代谢基因而共同增加肝脏脂肪的从头合成,形成相互交织的恶性循环。
2.2 脂肪组织功能障碍 脂肪组织功能障碍是T2DM和NAFLD疾病进展过程中的触发因素。肝脏脂肪酸酯化为TG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向肝脏转运的FFA,而不是肝脏胰岛素信号[15]。脂肪组织功能障碍也涉及脂肪因子和细胞因子释放失调,从而促进DM、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16]。这些促炎脂肪因子可激活c-Jun NH2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和NF-κB通路,促进全身IR和炎症的发生。脂联素作为外周血含量最高的脂肪因子,发挥着胰岛素增敏、抗炎症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脂联素的循环水平与纤维化进程呈负相关,低循环水平的脂联素与T2DM的发生有关[17]。新的研究发现,肥胖个体PH结构域富含亮氨酸的重复蛋白磷酸酶2(PH domain and leucine rich repeat protein phosphatase 2,PHLPP2)表达升高,而PPARα活性和脂联素分泌却降低,脂肪酸氧化减少。在特异性敲除PHLPP2基因小鼠发现了更高的血清脂联素水平,从而对肥胖相关疾病产生保护作用[18]。脂肪因子Gremlin-1对脂肪组织、肌肉和肝细胞胰岛素信号产生负面影响,被认为与T2DM和NAFLD的发生有关。研究发现,T2DM伴NASH患者肝组织Gremlin-1 mRNA水平显著高于单纯肝脂肪变性患者[19]。脂肪细胞脂肪酸结合蛋白 (adipocyte fatty binding protein,AFABP) 是由脂肪细胞分泌的细胞溶质蛋白。循环AFABP水平与代谢综合征有关,也是T2DM进展的独立预测因素。AFABP可通过增加肝星状细胞TGF-β1的产生促进肝纤维化,而抑制AFABP可缓解小鼠NASH和肝纤维化,提示AFABP可作为NAFLD和T2DM的潜在治疗靶点[20]。
2.3 炎症、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 NAFLD和T2DM的发生发展与炎症息息相关,主要涉及NF-κB和JNK通路。近年来,炎症反应被认为是DM的原因之一,肥胖型NAFLD患者持续存在炎症反应。TNF-α不但是其中的经典炎性因子,同时也是致IR的因素之一。通常,炎症与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伴随存在,可激活肝星状细胞纤维化反应,促进NASH和肝硬化的发生发展[21]。JNK通路是MAPK家族的重要分支,过量的FFA经线粒体代谢后产生大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破坏线粒体膜和DNA,损伤胰岛细胞,产生脂毒性产物而激活JNK通路[22, 23]。相关研究证明,JNK通路能够直接抑制胰岛素受体底物磷酸化而影响胰岛素作用,也可抑制PPARα转录活性,导致肝脏脂质堆积[24]。NAFLD患者肝脏脂肪变性和持续的炎性状态影响了正常的糖代谢过程,促进IR和T2DM的发生。相应地,IR的存在最终也会作用于炎症通路,致使NAFLD的发生,形成恶性循环。
2.4 肝细胞因子与肠道菌群肝细胞因子在NAFLD和T2DM患者病情进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胎球蛋白A(fetuin-A,FA)是由肝脏分泌的胰岛素受体酪氨酸激酶的天然抑制剂,其血清水平与肝脏脂肪堆积呈正相关,也与T2DM风险显著相关[25]。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21)可通过ERK1/ERK2的激活促进葡萄糖在脂肪细胞的摄取。当NAFLD患者肝细胞变性明显时,血清FGF21水平也随之升高,但此时后者抑制脂肪细胞脂解的作用却减弱,因此NAFLD患者也可能存在FGF21抵抗[26]。此外,肠道菌群的作用在多种疾病中已被证实。与健康人群比,NAFLD合并T2DM患者肠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明显增加[27]。T2DM患者肠屏障功能受损,黏膜通透性增加导致脂多糖增多,后者则是炎症级联反应的触发要素,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TLR)通路导致慢性炎症和IR,加速NAFLD形成。因此,肠菌失调可能是T2DM和NAFLD患者共同的危险因素。
3 促进NAFLD相关肝癌进展
根据18万人群的真实世界研究结果,糖尿病是HCC最强的独立预测因子[28]。与无代谢症状的患者比,DM使NAFLD进展为HCC的风险高出2.6倍,也是最高的危险因素[29]。与非DM组比,在2年内,DM患者发展成HCC的多变量风险比为2.96,2~10年内升至6.08,10年及以上则达到7.52[30]。IR和过量的FFA可促进炎症发展,氧化应激和靶器官功能障碍,最终诱导癌变。ROS水平升高能够损伤DNA,导致基因突变,诱导肿瘤生成。DM能够影响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导致T淋巴细胞比例失调,免疫功能受损[31],恶性细胞即可逃避免疫监视。长期使用MCD饲喂的小鼠肝内CD8+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被激活[32],当进展至NASH阶段时肝内CD4+T淋巴细胞减少[33],驱动NAFLD相关肝癌的发生。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和IGF-2能刺激细胞生长、抑制凋亡。DM患者IR状态和高胰岛素血症减少了IGF结合蛋白水平,对IGF-1和IGF-2的利用率提高,影响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诱发肿瘤形成[34]。肠菌失调在肝癌发生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菌群失调可升高ROS水平而损伤DNA,增加肝癌发生风险[35]。革兰阳性菌细胞壁成分脂磷壁酸也与脱氧胆酸协同刺激TLR2通路,诱导肝星状细胞衰老和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过表达,抑制抗肿瘤免疫[36]。
4 GLP-1与FXR交叉关系
胰高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是一种主要由肠内L细胞分泌的肠道促胰岛素,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在血糖调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GLP-1的多重促代谢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其与NAFLD的关系。研究发现,212例NAFLD患者血清GLP-1水平降低,与IR呈负相关[37]。GLP-1能够激活AMPK通路,调节细胞自噬水平而延缓NAFLD的进展。巨噬细胞在NAFLD慢性炎症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受到GLP-1的调控[38]。过表达GLP-1可致使巨噬细胞从促炎M1表型转变为抗炎M2表型[39]。研究表明,GLP-1类似物利拉鲁肽可显著改善高脂饲喂小鼠血清肝酶学指标,促进肝组织ATGL/Sirt1信号表达,改善肝脏脂质沉积和炎症因子水平[40]。法尼醇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是一种以胆汁酸为天然配体的转录因子,负责维持或参与机体胆汁酸动态平衡、糖脂代谢紊乱和胰岛素信号通路。许多研究结果均表明胆汁酸和FXR失衡是NAFLD患者代谢特征之一。肠FXR能够调控肠内神经酰胺分泌。NAFLD患者体内神经酰胺水平升高加强了SREBP-1c等脂肪酸合成基因表达[41]。应用特异性肠FXR拮抗剂可改善此过程诱导的肝脏脂肪沉积。FXR特异性拮抗剂HS218可通过阻止FXR与PGC-1α启动子的结合抑制糖异生[42]。但也有研究发现肠道FXR激动剂可改善T2DM小鼠的IR状态。这些结果表明FXR激动剂或拮抗剂均可参与维持葡萄糖稳态,但不同的实验结果也提示不同阶段、不同条件或者不同部位的FXR作用可能不同,甚至相反,仍需进一步研究。
5 总结
肝脏是调节糖脂代谢的重要组织,也是胰岛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靶器官。在各种肝脏疾病中,NAFLD最常与DM伴随发生,两者有着相似的发病机制,相互交织加速危害。NAFLD被视为DM流行的驱动力和结果,DM同样促进NAFLD相关肝癌的进展和发生终末期肝病的风险。GLP-1和FXR在维持糖脂代谢平衡方面也有着十分复杂的交叉关系,进一步研究有利于临床药物的转化应用。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减重是防治疾病进展的关键,患者尚需严密检测肝脏病变程度和DM并发症,避免不良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