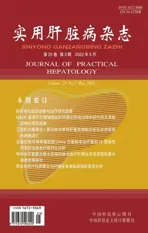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肝损伤机制研究进展*
2022-11-26胡灵溪综述王荣琦审校
胡灵溪,崔 坡 综述,王荣琦 审校
2019年12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2,SARS-CoV-2)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在一年内就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全球性健康和经济危机。截至2021年1月27日,全球报告确诊病例已突破1亿人,导致200多万人死亡。患者多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多数重症患者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症状,严重者可迅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COVID-19除累及肺脏外,可出现肝脏、肾脏、心脏、大脑、免疫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多系统器官病理学改变[1]。研究表明[2],肝损伤在COVID-19患者危重病例中尤为常见,并且COVID-19的严重程度可能是肝功能异常的危险因素。但COVID-19患者肝损伤的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文通过查阅最新的相关研究文献,分析造成肝损伤的机制,为临床COVID-19相关肝损伤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1 SARS-CoV-2的直接毒性作用
通过定量检测22例COVID-19死亡患者尸检组织SARS-CoV-2病毒载量,发现在肺、咽、心、肝、脑和肾脏等多个器官组织存在SARS-CoV-2,说明其具有广泛的器官嗜性[3]。尽管通过全组织匀浆已将核酸分离出来,但确切的复制部位仍未确定。另外,原位杂交分析显示,COVID-19肝组织血管腔和门静脉内皮细胞有SARS-CoV-2病毒的存在[4]。对2例血清转氨酶升高的死亡COVID-19患者肝组织进行活检,电镜分析发现肝细胞胞浆中存在完整的病毒颗粒[5]。由此可见,SARS-CoV-2对肝脏具有趋向性和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
SARS-CoV-2感染的关键是侵入宿主细胞。SARS-CoV-2通过其表面的刺突蛋白(Spike 蛋白,S蛋白)与宿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特异性地结合,S蛋白被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MPRSS2)所切割,从而使病毒进入宿主细胞。通过4例肝移植供者新鲜正常肝组织和9例结肠癌患者正常肝组织的RNA-seq数据分析发现,ACE2在大部分胆管细胞(59.7%)中高表达,在肝细胞中为低表达(2.6%)。ACE2在胆管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与肺泡Ⅱ型细胞的表达水平相当[6]。因此,ACE2作为宿主细胞受体可能是SARS-CoV-2感染和直接损伤胆管的潜在靶点。有报道称[7],在部分SARS-CoV-2患者中碱性磷酸酶和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与胆管上皮细胞损伤相一致,约10%COVID-19患者同时伴有总胆红素水平升高,提示SARS-CoV-2可能直接与表达ACE2的胆管细胞结合,导致胆管细胞损伤。另外研究[8]显示,肝纤维化时肝细胞ACE2的表达增加,故患者既往存在的肝损伤可能会加剧SARS-CoV-2的肝脏趋向性。
有研究将SARS-CoV-2 Spike蛋白结合至水泡性口炎病毒(VSV)假型ΔG-荧光素酶病毒颗粒表面形成表达SARS-CoV-2 Spike蛋白的假病毒颗粒[9],通过人类多能干细胞(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HPSCs)衍生细胞病毒嗜性分析表明,HPSCs衍生的肝细胞被表达SARS-CoV-2 Spike蛋白的假病毒颗粒感染,证明了SARS-CoV-2对肝细胞的趋向性。同时,以SARS-CoV-2感染人类原代肝细胞类器官检测SARS-CoV-2基因组的覆盖率,证实SARS-CoV-2感染导致了强大的病毒复制。在2名已故COVID-19患者的肝组织[5],电镜检查发现在肝细胞中有与SARS-CoV-2病毒明显相似的病毒结构,推测在这些患者中看到的组织病理学改变可能是由SARS-CoV-2的直接细胞病变效应引起的。
2 细胞因子所致的全身效应与局部效应
细胞因子在调节宿主防御和维持体内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干扰素-γ、CXC趋化因子10和CXC趋化因子8等在COVID-19患者血浆中的水平升高[10]。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乳酸脱氢酶和铁蛋白在COVID-19患者中也明显升高[11],并且铁蛋白、CRP、LDH、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D-二聚体升高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增加相关[10]。在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发现,严重急性肝损伤与包括铁蛋白和IL-6在内的炎症标志物升高显著相关[11]。在另一项对来自中国的148例COVID-19患者进行的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发现肝功能检查异常的患者降钙素原和C反应蛋白水平较高[12],表明细胞因子的释放可能诱发和加重了肝功能障碍。
2.1 细胞因子释放的全身效应肝脏对全身稳态的紊乱极为敏感,并通过多种机制受到影响,其中包括血管和免疫介导的途径[13]。众所周知,细胞因子诱导的血管功能障碍、低灌注和氧化应激可引起免疫细胞与内皮细胞粘附,从而增加血管通透性[12]。TNF-α可诱导凝血酶反应导致肺动脉内皮细胞功能障碍[14],损害血管内皮细胞依赖性和一氧化氮(NO)介导的各种血管床的血管舒张功能[15]。细胞因子还可导致活性氧生成增加,进而发生血管渗漏和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16],后者可导致肺泡水肿和缺氧,并使脑、心、肝和肾等器官发生水肿[17],在低动力感染性休克期间,肝脏微循环血流量减少到基线的50%[18]。另外,α-硫辛酸治疗可提高重症COVID-19患者的30 d生存率,表明活性氧的产生在COVID-19的病理生理学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9]。因此,细胞因子释放、低灌注、内皮功能障碍、活性氧生成等导致的肝脏血管通透性增加是细胞因子风暴全身效应导致肝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在高细胞因子血症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TNF-α介导的肺损伤需要血管紧张素Ⅱ的参与[21],血管紧张素Ⅱ与炎症、组织损伤和氧化应激有关[22],其可通过血管紧张素Ⅰ受体诱导炎症反应。ACE2下调使RAAS轴抑制抗炎血管紧张素途径,并增强促炎症血管紧张素Ⅱ-血管紧张素Ⅰ途径,促进血栓形成[23]。RAAS的失衡还通过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的表达、缓激肽积聚、血管紧张素Ⅳ和醛固酮介导的纤溶功能障碍等促进血栓形成[24-26]。肝脏中局部RAAS的存在和RAAS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失衡可在肝细胞炎症和损伤中起关键作用[27]。
2.2 细胞因子释放的局部效应细胞因子释放可在肝细胞中引起急性时相反应造成肝脏的局部损伤[28]。库普弗细胞、中性粒细胞、肝细胞和肝窦内皮细胞介导肝脏对细胞因子释放的反应[29]。肝细胞损伤激活库普弗细胞,释放细胞因子、活性氧和一氧化氮,诱导肝窦内皮细胞持续损伤肝细胞[30]。TNF-α可直接刺激肝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6。由激活的中性粒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可导致过氧亚硝酸盐的形成,损伤线粒体,导致肝细胞坏死和凋亡。肝窦内皮细胞、肝巨噬细胞和白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肝内血流的重新分布,肝窦血流灌注减少[31]。内皮功能障碍、中性粒细胞入侵和微血栓形成进一步加剧了肝组织的缺血和损伤。COVID-19患者的肝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微泡脂肪变性以及小叶和门静脉炎症活动,提示存在病毒或药物诱导的肝损伤[32]。在某尸检病例中发现多个器官有血栓形成,甚至在抗凝后仍存在血栓,在肝组织显示血小板-纤维蛋白微血栓聚集在肝窦内[33]。关于治疗凝血功能障碍的共识声明[13]中提到,SARS-CoV-2感染可引起肺、肝脏等不同器官发生强烈炎症,造成微血管损伤,从而形成广泛的微血栓[34],累及肝脏等器官。因此,肝脏微血栓的发生可能是肝损伤的一个潜在机制。事实上,有新的证据表明,抗凝治疗是COVID-19的治疗策略之一[35]。
3 COVID-19所致的肝脏缺血和低氧
COVID-19相关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仍然是最常见的并发症,需要重症监护治疗,包括有创通气、高水平的呼气末正压和血管收缩剂治疗,以防血流动力学不稳定[36]。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期间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导致的高肺血管阻力可引起右心室功能障碍[37]。另外,COVID-19可致高凝状态,肺血栓并发症的显著发生率加剧急性右心衰竭,从而加重肝脏充血[38]。长时间的缺氧和再灌注损伤是导致肝损伤的原因之一[39]。然而,在大多数病例中,COVID-19相关的肝损伤一般较轻,血清转氨酶水平没有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的5倍,因此不符合缺氧性肝病的诊断标准[40]。在转诊到ICU的危重患者也是这样表明即使SARS-CoV-2感染发生了严重的呼吸衰竭,其代偿机制也可保证肝脏的充足氧供。
4 药物引起的肝损伤
自SARS-CoV-2疫情爆发以来,各种抗病毒药物(瑞希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抗生素(大环内酯类)、抗疟/抗风湿药物(羟氯喹)、免疫调节药物(皮质类固醇、托西珠单抗)和解热药物(对乙酰氨基酚)被用于临床研究,其中大多数药物经体外和体内实验已被证实其潜在的肝毒性。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推荐用于严重SARS-CoV-2感染患者的皮质类固醇疗法,也是明确与脂肪变性或糖原沉积有关[41,42]。另外,目前已出现COVID-19患者使用托西珠单抗导致的药物性肝损伤的报道[22]。托西珠单抗肝脏代谢最低,其肝毒性作用最可能的机制是干扰了白细胞介素-6途径,而后者在肝脏再生过程中起关键作用[43]。
5 肠肝循环是SARS-CoV-2感染肝脏的潜在途径
SARS-CoV-2感染会影响胃肠道,引起恶心和呕吐[43]。值得注意的是,在感染患者和尸检的粪便中都发现了SARS-CoV-2 RNA和活病毒颗粒[44,45],且既往有慢性肝病的患者在感染SARS-CoV-2时更容易引发肠道反应。由于回肠和结肠肠细胞均表达病毒附着的中心蛋白ACE2和TMPRSS2,SARS-CoV-2能够感染胃肠道细胞[46]。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在肠细胞内发现病毒核衣壳蛋白[47]。在人类蛋白图谱数据库进一步证实,在整个人类细胞类型谱系中,肠细胞表现出最高的ACE2表达量[48]。除此之外,胃肠道症状可出现在呼吸道症状之前[49],表明胃肠道可能是SARS-CoV-2感染的部位。因此, 有人推测粪-口传播是SARS-CoV-2的感染途径之一[50]。
另外,肝胆系统可能是感染SARS-CoV-2的另一个途径。COVID-19患者肠道感染可能会破坏肠道上皮屏障和血管屏障,最终导致病毒通过门静脉到达肝脏。肝细胞表达所需的受体结合蛋白,与门静脉循环直接接触。因此,肝脏感染可能始于肝细胞。随后,SARS-CoV-2病毒颗粒通过跨细胞囊泡途径离开受感染的肝细胞,到达胆汁,部分COVID-19患者胆汁SARS-CoV-2 RNA检测呈阳性[28]。因此,胆管细胞也可能接触并感染SARS-CoV-2。由于胆道在肝脏和肠道之间提供了直接的联系,SARS-CoV-2可能通过胆汁到达并感染肠道,进而导致二次感染,由此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增加病毒存活的机会。SARS-CoV-2感染后出现肝脏和肠道症状的患者总体预后较差。
6 基础肝病的恶化
由于与肝硬化相关的免疫功能障碍以及用于自身免疫性肝病治疗的免疫抑制疗法,晚期慢性肝病患者将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51]。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和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会(ESCMID)目前的指南建议,不要减少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的免疫抑制治疗。在1099例COVID-19患者中,2.1%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研究表明,病情较重的患者感染HBV的可能性(2.4%)显著高于非严重病例(0.6%)[52]。迄今为止,大多数COVID-19的研究都没有描述患者是否既往存在肝病病史,需要进一步分析肝病与SARS-CoV-2感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和相关免疫修饰是对单纯性脂肪肝的“二次打击”,并可导致肝脏损伤和脂肪性肝炎。免疫应激在肝硬化患者中可引发慢加急性肝衰竭[53,54]。高龄或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的肝硬化患者,因其全身免疫功能受损,可能更容易受到感染,故感染SARS-CoV-2后预后更差。中、重度呼吸衰竭和肝功能恶化程度较重的患者30 d病死率较高。感染SARS-CoV-2导致肝硬化患者病情由稳定迅速恶化,突显了在肝病患者预防SARS-CoV-2感染的重要性。
7 总结
总之,COVID-19导致肝损伤非常常见,重症或危重COVID-19患者肝损伤发生率显著高于轻症患者。COVID-19患者肝损伤可能由多种机制引起,如直接病毒损害、免疫损伤、药物性肝损伤、全身炎症反应、缺血缺氧和潜在的肝病复发或加重等。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能量代谢器官,肝功能受损严重影响机体的合成代谢和疾病的预后。因此,临床医生在诊断和治疗COVID-19患者时应更加重视肝损害的发生,全面分析COVD-19患者肝损害的发病机制,制定合理的个体化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