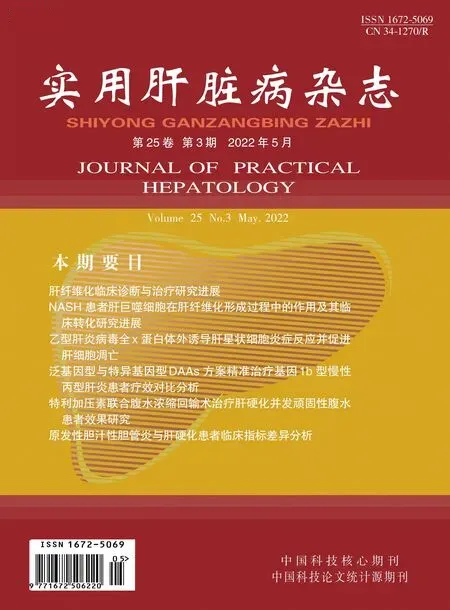NASH患者肝巨噬细胞在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临床转化研究进展*
2022-11-26韩冰涂传涛
韩冰,涂传涛
各种病因所致的慢性肝病及其并发症仍然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严峻的挑战[1,2]。近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发病率急剧增加,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慢性肝病的主要病因[3]。NAFLD是一种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和遗传易感密切相关的代谢应激性肝损伤。NAFLD是一个连续的肝脏疾病谱,可由单纯的肝脂肪变进展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steatohepatitis,NASH)。临床数据显示,15%~20%NASH相关纤维化患者可进展为肝硬化、终末期肝病、甚至肝细胞癌(HCC)[3]。肝纤维化是NASH相关的远期病死率、肝移植和肝脏相关的临床事件最重要的预测因素[2-4]。因此,阻止或逆转NASH及其肝纤维化进展是改善预后的关键,对解决人类健康关切和降低沉重的疾病负担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然而,因NASH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临床上仍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2, 3]。因此,重视NASH形成和进展的机制研究,发掘具有潜在治疗价值的新靶点,不仅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更是临床转化研究的迫切需求。
1 NASH相关肝纤维化形成的细胞与分子机制
尽管NASH的病理学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但仍存在某些共同的促发因素。“多重平行打击”学说的提出有助于理解NASH病理学形成过程[5,6]。一般认为,NASH形成和进展是多因素平行作用的结果,肥胖、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和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伴随IR导致肝细胞脂质沉积为“首次打击”环节。随后,引起的肝细胞脂肪变性、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等因素促进肝细胞损伤和死亡,最终触发炎症反应和肝纤维化形成[3-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打击的强度及其后果在不同程度上还取决于个体遗传背景和表观遗传学的改变。肝纤维化是肝脏损伤-修复的动态过程,是以胶原为主的细胞外基质(ECM)的产生超过肝脏的降解能力,导致ECM在肝脏过度沉积形成所谓的纤维“疤痕”。活化的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是ECM最主要的来源[3,4]。肝细胞损伤和过度死亡触发的炎症反应是导致NASH及其纤维化形成的关键[4-9]。死亡的肝细胞不仅可直接激活HSC和汇管区成纤维细胞,而且还可以通过释放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激活天然免疫细胞(主要是巨噬细胞)促进炎症形成,间接活化HSC;受损的肝细胞产生或激活炎症介质,可调控NLRP3炎症小体激活,致下游caspase-1活化,促进分泌IL-1β和IL-18,参与细胞凋亡[3, 9]。肝脏作为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拥有大量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细胞,如T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B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细胞[10-12]。肝脏免疫细胞富聚的微环境无疑在维持机体免疫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NASH等慢性肝病所致的肝纤维化病理学形成过程中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9-12]。近年的单细胞转录组研究进一步揭示,肝脏免疫细胞图谱很可能通过促进肝脏炎症微环境失控,从而加剧肝损伤,导致NASH及其肝纤维化的形成。
2 肝脏巨噬细胞的来源、表型及其功能
巨噬细胞在体内分布广泛并且具有十分活跃的生物学功能。作为天然免疫系统的主要细胞成分,在机体防御和免疫应答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巨噬细胞具有明显的组织器官异质性。肝脏巨噬细胞由固有的和浸润的巨噬细胞共同组成,前者也称为Kupffer细胞(Kupffer cells, KCs),后者是未成熟的单核细胞由骨髓释放至血液循环,再浸润至肝脏,最终分化为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monocyte-derived macrophages, MdMs)[10-12]。KCs位于肝窦内,占肝内细胞总数的15%,占体内固有巨噬细胞总数的80%~90%,是维持肝脏耐受状态的主要细胞成分。固有的巨噬细胞表达F4/80hi和CD11bint等特异性表面标志物,有助于识别。此外,其表面还分布有高密度的清道夫受体(scavenger receptor,SCR)、Fc受体、补体受体、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 TLR)、Nod样受体和甘露糖受体等。单核细胞或MdMs则表达F4/80int和CD11bhi等特异性表面标志物。巨噬细胞具有较强的摄取抗原并呈递给活化的T细胞或效应T细胞,在进一步活化T细胞的同时巨噬细胞自身也被激活并发挥细胞免疫效应。
有关肝脏固有巨噬细胞的来源问题,近年有新的认识。2013年Yona et al[13]研究认为肝脏KCs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并在成年期通过自身增殖维持其种群。在肝脏损伤早期,KCs数量减少,随后通过自身增殖补充KCs池,浸润的MdMs不参与损伤过程中KCs的补充[13-16]。近年几项重要研究发现,在NASH过程中胚胎源性巨噬细胞自身更新受损,产生了MdMs[15-17]。细胞命运图谱研究表明,NASH小鼠单核细胞(TIMneg巨噬细胞)也参与调配KCs池,且免疫标记研究证实单核细胞来源的KCs位于肝窦内,类似胚胎来源的KCs[17, 18]。NASH患者单核细胞来源的KCs产生是对胚胎来源的巨噬细胞死亡增加的应答反应,旨在维持KCs的数量[16, 18]。巨噬细胞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细胞群体, 主要表现为其所产生的细胞因子、表面标志物和基因表达谱具有显著的多样性[14-18]。深入理解NAFLD形成过程中巨噬细胞异质性,对发掘潜在的治疗策略尤其有价值[10, 14]。活化的巨噬细胞分化或极化(polarization)为两个不同的亚群,即M1型和M2型[10-12]。Th1细胞因子和微生物的代谢产物诱导产生经典激活型巨噬细胞,称为M1型;M2型则由Th2细胞因子诱导产生的替代激活型巨噬细胞。根据表达的活化标志物不同,通常将M2型巨噬细胞分为三个亚群:由IL-4或IL-13诱导的M2a巨噬细胞;由免疫球蛋白Fc受体和免疫复合物诱导的M2b型巨噬细胞; 由IL-10、TGF-β、糖皮质激素诱导的M2c型巨噬细胞[10, 12]。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不仅在功能和基因表达谱上有显著的差异, 而且在代谢作用方面也不同。M1型糖酵解增强, 分解精氨酸产生一氧化氮(NO)增加;M2型依赖脂肪酸氧化,通过精氨酸酶分解代谢精氨酸[10]。
感染早期活化的NK细胞和随后活化的Th1细胞分泌的IFN-γ对巨噬细胞的活化至关重要。细菌产物,如脂多糖(LPS)、TNF-α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也能诱导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活化后的M1巨噬细胞能够产生大量的促炎因子、趋化因子,如 CCL2, CXCL10和CXCL11等、反应性氮和氧自由基。此外,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分解精氨酸生成NO, 直接杀灭细菌和原虫。M1型巨噬细胞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如IL-1、IL-6和IL-23,发挥重要的防御作用,但同时也可以造成组织损伤。M1的激活途径受到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TAT1、核因子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等多重信号通路的调控。不同亚型的M2型巨噬细胞作用有所不同。M2a型巨噬细胞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创伤愈合,组织损伤后释放的IL4可诱导激活M2a并产生IL-4、IL-10、TGF-β、IL-5和IL-13等细胞因子。此外,M2a型巨噬细胞能够间接地发挥免疫调节效应;因M2b和M2c都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而往往被统称为调节性巨噬细胞,但其诱导和分化的刺激信号和具体功能各不相同。M2b活化后产生高水平的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M2c具有抑制巨噬细胞介导的宿主防御和炎症性功能。M2的激活途径受到STAT6和锌指转录因子等信号通路的调控[12, 13]。
3 肝巨噬细胞在NASH及其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子机制
肝脏巨噬细胞在肝脏疾病进程的不同阶段,比如炎症、纤维生成和纤维降解调节过程中发挥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10]。在NASH形成过程中,来源不同的巨噬细胞的功能有所差异。MdMs抑制肝脏甘油三酯沉积,但与胚胎来源的KCs相比,更大程度上能促进肝损伤。此外,巨噬细胞还具有诱导肝细胞凋亡的特性。在NASH患者和小鼠发现巨噬细胞通常在肝脏中成簇或聚集,尤其是在大泡性脂肪变性区域,这些细胞聚集被称为肝花环样结构(hepatic crown-like structures, hCLSs)或脂肪肉芽肿(lipogranuloma),可促进单纯脂肪肝向NASH转化进展[10, 18]。研究还强调,NASH形成过程中巨噬细胞稳态明显被破坏,从而发挥破坏作用[11, 19, 20]。
3.1 肝巨噬细胞在NASH相关肝纤维化形成和进展过程中的作用在NAFLD病理学发展过程中,作为肝细胞损伤的应答反应细胞,Kupffer细胞被激活、表达细胞因子和信号分子[10-12, 14],主要包括炎症因子TNF-α、IL-1β和IL-6,趋化因子CCL2及其受体CCR2途径,参与招募中性粒细胞和循环单核细胞。单核细胞分化为促炎型巨噬细胞,进一步放大肝脏炎症反应,并通过TGF-β1刺激激活周围的HSCs,促进胶原为主ECM的生成[21-23]。此外,活化的KCs还呈现不同的表型,这种极化表型主要取决于其所接受的周围环境信号,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的平衡是调控肝脏炎症的关键[10-13]。KCs的活化和极化的主要途径是需要由肠道进入门脉循环的营养素和肠道源性细菌产物,如细菌LPS激活TLRs而发挥作用[10, 19, 20]。肝细胞损伤相关的分子途径,如富组氨酸糖蛋白(histidine-rich glycoprotein, HRG)和DAMPs[9, 10]。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 FFAs)途径,主要经由脂肪组织的TLRs和脂肪因子,如瘦素通过瘦素受体作用。通过胆固醇及其代谢产物,主要经由CD36和巨噬细胞清道夫受体1作用。肠道微生态是“肠-肝轴”学说的重要基础和纽带,在NAFLD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3, 20, 23]。在NAFLD患者和动物模型均证实,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和肠道通透性增加,导致通过门脉系统进入肝脏的LPS增加, 激活肝脏固有的KCs,而肝脏固有巨噬细胞表达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可能具有抑制NAFLD炎症反应和纤维化的作用。基于肠道微生态的宏基因组标签可将NAFLD患者轻、中度肝纤维化与进展期纤维化进行鉴别。甘油三酯和LPS的结合更易诱导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并招募更多的T细胞和B淋巴细胞。LPS诱导的炎症依赖于ROS介导的X-盒结合蛋白1 (X-box binding protein 1, XBP1)的激活[10]。LPS-TLR4信号通路在肠道和肝脏之间的“互作”中起着核心作用,在NASH患者肝内TLR4表达增加,TLR4+巨噬细胞也显著增加[20]。当Kupffer细胞衰竭时,出现门静脉LPS升高,导致脂肪变性和坏死性炎症,肝组织TNF-α、TGFβ1和胶原表达增加。然而,TLR4信号传导并不局限于Kupffer细胞,肝细胞TLR4信号通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肥胖相关的代谢异常。脂毒性被认为是NAFLD进展的关键机制之一,表现为NAFLD患者脂肪组织分解代谢增强,导致FFAs流入肝脏的量增加。肝脏新生脂肪的增加使整个代谢向导致肝损伤转变。肝细胞脂质沉积过度势必激活肝巨噬细胞促进NASH的形成和进展[19, 23]。不同的FFAs对巨噬细胞的影响方式不同,其中涉及了TLR4-NF-κB、MyD88-PI3K- AKT和NLRP3 炎性小体等信号途径的作用[9, 10, 22]。此外,脂质代谢产物,如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等修饰脂蛋白也都能够直接促进炎症性巨噬细胞的激活,并增加巨噬细胞对LPS诱导激活的敏感性。普遍存在快餐里的氧化脂质可诱导肝脏的促炎状态,可诱导肝脏巨噬细胞数量增加和炎症介质表达,如TNF-α、iNOS和COX2等。棕榈酸、LPS和oxLDL可刺激巨噬细胞产生ROS和促炎细胞因子。高胆固醇也是NAFLD和NASH形成潜在的致病因素之一。在NASH小鼠模型和患者发现,在坏死肝细胞残余脂滴周围形成的hCLS中含有胆固醇晶体。同时,还发现游离胆固醇积聚在活化的KCs转化为泡沫细胞,类似与粥样斑块中的巨噬细胞[10, 14]。脂滴中的胆固醇结晶参与巨噬细胞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从而在肝脏炎症和NASH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在NAFLD病程中,肝细胞损伤和死亡相关的分子可以进一步触发巨噬细胞的激活[2-4, 23]。凋亡小体可能通过肝脏的凋亡细胞或细胞碎片上的氧化特异性表位作为危险相关的分子模式,通过TLRs等模式识别受体,激活KCs。NASH患者肝细胞富含HRG,HRG高表达与疾病分期以及邻近的促炎巨噬细胞相关。体外研究也证实,HRG可诱导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向促炎型巨噬细胞激化[10]。脂毒性肝细胞释放包含CXCL10和TNF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细胞外囊泡,在NAFLD进展过程中促进巨噬细胞的募聚和炎症激活。细胞外囊泡也可能被巨噬细胞内化,导致NLRP3和IL-1β释放上调。ROS可以直接诱导Kuffer细胞产生TNF-α,并增加KCs对内毒素的敏感性。铁超载可以促进氧化损伤,促炎细胞因子释放。由肝细胞、KCs和其他非实质细胞释放的TNF可能以旁分泌和自分泌的方式激活肝巨噬细胞。在NASH小鼠,发现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在肝脏聚集组成脂质相关的巨噬细胞(lipid-associated macrophages, LAMs)[14, 18, 19],类似于纤维化患者肝内TREM2+CD+疤痕相关的巨噬细胞[11],可出现在肥胖的白色脂肪组织。肝脏LAMs多分布在纤维化区域,也称为NASH相关的巨噬细胞[18,19]。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和LAMs位于纤维化组织区域,在活化的HSC侧缘,高表达编码骨桥蛋白的SPP1基因,从而促进肝纤维化的形成。
3.2 肝巨噬细胞在NASH相关炎症消退和肝纤维化降解过程中的作用炎症的消退不再是炎症介质的稀释和消散的被动现象,而是一个暂时性精细调控和相继分泌促消炎分子信号的主动过程[23, 24]。在肝脏损伤阶段,KCs活化会募聚更多的免疫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抗原6C-high (LY6Chi)炎症性单核细胞,它们可以进一步分化为CD11b+F4/80+经典激活M1型巨噬细胞。该表型的巨噬细胞具有吞噬活性并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如IL-12和ROS,能够杀伤微生物和肿瘤细胞。在急性炎症发作期,M1占主导的巨噬细胞也可以通过释放抗纤维化或纤维溶解因子(如MMPs)抑制成纤维细胞的纤维化活性,从而诱导细胞外基质降解或纤维溶解[10, 11]。体外实验发现,典型的M1型肝巨噬细胞的激活可导致MMP7和MMP9高表达,这两种表达在胶原瘢痕中可能是清除胶原纤维所必需的纤维溶解因子。近年来,MMP13也被认为是M1型巨噬细胞在肝脏纤维降解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反,在肝脏急性炎症之后的修复期,肝脏巨噬细胞可以选择性地激活具有免疫抑制但促纤维化表型的M2型巨噬细胞,这些细胞分泌高水平的IL-13、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BB 、TGFβ1等促纤维化因子,并与纤维生成、组织重塑和血管生成增加相关,导致纤维化。M2巨噬细胞也与抗纤维化有关,可能与存在不同M2亚型和重叠有关。M2型巨噬细胞也可表达MMPs,尤其以MMP12最显著,被认为是胞葬和吞噬基质碎片的重要细胞。
在肝纤维化患者和小鼠肝组织,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共存,这两种细胞在纤维化反应中都是必要的[10-12]。具备结合M1型和M2型特征的“恢复性”或“促降解”的巨噬细胞仍不清楚,但这个亚群的巨噬细胞具有抗炎和抗纤维化的特性。这类细胞可在肝纤维化的自发逆转过程中出现,并以上调MMP表达和LY6ClowF4/80+表型为特征[10,23]。
4 基于肝巨噬细胞调控的治疗策略及其临床转化研究憧憬
糖皮质激素受体可以调节Kupffer细胞产生的炎症。通过CD163受体用地塞米松直接靶向巨噬细胞可以降低TNF水平,从而减轻肝脏炎症和纤维化。巨噬细胞半乳糖凝集素3高表达。半乳糖凝集素3抑制剂GR-MD-02可以改善纤维化评分和肝硬化程度。NASH患者KCs表达MSR1上调,阻断MSR1信号途径也能有效抑制脂质诱导的KCs激活,从而改善NASH及其肝纤维化[22]。鞘氨醇-1-磷酸受体4抑制剂SLB736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激活减轻NASH相关的炎症和纤维化[22]。单核细胞募集是NAFLD进展的重要步骤。CCR2-CCR5双拮抗剂Cenicriviroc可以通过抑制趋化因子受体阻止单核细胞向肝脏的募聚,也可直接作用于HSC,从而改善肝纤维化。吡格列酮通过激活PPARγ,在体外可以减轻肝脏炎症和单核细胞或巨噬细胞浸润,并下调巨噬细胞的促炎功能。法尼酸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 FXR),如奥贝胆酸可以下调肝糖和脂质代谢,发挥抗炎和抗纤维化作用。通过精细调控M1/M2型巨噬细胞的平衡是治疗NASH及其肝纤维化的有效策略之一[12, 23, 25]。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P1R)激动剂有许多作用靶点,可减少巨噬细胞的浸润,并使巨噬细胞极化向抗炎表型倾斜,从而促进NASH逆转。Elafibranor是一种双PPARα和PPARδ激动剂,可通过调节肝脏和脂肪组织代谢稳态和炎症,减少巨噬细胞浸润和向抗炎巨噬细胞表型转变。杨梅酮可通过调节巨噬细胞激化减轻肝脏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25]。凋亡信号调节激酶1 (ASK1)Selonsertib可抑制包括巨噬细胞在内的许多细胞从而减少炎性激活。MaR1作为一种特殊促消炎介质(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 SPM),可通过巨噬细胞重编程使其向抗炎表型转化,促进NASH相关炎症的消退[24, 26]。在NASH患者肝组织,CAR-T细胞靶向并消除uPAR+肝星状细胞和巨噬细胞,从而减轻纤维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