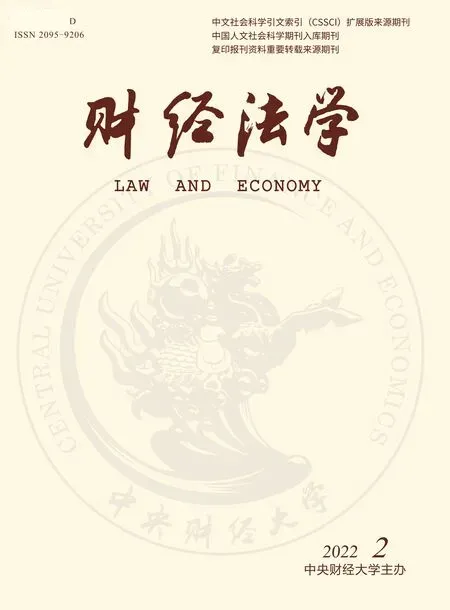民法典语境下交付移转风险规则的体系联动效应辨识
2022-11-26刘洋
刘 洋
内容提要:我国《民法典》在买卖合同一章(第604条以下)确立了交付移转风险的规则,这会在《民法典》规范框架内产生体系联动效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风险负担配置格局对于物上瑕疵责任可适用性有决定功能;二是风险转移会引发损害向债权人迁移,令其溯源性转嫁的规范通道之型塑成为必要。在前一方面,又须从“时间”和“空间”两重维度切入观察。在时间轴线上,物上瑕疵责任得贯通性地适用于从缔约至合同依约履行的整个期间,风险转移不足以成为物上瑕疵责任适用的时间界限,这植根于风险未转移状态下债务人须为标的物性能质量概括负责的规范机理。在空间方向上,风险转移排除了物上瑕疵责任在非可归责性标的物减损案型的适用;但对可归责于债务人的标的物减损,纵在风险转移后亦应承认规范性“瑕疵”和物上瑕疵责任的成立,而非借用一般履行障碍法予以调整。在后一方面,因风险转移的制度作用而迁移至债权人的损害,亦可能基于规范体系联动的范式引导而溯源归咎至他处。其中,就可控的第三人行为造成的损害作为被转移风险指涉的对象时,应藉“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机制或经由《民法典》第1181条第1款第1句之准用,赋予债权人以直接请求权,以此疏通该等损害进一步对外转嫁的规范通道,而非求诸比较法上渐遭扬弃的“第三人损害清算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负担规则是镶嵌于履行障碍规范体系中的一个亚群落,(1)参见韩世远、〔日〕下森定主编:《履行障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年2006版,第25页。在比较法层面,若以德国法为例,代表性的学理讨论,vgl.Emmerich,Das Recht der Leistungsstörungen,6.Aufl.,2005,C.H.Beck,S.154,322.其制度的构成和型塑无疑受到履行障碍法的整体框架这一先在性条件的制约。但与此同时,风险负担规则自身的立法设计以及由此塑造的风险负担配置格局和转移时点,也能以反作用的方式对履行障碍法产生冲击,从而引发规范内部的彼此牵连和体系联动效应。
这种反作用的一个重要面向就表现为:立法者就风险分配状态所作的价值取舍和风险转移的时间界限形成的政策决断一旦落实于具体的法律规则之上,便直接影响物上瑕疵责任的成立和适用。在物上瑕疵责任因风险负担之转移而被排除的场合,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因风险现实化而发生的损失,得否经由法体系内其他合适的制度门径对外转嫁。在事实层面言,前述问题关涉当事人法律地位的优劣和面临风险的强弱;从规范角度论,前述问题牵连着瑕疵给付的规范调整和法律体系的评价一贯,探究和释明的必要性应予肯定。然而,我国私法学理在此方面却着力不多。既有的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研究成果中,不论是聚焦于“交付”行为展开的讨论,(2)参见赵家仪、陈华庭:《我国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与“风险转移”》,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王雪琴:《风险负担规则中的“交付主义”模式之质疑》,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江海、石冠彬:《论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合同法〉第142条释评》,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抑或在整体把握的思维脉络下对风险负担制度内部规范体系所作的梳理,(3)参见宁红丽、耿艺:《合同法分则中的风险负担制度研究》,载《私法研究》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页以下;崔建远:《风险负担规则之完善》,载《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刘洋:《对待给付风险负担的基本原则及其突破》,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还是从法律移植角度对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和《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风险负担立法模式所作的比较观察,(4)参见朱晓喆:《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比较法困境——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14条为例》,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吴志忠:《试论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风险转移》,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李巍:《国际货物销售风险移转问题探讨》,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4期;王传丽:《划拨的概念与法律意义》,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视野都尚有局限,即主要致力于风险负担制度自身教义学构造澄清或其规范要素的厘定,未能有效地关照到风险配置的法政策和法规范对于整个履行障碍法体系,尤其是物上瑕疵责任所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直观地看,这可能与我国私法学理中习惯于把风险负担的适用场景标签化、简单化地固定和指向标的物灭失所导致给付不能的案型有关。可是,只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604条的文义解释出发即能发现,风险负担规则的风险分配功能,也把标的物毁损所产生的标的物瑕疵状况延纳在内,而这却常遭忽视。鉴于此,本文意图以买卖合同中风险随交付转移的规则为切入点,在体系化思维的引导下,揭示和呈现风险转移规则的现行法格局对于物上瑕疵责任之适用及履行障碍法整体框架所产生的“逆向”影响,期能裨益于风险负担、物上瑕疵责任和履行障碍法的教义学理解与司法适用。
二、风险负担配置格局对瑕疵责任可适用性的决定功能
风险负担配置格局对于物上瑕疵责任之成立及其适用范围均能产生影响,此乃风险负担及其转移规则体系联动效应的一个关键面向。对它的认识,又要从风险转移作为物上瑕疵责任成立的“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两个角度切入。
(一)风险转移作为物上瑕疵责任成立的时间界限?
《民法典》第617条是买卖合同中物上瑕疵责任的基础性规范,其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据本法第五百八十二条至第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请求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规则的文义解释出发,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要求而产生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唯当出卖人已完成“交付”行为时方可主张。与此同时,《民法典》第604条又将“交付”设定为风险转移的基准时点。于是,在该两条款的关联与整合之下,就生成了一个学理中普遍接受且广为流传的命题,即:物上瑕疵责任的成立须以风险转移为前提,而风险转移的规范机制则直接划定了物上瑕疵责任的时间界限。(5)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页;宁红丽:《试论出卖人物之瑕疵责任的构成》,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杜景林:《现代买卖法瑕疵概念的考察》,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3期;周友军:《论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1期;许德风:《论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载《法学》2006年第1期。立法层面的实证规范和学理讨论中的基本观念,自然会反映和投射到裁判实践之中。对于物上瑕疵责任的案型而言,一旦面临请求权规范前提的判断时,可说“标的物的瑕疵在标的物风险转移时存在”之语已是习以为常并且理所当然的金科玉律。(6)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商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6)冀0705民初54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终9209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1民初3516号民事判决书。
然而,对于物上瑕疵责任及其请求权为何在风险转移之前被排除的问题,我国履行障碍法的理论研究中,迄今少见认真的省思和讨论。在比较法层面,若以德国私法为参照,《德国民法典》第434条第1款亦存在直接将物上瑕疵的存在与风险移转相挂钩的现象,(7)Vgl.Brox/Walker,Besonderes Schuldrecht,41.Aufl.,2017,C.H.Beck,§4,Rn.21;auch MüKoBGB/Westermann,7.Aufl.2016,§434,Rn.50ff;und Staudinger/Annemarie Matusche-Beckmann,15.neubearb.Aufl.,2014,§434,Rn.160.由此引发的结果是:在德国私法学术界中,“风险负担移转的时点乃为买卖法中瑕疵担保责任的适用添加了必要的时间要素”这一观点也存在相当的市场和附和的声音。(8)Vgl.MüKoBGB/Westermann,7.Aufl.2016,§437,Rn.6;und Staudinger/Annemarie Matusche-Beckmann,15.neubearb.Aufl.2014,§437,Rn.20.这就是说,德国民法实证规范的文义解释脉络之下,也极易导出与我国民法典制度框架下相同的结论,即以风险移转的时点为界碑,此前的时段应当排除于瑕疵担保责任法律效果的涵盖范围之外。(9)Vgl.BGH 10.03.1995-V ZR 7/94;Looschelders,Schuldrecht,Besonderer Teil.,12.Aufl.,2017,Verlag Franz Vahlen,§4,Rn.82;andere Ansicht siehe aber Bamberger/Roth/Faust,3.Aufl.2012,BGB §437,Rn.4ff;und Erman/B.Grunewald,14.Aufl.2014,BGB §434,Rn.68.甚至至今仍然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声援前述观点,强调风险移转对于瑕疵担保责任主张的压抑性功能。(10)Vgl.Jürgen Oechsler,Vertragliche Schuldverhältnisse,2.Aufl.,2017,Mohr Siebeck Tübingen,§2,Rn.83.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是,德国学界主张废除第434条中“风险移转”一词的见解也越发受到重视。(11)Vgl.Gregor Bachmann,Gefahrübergang und Gewährleisutng,zum zeitlichen Anwendung des besonderen Leistungsstörungsrechts,AcP 211.Bd.,H.3/4,(2011),395,396ff.在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履行障碍法作为应时更新的核心内容,买卖瑕疵担保责任制度更是被置于放大镜和聚光灯之下观察,在此背景下,呼吁将“物上瑕疵担保责任”与“风险转移”脱钩的方案浮出水面并受到关注。从债法改革的结局来看,虽“风险转移”之术语依然得以保留,但是,瑕疵担保责任并非唯有在风险移转之后方可适用的命题却正得到迅速传播和日益广泛的接受。(12)Vgl.Wolfgang Ernst,Sachmängelhaftung und Gefahrtragung,Abgrenzung und Wechselwirkungen in der Dynamik des Vertragsvollzugs,in FS Ulrich Hube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2006,Mohr Siebeck Tübingen,S.165 und 169.
深究此一动向形成的根基和正当性,免不了要追问和探寻到底是何种因由的刺激,导致了“风险转移”得以进入立法规则并扮演“物上瑕疵责任”启动机制和时间界限的角色。就此,仍须回归到瑕疵担保责任的属性界定和体系定位。自纵向的历史脉络以观,早期德国法继受并延续了罗马法的思维模式,于买卖交易关系中奉行“买者当心”(caveat emptor)的通行观念,(13)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Roman Fundation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Juta & Co,Ltd,1990,p.307;auch vgl.Heinrich Honsell,Römisches Recht,8.Aufl.,2015,Springer,S.132.其投射到私法制度的建设和规范的设计,便以瑕疵担保责任作为独立、并行于违约行为且基于特有法政策考量而生成的“法定责任”为印迹和呈现方式。由此,在买卖瑕疵给付行为的私法规制问题上,便衍生出一般履行障碍法与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双轨并立、竞争共存的现象。为勘定二者的适用关系,风险转移的时点遂应时成为区隔和界分他们各自辐射领域或覆盖范围的法技术工具。然而,一个世纪的实践早已表明,瑕疵担保的“法定责任说”及建基于此的履行障碍双轨制引发大量评价矛盾和体系悖反,进而招致重重质疑。(14)双轨制前提下,作为法定责任的买卖瑕疵担保责任与一般履行障碍法规则在时效制度建设方面的冲突,是评价矛盾和体系悖反的典型表现方式之一。Vgl.Giesela Rühl,Die Verjährung kaufrechtlicher Gewährleistungsansprüche,AcP 207.Bd.,H.4/5(2007),614,614.2002年通过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正是围绕着整个履行障碍法的制度并轨与一体化统合而展开。该改革工程的实施和完成,令“风险转移”继续停留于物上瑕疵责任规范前提中的正当性危机更加凸显出来:平行式的双轨制履行障碍法体系既已消除,制度转轨和衔接的需求自亦无存,那么,原本担当着连接点和区界符使命的“风险转移”要素又有什么理由不消失呢?(15)《日本民法典》起初亦继受瑕疵担保责任与债务不履行责任二元并行的“双轨制”,但在长期的裁判实践和学理研究中,越来越多反思和批判的声音开始涌现。日本学者能见善久即明确指出,考虑从什么时点开始可以适用瑕疵担保责任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将瑕疵担保责任视为不同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并且前者作为特别规则的残留现象。参见能见善久:《履行障碍:日本法改正的课题与方向》,于敏、韩世远译,载前引〔1〕,韩世远、下森定主编书,第77页。
况且,据德国私法史学者的溯源性考证,《德国民法典》第434条第1款将瑕疵救济规则与风险转移时点相联结,其实是源自立法者对罗马法的错误解读和翻译。事实上,罗马法中对应性的市政官救济措施的触发和启动,并非与风险转移相联结,而是直接与合同缔结的时点相联结。(16)Vgl.Jan Harke,Das neue Sachmängelrecht in rechtshistorischer Sicht,AcP 205.Bd.,H.1(2005),67,75.这意味着,罗马法语境下的市政官救济完全能够涵盖合同履行的全过程。只不过,在罗马法的规范框架中,随着合同的成立,将同时发生风险转移的法律效果。(17)参见〔德〕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43页,边码21。缔约告成和风险转移两个时点的完全融合,极易给人带来的误会是,似乎买受人之所以可以物上瑕疵为由寻求市政官救济的庇护,恰由于标的物风险已经转移。而实际上,这背后真正机理的揭示和发掘,恐怕只有在结合罗马社会时空场域中唯以特定物买卖为常态和典型并且合同的缔结能直接促成所有权转移两项要素时,才算走上了正道。也就是说,缔约时点所承载的多重意义和复数功能之中,不是风险转移的伴生效果,而是给付内容瑕疵状态的基本定型,决定了市政官救济通道的开启。
对上述判断结论,还可从风险转移时点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时推移及其影响获得印证。在罗马早期,买卖合同主要呈现为现货即时交易形态,缔约、所有权变动、交付基本在同一时点发生,再把风险的转移附着于缔约之时,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可是,随着历时交易模式的出现和逐渐膨胀,缔约和交付之间就形成了或长或短的时间缝隙,于尚未取得标的物直接占有之前,买受人却已须基于合同成立而承受无法自行掌控的风险,此无异于把买受人的命运置于对方支配之下。这种利益格局难以持久,在照顾买受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下,风险转移机制所依托的规范基准终推迟至交付时点。该项制度变迁的意旨无非在于,买受人得因而免于为其尚未占有标的物情况下所无从防免的标的物减损、灭失负责,反面言之,交付之前标的物的减损、灭失均应由出卖人承担。可见,风险转移时点的向后推移,非但没有抑制债权人就物上瑕疵寻求救济的内涵,其本旨反倒在于扩大债务人的负责范围和提升债权人的法律地位。
由上可知,自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对于摄入“风险转移”用语的《德国民法典》第434条,妥当的解释论方案应当是:迟至风险转移发生之前,只要标的物遭受性能、质量方面的降低、减损,皆须由债务人负责,并可界定为规范意义上的“瑕疵”;而非认为所谓的“风险转移”设定了物上瑕疵责任及其对应请求权得以适用的时间界限。
以此为鉴,回归到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中,自亦不宜将第617条规则的适用主张和瑕疵责任法律效果的发生,限定于风险转移及交付行为发生之后。为此,须排除对该条作反面解释的方案。因为,它虽然从正面以积极的方式确认了,已交付的标的物被发现瑕疵的场合,应当赋予债权人以瑕疵担保责任的相关救济权,但却并没有直接从反面否认,如果尚未交付便已经能够终局性地确认物上瑕疵存在的情况下,径行于风险负担移转之前发动瑕疵担保责任之主张的可能性。只不过,对于“瑕疵”的存在和认定,应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而已。这实际上也是“请求权人须就其所主张的请求权之成立应当具备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之一般法理在瑕疵给付救济领域的具体应用和落实。就该举证责任之履行而言,固然不排除某些案型中举证难度的升高或负担的加重,比如瑕疵在性质上属于尚可消除者即为适例,但从反面而言,亦可能出现债务人严肃认真且终局性(ernsthaft und endgültig)地表示拒绝消除瑕疵、瑕疵在性质上属于无法消除者、综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情事显然可推断出债务人将不会消除瑕疵等(18)参见詹森林:《危险负担转移之前,出卖人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及买受人拒绝受领标的物之权利》,载《台大法学论丛》1992年第1期;颜佑紘:《买受人之拒绝受领权》,载《台大法学论丛》2019年第3期。举证难度降低或负担减轻的案型。总之,举证负担不应成为物上瑕疵责任之适用范围延伸及于风险转移之前的障碍。
实际上,类似于上述解释路径,允许债权人在履行期届至之前介入主张契约救济的规范性制度和条款,在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并非孤例。《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2项、第578条对预期违约的承认及其责任制度的配套建设,正是为债权人于履行期届至之前打开救济大门的极佳例证。故此,在体系解释的脉络之下,为避免评价矛盾发生和确保体系融贯的实现,(19)参见雷磊:《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兼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方新军:《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也应当摒弃以风险转移作为物上瑕疵责任必要条件或时间要素的观念。
另外,前已述及,风险转移作为物上瑕疵责任适用之时间界限的观念,历史上原为应对一般和特别履行障碍法的界分机制问题及其规范需求而生成,嗣后又因统合性债法改革方案的推行而消褪。与此恰成对照的是,我国民法的履行障碍制度建设从来就没有因循和袭用僵化的“特定物教条”,以此为基础衍生的“法定责任说”和“双轨制”无由存在;债务人的无瑕疵给付义务在立法(《民法典》第615条、第616条)、学理(20)参见吴香香:《〈合同法〉第142条(交付转移风险)评注》,载《法学家》2019年第3期;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55页。也有学者以出卖人的“标的物适约义务”加以指称。参见武腾:《买卖标的物不适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17年版,第98页。和裁判实践(21)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4135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书;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5民初5461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向得到认可。这种立足于统合思维而塑造形成的“单轨制”规范框架下,(22)详细的分析论证,参见韩世远:《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我国合同法》,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李永军:《论债法中本土化概念对统一的债法救济体系之影响》,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并没有调和、界分特殊性和一般性给付障碍法的规范需求,自然也不必假借风险转移的规范机制,追求或达成限缩物上瑕疵责任及其救济效果之适用范围的目标。单从这一点来看,可说我国民法在履行障碍制度的设计上,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优于《德国民法典》的地基上。
由上可见,不论基于比较法的参照借鉴,还是从我国实证规范的体系、历史解释出发,均不应认为风险转移未发生具有阻碍物上瑕疵责任适用的效果。事实上,只要进一步挖掘风险负担配置的制度本旨和规范功能,恰会导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详细而言,风险转移规则及其法定范围的确定本质上是对合同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和负责范围的重新调整。精确地说,其主要是对债务人责任范围的限缩与负担的减轻;而债权人方面则会产生此消彼长的对应性变化,即直接导致其责任范围的扩张和负担的加重。反面言之,风险负担的不移转便意味着并且决定了,就标的物性能、质量降低进而偏离于应然状态的情形,不论债务人方面有无过错,其皆须一揽子地承担概括性的责任、自行吸收由此衍生的损失。而这正是物上瑕疵责任的内容。所以,风险尚未移转的状态与买受人对于瑕疵救济权利的主张绝非相互排斥、无法兼容的关系,而正是因为风险负担停留于出卖人方面的状态决定了其应当不分过错地为物上瑕疵承担责任。而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说,其亦不必等到标的物交付完成、风险转移之后,方才行使瑕疵担保责任制度框架下的各项救济权,提前行权反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预防性的功能。
这清晰地显示了,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中,于风险负担转移到买方之前,风险负担及相关损失均落于出卖方的肩头。但是,在该基本价值判断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物上瑕疵责任制度的规则加以实现。也就是说,物上瑕疵责任制度在风险移转之前的适用,本质上是承担了落实风险负担规则内容的功能。(23)参见前引〔12〕,Wolfgang Ernst文,第165页以下。简而言之,在风险移转之前的时段区间,以出卖人负担风险损失作为隐藏线索,债权人主张瑕疵担保责任作为外显线索,前者决定了后者应予适用,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变相表现形式。
(二)风险转移作为物上瑕疵责任成立的空间界限?
基于上文的分析论证可知,在时间坐标的维度,物上瑕疵责任的规范效力实际上得贯通于从缔约至给付义务完全如约履行的整个区间。但就风险转移与物上瑕疵责任互动关系的全面把握而言,仍有必要在度量的视野中添加“空间”的切口。这一面向的讨论意在勘定风险转移机制对于物上瑕疵责任“物的适用范围”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前已论及,风险转移本身承载着对当事人负担进行调整和更新的功能。在固有内涵的意义上,相较于风险转移之前的区间,债务人于风险转移之后的法律地位得到优待和提升,肇因于非可归责于其的物上减损甚或灭失风险,均已跳转到债权人方面。因而致使标的物性能质量重新出现实然状态低于应然状态的场合,亦排除规范性“瑕疵”之存在。相应地,债权人也无权要求债务人承担瑕疵责任或者主张由此衍生的相应请求权。(24)Vgl.Daniela Dylakiewicz,Kaufrechtliche Sachmängelgewährleistung und allgemeine Prinzipen des Vertragsrechts,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der deutschen Sachmängelhaftung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nternationaler Entwicklungen,Dissertation der 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2003,S.80.可见,风险负担的转移直接压缩了物上瑕疵责任的适用空间和调整范围,致使风险转移时点之后,物上瑕疵责任制度的辐射能力止步于非可归责性的标的物减损现象之门前。这正是风险转移波及物上瑕疵责任“物的适用范围”的表现之一。
不过,设若嗣后肇致物之减损的因素可归属于债务人负责,则由此引发的损失不为“风险移转”的范围所覆盖,(25)参见前引〔10〕,Jürgen Oechsler书,边码491。必须转嫁到债务人一边。可有待厘清的是,应依托何种制度路径或借助怎样的规范管道以期有效地实现此种损失转嫁的目标。于此案型,单从外观考量,似乎能将可归责于债务人的标的物减损界定为规范意义上的“瑕疵”,并借以启动物上瑕疵责任的适用。然而,不应忽略的问题是,风险之转移是否会在体系效应上阻塞物上瑕疵责任制度适用的通道。
这种顾虑并非杞人忧天。从我国立法机关所主编的释义书针对《民法典》第617条所作的解释来看,在立法者的理念中,风险转移还构成了瑕疵判断的关键节点。(26)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46页。其实,这种观念在我国学界目前具有相当的影响。有学者明确指出,在买卖物之瑕疵的认定上,应以“风险转移之时”作为基准时。(27)参见秦静云、宋汝庆:《论买卖物之瑕疵的认定》,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卢谌:《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以法律原因引用为中心》,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1期;前引〔5〕,崔建远书,第446页。换言之,只有在风险转移之前即已存在的标的物性能、质量方面与应然状态的偏离,(28)参见金晶:《〈合同法〉第111条(质量不符合约定之违约责任)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3期;前引〔5〕,杜景林文。才能构成规范意义上的“瑕疵”,从而导致瑕疵给付语境下救济手段的触发和相应规范的启用(29)参见刘怡:《试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物之瑕疵担保制度的完善》,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反之,若风险转移完成之后出现的减损或性能、质量降低,就已经不再属于瑕疵给付救济手段能够辐射和覆盖的范围了。从效果来看,这种认识实质上通过“瑕疵”概念的外延框限,令风险转移取得了决定物上瑕疵责任及其相应救济制度得以适用的空间范围的功能。
如果把视野扩大至比较法,上述现象在德国同样存在。从《德国民法典》中履行障碍规范框架的设计及其演化历程观察,基于交付行为而引致的风险移转,直接在“物的范围”上严格框定了作为物上瑕疵责任必备要素的“瑕疵”出现的可能场合,(30)Vgl.Palandt/Weidenkaff,72.Aufl.2013,§434,Rn.8;auch siehe AnwK-BGB/Büdenbender 2005,§437,Rn.7.从而也同时划定了物上瑕疵责任可得适用和发挥损失转嫁功能的“空间界限”。由此,只有当风险负担移转之前即已存在,且于风险移转当时未被消除的性能偏差,才能认定为“瑕疵”,并受物上瑕疵责任的规范调整。(31)Vgl.AnwK-BGB/Büdenbender 2005,§434,Rn.84 und 85.反之,若风险转移之时并无瑕疵,仅仅嗣后由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因素引发的物上减损,虽亦应予以救济,但却并非通过债法分则专为买卖合同设计的瑕疵担保责任这一特殊制度,而是应当返回债法总则,以《德国民法典》第280条作为请求权基础,求助于积极契约违反的方式加以实现。(32)参见前引〔10〕,Jürgen Oechsler书,边码88。也就是说,站在《德国民法典》实证规范的框架下,风险负担对于整个履行障碍法体系的反作用还表现为,它将自身融入成为瑕疵救济请求权之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瑕疵”判定的前提,先在性地规定了物上瑕疵责任制度的适用空间,并直接型塑了债法分则与总则之间的交互关系。举例来说,如果出卖人交付货物于第一承运人时,未能合理妥善地履行包装义务,但标的物本身并无质量、性能等方面的瑕疵。在此场合,风险负担的移转将不受影响。然若在途货物恰因包装纰漏而遭受减损,此时便须否认“瑕疵”的存在与物上瑕疵责任特殊规则的适用。(33)Vgl.Malte Stieper,Gefahrtragung und Haftung des Verkäufers bei Versendung fehlerhaft verpackter Sachen,AcP 208.Bd.,H.6(2008),818,845.如欲令瑕疵标的物的修理、更换等更适当的救济方式重新成为可能,除非迂回至债法总则损害赔偿法的规范群落,借“恢复原状”的手段(《德国民法典》第249条)落实“损害赔偿”的目的和效果,(34)参见李承亮:《损害赔偿与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否则别无他法,瑕疵担保责任特有的修补履行或者替代交付的救济方式将被排除适用。在此意义上,德国债法改革后,就履行障碍法的体系而言,分则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责任存在相当的特殊之处,改革之初所预设的整合目标,仍旧未能完全实现。(35)参见前引〔10〕,Jürgen Oechsler书,边码80、83;Vgl.Haas,NJW 1992,2389.
回归到我国《民法典》合同编,须特别注意的是,从外在体系来看,作为瑕疵担保责任诸种救济方式的规范基础,《民法典》第582条直接位于合同编通则。这便已经与德国债法的规范体系设置有所不同。(36)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第582条已成为我国法语境下不完全履行的一般性条款,我国履行障碍法采取的是纯粹的救济进路作为规范建构理念,与德国履行障碍法差异明显,此观点和论证富有启发性。参见武腾:《救济路径下不完全履行的定位和效果》,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3期。更何况,该条所要求的适用前提中,唯以“履行不符合约定”的状态为必要条件,至于引发该状态的因素究竟出现于风险移转之前抑或其后,却并不具有《德国民法典》债法框架中那般重要的规范意义,亦非我国《民法典》瑕疵履行救济制度进行规范评价的对象。因而,德国法背景下,风险负担之移转对于物上瑕疵责任嗣后适用如此强烈的排斥效果,不宜直接植入对我国履行障碍法相应规则的解释适用之中。(37)参见王利明:《中德买卖合同制度的比较》,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即便风险移转之后,只要合同义务的内容尚未得到完全履行,嗣后再因为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导致标的物性能质量低于应然状态,没有理由不承认规范意义上“瑕疵”的存在以及物上瑕疵责任的适用和调整。(38)参见余延满:《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负担的比较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一般而言,前述所谓“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因素”往往由债务人附随性义务或者保护性义务的不完全履行而引发,比如货物包装不善、承运人选择不当、运输指示错误、航线选择疏失等等。诸如此类的场合,标的物本身并无瑕疵,风险自应移转。只不过,如若嗣后标的物自身亦受殃及,则须受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制而已,(39)同旨参见李大何:《论附随义务及其救济方式》,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该文中,作者明确指出,附随义务的保护对象并非仅限于固有利益,同样存在着将履行利益或积极利益纳入辐射及覆盖范围内的空间,故违反附随性义务的场合,完全可能导致“修理、重作、更换”等瑕疵责任制度框架下所特有的救济手段适用的结果出现。风险移转的事实亦不足以对此有所妨害。
综上所述,风险负担规则不单是履行障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它也能对履行障碍法产生非常重要的反作用。不论是对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和利益格局以法定的方式重新调整,抑或于风险移转之前,转用物上瑕疵责任的途径实现风险分配的内在功能,还是物上瑕疵责任的适用空间在风险移转完成之后的限缩与适用性的维持,可说均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系着风险负担规范的正面功能或者反射效应。这也恰恰体现了大陆法系规范框架中相当重要的体系关联的思维方式。
另外,前述分析也展示了,就我国履行障碍法的体系而言,瑕疵担保责任整合入债法总则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越于改革之后的德国债法。不仅在构成要件上,“瑕疵”不被限定于风险移转之前,而且在法律效果上,瑕疵担保责任成立之主张也不必等待风险移转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履行障碍法规范框架下的物上瑕疵担保责任,不仅在外在体系上立足于债法总则,(40)我国《民法典》虽未设置形式意义上的债法总则,但仍应承认,合同编通则大量条文其实担当了债法总则性规范的功能和角色。司法实践中,只要裁判者精准辨识,就能妥当地确定相应法条的体系定位。换言之,形式债法总则的欠缺,并不影响对我国《民法典》中实质意义上债法总则规范群的承认。参见翟远见:《论民法典中债总规范的识别与适用》,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也有学者鲜明地提出,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存在着“四阶层”的构造,其第一层也是适用范围最广、位阶最高一层的规范,便是实质意义上的债总规范。参见张谷:《民法典合同编若干问题漫谈》,载《法治研究》2019年第1期。而且在内在体系上,也俨然呈现出一般性规范的明显特质。(41)就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之贯通互动,详参方新军:《融贯民法典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的编纂技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2期;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在履行障碍法规范体系的建构上,采纳和贯彻的思路乃是统合制和一元化的路径。(42)同旨参见前引〔22〕,韩世远文;严之:《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合同法〉中的定位》,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至于检验期间与通知义务的规定,不过是根据买卖合同法自身所调整对象而做出的补充性规定,(43)一个批判性的分析讨论,参见武腾:《合同法上难以承受之混乱:围绕检验期间》,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无法改变制度整合的事实。这相较于德国债法框架下买卖合同法瑕疵担保责任与债法总则履行障碍法关系上依旧残留的割裂或者二元对立,(44)参见王洪亮:《物上瑕疵担保责任、履行障碍法与缔约过失责任》,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有明显的不同。围绕这一论题,我国民法学术界曾经一度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且形成“二元竞合论”与“一元统合论”的观点对立,(45)参见崔建远:《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定性与定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迄今尚未能达成共识。对此,如果从买卖合同价金风险及其对于瑕疵担保责任与履行障碍法体系反作用的角度切入观察,或许能够为问题的消解和共识的达成提供一种别样的视野。基于前文的释论,在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一元制及统合论更加契合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实证规范的内容与体系架构,且在某种意义更能迎合未来契约法发展的基本潮流和趋势。
三、基于风险转移的损害错置及其填补路径
风险转移规则在与履行障碍法互动的过程中,还可能引发损害的迁移或错置,进而令此种损害转嫁管道的疏通或其填补路径之探寻成为颇值关注的问题。此乃风险转移规则之体系联动效应的另一个面向。
具体而言,这种损害迁移现象的发生,集中于风险转移之后非可归责性因素造成标的物减损的场合。从直接的结果来看,此等案型中的物之减损,正是风险转移指涉的对象和涵括的内容,因而首先由买受人承受。(46)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终14322号民事判决书。本案涉及批量化的酒品买卖合同,出卖人办理托运并将标的物交付第一承运人后,货物在途灭失,买受人遂以未收到货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支付的货款和赔偿损失。法院以风险随交付行为的完成而转移为据,驳回买受人诉讼请求。实践中采行此种裁判思维并验证该种结论的案例十分常见,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663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3民终3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3民终2187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民终331号民事判决书等。但若有意地追究和发掘背后的原因,便可发现该“非可归责性因素”的概念之下,涵盖了形色各样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惹起原因的脉络之下,损害的进一步归咎和转嫁或许是可能的,故有必要再作考察。为此,可运用类型化的思维工具,将“非可归责性因素”整合区分成不可控的自然、社会性因素和可控的第三人行为两种基本情况。
对于不可控的自然、社会性因素来说,其表现形式同样丰富而多元。它既可以呈现为伴随着运输过程而存在的典型危险,比如装卸及在途磨损、温度变化而引发自燃、海水冲刷产生水渍等不可控的自然事件,(47)参见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7)苏0214民初4244号民事判决书。还囊括了长途乃至远洋运输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没收(征收)、(48)参见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9民终133号民事判决书。战乱或者其他不可控第三人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等社会性因素(比如海盗)(49)Vgl.Medicus/Lorenz,Schuldrecht II Besonderer Teil,17.Aufl.,2014,C.H.Beck,§75,Rn 56.;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2.Bd,Besonderer Teil,1.Halbband,13.Aufl.,1986,C.H.Beck,§42,S.102;Staudinger/Roland Michael Beckmann,15.neubearb.Aufl.2014,§447,Rn.26;Soergel/Huber,12.neubearb.Aufl.1991,§447,Rn.63ff.。当然,不论自然事件抑或社会性的因素,二者在法律效果方面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是源于出卖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其损失皆归属于债权人承受,并且债权人还无从借助于一定的规范管道将前述损害对外转嫁,除非存在保险机制的介入。不过,当存在保险合同之时,债权人多具有受利益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从而能够取得直接的保险金请求权,或者亦可经由代偿请求权的主张和适用,令保险金请求权归属于自己。这时的法律关系清晰明确,无待多论。
但若“非可归责性因素”导源于可控的第三人行为,这种案型中的利益格局与法律关系图景便呈现出另一种样态,故须详述。举例言之,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独立的第三方承运人,而运输途中,因承运人的过错导致标的物严重损毁。于此场合,买卖合同上的价金风险已经随着标的物交付运输而从出卖方转移到买受方。纵使毁损灭失因承运人的不当行为导致,鉴于交付完成之后的运输行为已非出卖人的义务内容,亦超出其负责的范围,该承运人并非“债务人为履行其自身的义务而自愿纳入行为领域”(50)Fikentscher/Heinemann,Schuldrecht,Allgemeiner und Besonderer Teil,11.Aufl.,2017,De Gruyter,§70,Rn.826;前引〔7〕,Brox、Walker书,第3节,边码29。,故不得被界定为履行辅助人。从而,承运人的过错不得被归属为债务人负责的对象,亦即此时标的物上出现的毁损灭失乃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因素导致。根据《民法典》第607条,该损失性质上属于风险的现实化,由买受人负担:一则其不得主张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二则,其自身根据买卖契约负担的价款义务不受任何影响。(51)不同观点,参见Dietrich Schultz,Preisgefahr und Gehilfenhaftung beim Vesendungskauf,JZ 8/1975,240,240 ff.然而,尚待澄清的问题是,承运人的不当行为或者过错应当如何处理,债权人如欲将损害向可归责的承运人归咎,又应当借助于何种适当的制度路径。(52)此乃我国交易及裁判实践中的常见纠纷,比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沪高民四(商)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终21645号民事判决书均属典型代表。
就此,通常情况下,出卖人与承运人之间订立了运输合同,而且,在途货物于其灭失之时,所有权亦保留在出卖人方面。(53)司法实践中,也有些法院认为随着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标的物所有权便直接转移到了买受人一边。参见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8民终1583号民事判决书。不过,货交第一承运人并非完成向买受人的交付,在我国法语境下能否导致动产物权的直接变动实际是有疑问的。这在本案判决中却被完全忽略,故判决径直认定货交第一承运人导致物权转移显得武断、值得商榷。由此,可供出卖人选择的路径,除了可以是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不无可能。不过根本性的障碍却在于,出卖人并不存在需要填补的损失。究其原因,其通过买卖合同订立而意欲获得的经济利益——价款——已经得到绝对的固定和保障。况且,通过该买卖契约的履行,其初衷本来就不欲继续保留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出卖人不得向承运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作为与出卖人相对的一方,买受人虽然履行了全部的价金支付义务,而物上利益的享有却未能如愿。且不言标的物所有权尚未转移,即便标的物上的实际占有权能都无从获取。(54)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申5574号民事裁定书。更有甚者,设若买受人已经提前与其他第三人达成转卖契约,不仅其通过转卖行为所可能赚取的增值利润消灭,后手交易对象完全有可能主张其承担违约金给付或者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诸此种种表明,因物之毁损灭失衍生的损害已经转移到买受人一边。而问题的症结却在于,买受人与承运人之间既无契约关系,又由于买受人所有权的缺乏而不得主张绝对权(所有权)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55)Vgl.Jochen Bernhard,Holschuld,Schickschuld,Bringschuld-Auswirkung auf Gerichtsstand,Konkretisierung und Gefahrübergang,JuS 2011(1),9,12 ff.
至此,风险转移规则所肇致的体系悖论和规范冲突之窘境得以揭示:出卖人固然享有请求权基础,但“损害”这一规范要件的不备,足以将其该请求权掏空和虚置;与此相对,买受人尽管遭受了实实在在的损害,而主张损害填补所必要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却无处找寻,这使其主张损害赔偿的要求失所依托。(56)相同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描述,也可参见朱晓喆:《寄送买卖的风险转移与损害赔偿》,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设若严格拘泥于这一形式逻辑,将造成受损害人保护不足、加害人却脱逸法外的不当结果。显然,这种利益格局因有悖于正义的法感而令人难以接受,应予修正。为此进行纠偏的具体方法选择上,无非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即令出卖人或者买受人其中一者取得针对作为加害方的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下,将分别就这两种可能的损害赔偿实现路径展开分析。
首先,若采进路一,即允许出卖人直接向承运人主张损害赔偿,又可能存在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虽然从举证责任之轻重与加害人免责可能性之大小出发,学理上一般认为,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请求权人更加有利,(57)Vgl.Brox/Walker,Allgemeines Schuldrecht,41.Aufl.,2017,C.H.Beck,§20,Rn.39.但是此种情境下,请求权的选择并非有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损害要件的缺失才是根本阻碍。在我国现行民法的规范框架内,目前尚未有合适的工具突破此一困局,为出卖人的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打通规范渠道。考察我国审判实践中涉及风险转移所致的损害错置案型,会发现司法者往往存在如下裁判趋势或倾向,即一方面基于风险的转移而否认债务人的责任承担,另一方面习惯性地将损害赔偿的实现或赔偿请求权的主张引向债权人和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中。(58)比如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终12006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商终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4民终1605号民事判决书等案中,皆清晰地呈现出此种判决逻辑和惯性。个中原因,应当说出卖人方面损害要素的欠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于此背景下,若将视线投向比较法,或许能借横向比较之助力为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提供启示。以德国为例,也是为了该种问题的有效解决,其法学界发展所谓的“第三人损害清算理论”。其要义是,在请求权与损害相割裂的案型中,为了防止加害人不当免责,从公平正义的基本观念出发,例外地突破“请求权人不得要求赔偿己身之外第三人所受的损害”这一损害赔偿法基本原则,(59)Vgl.Ulrich Büdenbender,Wechselwirkungen zwischen Vorteilsausgleichung und Drittschadensliquidation,JZ 19/1995,920,920;“daß der Anspruchsinhaber stets nur seinen eigenen Schaden,nicht aber den Schaden eines Dritten geltend zu machen befugt ist.“使用“损害向请求权人处转移”的法技术,(60)Vgl.Medicus/Lorenz,Schuldrecht I Allgemeiner Teil,21.Aufl.,2015,C.H.Beck,§64,Rn.864. “schlagwortartig kann man also sagen,dass bei der Drittschadensliquidation der Schaden zum Anspruch gezogen wird.“借以填补损失缺乏的空隙,从而扫清出卖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道路。只不过,此时所请求的赔偿,并非填补卖方自己遭受的损害,而是作为买受方损害清算的工具而已。该道路固然缓解了债法上风险转移引发的损害赔偿法困局,却滋生了另一重窘境,即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如何划定。究竟仅限于该标的物的实际价值,还是应以买卖合同的价款额度为准,抑或买受人逸失的转卖利益以及可能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亦可纳入赔偿范围?对此问题的解答与澄清,该理论显得捉襟见肘,甚至置之不理,(61)Vgl.Frank Peters,Zum Problem der Drittschadensliquidation,AcP 180.Bd.,H.4(1980),329,372.以至于无法为损害赔偿义务人法律地位的安定性提供充分的防护。
当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暴露出来,在此起彼伏的批评和反思浪潮中,要求完全废弃该理论的声音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为加速该“第三人损害清算理论”的死亡进程,新的解决方案应运而生。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种观点是:探寻出路必须回归问题的缘起,而该语境下问题之产生,主要生发于风险转移与所有权的分离。所以,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此处入手。为此而不得不强调,债法上风险负担规则的根本目的在于,调整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且主要局限于契约上的价款请求权何时应当被绝对性地固定下来。然而,与其他第三人的外部关系,却已经跃出了该规范预设的调整范围之外;(62)参见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5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书。本案涉及大批量的墙地砖买卖合同,标的物在途因承运人过错而浸水全损,买受人针对承运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裁判文书明确指出:货交第一承运人的风险转移规则“只是对买卖合同双方的风险负担规定,并非对运输合同双方的规定”,承运人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自己过错导致的货物损失。相应地,免除第三人本来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自然亦非其期待的效果(63)参见前引〔61〕,Frank Peters文,第345页。。鉴于此,在进行损害赔偿法上的规范评价时,应当直接忽略债法上风险负担规则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出卖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便可以顺畅地请求、主张和完全实现。其后,再重新回归到契约内部买卖双方关系的平衡上。在这个环节,再赋予买方以代偿请求权,通过债权让与,即可实现损害赔偿请求权从出卖人向买受人的转移。(64)参见前引〔59〕,Ulrich Büdenbender文,第921页。
可见,这一方案的核心思想在于对风险负担与所有权的关系进行调整,精确地说,主要是变更风险负担的状态,使之与所有权的归属保持一致。于此,便产生如下疑问,即:既然能够对风险负担规则加以扭曲,使之服从于所有权归属,(65)Vgl.Stamm,Rechtsfortbildung der Drittschadensliquidation im Wege eines originären und rein deliktsrechtlichen Drittschadensersatzanspruchs analog §844 Abs.1 BGB,AcP 203.Bd.,H.3(2003),367,385ff.那么,为何不能从反面入手,以风险负担规则为纲,而所有权归属随之作调整。况且,从利益归属的角度来看,交付主义风险负担规则之所以能够打破债务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其正当性基础恰在于,交付乃是买卖契约履行的核心要素,借此基本上实现了经济意义上所有权的实质性转移。本着“风险利益相一致”的基本原则,有必要赋予交付行为以转移风险负担的功能与法律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后一路径经由“请求权向损害处转移”的法技术运用,能够使买受人本人获得针对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仅免除了经由代偿请求权之转介及债权让与而完成追索求偿的繁琐与曲折,并且有效地隔离了出卖人破产的风险,(66)Vgl.Thomas Henn,Zur Daseinsberechtigung der so genannten “Drittschadensliquidation“,2011,Duncker & Humbolt Berlin,S.294 ff.使其救济的获取和满足不会因出卖人破产而受殃及,显得更加合理和可行(67)参见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8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书。此案出卖人收款后将标的物交付承运人(本案第三人),法院明确指出:“第三人应按照约定将货物运送到原告处,交付给原告,而第三人至今未能将货物交付给原告,应承担货物不能交付的损害赔偿责任。”。于是,思维的脉络自然地被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即买受人的赔偿请求权及其规范构造。
如欲切换并尝试通过转向第二条路径来建构恰当的规范通道,就要使买受人自行取得针对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与我国司法实践的通常判决模式和努力方向相吻合。不过,此目标的达成,尚须依托于具体、适切的制度管道。检索审视我国裁判实践,可以提取出一种频繁见诸判决文书的理由说辞,其多以买受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所谓的“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为名,(68)参见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5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商终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推导出买受人由此可针对承运人直接主张赔偿请求权的结论。不得不指出,“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的概念运用,极易引发“事实契约说”的联想。而在纵向时间轴的视野中,该说早已在理论变迁和演进的历程中遭到扬弃,(69)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188页。故司法实践中的此种论证路径并不值得赞同。鉴于此,仍应另行探索妥当的规范路径。如从请求权基础搜寻的角度出发,可首先考虑经由“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的渠道实现买受人方面请求权获取的效果。为此,又要在案情事实(小前提)与规范要件(大前提)之间的匹配度进行目光往返和逻辑检验。尽管当事人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针对合同内容作出个性化的特殊约定,但不应否认从教义学构造的视角切入并提炼出规范共性的可能性。基于学理通说中的共识,“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之适用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包括:第三人须与债务人之给付义务及其履行具有“接近性”,以致其亦应被纳入基础合同关系的保护范围内;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须为第三人的“忧戚”或“福利”负责,从中导出债权人要求把第三人利益纳入基础合同保护领域存在充分且正当的理由;第三人对于债务人是可预见性的;第三人须值得保护。(70)参见前引〔57〕,Brox、Walker书,第33节,边码8以下。对应到寄送买卖中,虽然运输合同大多由出卖人与承运人直接缔结,而被运输的标的物却以买受人作为收货人,且由其承受全部意外毁损、灭失之风险。可见,买受人与运输契约的接近性及罹于风险的可能性应予肯定。而出卖人在买受人保护上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出卖人须做好充分的运输准备、谨慎选任运输人、合理指示并确定最佳运输路线、妥善包装标的物等保护性义务。更何况,运输契约的订立与履行也正是为了买卖契约的履行和结清。(71)参见前引〔65〕,Stamm文,第396页。至于承运人对于第三人之存在的预见可能性,考虑到货物恰以买受人作为最终交付的对象,肯定此一要件的满足应无障碍。最后,由于买受人并不享有直接针对承运人的契约上履行请求权,故有必要对其给予特殊的保护。职是之故,于此场合,应当认可借“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的制度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范围扩张及于第三人(即买受人),允许其直接针对承运人主张损害赔偿,令“有损害但无请求权”的困局得以化解。我国《民法典》尽管并未直接将“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的制度固定下来,但这完全可以借助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或依托诚信原则推导生成。(72)Vgl.Looschelders,Schuldrecht Allgemener Teil,17.Aufl.,2019,Verlag Franz Vahlen,§9,Rn.5 und 6.
当然,若契约上某些特殊因素或者当事人特别约定,排除了契约请求权主体范围扩大的可能性,则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实现买受人的保护,也是值得考虑的突破口。前文曾提及,从风险转移之后法定的利益归属状态出发,可以经济视角下的所有权实质转移为由,修正所有权状态以适应风险移转的法律利益格局,达成赋予买受人以直接请求权的目的。不过,所谓的“经济性所有权实质转移”毕竟无法在实证法的规范体系中寻得确实的法条依据。因而,此种将经济生活中具体的商业现象混同于规范概念的思维方式难获赞同。不过,在侵权法的规范框架中,类如寄送买卖的法律关系,同一侵权行为导致实际损害转移至绝对权享有者以外第三人的情形并非绝对地无从寻找。恰相反,在生命权侵害的案型中,该“损害转移至别处”的状况并不鲜见。举例来说,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81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因侵权而死亡者的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一规则调整的对象正涉及绝对权(生命权)被侵害之后,损失却于并非该权利实际享有者的第三人(近亲属/死者承担抚养、扶养、赡养义务的人)处发生的情形。为应对该特殊状况,该条直接赋予第三人以法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从法律关系与利益格局的基本构造观察,寄送买卖与之并无根本性的分殊。因而,可以通过类推适用的方式,(7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267页;屈茂辉:《类推适用私法价值和司法适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将《民法典》第1181条第1款第1句的规则直接准用于寄送买卖的案型,(74)类似观点,参见前引〔65〕,Stamm文,第366页以下。一则能实现第三人(买受人)利益的有效保障,防止本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人(承运人)不当免责,二则,也不会向原本并无契约上请求权的第三人提供过分的优待,殊为可取,值得赞同。
对比前述两个路径可知,寄送买卖中之所以出现此种损害赔偿的困局,主要根源于所有权与风险负担未能完全实现同步的变动。相应地,补救之途也便在于,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与缝隙,最终使请求权基础与损害之所在同归一处。审视比较法的范式可知,德国学理为解决该问题而发展出的“第三人损害清算理论”存在损害赔偿范围不确定、制度繁复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值得采纳和推崇。相反,“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的理论既能承担起促使请求权与损害再次粘合的重任,又与我国审判实践在此类案型中的一贯趋向相合致,颇值践行。从比较法的动向来看,德国法律改革与学术观点的变迁历程也能清晰印证此种方案的合理性。具体而言,德国1997年运输法(Frachtrecht)改革进程中,其立法者考虑到因寄送买卖而订立运输契约的案型,该运输服务不仅时间上紧随买卖合同之后,而且契约履行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也是以促成买卖合同的完全履行为导向,这些使得运输合同中“保护第三人”的特质尤为明显。结果,修订后的运输法明确肯定了收货人(买受人或其代理人)针对承运人直接享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75)Vgl.Oetker,Versendungskauf,Frachtrecht und Drittschadensliquidation,JuS 2001,Heft 9,833,841.另外,即便个案的特殊情形或者契约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排除了这一道路,也能够借类推适用的方法,将《民法典》第1181条第1款第1句的法理思想转用于此,赋予买受人以直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就对出卖人—承运人—买受人三方各自的利益均给予了充分的关照,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四、结 论
基于交付的风险转移规则,在我国私法实证规范体系中已经确立有年。然而可惜的是,我国民法学理中对于该规则的认识,迄今似仍未成功地发掘其“潜藏于水下”的另一面,即其与物上瑕疵责任的适用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损害迁移效果和转嫁通道之型塑。如今随着民法典时代的到来,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对于体系性的思维和视角的呼唤与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在此背景下,考察和厘定风险转移规则的体系联动效应于理论及实务层面皆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就此种体系联动效应的辨识,首先可从风险转移机制及其配置格局对于物上瑕疵责任之适用范围的影响切入。这一宏观视野之下,又可析取出横向的“时间”维度和纵向的“空间”维度两个切面加以揭示。在“时间”维度的坐标轴上,从风险负担及其转移规则本身对于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和负担轻重的调节功能出发,恰恰是风险未转移的状态决定了,债务人须不分过错地对于标的物性能、质量的降低和减损一揽子地承担概括式的责任,进而导出物上瑕疵责任即便在风险转移之前亦可适用的结论。于“空间”维度的延伸线上,在风险转移完成之后,基于风险转移的规范机理,非可归责于债务人的标的物减损正是被转移风险的内涵所指,物上瑕疵责任之适用于此被径直排除;不过,一旦债务人就风险转移后标的物性能、质量之降低和减损仍存可归责性,则依然要承认规范意义上“瑕疵”的发生和瑕疵救济请求权的成立。由是可知,风险转移并未划定物上瑕疵责任的时间界限,也不足以阻碍物上瑕疵责任得从缔约到合同完全依约履行整个期间内的贯通性适用;但从“物的范围”出发,风险转移之后,物上瑕疵责任的适用面临着“空间界限”的框定。由此看来,风险配置格局其实决定了物上瑕疵责任的可适用性及其辐射领域的广狭。
风险之转移导致非可归责性的损失向债权人方面迁移,在此利益格局下,进一步追溯损失发生的缘由和源头,债权人得否将自己蒙受的损失再次对外转嫁和归咎的问题便浮出水面。此属风险转移规则体系联动效应辨识的第二重任务。循此脉络探究,损失源头植根于可控的第三人行为之案型,须澄清的问题是:应经由何种制度途径或规范管道,令债权人之损失向第三人的转归成为可能和可行。
就此,比较法的学理中曾提出所谓的“第三人损害清算理论”以为应对之策。但因其未能妥善界定赔偿范围,以致沿循不同的规范依托可能导出殊异的结果,又无法摆脱过分造作和繁复之讥,且这一构造模式下,债权人须承受债务人破产的风险,故目前而言,该范式已在此起彼伏的批评声浪中渐遭扬弃,不宜引入我国现行法的框架。立足于我国民事立法的现行状态,可以站在“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制度的基点,使债权人得在承运合同“第三人”身份的庇佑之下,被纳入承运合同的保护领域;或在“附保护第三人效力契约”之制度门径难以畅行的场合,借助于《民法典》第1181条第1款第1句所蕴含法理思想的提取和准用,赋予债权人以针对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由此跨越因损害和请求权相割裂离散所形成的规范鸿沟,促使债法上风险转移的效力得到恰当界定,并在体系联动的视野下实现损害迁移和顺畅溯源、精准归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