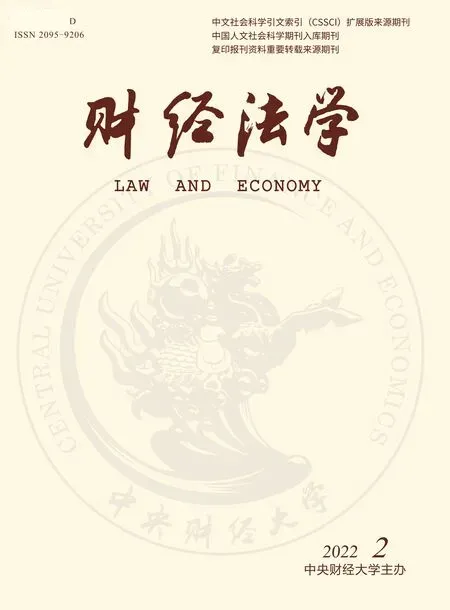刑事诉讼中人脸识别证据的理论界定与规则构建
2022-11-26赵敏
赵 敏
内容提要:人脸识别证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已实际应用,但规范缺失。基于人脸识别证据的形成机理及其科技性、盖然性、复验性和信息关联性特点,可在现阶段将人脸识别证据定位于鉴定意见类证据。但刑事诉讼中人脸识别证据与典型鉴定意见类证据在基本特点、形成机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有必要构建符合人脸识别证据特点的证据规则。我国应理性看待现行鉴定意见规范,适度参考域外规则的合理内核,从取证、举证与质证、认证三方面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人脸识别证据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人脸识别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个人身份识别与验证手段,(1)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脸识别技术在APP应用中的隐私安全研究报告(2020年)》,载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006/t20200608_283970.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2日。并以实时而高效的显著技术优势在域内外治安管理与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以中美两国为例,我国公安部早在2015年就在反恐活动中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数据库内是被列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越狱逃脱的服刑人员的数据资料,可以实现每秒识别5个人的身份。参见《公安部专家:“人脸识别”已用于反恐》,载http://www.cac.gov.cn/2015-06/01/c_1115476484.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7月6日。2018年,人脸识别技术已在我国16个省、市、自治区被广泛用于安防领域,并在各类刑侦、治安案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参见《“天网”:给安防装了双敏锐“法眼”》,载《工人日报》2018年3月23日,第6版。2019年4月,潜逃3年多的北大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被人脸识别系统查获后落网。参见《人脸识别如何通过4次抓拍对比助力警方抓获北大弑母案逃犯》,载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02501,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7月6日.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于2014年建立了人脸识别数据库,授权超过18000个执法机构共享使用。See Joseph Clarke Celentino,Face to Face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Evidence:Admissibility under the Post-Crawford Confrontation Clause,114 Mich.L.Rev.,1317(2016).美国国土安全部一直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审查进入美国国境以及特定活动区域的个人的身份。See John T.Wolak,Mitchell Boyarsky,Randy A.Gray,The Biometric Standards:How New York Measures Up in the Face of Biometric Use Regulations,available at https://www.law.com/newyorklawjournal/2018/06/01/the-biometric-standard-how-new-york-measures-up-with-regulations/,last visited on Feb. 11, 2022.聚焦刑事司法领域,人脸识别应用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查明已羁押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二是通过大规模实时监控查获已知面部数据的犯罪嫌疑人,三是利用案发现场照片或视频中的人脸图像识别并确认未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3)See Clare Garvie,Alvaro Bedoya,Jonathan Frankle,The Perpetual Line-Up:Unregulated Police Face Recognition in America,available at https://www.perpetuallineup.org/,last visited on Feb. 11, 2022.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人脸识别证据实际上已成为犯罪指控与刑事裁判证据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从取证、举证到质证、认证都缺乏适用规范性,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被置于传统证据阴影之下的隐性存在与默认状态。(4)我国的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笔者以“全文”检索模式搜集含有“人脸识别”关键词的刑事案件判决书919份,其中仅显示600份可供查阅,经逐一查阅,遴选出涉及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案件85件,该数据截止到2021年8月16日。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取人脸识别证据的任意性问题。考察来自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85份刑事判决书发现,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铁站、公园景区、宾馆、住宅小区等入口处以及交通路口都部署了具备人脸识别功能且与执法数据库互联互通的实时监控设备,一旦识别出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的人员便会立即自发报警;而公安民警也有权自行决定使用“警务通”等人脸识别系统,随时对履职中发现的可疑人员进行人脸识别,(5)在多起妨害公务案件中,案件起因均系有关人员当场拒绝公安民警对其进行人脸识别而发生争执所致。参见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1)沪0120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20)闽0302刑初67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7刑初82号刑事判决书。或者将人脸图像输入系统后查明涉案人员身份。而无论是远程实时人脸识别还是个案人脸识别,启用人脸识别系统的决定权与执行权都一并掌握在办案民警手中,缺乏必要的程序制约机制。
第二,人脸识别证据的举证与质证有名无实。进一步分析85份刑事判决书发现,当公诉方分组出示证据时,一般将人脸识别证据编入其他证据进行概括性证明,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忽视甚至架空了人脸识别证据的证明作用;同时,纵然有辩方提出人脸识别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公诉方也仅是作出应付性答辩,未针对人脸识别证据何以证明待证事实这一质疑作出具体解释说明。(6)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4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谢某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辩护人亦提出无法证明视频中戴口罩的女子是谢某,同时认为谢某随身携带的黑色IPhone11手机有可能是其姐姐送给其的,故本案指控证据不够充分。公诉人回应称公安机关通过视频人脸识别锁定被告人谢某,人像清晰。”这实质上都变相损害了辩方的质证权。
第三,法庭对人脸识别证据存有主观倾信。对比分析85份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方提交的证据与法庭采信的证据发现,法庭对公诉方提交的人脸识别证据均无异议、照单全收。比如在“杨吉松抢劫案”中,虽然人脸识别平台对监控视频中的男子(戴头盔、面罩,仅露出眼睛、鼻子部分)与被告人杨吉松进行人脸图像比对后的面部相似度仅为34%,但法庭依然采信了公诉方提交的人脸识别证据。(7)参见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1刑初1311号刑事判决书(杨吉松抢劫一审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证人耿某对监控视频中戴头盔、面罩,露出眼睛、鼻子部分的男子进行辨认后确认是被告人杨吉松,并有人脸识别平台对监控视频男子(戴头盔、面罩,仅露出眼睛、鼻子部分)与被告人杨吉松进行一比一人像比对,结果显示相似度为34%印证证实。”这一做法既没有意识到人脸识别错误带来的错认风险,也没有严格把握证据的证明力,体现出审判人员对公诉方提交的人脸识别证据的一种主观倾信,或者说在采信证据之前就已先入为主地认可了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此外,人脸识别证据的表现形式缺乏独立性与规范性。在85份刑事判决书中,人脸识别证据没有单独或统一的表现形式,而是被列入“破案经过”等情况说明材料或者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法定证据形式当中。这既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人员对人脸识别证据内涵的模糊认识,也体现出规范引导这一新型证据运用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人脸识别证据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厘清人脸识别证据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论内涵,进而缺乏专门证据规则的引导和规制。当前,我国学界对人脸识别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脸识别的法律属性、侵权风险、制度框架等宏观问题,(8)参见胡凌:《刷脸:身份制度、个人信息与法律规制》,载《法学家》2021年第2期;杜晓河等:《遏制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载《人民法院报》2021年6月3日,第2版;王俊秀:《数字社会中的隐私重塑——以“人脸识别”为例》,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林凌、贺小石:《人脸识别的法律规制路径》,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7期;蒋洁:《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侵权风险与控制策略》,载《图书与情报》2019年第5期。还没有针对人脸识别的证据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门探讨。放眼域外,美国学界基于较为深厚的证据法理论积淀和前沿的人脸识别技术实践优势,已就人脸识别证据的应用规则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对我们研究人脸识别证据、构建专门证据规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为了有效纠正人脸识别证据运用的无序状态,促进刑事司法公正,我们有必要剖析人脸识别证据的形成机理,明确其特点和定位,辩证借鉴域外规则的合理内核,立足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构建符合人脸识别证据特点的证据规则。
二、人脸识别证据的形成机理、内在特点与实践形式
作为刑事证据领域的新生事物,人脸识别证据的形成机理与传统证据相比具有显著特点,而解析其形成机理,深入分析其内在特点,是厘清人脸识别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区别并明确其实践表现形式的基础。
(一)形成机理:从人脸识别结果到人脸识别证据
人脸识别技术,是根据一个人独有的面部特征,自动识别或验证人的身份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9)See Facial Recognition,ELEC.FRONTIER FOUND,available at https://www.eff.org/pages/face-recognition%20,Last visited on Aug.12,2021.其主要功能是身份确认和身份识别。其中,身份确认功能是将未知身份的人脸图像同已知身份的人脸图像进行“1∶1”比对,以确认两张人脸图像是否指向同一个人,系统输出结果只有是或否;身份识别功能是将采集到的未知身份人员的人脸图像与特定数据库中的海量人脸图像进行“1∶N”比对,以识别一个人的身份,系统输出结果是相似度较高一个人或几个人。相比之下,“1∶N”的身份识别功能在刑事侦查的同一性判断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侦查部门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过程涉及人脸图像处理、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分析、数据比对、计算机决策、数据存储等多项数据处理任务,整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环节:一是图像处理与数据采集环节。在这一环节,侦查人员将源于案发现场的人脸图像输入人脸识别系统,或者由人脸识别摄像头将拍摄到的人脸图像传输至系统,系统基于特定算法,首先对图像进行人脸检测、面部关键点检测、人脸对齐、(10)人脸对齐主要是针对输入的人脸图像的尺寸大小不一、角度也不一的问题,根据人脸关键点坐标调整人脸的角度使不同的人脸对齐(比如将脸部置于图像中点,以及旋转脸部至相同的水平线且缩放到统一尺寸)。参见赖心瑜等:《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属性识别方法综述》,载《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21年第12期。人脸姿态及灰度标准化、人脸数据增强(11)比如通过对图像进行缩放、旋转、移动及模糊等操作进行数据增强。等基础处理,然后在矫正后的人脸不同部位创建特征点,测量各特征点之间的距离并提取测量值,(12)See Ari B.Rubin,A Facial Challenge: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arpenter Doctrine,27 Rich.J.L.& Tech.,1(2021).最终形成一套唯一的面部特征数据代码,称之为“人脸模板”。二是数据分析与比对环节。人脸识别系统对“人脸模板”的眼部、鼻部、嘴部等不同部位进行属性定位和标记,提取不同部位的位置信息和纹理信息,然后将“人脸模板”与专门数据库中的人脸图像进行数据分析和比对。(13)See Bridget Mallon,Every Breath You Take,Every Move You Make,I’ll Be Watching You:The Use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48(3)Villanova Law Review,955-988(2003).三是数据匹配与结果输出环节。人脸识别系统根据人工设置的匹配系数,从数据库中筛选出不低于匹配系数或者相似度较高的一份或几份人脸图像;根据特定算法,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输出的是一组盖然性的匹配结果,即数据库中哪“几个人”更有可能是被识别人脸图像中的那个人。(14)See Emmanuel Abraham Perea Jimenez,The Fourth Amendment Limits of Facial Recognition at the Border,70 Duke L.J.,1837(2021).
根据人脸识别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完成以上三个环节的数据处理任务即可生成一个或一组盖然性结果。但此时的人脸识别结果并非人脸识别证据。人脸识别结果强调的是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而非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生成的结果,即按照人脸识别技术原理与方法行事,基本可以生成一种具有客观中立性的结果;而人脸识别证据强调的是人脸识别结果具有被特定主体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而非其他事实或假说的资格。由此,要实现从人脸识别结果到证据的跨越,关键在于识别结果是否能够被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进一步说就是实现识别结果相对于案件事实的合法性、真实性和相关性。(15)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128页。然而,在现阶段技术条件下,人脸识别的算法设计、数据输入、参数设定、结果分析认定等环节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脸识别程序实际是人与机器两方主体共同参与、客观性与主观性交互影响的过程,其理论精确度和鲁棒性在现实复杂场景中的表现并不理想,要实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相关性,需要在数据源头、程序运算和结果认定等层面进行规范性引导,处理好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原始数据及程序运行的客观性,至少使识别结果的匹配度达到明显的优势证据标准。
首先,在数据源头层面保障人脸图像及提取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如果涉案人员的人脸图像并非由侦查部门直接采集或提取,而是由被害人、证人等其他涉案人员提供,则在深度伪造技术(16)“深度伪造”一词,是“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和“Fake”(伪造)两词结合而成的新单词,它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产生的新的伪造技术,其主要技术表现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时伪造他人面部表情和声音,并将其合成为新视频。比如,“ZAO”等手机APP,可以非常便利地将视频中影视明星的脸换成用户自己的脸。参见李怀胜:《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事制裁思路——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为例》,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4期。已走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人脸图像及面部数据就存在被主观伪造的可能性,所以增强识别客观性的重要途径就是确保用于识别的静态照片或动态视频为原始证据。其次,在程序运算层面实现人脸识别的算法优化、透明和普遍认可。人脸识别系统根据预置算法将提取的面部数据与数据库的“人脸模板”进行比对,(17)See John Edgar Hoover,The Role of Identification in Law Enforcement:An Historical Adventure,46 St.John’s L.Rev.,613-616(1972).而算法的源代码是科技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智力成果,具有一定的认知局限性,(18)笔者认为,即便算法中的运行逻辑符合理想状态下人脸识别的客观规律,但算法的呈现依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属于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因而不仅需要持续提高算法的精确度和鲁棒性,(19)See Andrew Jason Shepley,Deep Learning for Face Recognition:A Critical Analysis,Arxivlabs §§IV,VI(Jul.12,2019).还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算法公开,允许对包括算法在内的人脸识别原理和方法开展行业专家论证和法庭质证。再次,在结果认定层面避免人为干预。当人脸识别系统输出结果后,技术人员往往会对结果进行验证、对比和筛选,这便在某种意义上人为更改了系统识别结果,减损了识别结果的真实性与相关性,故而需要注重维护识别结果的真实性,避免非必要的人为介入。
(二)内在特点:基于形成机理的基本特征归纳
考察人脸识别证据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这种以人脸识别技术为支撑的新型证据与传统证据的形成机理具有显著区别,而人脸识别证据有别于传统证据的内在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科技性。人脸识别技术是人脸识别证据形成的技术基础,也是人脸识别证据区别于传统证据或者其他新型证据的最显著特征。从人脸图像的实时拍摄到面部特征定位、数据提取、“人脸模板”比对、识别结果输出等,识别结果的形成过程是以人脸识别技术为基础的数据化运行程序。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技术的助力下,人脸识别算法可以在反复运算中实现自我优化,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场景的能力,增强证据形成过程的智能化。
二是盖然性。尽管人脸识别的准确度在长期的研发测试与日常应用中已经有所保障,(20)从技术试验数据看,人脸识别结果确实具有较高的准确率。比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对全球近200个人脸识别系统作了研究,发现性能最差的系统的错误率不超过1%。参见前引〔12〕,Ari B.Rubin文,第1页;Michael McLaughlin,Daniel Castro,The Critics Were Wrong:NIST Data Shows the Best Facial Recognition Algorithms Are Neither Racist nor Sexist,available at https://itif.org/sites/default/files/2020-best-facial-recognition.pdf, last visited on Feb. 11, 2022.但在复杂场景、数据分布不平衡等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就复杂场景而言,采集设备质量、光照条件、佩戴墨镜等遮挡物、人像姿态动态变化等因素都会对人脸图像质量产生较大影响,(21)See William Crumpler,How Accurate are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s and Why Does It Matter?available at https://lab.imedd.org/en/how-accurate-facial-recognition-systems/,last visited on Feb. 11, 2022.而对同一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相貌以及同卵双胞胎等问题,目前没有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法(22)参见余璀璨、李慧斌:《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综述》,载《工程数学学报》2021年第4期。。同时,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算法模型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23)参见前引〔10〕,赖心瑜等文。在数据训练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一类人群的样本数据过多而另一类样本数据过少等问题,致使实践中产生识别错误。(24)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深色皮肤女性的人脸识别错误率高达35%,人脸识别系统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识别准确率较低已不言而喻;再如,根据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警察局统计,该局在2020年上半年实施70次人脸识别,其中有68次的识别结果都是黑人。See Th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Part II):Ensuring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Use,available at https://oversight.house.gov/legislation/hearings/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part-ii-ensuring-transparency-in-government-use,last visited on Feb. 11, 2022;Steve Lohr,Facial Recognition Is Accurate,if You’re a White Guy,N.Y.Times(Feb.9,2018);Kami Chavis Simmons,Futur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The Problem with Privacy,Poverty,and Policing,14 U.Md.L J.Race,Religion,Gender & Class,240(2014);Bianca A.White,The Invisible Victims of the School-to-Prison Pipeline:Understanding Black Girls,School Push-Out,and the Impact of the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24 Wm.& Mary J.Women & L.,641,646-648(2018).所以,在现实条件下,人脸识别证据不是确定无疑地证明某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是就某一个或几个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作出盖然性证明。
三是复验性。人脸识别主要是对人的面部特征进行数据化处理的机器运算分析过程。在以数据为内容的识别过程中,技术人员可以反复对同一份人脸图像进行数据分析,也可以换用其他研发企业的系统对识别结果进行反复验证,即在保持检材完整性的条件下,通过数据化的形式实现检材的无限次检测和验证。
四是信息关联性。当人脸识别系统从数据库中输出比对成功的特定个人信息时,此时的个人信息却不仅包含被识别人的清晰面貌、姓名、住址等,还可能含有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工作状况、社会交往、通讯及活动轨迹等信息,使得侦查人员完全可能通过一张照片窥探一个人的近期生活全景。此外,在大规模联网识别过程中,街头巷口的网络摄像头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脸识别,同时也对路过摄像头的任何人进行识别,而非涉案人员的人脸图像都会被永久存储在数据库中,成为未来面部数据比对程序中的潜在对象,面临着可能被错误识别的风险。
就此,相对于传统证据而言,人脸识别证据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种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证明犯罪主体身份同一性,并能够实现证明过程及证明结果反复检验和信息关联的盖然性根据。但作为一种由新兴技术孕育的新生事物,人脸识别证据究竟以何种证据形式呈现更为规范合理?
(三)实践形式:基于内在特点的证据形式定位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人脸识别证据没有独立的证据形式,基本上被混编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这三类法定证据形式当中,也有刑事司法人员将人脸识别证据作为侦查说明材料使用。(25)参见雷小政:《“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至于人脸识别证据可以采用哪种证据形式,需要结合不同证据形式的特点作具体分析。
1.人脸识别证据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及技术侦查说明材料之间具有本质区别
视听资料作为一种证据载体,通常表现为录音带、录像带、电影胶片等高科技材料,(26)参见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66-167页。所要记录的主要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声音、图像、活动画面,而评价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属于视听资料,主要依据其所记录内容的性质及其证明目的。相比之下,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据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数据,其记录的内容通常表现为网络聊天记录、电子签名等形成于互联网和通信网络中的交换信息。(27)参见前引〔26〕,何家弘、刘品新书,第171-175页。虽然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都是运用电子信息技术、以数据形式对案件信息的记录,但其本质上都是以动态、直观的形式对案件事实或涉案行为的客观呈现,本身并没有附带除案件事实之外的倾向性意见。
作为实践中“情况说明材料”的一种形式,技术侦查说明材料主要是公安、检察机关对实践中利用通信监控、场所监控、隐匿身份侦查等手段收集证据材料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等情况的说明,其本质上是对技术侦查行为的过程事实的一种客观记录和陈述,属于过程证据的范畴。(28)参见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对人脸识别证据而言,人脸识别的整个过程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一种数据分析和事实判断,其中的分析判断过程已不再是单纯地对案件事实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以同一性认定为目标对犯罪行为人身份的盖然性证明。所以笔者认为,人脸识别证据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及技术侦查说明材料具有本质区别,相互之间不具有证据形式上的适用性。
2.人脸识别证据与鉴定意见类证据的同质性
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在案件发生后,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形成的一种鉴别意见,(29)参见前引〔15〕,陈瑞华书,第307页。反映了专业鉴定人在案发后对特定专门问题的主观判断,所以学界将鉴定意见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科技性、意见性和事后性(30)参见邱爱民:《科学证据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0页。。相比之下,人脸识别证据在理论上同样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参与检测,同样具有科技性,同样是在案发后形成的判断性分析意见,所以笔者认为,在基本特征符合的宽泛条件下,可以将人脸识别证据列归鉴定意见类证据,并在实践中暂且参照鉴定意见这一法定证据形式适用。
三、构建人脸识别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尽管人脸识别证据可以采用鉴定意见这种证据形式,但进一步看,人脸识别证据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产物,其与指纹证据、DNA证据、人像鉴定证据等典型鉴定意见类证据具有显著的不同点,(31)See Gary Edmond,et al.,Admissibility Compared:The Reception of Incriminating Expert Evidence(I.E.,Forensic Science) in Four Adversarial Jurisdictions,3 U.Denv.Crim.L.Rev.,31(2013).况且我国现行鉴定意见规范缺乏程序性制裁效果,难以有效规范人脸识别证据的应用行为。这实质上都体现出构建符合人脸识别证据特点的证据规则的理论和现实必要性。
(一)人脸识别证据与指纹证据、DNA证据的区别
一是在识别准确度方面,传统鉴定意见类证据具有更为成熟的技术原理和方法,一次性鉴定的准确度往往高达99%以上,而这一准确度是人脸识别证据的盖然性所无法企及的。二是在可测试性方面,传统鉴定意见类证据的检材具有鲜明的生物或物理特性,鉴定过程中无法实现同一检材的多次反复利用,而以数据为基础的复验性却正是人脸识别证据的优势。三是在信息关联性方面,传统鉴定意见类证据的鉴定过程及其结果一般直接指向某一特定对象,并且无法在鉴定完成的同时获取被检测人员的个人信息,但人脸识别证据具有独特的信息关联性。
由此笔者认为,尽管可以将人脸识别证据定位为鉴定意见类证据,但人脸识别证据与指纹证据、DNA证据之间仍有显著区别,而其客观差异性意味着构建符合人脸识别证据特点的证据规则具有内在的必要性。
(二)人脸识别证据与人像鉴定证据的区别
一是在概念位阶方面,人像鉴定是我国声像鉴定的法定种类之一,是指就检材中目标人的五官形态特征、体型特征、衣着特征、体态特征等与样本照片或视频中的被检验人的上述特征是否具有同一性作出判断,(32)参见我国司法部于2020年印发的《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13条及附件;张大治、向宁、周鹏:《低质模糊视频人像的综合性检验与同一认定》,载《刑事技术》2015年第4期。而人脸识别仅是对诸多人像特征中涉及面部特征的部分进行识别并作出同一性判断,(33)参见曾锦华等:《人脸识别技术在人像鉴定中的应用研究》,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2期。也就是说,人脸识别证据是人像鉴定证据的下位概念。二是在检验方法方面,人像鉴定主要是由鉴定专家对源于案发现场的人像照片与源于侦查实验或被鉴定人的其他人像照片进行人像特征的全方面测量和对比,鉴定专家的个人经验和能力在鉴定中发挥着主要作用,(34)参见刘晓洁、毛欣娟:《侦查视角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研究》,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而人脸识别证据是以人脸识别技术为支撑,由人脸识别系统对源于案发现场的人脸照片与数据库中的人脸照片进行数据化分析判断的结果,计算机识别系统的性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三是在检验结果及性质方面,人像鉴定证据的判断意见包括“无法判断”“倾向肯定同一”“倾向否定同一”“肯定同一”和“否定同一”五种,本质上属于一种定性分析结果,而人脸识别证据可以显示出不同识别结果的具体相似度,属于一种定量分析结果。(35)参见前引〔33〕,曾锦华等文。所以,虽然人脸识别证据与人像鉴定证据都属于同一性鉴定,但数据化的定量分析方法与经验性的定性分析方法仍有本质不同,这同样是构建人脸识别证据规则的必要性所在。
(三)现行鉴定意见规范的实践效果不佳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36)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鉴定人资格条件、鉴定程序和方法、检材的真实性与同一性、鉴定文书形式要件、鉴定人回避、鉴定人出庭作证等等已经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范,尤其是针对八种具体情形规定了非法鉴定意见的强制排除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可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试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活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对鉴定资格、程序和方法作出的规范性要求,而少有从具体证据规则的角度对鉴定行为与程序作出具有制裁性效果的规定,进而无法从刑事鉴定实践的问题出发规范鉴定意见的司法应用,一定程度上难以保证鉴定意见具备应有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比如,尽管法律法规对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资格条件、鉴定程序与方法作出规定,但很多刑事鉴定机构由公安机关设立,鉴定程序的启动权由公安机关掌控,以致司法机关运用鉴定意见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中立性存疑;再比如,尽管法律法规明确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作出规定,但鉴定人仍可以“其他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而这种“逃避”法庭质证的行为却并不会影响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还有,尽管法律法规对非法鉴定意见作出了强制性排除的规定,但实践中却鲜有法庭排除公诉方鉴定意见的案例。(37)参见陈瑞华:《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问题》,载《中国司法鉴定》2011年第5期。简而言之,我国现行鉴定意见规范在鉴定主体、行为、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仍旧过于笼统,缺乏更为明确而具体的强制性与制裁性规则,难以很好地保障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人脸识别证据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中的新生事物,实践中出现的任意取证、变相质证等问题恰恰需要更具有强制性与制裁性的鉴定规则对其作出针对性规制。
四、证据规则构建比较分析及中国进路
面对人脸识别证据这一新型证据形态,美国学界围绕如何规制这一证据的实践运用作了探讨。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人脸识别证据取证、举证与质证、认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构建起符合人脸识别证据特点的证据规则,确保人脸识别证据具有充分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一)取证规则
构建取证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实践中调取人脸识别证据的任意性问题,从程序上构筑人脸识别证据的合法性屏障。但相对于人身、住宅等涉及公民隐私权、财产权的事物类型,人的面部特征是公开的,限制侦查部门进行人脸识别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是限制侦查部门搜查与扣押权力的根本依据,但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之前的判例却并没有将人的面部特征作为法律保护对象,(38)最初,美国司法实践采取“财产说”,将搜查对象严格限定于宪法规定的人身、住宅、文件及其他有形资产。19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最高法院在卡茨诉美国案中提出了“隐私说”,即一个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特别是在美国诉迪奥尼西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人不再享有其与公众共享的隐私和财产利益,包括她的笔迹、声音或“面部特征”。See Katz v.United States,389 U.S.347(1967);Kyllo v.United States,533 U.S.27(2001);United States v.Dionisio,410 U.S.1,14(1973);United States v.Miller,425 U.S.435,443(1976);Smith v.Maryland,442 U.S.735,743-744(1979).侦查部门进行人脸识别的行为无需受到法律限制(39)See Laurie Buchan Serafino,I Know My Rights,so You Go’n Need a Warrant for That:The Fourth Amendment,Riley’s Impact,and Warrantless Searches of Third-Party Clouds,19 Berkeley J.Crim.L.,154,166(2014).。直到201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诉琼斯案(United States v.Jones)中提出著名的马赛克理论,即个人信息中单一信息的隐私权益可能不受法律保护,但当侦查部门将不同的个人信息汇总后,就会形成较为完整的个人信息。(40)See United States v.Jones,565 U.S.400(2012).2018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卡彭特诉美国案(Carpenter v.United States)中认为,侦查部门未经授权获取当事人的手机通信记录和基站位置信息,经信息聚合后足以展示当事人的生活全貌,因而侵犯了当事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41)See Carpenter v.United States,138 S.Ct.2206,2211(2018).这便在新的判例中吸收了马赛克理论,形成了如今备受学者推崇的裁判规则——卡彭特法则,其宗旨就是反对侦查部门未经法律授权而追踪监视犯罪嫌疑人。(42)See Jennifer Valitino-Devries et al.,Your Apps Know Where You Were Last Night,and They’re Not Keeping It Secret,N.Y.Times(Dec.10,2018);Stephen E.Henderson,Fourth Amendment Time Machines(and What They Might Say About Police Body Cameras),18 U.Pa.J.Const.L.,933,935(2016);Rachel Levinson-Waldman,Cellphones,Law Enforcement,and the Right to Privacy,available at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8_12_CellSurveillanceV3.pdf,last visited on Feb. 11, 2022.纵观美国联邦法院判例,一种新的判决理念已经显现,即侦查部门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搜查涉案人员的行为,不是绝对不允许,而是须经法律授权。虽然美国法律对警方搜查权的制约源于美国宪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这里值得我们借鉴的并不是美国宪制下的隐私权保护,而是以“授权”方式限制警方利用新型技术取证的司法理念。我国《民法典》已对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作出专门规定,尊重和保障公民隐私权益理应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责任和义务。立足我国的刑事侦查实际,在构建人脸识别证据取证规则时,首先可以考虑嵌入“授权”内核,构建“启用程序合法规则”,同时也应针对取证主体专业化需求,探索构建专门的取证主体规则。
第一,构建启用程序合法规则,即侦查人员启用人脸识别系统,必须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或者获取法律授权,否则人脸识别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的授权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于利用源于案发现场的人脸图像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案件,侦查人员在启用系统前,应当参照立案侦查程序履行必要的书面审批手续,审批标准可以界定为被识别人具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合理怀疑;二是,对于需要在本行政区域或更大范围开展大规模人脸识别的重大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传统调查取证手段无法实现侦查目的”的前提下,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后方可启用系统。
第二,构建专业主体规则。当前,虽然人脸识别证据已被广泛应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但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人脸识别机构和人员的资质考核与认证制度,而放任非专业机构和人员在刑事案件中进行人脸识别,既不符合人脸识别证据本身的科技性要求,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证据的证明力。所以,在以授权方式规范刑事司法人员调取人脸识别证据的行为之外,也应对调取证据甚至是参与人脸识别证据分析的人员主体资格作出专门规范,要求相关人员应当具有人脸识别技术专业知识背景,通过国家或地方权威机构资质认证,否则有关人员不得独自负责人脸识别证据取证等活动。
(二)举证与质证规则
解决人脸识别证据举证与质证的有名无实问题,重点是通过人脸识别证据的独立、直接举证与充分质证,保障辩方的质证权。但公诉方为什么不能仅仅出示人脸识别证据的派生证据?又该如何实现充分质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判例中,只要传闻证据具有必要性以及充分的可靠性,就无需当庭对质而予以采信。(43)参见史立梅:《美国对质权条款与传闻证据规则关系之考察》,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6期;Ohio v.Roberts,448 U.S.56(1980).直到2004年,在克劳福德诉华盛顿州案(Crawford v.Washington)中确立了“证明性”标准,即只要传闻证据在本质上是具有证明性的,就应当进行当庭对质,否则予以排除。(44)See Crawford v.Washington,541 U.S.36(2004).对于何为“证明性”,联邦最高法院在戴维斯诉华盛顿州案(Davis v.Washington)中强调从陈述人的主要目的出发理解“证明性”,如果陈述人作出陈述的主要目的是确认或证明与刑事起诉有关的事实,则该陈述就具有证明性。(45)See Davis v.Washington,547 U.S.813(2006).美国学者认为,“是人的参与赋予了计算机系统生命”(46)前引〔2〕,Joseph Clarke Celentino文,第1317页。,人脸识别证据融入了人的主观认知甚至是个人意见,所以属于传闻;刑事司法人员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动机与目的就是控诉,而人脸识别正是搜集、充实追诉犯罪证据的过程,故而人脸识别证据具有证明性。(47)See Melendez-Diaz v.Massachusetts,557 U.S.305(2009).进而由此援引宪法第六修正案“对质权条款”的两点基本要求——证据属于传闻以及证据具有证明性,提出控辩双方应按照交叉询问规则对人脸识别证据进行当庭质证,否则应排除人脸识别证据。(48)参见前引〔2〕,Joseph Clarke Celentino文,第1317页。
诚然,中美之间的宪法理论与证据法实践迥然不同,无论是“对质权条款”还是传闻证据都无法适用于我国刑事司法生态。但笔者认为,如果抛开“对质权”“传闻”等制度性差异而仅从“证明性”对于实现当庭质证的意义而言,那种因“证据具有证明性而应当予以当庭质证”的证据法理念对于我们构建举证、质证规则,保障辩方的质证权具有积极的实践参考价值。就此,构建我国的人脸识别证据举证、质证规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构建直接举证规则,即公诉方应当直接把人脸识别证据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不得变相隐瞒,否则相关证据可予排除。一般而言,公诉方对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需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同时基于其客观中立义务,理应一并出示有利于与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所以从严格公诉方举证责任以及保障辩方质证权的角度考量,公诉方应当如实向法庭出示已经掌握的人脸识别证据,如果有证据证实公诉方隐瞒证据,法庭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排除人脸识别证据及其派生证据。
第二,构建技术专家出庭规则,即出具人脸识别报告的技术专家应当根据法庭要求出庭接受询问,否则相关人脸识别证据应予排除。一方面,在围绕人脸识别证据的质证、辩论过程中,如果辩方申请出具人脸识别报告的技术专家出庭作出解释说明,法庭应当准许并传唤技术专家出庭接受询问,如果技术专家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当庭无法证明人脸识别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相关性,法庭应排除人脸识别证据;另一方面,如果辩方有证据证明人脸识别程序不符合法定鉴定程序并申请由第三方鉴定机构重新出具人脸识别报告,法庭应当准许并择期传唤第三方技术专家出庭接受询问,如果第三方技术专家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法庭也应排除辩方提供的人脸识别证据。
第三,构建算法有限信赖规则,即应谨慎看待人脸识别算法的可靠性,如果辩方对算法可靠性提出质疑,法庭可将算法纳入法庭质证内容。由于人脸识别算法在系统运行中的核心作用,研发企业普遍将算法作为商业秘密予以特殊保护,乃至出具人脸识别报告的技术专家也可能无法对人脸识别的底层技术原理作出解释。如果辩方对人脸识别算法是否获得行业普遍认可提出质疑,法庭应当综合衡量辩方的质疑是否具有合理依据、人脸识别证据的证明作用以及算法公开对企业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必要时可要求公诉方向研发企业调取人脸识别算法是否获得行业普遍认可的证明材料,并对研发企业申请保密处理的内容实行有限公开,如果公诉方无法调取有关证明材料,法庭可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排除人脸识别证据。
(三)认证规则
为了解决法庭对人脸识别证据的主观倾信问题,有必要对法庭审查、采信证据的程序、标准等进行规制和引导,进一步保证定案证据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真实性和相关性。在美国证据法中,多伯特证据规则(49)See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509 U.S.579,587,595(1993).法院在判决中提出五项审查标准:(1)技术或理论是否经过检验;(2)是否经过同行评审;(3)错误率是否已知;(4)是否存在运作标准;(5)科学界是否普遍接受。多伯特证据规则实际上把举证责任转移至证据提出者。2000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将多伯特证据规则纳入第702条的规定。See John Nawara,Machine Learning: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vidence in Criminal Trials,49 U.Louisville L.Rev.,601,606-607(2011).是评估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流标准。面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人脸识别证据,有部分学者主张法庭以多伯特证据规则评估该类证据,(50)有学者提出,律师挑战人脸识别证据的可采性有很多渠道,首当其冲就是作为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参见前引〔51〕,John Nawara文,第606-607页。提出从人脸识别技术的可测试性、(51)See Mohammed Osman,Edward Imwinkelried,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s,50 Crim.L.Bull.,695(2014);Gabrielle M.Haddad,Confronting the Biased Algorithm:The Danger of Admitting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Results in the Courtroom,23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Law,891(2021).同行评审、(52)See Patrick W.Nutter,Comment,Machine Learning Evidence:Admissibility and Weight,21 U.Pa.J.Const.L.,919,927-928(2019);Christian Chessman,Note,A “Source” of Error:Computer Code,Criminal Defendants,and the Constitution,105 Calif.L.Rev.,179,215-219(2017).错误率、(53)参见前引〔52〕,Patrick W.Nutter文,第927-928页。执行标准、(54)参见前引〔49〕,John Nawara文,第606-607页;前引〔51〕,Gabrielle M.Haddad文,第891页。科学界的普遍认可(55)See Frye v.United States,293 F.1013(D.C.Cir.1923);前引〔51〕,Gabrielle M.Haddad文,第891页。这五个方面慎重审查人脸识别证据的可采性。(56)参见前引〔49〕,John Nawara文,第606-607页;ABF Freight Sys.,Inc.v.NLRB,510 U.S.317,323(1994).笔者认为,多伯特证据规则主要是从科学技术可靠性的角度对证据可采性的评价,而法庭对人脸识别证据的审查不仅要考量人脸识别技术的可靠性,还应综合分析运用技术的主体专业性以及证据本身的真实性等因素,这也应是认证规则的必备内容。结合人脸识别证据的特点,具体认证规则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证据鉴真规则。无论是人脸识别系统在复杂场景下出现的较高误识率,还是他人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对人脸图像进行故意伪造、变造,或者是人脸识别系统在深度学习中产生的程序运行故障,面部数据都可能会高度失真,致使人脸识别证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所以法庭应当在采信人脸识别证据前,单独审查人脸图像是否经过证据鉴真程序检验,并将未经证据鉴真程序检验的人脸识别证据定性为瑕疵证据,要求公诉方依据证据鉴真程序补充提供证明材料。
第二,普遍比对规则。由于不同的数据库存储着不同社会群体的面部数据,相对于使用存储普通公民面部数据的数据库而言,侦查人员仅仅使用存储违法犯罪人员面部数据的数据库进行人脸识别,其识别结果的真实性和相关性无法得到可靠保证。所以,法庭应审查人脸识别数据库是否具有面部数据的普遍代表性,如果发现数据库仅包含违法犯罪人员等特殊群体信息,可要求公诉方更换数据库或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用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为支撑的全员数据库,重新进行人脸识别。
五、结 语
理论界和实务界应对刑事诉讼中人脸识别证据的应用问题予以重视。在当前科技发展阶段,人脸识别证据的形成是人与机器两方主体共同参与、客观性与主观性交互影响的过程和结果,并由此蕴含着科技性、盖然性、复验性和信息关联性特点。结合人脸识别证据的内在特点,将人脸识别证据定位于鉴定意见类证据,在我国证据法理论与实践上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有利于解决当前人脸识别证据运用中的现实问题,但仍需从取证、举证与质证、认证各个方面构建符合人脸识别证据特点的证据规则。未来随着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成熟应用,人脸识别系统在复杂场景下的精确度、鲁棒性以及自主运行程度必将越来越高,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无需人工参与,自行采集、自主分析、自主决策、自主优化的高度智能系统。而彼时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比关系分析,完全智能化环境下生成的人脸识别证据必将在“意见性”方面与传统的鉴定意见具有本质不同,也预示着人脸识别证据将从鉴定意见中剥离,在法定证据形式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