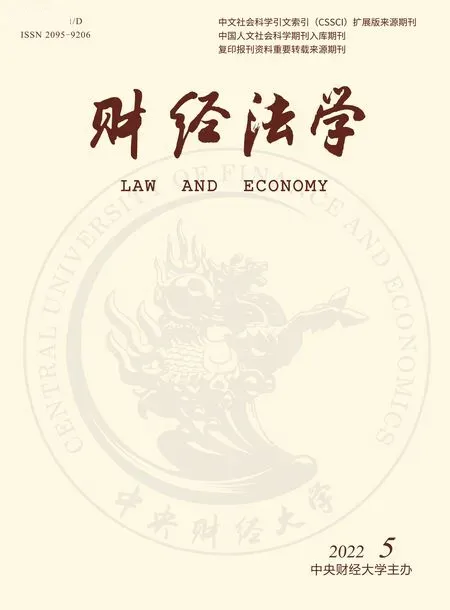根本违约场合风险负担规则的适用
2022-12-29杨勇
杨 勇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610条已经成为根本违约场合风险回转的一般规则。该条继受自《美国统一商法典》,但继受并不完整。在比较法层面,合同撤销场合下限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由出卖人承担的模式,对于合同解除场合同样适用,出卖人的可归责性并不足以作为证成风险回转的正当性根据。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带来的是当事人所承担的相对人返还不能的风险失衡。风险回转优待买受人,有违双务合同中买受人所享有的信赖,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第611条足以在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场合下为其提供充分救济。在因出卖人根本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时,风险负担规则应作如下解释: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前,若标的物发生意外毁损或灭失,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若标的物发生意外毁损或灭失,应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民法典》第610条规定,在标的物因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买受人可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由此所引发的法律后果是:标的物因意外而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民法典》第610条在理论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在违约责任趋向于涵括瑕疵担保责任的背景下,(1)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合同编》(上册),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法院将《民法典》第610条(《合同法》第148条)类推适用于因其他根本违约型态而解除合同的场合,(2)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3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第610条本身的正当性仍然存疑,(3)批判意见如陈自强:《契约解除原物返还嗣后不能》,载《政大法学评论》第165期(2021年);周江洪:《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靳羽:《合同解除效果:〈合同法〉第97 条的解释论》,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肯定意见如刘洋:《根本违约对风险负担的影响——以〈合同法〉第148 条的解释论为中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比较法层面的肯定与批判意见,野中貴弘「契約不適合物の危険移転法理—危険の移転と解除によるその回帰」日本法学82卷4号(2017年)67頁以下参照。理论界以比较法资源作为证成该条正当性的根据时,对比较法存在误读的倾向,而对第610条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一方面并未关注到赞成者对比较法的误读,另一方面也并未系统性地回应支持者的立场,因而对第610条的批判偏离了焦点。根本违约场合下的风险负担问题,一方面与合同解消后的返还清算问题存在体系上的联动效应,对于《民法典》的体系化解释论工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则关涉到作为给付人的违约方所应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及受领人在合同解除场合下所能够主张的返还范围问题,对当事人利益影响甚巨。若该条的正当性基础存在疑问,而理论与司法实务又倾向于扩张该条适用范围至所有因根本违约而解除的合同,则在因根本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时,第610条所体现的风险回转由出卖人承担的规则将会进一步侵蚀风险负担一般规则。在《民法典》并未针对该条规定进行修改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的妥当适用进行研究。
《民法典》并未一般性地对根本违约与风险负担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规定,而主要是在第610条所规范的瑕疵给付场合下,明确了出卖人瑕疵给付致使根本违约时,在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解除合同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应由出卖人承担的规则。但在我国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的背景下,第610条则成为所有的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负担规则的解释基点,因此,对第610条的继受来源的澄清,也就意味着对我国法中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负担规则的基点的厘清。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回归到作为第610条的继受来源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以下简称UCC)中的制度,明晰UCC中对应制度的具体构造,在此基础上,针对理论界论证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回转由出卖人承担的正当性论据,进行全面的回应,与此同时,结合《民法典》第986条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论证在合同解除场合下,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分配由不当得利债权人承担所产生的弊病,进而质疑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回转的正当性。最后,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针对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负担规则开展更为合理的解释论作业。
二、根本违约场合风险负担规则的继受
立法相关部门和理论界普遍认为,《民法典》第610条继受了UCC中的规则。(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25页;前引〔3〕,刘洋文;王洪亮主编:《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能够对应于《民法典》第610条的规则主要体现为UCC第2—510条及第2—608条。(5)参见武腾:《买卖标的物不适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 合同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4页。如果能够在UCC中寻找到比较法资源的支撑,至少第610条也并非比较法上的孤例,对第610条的正当性证成至少可以依赖于比较法资源。然而,如果第610条在继受UCC时发生偏差,那么以UCC为第610条寻求正当性支撑的做法也就丧失了根基。有学者已经逐渐察知《民法典》第610条与UCC中规则的差异,但并未作进一步分析。(6)参见韩世远:《中国合同法与CISG》,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对比《民法典》第610条与UCC第2—510条及第2—608条,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
(一)第610条的解释
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民法典》第610条的解释,在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时,若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解除合同,相当于并未交付标的物,既然标的物并未交付,则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应由出卖人承担。(7)参见前引〔4〕,黄薇主编书,第527页。这种解释在理论界、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支持。(8)参见王利明:《合同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1页;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921页。司法实践可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4民终2830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5民终110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1民终2480号民事判决书;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2民终639号民事判决书。王利明教授针对这一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致使构成根本违约时,若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买受人构成临时为出卖人保管标的物,但代为保管也并未构成真正的交付,并不发生风险移转的法律效果,仍应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9)参见前引〔8〕,王利明书,第361页。相似的考量在UCC中同样存在,当标的物存在瑕疵时,直到出卖人治愈瑕疵或者买受人接受标的物时,出卖人对标的物仍处于控制、支配的地位,因而应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10)See Charles S.Weems Jr.,Passage of Title and Risk of Loss under the UCC and Louisiana Law,27 Louisiana Law Review 299,309 (1967).如果这一解释成立,意味着《民法典》第610条并不构成对风险负担规则的突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仍与交付主义的风险负担规则保持一致性,第610条正当性自然不存在疑问。
如果从风险负担移转的交付主义规则出发,似乎可得到结论:《民法典》第610条规定的拒绝受领标的物发生于受领标的物之前,产生的效果是出卖人并未将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自然贯彻和遵循了风险负担移转的交付主义规则。(11)参见杜景林:《买卖法中瑕疵权利的规制问题》,载《法学》2009年第5期。就这点观察,《民法典》第610条所体现的并非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复归于出卖人,而是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从来就未移转至买受人。但理论界并未都采取此种解释路径。
理论界除了从交付主义的风险负担规则,论证《民法典》第610条的正当性之外,还存在的一种观点是,从风险回转的角度解释《民法典》第610条。例如,在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时,一方面,债权人可通过行使拒绝受领权来直接对抗风险向自己的转移,另一方面,即便是买受人在受领标的物后,交付也仅仅发生暂时性的风险移转的效果,买受人一旦行使合同解除权,则风险又会回转由出卖人承担。(12)参见刘洋:《对待给付风险负担的基本原则及其突破》,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 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冯德淦:《效力瑕疵合同的返还清算问题》,载《法学》2022年第2期。既然存在风险回转的问题,则说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曾移转至买受人,风险回转的解释与交付主义的解释已经大相径庭。
由此观之,尽管《民法典》第610条的正当性并未受到太多质疑,但对第610条的解释论路径却尚未形成共识。
(二)UCC第2—510条及第2—608条与《民法典》第610条的对比(13)以下关于UCC的内容可参见《美国统一商法典》,潘琪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第84-85页。
立法相关部门明确指出,《民法典》第610条是在参考UCC的基础上所作的规定。(14)参见前引〔4〕,黄薇主编书,第525页。按照UCC第2—510条,需要澄清以下内容:首先,在交付的标的物并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买方有权拒绝接受标的物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停留于出卖人,除非是买受人已接受标的物;其次,在买受人正确地撤回接受时,在买受人保单所承保的范围之外,视为损失风险自始由出卖人承担;再次,对于已经确定的符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在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移转于买受人之前,若买受人构成违约,在出卖人的保单所承保的范围之外,在商业上的合理时间内,损失风险由买受人承担。(15)See Sarah Howard Jenkins,Rejection,Revocation of Acceptance,and Avoidance: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UCC and CISG Goods Oriented Remedies,22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2(2013).
据此,按照UCC第2—510条第1款,当标的物存在瑕疵时,在买受人接受标的物之前,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旧由出卖人承担,该款等同于《民法典》第610条中“因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因此,买受人以出卖人所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为由,而在出卖人交付标的物时拒绝接受标的物的情形,在UCC第2—510条第1款中可寻找到支撑,此时也并未突破交付主义的风险移转规则,因而,对于第610条中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的情形,本文不作过多讨论,以下讨论重点集中于解除合同的情形。
UCC第2—510条第2款则指向UCC第2—608条,第2—608条的内容主要体现为:
第一,即使在买受人接受标的物时,买受人也可撤回其接受,但所需满足的条件是:买受人本可期待不符合约定的标的物的瑕疵可被治愈,但并未被治愈;或者在买受人接受标的物时,其并未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而买受人之所以并未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是因为在接受之前难以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或者因出卖人的保证所诱发。第二,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必须发生在买受人发现标的物或应该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并且撤回接受还应当发生在标的物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之前,不过,如果标的物发生实质性变化是因为标的物自身缺陷所导致的除外,此外,撤回接受必须在买受人通知出卖人时才发生效力。第三,如果买受人撤回自己对标的物的接受,买受人享有与拒绝接受标的物的买受人相同的权利。
UCC第2—608条主要规范的是买受人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该条用语为撤回而非合同的解除,在UCC语境下,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并不等同于解除合同,(16)参见潘琪:《〈美国统一商法典〉解读》,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解除可被解释为既终结合同关系,同时又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在此意义上而言,撤回与解除并不构成UCC第2—608条与《民法典》第610条的实质性差异,两者的实质性差异在于:
首先,按照UCC第2—608条第2款,买受人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必须发生在标的物产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之前,(17)See Note,Uniform Commercial Code-Sales-Sections 2-508 and 2-608-Limitations on the Perfect-Tender Rule,69 Michigan Law Review 130,145 (1970).如果对该款作反对解释,这也就意味着:在标的物产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后,买受人无法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18)See Royal Typewriter Co.,a Div.of Litton Bus.Sys.,Inc.v.Xerographic Supplies Corp.,719 F.2d 1092,1106-07 (11th Cir.1983); 前引〔15〕,Sarah Howard Jenkins文,第183-184页。此时如果标的物发生毁损或灭失的,则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19)長坂純「売買契約における危険負担—アメリカ統一商事法典を素材として」明治大学大学院紀要法学篇24卷(1987年)160頁参照。而之所以作此规定,其原因在于:如果买受人受领的标的物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则可能使得出卖人缺乏“现成市场”,以出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标的物,此时,买受人虽然无法享有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的救济权利,但仍可以诉诸UCC第2—714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救济。(20)参见前引〔15〕,Sarah Howard Jenkins文,第184页。而这一解释与《民法典》第610条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果说《民法典》第610条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与UCC第2—608条中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存在亲和性的话,那么,第610条却并未对买受人解除合同施加标的物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限定条件,这使得第610条中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转于出卖人的情形大大拓宽。从这个角度讲,《民法典》第610条没有完整继受UCC第2—608条的规定,因为UCC在一定程度上仍奉行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应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则,在买受人尚未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时,标的物意外毁损或灭失的,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而在买受人已经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后,标的物意外毁损或灭失的,则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21)日本理论界对UCC第2—608条第2款的解释,小野秀誠『給付障害と危険の法理』(信山社,1996年)96頁参照。
其次,按照UCC第2—510条,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回转于出卖人,仅限于买受人所投保的保险无法填补的损失范围,(22)参见前引〔16〕,潘琪书,第100页。如果买受人所投保的保险能够填补全部损失,则仍旧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并不发生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转于出卖人的法律后果。而《民法典》第610条则并未作此区分,只要标的物存在瑕疵使得出卖人构成根本违约,在买受人解除合同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便均由出卖人承担。
综上所述,在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导致买受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UCC并未完全贯彻买受人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转于出卖人的规则。而我国法却作出了不同于UCC的规定,并未区分买受人行使解除权时标的物是否发生毁损或灭失等不同情形,呈现出继受偏差的状况。
三、因根本违约解除合同时风险回转的正当性检验
尽管《民法典》第610条的继受并不完整,但这不足以根本否定在买受人因出卖人根本违约而解除合同时风险回转的正当性,下文将进一步对根本违约场合下合同解除发生风险回转效果的正当性进行检验。
(一)合同撤销场合下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分配的启示
我国通说认为,对于买卖合同等一时性合同,合同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果,合同关系自始归于消灭,这与合同撤销所发生的效果并无实质性差异,(23)参见前引〔8〕,王利明书,第247页。下文想要阐明的一项问题是:如果买受人撤销买卖合同后,买受人尚需要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那么,在合同解除场合下,并不存在充分理由对解除作区别对待,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24)比较法上类似的讨论方式,参见前引〔21〕,小野秀誠书,第104页。德国立法者也认为在解除法与不当得利法领域内的返还清算关系应倾向于作相似处理,vgl.Begr.z.RegE,BT-Drs.14/6040,S.194.日本法上相似的立场,磯村保「法律行為の無効·取消しと原状回復義務」Law & Practice12号(2018年)25頁参照;陈自强:《民法典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体系之展开》,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即便对合同解除不采直接效力说,也不会弱化本文的讨论,举重明轻,既然在具有溯及力的撤销场合下,都有必要要求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在不自始消灭合同关系的解除场合下,(25)关于合同解除效力的各种学说,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69页以下。则更是如此。
在现行法框架下,合同的撤销构成一类典型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的不当得利,受领人应当返还不当得利,而按照《民法典》第986条的规定,善意受领人还可主张得利丧失抗辩,在未知晓出卖人实施欺诈行为时,得利已经因意外原因而毁损或灭失,因而无需再承担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不过,这一论断是否成立也仍需进一步的探讨,其原因在于: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并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双务合同或有偿合同。
在此兹举一例以说明《民法典》第986条适用于双务合同或有偿合同中所出现的问题。
示例:甲以12万元的价格向乙购买一辆汽车,乙在买卖合同中向甲保证汽车虽然是二手车,但并未发生过交通事故,且该车零部件均处于完好状态,甲信以为真并与乙订立买卖合同,乙向甲交付汽车,后甲在驾驶汽车过程中与醉驾的丙相撞,汽车毁损已无法修理。事故后对汽车的检测显示,由于该车为事故车,乙驾驶该车发生事故后导致该车汽缸存在瑕疵,其实际价值仅值4万元,如果该车并非事故车的话,汽车价值为8万元。甲得知此一事实后,及时提起撤销之诉,以撤销买卖合同。(26)该案例根据《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评论中所举示例加以改编。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82页。
在该例中,若甲通过提起撤销之诉撤销买卖合同后,乙提起诉讼,主张根据《民法典》第157条,要求甲对汽车进行折价补偿,由于在汽车毁损或灭失时,甲并不知晓自己受到欺诈,构成善意,如果认定甲可以援引《民法典》第986条作为抗辩,则甲无需向乙承担折价补偿义务,而如果甲在诉讼中提起反诉,要求乙返还价款,所呈现的结果是甲无需承担折价补偿义务,乙需返还价款。
在比较法上,普遍认为上述结果并不合理,因为这使得已经移转至买受人的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又回转于出卖人,因而,各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修正上述结果。德国判例通过差额说等理论,限缩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在双务或有偿合同中的适用空间。(27)Vgl.RGZ 54,137 ff.所谓的差额说,适用到该案中,结果就呈现为:应当否认甲、乙分别享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认为甲、乙之间仅有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这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体现为对双方各自的返还范围进行清算后所得到的剩余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上文为例,若认为甲应向乙返还6万元(合同约定价款×汽车实际客观价值÷汽车承诺给付价值,也即:12万元×4万元÷8万元=6万元),乙则应向甲返还12万元,对双方之间的返还义务进行清算后,乙应向甲返还6万元。(28)差额说的介绍,vgl.Werner Flume,Die Saldotheorie und die Rechtsfigur der ungerechtfertigten Bereicherung,AcP 194 (1994),427 ff.中文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266页;〔德〕格哈德·瓦格纳:《20世纪不当得利法理论的发展与不当得利法领域的法律文献》,马丁译,王倩校,载《中德私法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以下。
2017年修改后的《日本民法典》第121条之2第2款,更是明文限制了不当得利法中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在双务合同或有偿合同无效、被撤销时的适用可能性,(29)潮见佳男「売買契約の無効·取消しと不当利得(その1)」法学教室455号(2018年)94頁以下参照。而我国理论界也在反思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在双务合同中适用的合理性。(30)参见赵文杰:《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以〈合同法〉第58条和第97条后段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限制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在合同无效、被撤销场合下的适用空间,相当于在合同无效、被撤销的场合下,仍然承认了合同法领域内风险移转规则的正当性,标的物一经交付,便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在合同无效、被撤销场合下,都应该尊重合同法领域内交付主义的风险移转规则,在合同解除场合下,也同样不应轻易突破交付主义的风险移转规则。(31)陈自强教授观点的变化,可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载《政大法学评论》第54期(1995年);前引〔3〕,陈自强文。
(二)可归责性能否作为风险分配的基准
从可归责性考察,若因为在瑕疵给付场合下出卖人存在可归责性,而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转由出卖人承担,那么,在合同无效、被撤销等场合下,同样可能存在因可归责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为贯彻相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于买受人后,也应当认定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转由出卖人承担。例如,出卖人对买受人实施欺诈,导致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出卖人存在可归责性,此时应当肯定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的适用空间,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分配给具有可归责性的出卖人承担。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曾认为,在出卖人对买受人进行欺诈使得买受人订立二手车买卖合同时,即便标的物在买受人撤销合同之前因其过失而毁损或灭失,买受人仍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全部价款。(32)Vgl.BGHZ 53,144 ff.由此,似乎印证了将出卖人的可归责性作为由其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合理性。
但是,本文认为,仅仅因为出卖人对合同的解除存在可归责性,而突破交付主义的风险移转规则并不合理。
第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出卖人欺诈的场合下,认可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由出卖人承担的做法本就遭到理论界的批评,(33)事实上,产生出差额说的判例即为出卖人欺诈型案件,vgl.RGZ 54,137 ff.认为欺诈并未提升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此时应当通过侵权责任等救济途径对买受人提供救济,而非改变风险负担主体。(34)Vgl.Hans Josef Wieling,Bereicherungsrecht,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GmbH,1993,S.68。《日本民法典》第121条之2排除了在无效的有偿法律行为中适用善意得利人的得利丧失抗辩规则的可能性,第3款则增设例外,但例外仅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而并未根据撤销权的相对人的可归责性作出不同处理。
第二,出卖人对合同的解除或具有可归责性,但这并不代表出卖人对标的物的毁损或灭失存在可归责性,典型的将合同解除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分配由出卖人承担的立法模式,多承认在买受人对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存在可归责性的背景下,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而非由对合同解除存在可归责性的出卖人承担。例如,《日本民法典》《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较为典型的将合同解除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分配由出卖人承担的立法模式,虽然两者在特定场合下通过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规定由买受人承担,但这些情形较为有限,(35)参见前引〔3〕,陈自强文。通常限于买受人存在特定作为或不作为的场合之下,此时多认为买受人对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存在可归责性,而在完全是因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等事由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时,买受人仍可行使解除权,并使得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而即便这些较为典型的将合同解除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分配由出卖人承担的立法模式,(36)但此类处理模式也受到批评,see Hein Kötz,European Contract Law,Second Edition,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Gill Mertens & Tony Wei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39-240.为了回应批评,日本2017年债法修改过程中,新增“若买受人不知自己享有解除权的,即便因故意或过失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也可解除合同”的规定。尚且承认了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情形,《民法典》第610条并未考虑到类似问题,欠缺合理性。另需指出的是,这些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分配由买受人承担的前提条件是,买受人的行为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因而买受人对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存在可归责性,但在此种场合下,若买受人信赖标的物为自己所有,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标的物,难以认定买受人存在可归责性,其实质仍是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因意外原因而产生的毁损或灭失风险。若严格贯彻这一逻辑,所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在因不可抗力等事由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时,也应当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
第三,从《民法典》第605条观察,在因买受人的原因导致出卖人无法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标的物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应自买受人违反约定时发生移转,(37)体现类似精神的还包括《民法典》第608条,在此仅以第605条为例进行分析。按照该条,可能得到的结论是: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移转可能按照合同当事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进行确定,但在第605条中,之所以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移转同买受人的违约事实相联系,是因为买受人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移转时点推迟,为了对作为非违约方的出卖人提供救济,应视为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自买受人违约时起便发生移转。但在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在瑕疵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背景下,以出卖人存在可归责性为由,而要求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并不合理。
第四,我国之所以在风险移转问题上将交付主义作为确定风险移转的标准,除将交付作为判断风险移转时点具有明确性外,(38)参见前引〔4〕,黄薇主编书,第515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一,当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至买受人后,标的物则处于买受人的控制之下,买受人能够更为有效地控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故而应当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39)参见前引〔12〕,谢鸿飞、朱广新主编书,第37页。制定《合同法》时的讨论,参见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载《法学前沿》编辑委员会编辑:《法学前沿》(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其二,按照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买受人获得对标的物的占有后,即便所有权尚未发生移转,买受人也获得了标的物的实际利益,(40)参见《民法典》第630条。立法机关在解释《民法典》第630条时,明确地提出该条建立在风险利益共担原则的基础上。参见前引〔4〕,黄薇主编书,第585页。因而应当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41)参见前引〔4〕,黄薇主编书,第585页;朱晓喆:《买卖之房屋因地震灭失的政府补偿金归属——刘国秀诉杨丽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评释》,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2期;赵家仪、陈华庭:《我国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与“风险转移”》,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王轶:《论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由此可见,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移转并不与可归责性挂钩。
综上所述,出卖人的可归责性并不足以证成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回转于出卖人的正当性。
(三)风险和利益相一致原则与合同解除场合下的风险回转
不过,既然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可以作为交付主义的风险移转规则的正当性根据,那么,从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的角度出发,似乎也可得出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的结论。在买受人以根本违约为由而解除合同的场合下,由于买受人应将标的物及其孳息一并返还至出卖人,标的物的实际利益事实上是由出卖人获得,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也应由出卖人承担。(42)参见吴香香:《〈合同法〉第142条(交付移转风险)评注》,载《法学家》2019年第3期;前引〔3〕,刘洋文。我国《民法典》第566条虽然并未就合同解除后的孳息及用益返还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理论界仍可能借助于比较法得出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应返还孳息及用益的结论,(43)德国法上的解释,vgl.Staudinger/Beckmann,15.neubearb.Auf.,2013,§446 Rn.9.如果能够得出这一结论,那么基于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便应当由出卖人承担。
不过,本文要指出的是,若将这一逻辑贯彻到双方均负担返还义务的场合下,则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在双务合同被解除时,不仅仅买受人一方负担返还标的物及其孳息、用益的义务,出卖人同样承担价金及其孳息的返还义务,但由于金钱债务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出卖人恒承担价款及其孳息的返还义务,若按照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则会导致出卖人永远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但买受人恒无需承担价款及其孳息返还不能的风险,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所带来的是风险承担的不均衡。
对此,可能给出的一项解释是:在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我国,(44)相关的论据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4号)第20条。在合同解除之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便欠缺法律原因的支撑,标的物所有权自动复归于出卖人,既然出卖人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此时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并无任何不公平之处,而出卖人应向买受人返还的价款为金钱,金钱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在买卖合同被解除后,买受人尚未获得价款的所有权,从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法律地位观察,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分配由出卖人承担,正是平衡出卖人与买受人法律地位的有效措施,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45)相似的逻辑可见于王轶:《论买卖合同中债务履行不能风险的分配——以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考察背景》,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本文对上述解释的质疑是:第一,仅仅因为一方给付的是金钱,而另一方给付的是货物,而使得当事人在合同关系解除后所应承担的对方履行不能的风险呈现实质性差异,不具有实质正当性。第二,从下文买受人的信赖保护观察,在买受人尚不知道标的物瑕疵进而未解除合同期间,为了保护买受人所享有的终局性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信赖,买受人对因使用标的物导致的标的物折旧、价值减损,在合同解除后,也无需向出卖人承担价值补偿义务,换言之,在此期间内,买受人享有了标的物的实际利益,如果从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角度出发,此时应当是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
(四)买受人的信赖保护优待与合同解除场合下的风险回转
买卖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对于买受人而言,其之所以信赖自己能够终局性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建立在买受人提出对待给付的基础之上。在买卖合同中,如果认定买卖合同因解除而使得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转至出卖人,而买受人又能够请求出卖人返还全部价款,则使得买受人获得了不当的优待,这一优待并不合理:
首先,这一优待完全是因为标的物存在瑕疵使得出卖人构成根本违约,而标的物的瑕疵很可能仅仅是一项偶然事件,以标的物存在瑕疵这一偶然事件来使得买受人获得优待并不具有充分正当性。(46)See Reinhard Zimmermann,Restitution After Termination for Breach of Contract: German Law After the Reform of 2002,in Andrew Burrows & Alan Rodger eds.,Mapping the Law: Essays in Memory of Peter Birk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36.
其次,如果说买受人在受领标的物时,买受人的信赖是在提出自己的对待给付的基础上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在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而毁损或灭失时,买受人却能够主张自己的信赖是无需提出对待给付的基础上便可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明显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回转于出卖人时,所得到的结果实质上就等同于:买受人无需支付价款,便可获得标的物所有权。
再次,如果说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分配由出卖人承担的话,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买受人获得了优待,那么,可能会存在观点指出,在出卖人向买受人移转的标的物存在瑕疵致使构成根本违约时,出卖人根本就无法期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移转于买受人,因而,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具有充分正当性,换言之,出卖人并不享有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移转于买受人的正当信赖,但问题在于,在很多场合下出卖人并不知晓标的物存在瑕疵致使构成根本违约。(47)参见前引〔46〕,Reinhard Zimmermann文,第336页。在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背景下,(48)参见前引〔25〕,韩世远书,第745页。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出卖人并不知道标的物存在瑕疵的场合下,出卖人反而会产生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移转于买受人的信赖,此时,如果因为《民法典》第610条的规定而使得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又回转于出卖人,恰恰会使得出卖人所享有的信赖利益无法获得保护。
最后,从比较法看,德国立法者指出,在出卖人根本违约的场合下,在买受人发现出卖人根本违约的事实之前,其相信自己终局性地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为了保护买受人的此种信赖利益,只要买受人对标的物尽到了在自己事务中应当注意的义务,便不对出卖人负有价值补偿义务。(49)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页;Hans Brox/Wolf-Dietrich Walker,Allgemeines Schuldrecht,37.Auflage,C.H.Beck,2013,S.163.Rn.27.然而,即便在买受人尽到对自己事务的注意义务时,若标的物仍因意外而毁损或灭失,正是基于买受人所享有的自己终局性地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信赖,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意外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才更为妥适。事实上,标的物因买受人正常使用而产生折旧、损耗时,买受人并不负有向出卖人进行折价补偿的义务,此时便足以保障买受人所享有的此种信赖利益,而在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毁损或灭失时,买受人并不拥有可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五)第611条与第610条的体系解释
第610条的支持者认为,第610条的实质正当性在于:避免因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导致买受人基于出卖人瑕疵履行的救济权利无法获得保障。(50)参见前引〔3〕,刘洋文。如果这一论断成立,所能够得到的进一步的结论便是,只要出卖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买受人基于出卖人根本违约所享有的救济权利就不应当因风险负担规则而受到影响。
从《民法典》第611条观察,在买受人应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时,不影响出卖人因合同履行不符合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该条意味着,风险负担问题与违约责任两个问题并不相互勾连,买受人可在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基础上,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5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著:《合同法释解与适用》(上册),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94页;余延满:《货物所有权的移转与风险负担的比较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郑旭文:《国际货物买卖中根本违约对风险转移的影响》,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7期。根据第610条,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回溯至出卖人承担,此时已不存在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问题,当然不存在第611条的适用空间,从这个角度观察,第611条与第610条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不过,从第611条可以推导出的另一项结论是:即使买受人需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也并不影响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点出发,如果将第610条的规则改变为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对于买受人而言,并不存在因出卖人瑕疵履行而在合同解除后无法获得救济的问题。因而,认为如果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便会影响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的论证并不成立。
综上所述,以《民法典》第610条为基点的根本违约场合下,买受人解除合同时的风险回转规则欠缺正当性。
四、根本违约场合下合同解除时风险负担的解释论
建立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下文将具体讨论如何对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负担规则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可否类推适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负担一般规则
《民法典》并未规定合同解除场合下返还清算关系中的风险负担规则,构成法律漏洞,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1条明确规定,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义务,准用第264条至第267条的规定,而第266条及第267条为双务合同中的风险负担规则,由此,即便是合同解除后的返还清算之债,也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风险负担一般规则的适用空间。(52)参见前引〔3〕,陈自强文。日本法在这一问题上也并不存在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存在类推适用合同履行过程中风险负担规则的观点,除可归责于出卖人的事由而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外,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买受人的事由而毁损或灭失时,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53)参见民法(債権関係)部会資料5—2:民法(債権関係)の改正に関する検討事項(1)(詳細版),第87页。《民法典》并未针对合同解除后返还清算之债中的风险负担规则作出明确规定,是否意味着合同履行场合下的风险负担规则可类推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下的返还清算之债?由此,在买受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之后,买受人将标的物交付给出卖人前,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应由买受人承担。(54)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民终4620号民事判决书(一审部分)。该案一审法院认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有权拒收标的物,并要求承运人原路退回,自此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似乎认定在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至承运人运输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便应由买受人承担。针对拒收的场合实际上是在类推适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负担规则。本文认为,类推适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负担一般规则并不可采。其原因在于:若类推适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负担一般规则,所导致的结果是,在买受人尚未将标的物交付至出卖人前,即便买受人已经解除合同,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停留于买受人,从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的角度出发,买受人此时已无法获得标的物的实际利益,要求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并不合理。
(二)可采的解释路径:UCC第2—510条及第2—608条的启发
按照前文论述,既然《民法典》第610条确实继受了UCC中的规定,只是在继受过程中发生了偏离,那么,在对根本违约场合下的风险负担规则开展解释论作业时,可能的一个方向便是:朝着作为继受法来源的UCC第2—510条及第2—608条进行解释,由此,第610条的适用范围就应当得到限缩,按照UCC第2—608条第2款,在买受人解除合同时,若标的物已经毁损或灭失,则应否认买受人的合同解除权,此时买受人将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对应于这一限定,在出卖人根本违约场合下,买受人解除合同也仅能发生在所受领的标的物尚未毁损或灭失之前,若标的物已经发生毁损或灭失,则不应承认买受人的解除权,但这一未作修正的解释结果可能并不合理。
在此,我们所要反思的是,按照UCC第2—510条及第2—608条,因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发生于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之前,而通过使得买受人解除权消灭,以实现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定是否合理。对此,本文将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根据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时间,来决定买受人可否享有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的权利,并不可采。德国法的转变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在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之前,旧《德国民法典》第351条采取了类似于UCC的做法,按照旧《德国民法典》第351条,在因可归责于解除权人的事由而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后,买受人的解除权消灭,但在买受人行使解除权之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则买受人的解除行为仍有效。这一“过时”的处理模式遭到了理论界的批评,(55)See Reinhard Zimmermann,Restitutio in Integrum: The Unwinding of Failed Contract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the UNIDROIT Principles and the Avant-Projet d'un Code Européen des Contrats,10 Uniform Law Review 719,730(2005).单纯以标的物毁损或灭失发生于解除权行使之前还是之后,来决定买受人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并不具有充分正当性。(56)Vgl.Begr.z.RegE,BT-Drs.14/6040,S.194;Peter Schlechtriem,Ulrich G.Schroeter,Internationales UK-Kaufrecht,6.Auflage,Mohr Siebeck,2016,S.340.从《民法典》观察,无论是第610条还是合同编通则部分有关合同解除的规定,都并未将标的物是否已经毁损或灭失,作为是否承认买受人合同解除权的一项考量因素,因而,即便UCC第2—608条构成《民法典》第610条的继受来源,也不能完全以UCC第2—608条为模板来解释我国法中根本违约场合下的风险负担规则。
第二,本文认为,UCC第2—510条、第2—608条仍可以作为我国解释根本违约场合下的风险负担规则的方向,但在规则具体构造层面与UCC会表现出较大差异。解释方向具体体现在: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前,若标的物已经发生毁损或灭失,则仍然遵照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由于标的物已经交付至买受人,因而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而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若标的物发生毁损或灭失,则应当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在买受人尚未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时,若标的物已经发生毁损或灭失,UCC实际上是通过否认买受人撤回对标的物的接受的权利,来实现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分配由买受人承担的法律效果,而在《民法典》第610条之下,并未通过否定买受人的合同解除权,来实现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的法律效果,而是通过要求买受人承担价值补偿义务,使得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之所以从上述方向开展解释论作业,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由于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前,标的物发生毁损或灭失的,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这就激励着买受人有效地对标的物进行检验,并在发现标的物的瑕疵后通知出卖人。合同法有着强烈的效率取向,(57)参见梁慧星:《从“三足鼎立”走向统一的合同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民法典》第621条至第624条所规定的买受人的检验及通知义务即为体现,(58)参见金晶:《〈合同法〉第158 条评注(买受人的通知义务)》,载《法学家》2020年第1期。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与合同法中的效率取向具有一致性。反之,如果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前,便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买受人便不存在充分的激励对标的物展开检验,尽管《民法典》第621条至第624条仍可在这一问题上发挥补强作用,但如果未辅之以风险负担规则,会使得出卖人对并不属于自己风险领域内的风险承担责任,也使得买受人在信赖保护层面获得了不当优待,并不合理,对此,前文已经阐明,在此不再详述。
其次,由于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标的物发生毁损或灭失的,应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这能够激励出卖人将买受人直接占有的标的物运送回至出卖人处,之后再由出卖人对标的物进行有效利用,如再以较低的价格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等等,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59)参见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11民终205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虽为拒绝受领情形,但和此处解除场合下的考量具有相似性。反之,如果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应由买受人承担的话,则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买受人需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另一方面,出卖人也不存在充足的动力取回标的物以对标的物进行最大程度的利用,买受人虽然此时可能会为避免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而投入资源避免标的物发生毁损或灭失,但在合同解除场合下,标的物最终将要返还至出卖人的背景下,此种模式显然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使得对标的物没有使用需求的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维护、照管。(60)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出卖人给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致使构成根本违约,出卖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形式体现为,由出卖人负担自行取回标的物的义务,并负担相关的费用。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民终11790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999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6民初17351号民事判决书。从信赖利益保护的角度出发,在买受人对出卖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出卖人无法享有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已经移转于买受人的信赖,要求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也不至于对出卖人的信赖利益造成侵害。
再次,上述解释路径也并不违反我国法中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在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至买受人后,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存在疑问的是,在买受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买受人尚未将标的物返还至出卖人时,此时仍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是否悖于我国法中交付主义的风险负担规则。对此,本文认为,买受人在解除合同后,买受人仅仅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对标的物的保管义务,在否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背景下,出卖人便成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这类似于保管合同中保管人与寄存人之间的关系,(61)部分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认为,此时在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参见前引〔1〕,梁慧星书,第293页。保管合同中标的物毁损或灭失风险应由寄存人承担,(62)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10031号民事判决书。寄存人自主选择保管人,保管人领域内的风险也为寄存人领域内的风险,由寄存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具有合理性。(63)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采取此种处理模式,比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商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
最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除严格适用《民法典》第610条(《合同法》第148条)的观点之外,(64)参见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2021)鲁0124民初104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3423民初74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3民终4086号民事判决书。有观点主张,在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至买受人后,即便标的物存在瑕疵,若买受人退货,在此之前,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不由出卖人承担。(65)参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7民终2581号民事判决书。只有在买受人解除合同后,此后发生的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才由出卖人承担。(66)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2020)宁0202民初920号民事判决书。
由此,针对《民法典》第610条应作限缩解释:除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时,买受人便以标的物存在瑕疵为由而拒绝受领标的物外,该条仅仅适用于买受人解除合同后标的物因意外而毁损或灭失的情形,而在标的物已经发生毁损或灭失而买受人尚未行使解除权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仍应由买受人承担。
(三)两种特殊情形的分析
第一,在合同解除之前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应由买受人承担,这符合买受人信赖自己终局性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事实,而从买受人的此种信赖出发,其因信赖自己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进而对标的物进行使用,由此导致标的物因折旧而产生贬值损失,对于此部分损失,如果认为同样应由买受人承担的话,所产生的后果是买受人终局性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并对标的物进行使用的信赖无法获得保护,为了保护买受人的此种信赖利益,应当否认买受人因使用标的物而导致标的物所产生的贬值损失同样应由买受人承担。(67)参见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0民终2366号民事判决书。但也存在相反观点,如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吉02民终426号民事判决书。类似判决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3民终2958号民事判决书。最终的结果是买受人享有在合同解除之前对标的物进行正常使用的利益,这也与买受人基于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的处理模式,具有内在关联性。
第二,在标的物的瑕疵直接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时,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发生于出卖人领域内,而非买受人可控制的范围,应当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68)比较法的参考如《德国民法典》346条第3款第1项第2小项第一种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第346条第3款第1项第2小项还规定的一种情形是,损害在出卖人处同样会发生的,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也应由出卖人承担。本文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同样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其原因在于导致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也同样处于买受人领域内。
五、结 语
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负担规则继受自《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相关规定,但继受过程中出现继受偏差及比较法误读的现象,有必要研究如何完善其解释论方案。根本违约场合下风险负担规则的合理建构不仅仅是合同法自身特有的问题,还关系到民事法律行为解消后返还清算规则的体系融贯性,外在体系的融贯背后隐藏的是内在体系的融贯。从内在体系出发,以信赖等价值为支点,更合理的解释论方案是,在对《民法典》第610条进行解释时,应区分标的物毁损或灭失的时点,该条适用范围限于买受人解除合同后,标的物发生毁损或灭失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