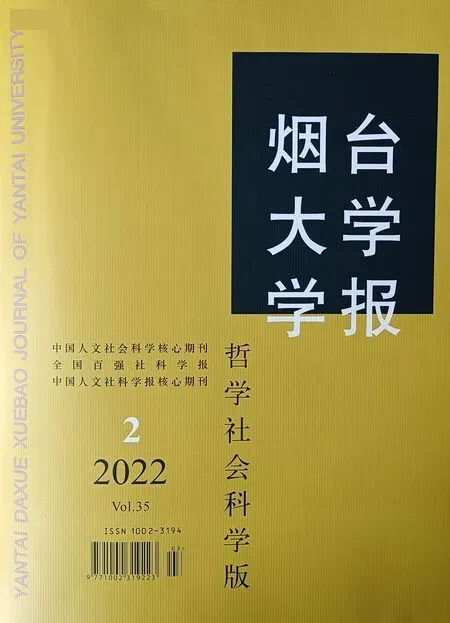清代朝鲜“仁祖辨诬”与明臣袁可立形象的书写
2022-11-26赵亚军
赵亚军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朝鲜听闻清朝将修《明史》的消息后,为防止《明史》中出现不利于朝鲜仁祖的记载,朝鲜方面发起了一场长达六十多年的辨诬活动。目前学界对于朝鲜此次辨诬活动关注较多,并从事件史、两国关系史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梳理与论述。(1)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该文收录于《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一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作者认为,清前期的朝鲜辨诬活动,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既涉及到朝鲜国王的正统性问题,也影响着朝鲜的自我认同,同时也彰显了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杨艳秋的《〈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辨诬活动中朝鲜与清朝双方反应的分析,阐明了朝鲜对清朝是政治上服从而文化心态上背离的矛盾,辨诬活动也折射出明清时期两国关系的错综复杂性。黄修志在其《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辨诬活动体现了朝鲜对王权正统性的维护,也反映出朝鲜对清朝历史书写权的承认,表明朝鲜已开始自觉加入清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并对之产生某种认同。赵蒙《“仁祖辩诬”事件再探——以康雍乾时期中朝辩诬交涉策略演变为视角》(《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将朝鲜辨诬活动纳入两国宗藩关系演变的历程中进行考察,分析了两国辨诬决策背后的利益考量,作者指出朝鲜的辨诬活动是清朝与朝鲜的良性互动,而最终的辨诬结果也反映出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在处理中朝宗藩策略问题上由防范到包容的变迁过程。相关研究还有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7年,第1-25页);季南《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韩明基《17、18世纪韩中关系与仁祖反正——朝鲜后期“仁祖反正辨诬”问题》(《韩国史学报》13辑,2002年)等。而曾在朝鲜请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明臣袁可立,亦对此次辨诬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学界对此仍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辨诬过程中袁可立被反复提及并被朝鲜重点攻击,这不仅影响了辨诬的效果与进程,也影响了清代对于袁可立的历史书写。本文拟在借鉴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等史料为基础,详细探讨袁可立在“仁祖辨诬”事件中的角色和地位,并揭示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清代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
一、袁可立视仁祖“篡逆媾倭”
明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三日,朝鲜绫阳君李倧趁国王光海君患病之际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国王李珲,自立为新王,史称“仁祖反正”或“癸亥靖社”。(2)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三《仁祖朝故事本末·癸亥靖社》,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66年,第723页。通过政变得位的仁祖必须取得宗主国明朝的册封,其政权才具合法性。因此李倧在政变之后即令议政府左仪征朴弘者等移文总兵毛文龙,乞为转奏。其文曰:
本年三月内,奉王太妃教旨,谓光海君珲自嗣位以来,失道悖德,罔有纪极……嗣王珲忘恩背德,罔畏天威……何幸大小臣民,不谋而同,合词举义,咸以陵(绫)阳君倧仁声夙著,天命攸归,乃于今月十三日讨平昏乱,已正位号……咨尔政府备将事意具奏天朝,一面咨会督抚衙门以凭转奏。(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740页。
在给明朝的奏报中,朝鲜李倧通过重点指责光海君“通虏背明”来表明自己政变的正当性。时任登莱巡抚的袁可立,接到毛文龙揭报后即上奏明廷:
夫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傥为封疆多事,兵戈宜戢,亦宜遣使宣谕,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亟讨篡逆之贼,复辟已废之主。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只奉国祀。如国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4)《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戊子,第1741页。
由题本可以看出,袁可立反应强烈,直接将发动政变的仁祖视为“篡逆”。他从君臣名分的角度出发,认为李倧自行废立形同篡逆,应当声罪致讨。袁可立先是将这场朝鲜政变定性为“篡逆”,接着又劾奏李倧对明朝实有不臣之心,其在《请讨簒逆疏》中称:
职犹有闻为珲境往来员役有语“朝鲜举国皆欲从权,而独李珲念昔年御倭之恩,望报中国,因罹今日之变”。而李倧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备。如此也,则徐可北联夷、南通倭,舟楫帆樯倭所惯习,载奴以来,海上之事将大有可虑者。(5)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3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1-502页。
身为登莱巡抚的袁可立,十分重视朝鲜政变对明朝海疆安全的影响。针对仁祖关于光海君“忘恩背德”的指责,袁可立不以为然,其向明廷言称,光海君在位时并未忘记明朝恩德,反而是发动政变的李倧有“媾倭”之嫌,即“珲顺倧逆”,不可不加以审处。袁可立将朝鲜仁祖定以“篡逆媾倭”的罪名,对明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继袁可立之后,天津督饷侍郎毕自严亦奏李倧勾结边将,“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李珲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议政府有自尽者”,同时称旧王光海君“通奴之显迹未著,尊王之常礼未失,且其即位数令颁布国中,咸以恭顺天朝为念,以协力助兵为辞”。(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334页。毕自严对李倧武力政变的描述,佐证了袁可立奏本中对仁祖的指责,进一步坐实了仁祖“篡逆”的罪名。对光海君的评价,毕自严则与袁可立持相同的态度,认为其并未倒向后金,对明朝颇为恭顺。袁可立、毕自严二人的奏本,无疑是对李倧发动政变具有正当性的彻底否定。
仁祖“篡逆媾倭”的罪名,随袁可立题本流播于明朝,对明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对请封的朝鲜使团有一连串的诘问。“坏旧君自立,事不明白,何以来请邪?”“何故不报朝廷而径自废置邪?”“你国举事时,引用倭兵三千何邪?”(7)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册,第295页。叶向高对朝鲜擅自废立以及引倭兵举事的诘问,显然是采信了袁可立奏本中关于仁祖“篡逆媾倭”的说法,而仁祖擅自废立的行为又为礼法所不容。为了明朝事体,内阁决定先行查明真相,而后再议是否册封。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袁可立所提供的政变情报,直接影响了明朝廷官员对于政变性质的认定。明廷经讨论后,委任袁可立负责行查朝鲜。在册封朝鲜一事上,以登莱巡抚为首的封疆诸臣的意见起到了主导作用。袁可立作为封疆大臣,更加看重朝鲜之于明朝的战略意义。
在查明仁祖并未“媾倭”,且主动表示愿意出兵助明之后,袁可立明显转变态度,主动为朝鲜助封,“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8)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拟山园选集》卷六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行查结束后,袁可立便奏请朝廷派出专使册封朝鲜。《明实录》载:
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朝鲜更立情实,请敕专使以重册典……登抚袁据公本结状回文内事理,细核之维栋语言相符,随具奏,复云:“彼国臣民之众拥戴已经一岁之久,迄无异言,人心所在,天命攸归,封倧之典似不容己者。但册典宜重以朝使,则遵旧章隆大典。倧之受命而王也,感戴之忱将与带砺而同永矣。”(9)《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四月辛亥,第2348-2351页。
在得到登莱巡抚助力后,朝鲜很快便取得了明廷的允封,但仁祖“篡逆”的罪名并未随着明朝册封而得以洗刷,明朝对于朝鲜“媾倭”的怀疑亦未彻底消释。
袁可立最初将朝鲜仁祖视为“篡逆”的态度,影响了时人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明朝官方史书《明熹宗实录》直接以“朝鲜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10)《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戊子,第1739页。记载此事。督饷侍郎毕自严的奏言,提及引兵入宫、杀害旧王的行为,进一步丰富了袁可立所称李倧“篡逆”的细节。当时广泛流传的关于朝鲜政变的说法,大多源于袁、毕二人的奏疏,《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两朝从信录》等书,便是以“篡逆”的性质记载朝鲜的这一政变:
高汝栻曰,朝鲜曩来贡献不绝……今不禀命干朝,竟尔易位,虽国妃之意,实篡立之奸也……又闻朝鲜咸欲从奴,珲念昔年卵翼之恩,誓报中国,倧又系倭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助也。(11)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第810页。
不难看出,此书记载的李珲恭顺、李倧媾倭等情节,几与袁可立奏疏相一致,可能是受到了袁可立的影响。同样,成书于崇祯初年的《两朝从信录》,对此事也是直书“篡逆”,该书作者沈国元将诸如火烧宫室、杀害旧王等事一并附于后,其文曰:
按李珲,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称仁孝。李倧其亲侄也,走马试剑,谋勇着闻,眉竖耳垂,姿表伟美,常在李珲左右用事,掌管笔札之役。因见李珲有疾,遂起谋逆,先令心腹游说符平山节度使李贵,练兵马五百调赴王京防御,又密约继祖母王太妃。于三月初九日在宫中举火为号,李倧率李贵等指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李珲,投之烈焰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议政府有自尽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后仪仗执言,数李珲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倧遂即王位。(1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356册,第499页。
这一则记载直接视李倧为“篡逆”的乱臣贼子,书中同时收录了袁可立、毕自严二人的奏疏,相关细节则完全取材于毕自严的奏本。另外明末文人陆人龙以时事小说形式写就的《毛文龙演义》(又名《辽海丹忠录》)一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开篇便是“君臣大义”,“臣弒君,子弒父,天下大逆……明明是篡,百口怎解?”(13)陆人龙撰,陈志明校:《毛文龙演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这一说法颇能代表当时明朝的民间对“仁祖反正”的看法,而且这一看法在明清鼎革之后依然存在。影响较大的明季私修史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俱为“篡”,如《国榷》指仁祖李倧“弑叔”,是“篡臣”;(14)谈迁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248页、第5776页。。《石匮书》载:“李珲为其逆侄李综(倧)所篡”;(15)张岱:《石匮书》卷二百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320册,第342页。《明书》记:“朝鲜李倧篡其君”;(16)傅维鳞:《明书》卷十八,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92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1页。《历代建元考》称,李倧“弑其君珲自立”。(17)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4页。由此可见,时人对于朝鲜政变的看法几乎一致。朝鲜新王即便得到了明朝的册封,但在明末士人看来,仁祖依然难逃“篡逆”的罪名。
朝鲜使臣高用厚曾在崇祯四年(1631)购得《两朝从信录》,其侄看到书中第十八卷内容后,“乃天启三年癸亥日录也。目不可覩、耳不忍闻,毛发上竖、肝胆俱裂!可胜痛哉!”(18)高傅川:《月峰集》卷三《封进从信录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9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第330页。于是上疏欲进呈仁祖,但承政院认为“此不过闾巷间浪杂之书,不足烦于睿览”,(19)《校勘标点承政院日记》,仁祖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第146页。没有呈送仁祖,因而未引起朝鲜君臣的震动。究其原因,应是朝鲜官员认为仁祖已经获得明朝册封,得到了宗主国的认可,私修野史之记载显然不足以代表明朝官方的立场。
袁可立在奏疏中称李倧为“倭婿”的说法,同样引起了明廷的重视。在请封之初,内阁就曾当面诘问使团有无倭兵一事,而在册封朝鲜之后的天启六年(1626),朝鲜“媾倭”一事再次被时任登莱巡抚的李嵩提及。面对李嵩的怀疑,朝鲜不得不遣使辨诬,使臣称:“小邦虽僻在海外,而久沐东渐之化,其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讲之有素,岂忍与异类忘仇结亲,以辱其祖先,以羞其臣民,以贻丑于天下后世也!”(20)金尚宪:《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一三,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358-359页。朝鲜的一番呈辩,暂时打消了李嵩的疑虑,“抚臣则答,以此等说意必虚传,今果释然,此后慎勿相疑云”。(21)《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十六,显宗十四年二月癸丑,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第38册,第137页。至崇祯元年(1628),登莱巡抚孙国祯又一次奏言朝鲜“媾倭”问题,“朝鲜与倭交和,万一倭、奴窃附贡使而来,国家之患不在山海,而在登莱;不在奴酋,而在贡使矣”。(22)《朝鲜仁祖实录》卷十九,仁祖六年七月己巳,第34册,第279页。新任督师袁崇焕出于统一事权的需要,奏请更改朝鲜贡路,其理由之一便是朝鲜有“媾倭”之嫌,为此朝鲜被迫再次遣使明朝辨诬。
此次针对“媾倭”之说,朝鲜认为有两种含义,即“和媾”和“婚媾”。“和媾”指与日本交往一事,这是经过明朝允许的,(23)张维:《溪谷集》卷二十二《辨诬奏本》,《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352页。而“婚媾”则断无此事。朝鲜大臣崔鸣吉认为,“今之所欲辨者,乃在婚媾一事,而反着赘语于其间……而反以致疑”。(24)崔鸣吉:《迟川集》卷九《论倭情请别为咨文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89册,1992年,第415页。为免横生枝节,崔鸣吉建议使臣重点陈述“婚媾”一事。朝鲜在给袁崇焕的揭帖中也对“婚媾”进行重点呈辩:“与倭为媾之云,讹言之无理,一至于此……今使村阎下贱与为婚媾,死且不从,况自祖先以来世守侯服,沐浴声教,而忍为嫁女娶妇之事,以贻千载之羞乎?”(25)郑经世:《愚伏集》卷三《袁军门揭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8册,1991年,第51页。可以看出,其辩解之词也与天启年间的说辞如出一辙。崇祯二年(1629)朝鲜使臣李忔见到袁崇焕,袁询问使臣“东夷南倭消息如何”。(26)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一三,第40页。使臣趁机申辩,袁回答“至于媾款等语,亦泛然说话,非有他意”。这表明“媾倭”一说主要是袁崇焕出于更改朝鲜贡路的需要,但也反映出明朝上下对于来自朝鲜“倭情”的警惕。李忔一行到达京师后即呈文辨诬,皇帝传谕,“该国素娴礼仪,世效忠勤……不必陈卞(辨)”。但使臣认为传谕并非正式敕命,李忔又再三呈文礼部,终得明朝敕谕。(27)宋德相:《果庵集》卷十三《雪汀李公谥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29册,1999年,第240-241页。由此可见,朝鲜上下对于洗刷“媾倭”之罪名何等重视。
朝鲜仁祖在取得明朝册封之后,得以成为朝鲜名正言顺的国王,对明廷而言已非“篡逆”,但“媾倭”的嫌疑却又被明廷屡次提及。在“丁卯虏祸”之后,朝鲜被迫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之后朝鲜虽及时向明朝作了汇报,(28)《尊周汇编·纪年第一·仁祖朝》,《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集部第4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但依然引起了明朝的警惕。朝鲜为此又多了一项“款奴”的罪名,对明朝而言,当初袁可立担心的“北联夷南通倭”的局面仿佛已经形成。此后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除了正使任务之外,还需应付来自明朝对于后金和日本消息的询问,“问倭情则呈文痛辨,问虏情则据实言之”。(29)《朝鲜仁祖实录》卷十九,仁祖六年七月己巳,第34册,第279页。向明朝汇报“倭情”“虏情”成为当时明鲜关系的常态,并一直持续到朝鲜臣服清朝。
“仁祖反正”事件发生之后,登莱巡抚袁可立最初对朝鲜仁祖“篡逆媾倭”的指责,为明朝士人接受并传扬开来,以至于影响了时人对这一事件的历史书写。朝鲜因而一再遭到明朝的质疑,不得不多次到明朝来辨诬,这也成为入清后朝鲜再次辨诬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所要辩白的重点内容。
二、入清后的朝鲜辨诬
袁可立在天启年间曾任登莱巡抚一职,在任期间适逢朝鲜发生“仁祖反正”事件,明廷将行查朝鲜政变实情的任务交由他负责。袁可立在核查事实和明朝册封朝鲜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其最初以“篡逆”看待朝鲜的政变,故而入清后袁可立成为朝鲜辨诬活动中重点攻击的对象。
(一)朝鲜君臣对袁可立助封仁祖的认识
入清后的朝鲜辨诬活动始于康熙年间,终于乾隆初年。(30)朝鲜使臣李宜显曾简明阐述了朝鲜辨诬的历程,参见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三五,483-484页。朝鲜辨诬最初是出于明季野史《皇明通纪》《十六朝广纪》等对仁祖癸亥事的记载不实。(31)这两部书的有关内容可参见陈健辑、江旭奇补订:《皇明通纪集要》卷五十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第597-598页;陈建辑:《皇明十六朝广汇纪》卷二十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2册,第559-560页。这两书关于“仁祖反正”的记载内容和《两朝从信录》如出一辙。朝鲜在康熙年间的辨诬取得了改动《明史》文字的进展。(32)《朝鲜肃宗实录》卷八,肃宗五年三月丙辰,第38册,第411页。雍正年间经皇帝特许,将《朝鲜列传》的内容按朝鲜要求予以更改,并先行颁发朝鲜。(33)《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雍正四年五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64页。另见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卷三四《陈奏二》,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第2592-2593页。至乾隆三年(1738)时,朝鲜取得《朝鲜列传》刊本,(34)《清高宗实录》卷八十一,乾隆三年十一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并于次年购得全套《明史》,(35)《朝鲜英祖实录》卷五十一,英祖十六年四月甲戌,第42册,第658页。朝鲜围绕“仁祖反正”一事的辨诬活动历经六十余年才结束。
在朝鲜请封之初,明朝已经有关于朝鲜政变的各种流言。针对明朝流传的关于朝鲜政变的不实说法,当时请封的使团推测,应主要出于驻扎东江的明将毛文龙的“浪言”,以及推官孟养志的诬陷。孟养志于天启二年(1622)七月从天津出发,“宣谕朝鲜,今于六月之杪倐然归来,赍有朝鲜回照,乃彼国篡立之详则”,(3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333页。经历了“仁祖反正”的整个过程。毕自严所获知的政变消息,以及奏本中武力政变、杀害旧王等说法,就是来自孟养志的叙述。
入清后朝鲜君臣在讨论是否遣使辨诬时,多数朝鲜官员都认为是毛文龙刻意诬陷,才致仁祖被诬。毛文龙曾与朝鲜频生龃龉,多次向明廷劾奏朝鲜,如“椵岛帅毛文龙构诬我国,至以交通北虏、合势袭岛等语,播告军门,事将不测”,(37)申悦道:《懒斋集》卷八《仲氏晩悟公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4册,2006年,第131页。因而才会引起朝鲜君臣的痛恨。朝鲜显宗十五年(1674),自清朝归国的朝鲜使臣就认为,明季野史关于“仁祖反正”一事不实的记载,乃是毛文龙故意以“诬言”奏报于登莱巡抚袁可立所致,“癸亥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听文龙之嗾,诬毁癸亥反正之举,极其诟辱者也”。(38)《朝鲜显宗实录》卷二十二,显宗十五年七月辛卯,第37册,第78页。大臣金万基认为:“至如《从信录》等书皆野史小说,不过以一人之误闻误传随录者,何可一一请改乎?”(39)《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十六,显宗十四年二月癸丑,第38册,第137页。在金万基看来,野史不能和登莱巡抚之题本相提并论,而当时行查朝鲜后,登莱巡抚已经具本为朝鲜请封,且题本内也已为仁祖正名,事实不辩自明。“有明朝野史记仁祖癸亥事,而备载莱抚查勘颠末,实未有可辨之诬。”(40)金万基:《瑞石集》卷十六《通政大夫司谏院大司谏知制教李公墓志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1995年,第61页。金万基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朝鲜官员中颇具代表性,显宗实录的纂修官特意在显宗十四年(1673)三月癸酉条下注云:
癸亥反正初,昏朝余孽,流言于椵岛,登州抚臣因以上闻。甲子,中朝遣差官查勘事实,本国臣民,各具奏本,申诉废置事状。敕命旋下,而有伦序相应,人心攸属等语,则诬罔之说,固未尝得售于中朝也。《从信录》等诸书,不过随前后所闻而备录之,记事之体,自不得不如此……到今兹事,非但不必辨,亦无可辨者。上意盖知其如此,故讫甲寅置之,而不复议。(41)《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十六,显宗十四年三月癸酉,第38册,第139页。
可见,在显宗朝辨诬之议初起时,朝鲜诸臣并未视袁可立为仁祖构诬之人,而且将袁可立请封题本视作为仁祖正名的权威证据。
朝鲜的肃宗担心野史所载会被清朝史官纳入《明史》,因而力主辨诬。鉴于国王的态度,朝鲜大臣再次言及当年仁祖请封详情:
第念当初因袁可立题本,礼、兵两部奉旨计议,委送登抚游击李惟栋、毛镇中军陈继盛等,来我查访。陪臣李光庭、李守一等七百二十余员呈文,先陈光海斁灭彝伦、自绝于天,次陈仁祖大王扶植民彝、迓续天命等项节次,明白痛陈。惟栋等取回口述并我国公文具奏,则阁部详覆内“惟栋语言,与结状内事理相符。臣民拥戴,已经一岁,迄无异言,人心所在,即天命攸归”云云。厥后袁可立奏本“废君自绝于命,昭敬王孙,聪明仁孝,宜为嗣君”云。前谩见,直已较然矣。是以甲子奏文有曰“前后事实,悉经阁部详覆,因蒙皇上领纳,流言屏息,封敕诞领”云尔。(42)《朝鲜肃宗实录》卷五,肃宗二年正月辛亥,第38册,第320页。
从大臣们向肃宗详陈当年登莱巡抚袁可立行查朝鲜以及为朝鲜请封的始末看,朝鲜官员对袁可立前后态度转变并为朝鲜助封一事相当熟悉。袁可立为朝鲜请封的奏本也曾指出朝野流言已经屏息,在当时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而仁祖之所以能够顺利取得明朝册封,袁可立可以说是多有助力。大臣在这里再次重申构诬者为明将毛文龙,“癸亥反正之举,明白如日月,如彼污蔑之言,必出于毛文龙之含愤构诬,以至书诸史册”,“毛文龙构诬之言,无所不至,致令传播于中朝,竟刊于史册,至有不忍闻之语”。(43)《朝鲜肃宗实录》卷五,肃宗二年正月辛亥,第38册,第320页。由此可见,视毛文龙为仁祖主要构诬者,已是当时朝鲜上下的共识。
在朝鲜辨诬受阻后,反对辨诬的声音再起。大司宪尹鑴奏言肃宗,再次重申袁可立对请封的助力作用,其奏曰:
至于辨诬事,臣适见董其昌《皇明通纪》续编,其中有天启三年癸亥事迹及登莱巡抚袁可立请讨事,督饷侍郎毕自严奏诬说寲言极其狼藉。其下又有四年甲子袁可立奏请,有曰“朝鲜更主情实,令文武陪臣会议,得废君自绝于天,昭敬大王孙某聪明仁孝,宜为嗣君,故有此请”云云,而“五年乙丑,封册遂行”。据此则巡抚袁可立初凭流言乱传,而至于请讨,及后廉得实状,乃有册封之请。数行称说,不啻披云睹日,足以昭示天下,传信万世。其为辨诬,孰大于是?(44)《朝鲜肃宗实录》卷六,肃宗三年二月壬戌,第38册,第348页。
尹鑴认为,袁可立的请封题本中对于仁祖的评价“足以昭示天下,传信万世”。但肃宗坚持认为,“辨诬事,予之切齿痛恨,必欲昭雪而后已,决不可中止”。大臣金锡胄也委婉进言肃宗,“兵曹判书金锡胄亦于昼讲白曰:‘当初虽因袁可立之构诬,至于来查,而其后册封诏有曰“民心所归,天命所与,旧臣亦皆归心”’云,此诏若载于《明史》,则实无更辨之事矣。’上不答”。(45)《朝鲜肃宗实录》卷六,肃宗三年二月壬戌,第38册,第348页。金锡胄也和尹鑴持相同的观点,反对辨诬,认为明朝的册封诏书足可作为信史,如若被《明史》采纳,实无再行辨诬的必要。对于朝鲜大臣认为袁可立题本以及明朝册封诏书可作为信史的观点,肃宗沉默以对,表明其对大臣们的看法大体认可。
时人李玄锡所纂《明史纲目》一书,对于登莱巡抚袁可立促成仁祖册封一事多有着墨,书中载曰:
先是,平辽总兵毛文龙、登莱巡抚袁可立等奏言:“朝鲜王珲失道悖德、伦理斁绝,国人咸怨。以王大妃金氏命,奉昭敬王孙绫阳君讨平昏乱,以主国事。”朝议请使可立等详加体访,于是可立遣游击李惟栋,与文龙参将陈继盛往查朝鲜。可立覆奏曰:“彼国臣民拥戴已经一载,迄无异言,人心所在,即天命攸归,封典似不容已。”至是,朝鲜陪臣李庆全、尹晖等赍本国奏文到京师,请册命,上许之。(46)李玄锡:《明史纲目》卷二十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史编史传类第5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虽然朝鲜请封经历相当坎坷,但可以看出,李玄锡认为仁祖之所以能够顺利取得明朝册封,应主要归功于袁可立的助封,李玄锡的这一看法在当时朝鲜士人中颇具代表性。至朝鲜英祖年间辨诬再起时,时人也未将袁可立视为仁祖的构诬者,有文曰:“此盖其时大北余孽,意在图复旧位,日夜流言于毛镇。故登州巡抚袁可立之疏,至曰‘闻往来员役言如此’云云。当日贼臣辈所为,据此可知。”(47)赵文命:《鹤岩集》第6册《燕行日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92册,1997年,第599页。
(二)朝鲜围绕“篡逆媾倭”的辨诬策略
朝鲜君臣虽未将袁可立视为构诬者,但在第一次呈交清廷的辨诬奏文中,袁可立却首当其冲。在得到明朝册封之后,朝鲜在明朝的辨诬活动主要是围绕“媾倭款奴”进行,即向明朝禀明与日本、后金(清朝)的关系。而在明清易代之后,朝鲜辨诬的对象也由明朝转变为清朝,“款奴”一项自然不能再提。朝鲜所见野史记载多为“篡逆媾倭”之语,于是“篡逆媾倭”便成为辨诬的重点,此两项罪名最初皆源于袁可立给明廷的奏本。
康熙十五年(1676),朝鲜首次向清朝辨诬。奏文有言:“《十六朝纪》所云‘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废君,投之烈焰’之白地诬捏,且言媾倭之说,万万无理。冀许删改,夬示昭雪。”(48)《朝鲜肃宗实录》卷五,肃宗二年八月丙辰,第38册,第334页。朝鲜驳斥了野史中诬仁祖为“篡逆”以及“虐杀旧王”的说法之后,又重点阐明了“媾倭”一说的虚妄:
一则曰倧走马试剑,谋勇着闻,常在废君左右用事;二则曰密约继祖母王太妃,以救火为名,令兵入宫。甚至谓绑缚废君,投之烈焰……复有登莱巡抚袁可立、侍郎毕自严诸人之疏,至以媾倭等语,大加诋诬……至于媾倭一款,尤万万无理。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隔海之外种也。虽强弱不敌,姑与之羁縻,而既是我之仇邦,又非我之匹偶。今以童儒之騃,儓隶之贱,若指之为婿于倭,则亦必骇然而愤,怫然而怒。矧以王室之亲,贵介之尊,宁有忍事忘耻,结秦晋于异类之理哉……臣不知登抚诸人,何所征据而作此不伦之语,至上诬天子也。(49)王士禛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二《朝鲜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6页。
朝鲜在呈交清朝的奏文中,对于“媾倭”罪名的辩解,与向明朝辨诬时的措辞相似,并且完全将袁可立作为仁祖“媾倭”一说的始作俑者。但在重点抨击袁可立的同时,朝鲜亦附带言及了毛文龙的构诬:“而小邦之所以受怼于文龙者,有不可以一二计。则文龙之巧作蜚语,肆然构诬于废兴之际者,又岂可量哉!因此而督抚有奏,因此而礼部有疏,始则以无罪见疑而为忧,终则以至冤将伸而为幸。”(50)王士禛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二《朝鲜疏》,第47页。朝鲜在这里又解释,由于毛文龙的原因,登莱巡抚才上奏明廷,才有了后来的行查,这也反映出朝鲜虽指责袁可立,却依旧未将其视为构诬者的心态。
在首次辨诬受阻后,由朝鲜大臣金锡胄撰写的辨诬奏文,亦主要围绕“篡逆媾倭”进行。金锡胄也认可袁可立曾助力朝鲜请封一事,因而在其执笔写就的辨诬奏文中,主要聚焦于明季野史的具体记载,并未论及袁可立等人。
臣之曾祖父庄穆王臣某……拨乱反正之君也。而小邦于顷岁得见明朝野史所谓《十六朝纪》者,其诋诬臣先祖,无所不至……至其媾倭等说,尤属虚捏诪张诬罔,诚有所不忍言者……及至昨岁,伏闻大朝方有纂修《明史》之役,臣于此又窃恐恶言之易逞、好机之难遇,删诖正谬,惟此时其会……逮伏奉该部所奉圣旨……一则曰该国癸亥年废立事始末及庄穆王事迹,即有定论;一则曰并无旁采私纪以入信史……惟此新修明朝正史……诚愿圣明亟命史阁修纂诸臣,重加研摩,其于纪臣先祖癸亥之事者,若犹有差谬不明,即加厘改。如果已刊正是实,仍许颁示……今臣诚得此书,不特以夬洗先祖污蔑之名,亦将以荐之祖庙,宝之西序,长与子孙、臣庶,赞叹大朝一视同文之盛,有没世而不敢忘者矣!(51)金锡胄:《息庵遗稿》卷十九《请改癸亥被诬事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1995年,第461-463页。
此次朝鲜在奏文中未对袁可立进行抨击,主要是对各种不利于仁祖的记载逐一进行了辩驳,继而请求清朝在修《明史》的过程中,将有关仁祖癸亥事“差谬不明”的记载加以厘正,进一步恳请清朝将厘正之后的《明史》颁赐朝鲜。
由以上两封辨诬奏文可见,在清朝修《明史》之际,朝鲜着重围绕“篡逆媾倭”进行辨诬,力求阻止有关“仁祖反正”中不利于朝鲜的记载被纳入正史。
为何此时朝鲜辨诬奏文中出现将矛头首先指向袁可立这一现象,或可以这样理解:对肃宗而言,作为构诬者,毛文龙对明廷的影响力显然不如登莱巡抚,(52)亦有学者认为毛文龙对在“仁祖请封”一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参见王桂东:《朝鲜仁祖国王请封述论——兼谈毛文龙之助力》,《韩国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黄修志:《朝鲜全湜〈槎行录〉版本考辨及史料价值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5期。并且肃宗意欲将清朝对朝鲜私买禁书的注意力引向明朝官员,登莱巡抚是其首选,这对于朝鲜来说不失为一种辨诬的策略。这样看来,朝鲜辨诬时将重点攻击对象转到以登莱巡抚袁可立为首的明朝官员,以此作为一种辨诬策略并非不可能。
雍正四年(1726),朝鲜再次遣使清朝,围绕“篡逆媾倭”进行辨诬,并称“倭婿等语,恣加丑诬”,“倭婿之诬,尤极骇愤”。(53)《朝鲜英祖实录》卷九,英祖二年二月辛未,第41册,第578页。朝鲜在辨诬疏中再次叙及袁可立,史载:
朝鲜国王李昑奏辩四世祖庄穆王倧篡逆之诬,乞改正《明史》……今皇朝诏修《明史》,恐秉笔之臣以外国事迹未及详察,敢沥陈先臣受诬概略,以冀皇上垂鉴焉。据前纪,一则曰倧走马试剑,常在废君左右用事;一则曰密约继祖母王太妃,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甚至谓绑缚废君,投之烈焰及为倭寇等语。此必出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督粮侍郎毕自严诸人之诬论……故珲于癸亥三月见废,至辛巳七月寿终,葬以王礼。则庄穆且待废君恩义之隆,从古未有。而谓投之烈焰,又何诬妄之甚也!日本于壬辰岁举兵入犯,烧毁我宫庙,国几灭亡,则小国百世之仇也,而顾有忍辱忘耻、结秦晋于仇敌之理……不知登抚何所据而作此不伦之语!(54)萧奭:《永宪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6页。
朝鲜于《明史》将成之际遣使清朝辨诬,仍沿袭先前的策略,将袁可立指为仁祖一事的主要构诬者并反复提及。此次朝鲜又将关于仁祖的“火烧宫室”“杀害旧王”以及“媾倭”等罪名,笼统地归为袁可立构诬。不难看出,此时朝鲜对通过抨击袁可立进而达到其辨诬目的这一策略之运用,已相当熟稔。朝鲜此行辨诬后,雍正帝尽数答应朝鲜改动《明史》文字的请求,对朝鲜所欲更改的地方“尽改之”,更有甚者“列传所付,皇帝亲自笔削”。(55)《朝鲜英祖实录》卷二十,英祖四年十二月己亥,第42册,第96页。朝鲜此后又请改明太祖、明熹宗本纪中有关朝鲜太祖、仁祖朝史事的记载,清朝史官为此将《明史》中朝鲜欲改的内容摘出,交与朝鲜使臣。朝鲜使臣圈点出诸如“纂”“攫”以及“自立”等敏感词汇,交付史官进行更改。对于这些更改的内容,清朝史官一应照办,并言皇帝已经特许朝鲜的请求,“可随意改之也”。(56)《朝鲜英祖实录》卷二十九,英祖七年癸巳,第42册,第250页。可见,清修《明史》中关于朝鲜“仁祖反正”的史事,完全是按照朝鲜的意愿进行撰写的。
三、朝鲜干涉《明史》纂修及对袁可立的影响
朝鲜政治上虽臣服清朝,但受思明思想的影响,(57)相关研究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吴政纬:《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文化心态上仍视清朝为夷狄。清朝为笼络朝鲜,维护和巩固两国间的宗藩关系,(58)黄修志:《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完全接受了其辨诬的请求,对《明史·朝鲜传》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
目前通行的《明史》是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殿本《明史》是在王鸿绪《明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的,而《明史稿》中有关“仁祖反正”的记载则取材于《明熹宗实录》。清朝在编纂朝鲜相关史事时,“所译朝鲜表文,满、汉文意皆不相符”,为此康熙帝指示史官,“作史之事,殊为重大,一字不可轻易增减也”。(5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七,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丁未,第275页。由王鸿绪《明史稿》对实录内容的大段引用可以看出,这种引用实录的做法对《明史》的修纂也产生了影响。除王鸿绪《明史稿》中用“篡”来记载此事外,万斯同《明史稿》亦是直书为“篡”。(60)万斯同《明史稿》卷二十二《熹宗本纪》载“朝鲜国王李晖为其侄倧所篡”,卷四一三《朝鲜传》载“倧废晖自立”,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324册第248页、第331册第585页。
《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四月戊子”条载“朝鲜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之后附有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本。(61)《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戊子,第1739-1741页。“天启三年八月丁丑”条又记载了朝鲜请封奏疏,以及礼部行查朝鲜的决议。(62)《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七,天启三年八月丁丑,第1915-1918页。“天启三年十二月癸巳”条则载明朝行查朝鲜的结果,以及明朝册封朝鲜。(63)《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三年十二月癸巳,第2185-2187页。“天启四年四月辛亥”条载袁可立为朝鲜请封的题本。(64)《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四月辛亥,第2348-2351页。
王鸿绪《明史稿·熹宗本纪》载:“朝鲜国王李珲为其侄倧所篡。”(65)王鸿绪:《明史稿》本纪十七《熹宗本纪》,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1册,第108页。《明史稿·朝鲜传》记载“仁祖反正”主要框架为实录中的袁可立奏本、礼部行查决议和明朝册封朝鲜。(66)记载详情参见王鸿绪:《明史稿·朝鲜传》,第7册,第224-225页。《明史》载曰:
(天启三年)三月癸卯,朝鲜废其主李珲。(67)《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册,第301页。
三年四月,国人废珲而立其侄绫阳君倧,以昭敬王妃之命权国事,令议政府移文督抚转奏,文龙为之揭报。登州巡抚袁可立上言:“珲果不道,宜听太妃具奏,以待中国更立。”疏留中。八月,王妃金氏疏请封倧,礼部尚书林尧俞言:“朝鲜废立之事,内外诸臣抒忠发愤……众论咸有可采……则更遣贞士信臣,会同文龙,公集臣民,再四询访,勘辨既明,再请圣断。”报可。十二月,礼部复上言:“臣前同兵部移咨登抚,并札毛师,遣官往勘。今据申送彼国公结十二道,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称倧为恭顺……乞先颁敕谕,令倧统理国事……俟渐有次第,始遣重臣往正封典。庶几字小之中,不失固圉之道。”从之。四年四月,封倧为国王。(68)《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第27册,第8303页。
王本《明史稿》对“仁祖反正”一事的书写颇为详尽,对袁可立奏疏内容近乎全文采用,对礼部奏疏也节录其中的主要内容,可谓是完全取材于实录。作者使用袁可立以及礼部奏疏内容,详细地阐述了朝鲜请封、明朝勘查乃至最后册封的始末,其中对奏疏中的“篡”“废”等敏感表述更是不加删减直接录用。而殿本《明史》则在王本《明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对袁可立、礼部题本内容中不利于仁祖的言辞尽行删削。朝鲜辨诬对于《明史》的干涉,清人也有清晰的了解,史载:“盖倧后臣于我大清,子孙继世不绝,故讳言之。《明史稿·朝鲜传》谓‘珲为侄倧所篡’。乾隆间重修《明史》,改为‘国人废珲而立其侄倧’。”(69)陈伯陶等纂:《民国东莞县志》卷六十一《袁崇焕传》,《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1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03页。《明史稿》中直书仁祖为“篡”,显示出明朝册封朝鲜本就出于“急在边疆”的考虑。在《明史》中记为国人废黜光海君,仁祖则是受臣民拥戴、顺天应命而得位,以此树立了一个得位之正的仁祖形象。
另外,《明史稿》以及殿本《明史》中,册封朝鲜的时间皆为天启四年(1624)四月,此系误载。明朝正式遣使在天启五年(1625)二月,(70)《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六,天启五年二月丙午,第2590页。六月诏使颁诏朝鲜,(71)《朝鲜仁祖实录》卷九,仁祖三年六月己卯,第34册,第11页。而天启四年(1624)四月,实际上是袁可立奏请明廷遣使册封朝鲜的时间。(72)《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四月辛亥,第2348-2351页。显然,《明史稿》是误将袁可立为朝鲜上请封题本的时间,当作了明廷正式册封朝鲜的时间,而《明史》的误记则是因袭《明史稿》的结果。由此可见,朝鲜力求抹去袁可立在《朝鲜传》中的影响,并将其奏疏内容几近尽删,但《明史》最后所误记的正式册封时间,恰恰是袁可立为朝鲜上请封题本的时间,朝鲜如此处心积虑却得到这一结果,不啻为历史的暗讽。而对于《明史·朝鲜传》中关于“仁祖反正”一事的失实记载,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与史实不符的伪史料”。(73)杨效雷:《中朝关系史上的一次所谓“史册辩诬”——兼谈伪史料产生的原因》,《东北史地》2011年第5期。
朝鲜辨诬的重点“篡逆媾倭”,皆出自登莱巡抚袁可立,他不仅影响了明季私史的记载,且对《明实录》乃至清初两部重要的《明史稿》也有直接的影响,袁可立因而成为朝鲜辨诬过程中绕不开的存在,被反复提及。朝鲜辨诬的结果,是将袁可立在“仁祖请封”一事中的影响降至最小,这也成为袁可立事迹在《明史》中被遮盖、泯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朝鲜对袁可立不遗余力地攻击,期望抹除他的印迹,但是仍不可避免清朝对袁可立主要事迹的关注。
袁可立,明朝睢阳卫人(今河南睢县),万历己丑(1589)进士,《明史》无传。万历年间曾任苏州府推官、监察御史。(74)(康熙)《睢州志》卷五《人物·袁可立传》,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商丘卷第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47页。泰昌、天启年间历任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通政使司左通政、廷试读卷官,侍经筵。天启二年(1622),出任登莱巡抚。(75)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2010年出土,睢县袁氏家藏。在抚登期间,又升兵部右侍郎。(76)天启三年《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夫妇诰》,睢县袁氏家藏。天启四年辞归,五年再起为兵部右侍郎,六年转兵部左侍郎,(77)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七年加兵部尚书衔致仕,崇祯六年(1633)卒于家。曾担任《明史》总裁官的清初名臣汤斌,为清初睢州人,与袁可立同里。汤、袁两家交好,汤斌与袁可立之孙袁赋谌私交甚笃,之后汤家更是与袁家结亲,汤斌次子汤浚娶袁赋谌长女为妻。(78)《睢州汤氏族谱》卷三,上海图书馆藏,1986年,第20页;田兰芳:《皇清太学生信菴袁公墓志铭》,睢县博物馆藏,1997年出土。汤斌家居期间曾主持修纂《睢州志》,汤斌在州志中为袁可立撰有传记,(79)汤斌于康熙十六年(1677)所纂《睢州志》人物传记部分已散佚不存,参见程正性修、汤斌纂:(康熙)《睢州志》,《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商丘卷第7册。康熙三十二年(1693)时任睢州知州马世英以汤斌版《睢州志》为蓝本,主持纂修了新版《睢州志》,此版州志收录有《袁可立传》。参见《睢州志》卷五《人物·袁可立传》,《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商丘卷第7册,第147页。后汤斌曾将袁可立等人的传记送与孙奇逢,以备其在撰写《中州人物考》时采用。(80)汤斌撰,段自成、沈红芳等编校:《汤子遗书》卷四《寄示诸子家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而在孙奇逢所撰《中州人物考》中,袁可立却被归为“拟入无传”,仅有“袁可立字礼卿,睢州人,司马”这样简单条目。(81)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八,《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141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680页。汤斌入史馆之际,正值朝鲜遣使清朝辨诬之时。康熙十七年(1678),汤斌“诏举博学鸿儒”,入史馆参与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充任《明史》总裁官;(82)汤斌撰,段自成、沈红芳等编校:《汤子遗书》卷首《汤斌传》,第3页。二十二年“日直讲筵”,裁定《明史》列传。(83)汤斌撰,段自成、沈红芳等编校:《汤子遗书》卷首《汤斌年谱》,第47页。汤斌在主持修纂《明史》期间,曾拟将袁可立传记列入《明史》。康熙十八年汤斌特意修书一封与家中诸子,嘱咐其子将袁可立等人的传记连同《睢州人物志》一并寄至京师,以备采入《明史》之用,(84)汤斌撰,段自成、沈红芳等编校:《汤子遗书》卷四《寄示诸子家书》,第245页。但从修史结果看,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除《明史》无袁可立传外,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皆无其传。
相较正史而言,地方志中却保留了对袁可立较为详细的记载。除《睢州志》外,成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的《顺治归德府志》中,亦立有袁可立传记,且对其涉辽事迹记载颇祥。(85)宋国荣修、羊琦纂:《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袁可立传》,《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商丘卷第1册,第328-329页。已经出仕清朝的袁可立之孙袁赋诚,在府志成书的次年,广邀族人组织编纂了《睢阳袁氏家谱》,(86)袁赋诚:《睢阳袁氏家谱》,顺治十八年手抄本,睢县袁氏家藏。袁氏此时修谱,对其先祖不无盖棺定论之意。从清初几版方志中对袁可立的记载来看,袁可立在地方志中不仅有传,同时亦名列睢州乡贤祠,(87)程正性修、汤斌纂:《康熙睢州志》卷二《学校》,《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商丘卷第7册,第27页。反映出清初地方上对袁可立这一故明官员的接受与认可。由清初所修地方志,以及汤斌欲将袁可立纳入正史的情形不难看出,袁可立这一历史人物在清初应是已有定论。
关于清人修《明史》,孟森先生曾言:“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或其人生平大见长之处在辽,则削其人不为立传。”(88)孟森:《明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袁可立生平为官主要功绩便是在巡抚登莱期间取得的,他曾参与明、后金(清)战争,且最后以兵部尚书衔致仕,反映出明廷对其军事功绩的最终肯定。袁可立对朝鲜请封的应对与处置,主要是出于制定针对后金军事战略的考虑,朝鲜辨诬对袁可立重点抨击,也使得曾深度参与辽事的袁可立一再出现在清朝史官的视野。清朝史官厘清“仁祖反正”事件始末时,会关注时任登莱巡抚的袁可立,在重新书写“仁祖反正”这一历史事件时,无疑也会影响到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清廷为了照顾朝鲜这一重要的藩属国,尽可能地简写、甚至不写袁可立的事迹,这也成为袁可立在《明史》无传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四、结 语
朝鲜辨诬事件不仅直接导致殿本《明史》对朝鲜废立一事大幅改写,而且也成为影响袁可立历史形象书写的开端。“仁祖反正”事件发生之后,袁可立是最早获知这一消息的明朝大臣,向明廷奏报朝鲜政变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受袁可立影响,上自明朝君臣,下到普通文人,皆视仁祖为“篡逆”,而袁可立关于朝鲜“媾倭”的说法,更是引起明朝疆臣的持续关注和警惕。入清后,清修《明史》在书写“仁祖反正”一事时,也受到了明人记载的影响,为此朝鲜发起了一场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辨诬活动。朝鲜辨诬干扰到《明史》的修纂,清朝对朝鲜所求尽数满足,不仅将《明史》中不利于仁祖的记载大幅删削,甚至于清帝亦曾一度亲自过问,因而《明史》最后呈现出的结果也终如朝鲜所愿。
清朝对朝鲜辨诬的态度,经历了“从斥责到容忍、纵容再到应其所需”的历程,(89)赵蒙:《“仁祖辩诬”事件再探——以康雍乾时期中朝辨诬交涉策略演变为视角》,《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6年第2期。最后为满足其所求而不惜曲笔更改史实。清人魏源曾为此不禁慨叹:“《明史》告成,许更正其先世庄穆王倧篡逆之诬,皆他国所未有。”(90)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六《外藩》,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0页。袁可立成为朝鲜与清朝围绕“仁祖辩诬”交涉过程中的重要关节,朝鲜一边将袁可立请封题本视作为仁祖正名的有力证据,一边又重点攻击袁可立以达到辨诬目的。在辨诬时,朝鲜通过贿赂清朝大臣对史册进行删改,要求多删袁可立事迹,这在《明史》纂修过程中,很容易引起清朝史官对前朝官员袁可立这一人物的注意。加之袁可立在抚登期间颇有建树,且曾参与辽东战争,其主要事迹多涉辽事,触犯清廷忌讳,进而影响到清朝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导致在清初已有定论的袁可立终在清修《明史》中无传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