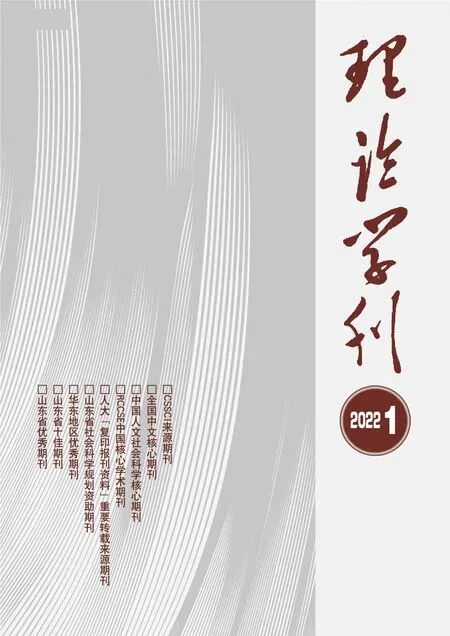汉儒三命说探析
2022-11-26贾新奇
贾新奇,任 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命运是人生与社会的大问题,自哲学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哲学反思的主题之一。中国古代哲学对命运问题的思考源远流长,形成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论,汉代儒者的三命说即是其中之一。三命说在儒家命运理论的嬗变进程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一学说至今未得到认真梳理,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甚至其基本内涵都处在迷离恍惚之中。本文将对三命说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学界。
一
关于三命说,流传至今的材料较为有限,并且在术语、释义上互有异同。为了讨论方便,在此将这些材料罗列出来,并添加了编号。明确提及“命有三科”的材料共有两条,其中一条出自唐孔颖达《礼记注疏》。《礼记·祭法》郑玄注“司命”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颖达疏引《援神契》:
(1)命有三科:有寿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年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所谓《援神契》,就是纬书《孝经援神契》。另一条出自班固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白虎观经学会议而编撰的《白虎通》:
(2)命有三科,以记验。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寿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国五十年。随命者,随行为命,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矣。又欲使民务仁立义,无滔天。滔天则司命举过言,则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残贼,若上逢乱君,下必灾变,暴至,夭绝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行正言,而遭恶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1—392页。陈立认为,句中“则用以弊之”的弊,同毙;“沙鹿崩于受邑”,当为“沙鹿崩,水袭邑”之讹。
上述除外,还有四条汉代的材料,虽然没有明言“命有三科”,但据其内容看,显然是在谈三命说。其一出自纬书《春秋元命苞》:
(3)行正不过得寿命,寿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也。(原注:《援神契》曰:随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则随其暴虐行以教之。)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误,逢世残贼,君上逆乱,辜咎下流,灾谴并发,阴阳散忤,暴气雷至,灭曰动地,夭绝人命,沙鹿袭邑是也。(2)李昉等:《太平御览》第4册,夏剑钦等点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灭曰动地,夭绝人命,沙鹿袭邑是也”,钟肇鹏等点校《七纬》作“灭日动地,天绝人命,沙鹿袭邑是”(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15页)。
其二出自东汉王充《论衡·命义篇》:
(4)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3)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50页。王充引述三命说,不是表示他赞同这一理论,而只是为了予以批判。
其三出自孔颖达《左传注疏》。《左传·成公十七年》“晋士燮祈死”。孔颖达疏引何休《左氏膏肓》:
(5)人生有三命,有寿命以保度,有随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闻死可祈也。
最后一条材料出自东汉末年赵岐。《孟子·尽心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赵岐注:
(6)莫,无也。人之终无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曰随命。惟顺受命为受其正也。(4)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0页。
以上材料,从时间前后看,最早的应是两种纬书,即《孝经援神契》和《春秋元命苞》。史书记载,被东汉政府认可的纬书共计30多种,《孝经援神契》《春秋元命苞》是其中的两种。所有纬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难以确考,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些作品大都产生于西汉末期,是深受阴阳五行理论影响的方士化的儒生将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进一步推向极端,并为了增强自身学说权威性而比附五经的产物(5)《七纬》,钟肇鹏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页。。纬书提出三命说,而后在东汉前期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理论观点,记载在《白虎通》当中。再之后,又被不少学者,包括何休、郑玄和赵岐这样的经学家所接受,用作注释、阐发五经等典籍的依据,当然同时也成为王充等思想家批判的靶子。
众所周知,命在古代思想中具有多重含义。在西周中叶之前的文字中,有令而无命。所谓令,就是下命令这一动作和所下之命令这一事物。命字出现在西周中叶,意思与用法和令字基本没有区别(6)傅斯年:《性命古训辨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7—39页。。商周时期,人们把上天理解为人格神,上天能够向人发布命令,能够通过命令来赋予人以道德的和非道德的先天属性,还能够通过命令来干预并造就人(这时的人,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群体的人即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的寿夭、贫富与贵贱等。这些都是所谓“天命”。后来有人否定上天的人格神性质,但命字包含的几层意思却传递下来。因此,天命或命有多种含义:人从上天或他处所得到的命令(指令之命)、先天禀赋等个人先决条件(先天命运之命),以及人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整个人生所得到的综合结果(后天命运之命)。由于人的生命也可以被视为上天赋予的,同时也是命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所以常常单列,此即生命或寿命之命(7)如果把指令侧重于指伦理道德指令,这种命就是“义理之命”,同时又把先天命运、后天命运和生命三者合而为一,这就是“命运之命”。把命作义理之命和命运之命的二分,是学术界较为普遍的一种意见。不过,我们要注意,命运之命是可以进一步细分的,这也是古代文献的真实情况,因此,如果不作这种细分,对许多文献的理解就容易发生偏差。。
按照这一划分,三命说所说的命基本上是生命或寿命之命。如,上引《春秋元命苞》即是承如下文字而来:“圣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辙。长生久视,不以命制,则愚者悖慢,智者无所施其术。……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节。”(8)《七纬》,钟肇鹏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14页。原文标点似有不妥处,酌改。大意谓,圣人和智者德性完美、遵循天道,来辅助上天治理众人;假如世人都长生不死,那么圣人、智者就失去以生死控制众人的权柄,对于愚者的胡作非为也就无可奈何。因此,上天才确立三命,以促使众人尊天行道。显然,三命就是上天所确定的生命、寿命的三个种类。《白虎通》讲三命,也是在谈人的生命、寿命:“命者,何谓也?人之寿也。天命已使生者也”(9)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1页。。细审《白虎通》论三命的整段文字,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即它可能是《孝经援神契》和《春秋元命苞》相关文字的拼接:三命的术语、界定来自《援神契》,而例证则来自《元命苞》。故而可以推断,《援神契》的三命,也是讲人的生命、寿命。至于何休《左氏膏肓》和赵岐《孟子注》的三命说,很明显所论也是生命、寿命问题。唯一的例外,是王充对三命的引述。无论是《命义篇》还是《论衡》的其他有关篇章,命有时是指生命、寿命,有时则更宽泛,泛指包括生命、寿命在内的整个命运。王充把原本以生命、寿命为主题的三命说扩展为更为宽泛的命运学说,其实也没有太偏离三命说的主旨,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生死与贫富、贵贱、穷达等都是构成命运的基本要素,只不过相对而言更基础、更重要,故而可拿出来单独讨论。作为构成命运的基本要素,生死与其他要素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以生命、寿命为主题的三命说很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人的整个命运,被当做关于一般命运的学说。易言之,就主题而言,三命说原本是关于人的生命、寿命的学说,但很大程度上又可视为一般命运的学说。
由此可以下一个基本判断,即三命说是产生于西汉末年而流行于东汉时期的一种儒家命运学说。
二
三命说作为儒家命运学说发展到汉代的理论形态,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是迄今为止,三命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表现在最基本的语义疏解上,也表现在更高层次的义理研究上。因此,本节我们首先来指出三命说各项材料的语义理解上的疑难,并尝试提出一些思路,力图克服这些疑难,达到对三命说涵义的基本理解。
三命说诸项材料中语义理解上的疑难,主要来自如下方面:
第一,名词、术语的生僻。三命说原出纬书,而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了自神其说,有意使用许多怪诞冷僻的名词、术语。此特点在三命说上也历历可见。如“保庆”“保度”“谪暴”“遇暴”“督行”和“应行”等都是三命说的基本术语,这些术语基本上都不见于其他典籍,因此它们的含义非常晦涩。词义与词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之间存在互释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借助首先把握思想观点而后反推词义的方法来应对这个难题。
第二,不同材料之间用词的歧异。如三命第一科有的写为“寿命”,也有的写为“正命”或“受命”;“有寿命以保庆”,有的写为“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谪暴”,有的写为“有遭命以摘暴”或“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有的写为“有随命以督行”。 这一现象当然可以归因于文献传抄中发生的错讹,可是完全归因于此,似乎又难以让人置信,因为歧异实在太严重了。我们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三命说的提出与阐述,起初就出现在多种纬书中,出于不同的作者之手,尤其是同是在讲三命说,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所谓不同的角度,最明显的有两种:一是从命的确定者即“天”着眼,二是从命的拥有者即人着眼。角度不同,所使用的词语就会有异。可以想象,在纬书中这些差异都很容易理解,但后世引述、传抄这些材料时,要么隐去了原有的角度和脉络,要么把不同出处的材料混杂在一起,甚至会在不同的词语中随意选择。如“谪暴”与“遇暴”、“督行”与“应行”,字形差异巨大,无法解释为仅仅是传抄上的讹误,而解释为来源原本不同似乎更为合理。
第三,更严重的是,在不同的材料中,对三命的解说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下文将详谈。总之,由于这些因素,三命说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是什么,显得扑朔迷离,难以索解。
三命说最令人困惑的关键之处在于,不同的材料对三命的解释明显不同。必须对这一点给出恰当的处理,否则整个三命说始终扞格难通。这里,我们尝试着提出一个处理思路。
根据对三命的不同分类和释义,现存的六项材料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孝经援神契》和《论衡》,即材料(1)(4);第二组包括《白虎通》《春秋元命苞》和赵岐《孟子注》,即材料(2)(3)(6);第三组则是何休《左氏膏肓》,即材料(5)。
关于第一组。《援神契》和王充所引,把命分为三种即受命(寿命、正命)、遭命和随命,并界定了三种命的涵义。遭命是“行善而遇凶”或“行善得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材料对遭命的释义是一致的,差异集中在受命和随命上。材料(1),“受命,谓年寿也”,年寿即年长、长寿;材料(4),“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可见,第一种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好命,而且由于这种好命并非以人的良好德行为前提,因此又可以叫做天定的好命。再看随命。材料(1),“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材料(4),“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可见,随命的基本特征是好坏未定,实际结果依据人的德行来确定;由于德行有优劣之分,所以随命也有好与坏两个实际种类。
关于第二组。对遭命的释义,第二组与第一组并无不同,可以姑置勿论,只看受命与随命。关于受命,材料(2),“寿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国五十年”;材料(3),“行正不过得寿命,寿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材料(6),“行善得善曰受命”。可见,第一种命的基本特征是好命,而且这种好命乃是德行优良的结果,并非天定的好命。关于随命,材料(2),“随命者,随行为命,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矣。又欲使民务仁立义,无滔天。滔天则司命举过言,则用以弊之”;材料(6),“行恶得恶曰随命”;材料(3),本身只说“随命者,随行为命也”,但原注又引《援神契》的话,“随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则随其暴虐行以教之”。可见,随命的基本特征是坏命,而且是由自身恶劣德行所导致的坏命,即上天的惩罚。
关于第三组。材料(5),“人生有三命,有寿命以保度,有随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这条材料只是从功能的角度对三命作了非常简单的解说,却未作进一步释义,也未给出例子,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何休对三命的界定。不过,从其描述三命功能的用词来推测,何休的界定很可能类似于材料(1)即《孝经援神契》的说法。
综上所述,现存三命说材料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命说A和三命说B。两种观点对遭命的界定是一致的,但对受命和随命的界定则明显不同。三命说A以《孝经援神契》和王充所引为代表,它的分类方法是,首先根据命运是否基于德行,把命分为天定之命与德行所成之命,而后又根据命的好坏,把天定之命分为好的天定之命(受命,或曰寿命、正命)和坏的天定之命(遭命),而对德行所成之命不再细分,笼统叫做随命。三命说B以《白虎通》《春秋元命苞》和赵岐《孟子注》为代表,它的分类方法,也是首先根据命运是否基于德行,把命分为天定之命与德行所成之命,而后根据好坏性质再进行细分。但是,它细分的是德行所成之命,好的叫做受命(或曰寿命、正命),坏的叫做随命;至于天定之命,虽然暗含着作了好坏的划分,但却舍弃了天定的好命,而只取了天定的坏命(遭命)。
可见,两种三命说都是两层分类、三种类型的结构,但其实质内容存在重要差别。从分类法的角度说,三命说A远胜于三命说B。逻辑上,经过两层二分,命的种类共有四种,不过我们看到,三命说却只包含三种。事实上,三命说A本质上是囊括了命的全部四种类型的,只不过没有把随命包括的两个子类直接列出而已。相比之下,三命说B却存在重要遗漏:与遭命相对的天定好命被舍弃了。假如这一种类的命只是理论上,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那么这种舍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数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缺少良好德行甚至德行败坏的人能够寿终正寝乃至得享长寿,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因此,这种理论观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推测个中缘由,大概有两种可能:要么一些纬书对命运学说的构想原本就是不成熟、不完整的,要么相关材料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脱漏、扭曲。真相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无从考知。所幸的是,《孝经援神契》和《论衡》所记载的三命说还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理论,能够作为汉代儒家命运学说的典型(10)以下所说的三命说就特指这一学说。另外,《春秋元命苞》原注所引《援神契》对随命的解释,明显不同于材料(1)对随命的解释。同一篇文献中存在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推测,《春秋元命苞》原注引用文献时或许误注了标题。。
三
三命说是此前儒家命运学说发展演变的结果。按照学界的普遍看法,商代人信奉命运天定,天是人格神,天在决定人的命运时依据的是人所不知的某些原因,充其量再适度考虑人对天是否虔敬,而不在意人对人的德行,即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品行。商周之际的政权鼎革,也带来了命运观的巨变。周人仍然信奉人格神的上天,相信上天造就人的命运,但同时认为上天在造就人的命运时依据的是人的德行。前者叫做命定论或盲目命运论,后者叫做命正论或道德定命论(11)关于这些术语,可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42—144页;陈宁:《中国古代命运观的现代诠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从西周到春秋,命正论或道德定命论是主流观念,这在《尚书》《左传》和《国语》等典籍中有充分反映。如《左传·僖公五年》载虞国大夫宫之奇对虞公的进谏:“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宫之奇所引《尚书·周书》及其本人的总结,表达的都是这个阶段典型的道德定命论。
当然,这种概括中的命是指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即所谓国命)和个人的整体含义的命运,用在生命、寿命这个特殊方面上时要略加辨析。商代人是如何理解生命、寿命之命的,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作判断。至于西周到春秋,道德定命论大体上也适用于生命、寿命这个特殊主题。也就是说,在上天的干预下,有德之人能够寿终正寝或长寿,而无德之人则不会得享天年甚至会夭亡。如《左传·哀公六年》记载,天有异象,太史解释这是楚昭王将有灾祸的征兆,并建议可以通过禳祭把灾祸转嫁给令尹、司马。对此,楚昭王回答:“除腹心之疾,而寘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之后,楚昭王有疾,又拒绝以祭祀禳疾的建议,终于病故。这里,楚昭王表达的就是个人寿命、生命方面的道德定命论:上天按照人的善恶来决定人的生死寿夭,这种安排是无法通过个人德行之外的方式来改变的(12)当然,从太史等人身上,也透露出春秋时期命运观念的多样性。他们相信,人的命运可以借助德行之外的手段来改变。这种观念对上天属性的理解、对个人命运根源的理解,已越出了道德定命论的范围。。
从商代的盲目命运论到周代的道德定命论,是命运学说的进步,因为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后天德行得到应有的承认,因而对人的命运有了更接近真理的认识。但是,道德定命论又夸大了德行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扭曲了德行与命运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并不相符,也就必然引发人们的质疑。我们看到,春秋末年起,许多思想家对命运的理解就已明显偏离正统的道德定命论,开始提出新的更具有解释力的命运学说,其中,孔子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关于孔子的“天”的涵义或者他是否相信存在具有超人权能与仁义德性的人格神,以及“天”与人的命运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个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这里我们无法作全面考察,仅限于表明我们自己的基本看法。一方面,孔子没有否定作为人格神的天,一些材料显示他是相信这种天的存在的。正因为这种天存在,人的命运就受着天的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大体上体现着福善祸淫的原则。如《论语·子罕》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相信西周文化的存亡续绝是由上天决定的,而且他暗示自己就是上天派遣来执行维护和传播西周文化这一天命的人。至于个人的生死祸福,上天也作了安排、进行着干预。文献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13)《论语·述而》。孔子不反对向神灵祈祷,只是不赞同子路那种祈福方式,而主张通过个人一贯的德行实践来祈福。他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4)《论语·八佾》。这些材料显示的观念是一致的,即上天、神灵的确是决定人的命运的重要力量,而且上天、神灵福善祸淫,根据人的德行善恶来安排人的命运。另一方面,孔子坦率论及一些事例,由于这些事例的存在,使得道德定命论无法成为一项普遍必然的法则。孔子在谈这些事例时,并没有直接阐明它们与道德定命论之间的矛盾关系,但他把这些事例也归结为“命”,这就不仅隐晦地否定了道德定命论的普遍必然性,还似乎暗示着对决定这种“命”的“天”的性质有特定的理解。如《论语·雍也》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又《论语·先进》又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冉耕(伯牛)、颜渊都是孔门出色的弟子,德行优异,却都早夭。此二人的命运,很难解释为个人后天作为、个人德行的结果,只能归因于外部力量。显然,在这样的事例中,道德定命论是不成立的;决定命运的乃是外部力量,而且这种外部力量并没有体现福善祸淫、赏善罚恶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把命归于人格神的天的话,对天的性质只能有三种解释:它要么不具有仁义的道德属性,要么不具有决定一切的权能,要么既不具有仁义的道德属性也不具有决定一切的权能。易言之,作为人格神的天,由于不能避免发生在冉耕、颜渊等人身上的现象,它在道德属性或权能上是有局限性的。
据此,我们可以把孔子的命运观作简单总结:由于天的存在,道德定命是一般原则,也就是说,就大多数人而言,其命运的好坏取决于自身德行的善恶;同时,由于天本身的局限性,道德定命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即是说,就少数人而言,其命运的好坏与自身德行的善恶没有关系。实际上,孟子的命运观与孔子是相同的,而荀子除了对天的性质的理解有所不同,单就命运观而言,与孔子、孟子也是相近的。傅斯年先生把先秦儒家的这种命运观叫做“俟命论”:“俟命论者,谓上天之意在大体上是福善而祸淫,然亦有不齐者焉,贤者不必寿,不仁者不必不禄也。夫论其大齐,天志可征;举其一事,吉凶未必。君子惟有敬德以祈天之永命(语见《召诰》),修身以俟天命之至也(语见《孟子》)。此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亦为非宗教的道德思想所必趋。”(15)傅斯年:《性命古训辨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44页。傅先生抓住了先秦儒家命运观的要旨,即它本质上是道德定命论与盲目命运论的糅合。不过,傅先生此说有一点不足:“俟命”是着眼于人对命运的主观态度,因此“俟命论”这一术语与着眼于命运客观成因的“命正论”(即道德定命论)和“命定论”(盲目命运论)相提并论,略嫌违背分类的逻辑。
至西汉,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命运学说作了继承与发展。虽然董仲舒传世著作中相关材料较为有限,但仍能使我们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从与三命说相关联的角度说,如下一条材料是最重要的: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体也。有变命存其间者,其政也。政不齐则人有忿怒之志,若将施危难之中。而时有随、遭者,神明之所接绝属之符也。亦有变其间,使之不齐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则重政之本矣。(16)②③⑤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9—150、149、137、348页。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包含了“大命”“变命”“随”“遭”等概念,很显然,此后的三命说与之存在密切关系。不过,这段话很晦涩,以致注释家的注解多有不切处。如认为此处的“大命”就是三命说中的“正命”,“变命”就是指“随命”“遭命”;还把此处的“神明”解释为“人的精神”等等②。但如此下来,这段话的语义变得难以理解。我们认为,“大命”不是专门概念,“大”只是形容天命的权威性。因此,人生而具有的命(“人始生有大命”)并不是单指三命说中的正命,而是一个笼统概念,囊括了正、随、遭三种命。“政不齐则人有忿怒之志,若将施危难之中”,是说政治不清明,人们就会产生忿恨情绪,如《孟子》引《周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由此将降下灾祸(这种由人的恶行招致的灾祸,属于随命,亦即变命)。至于灾祸有随命、遭命之分,是由于上天对人事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是时刻关注,根据人的行为善恶随时予以赏罚;其二是作一次性的安排,而后不再加以关注。此即“而时有随、遭者,神明之所接绝属之符也”。既然灾祸有随、遭的差别,就需要加以省察、区分,不应全部归于命定,而要对人事(此处强调的是“政”)的善恶予以重视。因此,整段话的主旨在于强调命有不同的类型,人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变命即随命上,从而在上天给出的初始条件基础上,通过好的政治活动为自己谋取好的命运。
董仲舒的其他一些论述能够为以上理解提供佐证。比如,上面那段话虽然没有明确“遭命”这一概念,但董仲舒是承认由外部因素所决定的、且人的良好德行无法予以扭转的坏命运的。他谈到颜渊的早亡、子路的横死、孔子的赍志而殁,然后总结道:“阶此而观,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③在其《士不遇赋》中,董仲舒感叹:“观上古之清浊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17)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有这些例子,都可归为三命说中的遭命范畴;即便把遭命限定为有德者的早夭或横死,除孔子外其他几人也属于典型的遭命。再如关于上天的性质。董仲舒固然强调上天具有利养万物的仁爱与赏善罚恶的正义属性以及超人的权能,但董仲舒的上天仍不同于基督教等一神教的上帝,它不像后者那样全知全能,甚至在道德上也存在人所难以理解的因素。他论及圣王之世遭遇天灾:“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⑤用“适遭世气之变”固然可以给出解释,但同时也暗含着承认,即便是上天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阴阳之气的运行,因此也就不能完全保证福善祸淫原则的普遍必然性。
据此,我们能看到董仲舒命运学说与先秦儒家的异同。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扬弃了道德定命论和盲目命运论,而主张两种命运论糅合而成的一种综合命运学说。不同之处在于,董仲舒在先秦儒家基础上对这种综合学说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是把“随”“遭”概念引入到命运学说中。董仲舒的作品在历史上有所散佚,因而我们难以判断他是否提出过“随命”“遭命”的概念。不过,他把《庄子·列御寇》中率先并列提出、但并无命运种类涵义的“随”“遭”引入到命运的分类中(18)《庄子·列御寇》:“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这里的随、遭,是指源于不同认识水平的两种生活态度。,距离纬书的三命说只有一步之遥。第二,从“人始生有大命,是其体也。有变命存其间者,其政也。……而时有随、遭者,神明之所接绝属之符也”这些说法看,董仲舒似乎不再像先秦儒家那样满足于对不同命运的承认,还试图解释不同命运的深层次成因。这些都是他试图发展儒家命运学说的地方。
四
表面看,三命说只流行于西汉末和东汉,是一种短命的学说,似乎是漫长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其实不然。它是此前儒家命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其某些理论要旨在此后的儒学中始终得到保留和传承,尽管相关的名词、术语基本上被弃置不用。另外,无论是王充命运理论的提出还是佛教、道教命运理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三命说为思想背景的,是对三命说的回应。但这些后出的学说未必实现了对三命说的彻底超越。在此我们把三命说放到儒学史以及与王充、佛道理论对照的框架中,简析其理论价值。
如前文所说,从命定论或盲目命运论到道德定命论,再到孔子等人对道德定命论的修正,最后到董仲舒对道德定命论与盲目命运论的有意识的综合,反映了中国命运学说从商周到西汉中期的曲折发展进程。董仲舒与三命说的确切关系怎样,现在已难以确知,不过,这样一个判断大概是合乎实际的:董仲舒提出了三命说的雏形,而这一学说在纬书作者们那里获得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形态。因此,三命说是儒家命运学说在西汉末和东汉时期的典型形式。
无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还是纬书中的谶纬神学,都有着肤浅粗鄙的性质。应该说,直接来自董仲舒和纬书的三命说之所以被后世儒家在表面上抛弃,其与粗陋的神学说教相纠缠是一个重要原因。三命说有粗陋的一面与错误的成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不应由此而将这种学说简单地全盘否定。三命说是对盲目命运论与道德定命论的综合与发展,拥有较后两者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和对命运现象的更大解释力。中国古代哲学经常把性、命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不妨把命运学说的演进与人性学说的演进作一个简单对比。先秦时期,在人性论领域出现了性善论、性恶论等理论,而董仲舒等人对这些理论作了扬弃,提出性三品论。性三品论当然存在自身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它具有先秦性善论、性恶论所不具有的复杂理论结构,对于人性现象也具有更大解释力。与之类似,在命运领域,先秦时期出现了盲目命运论和道德定命论,而汉代儒者将它们发展为三命说。三命说其实就是性三品论在命运问题上的对应物(19)汉代已有人有意识地参照性三品论来阐发三命说。东汉后期荀悦所著《申鉴·杂言下》有言:“或问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命相近也,事相远也,则吉凶殊矣。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荀悦此处明确提出命三品说的概念,认为命分上中下,上命、下命不由人为,而中命则由人为所定。就中命而言,天赋的初始条件是相似的,但人的后天努力是不同的,因此有了好坏的分化;亦因此之故,中命之人应该把握命运的道理,尽力培养、践行先天的德性,来造就自己的命运。荀悦没有使用受命、遭命、随命的术语,但显然承袭了三命说的要义。。具体说来,三命说在如下几点上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在大的结构上,三命说强调外部因素为不同的人所确定的命运或所提供的造就命运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抛开人格神(“天”)神学虚构的引入以及对外部因素决定作用的夸大姑且不论,三命说的这个基本观点还是合乎人类实际的。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而非对其视而不见,或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才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历程起步于一种怎样的起点,确切地说,一种多么有失公平正义的起点。第二,三命说的受命、遭命之说尤其是后者,体现了对人类局限性的一种深刻认识。人固然是万物之灵长,拥有高度的智能和德行,但这些并不足以使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无数无辜的甚至德行纯良的人遭受来自自然或社会的厄运,时刻昭示着人类局限性的事实。二是三命说承认受命、遭命的存在,但同时也强调随命的存在。这意味着它在克服了此前道德定命论的弊端的同时,保留了道德定命论的合理内核,即承认人的主观努力尤其是德行修养与实践在命运形成中的重要性。
三命说形成不久,就受到了王充的批判。王充的命运理论比较复杂,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展开。简单地说,王充对三命说有弃有取:他承认受命(正命)和遭命的存在,却否认随命的存在。这意味着,按照王充的观点,人的命运都是天定(当然,王充的天是自然之天,而非人格神之天),并借助各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幸、逢、遭、偶)得以实现;命运无关乎德行,易言之,德行的好坏在命运形成中不起作用(参见《论衡》中的《命义》《气寿》《命禄》和《幸偶》等篇)。王充否定了人格神的天,把神学从命运学说中驱逐出去,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否定人的后天努力,否定德行对命运的意义,从而滑向了宿命论。因此,王充的命运理论并未真正实现对三命说的超越。
那么,道教、佛教的命运学说又如何?对比三命说与道教、佛教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双方对立的焦点在于,在命运学说的构建中是否拘执于德福统一原则,即有德者必有福、无德者必有祸。三命说的受命、遭命显然是违背德福统一原则的,可见,三命说实质上放弃了德福统一原则,或者至少是放弃了这一原则的严格形式。无疑,这种放弃一方面使三命说更加接近于人的命运的真相,但另一方面也会引发人的精神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如果说善恶有报是公平正义的核心要素的话,放弃德福统一原则就等于承认公平正义是没有保证的。而这个精神难题会直接造成道德生活中的困惑:对于我们而言,如果德行并不必然地带给我们幸福,那么德行的意义又在哪里?三命说固然不像纯粹的盲目命定论那样完全割断德行与幸福的纽带,但毕竟也削弱了这一纽带。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能明白,道教的承负说、佛教的因果业报说所致力的方向何在:它们要挽救德福统一原则,从而坚固人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最终促成道德和宗教上的修养与实践。
汉以后的思想史显示,尽管道教、佛教命运学说对相当一些人产生了吸引力,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取代三命说。从魏晋到宋明,绝大多数儒者继续坚持三命说的理论要旨,尽管他们或许抛弃了神学的天,尽管他们不曾使用三命说的名词与术语。儒者采取这种立场,有着理智上的理由:承认受命、遭命的存在,固然会使我们陷入理性与道德上的迷茫,但佛道命运学说为摆脱这种迷茫,却又陷入形而上的理论虚构。至于三命说所导致的使人直面德行与个人幸福之间的断裂,对于哲学理论的探索与人类精神的发展未必是消极的,因为只有直面这一断裂的事实,我们才会真正抓住道德的本质,也才会在流俗理解的幸福之外寻找德行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一点,此后的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能够提供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