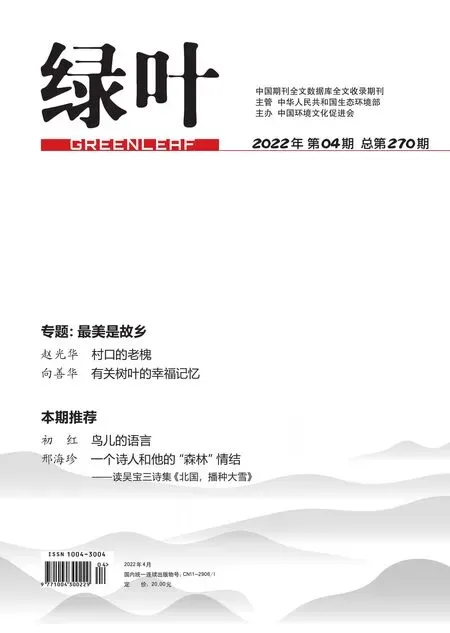一个诗人和他的“森林”情结
——读吴宝三诗集《北国,播种大雪》
2022-11-26邢海珍
◎邢海珍
1
翻开诗人吴宝三出版的诗集《北国,播种大雪》,白山黑水的大森林气息扑面而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吴宝三逐渐成为著名诗人,成为因“森林”而著名的诗人。1963年,吴宝三在林业战线参加工作并开始了诗歌写作。1964年,他在《东北林业报》发表了第一首诗《上工》,后来又在《黑龙江日报》副刊发表了《林区筑路(二首)》,从此开启了森林诗写作的绿色生涯,成为“森林诗人”。这部新近出版的诗集共分四辑,几乎都是写山与林,诗集收录了他森林诗的重要作品。
2
在吴宝三的森林诗中,我很喜欢那些歌唱“伐木者”的诗篇,今天的林区已不再以“伐木”为主业,也很少有人再说起伐木的话题了。但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从吴宝三的诗里看到的是当年的情境,是一段林区人难以忘怀的人生命运历程。如果说树木是资源,即使在今天,“伐木者”也必将还要存在下去的,只不过他们的劳作具有了更多的环保和生态意义。
当时间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那些当年的“伐木者”已经是全新的精神状态,吴宝三的森林诗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他笔下伐木者的诗意构建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半个世纪前,他在《伐木人》一诗中写道:“喊山声,/雄浑粗犷,/出色的歌唱家,/没有你的声情激昂;/大树倾倒,/雷般炸响,/有谁比得上/你这打虎的胆量!//你是这般富有——/原始林、人工林,/一代接一代的栋梁;/还有东西南北,/人间天上……/因此,/当你肩扛斧锯上工,/总是神采飞扬,/满腔自豪步步洒向山场;/当你伐倒一棵大树,/轻抚树墩,/哦,定是给/山岭起伏的国画,/盖一枚印章。”作为一个时代的劳动者,林业工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始的建设年代,开发深山老林,为国计民生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宝三有过林场工作的切身经历,领略了林区人开山伐树的胆量与气魄,诗人以写意的方式标举了林业工人的精神气概。诗简练生动,朗朗上口,诗的结尾把伐树留下的树墩比作国画上的“一枚印章”,富含着生活之美。
多年来,诗人吴宝三始终对森林怀有深情的热爱,无论是身在其中,还是长久离开,森林都让他魂牵梦绕难以释怀,他的许多诗作都有森林的浓重色彩和深情记忆。
在《松涛曲》中,诗人写下这样的情景:“万缕阳光,/从针叶的缝隙间筛落,/又被涌动的松涛溅起;/星光灿烂,/黑黝黝的大山,/传来急不可耐的呼吸。//哦,定然是/盼那悦耳的汽笛,/和朵朵白云挽着黎明升起,/把栋梁对远方的思念,/带给航船一样的城乡,/和帆樯一样的楼宇……”山林风物的描写饱含着无限深情,山林树木闪烁着人情人性的光芒,在时代和社会的怀抱中,“悦耳的汽笛”以及“栋梁对远方的思念”,都是诗人以诗的方式抒写的大爱之情。
小兴安岭是诗人吴宝三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写这一方山水的诗篇总有浓浓的意味,比如《桃山》的开头就是情趣十足:“你远近闻名因为像桃,/在山的家族中确乎很小;/然而,桃子长得天下难找,/森林是枝叶,白雪是绒毛。”在山的象形的“桃”字上打开了诗意的大门,“森林是枝叶,白雪是绒毛”的比喻,可谓微妙中含藏了深深的挚爱。
《我思念白桦树》是一首抒写怀念之情的诗,近似咏物,是以第一人称表达内在情感的言志之作。诗人把白桦树比作“慈母”,从儿子的角度抒写对于养育之恩的感激和对于久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诗人说,“我思念兴安岭的白桦树,/一个久别故乡的儿子,/思念远方的慈母。/梦中,/听见你的轻声呼唤,/醒来,/泪水山溪般涌出。//那一年出山离开你身边/你用衣裙编成小船,/将我摆渡;/记不清接到多少家书,/读不尽你那深情的嘱咐,/洁白洁白的信封,/点缀着斑斓,/哦,/那是你滴下的思念儿子的/颗颗泪珠。”诗人以白桦树为对象,表达对于“慈母”刻骨铭心的感恩之情。这种情感,正是诗人离开林区、离开大山、离开森林的一种不舍之情,是对生命中一种知遇之恩的发自内心的感念。诗人着力表现白桦树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呵!一场熊熊大火,
烧光了山林的繁茂,
唯有你没有沉沦不甘屈辱,
第一个在废墟上站起来,
织出树冠的绿网,
打捞出森林的希望,
滤走荒芜。
于是,
红松子孙代代繁衍,
有谁能够相信,
你拯救出一个兴旺的家族!
当松涛林浪唱起欢乐的歌,
你却倒下了,
化作青山忠骨……
山林遭遇火灾后,第一个生长出来的是白桦树。诗人在诗意的想象中把母亲与白桦树融为一体,表达了怀念慈母的赤子之情。山火中的母亲,不甘沉沦的母亲,打捞希望的母亲,为子孙献出一切的母亲!诗人把自我的一片真情寄托于白桦树,对林区怀有深深的爱,这就是诗人吴宝三的“森林”情结。
3
作为森林诗人,林区生活只是吴宝三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后来他上学读书,再后来离开了大山和森林。吴宝三的“森林”情结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森林的回忆、怀念,是对森林历史的瞻望与反思,是收藏在心中和生命深处的光。
诗人的代表作《一棵阔叶树的自述》,写作此诗时,诗人已经离开了兴安岭的森林,来到了渤海之滨的兴城,但诗人仍是怀揣着对森林、树木的深情和理想,抒写人生之路上不断进取的情怀。“一棵阔叶树”是诗人抒情的凭借,是以物喻人,是诗意感性构成的具象之物,一首近于直抒胸臆的诗,有了开口说话的树,树的生存环境让诗“同山溪絮语,/和流霞嬉戏”,“发芽”“落叶”都有所本,让诗之所以为诗多了一些必要条件。比如诗中这样写道:
我长得并不笔直,
甚至有些弯曲,
我的躯体,
有暴雪的箭伤,
狂风的刀痕;
我的形状,
残存着动乱年代的记忆。
抒写“人”的情志,却以“树”作为寄托,这就是诗人“森林”情结的作用,是它促成了诗的诞生。对树的描写就是写人,是物我同一的方式,从树的形象开始,却直达人生世界,“我的抱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只盼根深叶密!/倘若不能做一根栋梁,/也要走进大厦,/为欢乐的人家,/添一件可心的家具……”诗人借树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追求和希望,正是所谓的托物言志。读吴宝三的这些森林诗,我知道他的“森林”情结早已深深扎根于心灵,无论离开多远,无论走到哪里,他总会心系森林和大山,他生命和文化的根是不可拔出的。
在《北国,播种大雪》这部诗集中,还收入了写大海题材的一些诗作,但我们从另一种美质的情境中能够看到诗人心怀山林、刻骨铭心的“森林”情结。即使面对大海,也还是念念不忘森林。《伐木者的心》就是表达离开后对于森林的思念之情,诗人面对大海,而一颗心已经飞向了他想念的山林,“掬朵朵温泉浪花,/向大地深致谢意”,他一颗伐木者的心正朝着森林的方向飞去:“按捺不住似箭的归心,/站在屋檐下让水珠淋漓,/哦,干旱的心田湿润,/梦中的青山长绿……”归心似箭,情意淋漓,诗人的每一笔都写得情深意重。短诗《海边松林》是在海边写树,深切地表达了诗人眷恋大地的情愫:
一棵棵挺拔的油松似竞相奔跑,
全然不顾大海的日夜相邀——
那温柔的臂膀一阵阵张开,
你回答的却是一个个问号。
你并不怀疑大海的美丽,
是反躬自问一生的品操。
因此,虽有多情的浪花献上,
你还是痴情地向森林倾倒!
虽有海浪相邀,但仍坚守立足的大地,诗人还是让这些“油松”之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表达了一颗矢志不渝的坚贞之心不会因为眼前的风景而改变初心的坚定信念。诗人的心中有森林,诗的意象选择也多与森林相关,他对于森林和大山的赤子般的深情由此可见一斑。
4
在高唱“伐木者”之歌的年代,大山和林业完成了共和国早期基本建设的光荣使命,作为森林诗人的吴宝三和他的“森林”情结也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森林资源告急,生态环保提上日程,超量砍伐的时代结束,由“采山”到“护山”,中国的林业开始全面转型。诗人有一颗敏感的心,在歌唱伐木者的同时,吴宝三就关心生态,在一些诗中表现出反思精神。在《新生林》《绿色的书》《造林队伍进山去了》等一些诗篇中都表现出环保、造林的意识,对森林的未来和命运进行反思。在题为《山岭和伐木者的歌》的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山岭和伐木者各唱一支歌,
年复一年,花开花落,
“顺山倒”越唱越高,
松涛曲越唱越弱。
渐渐,深山的歌声日趋冷清,
消失了,伐木者脸上的笑靥。
送棵棵栋梁走向未来,
却为何挽不住今日之绿色?
伐木者唱起绿之歌哟,
千山万谷放开歌喉应和,
共一旋律,同一拍节——
填平伐木者眉宇间的大川,
抚平山山岭岭的每一道皱褶……
在“伐木”的歌声中,诗人也唱出了心中的隐忧,当“深山的歌声日趋冷清”,当“送棵棵栋梁走向未来”之时,诗人发问,“为何挽不住今日之绿色”?但诗人抬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希望,“伐木者唱起绿色之歌哟,/千山万谷放开歌喉应和”,诗人和森林一起走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绿色诗意情境之中。我们的山河大地,正在高举勃勃生机,大步走向无限葱茏美好的未来。
林区老英雄马永顺是全国劳动模范,共和国成立初期曾闻名全国。伐树一人能顶五六个人,但他对过度采伐所造成的林业危机,也有清醒的认识,于是他从采伐模范转而成为造林英雄。诗人吴宝三与人合作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马永顺传》,弘扬其伟大的造林精神,获得了《人民文学》奖。马永顺逝世后,诗人创作了组诗《一个人与一座山》,歌颂老人家为环保生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生命的号子》一诗中,吴宝三这样满怀深情地写道:
走进深山里,
有片马永顺林,
千万棵长大的小树,
歌唱一位离去的老人。
青山是巍峨的丰碑,
松涛是不尽的功勋。
啊——啊——啊——
一首生命的号子,
化作绵绵小兴安岭的绿魂。
在“伐木”的歌声中,诗人也唱出了心中的隐忧,当“深山的歌声日趋冷清”,当“送棵棵栋梁走向未来”之时,诗人发问,“为何挽不住今日之绿色”?
在马永顺的身后,是他亲手种下的树,是树苗长成的森林,“青山是巍峨的丰碑,/松涛是不尽的功勋”。一个平凡人的丰功伟业,将与绿树、青山一起,与“天保工程”一起蔚成壮丽的风景,不断地造福人民。
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吴宝三调到辽宁辽西工作,除了写森林诗之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有关大海的诗歌。从林涛到海浪,山与海携手,曾经陶醉于林涛的诗人,咏唱起山涛海浪来也是那么得心应手。
吴宝三毕竟是森林诗人,山林的情怀已成为他生命中永远的情结。当他来到海边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把林涛与海涛共同置于胸中,来激起生命中更富诗意的回响。他写过一首《海,我期冀会合》的诗,抒写了诗人心中的山海之情:“从森林到海洋,/我是一条奔跑的小河。/在林海和大海之间,/我跋涉着迢遥的寂寞。//林海里,/松涛层叠。/年复一年,/因为思念大海,/总有纷纷的落叶。/大海上,/那各样的船只,/本是林海派出的使者,/航行了千百年,/竟没有驶出沙滩的疆界。//我渴望,/哪年哪月——/林海和大海团聚,/山海相接,/大海的每一朵浪花,/跃上林海的每一个树冠,/大海涌起的潮头,/化作林海的万顷碧波。”这首富有激情和浪漫精神的诗作,拓展了诗意更宏阔美好的境界,诗人把森林和大海用想象和感情连接起来,让诗的意境有了新鲜的色彩。
5
诗集《北国,播种大雪》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书,上起1964年的《上工》,下至2021年的《北国,播种大雪》和《雪,落在兴安岭》两首,中间隔了近60年。如今,诗人吴宝三已近八旬,怀抱“森林”情结,仍在写诗作文,仍有许多著述接连不断地出版,其勤奋精神令人敬佩。
诗人吴宝三开始写诗的时代是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起步时期,文学经历了不寻常的艰辛跋涉,许多作品还带着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记。吴宝三穿过了漫长的时光厚壁,克服了许多时代的局限,显现了生命顽强努力的精神,在与时俱进中坚持自我的创造个性,确是难能可贵的。
放在文学发展的层面看,吴宝三的诗歌肯定不是新潮和新锐的一流,他还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吴宝三的诗仍与他的“森林”情结同在,在多元发展的时代,谁生长,谁死去,也是不好说的事。
我去过黑龙江的绥棱林业局,那里建了一个“吴宝三文学馆”,林区人民记着一个诗人的好,大山和森林以博大的胸怀滋养着诗人的大爱情怀,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知遇之恩呢?
诗集《北国,播种大雪》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书,上起1964年的《上工》,下至2021年的《北国,播种大雪》和《雪,落在兴安岭》两首,中间隔了近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