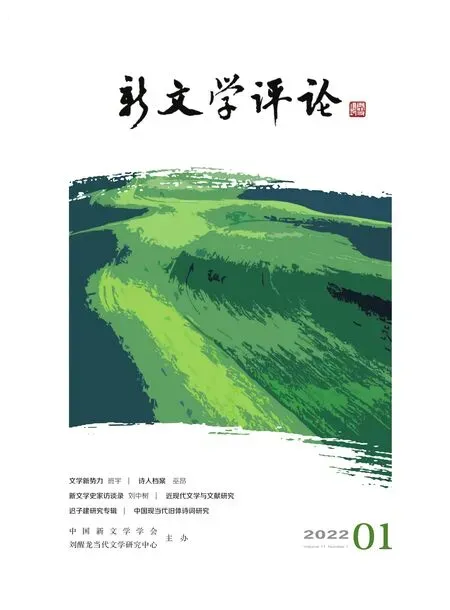羁鸟梦华录
——《民谣》读法一种
2022-11-24□赵晨
□ 赵 晨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这是《浮生六记》第二卷“闲情记趣”的首句。由此,我们发现,少年的目光中有天真、勇敢、张扬。“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面。”①我们再次看到少年人的目光,这目光越过码头、越过日影、越过湖面,越过时间,沾染了潮湿的水汽,裹挟着南方的蓬勃生机,直勾勾地看着回忆中的故乡,像是要将其看穿。惟有如此热烈坚毅,才能在故乡中看到自己的往昔岁月与年少情怀。《民谣》是从少年的目光开始的。
一、 羁鸟
飞鸟必须离开地面,才能获得一种俯瞰芸芸众生的目光,这样的目光清晰明澈,也掩藏着无尽的落寞。一旦起飞,就挥别了大地,天空成为他们有且仅有的无垠空间,于是飞鸟没有故乡。《民谣》就是在找寻自己的故乡,这个故乡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面目清晰。以天空为背景,此时的羁鸟是一种观看装置,故乡成为被拍摄的对象,而坐在码头上的少年成为用目光摄影的人。《民谣》犹如一部摄影作品,摄影主题是故乡,每一次回忆都是拍摄时瞬间的偶然,每一个当下的瞬间都借由摄影这一技术参与进过去的显现,于是少年王厚平不是再现了记忆,而是再现了生活。苏珊·桑塔格谈道:“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它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像知识,因而也像权力的关系。”②少年王厚平自出生起就与江南大队的历史关联在一起,他是被迫参与进故乡的权力更迭与变迁关系中的,可是他在观看的过程中有如此多得不到解答的疑惑,这促使他开始重新考察自我与故乡的关系,他想要澄明自我与世界的边缘。因此,这个敏感细腻的少年始终和村庄保持着距离,他始终在发问,始终在思考,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这个村庄。他的凝视是变幻世事中恒定的参照系,即便是几十年后他已身为人父,抱着女儿在水码头上观看村中少年游玩,他所感慨的也是:“他们与我们的不一样”。恰恰是无数个“我们”构成了故乡,正是“我”和“我们”一起构成了历史的连贯和故土的真相,故乡不是具象的此在,而是羁鸟情感的寄托之地,其真身在羁鸟的不同维度的目光中逐渐明朗清晰。
羁鸟也是一种身份。少年王厚平十三岁爬上了石油钻井队的井架时,他便短暂地飞出了这片故土,他有机会看到更完整更独立的庄舍,也有机会看到辽远的地平线。这个与江南大队一起成长的少年选择了飞向高空,选择了离开故土,选择了用冷静的眼光去逡巡故乡的每一个角落。“记忆不是对过去的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一种对事实的构建以及积极地对世界重构的形成。”③在冲淡的外衣包裹下,在有限的哀愁氤氲下,少年那迷惘的审视目光重塑了故土,在重构的过程中他建立起了离开的因由,唯有离开,才有机会重归故土。勇子永远地留在了江南大队,而王厚平飞出了江南大队,他这一飞,就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庄舍镇县,远离了自己父系母系的渊源,远离了奶奶背后的家族史和外公身后的革命史,远离了塑造王厚平的一切。同样是飞翔,马尔克斯笔下的巨翅老人在领悟了人群的冷漠无情之后,飞别人世,飞向海天交接处,凝成一个虚点,消失。王厚平没有翅膀,他借助文明的力量飞离了这片温暖、充满麦子霉味的故土,飞向天空,再折返。为何折返?因为思念故土的一切,无法割舍。在坚韧的记忆面前,唯有妥协唯有重返。两种飞翔,一去一回,一轻一重,都在彰显人情的质量。鸟儿天生就会振翅高飞,但是只有那些有故乡的鸟儿才能落地。羁鸟恋着旧林,池鱼思着故渊,未必是因为其他的林与渊不够好,只是我们穷尽一生也无法摆脱故林旧渊对我们的形成与塑造。沈从文的湘西山水,王安忆的上海弄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故土的无尽召唤。离开时也许需要千百个理由,但是重返时理由只需要一个:思念。故乡不是那些被无尽的生活细节淹没,并被我们逐渐遗忘的家园,而是我们心中无论存放多久都不会暗淡的存在,是千百个盖茨比的绿灯按照平方数汇聚叠加的衍生。“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④为了完成“我”和故乡的内在区分与深度关联,《民谣》必然要不断地去敞开一个新的世界,只有离去才能敞开、才能回归。未经敞开的封存是不够牢固的,未经离去的归来也谈不上归来。少年王厚平因为飞离了家乡,而获得了永久的回乡的可能与期待,他将永远被这份情感所慰藉,他也将永久地获得羁鸟的身份,这是故乡在他离开时所赠予他的礼物。正如海子早已写下的诗行:“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⑤
当我们在小说文本中捕捉到记忆这样精炼而繁复的字眼时,很轻易地会联想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但是我们不妨更谨慎一些。普氏小说所描绘的是静物般存在的过去,是按比例多倍缩小再嵌入玻璃罩的景观。正如纳博科夫所指出的:“普鲁斯特是一个透镜,他的——或说是它的——唯一的就是将景物缩小,并通过缩小景物的方法创造出一个回顾中的世界来。”⑥普氏在召唤过往,因此将过往缩小,好常置身边可随时取出来回味,就像随时可以放进茶杯的玛德莱纳小蛋糕,这样的景观是无呼吸的静止与精妙。而《民谣》所呈现的是借由文字魔力而等比还原的鲜活情境,从米水的波涛荡漾到大头放生的举动,从怀仁老头从河中捞起的死鱼到退水之后散发出的麦子霉味,这是小说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这些生活片段是立体的、成片的,非读者置身其中不能领悟,故乡中的每一个人都与身后的社会产生连接,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从“我”与河水的互动开始小说也开始游弋闪烁,从河流中散发出的油味,到河中吮吸着米水的小鱼儿,作者以极细腻的感官体验复苏了故乡,以匠人那般的细腻工笔烛照着故土的生机,在雨水不断冲刷下故乡浮出地表。多年后的王厚平抑或是作者本人想要钻进的是故乡的生活,而不是回忆,这是少年郎对于时间的不屑与偏执。
二、 岁时记
也许每位作家都有一条自己的河。
苏童的河透过后窗就可以看到,那条河“压抑、被玷污、患了思乡病”⑦;鲁迅的河澄碧轻灵,与萍藻游鱼一同荡漾,发出水银色焰;奈保尔的河在夜间散发出奇异的魔力,将人带回熟悉、亘古不变的状态。在《民谣》这里,河流是文本的底色。南方多水乡,河流不仅是村庄的一种构成,也是村庄的灵魂。无论人事如何变迁挪移,河流总是自顾向前,河中的水在奔流的过程中不断蒸发、降落、再蒸发,孜孜不倦地重塑着自己的生命形态,滋养着周遭的万物生灵。正是这样深沉稳健的生命力量让河流成为盘踞村庄的老魂灵。“循环”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概念,从王厚平与母亲讨论树叶与虫子的生命历程到朵儿对我的未来之问,循环的概念如同河水一般,在小说中涨落。流了千年百年,有无数人用竹篙击过水面,河水还在流,水花所闪烁的是永恒的光辉,是万般变化中的恒常。即使河流被文明建设的土填平,无法再沿水绕庄子一周,这循环也不会打破,流动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生命之河永不停歇,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王厚平与方小朵带着河流所塑造出的思维,背靠竹筏或河岸质询生存、生活与生命。所谓循环,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是历经无数次水波拍打后所沉淀下来的生活方式与坚持信念,是在河水的重力形塑下所积累的情感与生机。
望川而逝,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缕不灭的伤感情怀。从子在川上感悟到“逝者如斯夫”起,河流与时间的线性形成不置可否的对应,看见河流,便是看见了时间的观念。河流自顾自流走,时间自顾自走过去,《民谣》倔强地拉住了回忆的手,试图以小说的形式捕获时间的产物——回忆,借此回转时间。书写历史需要的是严谨的线性逻辑,复原的是固定的发展历程,但是回忆不同。回忆是流淌的河流中那些翻涌起来的浪花,它们轻灵跳跃,跃出了史的基本逻辑,打断了历史的连贯,是错位的断续的连接与重构。庄舍旁的河水是自西向东流的,坐在码头上的少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那时的他未必能够了解时间一去不复返,要等到1989年,已为人父、青春不在的“我”才会无比深刻地意识到时间的残酷。往事不可追,因为此时此刻的“我”已经不具备彼时彼地的情怀与心态,因为时间之河确然流逝。而作者一旦开启了回忆的入口,河水就会倒流,再次以过去的姿态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水波摇晃。川逝,而回忆在时间的肩头大声呼唤:“胡不归诶胡不归。”时间这条河在《民谣》中的流速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段、地点,有着不同的节奏,此处与彼处的流逝并不同。书写时,事件发生时,记忆浮现时,感觉重演时,不同的时间在精巧的文字中叠放、错落、交织,就像是各条支流各自流动,最终汇合到了一起,齐入大海。少年的成长故事节奏总是悠缓,时间宽裕到充分细化了少年的每一丝触感,甚至能够让“我”和方小朵经历分别,由分别而逐渐生疏,直到她成为少年心中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少年身后的故事,无论是和外公相关的还是和奶奶相关的都显得紧致急促,似乎再不抓紧时间将其封印在文字中,这些历史的光影就会被时代的尘土所掩埋。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魔咒,看似沉实厚重,然则飘逸轻渺,吸引着后来人不断飞奔追寻。从形式来说,《民谣》共有四卷,另附一个杂篇,杂篇与其说是形式的变化与创新,不如说是以史料的细致与翔实进入了虚构去弥补时间的断裂,复原了小说事件发生时的氛围,并借此树立叙述声音在文本内的权威。杂篇的叙述口吻虽统摄于成年后的知识分子王厚平,但内容面向广阔,时间跨度亦大。阿多诺曾将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萨义德认为“其再现的核心在于写作风格——极端讲究且精雕细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段、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⑧。这也可以形容杂篇中种种物料呈现出的复杂肌理纹路,这是回望故乡的羁鸟永远无法平静的内心。面对河流,面对流逝,作家王尧显然找到了另一种进入时间的方式,他没有随波逐流同河水一道流走,而是在河水中奋力摇桨、击打水面,凭借自己的清晰的记忆与浓烈情感统领时间碎片所组成的另一段完整时间。这之中隐含着一个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如果所有的时间元素和碎片都不是原来的,那么由这些碎片所组成的这条时间之河还是原来的吗?在这里显然是的,因为无论如何变更都没有动摇的那些人的良善悲悯,这些人性的光亮依然清晰可见,少年的目光也从未退缩。时间这条河流在小说中不是激荡前行,而是静水深流,其源头就在于作者所叹惋追忆的时间与流逝是形而上的,是与村庄大队史和少年的成长史并驾齐驱的,与乡间麦子同生同长的少年握住了开启时光之门的钥匙。
小说主要的脉络是少年王厚平的成长经历,其中穿插他对自己父系母系以及村庄抑或江南大队历史的整理,由此我们可以将《民谣》看作一部成长小说。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定义是:“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可称为成长小说。”⑨个体生命史、村庄史、大队史、文明史全都在王厚平这个少年身上重叠、浮现,他孤独地打捞着历史的碎片以及其背后所掩藏的观念。一个敏感的少年在一个敏感的年代中,面对历史与面对自我同样困难,他需要更多的细节与情感来树立对自我的认同、对家族的认同、对大队的认同。与其说小说描绘了王厚平的奋斗史,不如说小说复原了他的挣扎史,他用所观所察到的庞大公共世界在解读、阐释他的私人世界。通过梳理厚重的历史来明晰历史中的个人,胡鹤义、独膀子、外公李春山都没有被历史的阴霾所遮盖,反而散发出了坚韧的人之光芒;这个在村庄中奔跑着成长的少年坚持了“一己之念”,他没有完全臣服于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是哪怕摇摆、挣扎,也尽力握住了一丝人性那一端的绳索。与其说这是两种思想观念的斗争,不如说是少年的良善与整个时代的抗衡,虽然力量差距悬殊,但这抗争仍令人动容。在鸡蛋和高墙之间,选择支持鸡蛋那里一方也许是最为朴素的道德观,也是最难以贯彻的信条。王厚平以及他身后的家族都选择了鸡蛋,他们为此付出代价,也因此在混乱人世中泛出坚定动人的光亮。方小朵这个角色是如此的轻灵可爱也正是由于她身上携带这种朴素的道德和良善,她对村镇的看法、对勇子秋兰的看法都是那样的自然可亲。她的出现与离开都是突如其来的飘逸笔画,宛如神女现世,为那世人拨开眼前的迷障。她与王厚平复刻了阿里阿德涅之线这则故事,神话中米诺斯之女给了德修斯一个线团,德修斯凭借这个线团走出了复杂的迷宫。这个神话在《民谣》中被沧桑而童稚地戏仿,王厚平在青春悸动的潮湿情绪中拉住了那根线头,走出了历史与现实相交错的迷宫,人心与情感成为他们存在的依据与逃离迷宫的勇气。奶奶和母亲给政治身份有污点的大奶奶送红鸡蛋和糖粥,勇子和秋兰无所谓阶级有别的两情相悦、毅然结合,这些也许不足以改变一个潮湿阴郁的时代,但已足以温暖慰藉人心,足以让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感念一生。他和他们,这群故乡的人,用人性之光抚慰着故乡的断裂与伤痕。
三、 梦华录
孟元老在自序中言:“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⑩《民谣》何尝不是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小说从头到尾弥漫的麦子的霉味都是故乡隔着时间长河的召唤,这气味绵密复杂,随风而动。年轻时参与庄上舞龙灯的外公和独膀子,站在庄前打牛号子的怀仁老头,在女庙大门外烧纸扫灰的奶奶,在婚庆仪式上唱着《夫妻观灯》的父母,这些早已融进江南大队尘封历史的影子却有着如此清晰的边缘轮廓,这轮廓由少年时代的目光所勾勒。这些人会随着少年记忆的苏醒而一次又一次重生,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他们所生活的土地都会成为少年无法舍弃的永无乡,只要回去,就是少年的归来,就是生命四重奏的壮丽高潮。“我”患有神经衰弱,这是一种由无法遗忘所产生的不定的中间状态,混沌、迷离、复杂。向上则是借由此完成对现实的破坏与超越,向下则是与周遭一切共沉沦。白胡子老人的出现模糊了现实和梦境的边界,神经衰弱开启了现实之外的另一层世界,少年王厚平在挣扎,在故乡的多重线索与脉络之中泅渡。
热力学第二定律大概是最令人沮丧的知识,因为这一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的事物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混乱,这个过程被称为“增熵”,而我们绝大多数人穷尽一生想要从生活或命运中归纳出秩序,这个过程便是“负熵”。《民谣》的书写是一场诗意盎然的负熵之旅,少年王厚平的种种遭遇在这场书写试验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他想要重构一种秩序,这份少年目光背后所潜藏的野心不那么张扬,但是坚定有力。也许是因为“我”承担起了书写队史的责任,也许是“我”和村庄冥冥中的牵连,“我”始终自觉谨慎地站在一个恰当的疏离距离在观察村庄,而不是像勇子那样积极置身于村庄的历史之中。身处其中,就是顺应原有的秩序;身处其外,才有重建秩序的可能。书写大队史与少年王厚平的成长史重叠在一起,构成了小说最厚重的纠缠。在这样的纠缠中,历史与个人的关系首先是矛盾的,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我本身是‘历史’的对立物,为了我个人的历史,我这个历史的对立物是揭穿历史、破坏历史的。”而“我”却要被任命书写大队史,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也是矛盾的。王厚平的个人记忆是各种不同记忆的交叉点,他身上负载着祖父母的记忆、父母的记忆、李先生的记忆、勇子和胡鹤义一家的记忆,这些记忆分别意味着:家族、生活、文化、革命。可是王厚平并不是一个记忆的容器,因此他面对这些记忆不仅要储存,还要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秩序诞生了,是人性的恒常。“只有当统一叙述的历史不再侵占个体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置身于一个‘均匀曝光的世界’中,抵达日常经验的历史。”在重建秩序之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也重新拟定、关联,生活经验与故乡记忆壮阔复兴,少年不仅留存了记忆,也救赎了时间。
不见东流水,何时复西归?《民谣》借助叙事的力量让其归来,小说通过回忆联通外部的村庄演变历史和内部的少年成长经历,其中灌注积蓄已久的充沛情感势能,打通内外的界限,穿破时间的阻隔,让小说生成了混融巧妙的“克莱因瓶式”叙事结构。一条莫比乌斯带可以在三维空间中实现无限扩展,而两条莫比乌斯带就可以组成一个克莱因瓶,形成一个表面永远无法终结穷尽的物理模型。少年王厚平不是在庄上、镇上奔跑往复,他是在克莱因瓶式的叙述中往复,这是借由小说文本所实现的另一重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再也没有内外之分,读者得以感受四维的无定向。王厚平与故乡的每一个人、每一份情、每一抔土、每一滴水都紧密关联,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没有开头也没有终结,码头上的少年会凝固成一种永恒。土墙里的草籽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发芽生长,今年树虫死而明年树虫又生,时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小说的限度也被打破了,只要跃进瓶子里,一切就都有无限生长无限裂变的可能。这也许不仅是小说对于人世真理的一次重要发掘,也是作者给予读者的一次阅读训练,少年王厚平带着每一位读者不厌其烦地在故乡中、在回忆中、在梦境中奔跑,一次又一次,这不是西西弗斯式的苦役,而是温情幽微的回顾与演练,是少年目光与成人经验的有效融合,他的命运和他的时间都彻底地属于他自己。在希腊神话里,月神将文字交给了塔姆斯国王,王厚平抑或作家王尧将故乡赠予文字。
“我一直佩服奶奶的记忆力,她不识字,但听到的都记住了。”也许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也是《民谣》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发自然的流动,口耳相传的不仅是乡土杂事、流言纷飞,也是情感的流转与传递,能够记住的根本原因是用心体察、以情相待。《民谣》的故乡世界是一个有情的世界。奶奶和小云一生互相帮扶照顾,名曰过去的主仆实则姐妹体己 ;二先生胡若愚在监狱中收到的两只右手手套与其中蕴含的深情寓意;是剃头匠老杨以命相抵护住了外公和游击队的秘密,也是外公让“我”把老杨的遗腹子叫作舅舅。这些动人的情感片段也许就是小说中那个时代那个世界复活的暗号,“我”从始至终眷恋的并非只是那片用蜡笔无法画出的鲜活故土,而是生活在故土的那群人,是人与人之间或澎湃或静默的情感,是那些如今鲜见的良善与悲悯。“到民间去”是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民俗学者们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文化思维与内涵,按照洪长泰先生的说法这一口号至少包含了三个关键问题:“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心中的自我形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目的”。当我们参照这三个视点来回看《民谣》会发现,其中跳跃的不仅是少年炽热的脉搏,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成年之后的王厚平不是在为自己立传,是在梳理故乡的筋骨脉络,少年的深情回望是民谣传颂的精神旨归。他如此热切地感念着这片土地,关怀着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群,寻找着生活中闪光的那些善意,用人性的立场重塑历史,这是所谓民间,也是所谓乡情。故土人情和美,那些善良真诚的人们伴随着王厚平成长,眼看着他从一个大头娃娃成为写大字的人再成为飞出故乡的人,“我”在回忆和现实之间往返腾挪观看着大队的历史进程,也借由这凝望的目光重新审视当年的自我,在这过程中他借由记忆与情感复原了回不去的故乡和可回归的生活。庄子云:“夫藏身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即便已是如此安置,如此牢固,也无法防御有力者夜半来搬走,所以最可靠的还是藏天下于天下,藏故乡于故乡,藏民间于民间,这才是恒物之大情,才是《民谣》的智慧。
作家朱岳曾在《说部之乱》中写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将世界比作一只大碗,小说作者就是那些坐在大碗沿口的人,他们可以在俯视碗中世界的同时眺望碗外的虚空。对于坐在码头上的少年王厚平而言,故乡就是这只大碗,他以羁鸟的目光注视着这片有情故土中的种种往事,随后又飞到了空中去审视那个一直在寻找秩序、重建秩序的自我。他不是坐在碗边的人,他是沿着碗边奔跑的人,在一圈又一圈的汗水与欢欣后,他拥有了真正的飞翔的能力,他飞出了时间。
注释:
①王尧:《民谣》,《收获》2020年第6期。
②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插图珍藏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③阿斯特莉拉·埃尔著,吕欣译,蔡焰琼校:《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收录于《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6页。
⑤海子:《麦地与诗人》,《海子的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版,第16页。
⑥纳博科夫著,申慧辉译:《文学讲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6,第233页。
⑦苏童:《河流的秘密》,作家出版社2009版,第16页。
⑧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68页。
⑨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⑩杨春俏译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