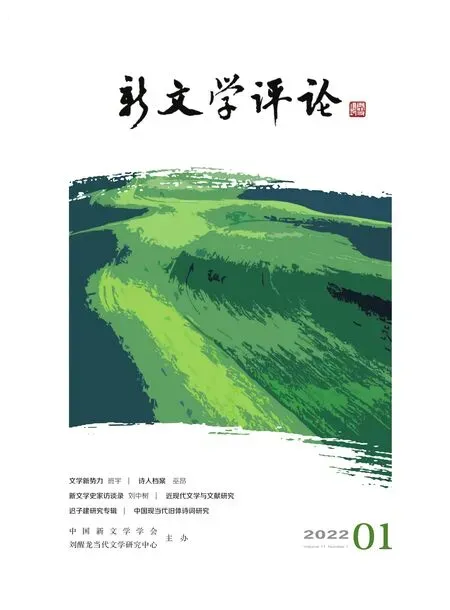论班宇后工人时代的人物书写
2022-11-24□王琨
□ 王 琨
班宇生于1986年,成长于沈阳铁西区,曾从事乐评工作十余年之久,2016年开始转向小说创作,于2016年在豆瓣首届征文大赛中凭《工人村》获得一等奖。近年来班宇的小说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班宇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冬泳》和《逍遥游》,2018年,他凭首部小说集《冬泳》获第17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班宇的创作大多以东北沈阳铁西区为背景,其所建构的铁西生活氛围具有典型的当代东北地域风格,细节上呈现出时代的骨感,语言简洁,洋溢着浓郁的东北特色,对于父一代和子一代双重命运的书写,饱含了丰富的时代密码和情感线索。对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的生存境况的书写,是班宇笔下的常态,以生活于其中的下岗工人和他们后代为主要表现对象,“失意者”是这些人物普遍带有的意识形态标签,正如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给予班宇的授奖词中所说:“时代的悖论成就了一个小说家的犀利,也守护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运。”
在以往的东北书写中,着墨最多的是东北参与宏观历史进程的宏阔身姿,它的自信与豪迈,丰富的资源,重厚的人情,共同构成雄浑壮阔的美学风格;而作为新生代作家的班宇,在书写东北时,呈现出不一样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质,体现了当代东北叙事的另一种可能。王德威在谈到迟子建的创作时,提出关于东北书写的另一种可能,即重新讲述东北故事:“当然不只限于文学虚构的起承转合,也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①班宇作为85后作家,他的东北后工业书写“以自身的青春成长经历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碰撞为底色,塑造了一群极具青春创伤经验的少年形象,以及挣扎、失落的工人父辈形象”②,班宇特有的主观情感色彩体现在他的写实与诗意交相呼应。一方面,班宇的后工业书写与他所经历的成长记忆和时代变迁有关,作家在青春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轨期所遭遇的生存体验,自我认知的转变,导致的社会身份认同焦虑,是班宇后工业书写的一个文化心理动因;另一方面,小说中所呈现的后工业书写的美学特征和思想内涵,还与作家本人的艺术追求息息相关,呈现出文化和生存双重审视的价值内涵。
一、 后工人村里的父辈群像
班宇不着意于宏观立场审视社会时代变迁,而是善于对父辈群体的生存进行审视,以精妙的观察,呈现了父辈在巨大的时代波涛中的反应,表现了他们的软弱、苟且、因循守旧、自我封闭,同时也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善良隐忍和坚毅的生命秉性。作为沈阳铁西区沈阳变压器厂工人的后代,班宇在文中所书写的铁西区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往,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沈阳铁西区几十万工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共同参与创造了共和国的一个个辉煌,作为国企员工的他们,也一同分享着为祖国创业的果实。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第一家国企倒闭的信号发出后,东北企业开始出现举步维艰的现象。
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人下岗失业现象终于潮涌般袭来,据2001年资料显示,“沈阳现在工业企业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③。在这种背景下,班宇的父母双双下岗,他们和其他几十万工人一样或者被买断工龄,或者短时拿着低保过日子,他们退回社会自谋生路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无奈以及未知的艰险,这些人是《盘锦豹子》里如豹子般怒吼的孙旭东,《肃杀》里下岗失业仍然不忘看现场球赛的肖树斌,《枪墓》中的抢劫杀人犯孙少军,《工人村》里的卖“古董”的老孙,跳大绳招摇撞骗的姐弟,开色情按摩店的夫妻。他们作为下岗职工,从国企员工流落到社会后,为了生存,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与自我角逐的过程往往意味着放弃自我。后工业时代,沈阳铁西区的父辈群像,由班宇的新鲜活泼又带有悲凉余味的文字晕染了出来。
《盘锦豹子》中孙旭东性格谦懦,爱岗顾家,但终究逃不了下岗、被妻子抛弃的命运,他默默隐忍着谋生的诸种不顺和艰辛。小说的结尾,当前妻的高利贷债主找上门来,要图谋他的房子时,孙旭东终于像一头发怒的豹子,他举着菜刀,后背上那黑棕色的火罐印子,像是豹子身上的纹路,随着他的一声声怒吼和反抗,逼债人的落荒而逃,积蓄了大半辈子的愤慨终于像湿气一样,从体内彻底散去。班宇将人物内心的悲屈聚集到极点来表现,更突出了人物的内在张力。即使在此之后,孙旭东依然要面对生活的苟且,继续逆来顺受的生活,但作者在那短短的一瞬所赋予孙旭东的英雄之光久久让人难忘。
《肃杀》中已经下岗的肖树斌,仍关心辽宁足球队的命运,虽然手中拮据,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看现场球赛的生活习惯。这个在之前平凡无奇的消费现在成了奢侈的追求,肖树斌还欣慰于凭下岗证带给他的半价球票资格。作者没有深入肖树斌的生命伦理去表现球赛对他的意义,但当他置身于一群摇旗呐喊的群体,可以自由地挥洒自己的激情与欢呼时,想必是他抛却尘世艰辛的逍遥时刻。肖树斌们在球场上与运动员一起挥散的激情青春,烙印着铁西的繁华记忆,但于现状无补,生存的困境毫无改变。肖树斌骗了同为下岗职工的“我”父亲的摩托车,“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辛,母亲卧病,摩托车是父亲的赚钱拉客的工具,失去它整个家庭就失去了经济来源。“我们”终于千辛万苦找到了肖树斌,当看到他在隧道口的身影时,“我”父亲却没有前去追问责备,而是继续坐着公交车默默离去,以作为最后的告别——“我”父亲的慈悲,无形中呈现了小人物之间的怜恤与温存。
《逍遥游》里,在“我”许玲玲的自述里,父亲许福明下岗后谋生无能,小本生意投资失败,让家里经济状况更加一塌糊涂,本来就掏空的家底又因为许玲玲的病更加雪上加霜。许福明曾经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执意离婚离家,女儿患重病以后,他赔钱卖了蹬三轮车拉脚挣来的二手厢货车。在前妻突然身亡后,他又背着行李卷返回家中,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负。靠“倒骑驴”拉点活,艰难地支付女儿巨额的透析费用。虽然在女儿的叙述里,对父亲偷蜂蜜、找情人等行为有所不齿,但许福明不失为一位伟大坚忍的父亲,他对父职的默默坚守,彰显了父一辈的高尚人格和人性最深处的柔软。
《工人村》里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国企下岗人员,几乎都在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或者被一两万块买断工龄,需要重新谋求生路,班宇通过他们谋求生存机遇的过程,形象展现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在《古董》篇里,老孙在没有搬迁的老房子开起了古董铺,但在工人村里,人们的基本生存尚不能满足,根本无暇赏玩所谓的古董,因此老孙并不盈利,在他所着意营造的神秘氛围里,他被骗,也骗人。在萧条的工人村里,开古董铺,他对这一生存方式抉择和坚持,体现了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者卑微的理想主义情怀。在《鸳鸯》篇里,吕秀芬刘建国夫妻,都曾经是厂子里的先进工作者,但都逃不脱下岗的命运,他们几经辗转,终于在警察妹夫的点拨和庇护下开起了色情足疗店,勉强糊口,但依然要时时遭受警察妹夫的经济勒索。作者在刻画这对夫妻艰难生存形象的同时,通过对警察妹夫渎职的种种行为,也流露出班宇的社会批判锋芒。
班宇在一篇访谈中说:“其实我想表现的是,东北是经历过大变迁的,人们的生活也确实经历了变故,却并没有穷途末路,每个人都活得特别顽强。”④班宇的父辈作为时代车轮的承受者,在下岗后他们大多是在挣扎地活着,艰难地求生,为自己为家人,无所顾忌地抛却个体尊严与昔日的光环,班宇把20世纪90年代至21世初的下岗工人群体作了具体而细微的描摹,提供了千姿百态的下岗工人群像。班宇从特定的时代精神出发,深化了民族个性所具有的坚韧品质,表现了东北工人在下岗风潮到来时,他们生命形态所彰显的特有光芒。
二、 子一辈的生存困境
沈阳铁西区工人村是班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作为铁西之子,他切身地感受到了下岗热潮对无数家庭后代的影响,工人村作为沈阳重工业时代的产物,见证了铁西区的鼎盛、繁荣的集体生活、国企改革后下岗带来的寥落与贫困。在创作中,班宇直视后工业时代子一辈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焦虑,他们在父辈的绝望里,艰难地寻找自我更新的出口,但又宿命般地徘徊于铁西老城区的精神地图。班宇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铁西区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记,是一个类似于符号化的、类似于记忆经验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写作者,我是想从这些记忆经验上面重新梳理或者提升出来;从精神层面上讲,这种转变形成的问题思考算是我的小说想要探讨的命题之一。”⑤
对于班宇本人来讲,从表面的人生经历看,他是成功突围的铁西之子,上了大学,后来在出版社工作,一直在各大媒体写乐评,后来又通过小说让更多人认识了自己。但作为铁西之子,工人村对班宇来讲,是永远无法逾越的飞地。青少年时期,父母下岗后,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于班宇的冲击是无形而绵延的,子一辈所经受的时代创伤往往没有父一辈所经历的那般直接凛厉,但是像班宇所说,东北人当时的心理落差某种意义上是跟既往的自己比较所产生的,上一代东北人的这种落差感会折射到下一代身上。他们在成长期被动地承受着来自父辈的无助,待成人后,在急促变化的时代节奏里,又比父辈多了焦虑和茫然,他们的生存困境来自历史和现实,在二者的双重夹击中,子一辈背负了更多的重担。班宇关于子一辈生存境况进行体察和书写的背后,蕴蓄着个体的温情与叛逆。总体上讲,“班宇的叙事主题为我们提供了‘子一代’记忆中世纪之交的东北社会变迁图景以及独有的城市经验,这不仅是对特定历史的独特阐释和文化叙事,而且让今天的读者对历史语境中的东北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认知”⑥。
《枪墓》中的“我”,是一位枪手撰稿人,时时被出版商给的命题作文所困扰,但“我”依然心心念念于自己心中的小说,那是一个关于东北铁西区下岗职工孙少军父子两代人的命运故事。“我”跟刚认识的女孩刘柳讲述其中的情节,渐渐刘柳和读者一样被吸引,在故事嵌故事的模式中,“我”完成了对自我与他者命运的双重讲述。随着刘柳的追问,故事脉络逐渐清晰,孙程背负着父辈的屈辱,度过漫长的成长岁月,虽然已经脱离父辈的生活轨迹,但他依然无法摆脱父辈给予的精神创伤,他的复仇情结让成长记忆中的暗角无限放大。终于有一天孙程带着那把手枪,来到曾经羞辱父亲和继母的人面前,他最后有没有扣动扳机,我们不得而知。孙程是“我”的化身吗?作者没有交代,孙程和“我”一样有着相似的从业经历,现实中的“我”,看似无所畏惧,是背离故乡的浪子,有点才华,有点好色,但是容易相信别人,即使最后被出版商骗走稿费,也毫无怨恨。在小说的末尾,“我”选择退出与刘柳的归程,独自走向未知的远方。无论“我”还是孙程,他们都共同构建了子一辈的人格图谱,他们背负着那块土地所给予的创痛与善良,在迎面而来的新生活里,常常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仍然选择相信和隐忍。
《梯形夕阳》里的“我”来到父亲工作的变压器厂,被调到销售科做科员,后来被分配去外地讨要欠款,在外地的“我”受尽冷眼和闭门羹,终于将工厂的部分欠账要回。“我”满心以为可以给工人发工资过年了,但得到的却是财务科长带秘书直接卷款潜逃的消息,“我”纵使踌躇满志,依然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财务科长卷款潜逃一事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却蕴含着作者的现实愤懑与批判,这种轻描淡写也许是作者曾耳闻目睹过多次的社会事件,也是作者对于东北工业溃败历程中,内部腐败的批判和反思,它们是压垮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班宇在表现子一辈个体生存困境的同时,也着意于营构人与人之间互相取暖,相互慰藉的温情书写。《逍遥游》中许玲玲身患重病,母亲离世,被爱人抛弃,与早已下岗多年的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没有谋生能力,只能每天用“倒骑驴”接点零活,每周的两次透析,使贫困的生活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病弱的许玲玲最大的愿望“就是天气挺好,周围没有障碍,身体也还行,有劲儿,走路轻松,自由自在”。赵东阳和谭娜这两位中学同学是她与现实联结的唯一窗口,他们三个人之间互相都有自己的现实困境,当然相比较于许玲玲事关生死的重病,他们婚姻感情的不顺利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二人同情许玲玲,尽力呵护她,又尽量不让她尊严受损。在三人旅行的最后一晚,当作者把赵东阳和谭娜的原始生命形态放到许玲玲的视野下去发现时,这种形态还是引发了许玲玲情感的绝望。她绝望的哭泣在暗夜的旅馆里终于无法自持,在她的呜咽中“我”倾听到一个压抑已久少女的内心声音,而这一声呜咽,正是作者“为弱小者给予支持,为卑微者延续幻梦”的慈悲,体现了班宇的个体人性关怀。
出于对铁西区工人群体生命形式的探寻,班宇善于从人性的阴暗里看到光明,在锋芒中微露仁厚。在其他表现当代东北的小说和电影里,东北往往是苦寒、萧条,是赵本山式的谐谑,是直播软件里的插科打诨。在班宇的创作里,他通过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观察,深入刻画了父一辈的艰辛、子一辈的困境。在这些表象之下,班宇更着重地表现了“那种个人生存的某种坚韧和自嘲的精神,那种尖锐的,可能是在相对冷酷的环境之下而形成的一种日常性,有人把它比作‘寒冷中的温暖’的东西”⑦。
三、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书写
班宇写出了父辈和子辈在时代浪潮中的生存体验和个体命运,同时还无形中呈现了一幅幅后工业时代的女性生存侧影。作为工业时代的一分子,女性职工随着下岗潮的到来,同样面临着生存的抉择,在产业转型期,她们可选择的空间往往比男性更逼仄。班宇在进行女性书写时,赋予她们不同的形象内涵,无形中折射出班宇男性叙事立场。
班宇笔下的女性有几类让人印象深刻。一是跋扈刻薄的女性,如《盘锦豹子》中的小姑,《云泥》中的张婷婷,《夜莺湖》中的吴小艺等,相对于男人的忠厚老实,她们往往表现得恣肆利己。她们的存在,像是一个命运的符号,给男性主人公带来的是精神伤害和物质损失,她们无尽地索取,从不回报,并且在关键时候还会给男性的灰色人生以致命一击,是男性命运里的坎坷,加速了男性悲剧命运到来的步伐。如《盘锦豹子》里的小姑,作为一名工人,她的个人命运与工厂变迁的关联并不大,她对生产线上当工人不感兴趣,结婚怀孕后她就不再去上班,喜欢轻松的工作,沉迷于打麻将。由于丈夫下岗引发的经济困顿自然要求小姑承担一些家庭的经济压力,以赌博养活自己和家庭成为她最终的选择。她常常在麻将桌上反思人生,确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这无疑是对小姑生存理念的讽刺。她“每日沉迷麻将之中不能自拔,她走路时又眼直勾勾的,步伐飘忽,若有所思,其实是在默默总结前一轮牌局的得与失”⑧。她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第四张牌,以至于流落到全国各处开麻将馆做生意,无奈运势不济,经营不善,欠下高利贷,并且用前夫的房子作抵押。班宇写了姑父孙东旭豹子般的暴发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而小姑的生存曲线则是一塌糊涂,作者对她嗜赌的人性之恶无限放大,所映现的是姑父踏实忠厚的生存姿态。在作者男性立场的观照下,小姑对传统妇德的僭越,对传统夫权的颠覆,并没有走向真正的自我,而是在沉沦中更加一败涂地。
班宇还善于塑造一些隐忍驯顺的女性形象。如《冬泳》里的隋菲,是一名离异的女性,她习惯于沉默,饱受前夫的虐待。“我”与隋菲通过相亲认识,并对她死心塌地,在“我”无法言传的爱情里,作者并没有给隋菲充分的个性展露,最后“我”为了给隋菲出气。在作者一系列有关“我”有勇有谋的细节铺展下,“我”一口气将隋菲前夫的头打烂,完成了英雄救美的现代演绎,即将来临的审判,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手中石头的起落中,完成了自我实现和超越的英雄壮举,完成了对弱小女性的救赎。隋菲这个角色,可以说只是让故事逻辑更顺畅、可读性更强的一个叙事符号,她无声的存在,对“我”的命运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无形中印证了母亲“这女的命里跟你犯克”的预言。
班宇笔下还有一类是知识型新女性,但这种“新”在作者传统性别观的烛照下,依然是一位倾听者,一位迷失者,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自我主体思考价值的否定,因为她们往往忘记男性的救赎力量。如《双河》《枪墓》中的“我”,是一名书写者,承担着启蒙女性智识的功能,“我”无处不在讲述,听众永远是虔诚的女性。这种听与被听的模式安排,无形中构造了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模式。
小说《于洪》依然是班宇东北经验的再次复现,但其所讲述的不仅是狭义上的东北,小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他们的人生困境适用于生一个人,每个人都能从斑驳的故事得到一点启示。郝洁遭遇过现实的重创,在阅读中消解伤痛,寻求自我与外界的和解。在她看来阅读是自我救赎的方式;但在丈夫“我”看来,郝洁的阅读正是二人关系的障碍,“这些日子里,我总觉得书像一道屏障,拦在我们两人之间,郝洁躲在后面,将自己遮蔽起来”。就这样,在丈夫面前,郝洁在阅读中达到自我与现实和解的努力,最终以婚姻的失败而告终。一百年前,伍尔夫认为女性应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呼唤,五四以来女性解放先驱所着意于耕耘的精神领地,在班宇的当代书写中完全溃败——在班宇笔下的“我”看来,女性获取知识,将是对日常的威胁,是对心中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在作者的叙述下,郝洁是“我”在现实中的温暖与亮光,但是他们终究免不了婚姻失败的结局。“阅读对人的拯救只能是一场虚妄”,这其中有“我”对知识本身和婚姻的多重思考,同时隐含着作者个人的价值反思,把妻子郝洁的追求与失败作为反思主体,反映了作家班宇的性别立场和局限。在班宇的创作中,可以看出,知识只可以作为女性形象的装点,就像《枪墓》里的刘柳,她的知识只要能够听懂“我”的讲述即可,她作为女文青的存在只是为了与我一起穿越困扰“我”的迷思,接下来的路,还需要由“我”来独自完成。而在另一篇小说《双河》里,作者对于男性知识则完全给予肯定的立场,“我”作为小说家,一个离异的失意男人,靠着口述的故事,成功获取异性的拥戴,同时取得了分开多年的女儿的肯定。
在班宇把女性客体化的写作中,女性形象往往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具有平面化、标签化特征,被压抑的女性生命逻辑,一方面是作者对异性的理解的欠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作家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班宇的女性书写,昭示着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尊重性别差异这些观念,远没有进入作家的潜意识成为一种内在、自发的人文价值尺度。
梁鸿说:“当一个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把一整拨人都挤压到外面的时候,这本身就是特别值得书写的一个东西。”⑨班宇一直孜孜不倦于对地域文化的审视、铁西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他见证了时代的车轮在父辈身上的印痕,作为子一辈的他间接承受到变动中的焦虑与茫然,针对不同人物,班宇所作的批判和审视指向不同价值内涵。在《冬泳》中,其表现风格是外向的,他从现实出发,反映铁西老一辈下岗职工的生存挣扎,和他们子一辈与命运抗争的徒劳与无力。在《逍遥游》里,除了对下岗职工生存状态的刻画外,班宇更加接近了自己的内心,将审美视角投入子一辈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兼顾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从现实与精神的双重角度,探讨现代个体生命精神动态的变化,这无疑加深了对生存真相的思考和审视。父辈败落后的疼痛一直伴随在他笔下人物的生命里,也成为班宇创作的源泉。但书写疼痛,并非班宇创作的全部,他具备多方面的叙事才能,他的创作前景值得期待。
注释:
①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②万国欣,黄育聪:《青春创伤与工人形象书写——论“80后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③张立勤:《沈阳:被贫困撕裂的繁荣》,《南风窗》2001年第10期。
④丁扬:《班宇:父辈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笔下》,《中华读书报》2020 年6月3 日。
⑤林喦、班宇:《构建新先锋的东北叙事模式——林喦与青年作家班宇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⑥朴竣麟:《“子一代”的战场——谈班宇小说〈枪墓〉〈双河〉》,《海燕》2021年第1期。
⑦杨沐:《讲述东北》,《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4期。
⑧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1页。
⑨孙若茜:《专访梁鸿:东北是可以虚构的》,《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