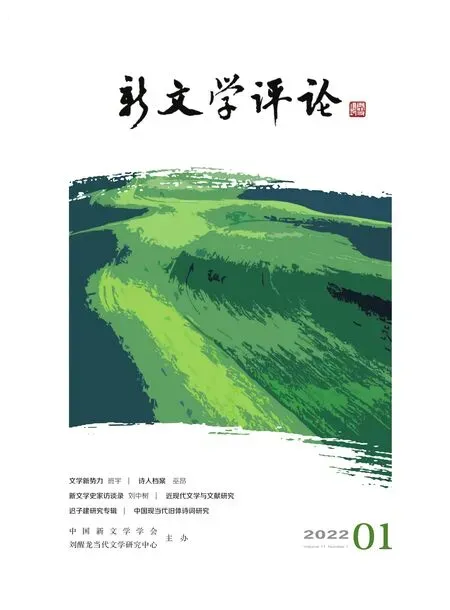一种自审的生命哲学
——读班宇的《冬泳》和《逍遥游》
2022-11-24李志雄
□ 李志雄
班宇因201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冬泳》而被文学界关注。他在2016年开始创作小说,收录在《冬泳》里的《工人村》是他的处女作。虽然在而立之年才开始创作小说,但班宇写作的起点却可以追溯到2007年。那时候,他的写作与音乐相关,写的是音乐评论。随着新媒体的诞生和消费市场的发展,传统纸媒遭到冲击,资讯不再匮乏反而变得触手可及,曾经承载着一定社会意义的乐评在多数时候变成了软性广告。面对新时代媒体格局的变化,班宇想从写作上寻求更多精神层面的探讨,于是从乐评写作转向小说创作。
由此我想到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现状。新媒体带来的便利,使得以网文为载体的小说喷涌式增长,但其中值得细嚼的却不多。造成这样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创作者欠缺思考,缺乏对当下社会与所处时代的反思,也缺乏对文学的自审。很多人的创作笔下没有鲜活的人,唯有天马行空的奇幻秘闻,置于架空世界的爱恨情仇。这样的写作只能给人以暂时性的情绪波动,却无法带来生命的哲思,不久就会被同类型的作品淹没,是可替代的,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独特性。
小说的道是思考,是静听时代的脉搏声,是探求文学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冬泳》和《逍遥游》里看到班宇的时代之思、文学之思。《冬泳》诉说的是一群生活在东北的普通人身处困境中的动荡、绝望、挣扎和顽强。小说讲东北却又超越东北,叙事所讨论的生命母题具有普遍性,能够引起不同地域,不同心境的人与之共鸣。而《逍遥游》在继承《冬泳》那种对现实生活进行反思叙事的风格外,还进行了自审,对内心情感进行剖析,对自身的文学创作进行思辨。班宇在《逍遥游》里对文学本质所做的探求,对叙事所做的文学技法层面的试验,甚至可以说是对先锋写作的致敬。由此可见,班宇的小说绝不局限于对东北的写实,而是有丰富的意蕴。
一
东北作家的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一脉,从萧红、穆木天到迟子建,再到“铁西三剑客”,有关东北的叙事从未中断。萧红《生死场》里苦寂的乡土,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壮阔自然和族群历史的碰撞,她们以不同的路径为东北“塑形”,而在当下,班宇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东北的新路径。
《冬泳》是一条布满锈迹的铁链,七个短篇环环相扣,共同铸成一个冷热交替、沉重、惨淡的“铁西世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掀起下岗潮,工厂接连倒闭,员工被遣散,东北工业区经济日渐衰落,这是《冬泳》的叙事背景。下岗潮是一个值得去反思的历史事件,但班宇并没有将文字聚焦在这个事件之上,只是将其作为背景,他关注的是下岗潮荡起的余波,下岗潮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一个事件通常是显性的、剧烈的,是符号化的,比如说工厂员工的突然失业,或是一座楼房的坍塌。但事件产生的影响却是隐性的,容易为人所忽视,如失业者自身精神状态的变化,和他所处社会、家庭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转变往往慢慢浮现出来。对于时代变革下发生的个体转变和个体间关系转变的思考,是班宇想在小说中重点探讨的命题。
时代经济大变革使无数个体陷进泥淖,或麻木,或茫然。小说呈现出来的冷寂感和困顿感是通过一个一个细节建立起来的。《肃杀》里有关环路电车事故的细节描写让人印象深刻,“我望见马路对面有阵阵黑烟上升扩散,蓝绿色的火焰缭绕,如同闪电一般迅疾而易逝,铁的骨架在其中若隐若现。半空里火花闪现,雾气之中有触手般的阴影来回甩动,惊恐、凄厉而无助的喊叫声也从中传”①。通过对火焰的色调、形状、晃动的人影和喊叫声的描写,我们感受到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恐惧和由心而生的悲痛。文本里的细节与细节间相互紧拽,后文有关围观者的细节描写与上述描写形成反讽。“围观者都在查数,踮脚默念,瞪大眼睛去分辨烧焦的白骨,有人数到四,有人数到五,烟尘不断袭来,他们揉揉眼睛咳嗽着,重新查数。”②这样的围观者不就是之前鲁迅笔下的看客吗?面对生命的不幸消逝,他们毫无悲悯和同情,而是持着看戏的态度,不厌其烦地耐心查数,这样的麻木冷漠比起蓝绿色的火焰,显然更让人恐惧。这两处细节的碰撞,直指困境下个体的某种转变:人的异化和退化。
班宇通过表现一系列人物言行的相悖构成反讽突显出个体的异化和退化。《工人村》里贩卖古董的老孙一方面痛斥乡亲们狡猾,迫使他买下假古董,另一方面他又用假古董讹诈长辈;在派出所担任警察的赵大明“黄赌均沾”,既到地下游戏厅里赌博,又怂恿亲戚开设违法的色情足疗店。《梯形夕阳》里的周科长非常看重变压器制造行业的相关知识理论,将销售策略和行业总体经济状况烂熟于心,并喜欢就此对下属进行随机提问,但他经营的变压厂却是负债累累,生产效率低下;职工费尽心思从外头收回欠款,将“把职工利益放在第一位”挂在嘴边的周科长却拿着这笔钱和会计私奔。老孙、赵大明、周科长,他们的社会身份因人性的异化而变得荒诞和虚假,古董店的老板专卖假古董,打击腐败的民警腐败,工厂负责人背弃工厂,班宇用尖锐的笔锋塑造了一群言行不一者的不堪群像。
在《工人村》里,班宇还有意地将战伟和李林两个从学识到生活状况都差异极大的人物联结在一块,并置于同一空间。战伟在赌桌上侥幸赢了李林,将此视作人生的大胜利,为之号啕呐喊。实际上,这场胜利没有太多现实意义,李林依旧是不愁吃喝的人生赢家,而战伟仍旧穷困潦倒,依靠母亲的丧葬费维生。这组对立充满着喜剧色彩,战伟的滑稽和尴尬体现了一种畸变的精神价值。
精神价值畸变是人性异化的显著症状。当个体陷入困境,原先秉持的价值信念无从帮助他突围,个体便会对原有的价值信念产生动摇和质疑。在困境中挣扎得愈久,原有的价值信念就被蚕食得愈加严重。一旦价值信念崩塌,精神价值便会畸变,个体甚至为逃离困境而做出残暴的恶性行为,自身的人性异化为原始的兽性。《盘锦豹子》里的孙旭庭,老实勤勉,做事肯钻研,为岳父家修天线,为工厂装设备;但个性软弱,在父亲葬礼上摔咸菜罐子,前后摔了两次才成。这样的一位老实人几经生活变故,因生产事故被调离车间,随后从事销售却因自己的无知触犯法规以致下岗。下岗后花掉积蓄买下彩票站卖彩票,生活重新上轨,却在此时碰上前妻惹来的麻烦,陷入住房不保的困境。被逼至绝境的孙旭庭最终不再平和,不再隐忍,异化为“豹子”,“像真正的野兽一样,鼻息粗野,双目布满血迹”③。他拎起菜刀直奔债权人而去,企图用暴力撕裂困境。《肃杀》里把刨锛藏在公文包的父亲,《枪墓》里杀人劫掠的孙少军,《冬泳》里用墙砖猛砸刘晓东的“我”,这些人原先性格和善甚至懦弱,但身上的人性逐渐被生活的动荡所剥蚀,最终退还到原始的“野兽”之列。
个体发生转变,个体间的关系也发生转变。在国企改制前,工厂员工根据工种分派到相应的宿舍,员工们上班时是同事,下班后是邻居,彼此非常熟悉,犹如一个大家庭,呈现出的关系特征是“合”。但随着改制到来,下岗后的员工与工厂之间的联结断开;厂区宿舍的拆迁,意味着邻里关系的结束,此时呈现出的关系特征是“裂”。工人们外在的社会关系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内部家庭关系也因下岗潮发生转变。
而《冬泳》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困境下个体间关系的转变做出了思考。在作品中,个体间的关系通常是破碎的,最突出的是婚姻伦理关系的消解,自己或父母离异是多数人的常态,如《盘锦豹子》里的孙旭庭、《肃杀》里的肖树斌、《冬泳》里的隋菲、《云泥》里的余正国。双亲离异的家庭结构,对后一代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盘锦豹子》里的孙旭东原来是文静聪明的诗词天才,父母离异后,他变得顽劣,最大的爱好是扯下同学裤衩。婚姻伦理关系的消解连带亲子伦理的消解,《肃杀》里甚至出现了孩子对父亲肖树斌拳打脚踢的扭曲行径。家庭内部是如此地“裂”,那社会里个体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肃杀》里的肖树斌骗取友人赖以维生的摩托车,《冬泳》里的“我”眼睁睁地看着小孩子跌入冰面,沉入水底,坐视不管。诚信、行善被欺诈、冷漠所替代。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陷入“异化之阵”:动荡变革下,似乎只有通过暴虐、欺诈、漠视等不符合社会伦理的行径,才能在困境中艰难生存。
为何会陷入“异化之阵”?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客观原因,下岗工人或因年龄偏大,或因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无法再就业。经济来源断链导致他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重压之下日渐消极,抗压失败者便选择自暴自弃,乃至异化。但作者在文本里的思考绝不止于此,而是对异化的个体的心理与精神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下岗后,精神上突如其来的恐惧、寂寥和茫然足以将人吞噬。人生活在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企改制导致的下岗,个体与社会间的某些重要联系被迅猛地撕裂,令人手足无措。“厂区里总有下岗职工出现,有来办手续的,甚至还有一觉醒来,照旧上班,到了单位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下岗,不知何去何从,围着厂区骑车绕圈。”④在国企工作的时候,职工们身处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除了干活,彼此碰上困难时还可以互相倾诉,协力解决问题。而下岗就意味从集体中被放逐,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让我想起来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戈尔丁进行了一场人性的实验,作品里,一群孩童因飞行事故坠入孤岛,逐渐从和睦相处走向互相残杀的悲剧。孩童们的童真善良因孤岛恶劣的环境和人际的利益冲突而逐步泯灭,童心最终被兽性所取代,连理性正直的拉尔夫在不自觉中也参与了对同伴的迫害。而身处在“铁西世界”里的这群职工,下岗就如同经历一场飞行事故,他们就此坠入一座城市孤岛。他们的生活环境恶劣,《枪墓》里的孙程骑车归家却发现自家房屋塌掉了一半;吴红在火车站违规拉客被送往劳动改造,却在收容所里遭到了数次侵害。没有了道德纲纪,没有了互助友爱,唯有恐怖与孤独,人们身上潜藏的恶不断被激发,最终人性异化为兽性,人异化为粗野的“盘锦豹子”,变为暴虐的“蝇王”。
随着时间流逝,下岗工人内心的落差感随之而来,落差感是使得他们陷入困境而无从突围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人村·破五》里的“我”说道:“我从前作息规律,上班下班,雷打不动;如今下岗半年,从前的好习惯全还回去,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处于坐吃山空状态,靠单位买断工龄给的钱过日子。我都想好了要是哪天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这老房子一卖,还能混个几年吃喝。”⑤这种落差不是和他者相比而产生的落差,而是纵向的,是跟过去的自己比较所产生的。改制前,在国企工厂工作是无比荣耀的事,铁饭碗,好待遇,下岗后却四处碰壁。班宇坦言:“上一代东北人的这种落差感会折射到下一代人身上,八○后创作者都会或多或少在作品中流露出这样的落差感。”⑥落差感会使人沉溺在对过往生活的怀念,而放弃尝新,放弃去寻找新的可能,“没想到,以前不甘心一辈子开吊车,现在觉得,真能开一辈子,倒也没啥不好”⑦。一旦和过往的安定相比较,当下的动荡就愈显动荡,人便会焦虑地寻求慰藉,会试图去弥补落差,经济不宽裕者便会转而追求其他东西——《枪墓》里的孙程把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堆在地上,彻夜阅读”⑧。但是,在寻求慰藉的过程中,人同样很容易走向自我麻醉的道路。《工人村》里,店铺发生冲突,负责安保的刘建国却沉迷在斗地主,“这一轮他抢到地主,正在以一敌三,情势危急,需要调动全部智商来应对,对于屋外发生的一切暂顾不上回应”⑨。刘建国不去解决现实事务,却在虚幻世界里竭力思索如何“应敌”,这看似是对困境的逃离,实际上给自己套上了又一重困境。
二
在“铁西世界”里,无常,动荡乃至绝望成了人生常态。《空中道路》里的班立新上夜班的时候忽然被电击倒,直至凌晨才被送完医院;李承杰给住户装铝合金窗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从高空摔倒,入院后身体各种毛病发作,不幸病逝。二人此前共同搭乘缆车,却碰上了十三年来的第一次缆车事故。他们的人生似乎笼罩在迷雾当中,随时被躲匿在雾里的触手绊倒。《冬泳》写出了个体的困顿、彷徨、卑微和痛苦,呈现了一个时代的悖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班宇在替失语的父辈代言,去诉说时代旧事的同时,他试图假托八九十年代这个介质去表达一种生命哲学。
班宇曾说:“乔治·希尔泰什有一句诗,他说:我乘坐的列车长如黑夜,长如记忆。那么我想,我的这些小说,或许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一节车厢,满载着哀愁而坚忍的过客,映在星光之下,轰鸣着向前驶去。”⑩照在过客身上的星光是什么?我以为是一种顽强,坚忍的精神。在时代困境下,有人身处逼仄的角落陷入绝望,走向异化和退化的道路,但也有人怀着希望负重前行。《空中道路》里班立新对下岗的友人劝说道:“树挪死,人挪活,别太担心,总有出路”;《枪墓》的结尾里,“我”历经起伏后,重新打起精神,继续前行。班立新和“我”依旧面对着种种困境,但他们内心相信:前方还有路。
《冬泳》的文本语言鲜活,班宇很好地将方言融入文学叙事中去,并且巧妙地借助对话来阐释人物的心境,但他的叙事语言里也有令人感到不协调的地方。叙事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主人公偶尔会变了个样,忽然讲出一段极具文学性,甚至是哲理性的话语,而这段话语用的也不是他日常惯用的方言,而是汉语,如《冬泳》里的“我”再浮出水面后的那段内心感慨:“我一路走回去,没有看见树,灰烬、火光与星系,岸上除我之外,再无他人,风将一切吹散,甚至在那些燃烧过的地面上,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不过这也不要紧,我想,像是一场午后的散步,我往前走一走,再走一走,只要我们都在岸边,总会再次遇见。”我们能从这段话中读出淡淡的希望。显然,这段富有思辨性的话语与说话者的身份(没念过多少书的工厂工人)是不相符的,那为何作者要做这样的处理?
或许,这构成了一种复调。代表现实生活的、粗俗幽默的方言与有着浓厚文学性的、内嵌思辨和悲壮的汉语表达构成复调,后者既属于文本叙事主人公也属于作者自身。对叙事主人公而言,那些具有思辨性的话语具有自审、忏悔和升华的功能,主人公从现实困境中找寻到了一种宁静,一种生的乐观与希望,彷徨挣扎的情绪得以淡化。对作者而言,这是他的内心表达,他所认可的生命哲学的表露:在绝望的困境里,依然要活得顽强,对未来要有希望。正如《梯形夕阳》里“我”所说的话: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恩慈。复调的构成使者和叙事主人公在某些瞬间融为一体,作者得以假托言志,也让以困顿、黯淡、无常为主调的文本多了星光。《冬泳》里的所蕴含的生命哲学不禁让人想起鲁迅,想起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想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冬泳》在书写东北的同时超越东北,这种超越性源于作者的历史意识和生命意识。这部作品的品质没有局限在铁西地域这个空间维度,没有局限在过去这个时间维度,它所探讨的命题具有普遍意义,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建构联系。文学史上从不缺乏对困境的书写,“困境”之所以成为一个被长久讨论的对象,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某种生命状态,它不可回避。人会有登临高峰的时候,也会有徘徊低谷的时候,是螺旋发展的而非直线发展的。在疫情反复的当下,人们会有恐惧,会感受到动荡和无常,这些情绪与当年亲历下岗潮的职工们是相通的。班宇说:“我们此刻和东北当时的精神位置上是相同的,在一个正弦波上,所以会产生一些共振。即便今天经济情况不再一样,但精神困境也许一样,所以会有感同身受。读者和我不是寻找记忆,而是对照当下处境。”《冬泳》的未来性体现在它的警醒作用。身处困境的个体很容易因绝望而走向异化,走向堕落。当我们有一天忽然坠入困境之中,我们要秉持乐观顽强的生命哲学,绝不放弃希望。
三
《冬泳》是一条布满锈迹却又牢固的铁链,它展现了生的韧劲。而《逍遥游》是河流,班宇说:“《逍遥游》是一条大河,有狭窄的地方,也有宽阔的地方,水流过宽阔,又流到狭窄。”相较《冬泳》里七个短篇结构和主题的统一,《逍遥游》是多元的,呈现出许多新变化。它继承了《冬泳》里的宽阔宏大的命题——延续着对人生困境的讨论,同时容纳了作者的自审。班宇将思考的对象内转,他借助文学审视自我的内心情感,审视自身的文学创作,对文学的本质进行追问,作品在艺术上有先锋派的特征。于是,《逍遥游》成了一条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流域不断交叉流淌的大河。
《逍遥游》和《渠潮》继承了《冬泳》的写实风格。母亲意外离世,身患尿毒症的许玲玲、靠着“倒骑驴”维生的许福明、父亲失踪的李氏兄弟,他们都是在生活泥淖中挣扎的小人物。作者在这两个短篇里增添了不少游离于现实的玄幻性意境,使写实和虚幻集于一体,如许玲玲登临澄海楼时的所见:海天一色,云雾被吹成各种形状,像水草、骏马,也像树叶,或者帆船,幻景重重,甚至耳畔还有嘶鸣声……霞光从云中经过,此刻正照耀着我,金灿灿的,像黎明也像暮晚,让人直想落泪,直想被风带走,直想纵身一跃,游向深海,从此不再回头。此处所传达出来的对自由和逍遥的渴望,与许玲玲被疾病缠身的现实形成反讽,让人不觉萌生悲悯和叹息。
班宇曾说:“相比社会命题,我其实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包括语言和叙述技巧等等,把文学还给文学,也许收获能更多一些。”而《逍遥游》这部小说集不妨视作他探寻小说本质过程中的其中一个试验场,里面不乏他对于小说叙事的理解和新尝试。
谈小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去追溯作者为何要创作小说这个问题。小说创作发生学是个复杂的话题,因为作者的创作缘起和后续的创作姿态是多重性的,小说的内驱动力可能源自某个短暂模糊的瞬间,或是一段忽然浮现的回忆,或是某种情感冲动。像《妻妾成群》这部小说,苏童曾就它的创作缘起做过相关表述:“对旧时代的一种古怪的激情。”而对班宇而言,“最要紧的是有一个情感上的冲动”。
《夜莺湖》的叙事驱动力就是源于某种情感冲动。创作《夜莺湖》的时候,班宇处于一个彷徨的时刻,他对自己能否继续写小说这事产生很大的怀疑,而这种自我怀疑的情绪导致了《夜莺湖》的出现。在阅读这篇小说时,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在用叙事、造境、独白等方式去描摹某种微妙的情感——困惑而不知所措,小说笼罩在一种混沌的氛围,主人公“我”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夜里所梦是杂乱的,思绪在过去和现在徘徊。面对和苏丽的爱情,“我”始终处于凝滞、延宕和犹豫,在等候着唤醒自己的“击鼓之音”。班宇不排斥将个人经验嵌入到虚构叙事中,在《夜莺湖》里,他把个人情感磨得细碎,把它们渗透在小说叙事当中,从而完成了一次对内心情感的自审和抒发。
仅有内驱动力,小说显然是无法生成的,小说的生成还需要技法层面的东西,需要借助各种叙事和语言技巧去构建文本,去呈现某种文学审美形态。21世纪,读者的阅读模式,接纳知识信息的方式日新月异,这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小说的叙述节奏和语言气息。读者追求新鲜感,寻求精神刺激的体验,这对传统严肃文学的叙事产生了冲击。作者如何处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成为21世纪的写作的一个焦点,班宇说:“作者和读者在某个程度上都是在共同阅读的,对我来说,我就需要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比如我在我的小说里,我就想跟你面对面说话。”这种对话意识促成了新的叙事形式的出现。
在《冬泳》里,班宇就曾对小说叙事的方式进行过不同尝试,如打乱线性时间进行无序叙事(如《空中道路》),或者进行嵌套式写作,故事里套故事(如《枪墓》)。而在《逍遥游》里,叙事语言就更为大胆,有意地通过叙事与读者对话,布下暗线甚至是陷阱,典型的代表是《山脉》。《山脉》是一种杂语体写作,作者打破文体的边界,将文学评论、讣告、日记、小说手稿和访谈五种文体并置在一个统一文本,文言和现代白话穿插其中,诗性表达和理性陈述混杂,无疑是一场叙述语言盛宴。读者需要对文体各异的五章内容进行解读,并为之整合,去组装一个消失了的小说。然而小说的存在与否只是作者给读者留下的最为表象的谜。当读者仔细比对每章内容,会发现它们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与悖论,每个小文本的真实性成谜。读者如果不辨真假地根据这些小文本去进行的演绎推理,得出的结果显然是不牢靠的,这也迫使读者去研究小文本的真实性,由此,读者进入了作者布下的圈套,不知不觉中走进一个难以寻觅真相的叙事迷宫。《山脉》这样具有开放性的文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格非、马原的先锋写作。
《山脉》既是叙事试验,也是一个用于探寻文学本质的装置。21世纪是信息数据时代,作家日记,访谈,创作谈,批评家评论等材料随手可得,当代读者可以借助信息技术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一部小说。但信息的便利也引发了舍本逐末的阅读怪相:在试图了解某部作品时,部分读者首先接触的不是作品文本本身,而是文本的衍生物,如创作谈和文学评论;而在通读完这些衍生品后,部分读者自以为理解了文本,不愿再去翻阅作品本身。于是,一种阅读悖论便随之产生:理解作品文本无需阅读作品文本本身。这种衍生式阅读消解了作品本体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在追求高效的当代社会,这样的阅读方式竟有趋于流行的倾向,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山脉》犹如一个警报器,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会发现仅凭借文本衍生材料,也许能描绘出些许文本的轮廓,但无法重新组合出那篇消失了的小说——作者以此向读者做出提醒:作品真正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都在作品文本本身。
班宇有读者意识,也有自审意识。他向外界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同时审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喜欢在小说中虚构一个作家的形象,如《双河》《蚁人》《山脉》等。这个虚构的形象可以视作为一种镜像,是作者进行自我观照的投射。班宇通过讲述虚构的作家的创作故事对文学创作进行反思,如《双河》里对于文学作品中现实原型与虚构形象关系的讨论:“我竟然想念刘菲,当然,并不是小说里的虚构角色,而是我的那位朋友,不可否认的是,二者的形象在某一时刻是重合的,交错之后,又逐渐分离,互为映像。”反观班宇和他笔下的作家形象,二者不正有着这样互为映像的联系吗?他在《山脉》里借虚构的评论家进行自我调侃:“工人村……这是班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意象,正因这些语汇,我们曾将他定义为肮脏现实主义的模仿者……或者作者是在双线叙事(毕竟他曾十分热衷于……这种结构)”;“子集和真子集的吞噬和僭越,实则是矛盾体的怪异中和”。这些论述显然是对自我创作的解剖,意象组合,双线叙事,矛盾叙事是班宇惯用的技巧,“肮脏现实主义”是部分评论家给他的定位。而这些却又是他渴望摆脱的,“这种技巧和笔法,我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想要做更难的事”。
这种文学自审的意识,驱动着班宇不断求新。他既有对叙事方式的新尝试,如运用精神分析写成的《蚁人》,也有对惯用技巧的重新打造。《枪墓》和《双河》都运用了嵌套式叙事,但后者的叙事比前者更为复杂,更为深刻。如果说《枪墓》是故事套故事,那《双河》是连环故事套故事,人物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文本的每处叙事都是复合的、双面的,真假难辨,这使文本指向一个深刻的主题:生活的真相往往难以捉摸。
“我现在不断回溯我为什么需要写小说,本来是因为我想要一个自由,这个不是创作身份上的自由,而是我想在故事里面体验出来的自由。而我反而这条路上如果越写越窄的话,我越来越不自由。”班宇有着自己的写作理想,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能够屏蔽外界的种种诱惑,而将注意力聚焦在文学本身,时刻审视自我的文学初心,难能可贵。当然,他的小说也有不足,如不同人物的个性不够突出,阅读小说集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人物有同质化的倾向;部分情节和意境的插入略显生硬刻意,不够浑融。但以乐观内省为内核的生命哲学,印刻在了《冬泳》这条布满锈迹而又牢固的铁链上,寻求文学自审和文学自由的鱼儿也在《逍遥游》这条大河里奔泳,这样的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新鲜的、异质的,值得重视。
注释:
①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4页。
②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5页。
③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4页。
④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40页。
⑤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32页。
⑥丁扬:《班宇:父辈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笔下》,《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
⑦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3页。
⑧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91页。
⑨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91~192页。
⑩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201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