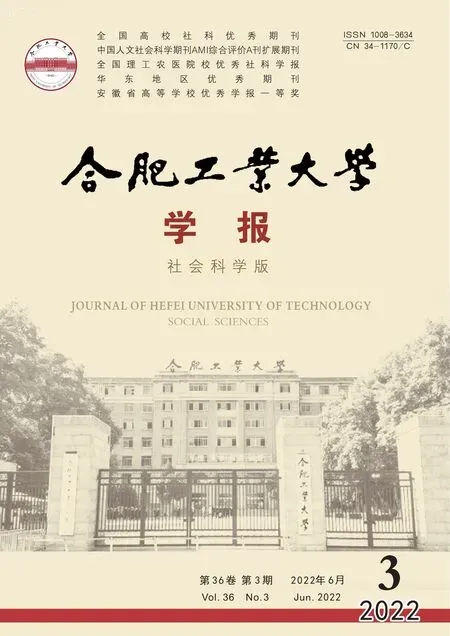“终当为情死”
——论魏晋深情中的时间与死亡意识
2022-11-24刘笑非
张 运, 刘笑非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儒家思想主流裹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对情性关系的看法几乎使魏晋士人的深情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宗白华说:“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1]156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也将“必有深情”作为魏晋风流的标志之一[2],并且对这种极具时代风格的情感评价颇高。在魏晋士人那里,逐渐觉醒的强烈个人意识并没有在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反而为这种环境所激发而淳化为对自然、生命的无限深情。这是一种指向存在问题的生命情态,这一生命情态从具体的个体生命、自然万物乃至超越的宇宙、人生中获得其哲学内涵,在士人们看似怪诞、离经叛道的言行中获得其外在形式。就其哲学内涵而言,时间意识与死亡意识构成了魏晋深情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两个来源。学界以往对魏晋深情问题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这些关键的方面,将“深情”与时间和死亡等概念并提来阐释相关问题,但也往往止步于“天地情怀”“宇宙人生”这样笼统的描述或总结,因而对“深情”本身的含义语焉不详。实际上,无论是时间意识还是死亡意识,二者作为纯粹的存在意识都还只是构成魏晋深情的可能因素,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才能真正触及这种独特的情感之本质。
一、“性情”“无情”与“深情”
“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虽然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概念,但是由于情感本身天然的切身性,“情”的问题在任何时代又都是哲学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站在何种立场上理解情感,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情感,哲学作为一种理论都需要给出自己的回答以便完善自身。缺失“情”这一维度的哲学是残缺的。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深情”既不同于先秦两汉时代儒家群体性思维中的“性情”,也不同于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中所理想的“无情”,更不同于近代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含义下的个人“感情”。魏晋“深情”是一种“本体的感受”,正如李泽厚所言,“它是在个体情感的感性中来探询、领会、把握和达到那‘无形’、‘无名’、‘无味’、‘无声无臭’的本体。这是一种具体的、充满了人世情感的感受。”[3]348-349
许慎的《说文解字》将“情”释为“人之阴气有欲者”,这显然是受到了儒家正统哲学的影响。“情”这一概念在儒家哲学中得到具体的论述应该说是从荀子开始的。在荀子之前,孔子虽然早已注意到情感的重要作用,也强调内含在“仁”“礼”等道德理想、行为中的人的“真情”,疾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以及“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反对乡愿小人式的虚假,但孔子毕竟没有正面说到情的问题,而更多地是通过突出情感中“真”的重要性来为其整个学说纠偏。实际上,“情”本来就有“真”和“实”的意思。有研究者指出,“‘情’之本义为‘实’, 而由‘实’之义到作为情感的涵义, 是经过一定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各种用法的‘情’,都不离实、真之义,实、真可以说是‘情’字的本质涵义。”[4]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解释:“情犹素也,实也。”这里孟子是指人的天然质性,“情”就是“实情”的意思[5]。到了荀子这里,“情”才在与“性”相对的意义下获得了明确的含义,而这一与“性”相对举的解释模式直接影响了后代儒家学者对情感的基本看法。荀子明确地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乐谓之情。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正名》)这里荀子不仅对“情”的来源、形式作了解释,而且对“情”与“性”“欲”等概念的关系作了清楚的说明。将“情”向上定义为“性之质”,向下理解为“求所欲”,这就使得“情”在儒家哲学中始终处于既不被更高的“性”所接纳,又无法“从其所欲”而滑向更低的“欲”的尴尬境地。否定“求所欲”的情而追求和肯定作为“性之质”的情,同时又没有给出“情”以某种方式通向为“性”的上升之路,这样的“情”当然不会被正统儒家君子人格所接纳。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正是从情、性的分别和情、欲的关联两个方面强化了荀子对情的看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里董仲舒要强调的不是“情性同出一体”,而是“情性同出一体而相对”,因为在他看来,“‘性’为阳、为仁、为尊;‘情’为阴、为贪、为卑,由于‘情’本身乃是恶、贪等负价值,而‘性’则是善、仁等正价值,这样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就要求以‘性’来抑制‘情’”[6]。汉代儒家正统哲学乃至其后的主流儒家哲学对情、性、欲三者的看法基本上不离在董仲舒这里已经成型的“性善情恶”论。儒家情性关系中的“情”始终是在价值上负面因而在实践上不被接纳的。
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的哲学,在如何对待情的问题上则采取一种“无情”的态度。《徳充符》中有一段庄子与惠子关于“情”的对话很有代表性: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
庄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
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
这里庄子说的“无情”看似与儒家否定情感的做法一样都不承认情感的正当地位,但实际上二者却根本不同。否定情感是对情感采取某种价值评判的结果,其评判标准在儒家就是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庄子的“无情”却是他所理想和期望人能所能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即一种“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的生命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庄子所说的“情”可以被理解为人的“意志”“欲望”。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意志或欲望并不带有在儒家“性情欲”三者关系中被理解的“欲”所具有的价值上负面的含义,而只表示与道家一贯强调的“自然”相对的一种存在状态(其表现形式就是“好”“恶”这样的意志行为)。“无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意思是“放下意志追求”,不去刻意要求什么,它与“否定情感”的差别的关键就在于,“否定情”仍然是一种意志行为,是一种“求否定的意志”;“无情”却是放下意志追求而“任自然”。按照这种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无情”在本质上强调的就是庄子那里的“自然”,即“顺其自然”[7]。这一点恰恰是构成魏晋“深情”的一个重要维度。
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157到了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下异化了的儒家名教早已无法带领魏晋士人走向心灵的安顿,个人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对情感的态度发生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巨大翻转。如果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这场由当时的名士们所发起的“深情”运动的口号,那么王弼的“圣人有情论”就是这场运动重要的理论支撑,而庄子哲学中的“无情”论则为这一“深情”提供了超越的维度,使得其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上根本不同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那种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性解放意义下的个人“感情”(个体情感欲求),更不是“那种‘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洫’式的负气,而是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做到的以死亡来抗衡荒谬的世界。……它既不神秘,也非狂热,而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态度。”[3]338-339对魏晋士人来说,无论是造化自然还是自己内心的深情,都共同系于某种更加本质的东西,即对存在问题的强烈意识。正是这种本质的东西使得自身之外的自然和自身之内的深情在具体问题上各有侧重的同时又有着共同的追求。总体来看,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在魏晋士人那里呈现为对时间和死亡问题的探询与思索,而其结果就是他们对自然和个体生命的一往情深。
二、时间意识与深情
时间意识的觉醒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很早就开始了[8]。在个人意识真正觉醒之前,人们就已经在自然和人生的变化流转中对时间有了深切的感受。这些体验和感受在诗歌艺术中得到了细腻而真挚的描写,但在中国哲学中却一直未能得到重视并加以理论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流的儒家哲学重伦理而轻形而上的玄思所致,另一方面则由于时间本身具有很强的切身性,因此比起理论上抽象的总结,诗歌中生动的描绘显然更能让人领会到时间为何物(即使不能清楚明确地给时间下定义)。《诗经》的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用短短十六个字就将在时间流变中的自然与人生情状写得淋漓尽致,抚今追昔,让人感慨万千;《古诗十九首》中也有“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的深情慨叹;江淹的《别赋》同样以“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这样的时序之景渲染离别时的悲情。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其中所缘之情就包括对时间的深情,而这种深情又是由自然中的四时之景兴发起来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些对自然中时间现象的书写都成为了魏晋士人深情的底色。自然塑造着时间性,根本上说,时间感乃是事物的变化引起的,自然正是以其四时之景的变化更迭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作为“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此在(Dasein),人也是在时间的洪流中被裹挟而行的一员。
一般认为,自然独立的审美价值是在魏晋时期才被真正发现的。《诗经》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多是作比兴之用,是在文学修辞意义上使用自然;而儒家思想自孔子开始便将自然纳入“比德”的框架中来理解,以此实现道德对自然的规训。只有到了魏晋时期,在士人们活泼而自由的心灵的观照下,自然才开始作为它本身而存在,因此也就从文学和道德的附属地位中脱离出来而被独立地欣赏,这就是“自然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含义。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把魏晋时期士人眼中的自然与之前比兴、比德意义下的自然区别开来了,并且也由此突出了前者独特的审美价值,但更深入地看,这种说法还是太过笼统,以至于竟将早期诗歌及部分文学理论中对自然的切身感受忽略了(或者说其思考的逻辑重心并不在于“自然-时间”)。诚然,《诗经》中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跳出比兴用法的“自然-时间”描写并不多见,多数诗篇中的自然意象仍然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样典型的“比兴自然”;汉代词赋中也多有以华丽的自然景物描写来铺陈叙事的矫揉浮夸之作。但是这些客观存在的主流现象并不意味着处于那些时代的人没有对自然独立审美价值的发掘。与其说他们相比于魏晋士人还没有独立地欣赏自然,不如说他们是在用一种不同于魏晋士人的方式来欣赏自然。说二者都能够欣赏自然,乃是因为他们都在“自然-时间”的模式下进行欣赏;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独立欣赏自然,乃是因为魏晋以前人们主要在时间的变易中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而魏晋士人则在时间的当下(现在)欣赏自然。
宗白华说:“这(魏晋士人)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于……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1]163“现量”是王夫之从印度因明学中引入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和“显现真实”(“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9]。魏晋人在面对自然时无疑表现出一种看重当下的、追求“现量”的审美态度,可以说这三层含义在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深情欣赏中都有极好的体现:
顾长康从会嵇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晋人对自然景物如此细腻的感受和细致入微的描写得益于一双“当下”之眼。对自然的观看主要不再是通过景物的变化传达出不可抗拒的时间流变的方式,而是通过这“不必在远”的眼下诸景、这就在自己面前的“虚灵化、情致化”了的山水来进行。甚至当老病俱至不能亲自登山临水时,也要以“卧游”的方式在画中体验自己在山水中“当下在场”的感觉。《宋书》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10]正是通过对“自然-时间”中“当下”维度的发掘,魏晋士人在一种崭新的自然审美中创造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自然深情。
南北朝后期的锺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11]将人的情感与四时景物的关系用“摇荡”一词形容出来,可谓深得其中三昧。其实,无论是魏晋之前以时节变易为主的自然审美,还是魏晋士人这里以当下现量为主的自然审美,二者都是人在自然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最自由、最真实的存在状态。这种自由而真实的状态在工具化、价值化了的自然理解中显然是难寻踪迹的。无论伤春还是悲秋,无论仰视还是俯瞰,在“自然-时间”的涤荡下,人的情感方才洗去铅华而愈显真实和深刻,所谓深情正是人之内在“性情”在自然中“摇荡”的结果。
三、死亡意识与深情
“自然塑造了时间性,而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时间意识的觉醒,并进而表现为对于死亡的敏感与自觉。”[8]死亡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逃不开的一个话题,而对死亡的态度又可以分为面对他人的死亡和面临自己的死亡时的态度。在这两个方面,魏晋士人都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深情姿态,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命深情。
就面对他人的死亡而言,在儒家那里,一个人不表现出悲伤或者悲伤过度都是有问题的,合理的做法是以礼来引导、规范自己的情感,使之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因此,儒家君子人格理想下的士人对死亡的态度直接背负着道德上完善自己的任务,人们需要在面对他人死亡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对礼的实践。虽然孔子本人很清楚在礼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人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但是客观上,为礼所代表了的对生命的敬重几乎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徒有其表的形式空壳中,以至于“临死作秀”的行为在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正统哲学之后一直持续不断地出现。
另一方面,魏晋士人的思想虽然毫无疑问地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对待他人死亡的问题上,士人们却并没有采取像庄子那样超然物外、“鼓盆而歌”的态度,反倒是更像一头扎在生活里不知理论为何物的普通人。在死亡面前,他们以自己的“痴言痴行”共同描绘着一幅对个体生命无限深情的时代图景: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阮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 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列传》)
这些人可谓是真正的“情种”了。在死亡面前,他们既没有选择儒家“舍生而取义”的道德超越之路,也没有选择道家“察其始而本无生”的物化还原之路,而是选择以自己最本真的生命状态直面死亡带来的一切,即一条向着自己最真实存在的复归之路。在魏晋士人那里,无论是用仁义道德为死亡赋予价值和意义,还是用大化流行抹去死亡存在的事实,都意味着对死亡、对生命真实性的遮蔽。能“悲不自胜”、“不胜其恸”甚至“吐血数升”的,不会是非礼勿动的圣人君子,也不会是道法自然的至人神人,更不会是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的“薄于情者”,而只有在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那份深情眷恋中,这些看起来难以理解的行为才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是我们的常人难以企及的。
死亡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面对自己的生与死时的选择。《世说新语》载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音乐成为了个体生命的象征,“于今绝矣”的不仅是作为琴曲的广陵散,更是那个在背后创造了广陵散的人的生命。临刑前索琴而弹所昭示的与其说是嵇康对音乐的无限热忱,不如说是对自己这只有一次且不可复制的生命的脉脉深情。
虽然嵇康之死展现了社会政治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魏晋士人可能的选择之一,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像嵇康这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抉择终究还是少数,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魏晋士人在政治上采取的仍然是瓦全之策。《晋书》中就记载了王戎为逃避政治迫害,无奈选择“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士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及家人的性命不得不时刻谨言慎行,敢怒不敢言的郁结只能通过饮酒、作诗甚至一些怪诞行为来排遣。他们是名士,是魏晋风流的塑造者,但他们更是普通人,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下的“终有一死者”。如果说嵇康给出了魏晋士人之生命深情的最高标准,那么像王戎这样的人则守住了这种深情的最低原则,即在存在(死亡)面前保持自身的真实。魏晋深情并不意味着某种正面价值,它与“名垂青史”“重于泰山”这样的价值评价没有关系。价值化的做法恰恰违背了这种深情的本质。并不是因为“大义凛然”,嵇康之死才有此深情一说,而只是因为他知道对人来说“终有一死”是逃无可逃的存在之真相,知道“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朴素的真理,知道这是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爱之深,悲之切,对个体生命的深爱造就了嵇康在生命消亡时的深情。诚然,能用某种信念(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宗教上的)说服自己在死亡来临时勇敢面对已经很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揭去这层信念的保护,让生命的真相在死亡中直接显现出来。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一书中有言:“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平静、勇敢而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但比较抽象。它只构成某种道德理念或绝对律令,却抽去了个体面临或选择死亡所必然产生的种种思虑、情感和意绪。”[3]333在魏晋那个朝不保夕的时代,比起那些情感上很害怕死亡却以理性的仁义道德等价值观念说服自己不必害怕的人(诚然这样的人也没做错),像王戎这样选择“苟活”的士人无论如何还保留了一份人在死亡面前的真实。追求价值——无论是黄金的价值还是道德的价值——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丢失存在的自由和真实。我们被那些价值所符号化,以至于当自己在做一件事、做一个选择时,不是“我”在做,而是价值符号在代替我做。将价值和意义“凌驾”于生命真实之上意味着以存在的自由换取对存在的庇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士人以自己在死亡面前战栗着的真实书写了这个时代对个体生命的自由与深情。
四、魏晋深情与存在问题
在时间意识和死亡意识的推动下,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个体生命,魏晋士人无不投之以热切而深情的目光。时间与死亡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存在意识,自然与个体生命也绝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存在领域。时间意识所造就的自然深情与死亡意识所造就的生命深情共同统一于深情的本质:存在之真实。深情乃“存在之真”。
这里关键是对“真”的理解。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极具启发意义,因此这里有必要理解其哲学的真理概念以及这种真理概念如何与存在问题联系起来。真理在海德格尔那里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任何一种传统真理观念能容纳得下的了,他对古希腊的“真理”一词做词源学上的分析,认为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是指“无蔽”,是由一个否定前缀加上“遮蔽”这个词得到的[12]。按照这种理解,真理就不是什么主客体符不符合的问题了(“知与物的符合”),也不是有一个客观的真理等着我们作为主体的人去认识(像柏拉图主义那样),而只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显现出来。不过我们要注意,古希腊人不直接说真理是“澄明”而是用“无-蔽”这样否定性的表达来理解真理,这说明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真理自身的遮蔽本质:“无-蔽”的前提和基础乃是“遮蔽”。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真理是在阴影中的,是阴森惊人的;因此,“事物自身的存在显现”这个听起来似乎不言自明的说法实际上最难以完成,因为这触及真理的遮蔽本质,这一“存在的显现”的过程并不在人的权能之内,人无法像科学那样通过掌握自然的规律来控制和利用真理,我们说“让(一事物)存在”与其说是人对存在者的存在做了什么,不如说是人对存在者的存在什么都没做即“如其本然”(自然)。不是先有一个被遮蔽的真理,然后去蔽了就是“发现了真理”,而是说,“去蔽”——让存在者之存在涌现出来——这就是真理。真理不是一个等待发现实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去蔽的过程。
因此,与其说魏晋士人是从老庄哲学中汲取了某种超越的维度,不如说他们更看重的是道家对“自然”(如其本然)的强调,对“真实”的强调。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庄子的“无情”实际上并不是否定情感,而是否定对价值的无限推崇,否定人依据某种外在于他自身的价值观念、以意志来扭曲自己存在的真实(“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也”)。在魏晋士人那里,所谓“超越”不一定就是向着某个形而上的、高于现实的不可见实体的超越,而可能恰恰就是向着存在自身最真实状态的复归。“魏晋风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智慧兼深情”[3]345——或许不必向玄之又玄的形上之道中去探本溯源,而只需让那个被价值化、符号化了的人自身的真实存在涌现出来: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王羲之的这两句诗用来解“宁作我”三个字再合适不过。“我是我”,这就是自我的真实存在;如果“我”只有在与非我的事物的比较中(“有竞心”“争先”)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那么“我”与自身就是割裂的。当“我”被“非我”遮蔽的时候,“我”的真实也就退回到它的源始遮蔽状态中了。无论是殷浩与自己的“周旋”,还是王羲之那里的“静照”“忘求”,都是他们让自身从遮蔽状态进入澄明的方式。但问题是,所谓的“周旋”“静照”“忘求”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实现存在之澄明即复归存在之真的方式何以成为魏晋风度、魏晋深情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如果说“深情”的含义是“在存在中保持自身为真实的”,那么时间意识和死亡意识就是这样一种场域:在其中存在得以本真地展开自身。这就是说:在时间所建构的“曾在-当下”的存在场域中,在个体生命所建构的“生-死”的存在场域中,人的存在才获得其进入本真状态的可能性。所谓“周旋”“静照”和“忘求”,不是别的,正是时间与死亡意识所衍生出的存在样式。正是先行到死的死亡意识呼唤此在的“良知”,并以此让自身是本真的。因此,从根本上说,魏晋深情乃是在时间与死亡所构成的存在场域中完成的对自身存在之真实的复归。
李泽厚曾说过,“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于总与对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识,从而达到哲理的高层。这正是由于以‘无’为寂然本体的老庄哲学以及它所高扬着的思辨智慧,已活生生地渗透和转化为热烈的情绪、敏锐的感受和对生活的顽强执着的缘故。……扩而充之,不仅对死亡,而且对人事、对风景、对自然,也都可以兴发起这种探询和感受,使世事情怀变得非常美丽。”[3]347的确,在魏晋士人那里,时间、死亡、存在、真实、自然和人生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深情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