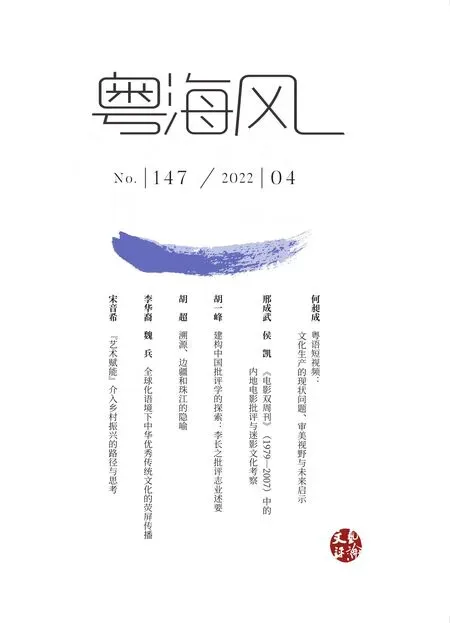未竟的牌局与永恒的人性
——以《海底捞月》为例浅析肖建国的创作特色
2022-11-24杨希
文/杨希
一、浓郁的湘南风情
故土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无法抹去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早期的生活经验对其创作个性和气质的影响更加深远,不管是自然风貌还是民俗特色,都烙印在其作品中。纵观文学史,每一个有特色的作家都有自己书写的地标,比如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山东高密,王安忆的上海……在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方言逐渐被普通话所替代,城市景观和生活习惯也趋于雷同,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就是在同质化的经验中开辟出独特的书写路径,丰富感和差异性是其重要的艺术标志。故土不仅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专属的创作资源,也给作品打上了鲜明的风格印记,故土的文化特色也由于作家的地域书写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一种相互浸润相互滋养的状态。
肖建国生长在湖南南部小城,对湘南地带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与他本身的阅历、见识、情感有着密切的关联。
地理上,湘南地处于两省交界地,毗邻广东,广西,这里是湖南的“南大门”,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到了明清时期,广东设立对外通商港口,湘南地区成为物流的必经通道,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这里的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了早期城镇化的景观。《海底捞月》的第二章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构建真实立体的小城风貌,作家从染坊写到热闹的手艺人店铺一条街,再从北门石埠头,县城的四个城门以及衙门口写到纵横交错的古老街巷、骑楼,围绕小城的是盘曲的麻地河,苍翠的城外四面山,山上的东塔岭,雷公菩萨庙……肖建国在这里用散文的笔触逐一抚过记忆之中的地理风物,描绘出一个富有肌理感的湘南小城。
由于湘南地带经商便利,这里文化交融,人民生活相对宽裕,性格奔放,形成了以坐歌堂为代表的地方风俗和以打麻将为主的生活娱乐。湘南地区的永州下灌村更是传说中麻将的起源地,在《海底捞月》中可以看到出现频次极高的麻将牌局,小说中作为关键意象的紫檀木盒子装载的象牙麻将是翠玉的父亲专门从马来西亚买回,由此可见湘南小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态。小说的标题“海底捞月”本身就是一种麻将的术语,目录名也直接取自坐歌堂的唱词与牌场黑话,小说的叙事更是一开场便在三天三夜的麻将牌局中展开,整部小说就是一幅鲜活的湘南市井生活图。
除此之外,小说的地域特色还体现在方言的运用上。普通话写作无疑有利于作品的理解和传播,但在地域描写的文本中就不可避免地被消解了一部分地方特性。方言写作则可以让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真正立起来活起来,这是因为方言的形成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社会结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紧密相关,方言汇集了地方文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和特质,是地区身份的重要标志。《海底捞月》中的湘南方言活泼,粗粝,语义丰富。比如小说中经常用来表达人物心情的形容词“松快”,不仅有快乐的意思,还包含着轻松、畅快的多层含义。名词“毛毛”“小把戏”用以指代婴儿、幼儿,极富形态特征,将较为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生动化,体现出了湘南地区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小说中大量的动词“搭”“搞”“拼”的使用可以感受到湘南地区人民的勇猛,利落。人物的名字更直接用了方言化名“细姥婢”“疤眼皮”“忠良婆”“三道弯”……这些人物名都极具个性特色,也暗含人物的部分生理和性格特征。可见方言体现出不同地区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生活本身。而牌桌上的交流、嬉闹,牌场黑话的使用,让麻将桌成为集中表现方言特色和人物个性的空间。纵观整部小说作品,方言的运用使其人物更加原生态,更加贴近土地,贴近真实生活。并且,方言的表达特性直接决定了作品整体的语言风格,《海底捞月》依托湘南方言所呈现出的语言风格就倾向于明快、率真、夸张。
小说通过描写时代激变之下的湘南地区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地域文化的强大惯性和内在力量,麻将作为其中的具体标志,也维系着湘南地区的文化认同。肖建国的创作以此践行着他的寻根理念,打造属于他的创作地标。
正如肖建国自己所言:“要当个作家,就应该有个‘根’。讲通俗点,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根据地。不管生活底子是厚是薄,生活面是宽是窄,但总应该有一块这样的根据地,并且经常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没有这个‘根’,就会是飘的。我的根在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1]
肖建国有意识地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书写湘南的自然风光、乡土人情,为其作品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标签,我们能从其中感受到作家对故土深沉的依恋和注视,这是肖建国小说的一种独特魅力所在。
二、起伏跌宕的情节
肖建国的小说作品是紧贴时代发展与社会现实的。《海底捞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写到土改运动、从““文化大革命””写到改革开放,人物历经了这些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70年的时间跨度使作品的情节非常丰富,麻将作为核心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已绝非一个普通的物件,因为“艺术的生命不是‘物’,而是内蕴着情意的象(意象世界)”[2]。它与人物的命运产生种种关联,构成了主要的情节线索。小说初始,通过唱坐歌堂的细姥婢在李家小姐翠玉出嫁前的一场三天三夜的麻将局中“担土”,将主要人物关联起来。家境富裕的翠玉姑娘是小城出名的“麻将鬼”,出嫁前,她一心想要自摸“海底捞月”,在最有希望之时,翠玉拈白板的手突然被流弹打中,鲜血直流,这场未竟的牌局成了翠玉一生的转折点,也标志着这个偏安一隅的湘南小城的突然解放,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时代也进入新的历程。如此难忘的首次牌局的经历,使麻将从此成了细姥婢人生中的重要内容,成功转化为作品叙事的关键要素。
出现次数不多但贯穿整部小说的象牙麻将,是触发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标志,它预示着人物将面临抉择,不同的抉择推动不一样的情节走向。命途骤变的翠玉姑娘将最珍爱的象牙麻将托付给年轻的细姥婢保管,是第一次抉择。从此,细姥婢的命运便和麻将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细姥婢的丈夫水旺忍受不了金钱的诱惑,将象牙麻将当做古董卖掉。细姥婢面临第二次抉择。在女儿三姥婢面对婚恋选择之时,象牙麻将再次出现,一场牌局让细姥婢看清未来女婿的人品和性格,预示着三姥婢一生幸福的开始。最后,细姥婢在自己的家庭棋牌室,终于放心拿出象牙麻将与姐妹们分享,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着早逝的翠玉。象牙麻将成为理解细姥婢命运的关键线索,也是整部小说中几次叙事高潮的标志。
除了象牙麻将,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普通牌局对情节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第四章“手气顺时搏自摸”是细姥婢前半生中屈指可数的幸福岁月。细姥婢与水旺破除万难成婚后,搬进了翠玉家的大宅,认识了土保主任的妻子含田婆。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土改,小城的生活回归平静,细佬婢终于能再打起麻将,但在麻将桌上的一次胎动让细姥婢经历了痛苦的难产,很快,这种平静安稳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第五章中,饥荒来临,水旺因事入狱,细姥婢开始经历人生低谷,就在众人担心细姥婢的精神状态时,恰是一场麻将牌让人看到她面对苦难的勇气,为后来细姥婢做苦力、捡拾腐肉、艰难度日做铺垫。第七章中,水旺出狱,心情愉悦的细姥婢邀约翠玉组起了麻将局,也正是在这场牌局中,翠玉第一次将自己对麻将的心得告诉细姥婢,使细姥婢领悟到牌场看人的至高境界,成为细姥婢以牌局测试准女婿的前提。也成为最后,年迈的细姥婢看淡输赢、看清人生时运的基础。
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轻松愉悦的牌局交替出现,使小说在叙事上显得张弛有度,增强了节奏感。尤其是从开头的紧张和高潮,到最终章的舒缓和开悟,整部作品由牌局始也由牌局终,形成了一个环状结构,仿若一场大型的命运的牌局。
纵观肖建国的写作,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命运上的激变与社会和时代的变化紧密相连,这种写法深刻揭示出小人物在时间洪流中被迫裹挟而行的生活本质,要掌握自身的命,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也就更突显出小人物身上的坚韧品质。
三、人物塑造
肖建国的小说总是聚焦于底层平民,所刻画的女性平民更能满足读者对于强韧、良善的人性美的期待和追求。《海底捞月》中的重点人物以女性居多,从细姥婢到翠玉、忠良婆、含田婆、三道弯等,这些湘南地区的女性生动而美好。相对而言,男性人物的缺陷更加明显,对于个体欲望的处理更缺乏理性,朴素的民间伦理观念在女性人物身上得到更好的体现。当然,小说也能直面她们的局限,比如疤眼皮,活泼热情之余有着自私苛刻的缺点。忠良婆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但思想传统,冥顽固执。最能集中体现作者对人性期待的是主人公细姥婢。细姥婢经历了牌局上的时输时赢,也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美好与艰辛,她的性格特征是:直爽真挚、勇敢善良。这是个有力度的人物,她的韧性和坚强撑起整个家庭在动荡时代中的稳固,她就像不断生长的藤蔓,哪怕历经秋风和苦寒依然保有茁壮的生命力,甚至更加通透和宽厚,终至成长为一棵庇佑家人的葱郁大树。除了细姥婢,小说中所有正面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道德持守:义、理、情。细姥婢的性格是在命运的历练中成长而成,性格的进化均在牌局中得到彰显。正如前人对参加打麻将的牌手曾有要求: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勿骄,失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乎声,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正代表性格的修炼过程和终极目标。
细姥婢身上最突出的,是她对“义”的坚守。她一生信守与翠玉的承诺——保护象牙麻将。虽然她并不真正了解翠玉,更谈不上熟识,但她不以外界评价和社会认同标准的变化为基准去评判翠玉,始终平等而视。当然,这种尊重并非毫无出处,正是通过她与翠玉相识的那一场三天三夜的牌局,细姥婢认定翠玉是纯粹的。作为一个大小姐,翠玉既不关心家族事业,也不关注个人婚姻,终日耽于牌场,她对麻将的痴迷除了是对娱乐的沉溺,也有将其视为理想和爱好的虔诚。细姥婢践行对翠玉的承诺,体现出一种任凭世事变迁都坚定不移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成为细姥婢面对抉择时的行事原则。丈夫水旺因非法炸鱼获刑5年,细佬婢挺身而出,打各种零工,独自抚养4个孩子,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但她毫无怨言,更时时处处维护着水旺。水旺在广州嫖娼入狱后,细姥婢放弃了自己心爱的麻将馆,带着仅有的5000元现金赴广州保释丈夫。义气让细姥婢身上不仅有传统女性充满坚韧和温情的部分,也有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强。“义”也是作品中湘南地区人民集体的价值认同,正面人物身上都有义气之举,细姥婢难产时,含田婆让丈夫欧土保连夜带领几个年轻人步行将细姥婢抬去一百多公里外的大医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单纯的付出靠的正是“义”的支撑。小说中的人物在赞叹对方之时常会说“这个人,好讲义气”[3],可见义气是湘南地区众人称道的精神品质,对“义”的赞美也是对传统精神力量的呼唤和回归。
如果说“义”是细姥婢性格中对传统价值观的持守,那么理性精神则是细姥婢身上的现代部分。细姥婢在面对人生际遇中的困惑和选择时,不是一味的妥协忍让,紧随潮流,而是据理力争,尝试主宰自己的命运,更可以在人云亦云的状况下做到不参与,不起哄。比如在小说第一篇章的解放情节中,众人将翠玉视为万恶的阶级敌人时,细姥婢有自己的判断,秉持自己的认知,不为外界所撼动,她会接受翠玉的象牙麻将就证明她并不认同对翠玉的审判。成年后的细姥婢坚决反抗代表传统思想的母亲阻挠自己的自由恋爱。中年的细姥婢遭遇““文化大革命””的乱象,面对被夺权的热情冲昏头脑的丈夫和女儿,以自己理性和温柔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感化与劝诫,更在游街途中救下了曾有一面之缘的段碧池。纵然““文化大革命””对底层平民有巨大的权力诱惑,细姥婢却绝不参与其中。她身上的理性精神来自父亲秋聋子,秋聋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劝诫水旺时所说的话,是为理性精神的一次申辩。肖建国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直呈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显然,他看到了这场浩劫的本质,看到了对于人性的扭曲,虽然依靠人物对话来陈述作家所思所想的手法不算高明,甚至稍显朴拙,但这种真诚的理性精神却是可贵的。作为一个平民,秋聋子有着深沉的智慧,他尊重女儿的个人选择,关键时刻他能透过社会现象看到其本质规律,对人对事的看法不被个人情绪和偏见所左右。小说将现代理性融入作品,使人物更具深度。
在经历了种种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人生遭际之后,细姥婢不断成长,她的世界观也如她对牌局的看法一样,达到了另一番境界——情的境界。对至情至真的参悟使细姥婢成为一个成熟豁达,通透达观的人。小说的后四个章节,湘南小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迎来发展机遇,商品经济迅速崛起,人们开始走出湘南,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要面临更多人性的摇摆。金钱和机遇,动摇了这片土地上最为朴素的价值观——“义”。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光飞和光雄两兄弟身上,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两兄弟不仁不义,不择手段,侵占和剥夺他人的财物,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脱离了故乡水土,常年在外的水旺,也逐渐遗落了本分与义气,暴露出性格中贪婪的一面,不仅偷偷拿了细姥婢的象牙麻将转手出卖,还深陷嫖娼风波,情感与灵魂都在迅速堕落。作家借此写出了人性的弱点,这些都属于小市民身上普遍存在的缺陷,也许离开了乡土文化和情感的滋养,人性中的弱点便会肆意滋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细姥婢,在经历时代动荡,生离死别之后,细姥婢变得温柔敦厚,她已明白生命最为重要的乃是当下的真情。黑格尔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4]在小说最后的牌局很显然象征着她的蜕变,这已不再只是一种娱乐手段了,甚至不再是她的爱好,而已经成为她人生哲学和生活意义的展示场。
细姥婢成为麻将高手,牌技与手气俱佳,但她放弃了靠着麻将馆致富的念头,也放下了牌桌上对赢的渴望,宁愿一次次输给自己的姐妹,只为将这牌局一直打下去,将眼前这向好的生活一直过下去。与真挚的情感相比,财富或者输赢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不能带来慰藉的,太在乎一时半刻的功成名就,就像终于自摸海底捞月的一天,那不是开始,而是结束。幸福的真谛无外乎就是有情有义地活着。
以《海底捞月》为代表的小说可以看到肖建国的创作路径是现实主义的,透过人物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表象对湘南地区市民的生存哲学、人生信仰进行追问、思考。肖建国对故土的深情,决定了其写作是真诚的,动情的。
湘南人对生活的期待和认知到底是怎样的,作家没有直接陈述,而是借用麻将这一隐喻叙事来达到对其命运和精神的认知与理解。苏珊·朗格认为隐喻其实说的是一件事物而暗指的又是另一件事物,并希望别人也从这种表达领悟到是指另一件事物的原理。[5]麻将在小说叙事中指代了一种轻松的、愉悦的生活方式,麻将桌提供了一个释放内心压力和纾解欲望的空间,在这个自由轻松的小世界,现实困境,矛盾纠葛,荒诞乱象都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只是毫无功利目的的“松快”。麻将是细姥婢和疤眼皮们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的精神寄托,以对抗平庸、枯燥、麻木。
另一方面,麻将也是时代命运的隐喻。细姥婢放弃对结果的关注,就是理解了命运和时代。在肖建国的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平民阶层均陷入一种困境中——作为大时代中的渺小个体,要走出普遍性的困境是困难重重的,人生正像牌局,输赢是难以预料的,不可掌控的。本着何种心态,持有什么样的信念参与其中才是个体生命应该去关注的,在无法依靠意志而左右的运气面前,享受过程,不论结果。小说并无叩问和责难,也不在深度上过多地挖掘,只是用本真的善意去启发和触动人的灵魂,去寻找一种由内而外自省的力量。深刻让位于温情,批判示弱于悲悯,这是肖建国的创作愈加成熟的标志。
注释:
[1]肖建国:《左撇子球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3]肖建国:《海底捞月》,深圳:海天出版社,2021年版。
[4][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5][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